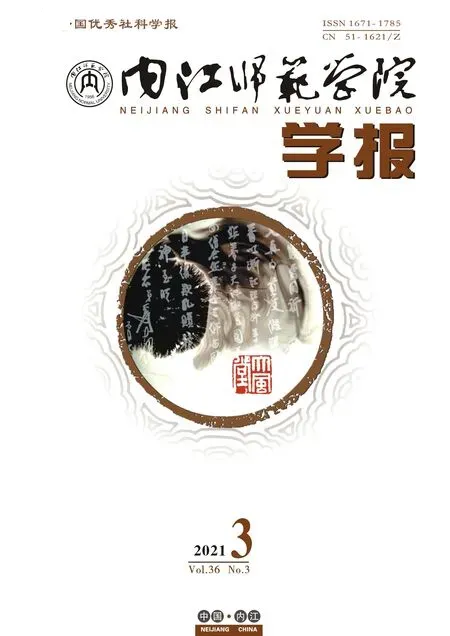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大”审美观解读
袁 丽 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0)
张大千说:“画有三美:大、亮、曲。”[1]32“三美”观中,“大”审美观居于首位,这不仅昭示“大”审美观在张大千绘画创作之审美观中的地位和意义,也反映“大”审美观的解读对理解张大千绘画创作的意义。文章拟从三个方面解读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大”审美观:立意之“大寄托”、形式之“大结构”及境界之集大成。文章注意以下方法的运用:首先是立意、形式和境界三方面虽各有其独立价值,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其次是三个方面的提出和形成,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和内在的用意。再次是三个方面的提出和形成,并非凭空而产生,在此之前已有此种倾向,在此之后必有流变。最后,“大”审美观解读的依据主要来自“大”的审美理论和审美创作实践。
“大”审美观解读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则是在已完成的《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曲”审美观解读》的基础上,通过“大”审美观的解读,增加“三美”观的认识和理解,丰富张大千研究成果;二则为有志于当代中国画创作研究的学者和艺术家提供启迪。
一、绘画创作立意之“大寄托”
张大千关于“大寄托”的观点:“立意,人物、故事、山水、花卉,虽小景要有大寄托。”[2]125又“所谓‘大’,不光指画的尺寸和篇幅大,而且角度要大,要开阔。就是一张小画,也要能小中见大,虽小景而有大气势、大寄托”[1]32。这两段文字透露“大寄托”说的以下特征:“大寄托”是针对绘画创作之“立意”而提出;各类题材都讲究有“大寄托”,即使是“小景”也不例外;“大寄托”要能小中见大。怎么全面理解张大千的“大寄托”说?“大寄托”说究竟包含哪些涵义?
先看诗之“寄托”论。钱钟书论诗之“言外之意”时,提出“含蓄”与“寄托”之辨,说:“‘言外之意’,说诗之常,然有含蓄与寄托之辩解。……前者顺诗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须求之文外。含蓄比于形与神,寄托则类形与影。”[3]钱钟书此段明确指出,诗之“含蓄”类于形与神的关系,即诗内、诗外为一体;诗之“寄托”则类于形与影的关系,诗内、诗外为两种事物。由此可知,诗之“寄托”是言此而意彼。
画之寄托为“借物以咏志”,即借所描写之物表达创作者的志向。诗、画之寄托论都是言此而意彼,有一致的思维模式。传统画论中的寄托论一般是借自然之物以咏“君子”之风范。如北宋郭熙《林泉高致》曰:“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无凭陵愁挫之态也。”[4]131又如南宋郑思肖的《墨兰图》之题识说:“纯是君子,绝无小人。”[4]124而清代盛大士所论则揭示所咏之“志”含义上的丰富特征。他说:“作诗须有寄托,作画亦然。旅雁孤飞,喻独客之飘零无定也;闲鸥戏水,喻隐者之徜徉肆志也;松树不见根,喻君子之在野也;杂树峥嵘,喻小人之昵比也……”[4]129以上所列“寄托”论中,所咏之“志”多与创作者的身世之感相关。况周颐《惠风词话》中谓这种“身世之感”通于“性灵”,说:“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5]127此种“性灵”式寄托是传统绘画或诗词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寄托”手法。
张大千绘画创作之“寄托”论讨论了两种状态。一种为上述之“性灵”式寄托。如张大千画学提到:古人画人物时多数以渔樵耕读为题材以象征士大夫归隐后的清高生活,以梅兰竹菊为题材代表与者受者的风骨性格[2]124。张大千此句中虽指出寄托手法与“古人”的关系,但实暗示他对此创作手法的认可。事实上,“性灵”式寄托的创作手法贯穿张大千整个绘画创作生涯,尤其是在他敦煌考察之前的摹古阶段,这类例子俯拾即是,此处不详述。一种是博大深厚的“大寄托”。与“性灵”式寄托关注的身世之感相区别,“大寄托”论主要围绕复兴中国美术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此论断可获得下面三条资料的支持。
第一,敦煌考察及之前,张大千已认识到当时人物画之弊端,而起振兴的思想。张大千敦煌之行即与此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联。张大千晚年所撰《叶恭绰先生书画集序》中,说:“惟先生于予画素所激赏,因谓予曰:‘人物画一脉自吴道玄、李公麟后已成绝响,仇实父失之软媚,陈老莲失之诡谲,有清三百年,更无一人焉。力劝予弃山水花竹专精人物,振此颓风,厥后西去流沙,寝馈于敦煌、榆林两石室,近三年,临抚魏、隋、唐、宋壁画,几三百帧,皆先生启之也。”[6]62张大千与叶恭绰首次相识于1928教育部筹划全国第一美展之时,自此至1940首次赴敦煌考察,期间共十二年之久。鉴于张大千与叶恭绰的交情,此十二年间张大千一定多次受叶恭绰的关于振兴人物画思想的启示和影响,且对这一问题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思考,否则难以因此促成敦煌之行。而在《谈敦煌壁画》一文中,张大千提到的敦煌壁画将对今后画坛产生的“十点”影响,都与人物画的发展与振兴相关。这为张大千敦煌考察以及之前意欲振兴人物画思想提供了佐证。第二,1944年的中华全国首届美术节纪念大会上,张大千说:“现代中国因抗战而促进文明的成长,而促进艺术地位的增高,确是当然的结果。……我们在抗战期间,所负的艺术使命责任很大。我愿意追随同仁一致努力,来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7]这段话无疑透露出两方面的信息:以美术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观念在当时的美术界已形成共识以及张大千本人公开表达了将追随同仁一起努力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决心。这次讲话可视为张大千意欲复兴中国美术的公开宣言。第三,1948年3月28日的成都大风堂同门会成立会上。张大千说:“今日我国画之前途,应由莘莘学子各尽所长,群策群力以开拓广阔之领域,要为整个汉画之宏伟成就计,不能如前人之孜孜矻矻仅为一己之名而已也。其于艺术所树目标、范围,亦自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8]此段中,张大千将“为整个汉画之宏伟成就计”与“为一己之名而已”并举,强调前者,贬抑后者,其深意必然也包括绘画创作之立意方面的计划:张大千实已意识到“性灵”式寄托对绘画发展的局限性,而意欲超越此而向更为博大深厚之“大寄托”发展的决心。此段话是对大风堂同门弟子的勉励之言,也是他要求自身绘画创作向更高远目标迈进的宣言。此次的讲话内容较之前次,在复兴中国美术方面,无疑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目标。
以上资料清晰地勾勒出张大千由意欲振兴人物画的思想而至提出中国美术复兴思想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也是他的“大寄托”论之内涵、目标由提出而至明确的过程。“大寄托”论的形成和提出源于对抗战时期“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响应。
对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主要思想的梳理,可以获得抗战时期“文艺复兴”思潮主旨。这里仅选取与本文有关的内容,按时间先后陈述。《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指出,中国文化存在“一般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不够”的问题,并提出强化民族意识的十点方案[9]206-217。《“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指出,“文艺复兴”的意义:“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9]31《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一文总结抗战时期“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为:“近于中体西用,而又超过中体西用的一种运动。其超过之点即在我们是真发现中国文化之体了,在作彻底全盘地吸收西洋文化之中,终不忘掉自己。”[9]111《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映》一文中则提出抗战时期之“大时代”特征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他说:“这时代的确太大了,大时代之‘大’几乎不足以形容”[9]240。又说“难道知识分子不也可以立点大志么?琐屑的考据应该唾弃了,吟风弄月的闲情应该杜绝了,气魄需要再大些,深邃的哲学应该钻研,各种文化的核心应该把握,较大的学术系统应该建立……”[9]242又“大时代的学者应该大,不要安于小。”[9]243《思想教育(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一文强调,“大学”之“大”在于“眼光大,胸襟大,目标大,风度大,体魄大和智慧大”[9]244。他进一步解释,“眼光大”指看得远而非只看到个人的出路;“胸襟大”是能容得下不同的思想而不仅仅于一派一系;“目标大”指担得住大责任,即可以担当国家大事;“风度大”指雍容通达而非局促偏执[9]245。
以上所论涉及对中国文艺复兴四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文化复兴中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问题;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西文化传统融合过程中的关系处理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责任和要求。
作为时代美术精英的徐悲鸿和张大千对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均有回应。关于第一个问题,徐悲鸿认为,“世界艺术正在没落的途径上”,如果中国在艺术方面能恢复到“汉唐全盛时代的水准”,就能达到中国艺术之复兴[10]498。张大千说:“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2]115对待第一个问题上,两人将中西文化置于同等地位,强调文化复兴中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表达出对民族绘画的充分自信。关于第二个问题,徐悲鸿和张大千对传统绘画的态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唐代绘画的态度。徐悲鸿提出希望将唐代全盛时期的绘画水准作为艺术复兴的参照标准。他说:“希望中国艺术要达到如唐代的昌盛”[10]506。又“想象当年吴道子所作,应当高妙奇美至如何程度?……我们要拿他做标准。”[10]506张大千则认为:“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11]19这一观点与他提出的将影响未来中国画坛的“十点”以及他的人物画风格的形成都与唐代壁画相关的观点是相通的。其次是对人物画的观点。徐悲鸿说:“我所谓中国艺术之复兴,乃完全回到自然师法造化,采取世界共同法则,以人为主题,要以人的活动为艺术中心……”[10]504张大千说:“大结构—如穆天子传、屈子离骚、唐文皇便桥会盟、郭汾阳单骑见虏等图。”[2]126由上可知,徐悲鸿所谓的中国艺术之复兴指的是以人为主题的人物画的复兴,而张大千的“大结构”是关于历史人物画创作,两人观点都与人物画相关。最后是关于文人画的观点,徐悲鸿对文人画持一种矛盾的观点和态度。一方面,他对文人画持贬抑的态度。他说:“中国艺术没落的原因是因为偏重文人画”[10]502。又“今日文人画是言之无物和废话。”[10]498另一方面,他不仅未排斥文人画家的作品,甚至还对此赞誉有加。如他在《张大千画集》序中赞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说:“其登罗浮,早流苦瓜之汗;入莲塘,忍剜朱耷之心。”[12]317此句中徐悲鸿明显表露出对清代文人画代表石涛和朱耷的推崇。张大千主要对文人画的“苟简”形式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弥漫画坛的文人画“苟简”风气埋没了古人的精益苦心,导致画坛小巧作风之弊端的形成。[12]96关于第三个问题,徐悲鸿主张采用西方素描代替传统的“师造化”,以解决中国画造型问题。他说:“在二十年前,中国罕能有象物极精之素描家,中国绘画纸进步,乃二十年以来之事。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师造化而已。”[14]510徐悲鸿的“师造化”显然与传统画论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造化”已有区别。前者与西方造型艺术之基础素描一致,后者与张大千强调的 “物之理、情、态”造型观一致。张大千则说:“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2]116由话可知,张大千是主张中西绘画融合的,不过,他要求融合的前提是不能改变中国画的外在面貌与内在神韵。关于第四个问题,徐悲鸿希望艺术工作者:“第一要立大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等人,做出世界上第一等作品。……千万勿甘心于一种低能的摹仿一家……”[10]504张大千的所为,如拜访毕加索以及两人间的交流,积极变法以追赶世界绘画潮流,于世界各地频繁地举办画展,充分说明他志在成为世界一流画家的理想和决心。事实证明,他已实现了这一理想。
以上徐悲鸿和张大千对李长之提出的四方面问题的思考,实际为关于中国美术复兴的五个问题的观察:文人画的弊端、唐代壁画的价值、“师造化”要求、人物画的新发展以及艺术家的国际视野要求。两人对五个问题的意见除“师造化”和文人画的弊端存在较大的分歧外,其他大致一致。这五个问题实际归属于两个问题:中国画革新与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中国绘画传统与西方绘画传统的冲突。徐悲鸿和张大千对李长之提出的四方面问题的回应情况,恰说明了抗战时期“文艺复兴”思潮对当时美术界精英阶层所形成的影响这一事实。美术界精英阶层在这一影响下形成的意见,正是张大千“大寄托”说提出和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理解“大寄托”说含义之所在。
张大千“寄托”说的两种形态,即“性灵”式寄托和“大寄托”,既相似,也存在区别。相似之处在于,两者在表现原则上有相似的思维模式和思维结构,都是处理情(或意)与景(或境)的关系。区别之处是,在处理情与景的关系上,前者之情趋向身世之感,与情对应之景强调与客观事物之外部特征的联系;后者之情侧重于人类内心之“普遍意义”,与情对应之景或是与客观事物之外部特征存在联系的典型事物,或是脱离与客观事物之外部特征的联系,发展为“超乎形象之外”的抽象形式。“性灵”式寄托演变为“大寄托”,是绘画创作规律的自然发展。当然,也只有功力深厚的艺术家,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后者。
二、绘画创作形式之“大结构”
“形式”一词是西方绘画理论及绘画实践中普遍使用的概念,但此概念之含义至今未有统一界定。梳理西方重要美学家和美术史家关于形式一词的阐述,可获得对此词的基本认识。瑞士H.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一书中提出“再现形式”概念,将此归纳为五对相对的风格: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深、封闭与开放、多样性与同一性以及主题的绝对清晰与相对清晰[15]。俄国抽象绘画创始人之一瓦·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一书中说,“形式”是“一个面与另一个面之间的边线”[16]37,“点、线、面三要素”是构成艺术作品形式的基本要素[16]103。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中说,点、线、面、色彩是构成形式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之间存在必不可缺的构成关系[17]。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在《现代绘画简史》一书序言中说,色彩、线条、构图、体积等是构成艺术作品的形式要素[18]。以上讨论显示,以下特征:其一是西方关于形式的讨论在20世纪初已成为普遍现象,在中国关于形式的讨论中,个别艺术家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绘画创作中的形式,约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才形成重视形式的普遍风潮。其二是中外关于形式的阐述虽存在差异,但都承认形式的特征:点、线、面、色彩等是构成形式的基本要素;基本要素之间的构成关系同属形式的范畴。其三是沃尔夫林关于形式的阐释,是对形式最为宽泛的概括和认识。其他人关于形式的阐述在语义的表达上虽与沃尔夫林存在差异,但实际都包含于其中。
按一般的理解,“大结构”应属“章法”一词的范畴,但这里未用章法而用形式一词作为对“大结构”的限定,其理由在于,张大千的“大结构”的要求,实已超出章法一词的含义的范畴,因此用章法作为“大结构”的限定存在局限性。形式一词含义上的宽泛特征,可弥补章法含义的局限,更适合表达“大结构”的含义。
张大千的“大结构”说—“大结构—如穆天子传、屈子离骚、唐文皇便桥会盟、郭汾阳单骑见虏等图。”张大千画学中,“大结构”亦指“伟大的画”或“伟大场面的画”。关于前者,他说:“会做文章的一生必做几篇大文章,如记国家人物的兴废,或学术上的创见特解,这才可以站得住;画家也必要有几幅伟大的画,才能够在画坛立足。”[13]95关于后者,他说:“所谓大者,一方面是在面积上讲,一方面却在题材上讲。必定要能在寻丈绢素之上画出繁复的画,这才见本领,才见气魄。如果没有大的气魄、大的心胸,哪里可以画出伟大场面的画。”[13]95“大结构”“伟大的画”和“伟大场面的画”三者具备四个相同的特征:“面积”大、“题材”大、“繁复”“气魄”(或“心胸”)大。其中,面积与繁复属绘画创作之形式的范畴,气魄(或“心胸”)关乎人品修养。“大结构”说实涉及绘画创作之形式、题材和人品修养三个方面。这里主要就形式因素即面积之大与繁复,展开讨论。
第一,面积之大。现有文献资料观察,张大千绘画创作在面积上经历了大幅到巨幅、再到“伟大的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按时间先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前后,已有创作大幅山水画倾向。对“张善子、张大千昆仲联合画展”的时评中有“大幅《黄山奇景》震惊艺坛”之论[19]。由此评论大致可以获得两点推论,1935年前后张大千已有创作大幅山水画的倾向,此为其一。张大千此阶段的山水题材绘画创作,较之同时代其他画家的山水题材绘画创作,或是水平远超于同类,或是显现显著不同的艺术风格,此为其二。第二阶段:约1945年前后,张大千的各类题材绘画创作采用大幅和巨幅的形式基本成为常态。至少有三条记载可支持此一论断。1945年叶浅予随张大千到成都昭觉寺学画。叶浅予在记录此次学画经历的文章中,曾两次提到张大千创作大幅作品的经历。一次是张大千用“四张丈二大纸,画了一堂四屏荷塘通景大屏”,叶浅予“见此气派,大为吃惊”[20]9。冯幼衡认为,1945年创作的这幅四屏《荷塘通景大屏》“奠定了大千先生吞吐大荒的基础”[21]198。另一次是张大千现场创作“一幅六尺唐装水墨仕女”赠予叶浅予[20]5。四屏《荷塘通景大屏》属大幅无疑,而六尺水墨仕女相比一般仕女画创作采用的尺寸,应也属大幅之列。此外,在此地和此期间,还有张大千创作巨幅作品—八屏《西园雅集》的记录[22]。三件大幅或巨幅的绘画创作出现在同一时间段和同一地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在居住成都昭觉寺这段时期,张大千已经熟练掌握大幅或巨幅绘画创作的相关技法,且大幅或巨幅绘画创作已成为他绘画创作的常态。提出此一论断的理由在于,大幅或巨幅绘画创作的完成,除要求创作者具有与之相应的技法之外,还对创作者的人格提出很高要求,即要有大的心胸、气魄,否则难以驾驭大幅或巨幅绘画创作。创作大幅或巨幅的技法,尤其是大的心胸(或气魄)的形成,绝非偶然情况下的产物,必定是历经较长时间的有针对性的积累和修炼后方才形成。因此,这种在同一时间段和同一地点出现多幅大幅或巨幅绘画创作的现象只能解释为是一种常态的出现,而非偶然的现象。以上提到的三件作品并不含山水题材的绘画创作,但对1935年就以“大幅《黄山奇景》震惊艺坛”的张大千而言,在1935年至 1945年十年间,在人物、荷为题材的大幅或巨幅绘画创作成为常态的情况下,认为他在此一阶段并未创作大幅或巨幅山水题材绘画创作,这一立论实难成立。因此,可以推测,以上列举的三件作品只是他此阶段创作的大幅或巨幅作品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则因记载的缺失而无从查找。
第三阶段:60年代至80年代,传统手卷形式《长江万里图卷》[22]320-321(53.2cm×1979.5cm,1968)的创作完成,标志着张大千绘画创作在面积上进入他所期望的“伟大的画”的绘画创作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除《长江万里图卷》外,还包括《庐山图》[23]342(180cm×1080cm,1981-1983)。值得注意的是,从长与宽的比例关系上观察,后者已偏离前者的传统手卷形式,同时也与立轴形式拉开了距离,采用了具有现代气息的方构图。换言之,张大千在绘画创作生涯的最后时期,仍积极地进行绘画创作之面积上的革新。此阶段在面积上有突出影响力的作品还包括纽约现代博物馆购藏的《荷花通景屏》[21]215(尺寸不详,1961),《青城山通景屏》[23]283(195cm×555.4cm,1962),美国读者文摘社购藏的《墨荷通景六屏》[21]215(尺寸不详,1963)。
中国美术史上手卷形式的大幅绘画创作的最突出的代表作品,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24]129(24.8cm×528.7cm,年代不详)、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24]137(51.5cm×1191.5cm,1113)。若将张大千的“伟大的画”的两件代表作品置于美术史的范畴,与上述所列两件作品对比观察,则可发现,在面积之大上,张大千除完成对自身不断超越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美术史的超越,他将传统手卷形式绘画创作的长度扩展至史无前例。《长江万里图卷》较之《千里江山图卷》在长度上,前者几乎达到后者的近两倍,前者大幅度超越后者。此外,《庐山图》具有现代气息的巨幅方构图,在美术史上也极其少见。
第二,繁复。繁复实涉及形式的两个方面:一是造型之繁复。张大千说:唐宋山水画“千岩万壑,繁复异常”[13]95。又未来画坛将由“苟简之风变为精密”[13]96。以上两条信息讨论的内容都关乎造型之繁复。二是章法之繁复。张大千说,敦煌壁画中的经变、地狱变相、出行图中的“人物真是繁多”,极乐世界图中的楼台花木人物等“繁不胜数”,而这些“真是叹为观止矣”[12]95。这里多次提到的“繁”,固然与题材之“繁”相关,但实际是因落实于章法(或曰布局)的繁复多变而产生的效果。“大结构”的形成,造型之繁复与章法之繁复较之面积之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观察造型之繁复。此方面通过考察张大千工笔重彩仕女题材绘画创作(以下简称仕女画)造型之繁复的演变过程,可以对这一特征获得清晰的认识。此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40年代中、晚期和60年代三个阶段。
30年代晚期仕女画的繁复风格主要借助衣纹线条的密集组合构成繁复的装饰效果。如《散花图》[25]82中,铁笔银钩般劲秀的墨线在衫裙处构成密集的装饰效果,表达动态的同时,传递一种繁复精细的美感。
40年代中期即敦煌考察后,仕女画造型之繁复风格达到其人物画创作的最高点。此阶段繁复风格的形成,在籍由30年代晚期仕女画之产生繁复效果的线条因素的基础上,增添色彩和服饰图案两个因素,三个因素相结合,助推此阶段仕女画达到繁复精细的顶点。具体而言,线条上,强调运用劲秀流利的铁线描或高古游丝描的疏密对比在衫裙处构成装饰趣味。色彩上,一般以大面积的石绿搭配小块面积的朱砂(或是大面积的朱砂搭配小面积的石绿),构成冷暖对比的强烈视觉效果。同时注意在冷暖对比中使用白色、黄色和黑色增亮和协调整体。服饰图案上,以中国传统图案纹样覆满仕女的齐胸衫裙,可谓繁缛精细至极。此阶段效果的形成,显然是受张大千敦煌考察时所掌握的传统人物画尤其是唐代人物画的技法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1944年的《鱼篮大士图》[25]65、《纨扇仕女》[25]100、《红拂女》[25]128、1945年的《团扇仕女》[25]98、《美人秋扇》[25]103等都是此阶段的代表作品。
40年代晚期与中期相比较,前者大体上沿袭后者的风格。但在线条、服饰图案的繁缛程度上以及色彩的面积上,前者较后者明显地减弱(少)。色彩方面,前者将后者习惯运用的大面积重色的冷暖对比消减为小面积重色的冷暖对比;面积消减后的余下部分由水墨取代,整体风格上减弱了富丽感而增添雅致秀韵的趣味。《初唐供养天女像图轴》[25]94是此阶段风格的代表作品。此图中,色彩上,仅在仕女齐胸衫裙的腰部染以重色朱砂色,其余大部分则以淡薄的青色染出。同时在朱砂和青色间以少量黄、白色和黑色协调。中期至后期的风格演变,无疑透露出张大千有意地弱化华贵富丽风格而增加秀韵趣味的审美思想。后者的出现,可以说是张大千对20、30年代所偏爱的且能娴熟表现的文人画之秀逸风格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也与他对时代审美的敏锐回应有关,毕竟与敦煌壁画审美风格过于接近的40年代中期仕女画风格难以体现时代的审美趣味。
60年代仕女画创作,由之前强调仕女造型本身之繁复,演变为强调仕女造型与背景造型之间的对比与呼应关系的探索。导致繁复效果形成的因素来自服饰图案和色彩两方面。《荷屏仕女图系列》[25]179-183和《荷屏仕女图》[25]185是此阶段风格的代表作品。以上所列图中,仕女在装束上虽由古装仕女变为现代女性,但依然倾心于表现繁缛的服装图案。在此种情况下,作为背景的屏风在造型上就不得不配以繁缛的形象与主体相呼应。图案的呼应与对比自然促成色彩的呼应与对比,这些都加强了绘画作品在整体上的繁缛感。屏风是日本仕女画背景普遍应用的造型因素。张大千在以上所列图中的屏风造型,揭示他对日本画造型因素的思考和借鉴。60年代仕女画在造型上,与之前的以空白或山石竹木为背景的传统仕女画拉开了距离,显现出现代绘画所具有构成特征。
若将张大千仕女画与同时代人物画中的代表画家的仕女造型特征相比较,则可愈见其造型上所具有的繁复的特征。张大千说:“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26]54薛永年更称徐燕孙为“20世纪传统人物画的重要代表和画坛师首”[27]。以上评价说明徐燕孙仕女画在20世纪人物画坛的代表地位和影响力。若将张大千与徐燕孙两人的仕女画在造型之繁复的特征上进行对照,探寻两者在此方面的特征,应能很好地说明前者的独特性与突出性。
将张大千的《红拂女》[25]125中的仕女造型与徐燕孙《纨扇仕女》[27]、《仕女》[27]、《参禅图》[27]、《爱莲图》[27]中的仕女造型相比较,两者之间最突出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线描营造平面装饰的趣味,后者趋向将线描与局部的立体造型相结合。如徐燕孙的《纨扇仕女》中,仕女之手臂和裙装部分的造型,将传统线描与由传统线描构建的立体效果相结合。当然,这种立体效果有别于西方绘画中因光影的明暗对比而产生的立体感,而是线描和晕染结合形成的立体效果。
当线描与平面造型观念结合时,线条可以极尽其繁,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特征与优势。而当线描与立体造型合于一体时,线描至多能存在于造型物的轮廓或某些局部,因为线条与体积是一对矛盾体,因此,很难想象张大千仕女画繁缛的服装图案可以在徐燕孙所画仕女的衫裙上立足。张大千仕女画造型的繁复程度自然是远甚于徐燕孙的。张大千仕女画造型之繁复特征的形成,与他始终坚持中国传统绘画之平面造型观念,而对西方传统绘画的立体造型观念保持距离,有直接的关系。今天看来,张大千对中国传统绘画之平面造型观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革新,恰恰成就了他的人物画在中国画坛乃至世界画坛的地位和影响。
以上所论并非欲对张大千和徐燕孙的人物造型观以高下评价。这里只是希望通过对比引起对中国传统绘画之平面造型观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再认识。
再说章法之繁复。张大千所谓的“大结构”,原意是指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绘画创作。但他的人物画创作一般以仕女为题材,且所画人物数量一般为一人或二人,因此,张大千人物画的最终效果实与他的“大结构”的绘画创作审美理想相差甚远。当然,在人物画中我们也无法领略其所期待的章法之繁复的效果。但他的“大结构”的审美理想最终还是在山水、荷题材的绘画创作中得以实现。在此类题材的绘画创作中,张大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章法之繁复的理想追求。欲了解张大千绘画创作章法之繁复的特征,须先对传统“章法”论有大致的认识。
“章法”是传统画论中的重要概念。东晋顾恺之《论画》中的“置陈布势”[4]400、南朝谢赫“六法论”中的“经营位置”[4]156,都可谓章法代名词。概言之,传统章法论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在绘画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如唐张彦远的“画之总要”[4]389、明李日华的“以布置意象为第一”[4]391、清方薰的“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4]399,即是此意。二是取景原理,如北宋郭熙《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4]429。三是布景法则,如“宾主”“呼应”“开合”“虚实”“藏露”“繁简”等布景的对立统一法则[4]405-423。以上所论主要针对山水画章法而言。
张大千认为绘画创作的章法源于两个方面:传统绘画作品和自然(或曰生活)。他说:“至于绘画创作的布局,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师古人,从古画中吸取艺术修养;二是师造化,就是要游历,从实景中观察。……只有熟悉了各种山山水水,胸有丘壑,布局自然有所依据,并从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来养成广阔的心胸。”[28] 50这里主要讨论他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过程中怎样完成他的“大结构”的山水画对传统章法的继承和革新。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可谓宋及之前山水画最高成就之代表,其章法自然为传统章法之代表。若将张大千的“大结构”的山水画《长江万里图》和《庐山图》与《千里江山图卷》作章法上的比较,于两者的同与异之处,最能说明前两者对后者的继承及革新。
张大千对传统章法的继承与革新突出体现在对取景原则的继承与革新。首先是传统“三远”法的继承与革新。宋郭熙阐释“三远”法,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4]429北宋韩拙在郭熙“三远”法之外,又提出“阔远、迷远、幽远”之说[4]430;韩拙之说实属“平远”的范畴,可谓“三远”法的发展。“三远”中以“深远”最难表现。清代费汉源说:“三远惟深远为难,要使人望之莫穷其际,不知其为几千万重,非有奇思者不能作。”[4]431由以上所论可知,传统章法论更重视平远和深远,而较少强调高远。《千里江山图卷》作为传统章法代表,与传统章法论的要旨一致,强调平远和深远,而削弱高远,意在天际浩渺、江山无限之意境,这也是山水史上传统手卷所采用的常见取景原则和意境效果。
《长江万里图》对传统章法的继承性体现在其取景原则依然依据传统三远法的框架和含义,其革新处在于突出三远中的高远和深远,而使平远处于陪衬地位。这与传统章法论中的扬平远抑高远形成区别。此图起始便是高远和深远的结合,以高远法截取山形上部以抵于画幅之前景,产生突兀雄伟的视觉效果;以深远取山形由中景至远景延伸,产生“不知为几千万重”的效果;高远与深远的结合兼具辽阔与巍峨的视觉效果。此种结合在图中有三大处,成为此图中最突出的章法形式。此图末尾以平远法显现长江入海之景色,浩浩荡荡,与前面之巍峨雄伟相得益彰。传统手卷形式,由于通常将平远与深远的结合为主要的取景形式,其意自然在江山无限的意境追求;《长江万里图》将通常的平远与深远结合的取景形式的革新为深远与高远结合为主要的取景形式,在江山无限的意境之外,更满足了他对巍峨雄伟境界的追求。
其次是对传统“上留天,下留地”取景原则的继承与革新。“上留天,下留地”是传统山水画中必用之取景原则。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宋郭熙在阐释“上留天,下留地”时说:“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见世之初学,遽把笔下去,率尔立意触情,涂抹满幅,看之填塞入目,已令人意不快。哪得取赏于潇洒,见情于高大哉?”[4]396-397郭熙此段中,强调“上留天,下留地”取景原则在山水画中的必须性、结构要求,贬抑与之相左的“涂抹满幅”作风。明代沈颢也提出相同观点,说:“大痴谓画须留天地之位,常法也。”[4]402黄大痴是否有此论,已难以考证。但此论中的“画须留天地之位”的观点是当时山水画普遍运用的取景原则,应是事实。此章法利于开阔意境。
《千里江山图卷》是传统“上留天,下留地”取景原则的典范代表。此图自首至尾,都将景物置于天地之间,且天、地(或水)占图中面积的较大比例;某些局部即使所留天、地面积极小,但仍显示对“上留天,下留地”取法原则的坚持。《长江万里图》对“上留天,下留地”取景原则的处理上,明显地降低了天、地面积在整图面积中的比例,甚至在某些局部,天、地消失而以景物满幅。
第三是对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继承与革新。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与传统山水画中将远景置于前景的“以小观大”法相关,典型图式为南宋山水画中普遍存在的将山石或树木置于前景之“一边”或“一角”。南宋山水画家马远《雪图一》[29]图版89中位于画幅前景的山石及其上的楼阁,夏圭(生卒年不详)《雪屐探梅图》[29]图版186中从画幅前景左下角斜向伸入画幅中心的古松,即是“截取式”取景原则的典型范式。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优势在于能细致地表现景物之形态和质感;这恰是在平远、深远取景原则下描绘景物的欠缺之处。传统“截取式”一般仍置于“上留天,下留地”中,以兼顾两者的优势。
《千里江山图卷》图中未采用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长江万里图》中的“截取式”与传统“截取式”相比较,既存在一致之处,也有区别。一致之处体现在某些部分以景物的截取局部置于前景,但仍限于“上留天,下留地”的格局之中。这是对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继承。区别之处在于,某些部分已脱离“上留天,下留地”的限定,全以截取的局部满幅。这种非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与西方近现代绘画的构图特征类似。
将《长江万里图》中这种非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应用归结为西方近现代绘画构图的影响,其理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两者在构图形式上的相似。西方近现代绘画构图上通常截取事物之局部作为构图的全部。如马蒂斯的《餐桌》[30]581在构图处理上,画面中心被桌布覆盖的餐桌的下部,靠画面右侧边缘的女主人裙子,画面左下角椅子的左侧和下部,左上角窗户的上部和左边部分,上部的墙壁的上方和右上方,都被截取在画面之外。靠近画面边缘的描写物无一以完整的形象存在。修拉《库尔波伏瓦之桥》[30]545、毕沙罗《清晨阳光下的意大利大道》[30]548、伍德《春回大地》[30]589等在构图上都存在与马蒂斯的《餐桌》类似的现象。西方近现代绘画的这种“截取式”构图特征与中国传统山水画“截取式”取景原则的迥异本质上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审美思维方式。《长江万里图》中将两种审美思维方式迥异的取景原则统一于一体,很难想象是一种偶然的发生,更像是有意而为之。二是此图之前的泼墨泼彩中就存在采用这种非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现象,而此图之后的若干年后,此种现象减抑,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大致可以推断非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出现是一种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长江万里图》之前的《青城山通景屏》《幽谷图》[23]307、《山雨欲来》[23]311、《四天下》[23]284-285等泼墨泼彩中,都存在采用这种非传统“截取式”取景原则的现象。这说明,此种现象的形成非一日之功或由水墨生发形成的偶然效果,而是经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后才形成的。但在《庐山图》中,画面下部和右边虽呈“截取式”,但这种“截取式”是限于“天”之下。可以说,此时的张大千在山水画的取景上重新回归到了传统的“上留天,下留地”的取景原则。对《庐山图》中“截取式”取景原则的观察结果,说明张大千对其作品中的西方绘画元素所持的实验精神和谨慎态度。三是自1956年5月游欧洲以来至1968年长卷《长江万里图》制作完成的期间12年间,张大千频频往来与欧洲、东京、美国举办画展。这期间张大千耳濡目染西方现代绘画,接受其观点和绘画形式亦是在所难免。实际上,很多史料表明,张大千确有对西方绘画有深入研究及融合中西绘画的心意。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三节的讨论中有详细的论述。张大千在欧洲举办的展览和所参加的展览,如“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1956,巴黎东方博物馆),参加法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画展览”(1958),“张大千近作展”(1960,西班牙马德里),瑞士日内瓦艺术历史博物馆展出作品三十幅等[43]31-33。以上所列还不包括非常重要的1956年张大千造访毕加索事件,以及在其他国家城市如东京、纽约等地举办的展览。这些展览的举办,一方面提升张大千作为世界级画家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促成张大千对西方绘画的理解。这是成就张大千山水画中非传统“截取式”取景的重要因素。
非传统“截取式”取景使景物在高度、体量和质感的塑造上获得更大施展空间,有助于景物之巍峨雄壮气势表现。传统与非传统“截取式”取景的结合,在赋予景物之无限之意境的同时,增加巍峨雄壮的效果。非传统“截取式”取景应用与张大千造型之繁复与章法之繁复的绘画创作理想一致。
张大千为了实现他的绘画创作形式之“大结构”的审美理想,在面积之大与造型、章法之繁复上,历经万难,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经取舍与协调,最终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也许在张大千看来,《长江万里图》和《庐山图》所体现的“大结构”审美特征并非一种完美的呈现,但对中国美术史而言,他创造的“大结构”的审美样式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达到现代中国画形式审美的最高点。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他对以民族特色为前提的东西融合观的坚持和力行不无关系。
三、绘画创作境界之集大成
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31]269汉儒赵岐注释此条,说:“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31]269赵岐的注释透露“集大成”涉及三方面含义:集以往文化于大成;成就自己之圣德,即开创了新的传统;具有开后学的性质。明代书画家、鉴赏家莫是龙在《画说》中也提出“集其大成”说。他说:“画平远师赵大年,重山叠嶂师江贯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即潇湘图点子。皴树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画法有小帧水墨即着色青绿,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32]莫是龙“集其大成”说的要义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指章法、皴法、点法、着色等画法上以赵大年、江贯道、北苑、子昂、大李将军、郭忠恕、李成等为宗,以集古人画法于大成;一是将“集其大成”和“自出机轴”并提,强调“集其大成”与创造新风格的必然关系。由以上两例可知,“集大成”实蕴涵三方面的含义:集以往思想或学说于大成、形成新的风格和开后学,即开悟自此之后的学者。依“集大成”含义观察,张大千的绘画创作实已达到集大成之境界。
在集以往文化于大成方面,张大千的绘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集古画之大成。张大千的集古对象可藉由以下诸条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获得大致的了解。他说:“余幼饫内训,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穷源篆籀。临川衡阳二师所传,石涛渐江诸贤之作,上窥董巨,旁猎倪黄,莫不心摹手追,思通冥合。”[33] 21-22又说:“盖大千平生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什九矣。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壁画,简藉所不载,往哲所未闻。……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至元魏,下迄西夏,绵历千祀,极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矩矩。”[11]18以上两条资料揭示张大千集古对象的三个特征:由近溯远,即由清代向上追溯,至宋、元、五代,再至隋唐、六朝,几为一部中国绘画史;宋元及以上全为真迹;有些古画为简藉不载、往哲未闻者。
古画资源可谓浩如烟海,张大千临摹古画并非照单全说,而是依照一定原则有选择性地临摹古画。他选择临摹的古画大致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六法”具备。“六法”者,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也[34]。“六法”论包含的绘画创作诸种因素,历来为指导中国画创作的基本法则,其中居于首位的“气韵生动”尤被奉为中国画创作和鉴赏的圭臬。张大千绘画创作和鉴赏都视“六法”为研习的首要。他说:“大千髫年,当北堂之暇日,初识六法。”[35]又说:“蝯幼研六法,不敢自为有得。”[36]他评价石窟壁画也说:“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矩矩”。[11]18“六法”中又以“气韵生动”者尤为张大千推崇和重视。关于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气韵”理论以及“气韵”绘画创作实践,在笔者的《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曲”审美观》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述。其次是有“雍穆之象”者。他说:“抑余闻艺事虽微,其所系于人心风俗运会则甚大。世之治也,则文章诗歌书画金石,莫不有雍穆之象焉。及其乱也,则非狂怪险谲无以厌其欲。”[37]“雍”者,和谐也[38]。“穆”者,“静而兼厚、重、大也”[5]22。又说:“花鸟以宋朝为最好。……宋人对于物理、物情、物态观察的极细微,……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崔白山雀野兔图、李安忠浴沙鹌鹑图、宋人无款梅竹聚禽图、宋人无款芦汀双鸭图,又长春散出徽宗金英秋禽图,以上都是神品。”[39]108张大千认为“花鸟以宋朝为最好”,殆因宋朝花鸟画对物理、物情、物态刻画得极细微的原因,而这应是张大千所谓的“有雍穆之象”者的最重要特征。三是忌偏爱而应博采众长。他说:“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故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采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2] 122此外,张大千在此段话中还提出临摹古画的另一重要要求,即临摹时须“凭理智聪慧采取名作精神并进行转化”。这一要求的提出揭示张大千集古画于大成的目的是为了创作出新的风格;这应是张大千绘画创作虽起于集古,但并未陷入旧法的窠臼而能自出机杼的主要原因。
傅申将张大千的集大成特征概括为三点:张大千一生力行、实践董其昌的“集大成”理论;张大千在集大成上,与中国画史上公认的集大成者元代赵孟頫和清代王翚相比,后两者在观赏古画的方便与视野所及的层面上远逊于前者;张大千是中国绘画集大成传统的光辉的结束者[40]。董其昌“集大成”说与莫是龙“集大成”说内容完全一致。傅申认为“集大成”说由董其昌提出,俞剑华则明确为莫是龙,而非董其昌。“集大成”说的董、莫之争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这里只是借此提出一个观点,即董、莫的“集大成”说都强调集古画之正统者。傅申界定张大千为集大成者,正是针对他集古画之正统者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正如前述,于正统之外,张大千还提到对“简藉所不载,往哲所未闻”之古画的研习。这自然扩展了张大千集大成的内涵。
临摹古画须与写生相结合。张大千认为临摹和写生对绘画创作的形成各有意义。他说:“临摹古人,要学他用笔用墨,懂得他苦心构思。写生要认识万物的情态,勾出心理面要吐出来的境界。”[39]96张大千在此段中指出,临摹的目的是掌握中国画的用笔、用墨以及章法营造。写生目的中提到的“认识万物的情态、勾出心理的境界”之语实指须在写生中积累绘画资源和发现自我。如张大千说他游历黄山的“三度裹粮,得穷松石之奇诡,烟云之幻变”之语,指的是写生对积累绘画资源的意义[26]55。临摹与写生交替进行,最突出的意义在于,促成古画与张大千个人感受相贯通、融合,形成临摹与写生相促进的效果。
第二为寓通于专的全能型画家。“专”即专才,指张大千的绘画创作才能,以绘画创作才能衡量,张大千是全能型的画家。在题材方面,人物、山水、花鸟题材的绘画创作皆擅长。在表现形式上,几乎每类题材都掌握工笔、写意、浅绛、没骨等多种表现形式。“通”即通才,指张大千对与绘画创作相关的书法篆刻、诗词创作、 精鉴、画史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通。张大千绘画创作上能达到集大成之境界,与他的通才有很大的联系。在书法方面,张大千自言二十岁时在上海即受业于曾农髯 、李瑞清,“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26]55。此自评除表明书法以金石为主攻方向外,还涵有取法高、研习广之义。在诗词方面,张大千自称叶遐庵“极赏予长短句,以为得坡翁神韵。”[6]61能得“坡翁神韵”之评语,说明张大千诗词创作达到高妙的境界。精鉴方面,张大千自诩“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33]23徐悲鸿曾谓张大千的绘画创作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也”,张大千对此惶恐应以“五百年来一人,毋乃太过”,这说明张大千本质上是一位谦虚的人。而在精鉴方面,张大千却毫不谦虚,自诩“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这说明张大千在精鉴上确有能力超群之处[26] 53-54。画史方面,可藉由他的《故宫名画读画记》略窥一斑,更能从其绘画创作之集大成的特征获得认识。
张大千通才还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思考和实践。张大千对“中国美术复兴”存在问题的思考、主张和实践,对绘画创作中的物之理、情、态的极致追求,对良好风骨、情操的强调,正体现儒家哲学之“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格物致知诚意修身”思想的影响。张大千绘画创作与道家思想也有不解之缘。张大千在谈到他的减笔破墨(即泼墨或泼墨泼彩)是否为创新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老子思想的启发。他说“老子云:‘得其环中,超以象外。’此境界良不易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其庶几乎。”[26] 57正因“此境界良不易到”,而张大千却能成功地得以实现,这正说明此境界的实现是受老子思想的启发并于此自觉尽力探索而成。因此,他自然能自信大胆地提出“抽象的始祖出于我们中国的老子”的观点[28]7。此外,佛学的禅宗思想对张大千的绘画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大千阐发其“曲”审美观所包含的“余音袅袅,回味无穷”含义,与文人画追求“画外之画”意境,两者都是禅境的示现[1]32。又说:“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画得熟练了,何必墨守成规呢!”[2] 123-124“一个艺术家最需要的,就是自由。”[28]1又说:“我作画是常常随兴之所至,画到哪里算到哪里。这样子作画时,心情如冥游天地,与造化合一。”[28]51以上资料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无疑深受南宗不拘形式、明心见性的思想的影响。张大千绘画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儒、道、禅的影响揭示其绘画创作对“道”境的追求和实现。而这通常被认为是绘画创作的最高境界。
中国绘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和会通性特征,使得通才成为中国绘画创作展开和深入的基本条件。中国绘画创作者在通才的状态下,更易通过不同类型知识间的贯通和融合激发创造性的思维,推动绘画创作朝更大、更深厚的境界发展。
第三是融合域外绘画因素以滋养强壮其绘画创作。从现有文字资料以及绘画作品观察,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域外绘画因素中较突出的因素包括西方绘画因素、日本画因素和印度壁画因素。
张大千多次提出关于中西绘画的观点。首先,张大千认为中西绘画交流融合应以保持中国画本色为前提。他说:“中西画应无鸿沟之分,只因不同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和画具的不同,各具特色。在不失自己本色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共同进步,世界才永远有丰富多彩的绘画。”[28]5又说:“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张大千强调的中国画的本色指的是中国画的外在面貌及内在神韵。其次提出中西绘画存在一致性的观点。“画无论中西,都是由点、线构成的。”[28]6“中西艺术达到最高境地时,都是相同的。”[28]6三是关于“抽象”的观点。“近代西洋各画家所倡导的抽象派,其实就是受中国画的影响。”[28]7“我认为,抽象的始祖出于我们中国的老子。”“我们通常是精神的抽象”[28]7。张大千关于“抽象”的论述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常丰富,概言之,可总结如下:近代西方抽象派的起源在中国画;抽象的始祖是道家的老子;西方抽象派是一种形式的抽象,而中国画的抽象是精神的抽象。四是对毕加索作品的研究评价。张大千认为毕加索作品“与传统西画有异,而其思想内容是亦基于西方”[41]68。毕加索“早期所倡之立体主义,乃循塞尚之立论从事理性创作,而吸取黑人雕刻之犷野,突破写实之约束,不过强化之表现而已。”[41]68张大千能从绘画创作的本源评价毕加索艺术的特征,说明他是将毕加索研究置于西方美术史的范畴中进行考察。五是关于西方传统艺术的观察。1956年夏,张大千于罗马参观文艺复兴三杰的壁画、雕塑,实地研考西方传统艺术,“深感艺术为人类共通语言,表现方式或殊,而讲求意境、功力、技巧则一”[41]68。综上所述,可知张大千的确全面深入地考察过西方绘画,并在此基础上将中西绘画从精神、思想、形式诸方面逐一相对比,以希冀找到两者的契合之处。虽然张大千否认其绘画创作中有西方绘画因素,但他的画学中对西方绘画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他的绘画创作中存在与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但和西方绘画类似的如光、体量、色彩等形式因素以及即兴表现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关于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日本绘画因素可从以下两方面认识。一是绘画创作的工具材料绝大部分都由日本采购,制作《庐山图》所用的大幅绢就定制于日本。二是绘画创作形式上存在明显的日本画痕迹。前述中提到的张大千《荷屏仕女图系列》中的屏风造型,清新明丽的设色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日本画特征。另外,《午息图》[25]134中的仕女,其造型的倾斜走向及环境布置极类似铃木春信的《春宵》[42]图版47中的仕女与环境的构图关系,而设色之深与浅的对比搭配以及腰部服饰的纹饰分布和色彩处理又与伊东深水《初秋》[42]图版52中仕女造型的相似度极高。
张大千曾实地考察印度石窟壁画艺术。“民国三十八年冬,……留于印度阿坚达窟三月,研讨与敦煌壁画异同,颇为有得。”[26]56又1950年4月,赴印度文达雅山阿旃陀石窟考察研究并临摹壁画,共费时一个多月[43]26。在此之后,即1950年5月至次年3月,张大千旅居印度大吉岭[43] 26-27。此间,张大千创作不少以印度女人为题材的工笔作品,代表作如1950年制作的《印度仕女》[25]147、《汲水仕女》[25]147和《阿坚鞑养鹅女郎》[25]147。这些代表作品中,人物和背景从形态到设色都具有浓郁的印度绘画艺术的风格特征。而在此之前与之后,张大千的人物画都体现为超逸的风格特征,未见旅居大吉岭时这种泥金重彩形式的人物画作品。张大千并非局限与中西绘画间的融合,而是扩展至东西方绘画间探寻契合点。
无疑,张大千的绘画创作是集以往于大成的绘画艺术,而集大成者必能自出机杼。至今仍有不少人将他归为“善摹古者”一类。对于这种盲目的贬抑,徐悲鸿在1936年的《张大千画集序》中就对持此观点的人提出了驳斥。他说:“徒知大千善摹古人者,皆浅之乎测大千也。”[12]3171936年是张大千绘画创作的摹古期。在张大千的摹古期徐悲鸿就肯定了其绘画创作的独创性。那么,自1936年之后,众所周知,张大千的绘画创作历经了三次明显的大的变法—敦煌考察后为一变,60年代的泼墨泼彩为一大变,《庐山图》又为一变,每一次变法,就是一种新的风格的形成。由此观之,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虽集古画于大成,但绝非某些人口中的“善摹古者”,而是乘风破浪的革新者。他的革新即自出机杼主要体现为,身体力行地扭转了笼罩当时画坛的“写意只要几笔”的文人画之颓靡、因循守旧的作风,而倡导和创立了立意之“大寄托”、形式之“大结构”以及境界之集大成的绘画创作。
张大千绘画创作在大陆的影响度远不能与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相匹配。这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或许是因为集大成的难度,或许是因为张大千长期旅居海外的原因,也或许是对张大千艺术价值的认识不够而导致学术层面研究的不足。总而言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不足。张大千绘画创作的学术价值确实有待于更深入地认识和挖掘。
四、结语
张大千绘画创作中的“大”审美观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以下问题:其立意之“大寄托”提出绘画创作与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关系的问题;其形式之“大结构”提出绘画创作在形式上如何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中国绘画与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诸种因素相融合的问题;在境界之集大成上提出集大成和自出机杼的关系的问题。张大千的“大”审美观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由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时所提出和应用的民族观和世界精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全球文化日益一体化的形势之下,对如何在坚守民族传统文化形式与精神的基础上有效地吸取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以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中国画的当代学者和艺术家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