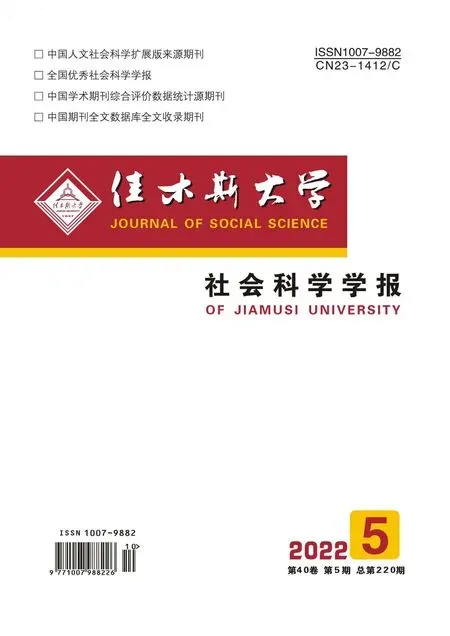女性主义叙事学下《幸福过了头》的女性叙事权威建构
程智贤,刘玉红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2.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的小说集《幸福过了头》(TooMuchHappiness)于2009年出版,《幸福过了头》是该小说集的压轴作,与小说同名。它讲述了19世纪俄国天才数学家索菲娅的故事,作为一名女性,她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与世俗的偏见作斗争,努力寻找幸福。为出国留学,她委身于一段短暂而不愉快的婚姻;而后,她与马克西姆的婚姻让她重燃对婚姻的期待,但因马克西姆的虚伪、专横,她只能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幸福之中。尽管她在数学方面天资过人,求职却遭遇失败。她博学却不受重视,并因其女性的身份让她承受了很多痛苦。读者也可以从她的过往遭遇中得以窥见当时身处俄国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苏珊·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先驱者。根据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女性叙事权威指的是叙事者权威向女性角色转移,以建立女性话语权并实现女性主体性。《幸福过了头》里有两种声音:第一种是叙述者声音,这种声音利于客观地揭示女性面临的困境,暗示对受压迫女性的同情,委婉表达女性主义观点,号召女性叙事权威的觉醒;第二种是人物声音,男性和女性都能在谈话或冥想过程中表达观点,展现两性的冲突和女性的成功反抗,从而加强女性的话语权。本文采用作者型声音与人物声音论证女性叙事权威的构建,凸显女性主体性。
一、叙事者声音:作者型声音对女性叙事权威的影响
叙事者在《幸福过了头》中运用客观的和含混的中性化作者型声音间接为女性发声。客观的作者型声音为叙事权威的崛起如虎添翼,便于表达作者的女性观点。含混的中性化作者型声音,即叙述者尽量不带任何性别色彩来讲述故事,表面上削弱女性叙事权威,从而曲折建构女性叙事权威。
(一)客观的作者型声音——女性叙事权威的崛起
作者型声音指的是“具有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1]17。“异故事”指叙述者从不是故事的直接参与者。由于作者型叙述者不受故事的约束,自由出入故事,捕捉人物内心的瞬息万变,因此叙事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叙述者更容易建立起叙事权威。
首先,客观的作者型声音赋予故事全知的叙事权威。故事里叙事者退居幕后来讲述故事。故事中的叙事者不是小说中的某一特定人物,叙述的视角不断变化,赋予了作者型声音全知全能的叙事权威。例如,故事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开始介绍主人公的情况,然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索菲娅的故事,接着又转换到马克西姆的视角。当索菲娅第一次拜访教授时,故事是从克拉拉和伊利斯的角度来讲述的。不断变化的叙事视角给予了作者型声音全知全能的叙事权威,让故事的叙述更加客观可信。
叙事者对死亡的描述是建立叙事权威的关键因素之一。叙事者选择三言两语来简洁地描绘索菲娅和她丈夫弗拉迪米尔的死亡。弗拉迪米尔“四月的时候,用一个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了氯仿”[2]330,另一处则是索菲娅:“大约四点钟,索菲娅去世。尸体解剖将会显示,她的肺已经完全被肺炎摧毁,心脏的毛病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2]348叙述者简短冷静地讲述死亡,没有过多情绪波动和主观评论,像机器一样记录所发生的一切,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不到叙述者的存在,文本的内容更容易被接受,更易建立叙事权威。
其次,给人以客观印象的作者型声音向读者渗透女性主义观点,含蓄构建女性话语权,有力压制男性话语的霸权主义。面对男性的压迫,索菲娅勇于反抗。例如,向男性数学教授魏尔斯特拉斯求学遭到刁难时,索菲娅以顽强的毅力解决了难题。由于她的天赋,魏尔斯特拉斯“尽量掩饰他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和他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漂亮解法”,并且“她对他来说是一个冲击。在许多方面都是。”[2]313因为索菲娅的数学才华与能力让男性教授魏尔斯特拉斯对她刮目相看,甚至到敬佩的地步。叙事者把一个勇敢、坚韧、有抱负、有才华的索菲娅带到读者的面前。
作者型声音展示了一位备受压迫女性的内心世界,但没有被命运眷顾的她仍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事业。索菲娅的不幸经历暗指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索菲娅”存在,揭示了当时大多数女性面临的困境,作者型声音借她的故事为女性发声,构建女性话语权与叙事权威。
(二)含混的中性化作者型声音——女性叙事权威的削弱
“女性作家对公开的权威性的改编通常意味着对性别规范的挑战。”[1]25为建构女性叙事权威,门罗采用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巧妙地避免了公开挑战现有男性权威的风险,通过作者型声音客观地表达自己的女性观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叙事权威部分被削弱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学者申丹指出小说中叙述者的性别在叙事形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7。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型声音却刻意淡化叙述者的性别区分。例如,叙事者对马克西姆和索菲娅各自的职业的评论。“索菲娅她除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而他一个也不是,只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叙述者评论说:“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2]296作为男性,马克西姆是一个不知名常被冷落的学者。而索菲娅区区一个女性,却是一个有极大数学才能的人才。马克西姆因自己和索菲娅之间的差异感到又嫉妒又愤怒又失望。讽刺的是,在那个时代女性普遍被看为男性的附属品,地位也理应比男性低。叙述者的评论似乎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的认知,因此才会将他们之间的差距看作笑话。叙事者的性别和态度都模棱两可。叙事者可能是支持马克西姆这种思想的男性或讽刺具有这种社会偏见的女性,甚至有可能是无奈下不得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女性。
叙事者对男性尤里关于索菲娅的看法评论道:“尤里的人生也许会改变,说不好。他甚至有可能会再次对他的索菲娅姨妈有些许喜爱之情。虽然,也许要到他有如今的她这么老,要等她死去以后很久。”[2]308尤里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对她们十分轻蔑。但叙事者希望将来他能抛下对女性的偏见,平等地对待女性。“再次”一词可以看出,尤里孩童时期一开始也许并没有歧视女性的概念,由于周围大环境的影响形成这种观念,所以叙事者对尤里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盼。但从“也许”“说不好”“甚至”“有可能”等不确定的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叙事者的犹疑。叙事者认为可能要等到很久之后才能再次对索菲娅有喜爱之情,重新正视女性,也可能尤里永远都不会尊重女性,直到他的死亡。故事到结局并没有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叙事者犹疑不决的态度和模棱两可的性别都在表面上削弱了女性叙事权威。
叙事者在文本中难以察觉,这些是故事中为数不多读者可以直接感知到叙事者存在的例子。作者型声音模糊了性别、身份和态度,不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做明确的评论,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从而隐晦地表达女性观点。同时,女性的声音很容易被父权社会中男性的声音的权威所主导、所压制,运用中性化的叙述者和没有过多压迫性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者型叙事声音所能激发的最大化的叙事权威,但女性的叙事权威能够被隐性间接地建构。
二、人物声音:时涨时落的女性叙事权威
在故事中,男性声音展现了男性人物对女性的看法。在男性看来,像索菲娅这样的女性必须为男性服务,服从男性。张扬的女性声音告诉人们: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并没有一直处于沉默状态,而是有渠道为自己发声。通过对比男性和女性人物声音,我们可以知道两性之间的冲突,女性对男性压迫的成功抵抗都代表着女性话语权的崛起,叙事权威的构建,女性主体性的凸显。
(一)压迫的男性声音:“他者”索菲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把两性关系中的女性定义为“他者”,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个体,他是“中心”,她则是无关紧要的“他者”[4]。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歧视女性的观念根深蒂固,把索菲娅在内的女性视为无足轻重的“他者”。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文化的小人物,都处于优于女性的地位。他们对索菲娅的所作所为,让她意识到她是她自己而不是任何人的附庸。这些也反映了门罗对两性关系的思考。耿力平(2018)指出门罗笔下女性的成长离不开男性:首先,女性成长中的羁绊既可能是男性设置的也可能是女性制造的,所以男性给予女性的影响既有反面也有正面;其次,女性在同男性的相互作用中,尤其在作为对手进行博弈时,能够获取有益的体验,进而促进她们拓展心智。[5]这种情况也可以在《幸福过了头》中找到。正因为男性站在女性的对立面,将女性视为“他者”,才促进了女性成长,让其变得更强大。她们遭受的打击和伤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她们成长和蜕变的动力。压迫的男性声音是女性叙事权威减弱的象征。在经历了所有的磨难后,女性声音最终还是会强大到足以对抗男性的声音,使得女性叙事权威增强。
故事中的男性总处于支配地位。索菲娅的父亲不同意她出国留学时,她只能通过与其他男性结婚的方式摆脱控制。她姐姐阿纽塔因兴趣写作投稿给杂志社,父亲大发雷霆,在父亲眼里,她与姐姐没有权利做她想做的事,包括写作,因为这些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处于男性世界之外;索菲娅的侄子尤里对索菲娅与母亲的态度十分轻蔑,言语间从不尊重女性。他还只是个孩子,但心中早已狭隘地种下“女性是他者”的种子。
索菲娅的丈夫认为“除了那些勾引、谋杀男人的以外,没有女人重要到让世界有所不同。”[2]17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男性的想法,女性的成功要依附男性才能实现。女性自己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索菲娅只配成为生活的看客和“他者”。但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男性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她不仅成长起来,还依靠自己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
索菲娅的老师兼朋友,教授魏尔斯特拉斯在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时,说:“结婚就是给你的事业划了句号。”[2]324他是小说中唯一欣赏索菲娅的才华并支持她的事业的男性。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才的人,在长期以来社会偏见下,仍难全身而退,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普遍又根深蒂固的偏见。所幸索菲娅后来在数学领域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推翻了他对女性的一切落后、消极的看法。
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文盲,几乎所有男性都认为包括索菲娅在内的女性是“他者”。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处于被男性压制的艰难处境,不能踏入男性的领域,与男性平等竞争。但索菲娅颠覆了男性主导的世界里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也表明,女性不愿意屈从于男性,也不愿意被男性所定义,女性是一个独立和强大的个体,从而稳固女性话语地位。
(二)张扬的女性声音:索菲娅非“他者”形象
兰瑟认为在叙事中不存在单一的声音,声音之间彼此重合[6]348。故事中压迫的男性声音造就了张扬的女性声音的崛起。女性声音描绘了各种各样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这不仅反映了女性所遭受的不公,也象征着对父权的反抗和女性叙事权威的上升。
首先,索菲娅所写的信件对男性角色马克西姆极力称赞。她深爱并崇拜着他,但马克西姆无法忍受她在数学方面的才华和名望。对姐夫雅克拉尔,索菲娅“自始至终都是鄙视他的”[2]304。他不忠,刻薄,傲慢。尽管姐姐阿纽塔一直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还是爱他。从她们间不平等的关系可见女性遭受的不公和困难。女性声音塑造了典型自负的男性马克西姆和卑鄙的花花公子雅克拉尔两种人物,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消极态度与身体心理上的双层压迫。
其次,女性声音中的女性形象也各有不同。教授的两个妹妹克拉拉和伊利斯被刻画成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们把哥哥作为生活的核心。对此索菲娅悲哀地叹息并一针见血地反问到:“他的生活,比起他的妹妹的生活,就更应该,更值得满足吗?”[2]325门罗生动地描述了女性如何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被视为“他者”。如果我们说其他女性角色的观念代表了女性叙事权威的削弱,那么索菲娅的想法和观点将是女性叙事权威崛起的象征。
在索菲娅的描述中,科学家的妻子们反映了当时矛盾的女性形象。她们对待索菲娅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们认为索菲娅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因为她从未将所有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家庭或丈夫,从未失去追求事业的信心。另一方面,她们渴望成为像索菲娅一样的女性,但她们没有勇气改变。
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内心充满了对当下生活的鄙夷,她坚信命运将带她去一个崭新的、公平的、无情的世界”[2]310,与以上女性角色相比,她渴望男女平等,勇于对不公抗争。但由于残酷的现实和扭曲的命运,她以悲剧收场。最后她在孩子的记忆中只是个“不好看,哮喘,癌症,说自己盼着死去”[2]304的母亲,这与曾经的她形成强烈的对比。
索菲娅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和大男子主义传统的反抗者。她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的条条框框,塑造了敢于挑战社会传统的新型女性形象。她有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受制于家庭的束缚。对于世俗的偏见与男性的压迫,她感到气愤但并未放弃抗争,直到成功在大学任教,成为俄国第一位女数学家。
索菲娅不甘心只做男性的附庸,与其他女性形成鲜明的对比,门罗借索菲娅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突出现代女性的与众不同和对传统两性社会价值观的质疑。
门罗通过张扬的女性声音塑造了四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以唤起女性的自觉,让她们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女性话语权,形成叙事权威与主体性。她们彼此之间各不相同。第一类是身心完全服从于男性,如克拉拉和伊利斯。第二类是自相矛盾的妻子们。她们渴望自由,但因为懦弱而并未付诸实际行动改变现状。另一种是阿纽塔,她渴望平等,付诸行动,但以悲剧收场。最后一个是索菲娅。她坚决不做一个温顺脆弱的女性,这一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使女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服务于家庭的工具。她为女性发声,争夺女性话语权,强化叙事权威与主体性。
三、结语
《幸福过了头》是在门罗罹患癌症时期的作品,期间她饱受疾病折磨,使得其身体和精神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她开始重新审视两性关系和婚姻。门罗将此故事作为表达自己对获得幸福的方法和观点的窗口。故事从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女性观点,稳固女性话语权,从而迂回地建立女性叙事权威,突出女性主体性。同时,门罗以精巧的叙事技巧生动地刻画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独特的女性气质,揭示了女性的困境和她们对自由、独立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