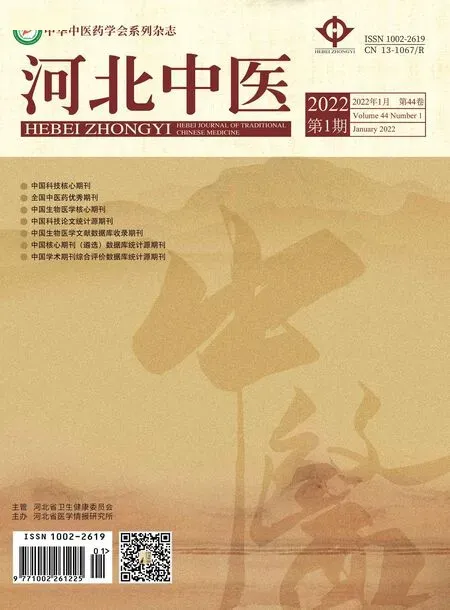范冠杰教授从肝脾论治湿疹经验※
黄锦珠 夏亚情 吴明慧 李安香 卢绮韵△
(1.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广东 东莞 523710;2.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广东 广州 510120)
湿疹是临床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其病因尚未明确,现多认为是由过敏性体质、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多汗、干燥,或接触变应原等诱导产生[1-2],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3个阶段。湿疹全期可伴剧烈瘙痒、皮肤损伤,病程缠绵难愈,症状剧烈,给患者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现代医学一般采用抗组胺药、镇静安定药配合外用糖皮质激素乳膏[3]以抗炎、止痒,缓解患者刻下症状,但常无法根治,极易反复,且长期使用会产生耐药性,远期疗效不佳。中医药治疗湿疹临床疗效显著[4-5],可快速缓解湿疹症状,部分患者可达到根治的效果。
范冠杰,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省级名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指导教授。范教授临证20余载,总结出一种将中医经典理论与中国哲学思维相结合的原创辨治体系—“动-定序贯八法”,在“药对”的基础上提出“药串”概念,形成“症状-证素-核心病机-药串”一体化辨证模式[6]。在该理论指导下,范教授从肝脾论治湿疹,以疏肝、运脾法为基本原则,配合清热利湿、活血化瘀、透表、止痒等法精准治疗,快速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治疗周期明显缩短,效果确切。兹将其从肝脾论治湿疹经验介绍如下。
1 “动-定序贯八法”的理论本质
中医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临床指导作用,但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目前仍未取得突破性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的理论框架仍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普适性[7],无鲜明的理论体系加以整理和优化。针对目前中医面临的窘境,范教授从中医理论框架上突破,运用理论指导临床,在治疗上取得新进展。
1.1 动 “动”指变化,体现一种动态思维,以发展、突破的眼光审视、判断问题,是中医辨证论治基本原则的经典体现。辨证论治是指用各种方法全面分析病症性质、原因及患者情况,做出正确判断,然后根据辨证结果,给予相应治疗[8]。临床中病情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各自的核心病机,从而表现出“证”的不同症状形式,若以独立分开的思维思考疾病所处阶段,不以疾病始终的发展规律把控诊疗过程,单纯以患者的不适为基础遣方用药,滞后于疾病的发展进程,则十分被动,仅缓解刻下症状而无法截断病势,根治疾病,致本末倒置。因此,范教授提出只有运用动态思维,掌握疾病变化规律,辨别疾病所处阶段的核心病机,识别证候本质,才能精准、科学辨证,做到用药有依据、有目的、有疗效,打破“一证到底”“以证治病”的刻板辨证,更加符合中医临床实际。
1.2 定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内涵是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为有机整体,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强调人体、自然、社会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联系性[6]。正如《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动-定序贯八法”提出,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应将人与疾病、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患者的四诊资料中找到核心症状,抓住核心病机,将核心病机的发生发展规律作为诊疗方针,指导临床诊疗,这正是“动-定序贯八法”中“定”的含义,相比传统诊疗思路中按照各证型之主症、次症一一对症、归证论治,则更加科学、准确、清晰、快捷,避免了在四诊资料中左右顾虑,无的放矢,耽误患者病情。
1.3 序贯 正因事物发展是变化的,人与疾病、环境的外在表现必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和转化的内在规律可循,故在辨别分析时不能将每一个事件当作独立个体,切割其中的逻辑联系,于诊疗中像素化疾病,导致病情割裂,顾此失彼,反复发作,缠绵难愈。范教授提出,在临床工作中,仅掌握当下疾病的核心病机和变化趋势,则缺乏连贯有序性,应当注意前后疾病变化的因果关系,有序分析阶段之间的前后联系,贯通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外逻辑,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站在人、疾病、环境的立体思维去考量问题,才能认识到整体联系和运动变化的处处合一,这就是“序贯”的意义。
1.4 八法 八法,取八卦之变化无穷、能生大业[9],范教授临证实践总结认为,以补肾、疏肝、润肺、养心、运脾、理血、调气、和畅三焦共为系统治法,形成“范氏八法”。通过在临床复杂诊疗过程中抓取核心症状,把握疾病核心病机,以八法为经纬,选择合适药串,临证加减,解决患者不适,形成科学有效的“核心症状-核心病机-药串”的临床诊疗模式。广至辨证分析,细至遣方用药,均体现了体系中动定结合、整体序贯的理论思维,突破了传统诊治中的或单病、或单证、或单方思考疾病的局限与不足。
“动-定序贯八法”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活动,根植于中医哲学体系,实践促进了理论的完善,哲学指导着理论的发展。随着实践与哲学的不断发展,“动-定序贯八法”也体现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使其不仅具备普适性,同时具有包容性,可根据临床实践演变出千万个体化治疗方案。
2 基于“动-定序贯八法”理论对湿疹病因病机的认识
湿疹属中医学湿疮范畴,临床症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急性湿疹可发生于全身各个部位,常见于头面部、四肢屈侧、手足背部,皮损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红斑、丘疹、水疱、糜烂、渗出、结痂、脱屑等,并且常伴有明显的瘙痒感及炎性反应;亚急性湿疹的皮损程度较急性期轻,多见丘疹、结痂、鳞屑等,部分可见水疱、糜烂、红肿、疼痛等;慢性湿疹主要是因为急性或亚急性湿疹未规范诊疗,或皮损部位反复发作转变,患处常发生角质化或苔藓样病变,表现出皮肤肥厚粗糙、脱屑、抓痕样条纹明显,且病损部分仍可出现丘疹、水疱、渗液。由于湿疹全期可伴剧烈瘙痒及明显皮肤损伤,常规治疗只能缓解当下症状,导致病情反复发作,病程持久则可出现明显耐药性,继发刺激性皮炎、感染、变态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睡眠、情绪、工作等多方面,导致长期失眠、脾气急躁或抑郁、纳差,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结合湿疹的临床表现和发病规律,范教授治疗湿疹多从肝脾入手,重新解读当代环境下湿疹的普遍病机。
2.1 肝与湿疹 肝脏体阴而用阳,主疏泄,主升,主阳,可调动津液气血,疏畅气机,调节情志。肝失疏泄则气机紊乱,津血输布失常,则不在其位而成邪,故水湿内生,瘀血内阻,气机内陷,久则郁而化热,外溢于肌肤则成局部皮疹、红肿,脉多弦、弦紧或弦滑;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血虚风燥,故见剧烈、反复瘙痒,《丹溪心法》曰“身上虚痒,血不荣于腠理,所以痒也”。患者病情缠绵,症状反复,不适感明显,给生活造成严重不便,致心理负担加重,肝气郁结更甚,反加重湿疹发作,导致恶性循环,进而造成患者继发的长期失眠,女性可伴有月经失调,情绪急躁或抑郁,首诊时常见满面愁容及低落情绪。且现代人们生存、工作压力剧增,影响肝气疏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儒门事亲》曰“愤郁而不得伸,则肝气乘脾,脾气不化,故为留饮”,可见肝病极易累及脾脏,肝气抑郁则横逆克脾,脾胃功能受损,无法升清降浊,水饮不化,聚成湿浊,脾主四肢,故脾虚患者常见四肢皮肤湿疹发作。
2.2 脾与湿疹 湿疹的病理因素多为湿、热、瘀、风、虚、寒等,其中以湿邪为主要因素[10]。湿邪黏腻、停滞、弥漫,脾虚之人易得。脾胃运化有权,可吸收精微物质后转输营养全身,运化受阻则水液输布失调,聚成水邪,浸淫肌肤,发为水疱、渗出;或生成不足,机体失养,致皮损反复难愈。脾虚则纳差,后天生化乏源,然卫气滋于中焦,《灵枢·本脏》谓“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卫气不足则无力防御外邪,易受六淫邪气致湿疹发作,且腠理开阖功能失调,内外湿邪无法从汗液排出,导致湿浊黏滞缠绵。湿疹好发于中老年人[11]或幼儿,这类人群或因长期饮食、生活作息不佳损伤脾胃,或脾胃之气尚不充实,无法正常运化水湿,抵御外邪,导致湿疹发作,故临床诊治中应重视脾胃中焦功能的调理。湿疹病情持久反复,长期影响患者生理、心理健康发展,久则肝气郁滞,疏泄不畅,加重气血津液瘀滞;或肝病反克脾土,损伤脾气,形成恶性循环。
3 基于“动-定序贯八法”理论从肝脾论治湿疹
3.1 疏肝运脾治法及其药串 范教授指出,湿疹虽是在皮之病,但实际是人体脏腑气血津液失调的外在表现,《丹溪心法·能合脉色可以万全》谓“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结合湿疹的发病特点及当今自然、社会的环境特点,范教授认为湿疹的核心病机为肝郁脾虚,治疗应紧抓疏肝运脾大法,运用核心药串,解决主要矛盾,这也是“动-定序贯八法”治疗湿疹中“定”的体现。
范教授疏肝药串包括柴胡5~15 g、白芍10~30 g、薄荷5~10 g、郁金10~20 g,药串搭配严谨,可用于各种肝郁类疾病。其中柴胡、白芍为核心药对,柴胡主疏肝解郁,白芍主柔肝养血,二者互相配伍,可谓一刚一柔,一散一收,可防柴胡伤阴太过,免白芍收敛留邪,使肝气条达,血行通畅,减轻皮肤损伤处的红肿、炎症、感染等,缓解患者长期紧张情绪。薄荷性凉,味辛,《本草新编》指出薄荷“尤能解忧郁”。现代药理研究也证明,薄荷除可兴奋神经中枢,还具有抗炎镇痛、抗病毒、促渗透等药理作用[12],于疏肝药串中可增强柴胡疏泄之功[13],使辛散之力通行内外,同时达到疏风清热、发散透疹作用。郁金性寒,味辛、苦,入肝经,有活血行气、清心解郁、调和营卫功效,患者若见皮损处红肿、淤滞、糜烂,伴月经不调、胸脘痞闷等肝郁血瘀症状时,可根据症状轻重加减运用。
针对脾虚患者,范教授常用运脾药串党参10~15 g、茯苓10~15 g、白术10~30 g、黄芪10~30 g、半夏10~15 g、神曲10~30 g扶脾益气。由于岭南地区以潮湿多雨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该地区人群常伴有明显脾虚夹湿证,药串中党参、白术、茯苓取四君子汤之意,以助脾胃受纳及健运,益气除湿。四君子汤温补缓调的药性既符合脾脏的生理病理特点,也能避免于方药中喧宾夺主,减弱攻邪之势。卫气靠脾胃消化水谷而不断生成,脾虚则卫气不固,风、湿、热等外邪易侵袭机体,邪气伤正,可引起湿疹发作,而卫气不足,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功能下降,则皮损反复难愈。因此,范教授常用黄芪托里气,实卫气,补脾扶正固表,托毒生肌,从内截断病势,且防止攻伐之势太过,误伤正气。岭南地区患者可用岭南特色药物五指毛桃健脾补肺,行气利湿,“气化则湿亦化”。若患者脾虚湿甚见痰多色白、胸闷痞满、舌体胖大水滑,则以半夏、薏苡仁燥湿化痰;若兼见口气重、反酸、便溏,则以神曲、山楂、布渣叶健脾和胃,消积化食。
3.2 清热利湿治法及其药串 通过长期临床观察,范教授认为湿疹病程中,常有湿、热二邪伴随致病。湿、热平衡失调是导致湿疹发作的主要因素,在急性期尤为明显。素体脾湿之人,复感湿热外邪,胶着于肌肤不去,久则蕴毒,闭合腠理,阻滞气机,折损阴阳。“动-定序贯八法”理论指导下的用药重视人体与疾病、整体与局部、标与本的辨证关系,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清热利湿药串苍术10~15 g、黄柏5~20 g、薏苡仁10~30 g、茵陈10~30 g、车前草10~30 g,并配合临床加减化裁。黄柏苦甚主降,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使湿热之邪从下焦泻下,皮肤渗出明显者可用。茵陈性寒、平,味苦,清热利湿,宣湿开郁,但其“苦寒”之性并非大苦大寒,多数舌苔厚腻患者使用大量茵陈后,舌象可明显好转而无纳差、畏寒、神疲乏力等虚寒表现,其原因或许与全球环境变暖使当今茵陈苦寒之性下降有关。苍术、薏苡仁均入脾、胃二经,可健脾燥湿,除生湿之源,同时清除湿中郁热,有二妙丸之意,配伍车前草可引内湿从小便化去,使邪有出路。
3.3 活血化瘀治法及其药串 脾主统血,肝主藏血,肝脾二脏失常则易耗血伤血,肌肤失养,虚则萎陷,寒则收聚,瘀则凝滞,久则失其鲜华,则见皮损干燥增厚、颜色紫黯、淤斑等症状[14],血虚生风生燥,则见瘙痒、皮肤脱屑、结痂等。李梴在《医学入门》指出“人皆知百病生于气,而不知血为百病之始也。凡寒热、疼痛、蜷挛、痹痛、瘾疹、瘙痒……皆血病也”。可见理血法治疗湿疹的重要性。故范教授采用活血化瘀药串丹参15~30 g,赤芍10~30 g,三棱10~30 g,莪术10~30 g。丹参破瘀血,补新血,赤芍行而不留,主破血,三棱、莪术行气活血。对于活血化瘀药串在活血与破血之间的权衡转换,范教授于剂量把握十分严谨。血瘀重症,常用大剂量、多药串配伍大势破瘀,通贯经脉,使气血流畅,运行得道;血瘀轻症,则小剂量以活血为主,载气运行。若血瘀明显见月经夹血块,舌质紫黯、舌下静脉迂曲,或舌体见瘀斑,可加紫草、红花、川芎;皮损处肥厚、瘙痒、脱屑,可加当归、川芎;血热之证,加生地黄、玄参。
3.4 透表止痒治法及其药串 《灵枢·刺节真邪》曰“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人体正气虚衰,肺卫不固,天地时运变化则易感受外邪之风、湿、热、毒邪,侵袭皮肤以化生红疹、渗液、鳞屑、糜烂等病理产物和产生炎性反应,故治疗湿疹时注意引邪外出。邪自皮毛而来当从此而去,须开肺气,宣表闭,祛邪外出,避免病邪缠绵。麻黄、桂枝同味同经,主宣肺开闭,范教授常于皮肤性疾病中用麻黄、桂枝揭上肺之盖,开腠理,流畅气化。湿疹发作常由外湿侵入皮肤引动内湿,内外湿困合而为患,运用麻黄、桂枝宣发腠理,则外湿从汗而去,所谓善治者治皮毛。外湿常与内湿交合,导致内外湿困,风、热、瘀等病理产物包裹其中,导致瘙痒、红肿、感染、黄水淋漓等症状剧烈且持久难去,范教授常用透表止痒药串白鲜皮10~30 g、地肤子10~30 g、土茯苓10~30 g。白鲜皮、地肤子作为治疗皮肤疾病的经典药对,协同作用,加强清热祛湿、解毒止痒、利水之力。土茯苓又名土萆薢,《本草汇编》谓“土萆薢甘淡而平,能去脾湿,湿去则营卫从而筋脉柔,肌肉实而拘挛痈漏愈矣”。三药配伍,相须为用,疗效显著。若见皮损处生脓、破溃,舌紫红,加蒲公英、连翘、野菊花清热解毒;邪扰心神出现失眠、烦躁,加首乌藤、莲子心助眠安神;若邪伤肺胃出现口干苦、大便秘结,加石膏、葛根、知母清肺胃热毒。此外,范教授常建议患者在内服之余,煎药第2次取汁外洗湿疹处,内外同治。
动态思维是“动-定序贯八法”体系的重要理论之一。人处于环境之中,环境的温凉寒热、四季转化、社会发展等都会影响机体状态,进而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由于病情动态变化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临床诊治很难面面俱到,因此要抓住核心病机,使用核心药串,再根据兼症轻重加减用药,做到证随病变,药随症变,构建精准有效的“症状-证素-核心病机-药串”诊疗模型。“动-定序贯八法”从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出发,结合疾病发展特点及当代自然、社会环境,总结出湿疹的诊疗应当从肝脾入手,以疏肝运脾法为基准,配合清热利湿、活血化瘀、透表止痒精准治疗。
4 典型病例
詹某,男,22岁。2019-08-07初诊。主诉:反复全身至头面红斑、丘疹2年余,加重1月余。现病史:患者2017年1月起无明显诱因出现全身至头面红斑,丘疹,伴严重瘙痒,使用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服用多种抗变态反应药物及外用止痒乳膏、洗剂,症状时轻时重,反复难愈。既往哮喘病史,近期未发作,对鱼腥草、双黄连过敏。刻诊:全身散在红斑,头面部尤甚,瘙痒剧烈,伴搔抓后抓痕、血痂,多处有淡黄色浆液渗出,部分表面附着白色鳞屑,易剥脱,平素易疲倦,情绪低落,不喜与人交流,纳眠差,小便色黄,大便2~3 d一行。舌淡红,苔微腻,脉弦细。西医诊断:湿疹样皮炎。中医诊断:湿疮。辨证为肝郁脾虚,湿热浸淫。治宜疏肝健脾,清热利湿。药物组成:连翘30 g,柴胡5 g,地肤子30 g,白鲜皮30 g,薄荷(后下)5 g,牡丹皮30 g,桂枝10 g,金银花30 g,土茯苓30 g,甘草5 g,生地黄30 g,白术30 g,赤芍30 g,丹参30 g,麻黄5 g,白芍15 g。日1剂,水煎取汁2000 mL频饮,煎药第2次取汁外洗湿疹处,避免进食辛辣、刺激性食物。14剂。2019-08-20二诊,患者瘙痒减轻大半,红斑、鳞屑明显减少,新疹未见再生,部分红疹消退可见正常肤色,患者情绪明显改善,稍露喜色,问诊时描述较前详细。纳眠差,小便色黄,大便溏烂,每日2~3次。舌淡红,苔微腻,脉弦细。初诊方加野菊花15 g,煎服法同前,14剂。2019-09-03三诊,患者红疹、渗出消失,露出大片正常肌肤,鳞屑较前增加,脱落处可见正常皮肤,少许瘙痒,全身抓痕、血痂减退,纳眠好转,二便调。患者情绪改善,面露喜色,乐于交谈。继守二诊方,煎服法同前,每15 d复诊。2019-11-02末诊,患者红疹、鳞屑基本消失,唯劳累时少许瘙痒,后可自行消退。
按:本例结合患者临床表现,“湿疹”诊断明确。由患者既往哮喘病史及对药物有过敏史可知,患者自幼体虚,复感外界风、湿、热邪,留恋肌肤化为湿疹,伴剧烈瘙痒。严重不适与皮肤外观改变使患者情绪低落,肝郁气滞,故患者沉默寡言。内湿生发于脾虚,故淡黄色浆液渗出,为脾土本色。长期使用激素攻伐外邪反致内虚加重,无力祛邪外出。久病耗血伤津,又后天气血生化乏源,故见皮肤干燥、鳞屑满布。虚、实、表、里合而为病,仅以清热利湿、健脾祛湿或活血化瘀单独为法,无法顾及全局,难以根治。范教授以疏肝健脾为基本治法,方中柴胡、白芍、薄荷疏解肝郁,宣发木气,木气得升,则气机得运。白术、甘草健脾益气祛湿。兼以清热利湿,以土茯苓、金银花、连翘清热、利湿、解毒,以大量药物增强攻伐之势得到覆杯而愈之效,增强患者信心,配合重剂赤芍、牡丹皮、丹参活血化瘀,清血分郁热,生地黄走血分以凉血养血,使内外湿热之邪大减。麻黄、桂枝宣发腠理,地肤子、白鲜皮祛风止痒,清热解毒。患者二诊时红斑、瘙痒等湿疹症状明显减轻,情绪好转,辨证论治得法,故守前法,加野菊花乘胜追击,清除残余热毒。
5 结语
湿疹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皮肤性疾病,其现代医学病理机制复杂,目前以抗炎、止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往往无法根治疾病,病程缠绵,症状反复。范教授认为,中医药治疗湿疹有一定优势,其运用“动-定序贯八法”,从肝脾论治,以疏肝运脾法为基准,配合清热利湿、活血化瘀、透表止痒精准治疗,用药简洁有序,配伍得法,快速缓解患者红斑、丘疹、水疱、糜烂、渗出、结痂、脱屑等皮损症状,部分患者甚至达到根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