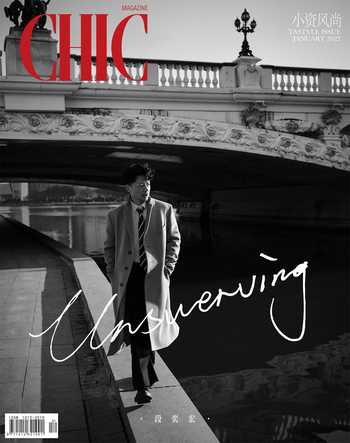以瞬息的光
徐絮 黄也






刘佳玉:难以预知的虚拟
一条穿过长城的小溪要如何流经泰晤士河,北京西山的天际流云要如何飘进曼城古老的维多利亚建筑里,冰岛的秋景要如何和三亚的热带植物共生……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奇思妙想其实皆源于青年新媒体艺术家刘佳玉的作品,在实地勘探、数据收集、实时渲染、数字投影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这些遥遥相隔的空间和迥然不同的景象,在一片荧荧蓝光中完成了蒙太奇式的拼贴和碰撞。
编程、数据、人工智能和蓝色灯光,提到这些名词人们总会联想到“理性”、“冷静”,充满科技感的新媒体艺术在人们看来总是“冷色调”的,而刘佳玉用它们来表现水流、花卉、天空、风等自然元素,冷色调中亦蕴藏着诗意。最初刘佳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众多作品都是蓝色的,她认为艺术的表达和人的感知一样,都是在自然而然中发生的。作家以文字感知世界、表达世界,而她用灯光和装置,不过是各有各的方式而已。
“经常有人问我:某个作品的灵感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的灯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装置……但其实我的作品往往没有一个具象的灵感来源,一切都是来源于生活本身,是我对生活自然而然的反馈。”艺术表达也会受到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她的作品中之所以展现出国画晕染的效果,是源于小时候学过国画、练过书法衍生出的感受,“画国画时我们会知道哪一笔要多沾点水,在我创作作品的时候我也知道自己更希望投影影像在软件制作时就需要拥有一些朦胧感,像会呼吸的气泡,这是我所欣赏的美。”
刘佳玉的作品并不都是冷色调的作品,她也不执著于以最新的科技为载体进行创作。在《菜市场和弦》/HappyRecipe 展览的现场,刘佳玉以明亮的空间与鲜艳的瓜果重塑了市井生活的面貌,互动者只需要像在菜市场里挑选那样,拍拍西瓜,掂掂苹果,就能把动作转化成有趣的音符。她说,“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些作品即便科技感很强,但依然是我的情感表达。我用灯光、用投影去呈现一个作品时,它们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技术,它们的存在是这份情感表达的组成部分。”
在作品《小溪》/The Riverside中,刘佳玉和团队对一条流经长城的小溪进行了河床3D扫描并复刻出长8米、宽3.5米的混凝土模型,从“河床”上流过的灵动“溪水”是由实时数据进行流体模拟得来的,快速运动的灯光粒子投影在模型上,奇幻而生动。特别的是,投影数据中嵌入了北京上空太阳和月亮的实时位置,这使得流淌的溪水有了变幻的波光,映现出日光照在水面的粼粼和月光摇晃的倒影,刘佳玉解释道:“自然界中最打动我的是影子,它证明了光的存在,也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水波之上呈现的倒影去感受时间的流转。虚拟世界里的光会随着真实世界的光不断变幻,我尝试着在作品中感知光、模拟光、控制光,然后让我创造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更多联结,而这些联结也引导着人们透视自然最本真的力量。”
作为一个新媒体艺术家,不管是对投影灯光还是对自然中的光,刘佳玉都有着双重的认知,并游走其间。就拿《小溪》/The Riverside来说,变幻的波光其实只是与日月的定位坐标公式有关,客观规律上讲每天的太阳只比前一天晚一分多钟,看似没有规律的变化其实和严谨的科学密不可分。但即便已经用软件模拟出了灯光和投影的效果图,最终所看到的呈现效果依然会让刘佳玉十分惊喜,“最难模拟,甚至不能模拟的就是光,它是你无法捕捉、无法预测的东西。这是光最吸引我的地方,效果图模拟出来的光束和影子,我脑海里想象的最终效果,这两者与现场永远不一样,因为此时的光是真正自然而然地散发的,永远可以带来新鲜感,永远可以带来令人激动的惊喜,正是光的这种特质在激发着人类的探索。”
光所带来的双重感受同样也是刘佳玉在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感受——既能用技术控制却又无法完全预知,它像某种介质,始终给人以介乎于两端之间的奇特体验,这种无法比拟和形容的未知性,是令艺术家们不断创作、不断探索的强大动力所在。
CHICX刘佳玉
CHIC:作品《菜市场和弦》/Happy Recipe 的风格和其他风格特别不一样,它的创作故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刘佳玉:其实在做这个作品之前,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再做过互动的作品了。在大众的认知里,互动性就是真的要做点儿什么动作才叫互动,但是其实你观赏一个作品的时候,人的感知和思考也是一种内在的互动。我希望在创作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很多时候一个必须做点儿什么动作产生的互动并不是必要的。
不过在这个菜市场的环境中,拍拍西瓜这些动作都是很自然的行为,当时我还特意选了几个方言比较特别的地方的菜市场去采集一些实际的录音,再把录音转换成音乐。我想通过作品传达的,就是在新媒体艺术的时代,艺术是触手可及的,是社会的,是公众的。就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菜市场里,人是不分阶层的,每个人各司其职。艺术也一样,它应该更具包容性。
CHIC:2018年的时候你曾说“艺术家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享受孤独”,现在呢?
刘佳玉:当时我的认知确实是这样,不过现在已经变了,我觉得这也是多年创作所带给我的改变吧,我自己的作品在不断变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是在变化的。2018年,让我产生这些感受的那段时间,我都一个人在伦敦,一个人默默地做创作,有技术需要的时候才去联系技术团队,所以我觉得艺术创作本该是孤独的。
但是我回国后开始创作《逆流而上》/ In the Flow这样一个体量非常大的作品,我开始需要和团队有更多的碰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整个幕后团队大概有30多个人。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新媒体艺术的更多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团队创作,你会感觉到团队创作的巨大能量。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艺术家最需要具備的特质其实是协作,同时也有热爱。当面对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时,遇到了问题,你不会觉得这是困难和挑战,你脑海里想到的一定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CHIC:灯光装置类的新媒体艺术在白天呈现时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对此你有些什么想法和尝试呢?
刘佳玉: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近几年才有的,这也是新媒体艺术诞生和发展势必会带来的矛盾性讨论。在新媒体艺术出现以前,人们不会去考虑一幅油画晚上要怎么观赏,城市里的雕塑如果晚上需要灯光,只要加两个灯就可以了。但是有了新媒体艺术或者数字艺术之后,人们会希望这个灯光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可以变色、感应、互动等等,进而希望灯光装置白天也同样具备观赏性。
其实最早关于新媒体艺术的两极化讨论是从“White Cube”(画廊和博物馆空间)与“Black Box”(除此之外的数字、物理空间)开始的,是关于艺术作品是否需要依托墙去呈现的讨论。2015年teamLab进入中国在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推动作用,让公众认识和认可了我热爱多年的这个领域,而现在这种灯光艺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公众已经有了广泛的接受度,人们对它的期待也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发展,事物的发展阶段都是彼此相连的,所以也促使着艺术家们去探寻下一个阶段。不过关于灯光装置在白天的观赏性这个问题,不光需要艺术家去努力,应该是这个领域中的各方要去共同面对、协作解决的。
CHIC:今年6月,你用约5000个废弃塑料瓶和渲染出的粒子动态海洋动画创作了《塑形》/Shape of Plastic,以唤醒公众对人与自然共生问题的关注。你在可持续理念上的思考是否延续到了后来的创作中?
刘佳玉:在最近的创作上,我们更多地在寻找新媒体艺术与可持续理念之间的不同可能性。
9月接到Adidasby StellaMcCartney和UCCA Lab的联合邀请,我创作了作品《造形》/Shape ofWeave,这也是6月与adidas合作作品《塑形》/Shape of Plastic的延续。这个作品中我尝试以品牌提供的回收旧衣作为原材料,融合环保树脂制作成岩石般的投影映射媒介,粒子动态图形展现的流动地表景观象征着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环之力。
9月底、10月初我们又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环资委、绿色纺织界、时尚造物、上海新天地共同发起了丹宁旧衣回收计划,我们使用该计划回收的旧衣铆钉、牛仔纱线,与竹子、清水混凝土相结合,在夜晚融入投影映射的蓝色水波纹,创作了作品《竹谷河鸣》/Natural Concerto,这个作品分为母体和子体两个部分,母体在10月期间呈现在上海新天地广场,而子体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专题影片的拍摄。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以“可持续时尚”为议题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作品,呼吁公众认可、接纳、推崇“可持续时尚”。
以及最近,在“爱的艺术”影像艺术展展出期间,我们受邀利用兰蔻品牌回收的产品空瓶创作出作品《与生之花》/Grow in Love,经过再塑造的空瓶展现出生长于岩体雕塑表层的花的姿态,将人与自然、消费与环保、循环与艺术以“重生”的概念结合了起来。
黄喆:向深层意识的行动
绚丽的色彩,入心的思索,在无量的瞬息中探知自我的边界,这是艺术家黄喆的个展“光入变”带来的观感。他对地质学、天文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关注,给其创作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光晕。“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高效和速度的环境中,追求即时性,这很容易产生焦虑,而专注于对地质学、天文学、考古学等的浅显研究,将获得的感受融入到作品中去,是一种回望的方式。它们的生成与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叠加的、不断探索的过程,这如同我回望自己对艺术与对生活的理解,也是我面对当下的补充,我用作品说出面对当下的感受。”
回望是一段漫长且深邃的历程,无形之中造就了一个难以形容的能量场,如同置身于“光入变”的展览现场,那种色彩与形式、虚空与存在、时间的流变与光线的变幻······无一不在呼唤回望自身的渴求,有对“我是谁”这一人生命题的求索。置身虚空之境带来的生命沉思,会触发人对时代的语境、自身的历程以及精神的追求等人生主题的质询,是向深层意识而前进的行动。“光入变”试图触发一种深渊式的共鸣,从而回归当下——“正入变出”。
一个展览或许是一个微小的存在,但一个展览背后的一切则是一个庞大的存在。早在七八年前黄喆就开始了“与光同行”的创作。初期的创作中,他专注于“图像的消解,光与图像的关系”,但随着创作的深入,光与材料本身所产生的力量让他更为着迷,于是“对材料的研究与感受”也成了他整个创作中不断深入探索与反复实践的主要内容。“光原本就有着独特的语言魅力与丰富性,让我更加专注于在创作中反复对材料的实验与实践去体现光的变化对我感受的引领。”从研究到更新,感受到体现,经“时间的线索”这一牵引点,他在创作上的表达有了更多重的呈现。
黄喆“追光”的创作经历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且持续更新的状态,随实验和实践的增多会生长出新的生命力。“有了限制才给予了我更多的自由,在这种‘追光’式的对材料语境的探索中,我获得了更多运用的自由度和可能性,从早期散射效果对图像的消解到近期以光为主的语言并置,都是一次次感受上的更新,同时希望建立一个对应的视觉语境。”顺自然之光,变化无处不在,奇异的发现便会应运而生,这是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获得,也是观看者在观看中经受的启示,微妙但确切。
CHICX黄喆
CHIC:你早前说过一句话“在我的创作当中,有一种关于时间的线索——一种时间对于材料和叙事的影响。时间、文化、历史,可以说一切事物都对材料自身产生影响。”那是否可以理解为“时间”是你的创作主线之一?
黄喆:时间的线索是我创作中的一个牵引点,而不能说是创作的主线,我由时间引发出对各个领域的探索冲动。如果要叙述创作主线的话,现在可能是多条主线并存的方式在进行,同时他们又互相影响,如关系的转化、力的变迁等,他们同时都是由时间所引发的。对材料的研究与感受,是我整个创作中不断需要深入探索与反复实践的。
CHIC:你创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重复、研磨、雕琢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那处于这种相对来说是繁复的无限循环的创作过程,你的观看的方式更接近于怎样一种状态?
黄喆:正如林叶老师在展览评论中说到:“这既是一种观看行为、也是经验时间的行为、同时也是生活的行为。人们可以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不断制作、重制、拆解观看的概念、时间的概念以及生活的概念。”那么我的创作是在时间的叠加中寻找痕迹,消解当下生活的焦虑,创作让我经验着时间,同时也理解着生活。
CHIC:“光入变”的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大地中的感知”、“宇宙中的星云”、“自我的边界”,分别又对应着大地、星空与自身,凝视、仰视与自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最终呈现,那关于创作阐述以及命名你是遵循着怎样的方式?
黄喆:展览中,这三个板块是相互关联的,如同我们抽身于繁忙,面对自己时,提出:“我是谁”这一古老问题后的思考与感受,思考我们与信仰、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摆脱虚无的困境。围绕这样的思考路径,与其相左的都会删除。
CHIC:光作为观看你作品的元素,不同角度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形、光、色彩是最直观的视觉呈现,很奇幻也很神秘,再深入的看有你对历史、时间、思维、宇宙、自我等内在的事物的探究,既有具象也有抽象的表达,你是如何中和的?
黄喆:就如同理想与爱情,它既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晚霞、雨声、一口甜品的滋味,它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那些激起你创作冲动的灵感,是内化后最终呈现在作品中的,这并不是一个如化学实验中的调配方法,而是一瞬间动人的可能性。
CHIC:艺术家的作品大多都是被放置在特定的展出空间,有一定的规划和布局,你有想过你的作品其实还可以被放置在哪里,会有不一样的艺术呈现?你理想中的展出你作品的场景是怎样的?
黃喆:对于放置作品的场地,越多的可能性,意味着越多的挑战与对材料运用的突破,我想勇于突破是一个艺术家应一直保留的信念,所以在我心中,没有固化的理想展示场景,而是一直需要去寻求能够赋予作品以更多生命力的空间。
- 小资CHIC!ELEGANCE的其它文章
- 淹没在透明的金色光芒里
- 间隙
- 迹象
- 文字投影下的光照图景
-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带温度的幸福画家
- 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