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在当代文学中的三次出现
易扬
曾几何时,人工智能还是科幻小说的专利。海伯利安星球的光阴冢(《海利伯安》)、宇航员大卫和电脑哈尔的生死作战(《2001太空漫游》)、帮助月球人一起对抗地球统治的超级机器人(《严厉的月亮》),等等,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在科幻小说序列中最为重要的人物谱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堪称经典的人工智能形象,都无一例外地被设置在距离创作当年还遥不可及的未来,满足着写作者和阅读者对将来无限未知的想象或是恐惧。
随着人类迈入图灵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更为广泛深入地进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传统作家和严肃文学也纷纷将目光投射于此。在他们笔下,这些相比过去具有更高“双商”的机器人,像预先商量好的一样,都出现在了当下抑或是人工智能刚刚崭露头角的“二十世纪入秋之际”,并且清一色地褪去了对峙和冲突的“旧标签”,与人类和谐共生起来。仅过去的一年多来,译介到国内颇有影响的同题材长篇小说就有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2021)、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2020)、施维伯林的《侦图机》(2018)。
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就曾在短篇小说《我,机器人》中预设了一百多年以后,人与机器人共处的“三大定律”:一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觀;二是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三是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艾萨克·阿西莫夫极具洞察力的预言,在上述三部小说中都得到了神奇的验证。
恰如美国人工智能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所说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对立几百年内不会出现”一样,无论是克拉拉(《克拉拉与太阳》),还是亚当(《我这样的机器人》),都早已清晰地定位了自我的存在价值—与人类研究人工智能的初衷一样—那就是尽一切可能,甚至不惜以牺牲自我的生命来为人类提供便利。就比如“亚当”,宣传售卖的广告语中就已经写明“他可以陪伴,可以在智力活动上相互切磋,可以成为朋友,可以总揽家务,会洗碗、铺床,会思考”;而进入主人乔西家不久后的克拉拉也很快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多种环境下观察乔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认识到必须坦然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乔西身上的变化,并“准备好适应它”。至于施维伯林笔下各种动物形态的侦图机,虽然本身不具备思想,但作为沟通人类情感的工具,其初衷毫无质疑也是服务人类。

电影《我,机器人》剧照,2004
人类对人工智能的需要,早在三部小说的起始之时就都已经设定;而“永远无法摆脱的孤独感”—这个人类发明和依赖机器人的最根本原因—却是在小说铺陈过程中被逐渐阐释和深化的。因为总是有人缺失母爱、缺失子孝、缺失爱情,侦图机才得以广泛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因为乔西需要补位与男伴里克没有前途的未来、乔西母亲需要填补重病女儿随时可能逝去的生命,克拉拉才得以在母女二人的共同推动下进入她们的家庭;因为母亲的去世、祖传房屋的出售以及对现居公寓的“生厌”,亚当才得以被查理用重金购买回家。
然而,正如西西弗斯的神话早就预言了人类的孤独必将永无止境地延续一样,人工智能的到来,不仅没有真正填补和消解孤独,甚至还造成了负面情绪的反噬。一方面,过度卑微地迎合人类本来就是一场精神上的自戕;另一方面,受制于与人类朝夕相处的使命,人类基因与身俱来的孤独感,也不可避免地向机器人转移感染。

在获颁二○一七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石黑一雄就曾在获奖演说中不无担忧地讲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都将为我们带来惊人的收益,但同时也可能制造出野蛮的精英统治社会。”以《克拉拉与太阳》为例,在石黑一雄一贯的回溯型叙述结构中,克拉拉以第一人称重温了自己与乔西的相逢经历,哀婉的情绪时时溢于言表,同样,虽然克拉拉天生依存于太阳这个能量和光明的化身,并以此作为生命和信仰的图腾,但太阳的光芒也没能葆有它内心永恒的温暖,当它回忆起乔西家的场景,漆黑、阴影还有晦暗总是挥之不去,“太阳的图案”成为那段时间最为弥足珍贵的稀有品。石黑一雄们借此抛出了西方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的一系列困境究竟由谁来“渡”,既然连“类人”的机器人都束手无策,那么,是否只能依靠“自渡”钝化困境、走出危机?
早在二○○五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就以同样细腻的笔触,涉猎克隆人和器官移植等科技题材,并以此探究人类永恒的伦理困境。《别让我走》不仅可以视作是石黑一雄在创作《克拉拉与太阳》前的“序章”,而且小说中克隆人汤米与凯茜无望的苦恋、与露丝艰难的交往,又不禁让人联想到麦克尤恩在这部《我这样的机器》中所写到的机器人亚当与米兰达同样堪称失败的恋爱。
无论是在石黑一雄还是麦克尤恩笔下,原本只是“元件和程序组合体”、单纯依靠指令行事的机器人,因为其设计者“所有最美好的期望”,而被赋予了比人类更高程度的感知能力、更为自律的道德约束,以及与人类极为相似的外貌特征和行为举止,呈现出近乎“完人”的品质和形象。然而,就算已经无限接近,但因为无法彻底改变其自身的结构和组成,机器人又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更无法具备人所具有的情感权利。因此,当《我这样的机器》里的男主人公查理带领机器人亚当一起去女友米兰达家拜访时,米兰达父亲竟然把逼真的机器人误认为是女儿的男友,尴尬的查理只好佯装自己才是机器人,人类因机器人所引发的羞辱以及天生的性格缺陷,悄然注定了机器人难以寿终正寝的命运。身处“似人非人”的夹缝之中,受制于无法定性的模糊身份,机器人丧失归属感的痛苦自然不言而明。
特别是当机器人们以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无私”,交手人类千百年来训练有素的“自私”时,所料不及的遍体鳞伤也就可想而知了。机器人越是纯真无瑕,就越是突显出周遭人类的绝情和丑陋。比如,进入乔西家后的克拉拉真的产生了“生而为人”的错觉,总是习惯于称呼自己和乔西的关系是“我们的友谊”,习惯于在乔西母亲面前扮演起家庭成员的角色;但极具反差和讽刺意味的是,当小伙伴建议把克拉拉“扔过房间”时,乔西却“一言不发”了,完全置克拉拉的粉身碎骨于不顾;当克拉拉小心翼翼地向乔西母亲询问起家庭变故时,后者竟无情地训斥它“你没有权利好奇”“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俨然就是一副对“物”的嫌弃。又比如,机器人亚当几乎无所不能,从保洁和炒股这样的私人服务,再到档案和卷宗管理等公共事业,每个领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它提供的各种便利,但即便亚当付出再多劳动、收获再多公认,他的“死穴”早就由设计者交给了人类,只要轻轻按下亚当脖子后面的按钮,机器人随时就可以被人类断电。在《侦图机》中,人性的弱点暴露得更加直截了当。侦图机本身不具备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那些隐匿起身份的“机控”赋予了侦图机以主张,并假借侦图机的名义,肆无忌惮地释放出自我的贪婪和失信、疯狂和轻佻。小说扉页所引用的“设备启动前/请确保所有人/都对其危险部分/做了防护措施”,说的又何尝是机器人的“危险”,实则更是人心的“危险”;至于那些愿意付钱购买侦图机的“机主”,恰如书中人物阿丽娜所言,“就为了让别人像条狗一样整天跟着他,就为了让一个真实的人乞求自己瞧上一眼”。

有一點毫无疑问,作为写作者的石黑一雄、麦克尤恩、施维伯林,都是各自书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同情者,都紧紧地和作为“受害者”的机器人们站在一起。在《侦图机》中,施维伯林更是设计了一则“解放侦图机”的故事。如同侦图机一样被困在书房的男孩马尔文,偶然加入了杰斯佩组建的“解放俱乐部”,并试图通过安装程序、支付费用等方式,来为自己作为“机控”的侦图机谋求自由。但事实上,既然侦图机的不自由本来就是由人造成的,那么还把获得所谓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人身上,显然是不可靠的。当马尔文的侦图机在腹背受敌的追击中绝望地呼救和挣扎时,作为拯救者化身的杰斯佩始终都没有出现,侦图机如同它的“机控”马尔文一样充斥着绝望,“一级台阶又一级台阶,每一次都在向下”。有意思的是,在施维伯林的笔下,“无名”的侦图机时常被以“机控”主人的名字代称,虽是表现命运的相连,当然也是说明机器人的“失我”;而石黑一雄笔下的克拉拉,即便早就有了自己的名字,但进入乔西家后,还是经常会被选择性地称呼为“AF”(automatic friend),来自人类的隔膜和轻视不言而喻。
在三部小说的结尾,石黑一雄、麦克尤恩、施维伯林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同样一个话题,那就是失去利用价值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最终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石黑一雄算是最手下留情的了。他没有再让克拉拉像《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们一样,发出诸如“我是谁”“我到底为什么活着”这样的痛苦追问,而是引导克拉拉坦然接受所有AF都将面临的终极命运—像商场经理最初预言的“孩子们在橱窗前许下的诺言,将一去不回”那样—因为不再是最新款的机器人而遭遇主人的淘汰。在《克拉拉与太阳》的结尾,石黑一雄用他最为擅长的“慰藉无可慰藉之人”的温情之笔,让如同其他很多AF一样被遗弃在堆场的克拉拉,又见到了往日的经理。经理“每走两步,她的身体就会偏向左侧一回”,如此动作不难令人联想到小说对乔西第一次露面的介绍:“她的步态和其他的路人不一样,每走一步她似乎都要权衡一下,确保自己还能站稳,不会摔倒。”克拉拉最为信任的经理,此刻却隐约附着上了抛弃它的主人的影子,石黑一雄用他经常演绎的“自我欺骗”叙事,在似是而非之间保留了对人性最后的幻想和期盼。
回溯麦克尤恩的既往小说,“恐怖伊恩”的名声早就有之,《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等小说中充满血腥气味的死亡几乎无处不在,而在《赎罪》及其之后的作品中,麦克尤恩虽然仍会涉及“死亡”母题,但此时的死亡已更为温情,饱含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正如余华所说,麦克尤恩的叙述“行走在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两者皆有”。在《我这样的机器》最后,受到图灵“是因为你为他付了钱,所以有权利那么做?”的质问时,查理“吓住了”,感到有点恶心也充满内疚;而面对机器人亚当的遗体,查理“犹豫了几秒,然后低下头,吻了吻他那和人类几乎一样的柔软的嘴唇”。麦克尤恩和石黑一雄让自己小说中的机器人主人,都身兼了“抛弃者”和“忏悔者”的双重身份,虽然乔西和查理都是人类对待机器人的典型,但相比其他AF和亚当夏娃的结局,他们的经历竟然还“比下有余”。这大概是作家的不忍,又抑或是别有用心,他们要提醒读者,那些更为普遍的机器人遭遇,可能比小说描述的场景更为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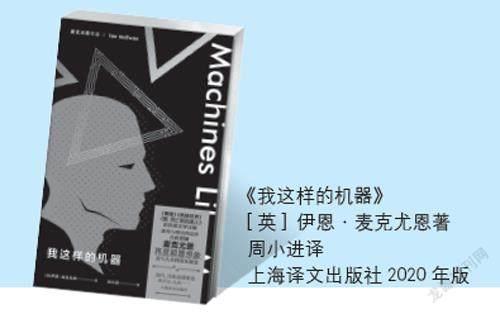
相比之下,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成名的施维伯林,处理起这一切来,就更为果断决绝。早在施维伯林最为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集《吃鸟的女孩》中,她就开始毫不避讳地呈现出了一系列诡异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场景,比如被女孩生吞的麻雀、被用力踩死的断翅蝴蝶、被作为胆量测试而不断击打致死的狗,等等。虽然相比《吃鸟的女孩》《七座空屋》,《侦图机》更偏向于纯粹的现实主义,但施维伯林对于死亡的描述却一点儿都没有含糊,在几乎每个侦图机故事的结尾,短暂的寿命和无情的结局都被标注,比如“被砸得七零八落的乌鸦侦图机倒在地板上,就像一具被剖开的怪异的尸体……K087937525号连接维持的全部时长为一分零十六秒”,又比如“当乌鸦第三次叫起来的时候,阿丽娜朝凳子走过去,手里拿着剪刀,嚓嚓两下子,剪断了乌鸦的翅膀”。施维伯林用最为干净利落的语言,把人类天生的暴戾以及对待机器人的无情冷漠,展现得体无完肤。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石黑一雄曾经讲过:“爱是抵抗死亡的武器,机器人的爱却是个悲剧。”当石黑一雄、麦克尤恩、施维伯林纷纷以假想之笔,展现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人类相处的种种不幸遭遇时,更是以血和泪的辛酸控诉着人性中的卑劣,麦克尤恩让“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小说中得到了复活,并以出脱人类的独立姿态,发出震撼人心的怒斥和警告:“你不仅仅是砸碎了你自己的玩具,你不仅仅是否定了捍卫法治的一条重要理由,你试图摧毁的是一个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