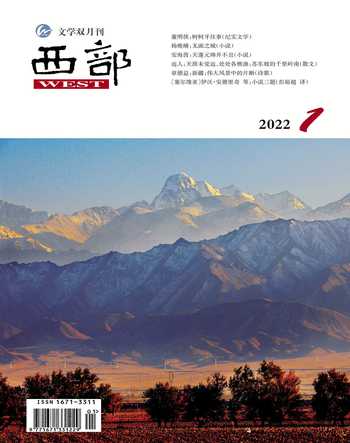爱吃玫瑰馕的麦麦提
王新梅
一
“如果你来新疆,一定不要忘了吃玫瑰馕。”朋友圈里,麦麦提又在给玫瑰馕做广告了。
我是在青园社区认识麦麦提的。社区所有员工加起来有八十多人,麦麦提有三个,开车的麦麦提、负责宣传工作的麦麦提,还有我说的门口的保安麦麦提。他是社区最有名的麦麦提,因为他最会唱歌,最爱吃玫瑰馕。
麦麦提爱吃有玫瑰花酱夹心的馕。给我第一个说这个事的是蔡姐。“一个男人家,要吃就吃辣子馕,皮芽子馕也行,歪江(维吾尔语‘惊讶’的意思),他竟然爱吃玫瑰馕。”她撇着嘴表示不解。
蔡姐是社区打扫卫生的。我妈以前也在这个社区打扫卫生。现在打扫卫生的都有个洋气的名字,叫“保洁员”。就像以前叫“看大门的”,现在叫“保安”。
高中毕业后,我就没再去学校。我妈不死心,想让我复读。我不想再读了,三百多的分数,基本没戏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靠出力挣钱的我妈偏不信这句话。我当年考上高中,她以为我离光宗耀祖不远了,就把强烈脱离底层劳动人民的想法全部寄托在我身上。
我放弃复读后,她认认真真地在家哭了三天。早晚一脸的哀伤。我爷爷死的那几天也没见她那么伤心过。
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家待着,每天和人说不了三句话。时间长了,我妈怕我看电影打游戏把眼睛弄瞎了,就鼓动我去社区。她去年才到门口超市干活的,之前一直在青园社区。社区是她来新疆后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社区招人呢,你去干几个月,挣了钱你自己花。”父亲也说。我也确实不想在家待了。再说我想换个手机,还想买个新吉他。
我到社区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麦麦提。麦麦提大我一岁。他,有些特别。别人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他高个子,却是细长条,腰薄得只有半拃厚,皮肤白,走路也轻,说话嗓门有点尖细。这样的人当保安?好在他个子大,大家默认了,彼此心照不宣:这保安多半就是个摆设。
我胖,三个月没动弹,长了六公斤,胖成球了。我俩一胖一瘦一高一矮走到一起,社区几个大妈戏谑我们是“黄金搭档”,意思是说我们像阿拉伯数字“10”。
麦麦提来自和田一个偏远的小乡村,去年来的。社区有个全疆最大的馕文化产业园。大部分工人都是从南疆来的维吾尔族青年。麦麦提上过职业高中,普通话明显比别的巴郎子(维吾尔语“男孩”的意思)说得好,社区招保安,他就报名了。“勤快,脾气又好,要是有文凭就好了。”社区书记不无遗憾地说。辖区少数民族工人多,社区需要懂双语的人。目前,麦麦提只能当个保安,是个临时工。我也是临时工。社区临时工挺多的。我和麦麦提在一楼门口守着,当了好多年临时工的蔡姐打扫完卫生也坐在门口的椅子上。
蔡姐和我妈之前当过几年同事,我一来,她便像个亲戚一样不见外地照应我,还像我妈那样喊我的小名。其实我之前也就见过她几面。蔡姐自己帶午饭,每次做了好吃的都会给我和麦麦提带一些来。“食堂的饭太难吃了,还不卫生,我就吃出来过——”她把苍蝇或者别的什么虫子的名字咽了回去,“不过饭是免费的。”社区吃食堂的大都是像我们一样不做饭也不带饭的年轻人。我们吃着,她就在旁边织着毛衣絮絮叨叨。“社区来了又走的年轻人十几个了。”她说。她手里的黄色毛衣就剩袖子了。她偷偷织的,不想让社区人看到她在干私活——织好的毛衣是卖给别人的。蔡姐缺钱,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她的手艺好,亲戚帮她在网上开了个淘宝店。一件毛衣的手工费要一百多呢。
“你们注定是要走的,年轻人啊,都干不长——”蔡姐在社区待的时间长了。其实她也想走,但除了力气,她没文化,更没姿色——她认为要是漂亮点她的命也许会好点儿——她能干啥呢,到哪儿都是出力气的,她已经认命了。不像我妈。
是呀,谁会当一辈子保安,但目前我又能干啥呢?家里再待下去,我和我妈就要势不两立了。我看见她垂头耷脑。她看见我唉声叹气。新学期开学的铃声响起后,她大哭一场后终于死心了,不再对我回学校重读抱有幻想。
“保安这工作,唏,”蔡姐龇着牙从牙缝里发出不屑的声音,“是个人都会干。”我和麦麦提面面相觑,无话可说。蔡姐今年四十五岁了,我原来喊她“姨”,麦麦提和同事都喊他“蔡姐”,我也就改口喊“姐”了。蔡姐有点跛足,之前站柜台卖东西、快递公司打包、饭馆洗碗都干过。我妈说,她命不好,结婚离婚两次,除了两个前夫的孩子,什么也没落下。第二任丈夫还老打她,她脖子上有块伤疤,是那个男人用烟头烫的。她头顶有一块没头发,也是那个男人拽掉的。为了离婚,她什么都没要,除了孩子。她对男人死了心,铁了心以后要一个人过。蔡姐是个糊涂的女人,傻子才会犯两次错误——社区有几个人很高傲,议论起她来毫不留情。切,好像他们自己多了不起似的。其实谁家不是一地鸡毛。社区辛苦而琐碎,临时工工资又不高,要有别的办法谁不想去别处——这点他们是一致的。
蔡姐大概总会在织东西时念叨她那些倒霉的事儿,说起前夫就“牲口牲口”地骂着。有一天,麦麦提说:“不要再说牲口了,牲口嘛也没惹你。”麦麦提的意思是牲口也没那么坏。麦麦提心很软,我早看出来了。他不允许我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发脾气。他呀,心软得像个丫头子(新疆话“女孩”的意思)。蔡姐也这样说。
麦麦提的家在和田一个名字有点长且有点拗口的小村子,他家最多的时候养过一百只羊,还有牛和马,还养过骆驼。他说,没人的地方,只要有牛和羊,你就不会觉得害怕。那年夏天刮沙尘暴,迷了路,他在一头骆驼的身边待了一晚。村里人都知道,沙尘暴来临的时候,骆驼的怀抱就是家。
保安工作不累人,就是熬人。往门口一坐,进来人就问:“您好,您找谁?”“好,请登记。”机器人一样地重复就行了。我干了不到一周就烦了。麦麦提有耐心,微笑得也很自然。我就笑不出来。麦麦提说:“我妈说,爱笑的人能看到尤里都斯(维吾尔语‘星星’的意思)。”麦麦提家附近有沙漠,沙尘暴来临时,看见星星就能找到回家的方向。星星是“好运气”的意思。
也有好玩的。比如,去市场巡逻。馕文化产业园的市场除了手工艺品,就是卖各种吃的,麦麦提叫它“巴扎”。每天我俩去巴扎巡逻的时间是两个小时。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儿。我俩戴上红袖章,在人群里来回走动。美食太多了,游客的眼睛都只盯着那些烤羊肉、烤鸽子、凉皮子、椒麻鸡,还有烤包子、烤鸡蛋——和我俩一样,世界一片祥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顶多看见不戴口罩的人提醒一下。我们绕来绕去。麦麦提说:“我俩像……一样,绕着这个地方转。”他说了两遍我才听清楚,他说的是苍蝇。
我们最爱吃阿布拉家的烤肉、马先生家的拌面、热孜万古丽大婶家的抓饭,还有南方的海鲜呢。我们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一会儿去吃烤鱼,一会儿去吃烤鹅蛋。
来馕产业园工作的大部分人是南疆较为偏远村子的维吾尔族男孩,家庭条件都不好。麦麦提的姐姐是个裁缝,家里的日子还过得去,但他还是报名来了。“太远了,我出来看看。”他说母亲和姐姐都让他来大城市见见世面。村子的工作队常常去他家,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出去多看看。那個队长用维吾尔谚语“没有见过绿洲的鸟儿,不知道春天的美好”鼓励麦麦提:“去吧,孩子,去首府城市看看,见识见识都市文明。”
“我不喜欢这两个字。”有一天,我们巡逻回来,他指着保安服上的“保安”二字说,“我想干别的。”
原来他也觉得保安工作没意思。“那你想干啥?”我问。
我们从巴扎上回来,要去社区门口守着了。秋天正午的阳光很猛烈,晒得我们脊背上热热的。他说:“不知道。”他眼睫毛又长又密,像一种甲壳虫的翅膀。说完“不知道”,“翅膀”就盖了下来。
有一天他开心地对我说:“我想当老师。”社区人都建议他念个文凭,然后考社区公岗,转正。村里工作队的队长建议他以后还可以考教师,现在需要好多双语老师。他兴致勃勃。我呵呵笑着,心想,我可不想当老师,现在的孩子多难教呀。但我也肯定不会当一辈子保安。麦麦提知道以后要干啥了,我呢?想起这个问题,我就有点惆怅。同学们个个为着前程拼搏,我却连自己要干什么都不知道。
每次回去,麦麦提总会带两个玫瑰馕,那是他的晚饭。我总像蔡姐那样打趣他:“一个男人爱吃个玫瑰馕。男人,难道不是应该吃辣子馕吗?”“辣子会伤到我的嗓子,”有一天他指着脖子认认真真告诉我原因,“我还要唱歌呢。”他比画着拿话筒的样子。
晚上社区值班,其他人都走了,我们就去楼上活动室,把墙上的都塔尔和吉他取下来。一楼门口有几把椅子,我们喜欢坐在那儿唱歌。青园社区离城区有二十几公里。辖区没有住家户,大小企业有十几家。企业建筑大都是两三层楼高,只有那家“卓越建筑”的烟囱高得像个碉堡。晚上八点一过,人走楼空,白日里喧闹的企业像沸腾的水冷却下来。墙面的某块玻璃折射的太阳光会投到我们这儿,很快又移到别处。几个维吾尔族男孩在宿舍楼那儿打篮球,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像老鼠的尖叫。太阳一点点沉下去,像被什么一点点吸走了,然后黑夜来临。天阴时,头顶是深浅不一的乌云;天晴时,东南西北散落着几颗星星。我们都发现了,这里的空气比市区好,城里哪能看到这么多星星。麦麦提说他们村子里的星星比这里的大。我说,星星都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对着天狼星唱歌,有时候对着北极星唱。整个园区都空空的,那个四米高的馕雕塑戳在月光下,被射灯照着,折射出淡淡的光晕来,好像落到人间的一个月亮。麦麦提学吉他很快,我却拨不来都塔尔。我特别喜欢听他唱那首他跟爷爷学的维吾尔族民歌《思念》。“百灵鸟在花丛中,歌声多美妙,我唱着忧郁的歌把你思念,心已随着歌声飞到了你身边,清晨醒来,把你思念……”琴弦仿佛拨动了内心的某根神经,我想起什么。
奇怪得很,平日里说话,麦麦提的普通话不算标准,但一唱歌,完全听不出拐音。清脆空灵的歌声让我想起“天籁”二字。办事处要举行才艺大赛。我和麦麦提要代表社区去参赛。我弹吉他,他唱歌。我俩每天练习,那是一段忘记了未来渺茫而不再忧伤的日子。
二
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要入户,还要去商户那里了解情况。商户都是做食品加工的,空气里充斥着酸辣、麻辣味儿。怕落一身油腻味儿回来,大家都备着一件旧衣服。天长日久下来,懒得换时,许多人就一天到晚地穿着旧衣服。女人也是。所以社区的女人就看着显老,还土气。只有茹孜古丽除外。茹孜古丽年轻,长得也漂亮,她娘家和婆家条件都好。她是个讲究人,入户是入户的衣服,一回来,立马换上时髦衣服。她每天都化妆,嘴巴总是红红的,睫毛翘翘的。美丽和快乐总是很容易打动人。“古丽呀,像只快活的布谷鸟。”一天到晚灰头土脸的蔡姐这么夸她。
茹孜古丽的快递也最多,来不及取时就给麦麦提发语音:“阿达西(维吾尔语‘朋友’的意思),麻烦你一趟行吗?”麦麦提说:“好的,姐姐。”也有人让麦麦提去街道拷个资料,送个文件啥的,他一律应允。麦麦提的人缘很好。几个麦麦提都在的时候,大家就喊他“爱吃玫瑰馕的麦麦提”“爱唱歌的麦麦提”。
麦麦提把快递拿回来就给茹孜古丽送过去。茹孜古丽多半会立马拆开包裹。几包零食、一个包,或者一件衣服,吃喝穿用,她一年要给淘宝贡献好几万吧。她爱吃零食,整天乐呵呵的,让我想起一个人。她是我的高中同学,现在已经是上海一所高校的大学生了,也是一个爱笑的胖女孩。她不知道我喜欢她。高中时忙着学习,也没怎么说过话。只是离开学校后回忆起来,我脑海里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她。她爱吃抓饭,爱吃烤肉,不知道上海的饭她吃得习惯不?我没有她的微信,高中的班级群还在。一开始,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都在发照片。尤其是那些爱花的女生,武汉的樱花、厦门的炮仗花……南方开得慷慨热烈的花给了女生太多的惊喜,她们一惊一乍的,毫不掩饰激情和快乐。
这几天,群里有人发红包,张小西过生日了,李蓓转专业成功了……她也发过。她在学校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她英语一直很好,高中时就拿过奖。大家纷纷发祝贺红包。我也想发,我有自己的银行卡了,且刚发了工资。但我忍住了。
我屏蔽了那个群。
只有白天和麦麦提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找到自信和快乐。他总是找我学普通话,我也跟他学维吾尔语。我学得最快的是“歪江”,惊讶的时候用,叹气的时候用,疑问的时候也可以用,我有事没事就把“歪江”挂到嘴上。麦麦提的脑子挺好用的,记忆力强。“歪江,当年你为啥不好好把学上完?”我问。麦麦提说:“爸爸走了,我要帮妈妈和姐姐干活。”说完,他的睫毛又像翅膀一样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麦麦提十二岁那年他爸爸得癌症走了。他有个姐姐和哥哥,除了姐姐缝纫的手工费,一家人全靠一百只羊过日子。村里这样的人家不少,维持日常生活可以,一旦家里有了病人,立马就会拖垮一个家庭。政府组织了一批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出来,让他们见世面学技术,挣工资。他现在每个月至少可以给家里寄去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那些馕园里打馕的巴郎子寄回去的钱更多。
我们这个馕文化产业园每天生产一万个馕,销售到全国各地。核桃馕、辣子馕、玫瑰馕、苞谷面馕……几百个品种。我们最近都爱买那个巴郎馕。巴郎馕个头很小,还有个名字叫“牛乳馕”,一滴水都不放,是用牛奶和面做的。一口咬下去,满是浓浓的奶香味。
馕园八百个馕坑里谁家的馕好吃,我们都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亚新家的辣子馕。麦麦提最爱吃的是馕王家的玫瑰馕。这种馕巴掌大小,夹心的,里面是玫瑰花做的酱。玫瑰花,想想都不是男人吃的東西。馕王家的面好,玫瑰是和田种植的。他家的之所以好吃,是因为中间夹层放的玫瑰花酱多,玫瑰花酱里放冰糖,不像别人家放的是白砂糖。
馕王的老板亚森江是个善良的人。他的邻居是个独居的汉族老人,亚森江常常照顾她,他告诉我们,老人也爱吃玫瑰馕。麦麦提和我觉得他真是个好人,我们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馕王家广告的链接,都配了一句话:“如果你来新疆,一定不要忘了吃玫瑰馕。”
我们常常会在巡逻的时候去馕王家吃热馕。我俩守在烤炉边,打馕人会多放点玫瑰花酱。馕贴在坑里,四分钟后就烤好了。刚出坑的馕烫手烫嘴,忍着烫撕一点儿放嘴里,满口都是面和玫瑰花的香味,辣子馕也是。热馕原来这么好吃。我发了条朋友圈:“吃馕和吃热馕原来是两种体验。”麦麦提吃着馕,让我给他录视频。他要发给他妈妈。妈妈总牵挂着他,他想发个视频告诉妈妈,他过得挺好的,还交到了朋友,说着搂过我的肩膀。
如果下班早,我们就去篮球场打篮球。
馕园里维吾尔族年轻人很多,虽然交流起来磕磕绊绊,但手势加语言不妨碍我们的沟通。有天下午打篮球时,几个人因为抢球撞到一起,我被撞倒在地,胳膊摔伤了。他们几个又背又扛才把我这个胖子弄到医务室。我龇着牙叫唤着,麦麦提用手掌一直搓着我的另一条胳膊,念念有词。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妈妈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的一条腿受伤了,他妈妈就是这样安慰他的另一条腿的。呵呵,真有趣。
胳膊打上石膏后,我休息了二十天才回去上班。那段时间,麦麦提和我形影不离,细致地照顾我。他真是个很温柔的人,是不是吃玫瑰馕的人就这么温柔了?在我的身边,多是被生活锻造得粗粝和强悍的人,他们像蔡姐那样脏话整天挂在嘴上。麦麦提这么温柔的人太少了。唉,每个人都应该多吃点玫瑰馕。
麦麦提吃馕也和我不一样,轻拿轻放的,好像馕是个名贵瓷器。如果是冷却的干馕,他会两只手端在前方,均匀发力,掰断,再掰,掰成四份后,放到盘子上或者袋子里。拿出其中一块,泡一壶浓茶,吃一口馕,喝一口茶或者酸奶。一招一式看着很斯文,很有仪式感。他绝不会像我一样直接下口。我说麦麦提,你现在一点儿不像保安,像个绅士。他问我“绅士”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讲了起来。扯着扯着,就扯到了上海。他没去过上海,我也没去过。我没忍住,在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闻着玫瑰馕的香味,我讲述了女同学的故事。
麦麦提听完,憨憨地笑着,笑完了,细长的身子像大虾一样弯下去,把脚上的球鞋鞋带松开,又一丝不苟地系上。这些天他也是这样帮我系鞋带的——他的手指修长又灵巧。他害羞地说:“我,要赶快增长本领,我是男人,养家。”
“歪江——”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社区几个老男人背后叫他“丫头子”,也没有太大的恶意,但和他现在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是个男人的话比起来,总是有点滑稽。
有的男人像女人。有的女人像男人。蔡姐就像个男人。男人婆,太能干了。社区附近有几个工地,正在盖楼。最近她周末都去工地干活。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被骗了。她买的毛线丢了,骗子冒充快递公司给她赔钱,她相信了,加了骗子的微信,在骗子提供的网址上输了银行卡号和密码,然后辛辛苦苦存的两万多块钱没了。我和麦麦提陪她报了案。警察也说了,网络诈骗技术很复杂,破案的可能性不大。蔡姐不死心,一遍遍给公安局打电话询问破案的事情。“几万几十万的被骗掉都找不回来。”茹孜古丽见多识广地说。她的朋友曾经也被骗过。“人只要想着贪便宜,就容易上当。”她没心没肺地说着,完全不顾忌蔡姐的颜面。
为了把损失弥补回来,蔡姐像个男人一样又在工地找了份活干。
馕文化产业园的效益越来越好,最近和上海签订了合作项目,要在那里成立一个办事处,招一批工人过去,工资很高,是我们现在工资的两倍。大家都想去。我和麦麦提也填了报名表。我俩在街道举办的才艺大赛中拿了第一名,唱歌的视频被社区上传到抖音上,点击率第一天就上万了。社区人都觉得我俩是名人了。蔡姐给我们做了大盘鸡表示庆祝。她把鸡翅膀给我们一人一个,说:“你们飞吧,飞到上海才好呢。”
三
社区发生了件大事。茹孜古丽的金项链丢了。那是她新买的。我见过她戴,细细的一条,要九千八呢。她之前戴的都是一线二线品牌,价格不菲,要不我们咋都叫她“暴发户”呢。
茹孜古丽说,那天值班,洗了澡出来,桌子上的项链就没了。社区的办公室都没有上锁。十几个人都在一个大厅里上班,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茹孜古丽本来就有乱放东西的毛病。不过,大家一时半会儿没拿回去的包裹都在单位一放好几天,从来没有丢过。
社区领导赶紧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书记主任都发话了,家丑不可外扬。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年底有个奖金好像和这个有关系呢,要是出刑事案件了,谁也拿不上那份钱。书记用宽宏大量的口气说:“谁要是不小心拿了,就还给人家。”还发动大家开始找。也许是她自己不小心弄丢了呢,我们也这样想。
书记循循善诱,给了三天时间,让偷了项链的人赶快承认,坦白从宽。书记胖胖的指头点着会议室的桌子说:“不然,我们就要……”就要干什么?报警?搜身?书记不说了,不满地看着我们。一场好戏即将上演,我竟然还有点小兴奋,每天关注着茹孜古丽的脖子,看项链找回来没。谁是贼呢?社区竟然有了贼。大家开始把抽屉里稍微上心的东西往回拿了。除了开会,中午吃饭的时候人最多,大家胡乱猜测着。有人说,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上去,我们这几个迟来的像是重点怀疑对象。
三天后,茹孜古丽还是没有找回她的项链。她找到书记,说要报警。书记不想把事情闹大,搪塞着。第二天,茹孜古丽把发票都拿来了。书记一看,确实是九千八买的。尽管之前说要报警,可茹孜古丽真要报警了,书记又坚决不同意。他像警察一样仔细询问了茹孜古丽当天的行动轨迹,查了考勤表和值班表,还有加班的人、谁最后离开办公室。一番筛选,目标锁定在五个人身上,其中就有我和麦麦提。还有两个值班的人和当天的保洁员蔡姐。我一点儿都不慌张。我当然相信麦麦提也是清白的。另外三个人都是女同志,包括蔡姐。调楼道的监控,显示大家都进去过。只有大厅有热水,我们那天泡方便面了。我们的理由都差不多。蔡姐她们当然是去打扫卫生的。
书记和社区几个人一对一进行问话。我也被问了,问我家庭情况,你那天都干了啥,除了喝水还干什么没?谁和茹孜古丽的关系不好?你觉得除了你们五个人谁还可能会和这件事有关系?第三天,书记说,再没有人承认,明天下午警察就来一个个谈话。我是第一个,麦麦提第二个……
“你第二,”我重复着书记的话。“麦麦提。”我喊。他有两秒钟没动弹。我再喊,他脊背像电打一般挺直了,看着我的眼神有一丝慌乱。
麦麦提认了。第二天我们就知道了。项链是书记交给茹孜古丽的。项链完好无损。大家都吁了口气,彼此心照不宣:警察不用来了,年底精神文明奖也不会受影响了。接着,大家就开始感慨,这麦麦提藏得深呀,没看出来是这么个人,竟干出这样的事。纷纷感慨,人心难测。有人说,到底是岁数小,容易犯错。还有人说,他真傻,犯不上偷条项链。有的人查找原因,说麦麦提妈妈一个人照顾他们三个孩子,家里条件不好。他的意思是条件不好就是缺钱嘛,缺钱就会……社区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大家都忘记了几个小时前,因为办公楼停水,麥麦提还跑到食堂为大家打来一大壶纯净水呢。我呢,也忽然想起那天本来不是他的班,是别人跟他换班了,莫非……我脑子里电光火石般闪过一念。
麦麦提那天一直躲在宿舍里没出来。我过去找他,问他为什么,真像他们所说的,项链是给他妈妈的?他盖着被子睡觉,石头一般沉默。
麦麦提被辞退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书记说这是最轻的处罚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他不可能再留在这儿了。
我去问麦麦提。他不正面回答我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而是把保安服脱了叠好放在一边,摆摆手说:“保安,不想干了,我。”
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青园社区。他提着行李消失在大门口,蔡姐和我都要掉眼泪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不习惯麦麦提的消失。大厅的纯净水需要一桶桶从楼道尽头的净水器里打来,之前几乎都是麦麦提打的。他走了后,水桶就经常空着了。快递也是麦麦提帮大家拿回来的,现在他们得自己去拿了。之前他去食堂打饭,总会快乐地答应帮别人带饭回来。还有,去企业入户,遇到维吾尔族职工,麦麦提总是最耐心的翻译者。茹孜古丽又戴上了她的项链。她还是那么快活,那么鲜亮。虽然她是无辜的。几天后,看到茹孜古丽又乱放东西,脾气不好的阿斯亚大姐白了她一眼,说:“以后嘛,把你的宝贝看好。”
一时半会儿招不来人,那一个多星期,我一个人站岗、巡逻,很没意思。后面来了个六十岁的老人先顶替着。那个老头烟瘾大,熏死人了。
宿舍里,麦麦提的床空了几天后就有别人来住了。我一躺下去,就想起他常常坐在床边唱歌的样子,还有他带我去吃刚烤好的热馕的情景。辣子馕、玫瑰馕……我真正爱上吃馕是和麦麦提吃了热馕后开始的。我爱吃辣子馕,他爱吃玫瑰馕,我俩都认为只要是热馕都是最好吃的。我也学会了像他那样吃馕:小心翼翼地掰开,用酸奶蘸着吃。
突然,我看见麦麦提回来了。“麦麦提!”我喊。是那个爱吃玫瑰馕的麦麦提,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里都是笑意,他一定也想我了。我跑过去,想搂过他的肩膀。和以前一样,他个子太高了,我只能像个皮球一样挎在他肩膀上。等我醒来,才知道是个梦。
“麦麦提,我不相信你会偷东西。”我在他微信上留言。他很快回复了,是个微笑的表情。后来我又说,我不相信你会干那种事。他语音回复:“没事,早都不想当保安了,我。”
“我也不想当了。”有一天,我回复他。
四
第二年五月,我才离开馕园。馕园要和上海合作成立馕食品公司的事要变成事实了。产业园要在网上建立展示平台,还要用各种软件制作宣传片。我试了试,把游戏里的人物和馕食品的元素结合起来,制作了个小视频发到指定的征集邮箱了。虽然最终没入选,但征集者回复了我,说我把新疆元素和游戏结合起来的想法很好。我挺兴奋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上海要在新疆办一个班,培训一批电商销售的技术人员。我报名了,还报了计算机专业的自学考试。我不能老玩游戏了,也不能看电影了……战胜自己才是世上最难的事儿。那天,高中女孩在同学群里发了个图片,图片中,一只兔子在奋力拔一个深深埋在地下的大萝卜,并配了一句话:有时候你觉得特别难,也许是因为有更大的收获。总觉得她这是对我说的话。等拿上计算机专业的文凭,说不定我可以去上海的馕园上班了。一想到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女孩面前,我就充满了学习的斗志。离开馕园的前一天,我给她寄了一箱麦麦提爱吃的玫瑰馕和我爱吃的辣子馕。
除了微信联系,我再没见过麦麦提,只是有时候听妈妈说起他。妈妈也是听她的老同事说的。麦麦提离开社区后先是去了一家歌厅唱歌,后来又被街道办事处叫回去教歌呢。街道成立了一个夕阳红歌舞队,麦麦提去给他们教歌教舞。他们喊他小麦老师。他还报名了市职专学校幼师专业的学习。村里的工作队筹钱给村子盖了个幼儿园,等着他回去当老师呢。当老师的目标好像离他越来越近了。我想起了他的那句话:“爱笑的人能看到星星。”
有一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视频。视频里,麦麦提正在唱歌。他纤瘦的身子唱着唱着便随着旋律左右摇晃起来。高挺的鼻梁,翅膀一样的长睫毛,轻柔的声音……我想起了夜晚我俩在社区里唱歌的情景。
有如此美好声音的人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秋天的时候,我妈在路上碰到了蔡姐。两人在路边的凳子上聊了大半天。她告诉我妈麦麦提不是贼,她才是。那些天为了省出白天打毛衣的时间,她都是晚上去打扫卫生。那天,她在茹孜古丽的桌子下捡了项链。她当然知道项链的主人是谁。可是她一时糊涂,想拿这金项链卖钱。她想着把项链卖了,丢的一部分钱就算失而复得了。事发后的一个夜晚,麦麦提又替别人值班时,蔡姐给麦麦提说了。她是被气傻了。她说着骗子如何高明,她如何去报警……直到说到藏了项链。蔡姐哭着说,她很后悔,但如果承认了,她就会没了工作,本来就被骗走了两万多的存款……她一直哭诉着命不好。麦麦提想到了妈妈,蔡姐是个像妈妈一样辛苦的妈妈,蔡姐对他也很好。麦麦提来馕园的第一个冬天,不适应北疆的寒冷,是蔡姐给他织了一条毛裤。蔡姐虽然笑话麦麦提吃玫瑰馕,可每次做大盘鸡时总会像妈妈一样少放辣子……后来,麦麦提主动找书记,说项链是他捡的。麦麦提走后不到一个月,蔡姐最终向书记说明了这一切。她求书记想办法让麦麦提回来。麦麦提不是贼,是个好孩子……
蔡姐还要继续留在社区工作。我们都原谅了蔡姐,书记、我,或者还有别人。我们打算像麦麦提一样替她保守这个秘密。但社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和田来的爱唱歌爱吃玫瑰馕的麦麦提是个好巴郎。
栏目责编: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