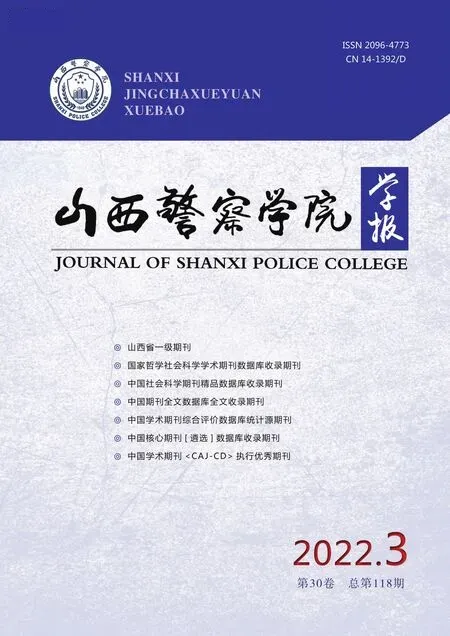论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法律保障
徐丹彤,赵桂民,张宽广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河北 廊坊 065000)
一、法律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必要性
我国法律对警察使用武力设计了基本的制度规范,同时对袭警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戒措施,但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不同于其他法定情形下使用武力,具有独特性,而且法律对袭警行为规定的惩戒措施具有事后性,难以制止正在发生的袭警行为,因此,法律对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专门加以保障十分必要。
(一)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具有独特性
应对袭警行为是警察依法使用武力的具体情形之一。警察为了应对袭警行为而使用武力,不同于使用武力应对其他情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就需要法律予以特别保障。而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之所以具有独特性,主要取决于袭警行为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袭警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人非法使用暴力手段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的行为,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暴力性。这是袭警行为的首要特征,可以做以下具体理解:(1)暴力是指“有形力或物理力”[1],“是具有侵害人民警察身体健康危险性的行为手段”[2],具有实质的伤害力,而非软暴力(1)“软暴力”是指行为人非法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2)暴力是指行为人积极主动的攻击行为,而不包含单纯的被动抵抗行为。例如,警察为逮捕犯罪嫌疑人,抓住其手脚时,犯罪嫌疑人拒捕,为摆脱警察控制而甩手蹬脚的行为,不构成袭警。(3)暴力的形式多样。根据2019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袭警的暴力形式包括两类:一是“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二是“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此外,我国《刑法》第277条第5款明确列举了“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三种加重处罚的暴力情节,是袭警行为典型和常见的形式。实践中袭警的具体暴力形式不止这些,还包括放火、爆炸、使用棍棒击打等。(4)暴力行为的后果严重。袭警与妨害公务行为同样可以采取暴力手段实施,袭警者使用的暴力相对于妨害公务的暴力,通常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袭警者为了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防止有武力使用权的警察进行反击,往往会孤注一掷,对警察实施武装的或群体的进攻,不计后果,使用的暴力手段比较残忍,严重威胁警察的生命健康甚至公共安全。例如,警察携带武器时,袭警行为可能导致警察的武器被抢夺,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因而不同于袭击其他公务人员。
2.针对性。(1)暴力分为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袭警行为是一种对人暴力,且针对的是警察的身体而非物或者第三人。这是因为,只有暴力指向警察的身体,才能对警察产生实际损害。如果暴力直接针对物或者第三人,则不构成袭警,除非行为人的目的是借助物或第三人对警察的身体产生实际影响,具有导致警察伤亡的现实性或高度可能性。例如,对警察正在使用的车辆实施打砸、毁坏,或对警察机关的办公训练场所、设施实施枪击、放火、爆炸等,借以对警察的身体进行攻击的,也构成袭警行为。(2)袭警者针对警察使用暴力的目的可能是单一的,即通过袭警来损害警察的生命健康权;也可能是双重的,既损害警察生命健康权,又妨碍警察执行职务。无论袭警者出于何种目的,损害警察的生命健康权都是袭警行为必不可少的目的。
3.突然性。即针对警察使用的暴力是在警察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实施的。袭警者要实现其目的,通常事前有预谋并隐藏其意图和工具,例如,行为人佯装要离开,或设法转移警察的注意力,多趁警察不备突然使用暴力实施攻击行为,其行为的隐蔽性、迷惑性强。袭警者借助暴力行为的突然性,以求压制警察并使其无力反击,顺利实现袭警的目的。
袭警行为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不同于处置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一是使用武力应当更加坚决果断。二是使用武力应当实现有效压制。三是应当减少使用武力的制约因素。这就需要法律对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给予特别保障,赋予警察更多权利,简化使用武力的程序。
(二)法律对袭警行为的实体制裁具有事后性
随着我国立法的不断完善,对袭警行为的打击力度在不断强化。《刑法修正案(九)》在妨害公务罪中规定袭警从重处罚,《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设置了袭警罪,并规定了加重处罚的情节,(2)《刑法》第277条第5款的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控制袭警行为的高度重视,再加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共同构成了针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法律体系,对袭警者具有较强的震慑力。但是,它们作为一种事后的法律制裁,无法控制正在发生的袭警行为并减少、消除其损害后果,只有采取实时的武力控制措施,才能及时有效地防止袭警的风险转变为现实的损害或者危害后果扩大,从而保障警察执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主要涉及实体惩戒和刑事追诉程序方面的内容,虽然规定“民警对于袭警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止,并根据现场条件,妥善保护案发现场,控制犯罪嫌疑人”“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依法依规使用武器、警械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制止袭警行为,受法律保护”,但对于警察如何使用武力制止袭警行为,警察使用武力有何特殊规则,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却没有专门做出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实现控制袭警行为的目标,除了完善袭警行为的惩戒法律制度外,还需重视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法律保障,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完整的法律体系,从而更加有力地保障警察的执法权益和公共利益。法律对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保障方式,不仅在于全面充分地提供警察使用武力的一般规则,更要注意针对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特殊性,明确规定其特有的规则。
二、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法律依据
对于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无论是宪法还是法律法规,都不乏保障性规定,都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各国对于运用法律手段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共识。
(一)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法律依据的内容
1.国内法依据。根据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7条第1款第6项和第9条第1款第10项的规定,对于“袭击人民警察的”,警察可以使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等驱逐性、制服性警械;对于“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警察可以使用武器。我国香港《警察通例》第29-03条(警察枪械的使用)规定:“警务人员可在下述情况使用枪械:(a)保护任何人,包括自己,以免生命受到威胁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台湾地区“警械使用条例”第4条规定:“警察人员执行职务时,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枪械:……五、警察人员之生命、身体、自由、装备遭受强暴或胁迫,或有事实足认为有受危害之虞时。”
2.外国法依据。(1)外国宪法规定。多国宪法在有关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授权条款中将保护人身不受暴力侵害规定为使用武力的情形之一。例如,英国《人权法》第2条规定:“一、每个人的生存权均应依法受到保护。任何人均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除非执行法院依据他的罪行依法对其作出的处罚判决。二、当其为绝对有必要使用武力所造成的结果时,剥夺生命不应被视为违反本条规定:(一)为保护任何人免受非法的暴力;(二)为合法逮捕某人或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逃跑;(三)为镇压骚乱或暴动合法采取的行动。”再如,塞浦路斯《宪法》第7条在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任何人的生命不受剥夺”后,设置了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形作为例外:“在下列情形下,因绝对必要使用武力而造成生命剥夺,不视为与本条规定相抵触:(a)为保护人身或财产免受对等的并且不可弥补的侵害;(b)为实施逮捕或者阻止被依法关押的人逃跑;(c)为平息骚乱或叛乱而依法采取行动。”此外,尼日利亚、多米尼克、瑙鲁、所罗门群岛、马耳他、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圭亚那、基里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牙买加、巴巴多斯、萨摩亚独立国、图瓦卢等国宪法也有类似规定。(2)外国法律规定。例如,《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21条(使用专门工具)规定:“为了击退对公民或者警务人员的攻击”,警务人员有权个人或作为分队(组)成员使用专门工具;第23条(使用火器)规定:“为了保护他人或自身免受侵害,如果这种侵害是带有危及生命和健康的暴力”,警务人员有权个人或作为分队(组)成员使用火器。《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7条规定:“警察官为逮捕犯人或防止犯人脱逃,或为保护自己或他人,或为制止犯人抵抗的需要,有相当理由认为必要时,按照该事态,在合理判断的必要限度内,可以使用武器。”《德国联邦与各州统一警察法示范草案》具体规定了可以对人使用射击武器的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为了防御一个当前的身体或生命危险”[3]。
3.国际法依据。《欧洲人权公约》(1950年)第2条规定:“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得故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但是,法院依法对他的罪行定罪并付诸执行的除外。当由于绝对必要使用武力而造成生命的剥夺时,不应当被认为同本条相抵触:(1)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2)为执行合法逮捕或者是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3)为镇压暴力或者是叛乱而采取的行动。”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第9条规定:“执法人员不得对他人使用火器,除非为了自卫或保卫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上述规定中的“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为了自卫”显然包含应对袭警行为在内。
(二)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法律依据的特点
1.阶位较高。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法律依据,除了法律层级的规定,还体现为具有宪法和国际法依据。具有宪法依据,意味着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相关立法可以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找到根据,充分体现了国家立法者的高度重视,不仅为下位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下位法相关规定的有效实施大有裨益;具有国际法依据,则对世界各国推动该领域立法和执法工作,实现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所要求的“会员国确保和促进执法人员发挥正当作用”,产生深刻的影响。
2.多将应对袭警行为作为警察使用武力的独立情形。各国(地区)对警察使用武力的法定情形,有的作出类型化规定,高度概括;有的作出列举式规定,比较细密,但无论是类型化规定还是列举式规定,多将应对袭警行为作为警察使用武力的独立情形。前者如《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7条(武器的使用)和我国香港《警察通例》第29-03条的规定;后者如《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21条和第23条的规定,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7条和第9条的规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警械使用条例”第4条的规定。应对袭警行为能够作为独立情形被法律专门加以规定,意味着它在实践中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是警察使用武力的一类重要事由。
3.多将应对袭警行为作为警察使用武力的首要情形。除了将应对袭警行为作为警察使用武力的独立情形外,一些国家(地区)的法律还将其置于法定情形的首位。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警察法》第31条规定:“在执行公务时,警察个人或分队有权按规定使用特殊装备:(一)制止对公民和警察的攻击时”;再如,我国香港《警察通例》第29-03条的规定,《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7条的规定,以及《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21条和第23条的规定,均是如此。法律对于警察使用武力各项法定情形的顺序安排是有意义的,置于前列甚至是首位的,充分体现了其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和立法者的高度重视。
三、法律保障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特殊规则
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具体规则,有的隐含在众多的一般性法律规则中,并未因其具有特殊性而被凸显出来;有的则在法律中难以找到明确的规定,在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中甚至存在争议,这显然不利于警察在执行职务中遇袭时果断精准地适用。笔者认为,法律应当对此作出明确和集中的规定,从而更加有力地遏制袭警行为,有效保障警察的执法权益。
(一)可以先于袭警者使用武力
警察根据事实和证据判明对方有袭警意图,袭警行为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和严重危害性时,可以在袭警者实际使用暴力特别是致命性暴力手段之前,先行使用武力予以压制,无须等到对方实施袭警行为后再予还击。
允许警察先行使用武力的原因在于:警察使用武力与袭警者使用暴力会呈现出时间上的先后,如果袭警行为发生在先,暴力作用于警察身体,就会导致警察使用武力的能力受到限制,此时再使用武力,往往为时已晚,尤其是对方使用致命性暴力时,警察自身权益(特别是生命权)和公共利益都将遭受不可逆的重大损失。相反,如果警察先行使用武力,就可以掌握主动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法律对于警察先行使用武力是支持的。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警察法》第33条规定:“被拘留者试图接近正在使用枪支实行逮捕的警察(违反其指定的距离),未经允许突然移动,将手放在口袋里或触摸武器的企图,都赋予该警察本法第32条第1部分第2款(3)该款规定的内容是“警察个人或分队有权使用枪支”的情形之二:“在警察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并企图占有其武器时,采取行动击退攻击”。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使用枪支的权力。”试图接近警察、未经允许突然移动、将手放在口袋里或触摸武器的企图等行为并不意味着后续一定会有袭警行为发生,但却允许警察使用枪支,这恰是法律对警察先行使用武力的授权。再如,我国台湾地区“警械使用条例”第4条规定:“警察人员之生命、身体、自由、装备遭受强暴或胁迫,或有事实足认为有受危害之虞时”,得使用警刀或枪械。第5条规定:“警察人员依法令执行取缔、盘查等勤务时,如有必要得命其停止举动或高举双手,并检查是否持有凶器。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击之虞(4)在现代汉语中,“虞”的含义是“忧虑”,这意味着此时袭警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或产生实害。例如,机动车司机面对警察的盘查和“停止举动或高举双手”的命令,拒不举手,拒不熄火,猛踩油门,显然意图冲撞警察,即有袭警之虞。时,得依本条例规定使用警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解释这样立法的理由是:“该两段条文之规定皆在防卫警察人员执勤之安全,因此较之正当防卫构成要件宽松。”“有危害之虞时应系尚未受到危害,只是即将受危害之虞的不确定危害。此与刑法第23条之正当防卫,必须是对遭受现在的侵害有所差别。”如果要求警察“必须实际已经受到危害,始能使用警械,无法确保执勤安全并严重挫伤公权力,宜修正为遭到强暴胁迫或依事实认有危害之虞俾能机先制服持有枪械之歹徒。”[4]130-133
先行使用武力是警察应对袭警行为时适用的特殊规则,而非警察执行职务时的普遍规则。它是适应执法环境和袭警行为危险性的产物。例如,美国民众有权持枪,警察执法风险较大,所以法律允许警察判断对方有危险举动时即可使用武力甚至开枪,否则,在对方火力更强的情况下,警察稍有迟疑就会造成自身的伤亡。但在我国,政府对于枪支、刀具等违禁品的管理严格,执法风险总体较低,因此警察并不享有普遍的先行使用武力权,只有对袭警这种突然性强、危险性大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才有必要先行使用武力。
(二)可以不经警告直接使用武力
对于警察使用武力前应否发出警告,国内外法律通常的规定是以警告为原则,不警告为例外,但对于袭警者,则可以在不警告的情况下立即予以反击。对此,域外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19条规定:“警务人员有权不事先说明使用身体力量、专门工具或者火器的意图,如果延误其使用会对公民或者警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构成直接威胁或者可能发生其他严重的后果。”《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政机关法》第24条规定:“在使用武器之前,内政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预先警告,工作人员或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除外。”前述《亚美尼亚共和国警察法》第33条的规定也将应对袭警行为作为无须警告的一项具体情形。
不必警告的理由在于:袭警行为大多实施在前,情况紧急,损害结果即将发生甚至已经发生,来不及警告或警告已无意义,因此可以不经警告而直接使用武力,否则,不仅无法有效应对袭警行为,还可能导致损害后果的扩大。
(三)可以使用更高等级的武力手段
警察要消除袭警行为的现实危险性,仅仅采用谈判、劝说等温和手段往往难以奏效或者来不及实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只能使用武力,而且需要使用较袭警者的暴力手段更高等级的武力。对此,我国香港《警察程序手册》第29章“武力与枪械的使用”第29-02条规定:“武力使用层次是一连串既提升而又紧密联系的武力程度”“为控制局面,人员使用的武力程度,可以比对方高一个层次。”警察应对袭警行为即属于此规则的适用情形,据此,警察对于持刀袭警者,可以使用枪支,而针对疑犯实施的“暴力攻击”(指殴打行动但无意图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所列举出的供警察参考的对应方法及具体措施,除了“强硬拘押控制”(5)具体包括“胡椒喷剂、强硬徒手控制方法(掌跟击、震击、膝撞、前踢、侧踢、押解手腕锁压倒、直臂压倒、手扣压倒)”。外,还可以使用警棍。
警察可以使用更高等级武力的理由在于:第一,袭警者使用的暴力随时可能升级,警察使用更高等级武力才能迅速有效控制住袭警者,取得主动,减少损失,避免事态反复。第二,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是以合法的武力制止非法的暴力,以正压邪,只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才能有效执行职务。
(四)可以使用一切可行的武力手段
警察使用的武力手段由法律规定,或由政府(或政府部门)制定并由国家元首(或政府)批准的清单加以规定,一般禁止使用未列入法律或清单规定的非制式武力手段。(6)《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机构组织法》第14条(使用专用工具)规定:“专用工具清单由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制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政机关法》第23条(专用器械的使用)规定:“内政机关制定的专用器械清单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阁批准。”第24条(武器的使用)规定:“内政机关使用枪支弹药的清单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批准。禁止使用未列入该清单的枪支弹药。”但袭警行为具有突然性,警察猝不及防,缺乏武力准备,为了保障警察具备足够的手段应对袭警行为,一些国家的法律授权警察在没有携带武器警械时有权就近使用现场的一切工具。例如,《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18条规定:“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抓捕实施了犯罪的人时,在警务人员缺乏必要的专门工具或者火器时,有权使用任何随手的工具,以及根据本联邦法律规定理由和程序使用其他不属于警察武器的武器。”根据《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21条的规定:警务人员有权使用的专门工具包括限制活动的工具,“在没有限制活动的工具时,警务人员有权使用手边的捆绑工具”。《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警察法》第13条规定:为实行自卫,“警员有权使用包括徒手格斗在内的武力和随身工具”。《亚美尼亚共和国警察法》第31条规定:“在必要的防卫或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如没有特殊装备或火药枪支,警察有权使用一切可能的简易工具。”这里的“随手的工具”“手边的捆绑工具”“随身工具”“一切可能的简易工具”是指配发的制式装备之外的在现场可以得到和利用的各种工具。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我国法律中尚无类似规定,有待完善。《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借鉴域外经验,在第34条规定:“人民警察遇有可以使用警械、武器的情形,但未携带或者无法有效使用警械、武器的,可以使用现场足以制止违法犯罪的物品。”这一规则很有必要在修法时正式确立。
(五)可以不受比例原则的严格约束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警察使用武力时总体上应当遵循该原则,但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时应否也要受到该原则的严格约束?有观点认为,“警察使用武器进行防卫,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的规范和制约,既要确保所采取的措施能够实现执法目的,还应尽可能做到对执法相对人的最小侵害,同时还要做到防卫手段武力层级与执法相对人所采取的侵害手段尽可能等比例进阶”。[5]然而这样的要求未免理想化,在笔者看来,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时可以不受比例原则的严格约束。理由是:
第一,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不具有完全适用比例原则的主客观条件。比例原则适用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具备裁量的充分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从而做出合理的决定。而袭警行为具有突然性、针对性,导致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成为“特别紧急情况下的一种自然的本能性防卫”[6]“往往是在瞬息万变的紧迫情形下迅速作出判断与行动的动态过程,现场的危险性和强压性,使得警察很难拥有充足的时间作出‘理性判断’”,[5]被动应对之中自然难以精确地遵循比例原则。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有检察官指出:“警察使用枪械时在那生死瞬间难用得‘恰恰好’,若‘过分’便打死对抗人犯,若‘不过分’便被人犯打死。”[4]313英国学者指出:“即便是正常的人也不能被期望对暴力使用的恰到好处的最低限度作出判断”“在具体的情况下,不能用珠宝商的秤去衡量暴力的合理性。”[7]
第二,警察应对袭警行为的本质是防卫行为,而比例原则适用于一般职务行为。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包括一般职务行为和特殊职务行为,特殊职务行为是体现为强制力运用的行为,警察使用武力的行为即属于特殊职务行为,这类特殊职务行为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进攻行为,例如使用武力抓捕逃跑重罪犯或制止罪犯越狱脱逃;另一类是防卫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防卫威胁无辜公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劫持人质、行凶杀人等;二是防卫威胁警察自身生命安全的袭警行为。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虽然具有职务行为的属性,但它显然不同于一般职务行为,也不同于使用武力进攻的行为,防卫性是其第一属性,而且基于前文对于袭警行为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警察防卫袭警行为的危险性、紧迫性大于防卫威胁无辜公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也导致警察使用武力的行为难以精准契合比例原则。不仅如此,“使用警械枪支进行防卫之时,防卫的重点是保护警察的生命安全、或者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而非公务。这样一来,就同普通公众的正当防卫的目的并无不同”。[8]而普通公众的正当防卫,对于严重暴力犯罪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如果要求警察在遇袭进行防卫时仍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显然过于苛刻,既不现实,也不合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第三,警察应对袭警行为不具备比例原则适用的事实构造。在一般的职务行为中,警察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构造表现为“警察是公权力的积极行使者,而相对人是行使公权力造成的不利益的消极的接受者……由于不利益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公权力的行使行为,而为了避免因强势的公权力的行使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自然有必要根据比例原则对权力的行使做严格的限制。”而在警察应对袭警行为时,“处于积极侵害他人利益地位的是袭警者,而直接受此不利益地位的则是警察。”[8]显然,在这样的事实构造下,比例原则是难以严格适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可以不受比例原则的严格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使用武力,而是要遵循合法、必要原则和现有法律规范,履行“尽量减少损失”等法定注意义务,在此基础上,根据行为的特殊性,不苛求警察使用的武力与袭警者使用的暴力必须严格成比例,例如对于开枪的部位和次数等给予警察充分的裁量权,并对其使用武力造成的过度损害结果,按照容错机制,给予适当的宽宥。
(六)可以不受使用武力禁则的限制
警察使用武力的禁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通常情况下禁止警察对特定对象使用武力的条款,主要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也与使用武力必要性降低有关,但应对袭警行为却是一项例外情形,警察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时可以不受禁则的限制,或者说是解除禁则。例如,《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22条(对使用专门工具的禁止和限制)规定:“警务人员禁止使用专门工具的情形如下:(1)对方显然是孕妇、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时,但上述人员进行武装反抗,实施威胁公民或者警务人员生命和健康的群体的或者其他的攻击行为的除外。”第23条(使用火器)规定:“禁止使用火器对妇女、有明显残疾特征的人、年龄显然是未成年人或者警察已知的未成年人进行射击,但上述人员进行武装反抗或者威胁公民或者警察生命和健康的攻击的情形除外。”《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机构组织法》第15条(持有和使用武器)规定:“禁止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武器,除非他们进行武装攻击,使用武力抵抗,劫持人质,运输车辆或进行有生命威胁的群体性攻击。”即:孕妇(妇女)、残疾人和未成年人袭警时,警察不受使用武力禁则的限制。上述规定优先考虑袭警行为具有的严重危害性和使用武力应对袭警行为的高度迫切性,同时,法律在对警察解除禁则时也附加了一定的条件,即对袭警方式作出了限定,要求袭警方式必须是“群体的攻击”或者“武装的攻击”,也就是要求袭警方式具有显著的危害性。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周全的,也是合理的。
——评《公安民警警械武器使用训练教程(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