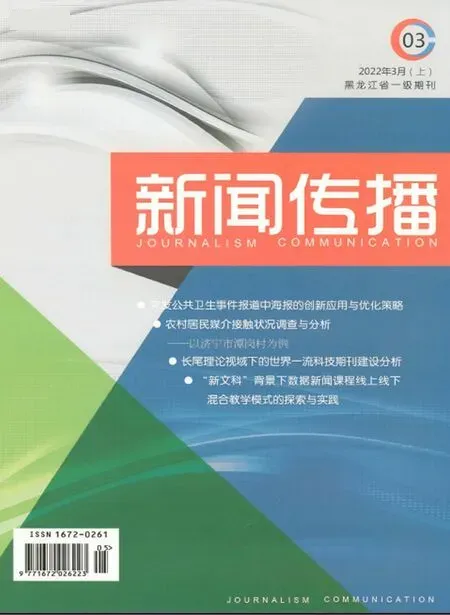《波斯语课》
——语言的面容与平庸之恶
刘明珠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一、另类语言的发明:钩沉历史与面容
影片《波斯语课》讲述比利时犹太人吉勒斯(以下将沿用人物的本名代指该角色)被德军抓捕时,为了活下来假扮波斯人的故事,贯穿影片的戏剧点在于比利时人吉勒斯如何假冒波斯人雷扎,寻找自创“波斯语”的灵感。在发明语言的过程中,具体的人得以被铭记,而这门另类的语言,也阴差阳错地书写了这段历史,重塑了吉勒斯的人格。而随着吉勒斯将上尉科赫引入这片他用语言开掘的领地,两人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接下来,笔者将从语言的发明和语言对人格的重塑两个方面来阐述此“波斯语”的发明过程。
首先,语言发明的具体过程体现在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在能指层面,词语中能指的来源从凭空捏造到截取集中营花名册上的人名,再到吉勒斯利用职务之便,在给俘虏分发餐食时,一一询问他们的姓名,从而提取语音。而对于所指层面,刚开始由上尉科赫“出题”,给定一个德语的单词清单,让吉勒斯翻译成波斯语,科赫自主决定着学习的方向和内容;接着,吉勒斯在俘虏们的身上汲取词语的意涵,他以一位急于领餐的战俘命名了“饥饿”,以一位处于古稀之年的老人命名为“年迈”,词语的所指来自于具体的人身上的特质,此时吉勒斯不仅主导了学习的内容,还将他在集中营中的所见所闻,纳粹暴行下的受害者书写进了他所发明的语言之中。影片结局中,德军战败撤退时,烧毁了集中营的档案资料,数万人的姓名隐匿于灰烬,而吉勒斯在逃出集中营后,面对法国盟军一一背出集中营中受害者的姓名,上尉科赫也在慕尼黑机场因说着伪造的“波斯语”而暴露身份,从而被捕。于是,在发明“波斯语”的过程中,集中营中数量庞大的受害者姓名是吉勒斯的词库,吉勒斯的所见所感是词语的意义来源,能指与所指的巧妙结合,使得受害者得以被记住,纳粹大屠杀的暴行也不会被抹去,而使追溯和偿还历史债务成为可能。
其次,吉勒斯的人格也在发明语言的过程中得到重塑。起初,吉勒斯在科赫的安排下做着抄写花名册的工作,他面对的是以姓名代指的抽象个体。而在吉勒斯目睹一位意大利青年挺身护住挨打的兄弟时,动情注视着这个场面时的他不小心切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是他第一次深刻地与同在集中营的受难者共情。吉勒斯在这次暴力中看到了他人的面容。在法国犹太裔伦理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那里,“面容”是一种首要的、直观的语言,它展示了生命的脆弱性,向观者掷出了强烈的伦理质询。“面容是人身上最为裸露的地方,它直观地显现了他人的脆弱,列维纳斯认为,这种他人面容的脆弱说出了首要的话语:不可杀人。面容的脆弱还预定了我对他人的伦理责任,由于他人是脆弱的,所以我需对他人负责。”[1]正是这种呼唤,促使吉勒斯给受伤的哑巴青年带肉罐头,而在哑巴的哥哥为吉勒斯牺牲后,也驱使着吉勒斯代替哑巴走向死亡。在这之后,吉勒斯进一步关注身边的人,当他在具体的人身上捕捉特质,发明词语时,影像配合着展现了具体的、各异的脸部特写,使得观众也对集中营中的受难者产生了共情,此时的面容对雷扎和观众而言,都呼唤起了强烈的伦理责任。吉勒斯的语言事业在此时,除了自救的目的,还承载了对他者的关怀。最后,正是词语与面容的连接,使得吉勒斯在被救之后,一个个背诵出来的名字,得以有召唤逝者的力量,那些被焚烧的纪录,那些在枪口前倒下的人,此时都汇聚成一个个独特的、饱经创伤的面容,呼唤着生者为其讨还正义。而吉勒斯的人格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识别他者的面容,进而付诸行动,承担了伦理责任,成为了能关怀他者的人。
于是,吉勒斯通过编造波斯语完成了双重自救,一是让自己在集中营中暂时保全性命,二是在对他人的共情中,救赎自己的灵魂。而科赫也被动地将恶果记录在自己的身上,进而难逃惩罚。
二、平庸之恶:无思的暴力
影片展示了两种暴力,一种是直接诉诸于被害者身体、精神的暴力,以押解囚犯、监督囚犯的日常工作的下士拜尔为代表,他具有强烈的排犹情绪及种族主义立场,不仅随意体罚打骂囚犯,还直接参与到屠杀的执行中;另一种是在一个作恶的体制内,间接实施的暴力,以科赫的工作日常为代表。虽然科赫也肆意殴打囚犯,但其本职工作是负责整个集中营中军官、士兵的餐饮,以这样间接的方式,科赫影响着更多犹太人的生死。但正是这种“间接”,使他没能反思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透露了他贫困的出身促使他加入纳粹党,从而实现了阶级跃升。与处处针对吉勒斯的下士拜尔不同,他本人并不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排犹情绪,在面对吉勒斯指控他为杀人犯时,他辩解道,“我只是个厨师”,但这样无力的说辞并不能使他免于杀人作恶的指控。
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反思纳粹大屠杀时,提出了“平庸之恶”来描述纳粹军官艾希曼,她认为这个须为五百万人死亡负责的纳粹头号战犯相比于穷凶极恶的暴徒,只是“没有去反思自身行为的意义”的人,“无思想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这就是‘平庸’。”[2]她认为这就是恶的源头,“无思想就是平庸(banality),其特征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能力不充分。”这导致他不会对自己所承受的命令规矩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反思,也不会从他人的立场思辨个人行为的意义。[3]以艾希曼推至科赫也是如此,科赫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集中营正常运转,他不亲自杀人,但也导致了大量无辜者受到迫害。而他因为并不实际参与到迫害的过程中,无法反思和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带来的后果,他在这样的无思中“失明”,他无法从犹太人中识别出“面容“,无法体会他人的脆弱,而只是把他们当作低贱的生命,致使千万人的死亡。
三、集中营的另一面:军队生活的日常
在通过科赫集中体现“恶人也是普通人”的机制之外,《波斯语课》中还刻画了德军军官士兵日常中的休闲方式、感情体验等,进一步暗示了他们也是一群有血肉之躯的平庸者、普通人,从而由科赫代表的“点”延伸到整个德军代表的“面”,深化反思和批判。影片中士兵们的精神状态,与普通工人别无二致,区别只在于他们流水线上的产品是犹太人的生命。于是,不像《辛德勒的名单》(1993)、《钢琴家》(2002)等反战经典作品中对纳粹士兵单一的脸谱化表达,《波斯语课》中的德军超越了一贯凶狠的刽子手形象,而更加地立体、鲜活。
在细节层面,影片以具体的喜好丰富了士兵形象,在刻画工作场景时,加入了生活话题的讨论。比如在几个执勤的士兵讨论“中午吃什么”时,一个士兵表达了对鱼肉的厌恶,说“死都不要吃鱼肉”,并且拒绝和其他人一同去用餐。而几米开外,就是排队行走的犹太人,他们灰头土脸、衣衫褴褛,使得此场景进一步变得讽刺。纳粹士兵们纠结于自己饮食喜好,而对他们施加的暴力视而不见。另一个类似场景则更加赤裸,一个德军军官站在寒风中一边看着火车将犹太人送向集中处死的地点,一边跟旁边的同僚抱怨着天气寒冷,接着就进入室内用餐了。通过对比军官与囚犯的处境,影片从单纯地揭露非人道主义行径走向了更深的讽刺与控诉。
在情节设置层面,影片通过军营内野营、舞会等休闲活动,展现了德军的日常风貌。野营场景中描绘了军官士兵其乐融融的画面,在宁静的森林里,人们演奏音乐并合唱,上下级同桌用餐。此时吉勒斯因为口误遭受科赫的毒打,远处用餐的人却只把这个行为当作娱乐话题,谈笑风生,野餐的气氛丝毫不受影响。
影片并不是尝试以穷凶极恶的刻画将德军彻底的他者化,而是暗示德军也是人,也有关于温饱、冷热的感知和体验,但就是这样的普通人,面对犹太人,也可以马上变成冷血的暴徒。他们是“无思”的人,于是,影片对于平庸之恶的刻画由此从个人延伸到了集体,同时通过与犹太受难者的对比,进一步发出了批判的强音。
结语
影片独具创意地将历史记忆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展示了吉勒斯如何在能指与所指的空隙间,填上具体的生命,填上受害者,填上德军的历史债务,从而间接地书写了历史记忆。同时,通过表现科赫的“无思”状态,以及将背景中的德军士兵去猎奇化地表达,并与对犹太人的暴行并置,立体、全面地阐述了平庸之恶的内涵。以上两个层面交织,打开了是非善恶之外的讨论空间,实现了在同类型影片中的突破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