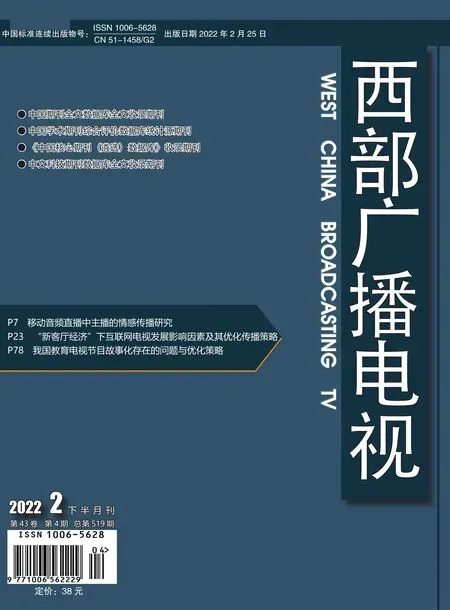纪录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艺术文化价值
杨若槿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群体的重要代表,贾樟柯执导的电影始终关注并展现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和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践行着为当代社会存像的创作追求和反思现实的文化使命。2021年9月19日,贾樟柯导演执导的纪录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国内正式公映。在此之前,该片已经在柏林电影节等多个电影节上进行展映,并在北美等地区发行。影片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马烽、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等的自述为线索,通过松散有序的结构和影像美学的艺术化运用,回溯作家们成长的文化语境和创作的心路历程,展现乡土中国画卷以及蕴藏其中的当代中国人精神还乡的旨归。
1 章回体结构:松散有序的口述史
对于贾樟柯导演而言,《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他继《海上传奇》之后,时隔10年再度回归纪录片创作的最新表达。该片源于其本人近年来返回故乡贾家庄暂居的生活感悟,体现着导演对于中国乡土文化的观察和反思。影片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场景出发,根据2019年在山西省汾阳举办的主题为农村或乡镇生活经历叙述,提炼出关乎日常生活的18个章节,通过一种松散有序的叙事,以“从乡村出发写作”的吕梁文学季系列文化活动为契机,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与乡土经历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贾樟柯导演选择贾平凹、余华等四位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借由他们对于自身的生活经历的叙述,连缀起一幅横跨70年的乡土中国的文化画卷。
首先,从主体内容来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采用“口述史”的纪实采访形式,从山西出发,辗转陕西、河南和浙江多地,带领观众走进四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之路。正如作家梁鸿所写道:“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1]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身为历史的见证者,以文学为名重返历史现场,体会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变迁。作为影片中的第一位主人公,贾樟柯选择了曾在贾家庄下乡的“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通过其女儿和同乡老人的回忆,讲述了马烽带领村民治理盐碱地、创造粮食丰收,并最终离开北京,扎根三晋大地进行小说创作的故事;作为“寻根文学”的标志性人物,生长在陕西省商洛的贾平凹则围绕着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将贫困年代的大家族生活、父亲被劳改对于自身成长的影响娓娓道来,展现出时代变革对于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对于作家余华来说,在故乡的医院成长和工作的经历为他观察世界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对文化馆工作的想象挖掘了他的文学天赋,并最终使其走上了创作之路;作为影片中唯一一位女性作家代表,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梁鸿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家庭往事,包括久病沉默的母亲、父亲的再婚风波及大姐对于家庭的辛勤付出,描绘出无数中国家庭遇到的困境与温暖。作家们对于过去生活经历和个人乡土经验的纪实性口述,从多个侧面聚合成一种历史叙事的文化脉络,实现了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描和反思。
其次,从形式结构来看,影片呈现为一种松散有序的章回体叙事架构。贾樟柯导演将作家们的个人故事和口述信息重新建构,进一步提炼为吃饭、恋爱、生病、远行、父亲、姐姐、儿子等18个关键词,并以标题化的字幕呈现。每一章节的长短各异,引领观众由关注作家的个人叙事进一步深入对日常生活和生命本身的观照,从而试图建构起一部描绘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心灵史。在此过程中,贾樟柯导演还展现了大量的现实场景片段,如养老院中老人们排队打饭、送餐的外卖员在街道中穿梭、西安火车站前旅客们聚集往来、农民在麦田中收割劳作的场景……这些现实场景穿插在作家们的个人自述之中,使得时间上的过去与现在、空间上的此地与远方在屏幕前交错汇聚,有效地增强了影片叙事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此外,围绕着作家这一核心叙事要素,影片还设计了多段普通人朗诵文学片段的镜头,将不同作家对于故乡的阐释予以呈现,形成了对于不同篇章主题的呼应,使影片叙事节奏更加灵活丰富。至此,作家口述、现实场景、诗歌朗诵这三部分作为影片的主要架构,形成了贾樟柯导演对于乡土文化的探索与追寻。
2 艺术化策略:交叠凝视的美学时刻
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不是将思想处理成画面,而是通过画面去思考。”[2]对于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而言,如何用影像这一视听综合艺术将个人经验与时代变革、文学表达与生活呈现有效地结合起来,是这部纪录电影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贾樟柯导演通过“文学与故乡”这一叙事母题,为影片中四位作家口述史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于影像美学的艺术化运用,充分展现并深化影片的思想内涵。
首先,从影片的视听呈现来看,其依旧延续了贾樟柯导演标志性的纪实美学风格,充分践行着巴赞“影像本体论”的理论本质,即“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3]。电影使用了大量的固定机位和长镜头,通过对于一定段落时间的完整记录,使影像具有“自己说话”的艺术魔力。无论是《三峡好人》中对于船舱乘客的描摹,还是《江湖儿女》中关于棋牌室的刻画,回顾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创作,可以发现他对于群像面孔的特写式塑造具有一种强烈的偏好,这种造型取向在这部纪录电影中被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养老院中,老人们清晰可见的皱纹,是岁月给予人的宁静与安详;火车站前,旅客们行色匆匆的神态,是日常生活的奔波与劳碌;学校食堂中,年轻人刷手机的笑容,是当下社会最常见的交往情境。贾樟柯导演用最忠实的影像刻画着鲜活的生命个体和转瞬即逝的现实存在,这些被镜头捕捉到的普通人群像,展现出的是芸芸大众被忽略的、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在镜头的凝视下,一张张带有生命印迹的“自然脸”在镜头的特写下化身为一个个动人的肖像,让观者在相对静止的画框中感受到一种情绪留存和张扬,他们与被镜头聚焦的作家们并置,作为时代变迁中社会影像档案的一部分,生成了一种朴实而动人的美学意味。
其次,除了对于群像面孔的独特描摹,贾樟柯导演还刻画了普通人作为“朗读者”的形象,将文学还原至生活的现场,进而探究文学与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正如契诃夫说:“现实主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而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4]无论是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余华的《活着》还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几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上所具有的乡土文化特性为影片叙事的展开奠定了基调。但贾樟柯导演并没有选择让作家本人充当文学的阐释者,而是将解读文学的权力交给了普通人。于是,影片中出现了这样的片段:在田间劳作的农妇自信、高昂地朗诵着于坚的诗歌“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年轻的女子在桥头深情地朗诵着沈从文的名篇“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乡村青年在树林旁朗诵着贾平凹的散文“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在这样的场景下,文学作为一种表意符号被提炼出来,但又被戏剧性地置于生活之中,建立起人与世界之间隐秘而流动的联系。在诗歌和散文的指引下,这些普通民众从现实生活的日常动作中停下来,短暂地进入文学的世界,通过语言、姿态和情感传达着自己对于文学的感知和理解,呈现出一种脱离世俗庸常的诗意气质。在这样的时刻,文学不再是触不可及的高雅存在,而是每个人所面对的生活本身,其赋予了普通个体拥有同等文化记忆的权力,彰显出生命本身的尊严和光辉。
再次,这部电影对于听觉符号的巧妙运用,也为影像叙事的审美表达提供了重要支持。对于贾樟柯导演而言,方言的使用是其电影创作的一个显著标识,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地域指向和文化身份。作家们带着各自独有的乡音出场,贾平凹朴实厚重的陕西商洛口音与余华风趣明快的浙江海盐腔调形成了鲜明对比,有效地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与作家们的方言写作形成了一种呼应。除此之外,贾樟柯导演在纪录片中还将戏曲纳入标志性的方言表意系统中,更加凸显出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特征。对应着不同作家的段落,贾樟柯导演将晋剧、秦腔、越剧与豫剧适时地穿插其中,有效地推动着影片的叙事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们时而化作讲故事的人,时而成为戏曲舞台的欣赏者。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与文学一起承担着传承历史经验和民族记忆的重要功能。与此相对的是,贾樟柯导演还在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包括钢琴和大提琴在内的西方古典乐器,这在其之前的创作中是极少出现的。古典音乐所具有的结构性和韵律感,可以成为不同章节之间的纽带,配合着作家们的个人讲述,营造出一种相对平和庄重的氛围。作为一种听觉媒介元素,西方古典音乐与方言戏曲代表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叙事张力和审美表现力。
3 人文性旨归:精神还乡的历史意识
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最初构思的名字是《一个村庄的文学》,但最终呈现的内容并没有局限在“文学还乡”的主题设定上,而是转向了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还乡”这一更大命题的探究和呈现上。在这个叙事过程中,贾樟柯导演带着自己对于乡土文化的观察出发,选择四位不同年代的作家以“口述史”的方式记述各自不同的乡土经验和生活往事,串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余年的社会变迁。贾樟柯导演认为电影是“一个记忆的方法”[5],其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和表达,还可以从电影中找寻某个历史阶段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对于贾樟柯导演而言,在山西汾阳小镇的成长经历使他将摄影机坚定地投向了默默无闻的小城和鲜活各异的普通人,关注并记录着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在这样的拍摄理念的指引下,影片并没有过度聚焦在作家与作品本身,而是在保留文学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作家还原为普罗大众,使他们跟随着时代变革的步伐,将私人化的乡土记忆和历史经验娓娓道来。对于贾平凹来说,回忆起身处穷困年代的少年生活,他讲述了大家族一同吃饭藏勺子的趣事,当谈到因父亲被下放而自己前途未卜时,凝重的语调背后是那一代人无法回避的伤痛;对于余华而言,政治动乱的阴霾已经逐渐远去,留在记忆中的是在太平间午睡的凉爽体验,以及第一次前往北京改稿并且尽兴游玩的美好时光,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变革与精神风貌;而在梁鸿看来,有关故乡的记忆更多是关于家庭的伤痛,因病卧床的母亲像是一道阴影,父亲的再婚风波和长姐的无私奉献仍是她难以忘却的心结。在影片中,作家们重返文学创作的生养之地,身处在街边的小饭馆、常见的裁缝店、古朴的戏台等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面对摄影机袒露着自己的心绪过往。这些关乎人伦亲情、生老病死的生命命题,正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面对和思考的,这种由个体记忆和生活经验建构起来的历史细节,其表征着某种时代普遍性。正如贾樟柯导演在采访中所谈到的:“我希望能够通过四代作家的接力表达,来谈一谈几代中国人的心事。”[6]
就像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所隐喻的,一代代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弄潮儿,每个人都迎着潮水而上,向着理想的海域进发,而那些试图挣脱却无法回避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所面对的乡土记忆和时代烙印。回不去的遥远故乡与不可磨灭的成长记忆,成为每一代人怀旧的主题。同贾樟柯导演一样,作家们从家乡走到大城市,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快速变革中,但他们的创作根基始终在故乡。他们有意识地从城市返回农村或小镇,在各自的生养之地徘徊守望,寻找、确认并传承各自的乡土记忆,以故乡为根据地,探寻万千变化的世界。如同跟随着母亲梁鸿返乡的儿子一样,这些生长在城市的当代青年们,正试图寻找祖辈生活的印迹,重新学习熟悉又陌生的乡音。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乡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和精神文化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人们触摸历史、理解现实提供了重要的落脚点和历史维度。
回望贾樟柯导演的创作历程,他始终用一种略显“粗糙”的纪实影像风格和缓慢沉稳的叙事节奏,注视着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底层人物,甚至是边缘人物的离合悲欢,展现出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映射与冲突,使观众在他的影像世界中寻找到回忆和人生经验。从《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这两部纪录片开始,贾樟柯导演关注普通个体的文化记忆成为其电影中反复咀嚼的主题。通过纪实口述等方式,呈现中国人内在的精神特质和情感结构,展现时代变迁对于社会及个人的深刻影响,建构起一种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化路径,以观照人们当下生存的危机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