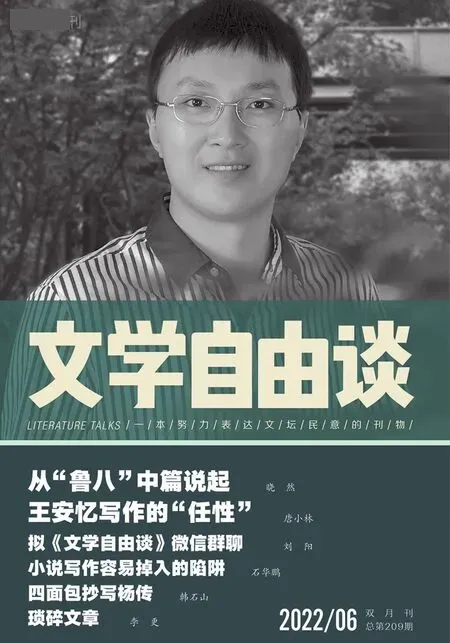四面包抄写杨传
□韩石山
“杨传”者,杨石先传也;“四面包抄”者,写法也。
先得说说,怎么揽下这个活儿的。
开起店铺,就会有生意。我的店铺,类似铁匠铺子,既自产自销,也来料加工。自己写下投出去是自产自销;受委托写的,是来料加工。这铺子原来开在太原,这几年搬到京城,赁屋开张,生意还行。今年早些时候接到这一单,写杨石先传,就是个大买卖。
明明是一单生意,起初做起来,跟演谍战剧似的。
我住在南三环边上。先是北大教授赵白生先生,领了天津某出版社的一个美女编辑来看我,说是他正好到南边有事,美女回天津在南站搭车,顺路也是慕名来见识一下。过后不久,赵教授来电话,说那天一起来的美女,想请我为他们社写一本杨石先传,不长,五万字就行。架不住他三说两说,也就应允了。此时那位美女,也亮出身份来,天津某出版社副总编辑;填合同,提要求,一点也不通融。
我是笨一点,但不傻,至此也就明白,前后是怎么一回事。美女领命来北京找个高手写杨石先传,赵教授推荐了我。七旬老翁,能否担此重任,美女不放心,赵教授说那就去见识一下,于是便来了。哪是什么慕名拜访,不过是验一下货,——看这货色写得了写不了他们的杨石先传。
我把人家视为订货人,人家把我视为做货人。
现代社会,再高雅的事情也逃不脱商业文明的法则。
1
事先有约定,基本资料由他们提供;我发现什么要的,他们在网上下单寄我。不久,寄来《杨石先纪念文集》《杨石先传》等读物,又遵我之请,网上下单买了《南开大学校史》《西南联大回忆录》等书籍。这些,对写一本新的《杨石先传》来说,只是提供了粗略的轮廓。按说该去一趟天津,去南开档案馆查查,找南开的老人手问问。疫情关系,几次动了念头,全都自己打消了。怕的是困在天津回不来。
有那么几十年,杨石先确实算不得名人。我在太原的书房有全套的《申报索引》,让女婿查了。从1919年到1949年三十年间,有他名字的新闻只有一条,用的还是他的本名“杨绍曾”。
但他确实是名人,有资历,有成就,越往后越受人尊仰。清华学堂第一届学生,1918年赴美留学,与徐志摩同船;1923年学成回国,与李济同船。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后期几年的教务,实则由他一人执掌,还曾一度代张伯苓任联大常委会主席。至于专业上的贡献,更是誉满学界。
杨石先传的难写,也还因为我夹带了私心。写传多部,我知道,写五万字的传记,要写好,跟写二十万字的传记,在拥有资料上无甚差别。该看的资料都得看,字数的多少,仅在选用的角度,取舍的详略。既如此,我何不先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传记,完稿之后大加删节,缩减成五万字交差?
好,就这么办。
资料这么少,怎么办?
想来想去,只有用“四面包抄”的办法。杨的一生,打交道的多是名人,他自己留下的资料不多,他人的记载中定然多有存留。只要掌握的材料丰富,多方印证,四面合围,不愁还原不出一个丰满鲜活的杨石先来。
在京城赁居之所,手边仅有几本书,如同光杆司令,只能徒唤奈何。暑假回到太原,在书房一坐,环伺皆书然,等于拥兵自重的统帅。且看我如何调兵遣将,用“四面包抄”的战法,打好这一艰巨的战役。
2
四面包抄是总的战略,实施起来,则分围、追、堵、截四种战术。
先说“围”。
写传的围,不是“围歼”,倒像是“围捕”,要抓住的是个活物。当然,从干脆利落上着眼,说是“围歼”也不算错。
杨石先是1923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应南开大学之聘来校任教的。普通书上,说来了南开就行了。写传不行,来了总得有个住处,没住处人跟飘蓬似的,落不到实处。起初依据的资料是《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3月),书中说,就他1923年所知,大学部设在一所旧中学里,有两百多名学生,十几位先生。这所旧中学叫什么呢?蒋先生没说,我们也不好说就是南开中学。张伯苓之子张锡祚在《张伯苓传》里说,1917年先生(指张伯苓)下决心创办大学教育,曾赴美国考察。1919年秋天,在南开中学校舍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转引自《张伯苓:一人一校一国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也就是说,这个旧中学,即南开中学。蒋廷黻是当年新聘的教授,何以连这个也弄不清?看一下该书的《译者序》就明白了。蒋先生此书,是退休后应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中心之邀而作,最早是英文版本。先由台湾翻译出版,大陆又引进的台版。想来英文里“老”“旧”二字是不分的,中文就不同了,“老的”仍存在,“旧的”是过去了的。既然大学部的小楼就在南开中学的校舍旁边,两校实为一体,杨石先到校后的住处,也就只会在中学的校舍内。
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还需要有力的旁证。
上过南开中学、留学美国,仅比杨、蒋二人迟一年回国的黄钰生在文章中说,南开中学有个礼堂,是袁世凯捐了一万块钱建的,名为“慰亭堂”,及至袁称帝,才将匾额撤下,礼堂还在叫着。礼堂周围向南的房子是教职员的宿舍,有的一人一间,有的两三人一间。校长张伯苓的宿舍是东南角的那一间。他的家当时在南马路,但他时常住在学校里。有几位国文老师,在天津有家,也住在学校,星期六下课后才回家。家在外埠的老师,就长期住校了。(转引自《张伯苓:一人一校一国家》)
这就清楚了。杨石先应聘到南开时,尚未成家,只会住在礼堂南边一人一间的宿舍里。
1929年,杨石先享受学术休假,赴美读博士,1931年9月回国,此时已结婚四年。再回南开时,便将家眷由北京搬来。这时,南开校园已全面建成,有了教授宿舍。多大呢?不必再“围”了,《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里有明确的记载,是四间一套的房子。何廉是新教授,享此待遇,杨石先是老人手,如今也是博士,带家眷住校也只会被同样对待。
四种战术中,“围”最好理解,不过是利用资料,多方求证罢了。
3
该着说“追”了。
战术上的追,若是在合围的态势下,当是对逸出之敌,尾随而进,于异地歼之。当然,也会有追不上的可能,让逸出之敌成功逃脱。我们这里,只是写书时的一种手段,既是在追,肯定是追得上的。
杨石先的经历,说简单也简单,成年后不是留学就是教书,一辈子都在学校里;说复杂也够复杂的:1897年出生,1985年去世,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民国的全程,解放后的风风雨雨,若以将军而论,可谓无役不与。现在的杨石先传记资料,无论是传略,还是年谱,甚至单篇的回忆文章,碍于时势,多是用笼统的语言,尽量往政治正确、品质优秀上靠。
对吗?肯定是对的。
准确吗?这就难说了。
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高校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又难说多好的“院系调整”。天津的情况,有人在回忆文章里说:“一九五二年,天津三大学院系调整……原本,南开大学1946年复员天津之后,是一个零散残破的局面。经过院系调整,南大六里台北院和甘肃路东院又全部划归其他单位。只剩下八里台南院的胜利楼(第一教学楼)和思源堂(第二教学楼),加起来不足一万平方米的教学和办公用房。就在八里台这一片被日军炸毁焚烧的废墟之上,要重新规划,建设新的南开大学。”当然是建起来了。文中接着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几幢教学楼和图书馆,几幢学生宿舍,食堂、游泳池和一片片教职员工宿舍拔地而起,南开大学,这所综合大学才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万华《南开精神永存,杨老音容常在》,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
光看这些话,给人感觉是院系调整给南开大学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校土面积越小,规划起来越好。可谁都知道,文中说的“南大六里台北院和甘肃路东院又全都划归其他单位”,这“其他单位”不是别的行政部门,恰是另外两所大学,一是天津大学,一是天津医学院。划出这么大一片“校土”,作为学校负责人的杨石先在做什么呢?
《杨石先生平纪事》里,“1952年”项下说:
5月3日,天津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院系调整简报》第1期上,刊载杨石先署名文章《群策群力搞好院系调整工作》。
11日,接教育部通知,决定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石先任主任委员。
11月29日,南开大学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院系调整工作顺利结束,杨石先在会上作题为《新南开大学的成立和它的任务》的报告。
不用查原文也可以知道,作为南开院系调整工作的主任委员,他在会上说的全是颂扬之词,振奋之语。
整整一本《杨石先纪念文集》,多数都谈到建政后的业绩,只有一处提到,对当年的院系调整,杨石先是有看法的。
这就要“追”了。
有看法归有看法,大片“校土”划归邻校,他是没办法的。其时他也只是个校务委员会主席,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是没有决定权的。这种事上要“追”,只能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对“院系调整”的态度。
这便是对郑天挺“调整”到南开大学的接待与安排上。
郑天挺(1899—1981),著名的历史学家,多少年都是北京大学校务的实际操作者。1952年从北大历史系主任,调整到南开大学当历史系主任,是院系调整中震动京津学界的一个不能叫小的事件。
北大那边为了腾位子,已弃之若敝履,南开大学这边,又是如何对待的呢?郑天挺是满怀委屈,单身来的,住处一时不好安排,连吃饭也不方便。杨石先将这个落难的老同事,迎进自己家里,单辟一室,安顿住下,吃饭也与家人同桌。对郑天挺来南开,有的文章说是为了加强南开的历史系教学,我只能说是“太动听”了。看看郑天挺的自述,就知道杨石先给了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怎样的慰藉。
在《郑天挺自述》里,先说1950年5月,他辞去北大秘书长工作,当时学校常委会曾表彰他做十八年行政工作的成绩,他也表示今后要为母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继续贡献力量。
有这样的表示,是觉得不当秘书长了,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能胜任的。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院系调整一开始,还是被调离了。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上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跟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它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它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生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愉快的只身来津任教。(《郑天挺学记》,冯尔康、郑克晟编,三联书店,1991年4月)
郑天挺住在杨家,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三年五年,“一住就是七八年”(魏宏运《风范永存》)。杨石先任南开校长不久,郑天挺也升了一格,成为南开副校长。
前面说了,郑天挺是1899年的生人,1952年来校一住七八年,就是六十岁了。也即是说,郑天挺从来天津到回北京,七八年来,吃住都在杨石先家里。
一个单身副校长,住在校长的家里,写到这里,我眼睛都湿了。
只有这样的“追”,才能见出历史的真相,也才能见出传主品质的高尚。
4
该着“堵”了。
按说“堵”和“截”差别不大,区别在于,堵,我方是静态的,等着敌方过来抗击之;截,是敌我两方都是动态的,只是我方的动作更猛些,插入敌前逆袭之。
这是指实战,写人物传记借用,又有不同。对虚高的评价,据实以核,可说是堵;不实之词摈弃之,可说是截。堵者挡也,截者弃也。
道理讲清楚了,先说要堵的。
杨石先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何时任职,又是如何任职,几种文本上说辞各异。王文俊《杨石先光辉的一生》(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文中说:“西南联大时期,杨石先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1943年任教务长。”杨光伟的《杨石先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上说:“西南联大最早的教务长是个国民党分子,学生对他的意见很大……1943年,原来的教务长做不下去了,提出了辞职。大家认为杨石先办事公正无私,便推选他兼任教务长。”
两文均用了“推选”,意在说明杨石先品德好,学问好,众望所归。说前任教务长是个国民党分子,不管是真是假,意在说明杨石先是个进步的,至少是个正派的教授。
杨任教务长一事,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有明确的记载。为省篇幅,不抄录了,改为叙事。
1941年10月15日,梅贻琦在昆明西仓坡主持联大常务会,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樊际昌提出辞职。讨论许久,不得解决。梅坚谓常委会主席、总务长、事务主任不宜由一校人担任,且总务长若再以沈履继任,则常委会竟是清华校务会议矣。
到了11月13日,下午三点又召开联大常委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因汽车在途被阻未赶到。到了四点,先开联大校务会议,五点半再开常委会议,通过改聘周炳琳为教务长,杨石先暂代;沈履为总务长。第二天下午接沈履辞职信,当即再致函郑天挺,促其复职。
隔了两天,11月17日,杨石先到教务处任事,郑天挺来相商,须下星期方可复职。
统观梅贻琦日记,联大的人事安排,主要由他与北大校长蒋梦麟相商而定,根本没有推选这一民主程序。梅蒋两人中,蒋基本不管事,人事安排,可说全由梅做主。梅在人事安排上的一个原则是,他已是常委会主席,下面大名头的职务,尽量给了北大和南开。原先的教务长樊际昌是北大的,再选的周炳琳还是北大的。周当时被教育部借调到重庆,整顿中央政治学校,不能履职,那就只有让南开的杨石先暂代了。
选南开的人,为什么选杨石先而不选旁人呢?仍关系着联大领导层的格局。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不设校长,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常委共同负责,值班的常委称常委会主席。蒋梦麟淡泊,不管事,张伯苓常住重庆,料理南开中学事务,好几年了,只能由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主持联大校务。所以选杨石先,最大的一个理由是,杨石先是张伯苓信任的南开校务负责人之一。张伯苓在重庆期间,指定的三个校务负责人,分别是黄钰生、陈序经和杨石先。黄原为建设长,新近又出任师范学院院长,自然不予考虑。陈序经一来昆明,便是商经学院的院长,也动不得。再选一个委以重任的,只能是杨石先了。至于说杨石先怎么个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杨石先担任教务长后的种种作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4月)中多有记载。摘取此书材料,在我的《杨石先传》中足足写了两节,多达万余字。
再说一件事。
1923年,杨石先与李济同时应聘到南开大学任教,好几个文本都说李济是教授,杨石先也是教授。《杨石先生平记事》1923年项下说:“9月21日,《南开周报》第68期报导,南开大学今年暑假所聘之教师有:化学教授杨绍曾先生。”其他几个文本未明确说杨一到南开就是教授,看行文的语气,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杨在康奈尔大学,仅获得硕士学位,一到南开就给了教授,不说物议了,以张伯苓的精明与自尊,断不会如此处置。
我记得看过写郁达夫的一篇文章上说,大约也是1923年,北大经济学教授陈某某赴苏俄考察,所遗课程由郁达夫暂代,给的名分是统计学讲师,月薪120大洋。郁是本科毕业,来北大任教连教授资格都不给。
还有可比衬的。1926年何廉获耶鲁大学博士回国,就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起薪给的是180元(大洋)。据此可知,180元该是南开聘任教授的最低薪水。
《杨石先图传——纪念杨石先诞辰120周年》上有图片,为《南开学校大学部教员录》之一页,上载杨石先1923年到校至1927年,历年所任课程、课时及薪金。1923年起薪为130元,到1925年增至235元,此后两年不变。比照耶鲁博士何廉的起薪,怎么都不能说杨石先一到南开就是教授。到了1929年,杨执意要去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固然有求知若渴的一面,与硕士学历在南开受的待遇,怕多少会有一些关系。须知张伯苓办学的眼界极高,杨石先他们那一茬的教师,理工科几乎全是博士。
像这类事,“堵”回原位,一点也不影响杨石先日后的如日中天。
5
说罢堵,来说截。
堵是辨析了之后还要肯定,截,干脆就是不要。
写传记,资料越多越好,莫非还有资料到手而舍弃不用的吗?原以为不会有的,看的多了方发觉还真有不能要的。比如一些溢美之词,在某个历史时期,听起来“杠杠的”,时过境迁,怎么看都是对传主的一种伤害,不是政治思想上的,而是人性人品上的。
这一节所引的材料,就不说文名与作者名了。所指摘的,仅是作者行文中具体的措辞,毕竟我作为一个后来的写传者,得人家的好处还是多些。我不是什么厚道人,但这点良知还没有全泯灭。
就看过的材料而言,杨石先此一生中,回拒或抗争的事件共有四宗。对这四宗事件,书写者有不同的措辞。
第一宗,上清华学堂时,拒绝了给他看过病的校医、也是神父的一位外国人要他入教的劝告。作者说,这件事让杨石先感到厌恶,当神父说了自己的要求之后,他先是惊愕地站了起来,惊恐地说:“不,我不入教!”
第二宗是1945年,杨石先公派赴美国考察教育,并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兼研究员。到了1947年,该回国了,该校化学系主任兼研究院院长挽留他说:“你们国家正在打仗,华北就要成为战场,你可以把家眷接来,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我们非常需要你这样有才干的人。”杨石先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国家更需要人,我要把我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踏上了归途。
这件事在另一个文本里,同样是回拒,杨石先是这么说的:“你们这里人才济济,我去不去,你们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我们国家不行,非常需要人,我不回去,有的工作就没法搞上去。”对方又劝他是否再工作两三年,等局面稳定了再作归计,他仍是谢绝,说:“国内局面很难估计,二三年未必能稳定。现在南开大学急需我回去,我不好再留了。”
第三宗,是1943年,杨石先正式就任联大教务长之后,奉命去重庆,参加设在复兴关(原名浮图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蒋介石亲任训练团主任,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任为段锡朋(原文是段锡鹏)。一次段找到杨石先说:“蒋主任要亲自介绍你参加三青团。”杨石先回绝说:他是搞教学的,搞科研的,没有时间再参加三青团。段非常不满地威胁说:“你不参加三青团,怎么做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务长?”杨很坦然地回答说:“不是我自己要做教务长,是大家逼我的。等我把应该做的几件事做完,一年以后,你们可以再找别人来做教务长,那时候你们再来动员我来参加三青团吧。”文中还说,他的刚正不阿得罪了蒋介石等人。
第四宗是十年浩劫后期,杨石先被送往农村“改造”,他能默默忍受。而当听说元素所的中试车间将被毁弃,他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简直胡闹,岂有此理!”他用颤抖着的手写了一张大字报,指责毁掉中试车间是对人民的犯罪。跟对方当面抗争时,他浑身抖动,把手攥得紧紧的。
现在来分析一下这四次回拒或抗争,杨石先的神态动作和言辞,是否合乎他其时的年龄、身份,还有他的性格与做派。
第一宗,他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有人劝他入教,惊愕乃至惊恐都能说的过去,对方劝说多了,有些烦是正常的,怎样厌恶就有些过了。毕竟这个校医刚给他治好病,还劝他好好锻炼身体,是劝他入教,非是劝他作恶。
第二宗,前一个文本有些生硬,后一个文本也还委婉。
第三宗就过分政治化也英雄化了。杨石先回答段锡朋的话,有点样板戏上沙老太太怒斥敌顽的口吻。作者可能不知道段锡朋是何等样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又是受一位爱国企业家资助,与傅斯年等共五人一起留学的“放洋五同学”之一。就是在国民党政府里,也是有名的清廉正直之士。他就是奉命劝杨石先加入三青团,也不会说出那么低俗的话。再就是,入了什么才能当什么,是中国当代人的做事理念。在那个年代,有这个迹象,并没有成为普适的法则。同样是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抗战时出任农本局局长,后来当过经济部副部长,在自传里说他一直未加入国民党,不也一样干着,这又怎么说?
第四宗里的发火,动怒,甚至浑身颤抖,最是荒唐可笑。这绝不是杨石先这样教养,这样身份的人做出的事。好几篇回忆文章里都说到,杨石先是个少言寡语、面容冷峻的人,看到不满意的事,多半是皱皱眉头。有人记述过一件事,最能见出杨校长的脾气。
1957年5月中下旬,搞大鸣大放,全校各系各部门提出不少意见,王瑞菁在校办公室工作,上面让他和几个同事整理这些材料。正好那几天杨校长去北京开会,上面就让他在校长室工作。各处送来的材料越来越多,他们就分别摊在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甚至也摆在地上,反正要持续干,每天下班也不收拾归拢。一天早上,杨校长来到办公室,看到桌上敞着口的墨水瓶,横七竖八的蘸笔杆,到处都是的纸张。王瑞菁一见校长来了,以为准要发火,没想到杨石先只说了一句:“屋里怎么可以搞得这么乱。”就皱皱眉头转身走了。
以我的揣想,其时学校的掌权者要毁掉中试车间,杨石先是会找见劝阻的,话嘛,怕只会说句:“这么做不好吧!”便扭身走了。什么拍案而起、浑身颤抖,他们不配,杨石先也不会给。
这类时髦而又不着边际的话语,还不该截而弃之吗?
6
说了这么多,非是说用了这几种“战法”,可以完满地体现出杨石先的业绩与人格。怎么可能呢?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说是补苴罅漏,聊胜于无。有的地方,没有过硬的材料是无法下手的。比如我的意念中,有两个题目,自认为该写也能写好,而用这种“包抄”的办法,却绝难完成,一是《杨石先的文学情怀》,一是《杨石先的书信情结》。
其文学情怀有一事可证。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邢公畹是个语言学专家,在西南联大时入职南开中文系,战后复员,回到天津南开,住在杨石先后排的院子里。两人交往不多,早晚相遇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杨宅前有个院子,杨爱在院里莳弄花木。有一天,邢与另一同事从系里开会回来,经过杨石先门前,看见一种长长枝条、开满黄花的植物,不知叫什么名字。杨石先提了一把水壶,正在浇水,他们进去相问,杨说:“这叫荼藤花,是一种蔷薇科植物,春天完了才开花,‘开到荼蘼春事了’嘛。”邢公畹一听杨说到这个断句时的语音节奏,就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素养的,这引起了他对杨极大的兴趣。
至于书信情结,起初是我的一种猜测。瞎子耳朵必灵,聋子眼睛必亮,不爱说话的文化人,笔头子必勤。先是这么想的,有了这个想法,就会留这个心。果不其然,此公不光爱写信,且一写就长。
再一个佐证是,杨石先的毛笔字写得好。不是别人说写得好,是他知道自己写得好。八十多岁了,南开校园的周恩来纪念碑的文字,是他拟的,也是他用毛笔写下上石的。书法漂亮的人爱写信,等于口才好的人爱演说,一个是说给千人听,一个是传到千里外。《颜氏家训》有言: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说实事吧。
联大化学系助教蒋明谦,1941年考取了清华第五届公费留美生。学校指定了国内导师三人负责指导,其中一人是杨石先。出国前,他给三个导师都写了求教的信,只得到了杨先生的回信,而且是十多页的长信。非常认真而详细地对选择学校、导师、课程,甚至行装、旅途以及国外礼节等做了全面的指导。(蒋明谦《杨石先师为我指明进学之路》)
胡孚琛“文革”前考上南开化学系,“文革”中毕业,分配到一个荒僻的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心情不好,有些消沉。在那里,不断收到杨老师的信,还将一部身边珍藏多年的善本《战国策》和郑板桥的《范县诗抄》寄赠来作为纪念。农场劳动结束后,胡留在当地工作,用非所学很是苦恼,不时将自己的境况写信告诉杨老师,每次都能很快收到杨的回信。离校十五年,年迈的老人给他写过四十多封信。
杨传已写完,还要过一遍,我拟在定稿前,在全书的后部(倒数第二第三节的位置),增加两节,节名即此两项的题名。内文呢,写不了多少。文学情怀一节,写上知道的两三件事;书信情结一节,开列名单说明曾寄给谁多少信,一两封的注明是什么信。天假以年,我能补上我补,我补不上,但愿有心人会给补上。比如蒋明谦名下,就说有杨的长信一封十几页,胡孚琛名下就说,有杨石先信四十几封。不用多,这两个人将信披露出来,书信一节就实实在在了。
将来出了的《杨石先传》,我是说这个长的,不是一本写得怎样的书,而是一本怎样写成的书。我希望这样写下的书,不光对做学问的人有所借鉴,就是对学理工的人也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