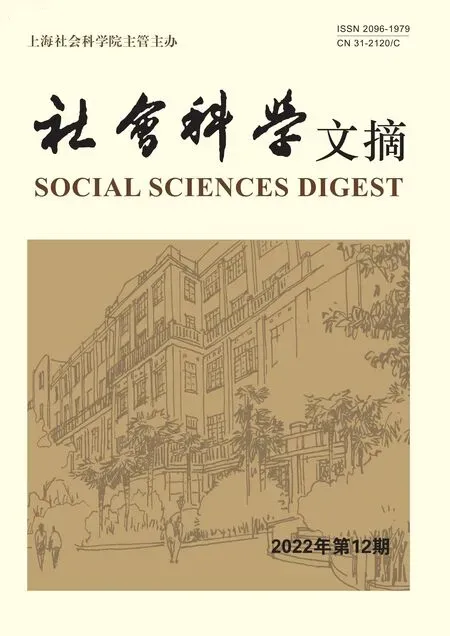Idealism:古典与现代的思想转换
文/聂敏里
2015年,保罗·古耶(Paul Guyer)和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为在线网站《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了“Idealism”的词条。在这个词条下,两位作者详细讨论了“作为18和19世纪一个主要运动的哲学idealism”,表明Idealism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最初被使用是在18世纪欧洲近代哲学的语境中,而且毫无疑问是处于笛卡尔主义的影响之下。由此,我们可以想见Idealism这个重要哲学术语所处的思想史语境。它显然是现代思想的产物。
但是,既然Idealism按其词源来自柏拉图的ἰδέα,而柏拉图的ἰδέα当然有它不同于现代的思想语境,显然这一点就给研究者们造成了困扰。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个术语所发生的争论,即,究竟应当保持传统的“唯心主义”或“唯心论”的汉译,还是采用新的“观念论”的汉译,甚或回到柏拉图的语境下采取“理念论”的汉译,正是这一困扰的反映。而这个困扰在根本上从属于中国思想界正在发生的“古今之争”这个总的思想范畴。换言之,在Idealism这个概念之下实际上蕴含着古今思想的重要转换,而搞清楚这个思想转换才能使我们深刻把握Idealism的现代思想意涵,而不致重新陷入古代思想的泥淖中。
一
让我们首先从巴门尼德(形而上学传统的奠基人)开始讨论。在残篇4中,巴门尼德这样写道:
λεῦ σσε δ’ ὅμως ἀ πεό ντα νόῳ παρεό ντα βεβαίως·οὐ γὰρ ἀ ποτμή ξει τὸ ἐὸν τοῦ ἐόντος ἔχεσθαι οὔτε σκιδνά μενον πά ντῃ πά ντως κατὰ κό σμον οὔτε συνιστά μενον.
你要盯着虽然远离但却确凿地近在心灵之中的存在;
因为你不会从存在的维系中割裂存在
因为它们既不是在世界上以各种方式到处散布的
也不是聚集的。
这则残篇的特殊之处在于,巴门尼德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属于心灵(νόῳ)的观看,并且认为只有这种观看才能把握他所说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正是巴门尼德的这则残篇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属于理智的观看(思维)与他所说的“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开始了西方哲学2500年的形而上学史,形而上学就是奠定在这个作为系词“是”的“存在”的基础上的,作为系词“是”它展现了其内在的基于逻辑谓词的肯定和否定的逻辑结构,而作为对象性表达的“存在”它展现了其对某种实存性的承诺,那么,与这一切相关联的那个“观看”——在巴门尼德这里就是用λεῦ σσε(盯着,凝视)来表达的——则揭示了其潜在的主观思维的向度。正是在这个理性目光的注视、凝视之下,我们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象性把握,亦即,我们获得了那被称作“存在”的东西。
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凝视”或“观看”所看到的东西——“存在”,而忽视了“凝视”或“观看”本身。因此,尽管“存在”对于巴门尼德是重要的,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来说也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恰恰是那个隐藏在其背后而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凝视”或“观看”,它可以说是隐藏的形而上学的秘密。
二
我们可以按此来考察柏拉图的理念论。在残篇4中,“存在”是心灵之眼凝视的对象,而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理念本身同样也是心灵之眼凝视的对象。这一点当然由“理念”一词的希腊语形式就可得到证明。理念就是看(ιδ)所看到的东西(ἰδέα),甚至“形式”也是看(ιδ)所看到的东西(εἶδος)。因而柏拉图的“理念”是思维的对象,作为思维的对象,它是思维单纯构想出来的高度理想性的存在,它的唯一性、单一性和同一性,它的严格的自身性和由此而来的超越性等,都来源于这样一种基于思维单纯构想的理想性。
不过,这一点对于柏拉图同样是被忽略的。这从他虽然注意到了那个“观看”,并且要求学会运用心灵之眼去观看,但始终只是凝视着所看到的东西,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个“观看”本身,就可以明白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性虽然是高度思辨性质的,却是缺少反思的,是一种自然的、无反思的理性。也就是说,这种理性是人类理性能力的一种直接运用,却不能对这种运用本身构成反思。观看者不知道自己是观看者,而把自己看成是完全透明的,或者像一面镜子一样,认为自己直接就与对象本身相同一,这就是古典理性的普遍特征。在观看的同时能意识到观看本身,或者换句话说,对观看本身进行观看,这只有反思性的理性才能达到,而这完全是现代理性的成就。
三
在此之后,我们可以来谈Idealism。这个词的词根Idea指示了它同柏拉图的ἰδέα的关联,也表明了Idealism这个词所隐含的古典与现代的思想转换。因为,虽然Idea是柏拉图的ἰδέα的拉丁字母的转写,但是,如果ἰδέα在柏拉图那里指向的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那么,现代思想中的Idea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恰恰指向一种主观存在,也就是作为我们主观思维对象的观念,这既可以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印象(impression)性质的,也可以是理性主义意义上的概念(concept)性质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在现代意义上使用Idealism,用它来指示以主观思维的观念作为理论的基本定向的各种现代哲学理论时,把它翻译成“观念论”就是正确的,而把它翻译成“唯心主义”或者“唯心论”则是更为正确的,因为,后者实际上揭示了持有Idealism哲学倾向的思想者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即,一种单纯从思维的主观性出发的理论立场,尽管有可能这位思想者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不承认这一点。
但这是否只适用于现代的各种相关的哲学理论,而不能适用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呢?换言之,我们能否以相同的方式将柏拉图的理念论也称作是一种“唯心主义”或者“唯心论”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尽管无论巴门尼德还是柏拉图都认为他们的理论所关注的是存在本身,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存在”还是“理念”都是心灵之眼——思维——所把握的对象,他们只是在他们的理论中要么忽略了自己所具有的主观思维的立场,要么认为自己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超越这种主观思维的立场而达到与存在本身的直接同一。就此而言,“唯心主义”或者“唯心论”实则同样准确地揭示了他们思想的实质,作为他们思维对象的那个存在实际上是他们的思想脱离了经验、单纯运用理性所先验构想出来的存在,他们的思维对象的实在性和客观性仅仅是逻辑必然性意义上的实在性和客观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的部分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柏拉图式的理念产生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的理性(它被主观地视为一种人的知识能力)中蕴含着其应用的一些基本规则和准则,它们完全具有客观原理的外表,由于它们而导致,为了知性而对我们的概念进行某种联结的主观必然性被视为物自身的规定的客观必然性。”康德把理性这样的运用所产生的概念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名称,这就是“先验理念”。他明确地指出这个概念是对柏拉图的“理念”的借用,并向我们表明,传统形而上学所赋予其先验实在性的东西,无论是灵魂、世界还是上帝,实际上都是我们的理性基于其自身本性的建构,因此,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心灵的主观产物,但是,我们却误以为它们是客观的。而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亦肯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唯心主义的实质。他这样说:“他把握了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的全部真理,这原则认本质是在意识里,认本质为意识的本质。这就是说,绝对是在思想里面,并且一切实在都是思想——并不是片面的思想,或者是坏的唯心论所了解的思想,……而乃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在一个统一里,思想既是思维,也是实在,它就是概念同它的实在性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尽管柏拉图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和说过。它和主观唯心论的差别仅仅在于它把思维到的径直当成客观实在。
四
Idealism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上述思想转换究竟是在何时开始、何时完成的?我在这里能够提供的思想史上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笛卡尔。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延续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也就是说,他同样要寻求对真正存在的把握。但是,在按照传统的方式、从感觉经验到理性认识去把握真正存在的尝试失败之后,通过彻底怀疑,他最终获得的存在就是“我在”。
我们说,笛卡尔的这个思想转折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直接导致了“主体”(hypokeimenon, subject)这个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中作为核心存在的概念的主观化,即现在不是作为思维对象的实体是存在的主体,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才是真正无可怀疑的存在的主体,而且也直接导致了我们思维所把握住的对象失去了其存在的客观性,仅仅具有主观的意义。
五
在这一现代思想语境下,我们来具体考察Idea和Idealism的汉译问题。
首先,既然在思想史上从古典到现代围绕Idea存在着上述思想转换,我们在具体的哲学史语境中来翻译处理Idea这个词时,当然应当根据使用它的哲学家自己的主观意图来进行。因此,丝毫不应当存在争议的是,在古典思想的语境下,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中,无论是Idea还是ἰδέα,都应当翻译成“理念”,而不应当翻译成“观念”。而在现代思想的语境下,特别是涉及18、19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和德国先验唯心论哲学,Idea都应当翻译成“观念”,而不应当翻译成“理念”。
其次,正是在现代思想的语境下,Idealism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出现了。它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哲学术语,即,它主要是用来针对某种哲学体系(无论是某个思想家的,还是某一时期主要思想流派的)的思想本质进行判断;换言之,它属于哲学的二阶概念,而不是一阶概念,它对由许多一阶的哲学概念构成的一个思想体系整体进行某种总体性的特征描述。既然它是用来刻画某种哲学体系的思想本质的,因此,与我们对Idea这个概念的翻译处理需要遵循忠实于其使用者的主观意图的原则不同,对于Idealism,在翻译上,我们恰恰需要遵循的是把握其核心概念所指的原则。
那么,什么是Idealism这个术语的核心概念所指呢?古耶和霍斯特曼给出了Idealism最基本的概念所指:1.某种思维的东西(心灵、精神、理性、意志)是所有实在,甚或全部实在的终极基础;2.并且尽管某个独立于心灵的东西的存在被承认,但是我们关于这个独立于心灵的“实在”所能够知道的一切被认为渗透了(这种或那种)心灵的创造性的、形式性的或者构成性的活动,以致在某种意义上对知识的所有主张都必须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知识。在意义1上的Idealism可以被称作“形而上学的”或者“存在论的”Idealism,而在意义2上的Idealism可以被称作“形式的”或“认识论的”Idealism。
尽管“观念论”的译名企图避开“唯心”的意涵,它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Idealism这个术语中没有“心灵”的词义,但是,正如古耶和霍斯特曼所指出的,在现代哲学的范围内,Idealism这个术语恰恰与认识主体亦即思维、心灵、精神等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Idealism表明,无论是对于我们认识的东西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来说,它们都与我们的心灵、心灵的活动密不可分。
因此,尽管Idealism从词源学上考察,它的确来自柏拉图的ἰδέα,也没有“心灵”的词义,但是,作为一个二阶哲学概念,它是用来描述某种哲学体系的思想本质的,在它的描述中很重要的恰恰就是认识主体的思维、心灵、精神、意识等要素,从而,在根本上,“唯心主义”或“唯心论”这个译名抓住了Idealism的本质特征。
追究起来,就像“哲学”“形而上学”这些汉语哲学概念来自日本一样,Idealism的“唯心主义”或“唯心论”的汉译名也来自日本。在由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于1881年的《哲学字汇》一书中,在“Idea”一词后所附的汉译名是“观念”,但是,在“Idealism”一词后所附的汉译名就是“唯心论”。并且在这个汉译名下,他还加了按语:
按,人之于物,止知其形色而已矣,至其实体,毫不能窥,故古来有唯心之论。王守仁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这条按语的第一句话,即,“人之于物,止知其形色而已矣,至其实体,毫不能窥”,显然是在英国经验论的影响之下,就此而言,井上哲次郎无疑掌握了Idealism这个概念在现代哲学中的基本内涵。而他之所以采用“唯心论”的翻译,则是他将对这个概念的现代哲学内涵的把握与阳明心学联系在一起进行互证的结果。
或许有人会据此认为这是某种误读,即,既不能用西方哲学的Idealism来理解阳明心学,也不能用阳明心学来理解西方哲学的Idealism。但是,正像西方的philosophy与中国的“道问学”或“穷理学”虽然可能存在话语系统和语用环境上的根本差异,但不可否认它们作为人类理性思维有着共通的思想关切和追问,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是成立的,而且其在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运用中也是成立的;同样,尽管Idealism在西方有其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基于这个思想传统的独特的语用环境和话语系统,它肯定和阳明心学的特殊思想语境是不同的,但却不妨碍它们作为人类理性思维在一些基本思想旨趣上存在一致性。
因此,就阳明心学确实在认识论和存在论的意义上涉及了心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尽管在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它更多关注的是其人伦日用与道德价值的方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前一种意义上把西方思想话语系统中的Idealism运用于其上,并且形成互证关系。而正是在这种互证关系中,“唯心主义”或“唯心论”的汉译名也就获得了其意义的基础。更何况,即便不求证于阳明心学,仅就Idealism这个概念在西方现代哲学的语境中与思维、心灵、精神、意识的指涉关系而言,据此将它翻译成“唯心主义”或“唯心论”也有着充足的理由。相较于“观念论”的汉译,实际上它更深刻地把握住了Idealism这个概念的本质。
这一点也得到了现代中国哲学话语实践的支持。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34年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中便明确地指出:
心有二义:(1)心理意义的心;(2)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普通人所谓‘物’,在唯心论者看来,其色相皆是意识所渲染而成,其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认识的或评价的主体。此主体即心。一物之色相、意义、价值之所以有其客观性,即由于此认识的或评价的主体有其客观的必然的普遍的认识范畴或评价准则。……而心即理也的心,乃是“主乎身,一而不二,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朱熹语)的主体。换言之,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
在这里,对“心”的意义二分的探讨,尤其是对其中的“逻辑意义的心”的探讨,是打通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键。它不仅澄清了“唯心论”所唯的“心”究竟所指为何,而且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仅仅存在于现代哲学之中,而是也可以被用来把握和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在宋明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探讨中,作为“理”的“心”实际上也是作为“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而成立的。从而,贺麟先生通过他自己的哲学话语实践表明了“唯心论”这个概念术语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的合理性。
贺麟先生的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于1942年出版之后,谢幼伟先生曾专门写过一篇书评《何谓唯心论——兼评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在这篇文章中,谢幼伟先生从补充贺麟先生讨论所不及的角度出发,将唯心论明确划分为五种,即:(1)主观唯心论(subjective idealism),(2)客观唯心论(objective idealism),(3)柏拉图的唯心论(Platonic idealism),(4)批判的唯心论或现象论(critical idealism or phenomenalism),(5)神学的唯心论(theistic idealism),并分别对它们做了详细的界定。从谢幼伟先生对上述五种唯心论的命名和界定来看,民国一代学者对“唯心论”一词的哲学意涵显然已经有了十分透彻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唯心论”这个汉译哲学概念在彼时已经发展成熟。
我们以贺麟先生和谢幼伟先生有关“唯心论”的观点为例,目的就是要指出,在现代中国哲学话语实践中形成的有关Idealism的汉译——“唯心论”或“唯心主义”,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对Idealism这个西方哲学术语的扞格或无知。实际上,现代中国哲学学者正是在充分考察了Idealism在所谓“西洋哲学”中的各种意涵之后,在哲学地把握了宋明以来中国哲学的内在思想旨趣的基础上,才采用了“唯心论”或“唯心主义”的汉译。就这个汉译名本身在哲学内涵上的准确性和正确性而言,我们的确无需为Idealism再增新译了。
至此,我们就完成了对Idealism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思想转换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这个概念之中隐含着古今思想的关键性的变革,这就是主体思想立场的确立。正是这一点造成了Idealism这个哲学二阶概念的出现,并且被用来历史地把握与此相关的一切思想的精神实质。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古典哲学在总体上是无主体的哲学,而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有主体的哲学,无主体这一点造成了古典哲学的根本哲学主张和追求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有主体这一点则要求现代哲学始终活动在思维与存在的某种紧张关系中。凡是不能学会保持在这种紧张关系中的思想者,尽管他是一个现代人,也会使他的思想倒向古代,去寻求在某种特殊方法引导下的思维与存在的重新或更高的同一、统一或和谐。这样,他就试图超越唯心主义。但是,根据上面的论述,现代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的唯心论和经验的实在论的立场,恰恰是现代思想所应当恪守的界限,它永远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思维具有其主体的限度,从而,它永远处于自我克服的思维辩证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