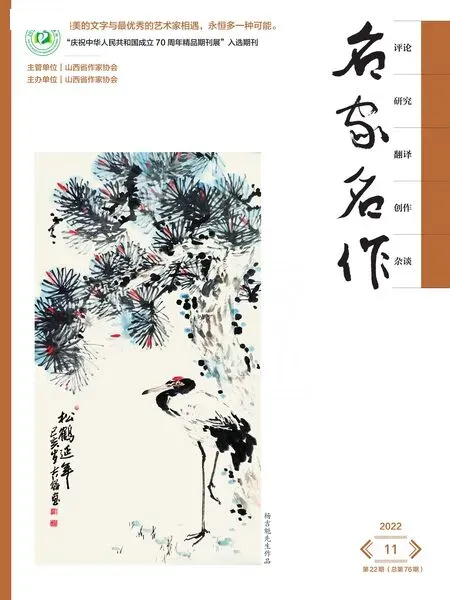从《楼兰》译本封面考察井上靖文学中国译介的特征
李思颖 何志勇
一、引言
《楼兰》于1958年7月发表。截至2022年8月,我国一共出版了八部《楼兰》译本。其中,中国台湾地区有两部,由于文化语境不同,在此暂不论述。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对井上靖及其作品的研究不断深入,但缺少译介学视角。以往的《楼兰》研究多以小说的主题和形式研究为主,本文则对《楼兰》进行译介研究,以弥补该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丰富我国对该作品的研究类型。
《楼兰》六部译本封面各具特色,微观翻译史中认为,译本的封面、标题、献辞/赠言、题记/引语、序跋、内标题、注释等,是与目标文本相伴相生的内副文本(张汨,2021:131),在研究译本的译介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国内六部《楼兰》译本的封面,对不同时期《楼兰》的译介情况进行分析,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译介井上靖文学作品的特征。
二、基于中日友好的《楼兰》译介
(一)1984年6月的《井上靖西域小说选》
《楼兰》原文篇幅短小,国内的六部译本均以合集形式出现。第一部译本是1984年6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耿金声和王庆江共同翻译的《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原书共收录10篇小说,《楼兰》位于第4篇。作为国内第一本译介《楼兰》的合集,此译本的封面采用的是敦煌白画中的伎乐飞天图。
整个封面以灰白色为底色,只有左下角有幅伎乐飞天图,其余部分散落着几朵白色的花。以敦煌白画为封面,可从侧面看出,楼兰首次进入国内读者的视野,是得益于《敦煌》在国内的译介和研究,同时也得益于国内敦煌学的研究。而中国最初关注原著作者井上靖及其作品《敦煌》,正是基于中日友好的状态下,中国学界对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作品进行关注的一个结果。
除封面外,从译本的序言和译者后记中也能看出彼时的中国对于《楼兰》的译介是出于中日友好建交的美好祝愿。译本中,冰心女士和井上靖先生分别在1982年的9月24日和1982年的7月7日为译本作序。冰心女士在序中提到,“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时期,《井上靖西域小说集》的译本付印了。”“我感谢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的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他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我向他致敬!”虽然译本是1984年6月出版,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但是通过序言注释和译者后记注释可知,此译本的完成时间是1982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这个节点。因此,此译本问世的原因与中日友好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
(二)1985年8月的《西域小说集》
第二部译本是1985年8月,由郭来舜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小说集》。作者井上靖和译者郭来舜曾一起游历过河西走廊,并且两人都在序中提到此事,可见两人是故交。井上靖也在1982年的8月为这部译本作了序。
有趣的是,井上靖所作的序的底稿被选取了一些片段,原封不动地成了译本的封面和封底。整个封面不含任何图画。其中前封面上的日文原文的序,还保留着修改的痕迹,经郭来舜翻译,中文意思是“唐代的敦煌城,也都埋在流沙之中。古昔的于阗也是一样。西域古老的历史都已埋在流沙之中”。后封面是“(最令人感动的,是)前年(1980年)走访西域南路的民丰、且末、若羌、米兰等所谓西域南路东部地区的诸部落”。以井上靖所写的序作为封面的大背景,通过修改的文字给读者传达出作者文学中的思考。就连书名“西域小说集”这几个大字,也采用了碑文拓片的形式。左下角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则采用戳的形式,更给译本增添了一种历史感。由此可见,封面想要突出对作家井上靖个人的认识以及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感。
此外,译者郭来舜在开篇的《井上靖和他的西域小说》中提到,“一九八〇年,笔者曾陪同井上靖先生游历河西走廊,目睹了他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风,至今难以忘怀”。“介绍和研究井上靖的西域小说,对于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对于继续研究和探索古西域与丝绸之路的奥秘,对于繁荣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当会有所裨益。”再通过对比前两部译本的完成时间和出版时间,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译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82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这两本译作圆满完成,因此,从译作的完成时间上我们可以得知,此书的出版目的离不开中日友好这个大基调,这与当时井上靖是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象征着中日友好交流的使者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基于中日友好的大基调,通过井上靖这个中日友好交流使者所描写的中国西域题材的小说,来反观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也是这两部译本得以问世的重要原因。只是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两部译本都是在1982年作的序,1982年完成的书,但是一部推迟到1984年出版,另一部则推迟到1985年才出版呢?作者推断这与出版社的考虑有关。但是具体原因尚需考察。
三、着眼作家文学性的《楼兰》译介
第三部译本是1998年,由郑民钦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井上靖文集》。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井上靖文学作品的中国译介进入了全集译本的新阶段。(何志勇,2020:66)首先,从封面来看,三部文集选取的作品虽然各不相同,但封面却统一是“白色的河床”。彼时的学界,已经把“白色的河床”看作是井上靖的美学本质和审美基础。以“白色的河床”为封面,直接体现出作家井上靖的文学性。其次,通过书名《井上靖文集》以及作品选取的文章《斗牛》《猎枪》《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冰壁》可以看出,《楼兰》的译介至此不仅局限于以往的西域小说与历史小说,而是放到井上靖的整体作品集里面去讨论井上靖作品的文学性。
此外,从主编郑民钦在卷首的评论性文章以及序言也能看出一二。主编郑民钦在每卷的开头都通过一篇评论性文章论述了一个主题,分别是卷1的《井上靖文学的人间性》、卷2的《文学孤独中的思索》、卷3的《井上文学的原型本质》。位于卷1首篇的《楼兰》自然归到井上靖文学的人间性这一主题中。文章中提到,“这种孤寂如同一条‘白色的河床’一直贯穿到井上靖文学的终点。”此外,林林在序中也说,“我国虽然译介不少他的书,但尚没有一套文集,始终觉得遗憾。”“这套文集的出版,不仅仅是对井上靖先生的纪念,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井上文学的深刻内涵及其在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郑民钦,1998:5)
由此可见,这部文集的出版已经不单单是出于中日友好的基调,而是转为对作家文学性的研究。由此可见,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井上靖文学作品的中国译介进入全集译本的新阶段,还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不仅把井上靖看作中日友好的使者,更是把井上靖看成一位文学家,对《楼兰》的译介开始转为对其文学性进行探讨。
四、侧重于中国历史的《楼兰》译介
第四部译本是200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这部全集式的小说选是继郑民钦主编《井上靖文集》后的又一套全面译介井上靖小说作品的译本。译作几乎都是之前发表过,深受好评的名家名译。《楼兰》作为1985年郭来舜版本的复译版,与前者共有15处不同,但多为一些错字纠正,并无大的改动。
此译本有三卷,封面各有特色。《楼兰》位于第一卷的第四篇。卷一封面是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北魏时期的壁画《鹿王本生图》。卷二封面是元代画家姚廷美的《雪江渔艇图》。卷三封面是一幅《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拓片。这些封面,有的取材于中国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有的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名家画作,有的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无不蕴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因素。此外,通过书名《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中的“历史”二字,以及译本中所选篇目的性质,均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
五、考虑市场文化需求的《楼兰》译介
第五部译本是2013年由赵峻翻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楼兰》。
译本封面正中央,白色字体的“楼兰”赫然映入眼帘。此译本是首部以《楼兰》为书名,并将《楼兰》放在首篇的译本。占据整个封面的是一片红色的沙漠中被风沙侵蚀过的丹霞地貌区域实景照。照片拍摄的地点是魔鬼城,又称乌尔禾风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佳木河下游乌尔禾矿区。而实际上,楼兰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沿岸,与封面上的照片不是同一地点。在当代,人们提起楼兰,脑海中就浮现出“消失的古城”。因此,仅凭封面上的“楼兰”二字,看到漫天黄沙下的残垣断壁,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封面上的就是楼兰遗址。
此外,译本于2013年出版,但201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出于政治上的敏感性或者出版社的考量等原因,使原本可能为了纪念中日建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以及娱乐大众的消遣读物的《楼兰》,最终省去了序言、前言和后记,于2013年出版问世,并最终凭借其语言的简洁性,成为大众化的猎奇读物。至此,《楼兰》单独作为书名,而楼兰也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进入大众认知的范畴。
第六部译本是2021年9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2013年版的再版。书名和译介的作品与2013年版一模一样,不过具体的内容略有修改。单从封面来看,再版的封面是由黄、蓝、黑色共同组成的一幅沙漠夜景画。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楼兰立于沙丘之上,通过罗布泊湖面的倒影,可以看到昔日繁华的楼兰古城。往昔的对比更突出楼兰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其实楼兰在汉代已经更名为鄯善,但“楼兰”作为一种意象,在唐代诗歌中多次出现。比如,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等。唐代的楼兰作为西域战地的代表,被诗人扩大为表示与西域战争的代名词。与唐代不同,作为文化意象的“楼兰”在当代则是“消失的古城”的代名词。一提起“楼兰”,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西域古城遗迹的画面。2013年和2021年版的《楼兰》译本,通过封面对“消失的古城”的再现,不仅体现出“楼兰”一词在当代的文化意象,也符合当今的市场文化需求。
六、结语
前两部《楼兰》译本,虽然分别出版于1984年和1985年,但均成书于1982年,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选择《楼兰》在内的西域题材的历史小说,进行选择性译介。第三部译本,内容开始不仅仅局限于西域题材的历史小说,还有井上靖的成名之作《斗牛》《猎枪》《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等前期悉心经营的力作,涵盖范围较广。基调也不仅仅是出于中日友好,更是立足于文学性审美的需求,对井上靖作品的文学性进行了研究。第四部译本《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是一部包含名家名译的全集,虽然没有序言,但是从时间上看,出版目的自然是为了纪念中日友好建交三十周年,只不过多了一层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强调。第五部译本,首次以《楼兰》为书名,赋予楼兰独立的文化意象。第六部译本作为第五部的再版,在中日友好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考虑了市场文化需求的动向。
综上可知,国内译介《楼兰》的动向,由最初的基于中日友好及对作家井上靖本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猎奇,逐渐转变为基于对作品文学性的探讨。21世纪初期,又转向基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宣传,近年来,基于市场文化需求这一点,对《楼兰》又进行了译介和再版。
其实,反观日本不难发现,不仅中国对日本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译介过程,有着从猎奇到学术再到迎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日本也同样,在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译介时,也经历了此类发展变化过程。可以说,日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的动向与井上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类似。由于篇幅有限,暂不在此做具体论述,留待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