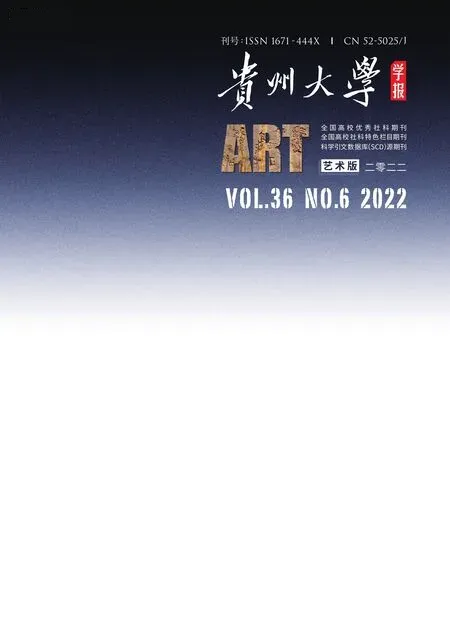“秘色”研究的四段基础文献
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1987年4月,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的考古发掘,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大发现。[1]对于千年“秘色”研究而言,它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转折性意义:其一,依据出土的十三件青瓷器(1)同时还出土有一件青瓷八棱净瓶。该瓶虽未录入“衣物帐”,但其造型、做工、釉色等的精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13件“瓷秘色”。考古学家据此认定,该瓶应属于“秘色”。因此,法门寺出土“秘色”也有14件说。参见禚振西等:《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初探》,载《文博》1995年6期。,以及记载这些青瓷器的“衣物帐”碑文可以推知,晚唐时期的秘色瓷已很精美。其二,有了这些标准器之后,“秘色”研究终于可以实现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之互证了。于是,“秘色”研究从此进入到“显学”行列(2)用王莉英先生的说法,“秘色”研究是现象级的选题。参见王莉英、王兴平:《秘色越器研究总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怪异的是,“秘色”之谜似乎并未因此而得到顺理成章的揭示。原因之一恐怕与学界未能在此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从唐至清之千年“秘色”古文献进行回溯性研究、甄别与挖掘等有关。在征引“秘色”古文献时,学界常犯的顺序颠倒、真假不辨、误读误引、以讹传讹等错误,应该说多源于此。失去可靠文献的有力支持,对任何学术研究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本文在法门寺等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千年“秘色”之代表性古文献,发现有四段学术价值不容小觑的基础文献。
一、《秘色越器》诗与“秘色”
《秘色越器》诗,是晚唐文学家、农学家陆龟蒙创作的一首七言诗。陆龟蒙,生年不详,约卒于唐中和元年,即公元881年。《新唐书》有他的传。[2]列传196追根溯源,在中文文献中,《秘色越器》诗应该是最早使用“秘色”来称呼瓷器的历史文献。因此,在“秘色”研究中,《秘色越器》诗的文献地位不容小觑。该诗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3]7216
的确,《秘色越器》诗属于文学作品,但陆龟蒙在诗中却为唐代“秘色”研究提供了四条不可多得的重要信息:第一,在陆龟蒙所生活的晚唐时期,“秘色”烧造已经比较成熟;第二,据《秘色越器》之诗名可知,“秘色”属于越州之越器;第三,关于“秘色”之釉色,陆龟蒙用了“千峰翠色”来形容;第四,在陆龟蒙看来,“秘色”是文人雅士,如嵇中散(康)们“盛沆瀣”“斗遗杯”的最佳选择。
根据“九秋风露越窑开”诗句可以推知,陆龟蒙对“九秋”(深秋)为越窑的最佳烧造季节,以及越窑的烧造情况等应该是比较了解的。而陆龟蒙以“千峰翠色”来形容“秘色”之釉色则表明,他可能目睹过越窑开窑时的盛况,并对越窑器丰富而复杂的釉色等比较知悉。从这个意义上说,《秘色越器》诗是具有相当纪实性特征的,在“秘色”研究中,是不可多得的“以诗证史”的好文献。
纵观千年“秘色”研究史,可以说《秘色越器》诗是被征引最多的历史文献。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法门寺唐代地宫等系列考古发掘之前,由于长期得不到可靠实物的佐证,《秘色越器》诗所记内容其实一直是个谜。该诗也因此成为被误读最严重的文献。如清代陶瓷“专业”人士郑廷桂,在《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中,竟然有“陆诗并无祕色字也”[4]这样连《秘色越器》诗名都不甚知悉的严重错误,即是典型例证。
在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学家发掘的不仅有十三件青瓷器,而且有唐懿宗咸通十五年“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在《衣物帐》碑上,与“秘色”有关的铭文共有21字,即“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3)“疊”拟为“碟”之误。子共六枚”。该铭文所载“瓷秘色”碗、盘、碟之数,与十三件青瓷器数完全吻合。[5]咸通十五年,为公元874年。(4)有学者研究认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应是公元872年,而不是874年”。见陆明华:《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载《文博》1995年6期。显然,在晚唐时期“秘色”烧造已经比较成熟这一点上,法门寺考古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实现了完全的互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难判定法门寺“秘色”与陆龟蒙“秘色”孰先孰后,但是通过上述文献与考古互证则可以获悉,至晚在9世纪后期,“秘色”之称谓已非个别现象。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一带,对越窑窑址等进行了系列考古发掘与调查。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莫过于刻有“大中”和“咸通”等唐代年款的窑具,尤其是带有“咸通”铭、施“封口釉”的专门用于烧造高档瓷器的瓷质匣钵。[6]虽然上林湖考古并未发现法门寺那样的“秘色”铭文,但考古学家依然据此作出推断,认为“秘色”烧造于越州之越窑。(5)2017年6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在《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之“前言”中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5—2017年,对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连续两年多的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说明该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器的生产地。”可见,在“秘色”属于越器这一点上,上林湖考古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联手实现了互证。
在法门寺唐代地宫,除了出土有《衣物帐》碑之外,还出土有《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根据这两通碑文大致可知,在法门寺唐代出土物中,既有唐懿宗的“恩赐”物,也有唐僖宗的“新恩赐”物。而十三件精美的“瓷秘色”正是属于前者。[7]毫无疑问,这十三件“瓷秘色”来源于李唐皇宫,属于皇家御用物品。另据北宋欧阳修《新唐书》记载,陆龟蒙实属不得志的文人,长期隐居在松江甫里。[2]列传196据此可以推断,陆龟蒙应该是难有机会与条件直接接触到类似于“恩赐”或“新恩赐”等御用器物的。某种意义上讲,陆龟蒙“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所表达的正是这一境况与情绪。由此可见,在唐代晚期,既有法门寺之“秘色”,也有陆龟蒙之“秘色”。换句话说,在9世纪后期,“秘色”既是皇家用品,也供给文人雅士。此外,从法门寺出土的未入《衣物帐》碑的青瓷八棱净瓶还可获悉,“秘色”可能还是佛家用器。(6)本文第1页脚注①中的青瓷八棱净瓶,从造型上看,应该属于佛家所用净水器,故有此推理。在“秘色”研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很容易被学界所忽视甚至误读的历史现象。(7)陈万里先生有:“唐代就有秘色瓷。越器是指民间用品,而秘色瓷是进御物品。两者同为越窑产品。”王莉英先生有:(秘色)“主要作为土贡或特贡品,为皇室和上层贵族所享用。”见陈万里《越窑与秘色瓷》,载《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第16页;王莉英、王兴平:《秘色越器研究总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以釉色命名瓷器其实是常有的事,因此“秘色”不可能不与釉色有关。对此,应该说清嘉庆时期郑廷桂“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8]的理解与表达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秘色”到底指何釉色或瓷色,在“秘色”研究中,似乎一直是个疑难问题。在《秘色越器》诗中,陆龟蒙用了“千峰翠色”来形容“秘色”之色。然而,对于何谓“千峰翠色”,却又是一个难解之谜。近年来围绕“千峰翠色”,学界也曾展开过较为广泛的讨论与商榷。但是由于陆龟蒙的思维太过文学、表达太过模糊,虽然颇费了不少周折,但学界似乎并未达成共识。殊不知,以谜解谜,其结果恐怕还是个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该说,用陆羽的《茶经》来解读“秘色”之色,似乎比从“千峰翠色”入手要来得更加直截了当。
二、《茶经》与“秘色”
《茶经》的作者,是中唐时期的文人陆羽。陆羽,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号“茶仙”。他约生于733年,约卒于804年。《新唐书》中有他的传,[2]列传121《文苑英华》中收有他的自传。[9]根据这些文献可以知悉,陆羽也是个隐士。陆羽一生著述颇丰,但让他真正闻名世界的还是《茶经》三卷。十分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中,陆羽竟然对越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全面的论证。在《茶经》卷中《四之器·碗》中,陆羽如是说: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10]
从品茶的角度出发,陆羽不仅认定越州瓷胜鼎州瓷、婺州瓷、岳州瓷、寿州瓷、洪州瓷等,甚至还认为越州瓷胜邢州瓷。殊不知,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内邱白瓮瓯”(即邢州瓷)与“端溪紫石砚”一样,都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珍品。[11]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是,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文学思维与模糊表达有所不同,陆羽的结论往往都是建立在他严谨认真的研究与论证之上的:从质感论,越瓷有“类玉”“类冰”之美;从釉色论,越瓷青,“青则益茶”;从造型论,越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从容量论,越瓯“受半升已下”,等等。可见,陆羽的“碗,越州上”与“瓯,越州上”,事实上已经蕴含了越瓷已然成为唐代“诸瓷之冠”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视陆羽为学者,视《茶经》为学术专著,似不为过。事实上,《茶经》的重大学术价值,不仅表现在人类茶文化史上,还表现在中国陶瓷审美史上。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以“玉质冰清”作为陶瓷美学之“格调最高雅、涵义最丰富、形象最美好的理想境界”[12],正是始于陆羽的《茶经》。
既然在《秘色越器》诗中,陆龟蒙已经明示“秘色”为越州之越窑所烧造,那么就越瓷与“秘色”之关系论,越瓷应属于“秘色”的母概念,“秘色”则属于越瓷的子概念。既然《茶经》成书要早于《秘色越器》诗,而陆羽又明确有“越瓷青”“越州瓷……青”的表达,那么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秘色”理应属于青瓷系列。如果上述推理大致不错,那么即便没有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十三件精美“瓷秘色”作证,只要做好陆羽《茶经》文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互证,同样可以推测出陆龟蒙笔下的“千峰翠色”所指之釉色。可见,陆羽的《茶经》虽然无“秘色”两字,但在“秘色”研究中,它的文献地位依然不可低估。十分遗憾的是,学界在“千峰翠色”指向的研究与论证上,似乎总在舍近求远,甚至画地为牢,对颇具文献价值的《茶经》未予足够的重视即是例证。
其实,陆羽的《茶经》对中国陶瓷文化史研究之文献价值远不止这些。在《茶经·四之器·碗》中,陆羽从质感、釉色、造型、容量等多方面论证了越瓷为“诸瓷之冠”的理由。可见,陆羽对越瓷的研究与鉴赏,并非停留在局部与个别,而是走向了立体与综合。这与诗圣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所表达的陶瓷鉴赏理念十分的相似。对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8)一作“寒”。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3]2448四句陶瓷诗,应该说清人的点评是非常清晰而精准的:“首句美其质,次句想其声,三句羡其色。”[13]无疑,这一审美层次是大大高于只谈釉色的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由此可见,早在8世纪的中国,不仅越瓷已经烧造得十分精美,而且文人圈综合鉴赏瓷器亦成时尚。其实,唐代文人这种综合研究、立体鉴赏的视角,才是陶瓷鉴赏之正道,是值得当代学者在“秘色”研究中认真学习与借鉴的。
不得不提的还有,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如果以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精美“瓷秘色”为标准器,将陆龟蒙“千峰翠色”之“秘色”,与陆羽“类玉”“类冰”之青色“越瓷”,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话,应该不难得出陆羽《茶经》的描述与法门寺实物之间的距离比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更近的结论。从生卒年上看,陆羽比陆龟蒙要早上半个世纪还要多。据此,我们似乎还可以有如下大胆的推测:越窑“秘色”的实际烧造,与越窑“秘色”概念的产生,在时间上并不同步;其烧造时间,不应该始于陆龟蒙的晚唐时期,至晚可以前提到陆羽的中唐时期。对此尽管目前既没有有力的考古支持,也没有直接的文献作证。
对于陆羽《茶经》之论瓷内容,有学者考证认为,并非原有文字,而是后人补入的。[14]的确,《茶经》论瓷并非十全十美。如其既有“越瓷青而茶色绿”,又有“越州瓷……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显然在表达上有自相矛盾之嫌。但是,其一,从唐五代之陶瓷发展史角度看,《茶经》对唐代七大名窑的研究与论证,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越瓷为魁”之主张,应该说是合理的。其二,从“越瓯”“越碗”“越瓶”“越瓷”“越器”乃至“越人”等皆成为唐五代时期文人咏题、赞美最多的对象[15]可知,越器为“唐时韵物”[16]当时已然形成共识。其三,以“类玉”来赞美瓷器,当时亦非个别现象,如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有“扣如哀玉锦城传”,顾况在《茶赋》中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17]等,而且杜甫与顾况的生卒年并不晚于陆羽。因此后人没有必要怀疑陆羽《茶经》论瓷文字的真实性。
三、《贡馀秘色茶盏》诗与“秘色”
《贡馀秘色茶盏》诗也是一首七言诗,其创作者叫徐夤。徐夤生卒年难考,从他公元894年和907年两中进士推断,其主要生活在晚唐五代时期。溯源中文文献可知,《贡馀秘色茶盏》诗应该是最早将“秘色”与“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文献。由于“贡”与“秘色”关系问题,与“秘色”釉色问题,为千年“秘色”研究中的两大基本问题,[12]因此尽管学界对《贡馀秘色茶盏》诗的重视程度远不及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但该诗的文献地位依然不容小觑。《贡馀秘色茶盏》诗共有八句五十六字,全文如下: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
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3]8174
显而易见,徐夤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了不起的陶瓷鉴赏大家。在《贡馀秘色茶盏》诗中,徐夤心中的“秘色”之美,不仅超过了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秘色”,而且超过了陆羽笔下“类玉”“类冰”的越瓷。在诗中,对于“秘色茶盏”的釉色之美与质感之美,徐夤用了“捩翠融青”“明月春水”“薄冰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中山竹叶”等系列华丽词藻进行比喻与描述。在诗中,徐夤还通过造型与薄胎等重要因素来表达“秘色茶盏”的烧造之美。如“秘色茶盏”具有“巧剜明月”的造型之美,“秘色茶盏”还有“轻旋薄冰”的薄胎之美,等等。可以想见,为了立体而综合地表达“秘色茶盏”之美,在词汇的搜集与应用上,徐夤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做到了“应用尽用”。毫无疑问,将“秘色”描写得美轮美奂的《贡馀秘色茶盏》诗,与将越瓷描写得美不胜收的《茶经》,业已成了唐代越瓷乃至“秘色”审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两段基础文献。(9)关于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所记对象,有唐代“秘色”说,有五代“秘色”说。历史文献记载的特征是,后代文献可以记载前代事,但前代文献则不可能记载后代事。结合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十三件精美“瓷秘色”,我们不难知悉,中国陶瓷美学的形成时期,其实是在唐代,并非学界常说的宋代。[18]不无遗憾的是,在中国陶瓷审美史研究中,相对于《茶经》的被重视程度,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的文献价值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除“秘色”审美之外,《贡馀秘色茶盏》诗的另一重大文献价值,就是徐夤于诗名和诗文中竟然两度使用了“贡”字,以及明确将“秘色”区分为“贡”与“贡馀”。
关于唐代的“贡”瓷,以及越窑烧造“贡”瓷等问题,应该说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等都能给予有力的支持。《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四曰河北道……厥贡……邢州瓷器”(10)该书约成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19];《新唐书·地理志》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2]志第31;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载,他曾受饶州刺史之托,向皇帝进贡瓷器。[20]显然,在唐代,邢州窑、越州窑、饶州窑等都在烧造“贡”瓷。另外,考古学家在浙江上林湖发现了两通墓志。一是唐光启三年(887)的《凌倜墓志》,一是宋开宝七年(974)的《罗坦墓志》。前者有铭文“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后者有“父是太祖肇启,毁家为国之时,立肱股于上林,与陆相公同置窑务”等铭文。据前者可知,至晚在公元887年,上林湖已经有烧制“贡瓷”的“贡窑”了;(11)此墓志罐于1977年出土于上林湖吴家溪唐墓,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参见厉祖浩编著:《越窑瓷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据后者大致可知,在唐乾宁三年即公元896年,钱镠占据浙东地区之后,便派遣有官员在上林湖设立“省瓷窑务”。(12)有学者研究认为:越窑“瓷窑务”的设立时间在唐乾宁三年(896)钱镠消灭董昌、据有浙东以后;其地点在越窑中心产地上林湖窑场。厉祖浩:《吴越时期“省瓷窑务”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3期。由此看来,明代嘉靖年间所修地方志中的秘色“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的表达是有根据的。(13)(清)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之《祕色甆》。显而易见,在唐代晚期,越州已然成为“贡”瓷的重要烧造地,为此还在当地设立有相应的管理机构。
徐夤虽然两中进士,但其身世似乎与陆龟蒙差不多,仍然属于不得志的文人,晚年隐居在福建莆田延寿溪。这一状况意味着徐夤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与条件直接接触到“贡”之“秘色”。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徐夤的为人并不虚伪,在《贡馀秘色茶盏》诗中,他如实地记载了这一状况。从“陶成先得贡吾君”诗句可知,“贡”宫廷使用的“秘色”,显然都是“陶成”的上等品;从《贡馀秘色茶盏》诗之诗名可知,徐夤诗中的“秘色”,其实是“贡馀”,而非“贡”;从全诗的表达可知,“贡馀”已经如此精美绝伦,那么“贡”品的审美境界应该更高。显而易见,在“秘色”与“贡”关系问题的表达上,如果说陆龟蒙《秘色越器》诗还有朦胧之意的话,那么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则可用直截了当、明确无误来形容了。看来,在晚唐五代时期,尽管“贡”是“秘色”的重要属性,但是“秘色”依然有着“贡馀”的属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历史事实。从这个角度讲,《贡馀秘色茶盏》诗之“以诗证史”的文献价值,显然并不逊色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不无遗憾的是,学界在征引与解读《贡馀秘色茶盏》诗时,总在有意无意地对最为关键的“贡馀”二字视而不见。《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氂,谬以千里”[21]。长期以来,学界如此这般地轻视文献、误读文献,怎么可能对“秘色”的内涵与外延给予较为准确的界定呢?
四、《侯鲭录》与“秘色”
关于“秘色”与“贡”的关系问题,除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之外,还有一种来自“世言”的声音。所谓“世言”,即民间传说。最早记载该“世言”的文献,应该是宋代赵令畤的《侯鲭录》。[22]该“世言”认为:“秘色”,为“钱氏有国”时,“越州烧进”;之所以称“秘”,是因为其“为供奉之物”,且“不得臣庶用之”。此即是说,“贡”才是“秘”之源,无“贡”便无“秘”。毫无疑问,这与前述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
针对“世言”所主张的“秘色”起源说,在《侯鲭录》卷六中,赵令畤进行了一番考证。其考证全文如下: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14)从赵令畤用陆龟蒙的诗来证明“唐时已有秘色”可知,他虽然标示了《陆龟蒙集·越器》,但他对《秘色越器》诗名应该是非常熟悉的。[22]
赵令畤,又名赵德麟,宋代文学家,《宋史》中有他的传。[23]卷244他生于1064年,卒于1134年,主要生活在北宋。他是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因而属于皇族集团成员。赵令畤与苏轼来往甚密,深受苏轼赏识,其“赵德麟”之名便来自苏轼。但由于受“苏案”的牵连,他亦落入不得志文人行列。[23]卷244因此与陆羽、陆龟蒙、徐夤等人稍有不同,赵令畤是具有皇族血统的不得志文人。
作为皇族成员,赵令畤对上层社会的情况应该有所知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越窑最后一次供奉时间是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24]此年赵令畤刚5岁,因此他很可能对“秘色”并不陌生。其“今之秘色瓷器”的说话口气,似可为此佐证。另从《侯鲭录》“世言……比见……乃知……”之严谨的行文格式可知,赵令畤与陆羽一样,应该是个思维缜密,且十分擅长逻辑推理和学术考据的学者。事实上,但凡知悉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人,都会认为《侯鲭录》关于“秘色”概念之起源的考证结果,即“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是可信的。从这个角度看,这并非十分疑难的考证。
值得继续深究的是,《侯鲭录》中的“世言”到底起始于何时?对此,赵令畤未作交待。但十分遗憾的是,学界也一直对此一问题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其实,它可能是“秘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据历史文献记载,钱镠实际控制浙江、形成割据,大约始于唐乾宁四年(897)。[25][26]卷77、78在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政权之后,钱氏政权还存续了18年,直至公元978年钱俶“纳土归宋”为止。[23]卷480可见,钱氏统治浙江的82年,实际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约10年,属于李唐王朝的藩镇;第二阶段约54年,为五代十国时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吴越国;第三阶段约18年,为赵宋王朝的附属政权。
在第一阶段,从相关历史文献,以及陆龟蒙诗、徐夤诗,甚至法门寺考古等皆可知,当时“秘色”虽“贡”,但并不禁止臣庶用,显然与“世言”不符。在第二阶段,钱氏虽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供奉”过“秘色”等,[27][26]卷78、79、80、81、82但从供奉次数不多、供奉数量不大,[28]以及钱氏家族墓几乎都出土有越窑青瓷等可知,[29]“秘色”似乎并非处于完全垄断状态。在第三阶段,应该说是钱氏供奉“秘色”的高峰期。据钱俨《吴越备史》载:仅在宋“太祖、太宗两朝”,钱氏便向北宋朝廷进贡有“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创造了历史之最。[25]为此,钱氏不得不在上虞增“置官窑三十六所”[30]等。而对于钱氏的倾巢进贡,宋祖却有言:“此吾帑中物,何用献为?”[26]卷82不难看出,赵令畤《侯鲭录》中的“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这三个极其严苛的条件,唯有在第三阶段才有可能实施。如果上述分析大致合理,那么《侯鲭录》“今之秘色瓷器”,并非指晚唐或五代之“秘色”,而是指宋初之“秘色”;赵令畤称“钱氏有国”,不称“吴越国”,并非指钱氏统治浙江的82年,而只是指北宋初的18年。由此看来,“世言”为北宋时期的民间传说的可能性最大,也最合情理。显而易见,学界误读《侯鲭录》久矣。(15)如,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有:“越窑瓷器在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这称呼的由来据宋人的解释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95-196页客观地讲,“秘色”毕竟烧造有约二百年之久。在这动荡不安的两百年里,政权一直在更替不止,“秘色”与“贡”的关系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从这个角度讲,相对于考证“秘色”之源起,《侯鲭录》更大的文献价值恰恰在于他记载下了当时流传亦达约百年的“世言”。
纵观我国古代陶瓷文化史,南宋应该是谈论“秘色”比较集中的历史时期。在赵令畤《侯鲭录》之外,曾慥(16)(宋)曾慥,生年难考,卒于1155年。《高斋漫录》、周煇《清波杂志》(17)(宋)周煇《清波杂志》成书于1192年。、叶寘(18)(宋)叶寘约生于公元1190年前后。《坦斋笔衡》、顾文荐(19)(宋)顾文荐的生卒年不可考。《负暄杂录》、赵彦卫(20)(宋)赵彦卫,约1195年前后在世。《云麓漫钞》以及施宿《嘉泰会稽志》(21)该志撰修于南宋嘉泰元年,即公元1201年。等文献都有谈论“秘色”的文字。从作者生卒年或者著作成书时间先后等推算,赵令畤应该是宋代第一个记载“世言”的人,也是第一个征引陆龟蒙《秘色越器》诗考证“秘色”之起源的人。换句话说,《侯鲭录》是宋代最早解读“秘色”的文献,其他宋代“秘色”文献在时间上都滞后于赵令畤的《侯鲭录》。不仅如此,宋代其他“秘色”文献,在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因袭”赵令畤《侯鲭录》的迹象。从学术发展史角度看,赵令畤的《侯鲭录》才是真正的具有原创价值的“秘色”文献。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在“秘色”研究中,学界似乎对《侯鲭录》如此重要的文献地位并不知情。否则在征引文献时就不至于对《侯鲭录》之外的其他“秘色”文献更为情有独钟。(22)如,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论“秘色青瓷”时,引叶寘《坦斋笔衡》作证,而不是赵令畤的《侯鲭录》。见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0-151页。当然,从“因袭”便是认可的角度看,宋代其他“秘色”文献并非毫无价值。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因袭”行为,至晚在南宋时期才事实上形成了关于“秘色”起源、“秘色”与“贡”关系的学术共识。值得提醒的是,南宋之后的“秘色”文献,总体上看其学术价值已经不是很高。[31]究其原因,或许与南宋末期“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32][33]有关。
结 语
在学术研究中,“秘色”是幸运的。因为1987年法门寺的发掘为其成功实现文献与考古“二重证据”之互证提供了可能与条件。然而,“秘色”又是不幸的。因为学界疏于在法门寺考古的基础上,对千年“秘色”文献进行细致梳理、认真甄别、深入挖掘,结果致使基础文献与其他文献、正读文献与误读文献之间的界线一直模糊不清。正如前述,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诗、赵令畤的《侯鲭录》等四段基础文献,不仅可以大致回答千年“秘色”研究中,“秘色”釉色和“贡”与“秘”关系等两大基本问题,[13]而且还可大致回答“秘色”之产地、起始、造型、质感、审美、变迁等许多问题。必须承认的是,其中不少问题的解决,恐怕仅靠考古资料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人们眼中乃至心中的“秘色”,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非依靠文献资料莫属。可见,在学术研究中,考古发掘固然十分重要,但无端轻视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放弃文献与考古之“二重证据”互证,并非睿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