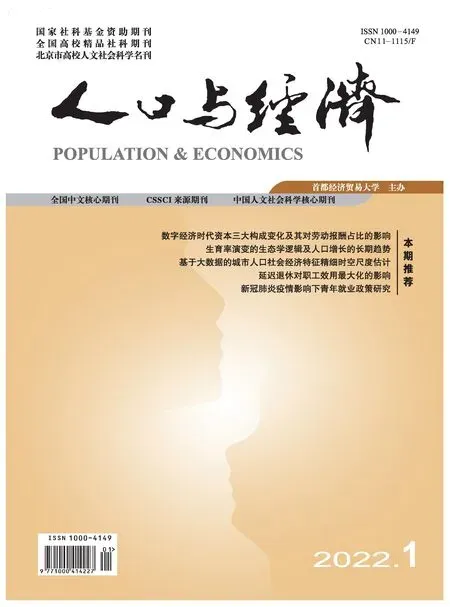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马 瑜,吕景春
(天津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38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精准脱贫攻坚的高效推进下,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共同富裕目标为新时代扶贫工作指明方向,因经济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城乡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治理的重点,扶贫政策更加关注社会弱势和边缘性群体是否能公平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同时需要监测低风险承担能力和低社会变化适应能力的脆弱性群体,防止其再次陷入绝对贫困。与新的贫困特征相适应,贫困标准界定和贫困指数构造方法也应随之调整和更新,为新时代贫困人口瞄准、贫困程度动态监测和贫困治理效果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已广泛应用于减贫实践的收入贫困识别方法主要包括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绝对贫困线是基本生活需要的货币度量,在短期内的名义价值会因通货膨胀和购买力水平而调整,但其实际价值固定不变,是发展中国家常用的贫困识别方法。然而,生活必需品会随社会、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被适应和扩展,社会融入成本也会不断增加,但绝对贫困线对居民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敏感,难以及时反映基本需要实际价值的变化。相对贫困线常根据某个国家(地区)居民家庭收入(消费)平均值(中位数)的一定比例(通常取40%—60%)设定,后被拉瓦雷(Ravallion)和陈少华称为强相对贫困线,是OECD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识别贫困的主流方法,但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
拉瓦雷和陈少华总结和比较了贫困线设定的两种理论基础。福利主义者基于相对剥夺视角认为个体效用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与相对收入水平相关。非福利主义者从能力视角出发认为个体免于贫困同时需要生存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而且实现社会融入能力所需的成本和支出是相对的。另外,通过实证研究115个国家的贫困线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拉瓦雷和陈少华发现国家贫困线在消费水平较低阶段增长缓慢,贫困线对平均消费的弹性接近于0,近似绝对贫困线;但在消费水平超过临界值后,国家贫困线随平均消费增长而迅速上升,弹性也随之增大渐趋于1,与强相对贫困线平行但截距大于0。正是基于各国贫困线与人均消费水平间的近似分段线性函数关系,在阿特金森(Atkinson)和布吉尼翁(Bourguignon)开创性地提出结合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AB相对贫困线后,拉瓦雷和陈少华分别从福利主义视角和非福利主义视角推导出满足弱相对贫困公理的弱相对贫困线,后有学者延续弱相对贫困线的设定思路并不断细化和拓展,提出社会贫困线和经基尼系数调整的弱相对贫困线。
然而,当采用强相对贫困线或弱相对贫困线识别贫困人口时,基于经典FGT测度方法计算的相对贫困率经常出现与绝对贫困率变化方向不一致的情形,难以直观比较贫困程度的时空演变并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综合减贫效应。例如,基于CFPS数据库测算中国城镇消费贫困在2012—2018年间的变化,绝对贫困率从8.82%减少到3.22%,而仅相对贫困率从13.86%增加到20.66%,意味着相对贫困率从22.68%增加到23.88%。为解决这一分歧,迪瑟夫(Decerf)通过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口进行分层加总,提出与弱相对贫困线识别方法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Hierarchical Additive Overall Poverty Index,HAOPI)。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贫困人口识别,采用HAOPI可测算得出中国城镇消费弱相对贫困从2012年的15.42%降低到2018年的12.89%,中国农村弱相对贫困状况也有类似趋势。可见,HAOPI对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有一个更为综合性和直观性的评估,尽管存在由高度不平等导致的较高相对贫困率,但由于绝对贫困大幅下降的贡献,中国城乡综合贫困指数在样本期间内仍然持续下降。
国内已有少量研究借鉴国际相对贫困标准设定经验,提出我国后扶贫时代分阶段和分区域的贫困线设计方案以及循序渐进的调整策略,并采用微观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研究多采用收入(消费)比例法作为相对贫困线的设计思路,但在基准值设定和具体比例值选择上,以及城乡分开或城乡融合计算,是否与国际标准接轨等问题上存在争议。极少数文献采用弱相对贫困线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如胡联等采用经基尼系数调整的弱相对贫困线识别弱相对贫困,李莹等采用社会贫困线制定相对贫困标准,但这些文献仍使用传统FGT指数测算相对贫困程度。
本文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考虑与现阶段绝对贫困线相衔接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采用弱相对贫困线分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具体区分为绝对贫困、仅相对贫困和非贫困三类贫困状态,并利用基于弱相对贫困识别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测度了中国城乡的收入(消费)综合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从新视角了解弱相对贫困人口的结构、分布特征以及动态变化趋势,有助于直观反映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以期为我国后扶贫时代建构贫困人口识别、测度和监测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测算方法
1.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理论基础:社会融入成本理论
基于森(Sen)的能力贫困方法,阿特金森和布吉尼翁构建了一种“能力—成本—贫困线”且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层次贫困识别框架,拉瓦雷和陈少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并推出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弱相对贫困线。综合上面的弱相对贫口人口识别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个体免于贫困需要两个层次的基本能力,优先考虑的第一层次能力是用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生存能力,第二层次能力是不被排斥在正常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社会融入能力。生存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的匮乏分别导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产生,且绝对贫困是比相对贫困更糟糕的生活状态,即相对贫困线应高于绝对贫困线。
第二,将需求从能力空间映射到消费空间,即将所需的生存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按照给定的价格转化为生存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社会融入成本可以理解为能够确保个体有尊严地参与通常社会经济活动所需的商品支出。森强调个体为避免贫困所需的能力和功能是绝对的,但实现能力所需的成本却是相对的,因时空差异而发生变化。因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变化,基本需要的构成会不断拓展,基本需要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满足基本需要所需的收入也随之提高。
第三,根据生存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分别确定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存成本的实际价值是基本固定的,可用绝对贫困线来表达,但社会融入成本与参照群体的收入(消费)平均水平相关,会随社会普遍接受的生活标准提高而增加。例如,当社会群体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受教育程度也随之攀升,低收入群体因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成本而被排斥在教育市场之外,又因受教育程度落后于劳动力市场需求而陷入贫困循环中。为简化问题,可以合理地假定社会融入成本与平均收入(消费)正相关,即相对贫困线会随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上升。
第四,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结合在一起,得到弱相对贫困线。当社会经济水平处于低位时,贫困线设定主要考虑基本生存需求,而生存成本随平均收入变化幅度不大,适合设定为平坦的绝对贫困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贫困线设定的重点转向相对剥夺问题,关注社会融入需求是否满足。因此在超过平均收入的某一临界值后,贫困线适合设定为随平均收入提高而上升的相对贫困线。此分段线性函数关系即可用弱相对贫困线表示。
2.弱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方法:弱相对贫困线


(1)


当≠0,≠0,=0时,即AB相对贫困线。阿特金森和布吉尼翁建议取世界银行的“每天1美元”标准(1985年购买力平价,以下简称PPP),并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水平的正比例关系,估计得出=037(1985年PPP)。AB相对贫困线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极端贫困国家无社会融入成本的论断缺乏说服力。


3.弱相对贫困程度的测算方法: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与弱相对贫困线相对应,贫困指数也应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广泛使用的传统FGT指数设计基于绝对贫困线识别方法,并不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测度。若基于强相对贫困线或赋权相对贫困较多的混合贫困线识别贫困人口,FGT指数的时空比较经常出现反直觉和相矛盾的问题。而基于弱相对贫困线识别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HAOPI)不仅满足聚焦公理等贫困公理,还可以避免传统可加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出现的分歧问题,且有更为直观的解释。
(1)传统FGT贫困指数测度相对贫困的缺点。常用的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均为可加FGT指数的特例。FGT指数表示为:

(2)
当=0时,FGT指数即贫困率,绝对贫困率、仅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分别为:

(3)

(4)

(5)
当=1时,FGT指数即贫困差距率,绝对贫困差距率和相对贫困差距率分别为:

(6)

(7)

(2)基于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迪瑟夫认为“不论社会贫富,绝对贫困个体比仅相对贫困个体更加贫困”,并在此假定下采用弱相对贫困线分类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分别计算个体的贫困贡献,最后加总得到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HAOPI)。
考虑一个贫困测度函数(),用于度量收入分布的弱相对贫困程度。

(8)


(9)

三、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估计
本文考虑城乡生活水平差异和价格水平变化,并与现阶段绝对贫困线相衔接,设定了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2011年标准,并分别从收入和消费视角估计得出我国各年度分城乡的弱相对贫困线。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有全国代表性。家庭人均收入是贫困测算的核心变量之一,考虑到CFPS中2010年的基线调查与后续追踪调查在收入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别,而2012年以后的历年收入数据在统计口径上基本一致,更具可比性。因此,本文选取CFPS中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家庭层面追踪调查数据库。经缺失值处理后,各年样本涵盖家庭户数均约在11600—14300之间,城乡家庭比例基本相当,但在逐年增加。
2.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设定标准


表1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2011年标准 元/年,人

二是确定相对贫困线部分的截距项,将按中国城乡调整系数转换成2011年以人民币计的价值。2011年“1天1美元”在中国城市相当于“1天3.9元”,在中国农村相当于“1天3.04元”,也就是城市1423.5元/年和农村1109.6元/年,即城市和农村社会贫困线的截距部分。弱相对贫困线与社会贫困线的区别仅在于截距项,将社会贫困线的截距乘以0.4即可得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截距分别为569.4元/年和443.84元/年。


图1 基于不同识别方法的2011年中国城镇贫困线比较

图2 基于不同识别方法的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线比较
3.基于收入(消费)的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
(1)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步骤。基于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2011年标准(见表1),经各年全国城乡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代入各年收入(消费)的中位数,即可推算得出其他年度的绝对贫困线(APL)、强相对贫困线(SRPL)、弱相对贫困线(WRPL)和社会贫困线(SPL)。收入弱相对贫困线和消费弱相对贫困线的估计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 元/年

表3 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位数的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 元/年
首先,估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的绝对贫困线部分()。①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根据《2019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可得同等生活水平下其他年度可比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依次是2625元、2800元、2952元和2995元。②全国和城市的绝对贫困标准。考虑物价水平变化,为确保全国和城市弱相对贫困线的2011年标准(见表1)所代表的生活水平不变,利用全国和城市CPI,将2011年标准调整到其他年份(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水平,得到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各年度全国和城市的。

(2)估计结果分析。弱相对贫困线(WRPL)和社会贫困线(SPL)同时考虑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分别用和识别。从表2可以发现,历年均大于,但差距随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增长而扩大。从表3可以发现,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位数估计的贫困线有类似特征和趋势,且消费弱相对贫困线的比收入弱相对贫困线更低。
四、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程度测算及时空演变
在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基础上,应用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分别从收入和消费视角测度了中国及代表性省份的城乡弱相对贫困程度及动态变化趋势。
1.我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1)我国城乡收入弱相对贫困测算及动态变化。经收入弱相对贫困线识别出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后,中国城乡历年的收入贫困率、贫困差距率及综合贫困指数如表4、图3和图4所示。由测算结果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无论城乡,绝对贫困程度大幅度下降,农村减贫效果尤其显著,但农村贫困程度仍显著高于城镇。从表4的第(1)列和第(4)列可以看出,2012—2018年期间,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大幅增长,绝对贫困显著下降。全国的绝对贫困率()从19.34%下降到8.45%,贫困差距率从10.24%下降到3.6%。从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均可看出,城镇和农村的绝对贫困程度连续下降,农村下降幅度更大,农村绝对贫困率()从2012年的21.72%下降到2018年的9.97%,城镇绝对贫困率从13.02%下降到4.24%。

表4 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贫困指数及动态变化 %

图3 不同测度方法下中国城镇贫困率变化趋势比较

图4 不同测度方法下中国农村贫困率变化趋势比较
第二,无论城乡,相对贫困程度下降缓慢,仍维持在高位水平。从表4的第(2)列和第(3)列可以看出,2012—2018年间,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程度也在增加,这一点不仅由表2的高基尼系数得出,同样体现在严重的相对贫困程度上。仅相对贫困率()逐年增加,部分群体尽管脱离绝对贫困但生活水平仍在相对贫困线之下,进而使得相对贫困率()基本无变化,从2012年到2018年仅下降了2.81%(=29.92%-27.11%)。与绝对贫困的巨大城乡差异不同,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同样严重,但农村的下降趋势比城市更为显著。在2012年,农村的相对贫困率高达30.87%,比城市高出4.84%,但2018年城乡的总相对贫困率()基本持平,一方面可体现农村减贫政策效应,另一方面可能受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考察期间内相对贫困差距率表现出类似趋势,各个年度城乡相对贫困差距率均高于10%,但农村相对贫困差距率比城市下降幅度快,在2012年和2014年,农村相对贫困差距率高于城市,但在2018年基本持平。
第三,无论城乡,用于测算弱相对贫困程度的综合贫困指数()稳健下降,下降幅度介于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之间,可有效评估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从表4的(1)、(3)和(7)列,以及图3和图4可得:首先,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是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加权平均,可以看作贫困率的拓展,不仅反映了绝对贫困,而且惩罚了高度不平等。其次,尽管高度不平等程度导致严重的相对贫困率,但绝对贫困的大幅度减少使得综合贫困指数()在2012—2018年期间持续下降,从2012年的24.49%下降到2018年的17.98%,下降了6.51%,尽管下降幅度低于(下降了1089),但高于(下降了2.81%)。最后,农村弱相对贫困程度虽高于城镇,但下降幅度更大。城镇弱相对贫困程度从2012年的19.4%下降到2018年的13.98%(下降了5.42%),农村弱相对贫困程度从2012年的26.14%下降到2018年的17.71%(下降了8.43%)。
第四,如果用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来衡量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当不平等效应超过经济增长效应时,和之间,以及和间会出现分歧,而综合贫困指数平衡了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变化趋势不一致的问题。比如城市2012年到2014年的贫困状况,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测量上即出现分歧。从13.02%降低到11.52%,从699降低到587;而则从2603上升26.86%,从13.10%上升到13.41%。综合贫困指数综合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情况,因绝对贫困下降幅度比相对贫困上升幅度大,绝对贫困的贡献更大,总体仍呈现下降趋势(从19.40%下降到19.14%)。这一期间的农村表现出类似特征,传统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测度方法出现分歧。
综上,中国城乡收入贫困在2012—2018年间的变化趋势如图3和图4所示。绝对贫困率()、综合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在2012—2018年间均持续下降,但变化幅度依次减弱。
(2)我国城乡消费弱相对贫困的测算及动态变化。在消费弱相对贫困线识别出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后,同样可得2012—2018年中国城乡消费贫困的动态变化特点。消费贫困率、消费贫困差距率和消费综合贫困指数如表5所示,分析结论如下:第一,与收入绝对贫困特点类似,无论城乡,消费绝对贫困大幅下降,农村绝对贫困程度更为严重。由于消费水平低于收入水平,而绝对贫困标准相同,使得消费绝对贫困率普遍比收入绝对贫困率低,绝对贫困差距率亦有类似特征。无论贫困率还是贫困差距率,农村消费绝对贫困比城市更为严重。第二,消费相对贫困率()在2012—2018年间普遍变化幅度不大,城乡差异亦不显著;相对贫困差距率()呈现上升趋势,农村尤其显著。第三,在考察样本期间,消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出现分歧,即和,以及和的变化趋势普遍不一致,难以评估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第四,与收入综合贫困指数变化趋势一致,消费综合贫困指数呈持续下降,但水平普遍比收入综合贫困指数低。

表5 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贫困指数及动态变化 %
2.我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
在省际贫困程度差异分析时,选取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广东五个省份城乡进行测算,为更具可比性,各省份的贫困识别标准仍以全国而非全省为参照群体。
(1)我国城乡收入弱相对贫困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测算的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率()和综合贫困指数()及时空差异如表6所示。

表6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收入贫困指数的时空差异 %
第一,除上海外,代表东、中、西部的四省份相对贫困率普遍严重,欠发达省份甚至有上升趋势。首先,除上海外,其余四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均在20%以上,河南和甘肃高达30%以上。发达地区上海和广东的相对贫困率均有下降,如上海从2012年的8.49%下降到2018年的1.29%。欠发达地区河南和甘肃的相对贫困率均有上升,如甘肃从2012年的37.66%上升到2018年的41.96%,这与相应省份绝对贫困率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其次,2012年城镇的相对贫困率普遍低于农村或基本持平,但到2018年,除辽宁外,城镇的相对贫困率普遍超过农村或基本持平。如甘肃,2012年农村(3322)比城镇(2517)高出805,但城乡相对贫困差距在2018年发生逆转,城镇(3649)比农村(2911)高出738。最后,多个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在2012—2018年间的变化趋势与绝对贫困率出现分歧,难以有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比如河南和甘肃的城镇地区。
第二,从综合贫困指数()可以看出,弱相对贫困稳健下降,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广东、上海、辽宁、河南和甘肃的弱相对贫困程度下降幅度依次递减,尽管河南和甘肃的绝对贫困大幅下降,但由于相对贫困上升,导致综合贫困程度下降幅度较低。除甘肃外,农村综合贫困率普遍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无论城乡,除甘肃城镇地区外,综合贫困率均下降显著。
(2)我国城乡消费弱相对贫困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测算的绝对贫困率()、相对贫困率()和综合贫困率()及时空差异如表7所示。与表6比较发现,消费贫困的、和普遍低于收入贫困相应指数。

表7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消费贫困指数的时空差异 %
第一,与收入绝对贫困特点类似,消费绝对贫困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更为严重。第二,消费相对贫困率的变化趋势及城乡差异与收入相对贫困所呈现特征略有不同。比如,消费相对贫困率在辽宁呈现上升趋势,在河南呈现下降趋势,与相应省份收入相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第三,通过消费贫困的和的变化趋势难以得出减贫效应评估的一致结论,比如辽宁和甘肃。第四,除2012年的广东和甘肃外,城镇的消费相对贫困普遍高于农村或基本持平。第五,与收入弱相对贫困特点及变化趋势一致,从可以看出,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稳健下降。在2012年,农村综合贫困更为严重,但到2018年,上海、河南和甘肃的城乡差距发生逆转,城镇地区的消费综合贫困率高于农村。
五、结论与建议
相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方向,但只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强相对贫困线,忽视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性,因此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由社会融入成本理论导出且满足弱相对贫困公理的弱相对贫困线更科学合理。另外,传统基于绝对贫困构造的FGT指数不再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测量和贫困程度的动态分析。基于弱相对贫困识别构造的有更好的贫困性质并在动态分析上有更直观的解释。
本文采用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历年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基于弱相对贫困线对绝对贫困人口和仅相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分类识别,应用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测度了中国城乡的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在样本考察期间(2012—2018年),主要有以下新的发现。
第一,如果采用基于FGT方法计算的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来衡量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当不平等效应超过经济增长效应时,收入(消费)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在测度中国城乡和多个省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程度及其动态变化上出现分歧,难以直观反映和有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综合减贫效应。在样本考察期间,中国收入(消费)绝对贫困程度大幅下降,农村减贫成就尤为卓著;而相对贫困程度持续处于高位水平,甚至欠发达省份有上升趋势。第二,综合贫困指数在评估弱相对贫困程度及其变化趋势方面有诸多优势。平衡了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可以看作贫困率的拓展,不仅反映了绝对贫困,而且惩罚了高度不平等,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变化趋势不一致的问题。尽管高度不平等程度导致严重的相对贫困率,但绝对贫困的大幅度减少使得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在2012—2018年期间稳健下降,下降幅度介于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之间。
根据本文的分析,针对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度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识别贫困人口与评估减贫效应时,应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借鉴和拓展满足弱相对性公理的弱相对贫困线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第二,未来可进一步细化收入、消费贫困线,分地区、家庭规模和结构以及年龄制定更为详尽的贫困标准,提高贫困人口瞄准的精确性。第三,贫困识别和测度不仅要考虑经济维度的不平等,同时要重视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体面就业等社会维度的相对剥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和指数测算体系。同时从社会融入成本和社会融入能力角度可得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政府需继续加强住房市场干预,稳定房价,让住房从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属性,逐渐剥离住房与城市落户、子女入学、公共服务等重要福利的牵连,减少城市移民获取住房资源的成本,避免因住房的过度投资功能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社会流动。第二,切实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继续加强校外教育市场的治理,减少家庭的教育成本。第三,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平台,通过人力资本开发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入能力,让弱相对贫困群体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有公平机会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