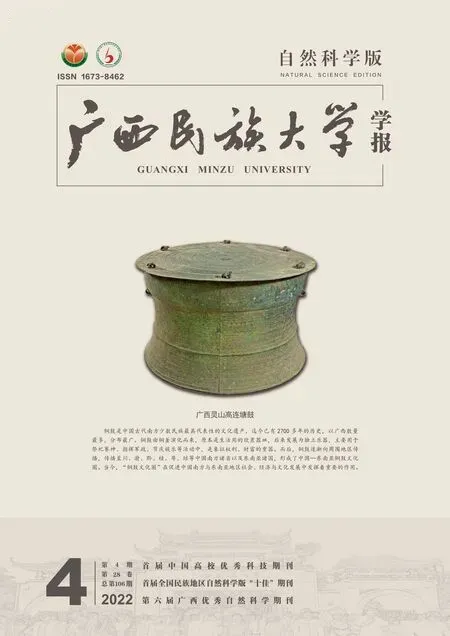朱洪元与粒子物理 *
丁兆君,李守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 合肥 230026)
1 出身于工程世家
1917年2月,朱洪元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工程师之家。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德国汉诺威大学,并获授特许工程师学位。父亲朱重光专长于水利航运,母亲王祖蕴专长于建筑。在20世纪早期,像王祖蕴这样能在学业和事业中都有所成就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朱洪元的外祖父在家中兴学,王祖蕴常常在窗外听课,由此接受了启蒙教育。后来她进入学堂,由于成绩优异,一直都免交学费。中学毕业后,王祖蕴只身前往新加坡教书,任南洋女子中学校长,然后又攒钱去德国留学,于1928年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归国的女工程师。至今,在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朱洪元的故居中,还挂着他的母亲王祖蕴留学德国时的建筑制图作品。在朱洪元刚满月的时候,王祖蕴便把他寄养在外婆家,然后自己辗转于新加坡、德国,且教且学。朱洪元4岁时入和桥镇养初小学读书,10岁时入彭城中学,11岁时转到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16岁那年,朱洪元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次年入同济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想弃学从军,抗击日寇,后在母亲的苦苦劝求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坚持把大学读完。母亲顽强、坚毅的性格,刻苦、认真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朱洪元。读大学时,朱洪元是工学院著名的高才生,头脑灵活,成绩突出。大学毕业后,朱洪元怀着为抗战出力的愿望,曾到重庆一家兵工厂工作,后又辗转到昆明机械厂工作。其间,他因患肺结核而回到学校,半工作半休养。[1]后来在学生们的申请下,他教授大学二年级的流体力学课程。据同济大学的1944届毕业生、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式枢院士回忆,听朱洪元的课,“很受启发,感到茅塞顿开”[2]310-311。
1944年,朱洪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文化协会的机械工程留英资助生。这对于当时以德文作为第一外语的他,实非易事。1945年,朱洪元踏上了赴英留学之路。
2 同步辐射研究的先驱
到了英国,朱洪元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学习机械(图1)。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机械并非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于是他便转到了物理系,师从194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系主任布莱克特(P.M.S.Blackett)。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具有辉煌的历史,卢瑟福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划时代的α粒子散射实验,并提出了原子核式结构模型。布莱克特曾作为弟子,在卢瑟福的指导下做过出色的研究。朱洪元转到布莱克特门下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理论物理的研究论文,[3]可见其“转型”之快。

图1 1947年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师生合影,前排为J.G.Wilson(左三)、G.Rochester(左四)、J.Braddick(左五)、J.Nuttall(左六)、P.Blackett(左 七)、L.Rosenfeld(左 八)、D.Broadbent(右一),二排右三为朱洪元
布莱克特曾设想过,宇宙线中的高能电子在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前,因地磁场的影响放出辐射,而在经过大气层后可能会在地球表面产生一个特大范围的光电簇射。他把这个问题交给朱洪元去研究。经过周密的考虑与精心的推演,朱洪元最终得到了这种辐射(即如今所谓的“同步辐射”)的能谱、角分布、强度、波长及极化的表达式。[4]结果表明,由于辐射只集中在一个沿电子速度方向很小的角度范围内,其实不会产生大范围的光电簇射,这与其导师布莱克特原先设想的结果大相径庭。为慎重起见,布莱克特让朱洪元把文章送交给当时客居英国的印度著名物理学家巴巴(H.Bhabha)审阅,巴巴亦提出了质疑。于是,朱洪元进行了认真的复核验算后复信巴巴(图2),解释其计算中的一步积分如何导致其结果与经验相左,从而消除了巴巴的疑虑。[5]在布莱克特的推荐下,朱洪元的论文《快速荷电粒子在磁场中所放出的辐射》于1948年2月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

图2 朱洪元致巴巴信
在朱洪元的论文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刊》接受一个月之后,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用电子同步加速器发现了同步辐射现象。1949年3月,美国物理学家施温格(J.Schwinger)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加速电子的经典辐射》一文,正是在研究加速器中的电子辐射性质的基础上得到了同步辐射的结论。施温格与朱洪元的工作结果相同,都是关于同步辐射应用的奠基性文章。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一个针对的是加速器产生的粒子,另一个针对的是宇宙线粒子。苏联的伊万年柯(D.Ivanenko)和索柯洛夫(A.A.sokolov)也在1948年3月发表文章,公布了其类似的工作。多年以来,人们总是把同步辐射与施温格、伊万年柯等联系起来,却忽略了朱洪元的奠基性工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1988年5月,北京召开同步辐射应用的国际会议,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同步辐射实验室(BSRF),并任该实验室第一任主任的冼鼎昌向大家展示了朱洪元那篇40年前发表的关于同步辐射的文章。在场的美国斯坦福同步辐射实验室教授、同步辐射应用权威温尼克(H.Winick)在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走到朱洪元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您在同步辐射发展初期,就进行了如此重要的工作,能够认识您,我感到很荣幸!”[5]13-14顿时,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很快,朱洪元那篇同步辐射应用的奠基性文献,在与会代表中传阅开来。
1947年,由布莱克特领导的宇宙线研究组成员罗彻斯特(G.D.Rochester)和巴特勒(C.C.Buttler)在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地下室的云雾室中,拍摄到了大量宇宙线簇射粒子的照片,并从中发现有两个呈V字形的径迹,这是粒子衰变形成的。对此,朱洪元最早作了估算,并指出衰变前粒子质量的下限为电子质量的900倍。这正是后来所谓的“奇异粒子”。笔者在朱洪元先生的家中亲见了当初由罗彻斯特和巴特勒所发表、如今业已发黄的论文中提到了他的工作。
1948年,朱洪元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物理系帝国化学工业科学基金会研究员,为期3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得悉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朱洪元于10月离英回国。
3 “层子模型”放异彩
自1950年回国至1957年,朱洪元一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该所后经扩建,于1958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朱洪元任理论研究室主任。
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粒子物理实验突飞猛进,与之相应的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包括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论、V-A理论、零质量中微子理论、中间玻色子理论等。而国内学术界却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1958年,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I.Y.Tamm)来访中国。朱洪元从他那儿得知了由费曼(R.P.Feynman)、盖尔曼(M.Gell-mann)与马沙克(Robert Marshak)、苏达山(E.C.George Sudashan)等人刚提出的普适弱相互作用的V-A理论。于是,他立即领导一个小组进行研究,讨论了K+介子衰变的分支比,并探讨了μ-子在质子上的辐射俘获过程,发现一个选择定则,并在后来进一步阐明了原因。
1959-1961年,朱洪元被派往苏联参加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色散关系对π介子之间及π介子与核子之间的低能强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与其合作者发现当时流行的角动量分波展开存在很大的误差,指出由此方法导出的方程含有不应有的奇异性质,从而否定了这个在1959年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由著名物理学家丘(Geof⁃frey F. Chew)和曼德斯塔姆(Mandelstam)提出的流行一时的方案,并推导出不含发散积分的π-π及π-N低能散射方程。
1961年,朱洪元自苏联回国以后,主要从事包括光子、电子、中子和原子核在内的高温、高密度系统的输运过程、反应过程和流体力学过程方面的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粒子物理学界进入研究强相互作用粒子内部结构的新阶段。早在1949年,费米(E.Fermi)和杨振宁就提出了π介子是由核子与反核子组成的假说。1955年,坂田昌一(S. Sakata)又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在内的强子结构的复合模型。1964年,盖尔曼和兹维格(G.Zweig)又改造坂田模型,提出夸克模型。这是一种由对称性分析得出的唯象理论,连盖尔曼本人都觉得夸克只是一种数学上的实体。
1965年,以朱洪元、胡宁为首,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数学所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个单位的39位粒子物理学工作者组成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图3)分析了当时已累积的实验和理论资料,认识到“基本粒子”并不基本,而有其内部结构。朱洪元考虑到在当时已知的最高能量下,在强子内部的微小尺度范围中,用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描述状态、用算符描述物理量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仍然有效,提出引入强子结构波函数来描述强子的状态,而强子的组成及其所遵从的对称性是否符合夸克模型或坂田模型的其他变种,则有待实验检验。他引入始态和终态强子结构波函数的重叠积分概念和具有特定对称性的强子构成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计算跃迁矩阵元,用以统一地描述一系列强子的转化过程。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在1965-1966年的9个月里发表了40多篇论文,得到了一系列理论结果。根据钱三强的建议,基本粒子理论组把强子的组分粒子称为“层子”,意谓强子的结构具有层次性,每个物质基元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基于“层子”概念,学术界把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提出的这一套理论称为层子模型理论。

图3 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讨论(左茶几后,左起为戴元本、朱洪元、胡宁)
1966年7月,亚太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在会上公布了层子模型的主要结果。在会后的招待宴会上,巴基斯坦物理学家、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萨拉姆(A.Salam)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称赞层子模型“是第一流的科学工作”[6]148。
“层子模型”是强子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开拓,它是在强子构成组分之间的动力学理论提出之前的一项重要探索性工作。层子模型理论提出的强子内部结构波函数和波函数的重叠积分的概念沿用至今,并随着强相互作用的动力学理论的建立而逐渐得以确定。可惜的是,“文革”期间,朱洪元等人的这一研究工作被打断。“文革”期间,国际上的粒子物理学科在飞速发展,强子结构沿着夸克模型的思路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层子模型的理论则被抛到了时代的后面。[7]
1980年1月,在广州市郊从化县,由李政道与杨振宁发起,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举办的国际华人粒子物理理论研讨会盛况空前。在此国际会议上,朱洪元以《层子模型的回顾》为题作大会报告,全面介绍了层子模型理论,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肯定。[8]1982年,朱洪元等因层子模型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 从理论拓荒到执鞭科大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研究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家屈指可数,仅有朱洪元、胡宁、彭桓武、张宗燧等人。当时国内可资参考的有关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书籍也少得可怜,而且内容陈旧,理论粒子物理的研究几乎是一片荒原。为了使有志进入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年轻人尽快掌握一些基础理论知识,1957年,朱洪元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量子场论”课,比较系统地讲授了这门前沿理论课程。1958年,在青岛举办了“量子场论”讲习班,朱洪元又为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60多名学员讲授了“量子场论”课,把听众从最基础的出发点引领到当时量子场论发展的最前沿。北京大学的授课和青岛的暑期讲习班,是粒子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普及,造就了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影响极其深远。[9]朱洪元的授课讲义后来整理成《量子场论》一书出版,成为中国几代粒子物理工作者的主要教科书和研究工作参考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成立不久,朱洪元便在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后更名为近代物理系)担任兼职教授,并兼任系副主任,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原子能所与科大之间。他认为,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到科大教学对其科学研究是有帮助的。听一门课与授一门课大不相同,研究人员从事了一定时间的研究工作后,到学校教学,不仅支援了学校的师资,而且可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加强基础。“要拿出一碗水,就得有一桶水”,这当然要多费心力,虽然苦些,但很值得。同样,学校的教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也可以到研究所里参加一些研究工作。这样不仅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好处,而且对科学研究也有好处。朱洪元的这些观点非常符合科大“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
朱洪元在科大所讲授的课程除了有“量子力学”“量子场论”这样的物理课程,还有“群论”这样的数学课程。谈到他授课之精彩,科大前几届毕业生一直赞不绝口。他所讲授的几门课程,艰深晦涩,要用到大量的数学知识,不容易学习也不好讲授,很容易给人以枯燥无味之感。而朱洪元总是将其内含的物理意义阐述得很清楚。譬如他讲到量子力学中用波函数描写粒子时,做了非常浅显的比喻:就像月亮,今天你看到它的这一面,认为是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你又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又认为它是另外一个样子,其实都是、又都不是。
朱洪元的治学严谨为粒子物理学界所公认,与此相应,他所授之课程亦正如他所著之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推导严格。被公认为朱洪元“四大弟子”(张肇西、黄涛、李炳安与杜东生)之一的科大近代物理系毕业生张肇西,当初就是被朱洪元的“群论”课的内容及其严谨的讲授风格所吸引而报考了他的研究生。[10]而他的另一位弟子李炳安则是当初量子力学课的课代表,同样是为其渊博的学识与精彩的授课内容所吸引。[11]
5 热心于实验的“物理界大人物”
1958-1973年,朱洪元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他不仅在理论物理研究中是所内的“领头羊”,而且也为中国建立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72年,朱洪元与张文裕、谢家麟等18名科学家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加强基础研究,建造高能物理实验基地。[12]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次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朱洪元先后任研究员、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他还长期担任《物理学报》副主编和《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高能物理》主编,此外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的主编。
1973年,朱洪元与张文裕等率团考察美国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及西欧核子研究中心(图4),其后逐渐形成了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方案。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该方案未能付诸实践。1981年,中国科学院派朱洪元、谢家麟会同当时在美访问学者叶铭汉,在李政道的协调下,到芝加哥费米国家实验室与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实验室的负责人进行非正式会晤,通报中国高能加速器调整方案,并听取他们对此方案的建议。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W.K.H.Panofsky)提出了建造2.2 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朱洪元、谢家麟对潘诺夫斯基的方案进行了非常详细且审慎的研究。朱洪元考察了该对撞机物理窗口的意义和生命力,并联系在美进行合作研究的中国高能物理访问学者,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谢家麟则考虑技术、经费与器材等问题。后来中国按照这个方案成功地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5),进行了高能物理实验和同步辐射应用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这与朱洪元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

图4 朱洪元率团赴国外考察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右起为谢家麟、吴健雄、朱洪元

图5 1984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工典礼上合影,左起为方毅、李政道、周培源、宋健、朱洪元、谢家麟
1992年11月4日,朱洪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中国物理学界的一颗明星就此陨落。半个月后,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物理界接连伤逝三大人物(钱三强、朱洪元、张文裕)!不胜悲伤!”[13]230这也道出了其他物理学界同仁乃至朱洪元所有同事、学生以及受过他影响的人们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