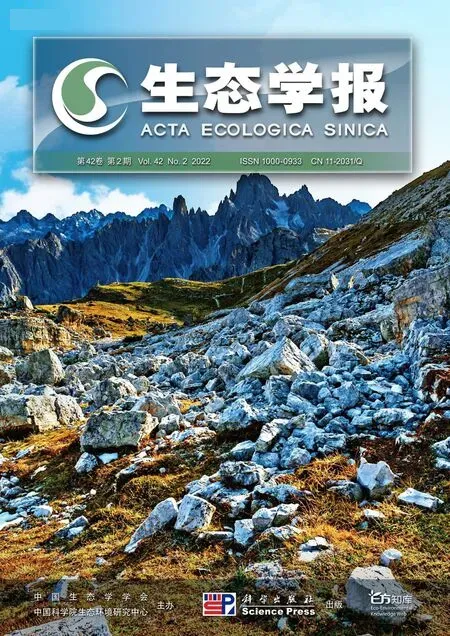福建省安溪县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关键驱动因素
江文甲,林满红,翁佩莹,庞孜钦,林文雄,魏道智,苏 凯
1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福州 350002 2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 福州 350002 3 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福州 350002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土地资源不合理利用已经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倒逼人们开始重视土地利用如何向合理利用的路径转型。另一方面,将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探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和景观生态格局演变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格局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4]。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区和生态脆弱区,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空间自相关和地统计学等方法,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空间分布格局[5—6]。多数学者基于线性相关,采用多元回归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7]。近年来有学者应用基于非线性假设的典范对应分析方法(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认为CCA能够直观地分析现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作关系[1,8]。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西部和北部的干旱、半干旱等水资源匮乏区域,而有关经济相对发达的我国东南部,特别是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分布并不均匀的福建闽南旱地生态环境脆弱区研究则相对较少[5,9]。本研究之所以选择福建乃至全国重点产茶第一县安溪作为研究的特定研究区位,是因为该县以茶业闻名全中国,是山地茶叶经济的典型代表和成功范例[10]。近20年来,随着人口不断的增加,安溪茶园面积也不断扩张,使茶产业一跃成为县域主导经济[11];由于安溪地处福建闽南丘陵山区,其地质结构较为复杂,地块破碎化程度较高,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程度也较为强烈[12]。例如,人们为了进一步发展茶产业,大量高坡度、低质量的茶园盲目开垦,在生产和开发过程中也不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导致水土流失现象相当普遍,安溪县生态环境相对脆弱[11,13]。而这种发展及资源消耗模式已导致诸多问题产生,如生态环境响应对土地利用变化十分敏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分散等[14—15],这势必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生态效益[16—18]。因此,选定该区域作为研究区域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为此,本研究运用地理信息学、空间自相关和典范对应分析等方法探究安溪县1999—2019年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以期为优化该地区土地资源配置和合理开发利用,进而为制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安溪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介于117°36′—118°17′E、24°50′—25°26′N之间)(图1),属泉州市管辖,下辖24个乡镇460个村居,总人口120 多万,其中农业人口 91.56 万,人均粮食种植面积远低于全省人均水平,仅为 0.019 hm2/人。由于地形地貌的差异,形成具有明显气候特点的内外安溪。东部外安溪属南亚热带,年均温度19—21 ℃,年降雨量1600 mm;内安溪年均温度16—18℃,年降雨量1800 mm,全年四季分明,是种植乌龙茶的优良区域。2019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达725.70 亿元,常住人口102.5万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7.73%、49.84%和42.42%。全县拥有茶园面积4万余hm2,约占福建全省茶叶总面积的1/3,已连续7年蝉联100个全国重点产茶县第一位,其铁观音茶叶品牌闻名中外,茶叶及其相关产业总产值达155.81亿元。从事茶叶及其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因此,茶产业是安溪县的经济支柱,也是农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然而,由于安溪县地处戴云山脉向东南延伸部分,平均海拔在700 m以上,主要河流贯串盆地,并切穿盆地之间的山岭。因此,保护好现有丘陵山地资源以及合理利用是解决当前安溪县人地矛盾问题的关键[19]。

图1 研究区区位图 Fig.1 Bitmap of research districts
2 材料和方法
2.1 数据采集及处理
本研究选取1999年、2009年和2019年三期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为30m×30m)为基础,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通过影像拼接、目视解译等一系列程序操作后,获得安溪县土地利用分类数据,由此建立安溪县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库。经检验,3期遥感影像的Kappa系数值和解译精度分别大于0.85和大于90%,符合研究要求。此外,社会经济数据则主要来源于《安溪县统计年鉴(2000—2020)》及历年统计公报。
2.2 研究方法
2.2.1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可以定量描述土地利用的变化速度,对于比较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和趋势起着重要作用[20]。其公式如下:
(1)
式中,K指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Ua、Ub分别表示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某种地类面积,T用来表示研究时段长。
2.2.2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对附近观测值之间相似性(相关性)的度量,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前者是在整体上判断土地利用变化是否存在聚集性特征,但无法确切的描绘出哪些地方存在聚集现象;后者则是在局部上判断土地利用变化是否存在相似的空间聚集状态。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分别采用Global Moran′sI统计量和Local Moran′sI统计量表示,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21—22]:
(2)
(3)
式中,n表示单元数量;xi、xj表示i和j地某要素属性值(i≠j);Wij为空间权重矩阵。I>0、I<0 和I=0分别表示空间分布呈空间正相关、空间负相关和空间无相关。
2.2.3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典范对应分析(CCA)是一种多变量约束排序技术,旨在从生态环境数据集中提取综合环境梯度,用于阐明物种的生物组合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1, 23]。因此,本研究采用典范对应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合,进一步讨论与明确安溪县及其所属乡镇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差异性特征。
(1)指标选取 研究选取了安溪县及其所属24个乡镇作为空间分析样本,从县域和镇域两个不同层面的7 个一级地类,即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作为物种变量。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和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性有极显著水平的14个社会经济指标为环境变量,这14个指标主要包括1999—2019年安溪县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年末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茶叶产量、粮食产量和水果产量,基本囊括了区域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对于乡镇而言,考虑到安溪县人口中80%以上涉及茶叶及其相关茶产业(包括第二、第三产业),同时兼顾地理条件和数据可得性,考虑了13个社会经济指标包括总人口、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产值、牧业产值、渔业产值、林业产值、茶叶产值、茶叶产量、粮食产量、水果产量和人均GDP(其中必然包含其他产业的效益)的变化,并鉴于近十年来安溪各乡镇土地利用差异明显与发展态势,选择了24个乡镇 2009—2019年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对应时间13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值变化进行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分别构成物种与环境因子数据矩阵。
(2)运算平台 本研究采用CANOCO 4.5软件和CANODRAW 4.5作图软件进行CCA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1999年、2009年和2019年3个时间节点安溪县土地利用分类面积及变化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1999—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变化统计
由表1可以看出,安溪县土地利用总体呈“三减四增”特征,即1999—2019年间,安溪县耕地面积、草地和水域面积分别减少36.82%、22.91%和8.18%,而林地、园地(主要是茶园)、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分别增加了10.37% 、56.39% 、206.08%和90.14%。此外,从图2 可知,1999年安溪县耕地面积为837.20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28.00%,其中耕地分布面积比较多的前五大乡镇为:龙涓乡(9.91%)、龙门镇(7.50%)、蓬莱镇(6.55%)、城厢镇(6.40%)和官桥镇(6.36%)。林地面积为安溪县的最大土地利用类型,其面积为1691.31 km2,主要分布在安溪县的西南部地区,如龙涓乡(12.99%)、祥华乡(8.59%)和福田乡(7.85%)。以茶叶种植为主要的园地面积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和气候温和的“内安溪”,如长坑、祥华和感德等地,这些地区适宜茶树生长。水域面积和未利用地面积分别为10.15 km2和2.13 km2,分别占总面积的1.67%和0.07%,所占面积相对最小。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大小排序及占比基本上保持不变,从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草地>园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其中,林地仍然为安溪县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其面积占比从1999年的56.57%上升至2019年的62.44%;园地(主要是茶园)占比从1999年的5.06%上升到2019年的7.92%。

图2 1999—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现状 Fig.2 Land use patterns in Anxi County from 1999—2019
为了能够反映土地利用的结构特征和各类型之间的转化情况和方向,揭示各地类转入转出信息,本研究采用马尔可夫模型(Markov)构建了1999—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表2)。

表2 1999—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km2
由表2可以看出,1999—2019年期间,流出的耕地主要变成林地和主要为种植茶叶的园地,转变面积分别为181.21 km2和56.81 km2;而新增耕地面积主要由草地转变而成。园地所增加面积主要由耕地、林地和草地转变而来,转变的面积分别为56.81 km2、23.00 km2和11.62 km2;整体来看,园地转为其他地类的面积相对较小,主要表现为“退茶还林”,即主要为茶园的园地转变为林地较多。而新增的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耕地和林地,两者面积流出面积对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6.16%和5.49%。可见,近20年来,安溪县耕地面积之所以从1999年的837.20 km2刚性降低到2019年的528.92 km2,下降了58.28%,这主要与发展茶叶和非农用地增大有关(表1,表2)。
但是,已如前述,不同乡镇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是不同。鉴于近十年来安溪各乡镇土地利用差异明显与发展态势,为此选择近十年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情况加以分析(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09—2019年在安溪县所属的24个乡镇中,耕地减少10 km2以上有龙涓(-13.11 km2)、祥华(-12.02 km2)、剑斗(-11.64 km2)和蓬莱(-10.89 km2) 4个乡镇;降低7—9 km2的乡镇有感德、湖头、金谷、西坪、官桥、虎邱和龙门7个乡镇;降低2—5 km2的有魁斗、长坑、尚卿、蓝田、白濑和湖上6个乡镇;其余乡镇,除参内乡的耕地略有增加外,其他乡镇的耕地总体上减少1 km2左右。从中也可以看出,耕地面积大幅度降低的乡镇,主要与园地(茶园)面积增加密切相关,靠近城郊的乡镇还与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有关。
3.2 安溪县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如表4所示,安溪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全局Moran′sI均大于0,Z统计值在16.496—54.130之间;在给定的3个年份内,全局Moran′sI值均大于0,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安溪县各地类整体上呈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表现出空间聚集性特征。1999—2019年,耕地空间分布集聚特征呈现缓慢下降;林地和草地分布集聚特征均先缓慢增加后减少;园地和建设用地空间分布集聚特征则呈逐渐上升趋势;水域和未利用土地聚集度相对较低,前者空间分布集聚度几乎保持稳定,而后者则呈先缓慢上升后下降。

表3 2009—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情况/km2
就土地利用类型局部自相关变化而言,由图3可知,1999—2019年耕地在安溪县西北部,涉及桃舟、福田和感德乡镇呈低低集聚(Low-low,LL)状态,且集聚格网数量有所增加;但位于其东部和东北部乡镇,主要包括魁斗、尚卿 、白濑、湖上、湖头、金谷、西坪、剑斗和官桥等则呈高高集聚(High-high, HH)状态,并随时间其集聚格网数下降。林地在安溪县的西北部,涉及桃舟、福田和感德等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而在东北部和东部几个乡镇如魁斗、白濑、湖上、湖头、金谷、西坪、剑斗和官桥等乡镇则呈低低集聚(LL)。草地在该县的中北部和西南部,涉及感德、祥华和龙娟等几个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其他乡镇则集聚不显著。园地则在该县的中南和中北部,涉及蓝田、长坑和祥华等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其他乡镇集聚不显著。水域则主要在东北一线上,涉及白濑、湖上、潮头、蓬莱、凤城和城厢等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其他的则不明显。建设用地则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如参内、城厢、官桥和龙门等城镇化较高的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其他乡镇则分布集聚度不高。该结果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与社会经济指标和宏观环境调控有关。
3.3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结果发现,从社会经济指标发展(环境因子)与排序轴之间的相关性而言,排序轴的总特征值为0.999,前两个排序轴分别解释总数据量的97.93%和2.065%。从表5及图4可以清晰地看出近20年来(1999—2019),安溪县14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变化均与第一、二排序轴有极显著的相关性。其中a地区生产总值,b第一产业,c第二产业,d第三产业,e农业总产值,f工业总产值,g年末户籍人口,h非农业人口,i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j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k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n茶叶产量与第一排序轴呈显著正相关,而粮食产量与第一排序轴呈显著负相关;第二轴则主要与m水果产量呈负相关关系。可见,安溪县各地类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互作关系97.93%体现在第一排序轴上,只有不到3%的解释率体现在第二轴。这意味着CCA分析法能够很好地挖掘出各地类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互作关系。由表6和图4可知,选取的14个社会经济指标中除了粮食和水果产量外,其重要性排序看均很高,其中排位最大的是前几个分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值、茶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在CCA排序中,指标建设用地和园地位于第一主轴右上端,林地与未利用面积位于其右下端,而耕地和水域面积位于第一主轴左上端,而草地在其左下端。这与上述所说的近2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成“三减四增”特征相一致(表1)。结果说明了安溪县社会经济生产投入和产出的增长,会驱动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而建设用地和园地面积的提高,会挤压耕地面积,从而导致粮食产量的降低。这可以从相关系数最大的安溪县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9—2019年分别增长了11.03倍和18.11倍;建设用地和园地面积也分别从50.01 km2,151.41 km2提高2019年的153.07 km2,236.79 km2,分别增加了2.06和0.56倍;而耕地面积从1999年的837.20 km2降低至2019年的528.92 km2,降低36.82%中得到验证。另一方面,g年末户籍人口,h非农人口与园地面积变化均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社会人口和非农人口的增长会驱动主要为种植茶叶的园地面积的提高,这与上述介绍的安溪县80%以上从业人口与茶叶生产及其相关产业(茶叶加工和茶庄园生态旅游等相关产业)有关。该排序图反映了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和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变化上的相对位置与关系。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安溪县各社会经济指标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驱动作用。

表4 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的全局Moran′ I 值

图3 安溪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3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and-use types in Anxi County

表5 安溪县社会经济指标与排序轴之间的相关性
当然,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态经济条件不同,不同乡镇的发展路径及其策略可能不同。进一步利用典范对应分析法分析安溪县所属24个乡镇近10年(2009—2019)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与对应乡镇社会经济指标变化的关系(图5)。

图4 安溪县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与社会经济指标的二维排序图 Fig.4 Two-dimensional ranking figure of land-use types and socioeconomic indexes in Anxi County a—n分别表示为:a地区生产总值,b第一产业,c第二产业,d第三产业,e农业总产值,f工业总产值,g年末户籍人口,h非农业人口,i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j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k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粮食产量,m水果产量和n茶叶产量。排序图的4 个象限中,箭头方向表示影响因子的变化趋势,线段长度表示影响因子与历年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程度,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距离表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相似性

表6 安溪县社会经济指标重要性

图5 安溪县所属24个乡镇土地利用类型与社会经济指标的二维排序图Fig.5 Two-dimensional ranking figure of land-use types and socioeconomic indexes in 24 townships of Anxi County
从图5可以看出,安溪县所属24个乡镇中草地位于排序图的第一象限,林地和建设用地位于第二象限,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位于第三象限,园地则位于第四象限。这说明位于同一象限的地类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变化关系。此外,在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组中,排序轴长短体现了各地类之间相关关系的大小。例如,建设用地的增多和林地面积的减少相关性最大。耕地用地的减少与未利用土地(弃耕或退化地)增多相关性次之。由此可见,在乡镇层面上看,建设用地扩展是以牺牲林地为代价的,而耕地用地的减少除了用于非农用地,也由于人口城镇化导致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未利用土地(弃耕地)增多有关。相比于其他类型而言,园地和草地各乡镇却相对稳定发展着,体现其空间分布的差异特征,深化了上述分析土地利用类型转移转出变化的内容,充分展现了县域土地类型变化的空间分布格局。从24个乡镇各自的土地利用策略来说,长坑、大坪、感德、白濑、湖上、虎邱6个乡镇与草地归第一相限,整体特征是近10年草地减少, 长坑、感德、白濑、剑斗、湖上5个乡镇却伴随着林地的增加,大坪、虎邱两乡镇则呈现草地增加,林地却减少的互补类型。其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受农林牧渔总产值(d),农业产值(e)和茶产量(j)的驱动。 参内、城厢、凤城、尚卿4个乡镇与建设用地、林地归在第二相限,其特征是建设用地增加、林地减少或增加(如尚卿乡),并受牧业产值(f), 渔业产值(g),粮食产值(m)和人均GDP(k)的驱动。龙门、魁斗、蓬莱、湖头、官桥5个乡镇与耕地、水域与未利用土地归在第3相限,其特征表现为耕地、水域与未利用土地,均减少,受3类人口(a, b, c)和渔业产值(h)和水果产量(l)的驱动。金谷、蓝田、芦田、福田、龙涓、桃舟、祥华、西坪8个乡镇与茶园地归在第4相限,其特征为近10年茶园面积均增加,耕地面积却不同程度地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受茶产值的强烈驱动。可见,不同乡镇发展的驱动力不同,导致了各乡镇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差异,这也与其地理条件,特别是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和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不同有密切关系。
此外,CCA分析结果还可以清晰地看出13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排序轴的总特征值为0.666,排序轴的前两个排序轴分别解释总数据量的35.4%和11.62%,说与前两个排序轴有很大的相关性(表7)。其中,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产值、茶叶产值、茶叶产量与第一排序轴的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上,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人口总数、城镇人口、乡村人口、粮食产量、水果产量和人均GDP与第一排序轴呈负相关。第二排序轴主要与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产值、牧业产值、粮食产量和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人口总数、城镇人口、乡村人口、林业产值、茶叶产值、水果产量呈负相关(表7)。可见,第一和第二排序轴均视为农业经济增长轴。

表7 安溪县各乡镇社会经济指标与排序轴之间的相关性
进一步从安溪县所属24乡镇社会经济指标重要性排序看(表8),13个指标中达到极显著水平的有5个,其中r2越大,Pr越小越重要。其大小顺序为茶叶产量>农业产值>茶叶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城镇人口。可见,发展茶叶是近10年导致乡镇土地利用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体现了乡镇发展与县域发展侧重点的异同点。

表8 安溪各乡镇社会经济指标重要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通过监督分类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获取1999年、2009年和2019年3期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应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等方法对1999—2019年安溪县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CCA方法分析1999—2019年安溪县及其所属24个乡镇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分析结果验证了CCA能够清晰地挖掘出各乡镇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指标间的多变量非线性对应关系分析,这是基于线性相关假设的其他方法所不及的优点,所获结果可为优化区域用地格局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安溪县 1999—2019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较为明显变化,总体特征是“三减四增”;其空间分布格局在全局上呈明显集聚状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在全局空间集聚状态变化趋势有所差异,但在局部空间分布格局有明显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证实,近20年来安溪县耕地面积、草地和水域面积分别减少36.82%、22.91%和8.18%,而林地、园地(主要是茶园)、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则分别增加了10.37% 、56.39% 、206.08%和 90.14%。林地整体上有所提升,但不同乡镇变化不一。进一步分析安溪县土地利用类型转出转入状况,结果表明(表1),1999—2019年期间,流出的耕地主要变成林地和主要种植茶叶的园地,转变面积分别为181.21 km2和56.81 km2;而耕地增补面积主要由草地转变而成。园地所增加的面积除了由耕地转变而来之外、也从林地和草地转入,分别转入了56.81 km2、23.00 km2和11.62 km2;整体来看,园地只增不减,转为其他地类的面积相对较小。而新增的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耕地和林地,两者流出的面积对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6.16%和5.49%。值得一提的是,林地虽然整体上有所提升,但不同乡镇变化不一。研究发现安溪县所辖24个乡镇,近10年来(2009—2019)有1/3的乡镇林地呈下降趋势。其中,祥华、大坪、虎邱、参内、福田,城厢6个乡镇林地降低明显,除城厢镇降低林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外,其余5个乡镇降低林地主要用于发展茶叶生产。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安溪县土地利用变化形成了明显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耕地在安溪县的西北部呈低低集聚(LL)状态,但位于其东部和东北部乡镇你则呈高高集聚(HH)状态,并随时间其集聚格网数明显下降。草地在该县的中北部和西南部几个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园地则在该县的中南和中北部几个乡镇呈高高集聚(HH)状态;水域则主要在东北一线上的几个乡镇中呈高高集聚(HH)状态,建设用地主要集聚在东南部那几个城镇化较高的乡镇中,呈高高集聚(HH)状态(图3)。其变化趋势与分布格局是县域社会经济、地理生态和宏观政策调控和驱动的结果。
(2)给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和宏观政策是驱动安溪县土地利用变化的关键因素。
研究表明,在近20年(1999—2019年),安溪县在7类一级土地利用类型中,由于水域和未利用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其余5类土地利用变化,除了受地理因素的制约外(如西南部地区所属乡镇主要是山区,交通相对不便,而东北地区海拔相对较低,交通较为方便,城镇化程度较高),主要受社会经济指标和宏观政策的驱动因素调控,排位最大的前3个因素分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和茶产量。但不同乡镇由于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土地利用的策略也不同。例如,参内、城厢、凤城和尚卿4个乡镇的特征是海拔相对较低,面向泉州、厦门,因此建设用地增加、林地减少为主,并主要受到牧业产值(f)、渔业产值(g)、粮食产值(m)和人均GDP(k)的驱动。另一方面,金谷、蓝田、芦田、福田、龙涓、桃舟、祥华和西坪8个乡镇的特征为近10年茶园面积均增加,耕地面积却不同程度地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受到茶产值的强烈驱动,真实地反映了区域社会生态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态势。可见,不同乡镇发展的驱动力不同,这是导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与地理条件,特别是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有密切关系。
此外,土地利用的变化格局还与当地政府的战略决策引导有关。从宏观环境而言,近20年来随着安溪县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城镇化加速,工商业、住宅和交通等建设用地需求急剧增加,驱动着其土地利用格局发生变化,总体上以耕地和草地持续减少,园地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为主。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速度最快,年均变化速率达到10.31%。此外,近20年来,安溪县坚持以茶立县,构建以茶叶为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全国有名的产茶县。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根据规划,到2010年安溪全县规划茶园总面积28000 hm2(其中铁观音15333.3 hm2),产量5 万t(其中铁观音2. 2 万t),涉茶总产值达到80亿元,年均增幅12.2%,其中第一产业(茶叶产值)40 亿元,年均增幅10%, 第二产业(茶叶加工相关产业产值)35 亿元,年均增幅1 6%,第三产业(相关旅游业产值)5 亿元,年均12%增幅[24]。可见,茶产业成为安溪主导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县的80%,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在这一宏观环境的引导下,2010年以来,安溪县茶农积极开垦茶园,使茶园面积逐渐扩大。据统计,2011—2015 年安溪县共新种植茶园面积达14991.6 hm2,年均新种植茶园面积达3330 hm2[11],可见,近几年安溪县茶园规模迅速扩大。本研究结果也证实,近20年来以茶叶种植为主的园地面积增加了5640 hm2;特别是一些山地新建茶园普遍存在机械开挖建园,超坡度开垦,一开到“顶”、“四面光”的现象[25]。究其原因是安溪县以茶叶为主导的全产业链作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和民生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促农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6]。余文权等利用关联度分析法,研究发现安溪县茶产业发展与总体经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均存在高度关联,这意味着茶叶产业的迅速发展是推进安溪县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27]。此外,为促进茶叶产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安溪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在“建设山川秀美的茶乡”和“森林安溪”的总体要求下,采取多重措施进行各类林业生态和茶园生态工程建设。例如,2009年安溪县政府印发《百座茶园山体植树造林绿化规划意见》,随后实行“退茶还林”政策,将生态脆弱区域、低山及荒废的茶园茶山“退茶还林”,套种名贵绿化树种,推进茶园由单一模式向原生态模式转变,加强生态茶园建设,其目的是有效控制该区域的水土流失,促进茶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据调查发现目前属生态茶园的只有42%,实地考察还发现,有很多茶农所说的“生态茶园”是自然形成的,导致许多茶园不符合真正生态茶园的标准[10]。另外,依据山地坡度大小,安溪县茶园可划分为5—15° 茶园、15—25°茶园和大于 25° 茶园,这三类面积大约分别占总面积的 70% 、20%和10%;其中,由于强降雨、人为扰动表土等外在因素,使得前两类茶园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现象且流失强度较大。而大于 25° 茶园则大部分是面狭窄、前无埂、后无沟的现状且分布较为分散,若遇强降雨等外在因素,也极易发生坍塌和冲毁等现象,是水土流失易发区[28]。可见,上述因素使得生态茶园建设的任务还存在较大挑战性。因此,安溪县政府除了制定合理的政策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以便纾解生态茶园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和管理问题。
总之,安溪县及其所属乡镇的土地利用演变规律是生态地理及其社会经济和宏观政策驱动的结果。不同乡镇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发展策略不同导致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化格局存在微小差异;尽管如此,茶产业发展仍是区域发展的驱动力,并由此引发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如近年来由于茶园开发过度和栽培管理不当而导致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时有发生,越演越烈[29—30]。因此,安溪县必须重视土地利用的科学规划,加强茶园生态建设和科学管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实施合理土地利用和科学保护相结合的技术措施和政策法规,防止因发展茶产业而过度开发土地,特别是耕地和林地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进而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