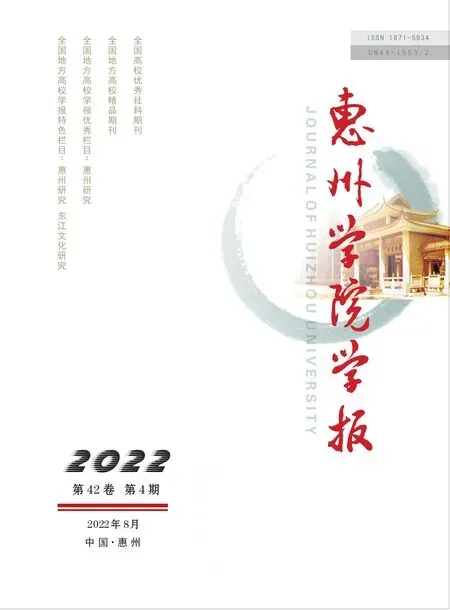葛洪:岭南地域文化符号的当代价值与传承1
刘玲娣,邓继鹏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0)
在岭南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量先贤曾以文化精英、社会功臣等角色出现,推动了岭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至今仍为人们景仰和怀念。东晋人葛洪并非岭南人,但他一生两度南下,避居广东博罗县罗浮山前后长达约二十年,对岭南的地域信仰、医学技术、养生文化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唐代韩愈、宋代苏轼等宦海沉浮、谪居岭南的历史名人一样,长期以来葛洪被岭南人民遵奉为先贤。
在岭南近二十年的岁月里,葛洪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娶其女鲍姑为妻,钻研医术,勤于笔耕,撰写了《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等大量著作。为了炼制丹药,葛洪还四出寻找丹砂等物,足迹远及扶南(位于中南半岛南部,今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地区)。葛洪晚年长居罗浮山,潜心修炼仙道,于东晋建元元年(343年)61岁①时在山中“尸解而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道教学术研究在大陆的勃兴,围绕葛洪的诸多研究得以逐步展开,学术界在葛洪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道教理论贡献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1]。其中有关葛洪生平事迹的研究,除了围绕其卒年的争论外,他在岭南的活动及其影响吸引了学界特别是广东学者的关注②。
2007年广东省政府确定的56位南粤先贤名单(按时代先后)③中,葛洪排在南越王赵佗、东汉学者杨孚以及陈隋之际南越俚族女首领冼夫人之前,这是官方首次正式确定葛洪在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的地位。如何深入发掘葛洪留下的文化遗产,弘扬葛洪所代表的道家、道教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岭南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葛洪与岭南道教
(一)结缘岭南,道显罗浮
葛洪一生两次南下,留止罗浮,从此与岭南结下不解之缘。东晋太安二年(303年),二十一岁的葛洪随吴兴太守顾秘、周玘等讨破石冰叛乱,平叛之后葛洪北上洛阳欲广寻异书,适逢八王之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途隔塞[2]”,葛洪返乡无望,被迫“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3]70。其后葛洪受广州刺史嵇含举荐,出任参军,“利可避地于南[3]689”。葛洪先行到达广州,嵇含却因政治斗争遇害。葛洪无所依托,遂“还留广州,乃憩于此山(按:罗浮山)”[4]5b。三十二岁时④,葛洪返回家乡丹阳句容。
《晋书》本传说葛洪年轻时虽然是以儒学知名于当世,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对长生成仙的不倦追求。葛洪第二次南下,很大程度地受到了他信道向仙志趣的影响。返乡后的葛洪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例如在晋元帝时他以平贼之功获封关内侯,后又因“才堪国史”,蒙干宝推荐,选为散骑常侍。然而此时葛洪已无意于世俗功名,所辟皆不就,做好了举家迁往岭南的准备。
岭南之所以对葛洪具有这样的吸引力,自然不排除他曾有南游广州的经验,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葛洪从小就爱好仙道,其从祖葛玄为三国吴时著名道士,学道得仙,号“葛仙公”,在道教史籍中葛仙公是得道成仙的榜样和德高望重的先师。其弟子郑隐得师亲授练丹秘术,葛洪早年即跟随郑隐学道,“悉得其法”;在他第一次南下广州时,又与精研内学的南海太守鲍靓交游,道术日进。在记载“黄白之事”的《抱朴子内篇》中,葛洪所述皆为“长生之理”,他深信在当时流行的长生之术中,唯有金丹最为重要,他反复强调修道“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3]70,“欲修神仙者,则非丹不升[5]13”。但是在中原地区,炼制金丹的主要物质丹砂本来就是稀有之物,价格昂贵,“国贵八石,求之无方[5]13”。葛洪可能在第一次来广州时就已听闻交广扶南等地盛产丹砂,“称丹砂如东沤之瓦石,履流丹若甄陶之灰壤,触地比目,不可称量[5]13”,因此在他五十岁左右时,儒家功名之心已息,遂“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6]1911,寄希望于“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5]13。晋元帝虽然以葛洪“资高”而不许,终究还是从其所愿。葛洪携子侄前往勾漏赴任,途经广州时,“刺史邓岱(岳)以丹砂可致[4]5b-6a”,极力挽留葛洪,葛洪遂停留在罗浮山。
《晋书》记葛洪未接受邓岳表其补东官太守的好意,“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6]1911”。某一日突然对邓岳说“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随后兀然若睡而卒,由于葛洪卒后“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人皆以为“尸解得仙”[6]1911。自此以后,罗浮山在后人心目中成为仙缘福地和道教圣山。两晋南北朝是南北道教同时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岭南虽远离中原和六朝繁华之地,但是道教在这里仍然传承不绝。到唐朝时期,罗浮洞朱明耀真天成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是避世求仙之人心心向往之地,这一事实在唐宋以来的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反映。例如宋代道士莫洞观曾在罗浮山石洞中修炼,有诗云:“借问稚川今在否,待飞双燕结真游”[7]388。诗句借用鲍靓化履为燕的典故,表达了作者欲与葛洪同修仙道的美好期望;又比如被尊为“南宗五祖”之一的南宋道士葛长庚也曾在罗浮山习道多年,他留下了很多赞美葛洪和罗浮山的诗句,如“摩拏东晋苍苔灶,细说仙翁炼药方”[8],体现出他对罗浮山、葛洪的别样情感。在这种道教气息浓郁的环境中,罗浮山承载了万千信徒得道成仙的梦想,逐渐发展为岭南地区的道教中心。
现在的罗浮山上,留下了众多与葛洪有关的遗迹,比如罗浮山上最重要的四处道观——白鹤观、冲虚观、黄龙观和酥醪观,据说就是后人在葛洪创建的东南西北四庵基础上修建的。四座道观与其它不同时期建立的道观,在罗浮山上共同构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群。再如洗药池、稚川丹灶、葛洪衣冠冢等遗迹,无声地传递着葛洪在罗浮山炼丹和升仙的历史。而遗履轩、双燕亭等建筑的名称,蕴藏着葛洪在罗浮山拜师鲍靓、论仙学道等传奇故事。古往今来,过往的文人墨客在游览罗浮山时,留下了众多吟诵这些遗迹的诗篇。宋人吴与在广东任职时游览罗浮山,目睹葛洪丹灶与衣冠冢之状,不由想到葛洪炼丹尸解之事怀古成诗,写下了“丹灶久空遗迹在,冢中曾见旧衣冠”[7]376的诗句。这些遗迹承载的葛洪事迹与成仙传闻,是罗浮山乃至岭南地域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为罗浮山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文化符号,连接古今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葛洪在后世影响的延伸和扩大,大约从道教高度繁荣的南北朝开始,葛洪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文献记载中。一些原本分散的内容,通过葛洪的符号功能,被有目的地串联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寓意明确的意象,这种意象将葛洪一生的事迹传说与文人、修道者的精神追求紧紧联系起来。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葛洪及其相关的典型性行为、事件、故事、遗迹、遗物等,往往成为常见的创作典故和创作主题。例如唐代诗人顾况之诗《山中听子规》:“野人自爱山中宿,况是葛洪丹井西。庭前有棵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9]。又如宋代诗人耿南仲之诗《题丹灶》:“过客空寻访,飞仙已杳冥。他山多可买,归去读黄庭”[7]384。以元代王蒙《葛稚川移居图》为代表的文人绘画将葛洪南下岭南符号化为远离无道之天下、追求洁身自好之理想的意象。通过众多文学作品对葛洪意象的塑造与运用,葛洪不再是“葛洪”本身,而是成为蕴含着求仙信道意义的符号性表达。元人王冕在《葛仙翁移家图》一诗中由葛洪这一符号出发,提出自己对求仙之事的观点:“神仙有无未知,人生有酒且自持,秦皇汉武徒尔为?”[10]由意象到符号,葛洪在文学作品中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葛洪这一文化符号成为了创作者们神交的对象,跨越时间与空间与葛洪产生精神联系。如苏轼在岭南期间,多次游览罗浮山,有“东坡之师抱仆老,真契早已交前生”[11]18b-20a之句。也有一些诗人并未到过岭南、罗浮,仍然可以在其作品中看到葛洪的相关典故。如杜甫“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12]的诗句。在这种意义上,葛洪及其炼丹成仙的事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人们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思想上与葛洪形成一种精神共鸣,用以抒发诗人们自身的情感。更进一步地说,这一文化符号也可让人们将自身与罗浮山、道教乃至于神仙联系在一起,从而拉近与葛洪以及罗浮山、道教、神仙之间的距离,达到思想上的升华。
葛洪与罗浮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频繁地出现在后世文学创作与文献记载之中,与葛洪在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葛洪以其博采众长、集前代仙术之大成的历史性贡献,成为道教金丹派的杰出代表性人物。卿希泰曾从修炼方术和教义阐释两个方面充分肯定葛洪金丹道的历史地位,认为它是在旧天师道、太平道等民间道教与后来上清派、灵宝派为代表的上层道教之间的过渡桥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3],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葛洪师从郑隐得授左慈、葛玄等人的《太清丹经》《金液丹经》《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等经典;在岭南期间,葛洪又师事鲍靓,得授马鸣生、阴长生等人。葛洪对不同派别经典的吸收融合,以及在岭南的长期仙道实践活动,是促成其道教体系形成并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
发掘葛洪与岭南地域文化的关系,对现当代岭南道教的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促进和引领作用。作为南粤先贤中的早期代表人物,葛洪的著述,葛洪的思想,是应受到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深掘葛洪与岭南的历史渊源,总结葛洪一生的思想贡献,弘扬葛洪洁身自好、潜心修道的精神,对于当代岭南道教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葛洪从早年投身功名,到中年逐渐远离事功,毅然南下岭南,再到全身心投入仙学,潜心问道并著书立说,体现了中国士大夫显隐不二的伟大精神品格。葛洪及其文化遗产是岭南人民的共同财富,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以葛洪为代表的岭南道教人物的研究和宣传,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或面对大众的研习班等方式让道教文化中的菁华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和接受。立足葛洪与岭南的关系,依托以罗浮山为代表的道教名山和宫观文化,积极为当代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寻找新的思路。
为了将葛洪这张岭南地区独特的文化名片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有必要对罗浮山及葛洪事迹进行宣传。改革开放以来,旅游文化出版部门策划推出了不少有关葛洪与罗浮山的雅俗共赏的书籍,如广东旅游出版社先出版的《岭南第一山:罗浮山》(1989年)、《神仙洞府罗浮山》(1993年)、《罗浮山历代诗选》(1995年)等,又如惠州博罗县罗浮山文化研究会编著的《葛洪与罗浮山》(2016年)。这些书籍的出版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葛洪和罗浮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走近了葛洪与罗浮山,进一步触摸到了岭南文化的脉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葛洪对岭南社会的当代影响力。
二、葛洪与岭南医药养生
(一)医药养生,福泽百姓
修道者大半通医术。葛洪在岭南的修道活动,与其行医救疾、撰写医书等医学活动相辅相成。由于他在医学上的巨大贡献,被后世誉为“岭南医药之祖”。《肘后备急方》是葛洪众多著述中有幸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医书之一。此书是他穷览医书,患其繁杂,选而集之所成。他编纂此书的初衷是为普通老百姓“备急”,急老百姓之所急,他在序言中自陈:“然非有力不能尽写,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14]608因而“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所载之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又“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14]608。《肘后备急方》不但在药物选择、治疗方法上偏向普通民众,书中所录之病也多为民间所常见,几乎涵盖了百姓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所有病痛。《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多种治疗毒虫蛰咬的病方,对毒虫众多的岭南地区来说,有很强的实用性。葛洪对《肘后备急方》非常自信,“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3]272”。后世对《肘后备急方》评价很高,宋代诗人陈应斗诗云:“肘后应难一一传,多将灵药种仙山。仙禽来捣仙翁卖,挑杖悬壶走世间”[15]。
葛洪在悬壶济世的同时,还呼吁人们注重对身体的保养。比如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提到,“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3]245”。这些来自生活经验和长期观察的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
葛洪的妻子鲍姑,在民间传说中有很高的医术造诣,相传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灸法便是出自鲍姑。葛洪师从鲍靓时,鲍靓“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6]1911。《云笈七签》说,鲍姑继承了鲍靓的尸解之法,“与稚川相次登仙[16]”。在道教传记和民间传闻中,鲍靓和葛洪夫妻都是得道成仙的典型,例如在唐代裴铏的《传奇》中,传奇人物崔炜为化身老妇的鲍姑解围,鲍姑以越冈艾答谢崔炜:“吾善炙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赘疣,只一炷耳”[17]。在这一传奇中,鲍姑幻化老妇行灸南海,以仙姑形象出现;艾灸也被赋予了神通广大的色彩,对治疗疣类疾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清代《鲍姑祠记》也有类似的记述:“越岗天产之艾,以灸人身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18]。民间相传鲍姑在广州越岗院以艾灸行医救人,后人为纪念鲍姑的贡献,为她在三元宫设殿、设祠供奉。葛洪与鲍姑在医药方面的影响,在岭南历史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食疗医药,泽及当代
葛洪夫妻在岭南行医救疾的行为,影响着当地人民的饮食和养生习惯。《肘后备急方》中载有多种食疗之方,如在《治伤寒时气瘟病方》中有以食鸡肉、饮鸡汤治疗之法:“金色脚鸡,雌鸡血,在治如食法,熟食肉饮汁令尽,不过,再作亦可,下少盐豉佳”[14]631。又如《治卒上气咳嗽方》中食梨治疗之法:“梨一颗去核,内酥、蜜,面裹烧令熟,食之”[14]653。岭南人民信医养生,引药入食,形成了独特的食疗文化,如在夏季炎热之时饮凉茶、老火汤等祛火,在秋冬阴凉之季吃猪肚鸡、椰子鸡等滋补,或许也有来自葛洪重视食疗的影响。广东民间广为流传一种粥食,专治伤风感冒导致的各种不适,老百姓称之为“神仙粥”,并以朗朗上口的歌诀呈现了这种粥食的烹调秘诀:“一把糯米煮成汤,七根葱白七片姜,熬熟对入半杯醋,伤风治感冒保安康。”其实“神仙”并没有那么难,一碗粥吃过,已向神仙接近一步,如此而已。葛洪仙学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仙可学致”,也就是说,神仙是积学而成的结果。
葛洪的医学理论与养生思想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着借鉴作用。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有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14]637治疗疟疾的病方,屠呦呦团队受此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用中国智慧为疟疾的现代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令中国传统医学再一次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惠州市和博罗县果断抓住契机,以罗浮山为依托,牵头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积极开发葛洪与岭南医药的当代价值。2016年9月4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正式揭牌开馆,“葛洪博物馆”牌匾由屠呦呦亲笔题字,以纪念她与葛洪之间跨越千年的医学传承。葛洪博物馆除展览葛洪与鲍姑的事迹文物外,还通过图片资料展示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科研历程,成为全国中医药科普宣传教育基地[19]。葛洪博物馆集古代医学与现代中医与一体,以青蒿为纽带联结两位时隔千年的中医医者,是弘扬中国传统医学的一扇窗口。2016年、2018年在罗浮山分别举行了第三届、第五届中医科学大会;2017年,在罗浮山成立了广东省葛洪中医院研究院。这一系列举措紧紧围绕着葛洪与中医的主题,积极弘扬传播葛洪的医学思想,令中医药文化知识在继承葛洪医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葛洪医疗养生思想的影响下,惠州市和博罗县政府抓住屠呦呦以青蒿素获诺贝尔奖的契机,积极发挥罗浮山与葛洪的龙头作用,重建罗浮山洞天药市,打造国家级健康产业基地、中医药创新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争创全国中医药强市。
以葛洪的医药养生思想作为依托,一批优秀的中医药企业受益于罗浮山的中医传统文化与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在此发展壮大。如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深掘和发扬中医精华,开发出一系列优秀中医药品,其中罗浮山百草油更是于2011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罗浮山”商标也被评选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又如广东葛仙堂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生产的“葛仙堂”牌姜茶而闻名全国。再如广东暨晴生物医药科技公司依托鲍姑艾灸的医药文化,培育红脚艾,开发出了一系列艾草养生产品。这些知名中医药企业深受葛洪思想与岭南文化的熏陶,一方面立足于岭南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开发了一批具有岭南特色的医药保健产品;另一方面又以这些知名产品为载体,将葛洪与岭南的医药文化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无论是葛洪的医学贡献,亦或是他的养生思想,都对现当代中医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三、葛洪与岭南黄野人传说及黄大仙信仰
(一)布道化民,岭南仙踪
黄大仙的传说与信仰在岭南地区广为流布,但其来历却众说纷纭,黄大仙的身份来源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浙江金华黄初平说,主要依据是葛洪所撰的《神仙传》;二是葛洪弟子黄野人说,认为葛洪炼丹成仙后,黄野人得葛洪遗丹,服之而成地仙;三是下邳黄石公说,相传张良曾师从黄石公学道,跟随刘邦夺取天下后,跟随赤松子神游,黄石公即赤松子;第四种说法是黄帝雨师赤松子[21]。黄大仙的四种不同来历,均含有明显的道教色彩,有三种观点认为赤松子即为黄大仙,或为黄初平,或为黄石公,亦或是黄帝雨师,都与赤松子有密切联系。反观黄野人即黄大仙一说,与赤松子并无瓜葛,且黄野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岭南地区,在四种说法中别具一格。这种独特性正是受葛洪在岭南的影响及道教在岭南的传播造成的。
相传葛洪留止罗浮山炼丹时,有黄野人伴随左右。苏轼之诗《寄邓道士》的序言中已提到黄野人传说:“罗浮山有野人,相传葛稚川之隶也。邓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尝于庵前见其足迹长二尺许”[11]2a-2b。北宋蔡條《西清诗话》也有关于罗浮山野人的记载:“近有人游罗浮,宿留岩谷间,中夜见一人,身无衣而绀毛覆体,意必仙也,乃再拜问道,其人了不顾,但长啸数声,响振林谷”[22]。结合北宋时期苏轼与蔡條对黄野人的记载,这一时期有关黄野人的传说已具有雏形,黄野人具有长足、无衣、绀毛等异于常人的特点,颇具神秘色彩,百姓睹之以为仙人。罗浮山野人传说经过岁月的发酵,到清代时更加丰富完善。屈大均《广东新语》详细地记录了罗浮当地的黄野人传说:“黄野人,相传葛洪弟子,洪仙去,留丹柱石间,野人服之。居罗浮为地行仙,往往与人相遇,或为黄冠,或儒者,或为溪翁、山妇,或牛,或犬,或鸟,或大胡蝶。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见之”[23]729。在屈大均的记载中,黄野人因服葛洪遗丹而拥有自由变换形象的“仙术”,成为护佑一方的仙人。黄野人还在罗浮山之中庇佑往来行人,有治疾救人之行。屈大均听闻,罗浮山中有樵者“患脚疮不愈,一老人隔溪唤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疮即愈”[23]730。为樵夫治疗脚疮的老人,被当地人认为是黄野人的化身。黄野人在传说之中与葛洪关系密切,他继承葛洪的医术行走人间、悬壶济世,自然无可指摘。在有关黄野人的传说故事中,无论是作为葛洪之徒,还是具有行医救人的本领,均可以看出其成型、发展与葛洪在岭南的活动密不可分。
在屈大均笔下,黄野人传说还带有浓郁的道教色彩。屈大均曾至罗浮,收集当地的黄野人传闻。他听人讲述虎粪化药的故事:“有僧于黄龙洞遇一老者,意其为黄野人也。拜求丹药,老者指虎粪示之,僧见虎粪犹暖,有气蒸然,且杂兽毛,腥秽不敢尝。俄而虎粪渐消灭,仅余一弹丸许。一樵者至取吞之,异香满口,后得寿百有余岁”[23]729。在这一故事中,黄野人将丹药幻化成虎粪之形,以考验求药人的向道之心。这种神仙考验凡人的情节脱胎于道教的三尸说,《太平经》与《抱朴子》等书中对三尸均有阐述,大意为人身中有三尸,察人之过告于司命;三尸也会在人修炼之时蛊惑人心,令人前功尽弃。只有通过三尸的考验,才可以修成正果。除此之外,在广东民间还流传有黄野人斗鹌鹑、黄野人携哑虎除暴安良的传说[24],这些惩恶扬善的故事,与道教神仙故事中仙人显灵、劝善弃恶的内核基本一致,突显了黄野人传说中的道教因素。
黄野人传说的成型与发展,不但蕴含着丰富的道教因素,也展现了百姓渴望被仙人庇佑的热切期望。百姓希望有神通广大的仙人可以聆听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祈求,庇佑他们的生活。传说中在罗浮山得道成仙的安期生、葛洪等人,因飞升而去,与百姓之间有着明显疏远的心理距离。黄野人不但是葛洪之徒,服食仙丹后成为地仙,神通广大;而且可以幻化形象,在民间悬壶济世、护佑一方,正符合百姓心目中仙人的形象。在这种热切的期望下,民众转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虚构的黄野人身上,因为他更为亲民,更能满足百姓的信仰与心理需求[25]。因此,有关黄野人的传说逐步转变为黄大仙信仰,与浙江金华的黄大仙信仰合流后,为黄大仙信仰增添了岭南的地域文化特征,增大了其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二)南粤仙祠,福泽百年
明清以来,黄大仙信仰广泛地流传于东南沿海地区,信仰的中心逐渐由浙江金华转移到岭南,供奉黄大仙的祠庙也随之在岭南广泛建立。受到黄野人传说的影响,罗浮山冲虚观内便有黄大仙祠,祠联云:“师去丹留度归天外客;缘深圣显笑乐地行仙。”将葛洪的事迹与黄野人的传说融入到黄大仙的信仰之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黄大仙普济坛在广东番禺成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普济坛道士及信众在广州花地建黄大仙庙,广州黄大仙庙在当时成为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中心。在其时的民间传闻中,黄大仙有求必应,颇为灵验;更重要的是,黄大仙庙为当时生活在列强环伺、封建压迫历史环境下的人们提供了心灵慰藉的场所,黄大仙这一亲民的仙人则成为了当时人们渴望摆脱苦难的精神寄托。
广州黄大仙庙吸引了众多香客,辐射区域涵盖整个岭南地区,广州的黄大仙信仰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后,黄大仙像由西樵山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开坛设祠,其后香港黄大仙祠逐渐兴盛,超越广州成为岭南最繁盛的黄大仙祠。随着香港频繁的人口流动,黄大仙信仰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足迹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即使在今天也仍旧有很大的影响。黄大仙祠作为黄大仙信仰的载体,在当代依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首先,以黄大仙祠为中心,继承和发扬黄大仙信仰,不但可以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性,而且也促进着粤港澳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黄大仙信仰在岭南成熟,受到葛洪事迹及黄野人传说的影响,吸收了岭南地区的文化与习俗,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立足于黄大仙祠,积极弘扬葛洪与黄野人的事迹传说,展示黄大仙信仰的特色与影响,对岭南来说无疑又是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对促进岭南的旅游文化事业有积极影响。2004年广州黄大仙祠重建工程完工,沉寂多年的黄大仙祠又重新面向社会开放。广州黄大仙庙还举办庙会,分别是正月初一至十五的新春庙会和农历八月二十三日的黄大仙诞庙会,庙会中有粤剧曲艺、醒狮、杂耍等表演,及民间工艺摆卖和慈善敬老等活动[26],吸引着本地的香客和外地的游客前来瞻览,充分发挥了黄大仙祠对旅游文化事业的带动作用。香港黄大仙祠在当代发展层面也有新的思路。除了传统的黄大仙信仰及祠庙建筑外,香港黄大仙祠周边还有众多公共屋邨,如彩虹邨等[27],现如今成为了热门的摄影地点,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其次,广州和香港的黄大仙祠也是岭南地区的重要宗教活动地点,以黄大仙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团体积极地履行着济困扶危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传说中黄大仙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宗教的普世价值。广州黄大仙祠多年来积极参与慈善事业,2014年、2015年,广州黄大仙祠和广州仁威祖庙每年向清水村捐款20万元,帮扶清水村脱贫致富[28]。依托香港黄大仙祠成立的啬色园同样致力于慈善事业,成立专项帮扶教育基金;设立中医药局推行义诊。2020年3月,香港啬色园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赈灾专户捐赠港币300万元整,以支援武汉抗疫[29]。
黄野人传说受到葛洪与罗浮山道教的影响,在明清之际的岭南形成了地域性特征明显的黄大仙信仰,长期影响着岭南地区的文化习俗。围绕着黄大仙信仰,祭祀供奉黄大仙的祠庙和信奉黄大仙的宗教团体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宗教团体以黄大仙祠为中心,以传说中黄大仙济困扶危、有求必应的行动为楷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各种善行义举将黄大仙信仰更广泛地传播,加深了黄大仙信仰在岭南地区的影响力。
四、结语
追慕先贤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作为岭南先贤之一,葛洪及其代表的道教文化既是岭南文化地域性特点的塑造者,其自身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宗教信仰方面,葛洪举家南迁是北方道教南传的重要契机,岭南成为道教南宗重镇,罗浮山在唐代成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即使在千年之后的今天,罗浮山仍旧在传播道教文化的前沿阵地上大放异彩。在医学养生方面,葛洪的道教养生思想和在岭南的医学实践,不仅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着借鉴作用,还影响着岭南人民的饮食习惯。在民俗层面,因葛洪事迹衍生出的黄野人传说,在历史的进程中与黄大仙信仰合流,将这一民间信仰岭南化、地域化,黄大仙信仰因此在岭南地区广为流行。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梳理与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葛洪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岭南地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传承与发扬葛洪这一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思想内核,对于深掘葛洪在岭南地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葛洪生卒年,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以钱穆《葛洪年谱》为代表,认为葛洪生年最高不过六十(参见钱穆《葛洪年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一种以王明为代表,认为葛洪享年八十一岁,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第1页)。刘固盛、刘玲娣主编的《葛洪研究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集中收录了相关成果,可参考。另外,有关葛洪生卒年及葬地问题,笔者在《葛洪与赤壁葛仙山——从葛洪生卒年及葬地谈起》(收入《葛洪生态健康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曾有系统总结。
②近年在钱穆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丁宏武撰写了新的《葛洪年表》,对原有年谱略有修订(《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有关葛洪事迹的考证,可参看王承文《葛洪早年南隐罗浮考》(《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冯汉镛《葛洪曾去印支考》(《文史》,1995年第39期)、丁宏武《葛洪扶南之行补证》(《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等。
③2007年7月广州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社科院等各方面专家,经过两年的研讨,向社会公示及广泛征求意见之后,确定了56位南粤先贤名单。参见夏令《广东南粤先贤馆公示首批56先贤》,《信息时报》,2007年7月8日。
④据钱穆考证,晋愍帝建兴三年,晋元帝司马睿当时以琅琊王为丞相,辟时年三十三岁的葛洪为掾属。参见钱穆《葛洪年谱》。参见刘固盛、刘玲娣编《葛洪研究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陈飞龙认为葛洪于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即在他三十二岁时返回故里。参见陈飞龙《葛洪年谱》,《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80年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