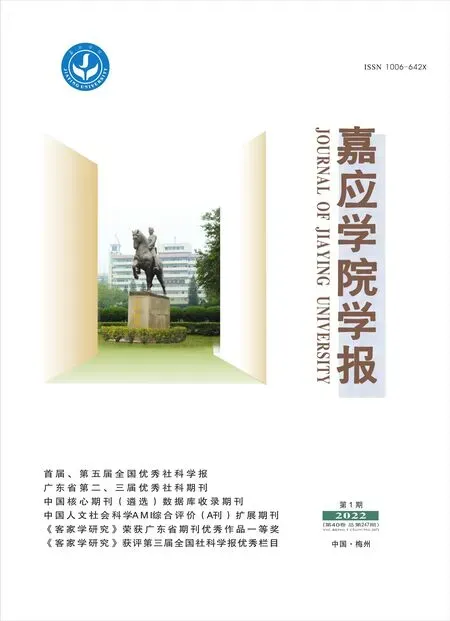启蒙逻辑与另类批判
——“五四”时期沈从文“从文”的心路历程
周晓平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五四”时期,一个狂飙突进的岁月,虽已渐行渐远,却深深地烙刻了时代文人的人生轨迹。沈从文经历了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到成长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由于“五四”启蒙的感召,带着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来到了繁华的都市,开启了人生的“从文”之旅,尽管路途曲折坎坷,步履蹒跚。都市生活的强力压抑,激发与激活了几千年巫楚文化储存在沈从文脑海中的文明基因,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皈依与诉求,抑或启蒙与批判,它凸显了沈从文不同寻常的“从文”历程。
一
那么,沈从文早期人生经历了哪些?有什么特殊的体验与影响呢?
顾名思义,湘西位于湖南西部。这里山清水秀,江河湍流不息。几千年以来,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如梦似幻般蕴育了遥远而神秘的巫楚文化,沅水流域则生动复现了楚地湘西的风土人情:古朴而淳净的苗族与土家族的民风、人性。沈从文在《边城》开头是这样展现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俨然就像一座古代希腊的神庙,在这座神庙中充满着古远的童话。因为偏隅一方,湘西地处崇山峻岭,形势险要。老林深山中暗藏着一个又一个的“迷”,它是土匪经常出没的荒蛮之处,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天灾、人祸、饥荒,天高皇帝远。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充满许多的迷幻,也呈现出落后与蒙昧。1902年沈从文诞生于此,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对于一个对未来充满着想象的沈从文,其前途注定充满着八卦与不测。他立志要解开这个“迷”。在那个时候,他生活中充满了疑问。因为求知若渴的他,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少时之狂、之野,耳闻目睹: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淋后放出的气味……蝙蝠的声音,黄牛被杀而叹息的声音,大黄喉蛇的鸣声,鱼在睡眠拨刺的微声,等等,也记得清清楚楚。[1]9涉世未深的沈从文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从自然世界到现实生活,人生、前途,沈从文都有一种敏感与痴迷。但又无法超越现实年龄与可能,只能在故乡的溪水山旁茫然、徘徊甚至惆怅。
这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1911 年辛亥革命发生了,它波及全国,惊动了偏僻山乡的凤凰古城。其父亲是反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沈从文目睹了家里进进出出的神秘而紧张的人群,隐约地感到一种不测。那年沈从文刚刚9 岁,那是一个长满记忆的岁月。事实是辛亥革命失败了,革命党人在凤凰组织的起义也遭到同样的厄运。他听到的是“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四百一十个人头,一大串耳朵,七架云梯”等不幸的消息。后来,还随同父亲在衙门口恶心地看到一大堆肮脏的污血,衙门的鹿角上、辕门上、云梯上到处挂满了人头。父亲沮丧着脸,年少的沈从文充满着恐惧。更加残酷的是,清廷官吏以更加疯狂的仇视对待起义的民众,他们到处搜捕屠杀苗民,不问青皂红白,任凭哀嚎,抓来就杀。不到一个月就横尸遍野。[1]11不仅如此,年幼无知的沈从文还去看一个个杀人的场面:“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人,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它小孩比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有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竹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那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样的,那分颓丧那分神埋怨的深情,真使我忘不了。”[2]126
沈从文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被砍?砍他们的又是什么人?”可是有谁能够满意地回答他呢?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乡下人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是读书;二是尚武(从军打仗)。摆在沈从文的面前也只有这两种选择。辛亥革命光复凤凰后,沈从文有幸来到了新式小学就读。初小的五年也许是沈从文少年最为快乐的岁月,他在这里识字认字,与伙伴一起玩耍,同时,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新的理想也逐渐萌芽。
从1911 年到1922 年,沈从文正处于蒙昧与求知的阶段,他20 岁的年龄经历了太多的懵懂与愚昧。14 岁高小毕业的那年,由于家境的原因,为了谋生,在行伍中混点口粮,沈从文从军了。可是在部队又经历了什么呢?又是看到杀人如麻的情形。当沈从文所在的这支部队过川东就食的时候,一个早上,因不知当地神兵和民兵一齐扑来,部队无设防,旅长、团长、营长全部被杀,队伍中几乎所有的官兵都被杀。还包括给沈从文熟知的一名军法长,以及使沈从文从愚顽自恃状态下走出来的长者。在龙潭驻防的将近半年中,沈从文感到生活中相当无奈,依然是残害人性的场面。一是同伴被杀;二是勇敢的汉子山大王被杀。那些杀人之前集合哨紧催,人马嘶嚷的阵式,成为沈从文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些都给了他人生一次次的教育,不过,这个时候,沈从文似乎懂事了许多。譬如,一些人在什么时候被拷打、头被砍下,似乎都看得清楚。也深感乡里人的无知与愚蠢。这份经验,使他活着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同步了。这种“乡下人”的不凡经历,使他对于城市中人在隔膜、慵懒的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引发同感,并因此使自己感到生活在城市中的孤独。[3]89
这些年的经历,沈从文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看客”的状态。在沈从文看来,他本人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一切事物的评判都有自己的原则,即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其爱憎。他认为自己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性时他永远是用艺术家的感情代替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4]120
沈从文看景物、看事物,这无可厚非,人人都会,人人都“看”。沈从文的“看”,有自己的说法,那就是不搀加爱憎,不进行道德的评判。
鲁迅在日本遇到“幻灯片事件”之后,决定“弃医从文”。在鲁迅看来:“凡愚弱的国民,即使身体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足以为幸。”[5]78鲁迅笔下有许多的“看客”,但对于那些丑恶的现象,譬如杀人如麻的场面,一种接近于愚昧而欣赏的“看”,鲁迅是进行无情地抨击的。在《阿Q 正传》中,鲁迅生动地描绘了阿Q 这一“看客”形象。“‘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 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咳,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对面的赵司成的脸上。”[5]215-216鲁迅表达了对于“阿Q 这一看客”形象的深恶痛绝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情感。鲁迅认为,“看”所显示出来的,往往不是直接“看”到的现象,而是“看”的行为本身及其体现出来的愚昧。《阿Q 正传》里相当多地运用了这样的意象和象征。当阿Q 被游街示众带到刑场上,他看到傻笑的看客的脸,明白了他们的眼睛似乎比狼还要可怕。于是,鲁迅对于自己的“呐喊”意义也感到怀疑,而且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怀疑。因为“看客”并不觉得自己痛苦,显然感到愉悦。与其喊醒,还不如让他们“昏死”下去。即使如此,鲁迅还是抱着“不可为而为之”,要做“遵命文学”。[6]43
20 岁的沈从文,虽然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并不成熟。它也无法超越现实与年龄的可能。何况沈从文思想中本来就囿有“不搀加爱憎”的观念。尽管作为一个“看客”的沈从文,他与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形象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置身于局外,显示漠然。应该说,“看客”是极权统治下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在那些怀抱浓烈的理想情怀和现代意识的人看来,这种无动于衷的看客就是麻木不仁的写照,就是集体自杀的症候。因此,与整个“五四”一代的中国青年、中国人一样,沈从文需要启蒙与被启蒙。但是沈从文的“看”,毕竟不同于那种对杀人场面起哄的“看”。这种场面对于沈从文的刺激不能说不大,其阴影在沈从文的脑海中是一直存活着的。若干年后,他写《边城》等作品的人物形象中,呈现了一种人性的复归,表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笔者认为这与他早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
沈从文来到北京,这是他对人生命运的一种改写,是新的人生观雏形的滥觞。他在《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中写道:“为了读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宁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在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为大多数人去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沈从文力图摆脱一种愚昧的人生,而“五四”的北京正是新事物、新理想的诞生地。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与“人的文学”相伴而成。中国新文学的滥觞的标志即人的现代化、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的现代化,求新、求变、求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面对“五千年之变局”,“人”与“思想”的藩篱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道鸿坎。“人的发现”即人性与尊严,重新得到审视。“启蒙”则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梁启超式的“少年中国”的新中国想象模式,及其中西、新旧价值观照下的取舍法则,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新人的思想与行为导向。他对于传统痼疾: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以及由这些痼疾带给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揭示,这成为了“五四”思想启蒙的最为基本的话语方式。[7]13继后,鲁迅身先士卒,把锐利的箭靶对准了几千年以来的愚昧、落后的国民性,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狂人日记》一声怒吼,“五四”启蒙文学思想运动成为社会的潮流。
与其它要求进步的新青年一样,沈从文接受了“五四”启蒙的洗礼,也正是“五四”时期,沈从文来到北京的前后,他翻阅古籍、鉴赏字画与古董;听“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这些都拓宽了沈从文的思路,增长了见识,启迪了对自然、人生的深层思考。以前思想深处那种山川草虫、湘西人性中的嫖客妓女、水手官兵、农夫村妇、人祸与战争,诸如此类,沈从文有了新的认识,他得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五四”的启蒙光辉驱赶着他脑海中愚昧而顽固的劣质,从而焕发出思想的光明。[1]43若干年以后,当沈从文回顾这段历程时,谈到了自己的感受:
……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于是产生了伟大的宗教。对于我呢,什么也不写,亦不说。我的一切官能都似乎在一种崭新教育中,经验了些纤细微妙的感觉。[8]81
“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这是“五四”时期,当初沈从文从凤凰来到北京的动机与朴素的出发点。又说,“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样的话,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感人的。他知道在旧的行伍中当兵是没有出路的,更何况形势比人强。“五四”启蒙文学运动的感召,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他同样要挤身于这种历史的潮流中去,试图有所作为。然而,前途并非沈从文所想象的那样,他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混战的时期。各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利益,矛盾重重,经常流血掠夺。老百姓死于非命,民间财富遭到毁灭。可是督办大帅则逍遥自在,失败后就带起二三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借一跑,万事大吉。……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奴性十足,浅薄无知,崇洋媚外。[9]45沈从文沉默了两年,沉默得近于有点衰老。几年来,他不写作,却在思考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义。“五四”新文化的思维与眼光在于民主与科学、道德与自由。而这种理念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呢?与大多数的“五四”青年一样,沈从文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茫然与徘徊之期,这是一个艰难的摸索阶段。
三
“五四”文学的意义,在于启蒙了一大批青年,启蒙了芸芸众生的国人。这是一个启蒙与被启蒙的过程。其实,启蒙又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永远不可穷极。严格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被启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10]71应该说,“五四”的主题及基本任务:民主、科学、自由、道德,诸如此类的启蒙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传播。然而,在广泛意义上,“五四”时期蒙昧的民众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任重而道远。
在沈从文接受了“五四”文化的洗礼后,作为一代启蒙作家,沈从文又是如何身体力行投入到这一时代洪流之中去?如果按照“五四”大的文化思路与叙事模式,沈从文作品中那些湘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又是如何被启蒙的?
在成长或创作的道路上,每个作家独有自己的心路历程。“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基本上决定了“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少年经验的“感性与理性生活”极大地制约着其后创作的发展方向。[11]184“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思想脉络:一是社会救亡意识;二是个性主义的启蒙。[12]143
1919 年,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的先驱们侧重以救亡意识为启蒙目标,形成一种文化场,其核心是对“人”的发现。人性、人权、自由、民主[7]27-28等成为重要的启蒙主题。鲁迅《狂人日记》《阿Q 正传》《长明灯》《故乡》《风波》等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文学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的启蒙,展示了相当的实力。无疑,加深了“五四”启蒙的文学的“国民性”反省的厚度。“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意义,则在于“个性主义”启蒙的展示。其创作复现了湘西民风、民俗,地域色彩的个性风貌与乡土特征。剽悍的水手、靠水手谋生做生意的吊脚楼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湘西,作为楚地一块古老生活之土,是没有被儒家与外来文化同化的土地。千百年以来形成了湘西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准则。生于斯,长于斯的沈从文要以独特的眼光打量、图解这片古老的土地与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外来人的眼里,这片未开化的土地是新鲜而陌生的,而在沈从文的笔下保留了它的自足性与自在性,[13]229从而加以引导与开化。事实上,沈从文认为,中国人身上有很多的病,这种病因源于“国民自私心”的扩张。认为两千年以来的儒家人生哲学,表面看来不自私,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国民虽容易统治,但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中说道:“事实上国民毛病再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须的新观念。使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是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一个国家多数人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豚,欲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9]27-28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沈从文创作中的启蒙立场是不同于“由启蒙到革命”的创作方向,回避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把创作视野转向了普通的民众社会,但也 绝不是左翼文学那样以某种意识形态来图解民众的生活,他们揭示出被启蒙主 义无意间所遮蔽的民间世界的真相。湘西的河水、街坊,及其生活在这河水、街坊的人民,无不是沈从文笔下描写的地方。沈从文不无自信地说,家乡的河水街坊,他看到的太多太多。他把这些都融进到他的创作之中。因为这是他眷念的地方:单纯的人性、古朴的街坊,他太“熟”了。并认为“五四”以来用这些作为创作对象他还是唯一的一人![9]121-122沈从文是把自己作为民间的一分子,在作品中体会其作为民间苦难的承受者置身其间,并非以他者的身份加以评判,而是创作一个作为“乡下人”的启蒙神话。
四
如果说,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幻灯片事件”为标志性转折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沈从文的“从文”是个人、家庭、社会与其特殊经历等综合因素致使的一种行为,尽管并不一定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导火索。其实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从文”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批判丑恶的社会现实,以改造人生与社会。
“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是一个主要的运动“主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物质承担者”,新文学最大的任务,就是对封建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的《狂人日记》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这种揭示的彻底性,如平地惊雷,直接把炮火对准了封建主义。鲁迅的《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端午节》《风波》《故乡》《目光》等作品,对国民愚顽的封建意识观念则进行了拷问与批判。相对于鲁迅对封建礼教与国民性的批判,沈从文的作品的批判意识,则显得更为委婉与另类,但是同样受到异曲同工的效果。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的主题,抒发自我,高扬个性。从而使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价值得到肯定、创造得到承认,使“五四”传统中平民意识与实用性扩张而成为现实。在20 年代初,沈从文初出茅庐进入创作时,其对于鲁迅为代表的以揭示和批判乡村丑恶为特色的“乡土文学”立场,就没有产生多少吸引力,他自己默默探索的是“乡土抒情”的创作之路。沈从文一旦发现自己在湘西题材的独特发掘与创作的擅长之后,则奋力向前、锐意进取。从1928 年至1933 年,他先后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其中包括1933 年的《边城》,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沈从文是在都市的强力压抑中激发起温柔的乡村怀念,在城市主流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产生对边缘文化的皈依与诉求。它凸显了乡土与主流文学迥异的批判手段。沈从文以湘西自然淳朴的民风来对比都市文化中那种油头粉面、阳奉阴违的扭曲人性。其批判题材的创作有两种:一方面是上层社会中达官贵人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嘲讽已经挤入上层社会生活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如《绅士太太》《八骏图》为代表,这种反讽的批判性是十分明显的。[13]236这些绅士淑女,人前满嘴讲究仁义道德的信条,背后却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生活在豪华、奢靡的大公馆,成天放浪形骸:忙于串门、吃喝、进赌场、吸食鸦片……这种道德观念体现为:虚伪、自私、怯懦。这些人使用虚假保持其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假文明。在沈从文《主妇》《或人的家庭》《自杀》等作品中,批判了都市情爱领域里琐碎、平庸、苍白、逢场作戏的爱情。在沈从文看来,即使是湘西的妓女,其人性、道德也总比洋场社会、夜总会里涂脂抹粉的摩登女郎要好得多,因为她们的贪欲、虚伪、扭曲、变形是与乡下妓女无法相比的。都市文明对于人性的异化,沈从文在作品中作了严厉的批判。
沈从文要为“这个国家”做些事,他要把自己融入到“文学革命”的大时代中去,要在这一洪流中有立足之地。由于与当时以鲁迅为主流文学群体之间的隔阂,沈从文似乎与“新月派”群体作家走得近些。由于徐志摩的欣赏,1924 年,沈从文的小说才在《晨报副刊》慢慢地得以有发表的机会。[14]127在这过程中,沈从文与徐志摩、陈西莹、凌淑华等交往甚密。后来因为胡适的赏析,进入了另类主流文化圈。但另一方面,沈从文与这些人在一起,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于是就把心中反抗的情绪转移到文学的创作中加以发泄。[15]沈从文之所以对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产生如此不同的情感价值的判断,是与他的人性观、人生观及思想深处的反现代性相关联的。他一再强调,只有在乡下,在那没有受到或者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污染的湘西,其淳朴的民俗才能蕴含出优美、健康、最自然的人性。而只有这种真、善、美才是对都市文明假、丑、恶的最为直接的批判。
“五四”时期是一个多元思想表现的时代,“五四”新文学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提供了生存空间。在“五四”启蒙主题的观照下,沈从文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启蒙发展之路。在《长河》中,湘西的人们都在“新生活”的到来陷入一种未知的命运和无措,风土人情、风俗习惯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变更,现代性的到来瓦解着美好的人性,沈从文竭力给人们保存抑或留下湘西这份遗迹。他进而思考着:“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普遍流行,腐蚀着我们的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像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毫无一种高尚的情感,更少用这种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办?”[8]81沈从文关心湘西人的生活与走向,同样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及未来。
文学创作应该依附于“生存与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肤浅、儿戏的“白相文学”的局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革命风云狂飙突进的时代,是“红色的年代”。就“五四”革命文学的进程而言,沈从文的思想意识有了些偏离。有时候对那些紧跟时代而艺术上比较幼稚的左翼作家的作品,进行了一些嘲讽。但是三十年代严峻的革命形势教育了他、启迪了他,尤其是他的好友、左联五烈士的胡也频也影响了他,促使了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的现实性、批判增强。在其创作中有时也可以看到革命的闪光。[1]45沈从文认为,我们要明白做人的权利,要有担当义务的精神去做一个拥有权利的国民。抛弃掉依赖、懒惰,并把它们视为极其道德的行为。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就必须有吃苦耐劳、死里逃生的精神,并与那些精神与身体两不健康的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9]132-133这也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色彩作家的沈从文的心灵告白。
五、结语
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早期的人生经历与“五四”的文化洗礼,无疑带给了他宝贵的人生体验。沈从文个性主义作家的创作,契合了“五四”多元化思想的文学创作的时代律动,人们不能对其有过于苛刻的创作要求。他“从文”的心路历程,及其丰富的早期作品与思想,至今对我们都有诸多的启迪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