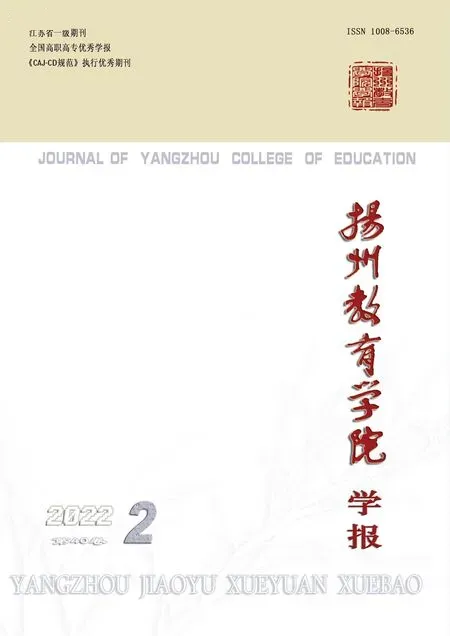务实精神对留日时期鲁迅的影响
瞿 学 森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原始文化早期,为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浙东人民逐渐形成了理性、务实的地域性品质,生于斯、长于斯的鲁迅,耳濡目染,无形中熏染出“理性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实践性品格”。[1]鲁迅在少年时期就结合实践经验对《花镜》一书中的错误进行订正,可以说鲁迅很早就建立了成熟的“务实”精神。历来针对鲁迅留日时期行为、思想转变的研究都强调外部因素对鲁迅的影响,缺乏对鲁迅自身内部要素的考察。这种忽略了鲁迅“务实”精神的研究无疑是片面的,只有将鲁迅主体和日本外部影响相结合才能客观理解鲁迅留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转变。鲁迅留日时期有两个大转变:剪辫和弃医从文。鲁迅剪辫时间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它非常巧合地夹在许寿裳等人剪辫和留学生剪辫潮之间。剪得稍早便显出极强的革命性,稍晚就可能被解释为跟风。鲁迅弃医从文的具体情况经过学术界多年考证已经相对明朗,引入“务实”精神能够在“革命”叙事之外给理解鲁迅带来新视点。
一、被“革命叙事”捆绑的鲁迅剪辫
长期以来有研究人员习惯于用后期成熟的鲁迅来理解早年的鲁迅,其直接表现就是用“革命性”对鲁迅早年的行为进行决定性的解释。
满人入关以后强制要求男性剃发留辫以示对清王朝的效忠,因此“剪辫”是最能体现同清政府决裂的行为。“反清”在很长一段时期属于民族主义行为,直到清末“反清”才和“革命”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剪辫”这一行为也就被赋予了“革命”意义。中国自辛亥以后“革命”就被视为绝对正确、绝对进步的行为,这种社会心理之下,身为革命家的鲁迅年轻时富有极强革命色彩的“剪辫”自然被认为是出于“革命”之故。许寿裳回忆鲁迅剪辫时,鲁迅的这一行为还没有被赋予“革命”的意义。许寿裳只是引用鲁迅文章证明鲁迅对辫子的仇恨,解释鲁迅剪辫后为何会“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2]5后来研究鲁迅留日的学者谈及鲁迅剪辫要么陈述事实却不展开,要么就将其解释为“革命”行为。比如程麻在《鲁迅留学日本史》中谈及鲁迅剪辫时写道:“鲁迅毅然在他所在的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着‘大清顺民’的发辫,和腐朽反动的满清政府正式决裂了。”[3]22刘再复和林非合著的《鲁迅传》中这样描述鲁迅的剪辫:“他决定刷洗这种耻辱,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决然地第一个剪掉了辫子,表示自己反抗种族压迫的决心。”[4]即便是鲁迅自己都说他的剪辫行为“毫不含有革命性”[5]579,但上述研究依然引用鲁迅后期的文字证明鲁迅剪辫是革命行为。用鲁迅1936年的自述证明他剪辫不含革命性,就如同用后期鲁迅的文字证明他早年的行为都具有革命性一样是不科学的论证。研究鲁迅剪辫的真正动机,将当时的情况尽可能地还原才是科学的办法。
剪辫的革命性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一行为的危险性,越是敢为他人之不敢为则反抗精神越强。国内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改良派就将剪辫提上了议程,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写道:“且垂辫既易污衣,而蓄发尤增多垢,衣污则观瞻不美,沐难则卫生非宜,梳刮则费时甚多,若在外国,为外人指笑,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去之无损,留之反劳。”[6]但是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剪辫之议未能落实。此后关于剪辫之争一直持续到清末,直到宣统三年清政府灭亡前才做出“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7]的决定。在海外,由于缺乏现代外交理念和外交机构,清政府对国人的管理鞭长莫及。早在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中,就有受国外环境影响“剪去辫子且皈依基督教”[8]的学生。清政府遂决定将赴美留学生撤回,可见此时“剪辫”依然是清王朝的逆鳞。如果按往常清政府的“留发不留头”的管理办法,部分主动剪辫的留学生按律应当处死。史料中只有“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9]161“均被立即遣送回华,以示惩罚”[9]138和“凡有水土不服过重及不尊约束者,先后分起撤回”[9]151之类的记载,未见关于这些被撤回的剪辫者处以极刑的记载。可见在对待留学生剪辫之事,清政府并未像对待普通国民那样严酷。正是清政府对留学生的另眼相看,为后来留日学生的剪辫潮打下了基础。
留美学生虽然被中途撤回,但其所学却依旧给封闭的清王朝做出突出贡献。各行各业越来越依仗留学生的学识,清政府不得不继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同时随着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越来越多的外国租界在中国出现。一方面是留学生对清王朝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清政府权力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两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了清末留学生的剪辫潮。邹容在1902年赴日留学的船上就将辫子剪去,断发后的邹容在日本期间一直在正常学习。鲁迅好友许寿裳年到东京第一天就剪去了辫子,许寿裳回忆:“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2]4许寿裳和韩强士二人是1902年秋到东京的,在日期间也未受到干扰一直在正常学习。
从1902年至1907年共有出使日本大臣发回的考察留学生情况及学务的文书共计6份,分别为《出使日本大臣蔡均奏陈驻日情形并请派科甲大员专管学务折》《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具陈兼管学务情形折》《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奏陈调查日本学务情形片》《学部:奏派刘崇杰等为驻日本调查学务委员片》。这些由官员实地考察后呈递中央的文书内容面面俱到但却只字未提留学生剪辫现象,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对留学生剪辫持有暧昧、模糊的态度。而且留学生回国后既可以靠假辫子伪装,也有租界可供避险,比如邹容回国后基本就在租界活动。鲁迅剪辫在邹容、许寿裳等人之后,以他在东京时期的观察力不可能意识不到剪辫的危险性已经大大下降。因此将鲁迅剪辫视为“革命”的说法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鲁迅剪辫并未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危险,他也并没有敢为人所不为。强行将鲁迅剪辫视为革命行为,实际上是对鲁迅自身的“务实”精神的忽略。
二、鲁迅剪辫:务实、洞察力、实践的合力结果
留学生剪辫的危险性既然大大下降,剪辫这一行为的革命性就只能来源于剪辫者的本心。鲁迅剪辫是否出于革命取决于留日时的鲁迅是否认为剪辫具有革命性。虽然鲁迅后来直言自己剪辫“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5]579。但这毕竟是鲁迅后期的文字,是否和青年鲁迅思想一致还需做进一步的考证。同时期革命派从剪辫开始他们的反清活动,根源在于革命派其实和清政府一样认同辫子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清政府认为辫子象征着忠诚和服从,革命派认为辫子代表着落后与奴隶。邹容回国后在著作《革命军》中对辫子大发批判,认为:“拖辫发,著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テセンセホツテ(译音施尾奴才)者。”[10]章太炎也撰写《解辫发》一文叹息自己剪辫太晚,并旁征博引论证剪辫的必要性。鲁迅并不在乎辫子所带来的除实际影响以外的问题。辫子对留学生最大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它时刻宣告着其主人来自中国,由此经常引起外国人的侮辱。鲁迅面对这些侮辱不仅能保持克制,还劝周围人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1)出自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1978年编著的《鲁迅在日本》。鲁迅的务实不但体现在他不为言语所动,更体现在他竟然为粗鲁的辱骂都想好了发挥其效用的办法。此外,鲁迅在东京时期已经达到了透过表象看本质的高度。许寿裳回忆鲁迅曾从蒋观云谈服饰的话“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2]9敏锐地观察出蒋思想的变化,后来蒋观云果然倒向了立宪派。对于能看透本质的鲁迅来说剪辫并不重要,“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5]576-577才重要。
留日时期鲁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高度,一方面让他透过辫子看到革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能让鲁迅洞察剪辫行为对革命而言并无多少实际作用。如果说鲁迅剪辫只是为了象征自己和清政府决裂,这无疑和鲁迅身上的“务实”性相冲突了。相反鲁迅之前不剪辫的行为倒是能够和其“务实”性相契合,剪辫这种于革命无实际作用的行为倒是有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日后鲁迅在绍兴中学做学监,就因为出于务实而禁止学生剪辫。怕学生“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5]195。即使鲁迅从其他剪辫者的经历中知道剪辫的麻烦未必会成真,但如果没有切实的必要鲁迅又何必多此一举。鲁迅后来之所以会剪辫,很可能只是因为辫子带给鲁迅实在的麻烦战胜了剪辫后可能的麻烦,所以鲁迅就出于解决麻烦的目的剪去辫子。鲁迅当时所面临的实在的麻烦很可能就是辫子妨碍了他学习柔道,这是不违背其性格的选择。
弘文学院的校长嘉纳治五郎不仅是一个教育家,还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在弘文学院创办牛逾分道场专门吸引中国留学生参加,鲁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道场开始学习柔道。此前鲁迅还能凭借极高的修养不在意辫子带来的麻烦,但在学习柔道时却无法再忽视辫子了,在对抗性体育运动中的辫子不但是累赘更是弱点。鲁迅在实践中感受到辫子的缺点并非只存在于非物质层面,而是切实存在于物质层面影响人的现实活动。身为一个务实的人,鲁迅自然而然就剪去了辫子。在以往的研究中,程麻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简单将不便归为剪发原因之一,没有深入探讨其中蕴含的务实精神。细野浩二虽然提出了导致鲁迅剪辫的是柔道,但他依然忽视了鲁迅的务实精神。鲁迅对剪下来的辫子做了如下处理,“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5]194。鲁迅并未做出像邹容那样将辫子抛进大海的极富象征意味的举动,也没有偷偷摸摸地藏起来或者扔掉,相反,鲁迅很自然地按其功用做出合理的安排,鲁迅的务实从其处理辫子的方式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不难看出鲁迅最初不剪辫是因为不想邀虚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后来剪辫是因为辫子带来了实在的麻烦。对于剪下的辫子鲁迅就同处理头发一样物尽其用,并没有赋予其特殊意义。甚至是后来归国禁止学生剪发也是希望学生们求心灵的觉醒,而不是专心于剪辫的形式。鲁迅无论在哪个阶段面对剪辫问题都一以贯之地以务实为出发点,因此鲁迅后期所说自己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5]579是没有自谦的实话,鲁迅所说的“不便”本质上是出于“务实”。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剪辫是其务实的精神、敏锐的洞察力和运动的实践三者合力后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学习柔道时上述条件才被同时满足。
三、被务实影响的救国思想
鲁迅的务实精神与其生长环境是分不开的,浙东地区的理性风气给予了鲁迅最初的务实启蒙。绍兴在地理上属于浙东,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越国。越国境内多水多山,生活环境恶劣,外有强敌环绕。为了适应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越人不得不发展出求真务实的作风。孔子来越国想为越王“述五帝三王之道”[11]51,但越王结合实际情况以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11]51为理由将其拒绝。此外,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的习惯虽然被中原视之为蛮夷之举,但这种生活作风又何尝不是越人务实的表现。因此越地人崇尚实用的精神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一直熏陶这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鲁迅的祖父就具备这种务实精神,他为子孙撰写的《恒训》中就记载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倘遇火灾,焚屋之中,烟气逼人,多被昏晕。急伏地下,匍匐走出,可免。”[12]有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和地方务实文化的熏染,鲁迅养成求真务实的性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鲁迅说自己剪辫不是效仿越人先祖,但鲁迅剪辫的动机和越人先祖不求虚名而追实用的精神一脉相承。
务实精神不但影响着鲁迅的剪辫,还影响着鲁迅救国思想的转变。以往的研究都注意到了鲁迅救国思想的两个阶段:科学救国和文学救国。但是学界不仅忽略了务实精神对鲁迅救国实践的影响,还轻视了务实精神在鲁迅救国思想转变中的重要性。当时的留学生主要通过加入革命团体和发表启蒙文章来救国。鲁迅加入了光复会,但由于鲁迅的务实思想使得他没有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鲁迅说自己“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13]鲁迅所说的“仔细”,本质上是他透彻的洞察力,而“疑虑”是发现事情和自己务实原则相悖的自然结果。光复会的很多活动尤其是刺杀违背自己的务实精神,所以鲁迅并没有积极参加。发表启蒙文章这种形式对于学生身份的鲁迅来说可行性高,而文章能直接影响读者的特点又十分实用。鲁迅因为曾经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过,对物理、地理、地质、矿务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鲁迅在留学时期能把所学和救国结合起来的最为实际的办法就是从所学出发,通过撰文科普对国人进行科学启蒙。所以鲁迅留学第二年就发表了科普文《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铂》。《中国地质略论》除了对中国地质矿产进行介绍外还有关于国家主权、命运的思考,在文末鲁迅直言:“吾既述地质之分布,地形之发育,连类而之矿藏,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掷笔大叹,思吾故国,如何如何。”[14]可见此时鲁迅已经在科普的基础上显示出救国意图,科学救国的思想便是在鲁迅学以致用的务实心理上形成的。
随着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的逐步了解,科学救国思想被鲁迅否定,这一过程发生在鲁迅在仙台学医的过程中。鲁迅选择学医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只有医专可去,另一方面是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5]438。因为去不了预想的东大读工科,鲁迅便选择了更容易入学的仙台医专,这当然是鲁迅务实的选择。而日本建立在医学之上的维新,又何尝不是促成鲁迅学医的因素。因此对于鲁迅来说学医既是出于个人人生的实用,又是出于救国的实用。在仙台学医期间鲁迅在一次出行中“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坐。这位妇人因此感激……并且送给他一大包咸煎饼。他大嚼一通,便觉得有点口渴……于是由她买了一壶送给他”[2]134。虽然鲁迅留日的文章经常提到那些羞辱鲁迅的日本人,但像藤野先生和这位老妇人也是善良日本人民的代表,因此鲁迅对日本人民并无偏见。而鲁迅在仙台却看见了身为强国的日本人民居然受着本国对外侵略战争的荼毒,“捐税和公债不断增加……物价不断上涨……青壮年男子大批被征入伍,或被征为民工……市内交通停滞……长子被拉去打仗,全家失去生活来源,其母被活活饿死”[3]131,这些情况都给鲁迅带来极大的震撼。1905年仙台的普通民众生活过得更差,因为仙台“有了俄国俘虏收容站,使得夏天的饥荒更严重了”[3]140。身处仙台的鲁迅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带给日本人民的苦难,不可能不重新思考中国走日本道路的正确性。科学救国的思想产生动摇,结合鲁迅在学校新闻中看见的中国人的麻木,务实的鲁迅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国人。能够使国人发生精神上的改变,从而建立起一个文明而强大的国家才是鲁迅真正想做的。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候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5]439这段话和鲁迅当时的心境是完全相符的。后来研究发现鲁迅退学的因素有很多,但避免投入精力在无谓的救国方式上也应被考虑在内。因此鲁迅选择从仙台医专退学而回东京创办《新生》,务实精神无疑在鲁迅从科学救国转到文学救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得出结论:“革命”并非鲁迅剪辫的决定因素,鲁迅之所以剪辫是由于他在学习柔道的实践中发现了辫子对人现实活动的束缚和妨碍。当时清政府对留学生剪辫的行为掌控力不够,剪辫的危险性已经大为削弱。务实的鲁迅不在乎辫子带给自己的非物质伤害,同时也洞察了剪辫对革命并没有实在作用。因此鲁迅并没有在别人剪辫无恙后就跟着剪辫,也没有在后期加入留学生剪辫的大潮。鲁迅在学习柔道时出于“务实”精神才将辫子剪去,所以其剪辫时间会处于许寿裳等人剪辫和留学生剪辫潮之间。务实精神不但促成了鲁迅剪辫,还影响着鲁迅救国思想的形成和转变。没有务实精神鲁迅不会注意到改变国人精神对救国的重要性,也就不会放弃科学救国拿起文学的武器。可以说正是在务实精神的影响下,鲁迅才踏上了文学救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