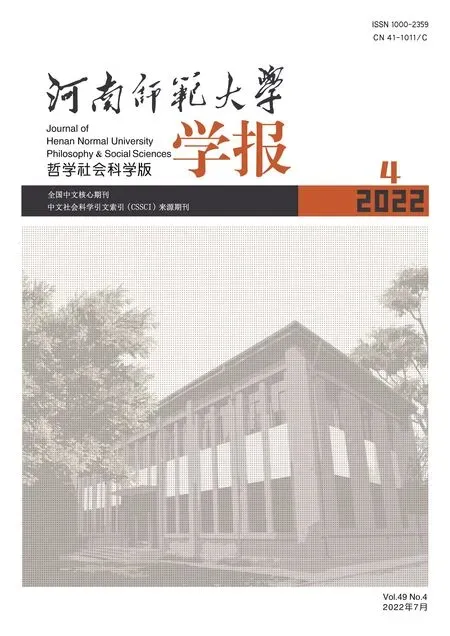在“笑”中认识自己
——论柏格森喜剧理论的一个重要向度
刘 臻,耿占春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笑”作为人类独有的经验,同时也是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动态映射。文学中的“笑”与滑稽常被予以典型化处理,并在理论层面被不断挖掘其作为某种“镜像”的人文内涵。相较于古典美学论及该问题的零星分散,柏格森的专著《笑》则凭借其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与深刻性,被视为喜剧理论的扛鼎之作。但我们也注意到,柏格森的研究建基于他对生命经验和动态生命哲学的推崇,他将人的本能和知性都纳入广阔的生命流动性之中,从而将“笑”与滑稽也视为活生生的、不断在社会中成长的过程。这就给了我们一种启发:如果我们从“笑”入手,抽丝剥茧进行追溯,是否会发现一种从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个体自我认知的现实可能?而“笑”又在个体自我认知的完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一
柏格森这样界定“笑”的动因:“当一群人全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不动感情,而只运用智力的时候,就产生滑稽。”(1)柏格森:《笑》,徐继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页。这里包含了三点要义:1.“笑”是人的经验反射;2.“笑”需要回响;3.“笑”源于智性的旁观。
柏格森从常识入手,界定引人发笑的“滑稽”仅属于人类,人类之外便无所谓滑稽。人之所以会在看到某种物或动物行为时乐不可支,那是因为人在物的身上或动物行为中看到了“人的态度或表情”或“古怪念头”(2)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3页。。可见,相较于以往哲学家所认为的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柏格森已更进一步,指出人不仅是笑声的发出者,也是引人发笑的对象。接着,柏格森又用了一个词来限定笑的发出者:笑在实际上总是“一群人”的笑。其中的深意是:“笑”的变动不居来自社会语境的变化,笑的行为在多数情境下乃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附和。从形式上看,一个人虽然可以偷笑,但即使偷笑也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包含有复杂的社会语境(“众人”)的因子。证据是,很多特定时空的笑料是无法移植到另一时空,并取得同样滑稽效果的。因为滑稽标准往往是特定时代思想与社会风俗的产物,是现实社会内容在文学虚构中激起的重重涟漪。此外,即便观众所观看的是同一部喜剧,一个人和一群人坐在剧院中观看喜剧的效果也会不同:对于个人而言,你的形单影只似乎附加了些许事实上的悲剧色彩——现实处境下被自我诗化的顾影自怜,而当你在众人中一起放声大笑时,周围的笑声则更能让你感受到“我是其中的一员”,你甚至会仅仅因为他人的笑而非剧情发展跟着去笑,这种与他人同步的安全感和集体归属感似乎才是人之所以发笑的深层根源。
继而,柏格森指出“笑”并非产生于情感的震颤,而是源于理性的旁观。欣赏者只有在“不动感情”的状态中,才能发现观察对象的不协调和可笑之处。一旦欣赏者对人物行为产生同情、怜悯或恐惧,笑就会消失。柏格森对于笑的理解,脱离了康德将“笑”视为一种感性游戏的观念,他将“笑”这一看似属于情感领域的活动,视为一种理性精神和富有哲理意味的生活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柏格森使用“不动感情”这个词时的言外之意:“一群人”对“一个人”的“笑”总是高高在上的,人们坚信自己只是笑的发出者,而绝非是笑的对象。笑的对象只能是“他人”所表现出的“滑稽”。这种对于“我”在“笑”所产生的对象关系中的定位,已触及人在精神层面上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而置身于滑稽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做讨论。现在,先来看上述三种动因所制造出的结果,即引人发笑的“滑稽”。
滑稽是“笑”的对象。自古典时期以来,便有很多关于“滑稽”的表述。譬如,亚里士多德将滑稽视为“丑陋的一种表现”(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8页。;席勒认定滑稽引发的“笑”在于它与真实的鲜明对比;黑格尔认为喜剧的意义在于主体对乖戾和卑鄙的超越;车尔尼雪夫斯基将滑稽等同于特定情境下因“不安其位”而显示出“荒唐”意味的丑(4)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89页。。以上不同时期的各家之言其实是同一种价值立场的延续和补充,即视滑稽为一种静态现象,将之等同于丑陋、悖谬乃至错误。与上述立场不同,柏格森敏锐地从生命本身的活跃与成长出发,指出引人发笑的“与其说是由于它们的不道德,不如说是由于它们的不合社会”(5)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93页。,从而将“滑稽”要义定位于“僵”,即一种“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机械的东西”(6)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5页。。这种非人的机械之物意味着人一旦被物化,便会呈现出毫无生气的外在机械表现和对灵动的生命活力的精神游离,从而以僵化的姿态产生滑稽的效果。
柏格森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乔治·桑塔耶纳就曾指出,对本性的强调和对生活的呐喊乃是人类的“原罪”,即便这种本能一直备受压抑,但它仍会在人的童年时期得到表达,并始终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之中(7)诺斯罗普·弗莱等:《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翔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既然对内在生命活力的执着是人的本能,那么对这种本能的抑制自然就会导致主体的“僵”。柏格森认为滑稽主人公的“僵”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本质的缺陷,是对自我本真的生命力加以束缚的“框子”(8)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页。,它具体表现为僵硬的表情、动作、姿态,以及固化的观念、智力、性格,外在的机械表现在根本上是与主人公内部精神的“心不在焉”(9)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7页。相呼应的,对于喜剧形象塑造而言,这二者往往能够相互叠加以增强滑稽效果。
重复、夸张、不合常理等都属于身体外在机械性表现,它们让观看者感受到,作为整体的滑稽人物虽然是活动的,但是其言行却是僵硬的、机械的。正如《伪君子》中达尔杜弗的入场,我们甚至坚信即便他身边无人旁观,他也会情真意切地说出那句“把我的修行衣和惩戒鞭收好”,这既是他的习惯,更是他的行动原则,即将一切行动都建立在他那套自我确信的内在逻辑之上的原则。这就是柏格森所说的精神的“心不在焉”,我们可以将这种“心不在焉”理解为主人公仿若置身梦境的理想化偏执。对于人们来说,走路摔跤本属正常现象,可是,假如他接二连三地摔跤,却丝毫不改他之前的步调,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滑稽的。《第十二夜》中备受女仆捉弄还“自信非凡,以为自己真了不得,谁看见他都会爱他”(10)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选》,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75页。的马伏里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百般出丑却还自命风流、慷慨激昂的福斯塔夫,显然都患有这类“过度自恋”的臆想症,他们沉浸于自说自话的姿态无疑是滑稽的。
柏格森将这种源于自恋的心理动机形容为喜剧人物的“虚荣心”,即一种“以想象中别人对他的欣赏为基础的自我欣赏”(11)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对于丑角而言,他们看不清自己的实际行动,更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不合社会”。这些人为了使他们自己的逻辑更具说服力,往往会像福斯塔夫将寻常村妇视作美人一样,赋予其他的人或物以新的形象。有意思的是,柏格森在描述这种滑稽人物所展现的“虚荣心”时,似乎不经意间提到,成为滑稽本身的可能并非仅仅局限于喜剧形象,反而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白日梦。他这样写道:“这种性格倾向(指滑稽丑角的虚荣心)虽为社会所不容,却又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离。”当喜剧作者们大费周章地创造出这种性格之后,却发现它“原来就像自然界中的空气一样,散布在人类之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2)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确实,在观看喜剧时,观众时常因为看到捉弄人者反被捉弄,或者自以为清醒之人掉进局中局而发出双重的笑声,这些笑声来自“我是清醒的”自我认知,但这一判断的成立却是以“合乎社会”的时代价值观为前提的。个体如果想要“合乎社会”,就必然会让理性代替经验、让知识而不是自我作为主体的判断依据,这就导致我们所感知的不过是“实用的简化了的现实”(13)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人们在应对现实时经常会因之将生命体验进行简单化的处理,甚至根据其“应有的模样”(14)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页。,而不是用真实的感受和思考来预设前景。这种对个人真实体验的遮蔽,以及将自己塞进世俗“框子”里的行为,不正是“僵”的表现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观看喜剧时,意识不到自己也置身其中呢?这就回到了柏格森在论证“笑”源自观众的“不动感情”和作为理想滑稽性格的“虚荣心”时所隐晦表达的观点,即观看者天然“自恋”导致了他们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荫蔽,往往会为了确保自我的优越感而不由自主地避开那些滑稽人物。如果说柏格森对于人类天然“虚荣心”的表达尚嫌含蓄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表达就显豁了许多,他从人类的无意识论域出发,直接将笑的动机之一归因于观看者的敌意本能。在论及模仿、伪装、解下面具、漫画、歪曲等制造滑稽的技术时,他认为这些技巧大多属于“贬低”手段(1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常宏,徐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207-210页。,即通过种种的具体技巧,人们会将他人置于某种滑稽情境之中,不仅会摧毁他们的品格与言行之间的一致性,而且会废除崇高事物既有的权威和庄严,人们由此会在攻击他人的快意中感受到一种优越感,并进而发出会心的笑声。
二
柏格森在对悲剧与喜剧的区分和梳理中也谈到了滑稽,他认为喜剧总是停留在生活的表面,通过对某种机械化人格的放大来表现生命之流的中断与僵化。这种机械性存在于现实人群之中,具体的滑稽形象总是能映衬出人们的性格缺陷,如吝啬、狂想、嫉妒,等等,因此,喜剧篇名往往是对现实性格类型的表达,如莫里哀的《吝啬鬼》《伪君子》、列雅尔的《赌徒》等均是如此。悲剧则不同,他认为悲剧旨在揭露人类在现实社会和功利理性之下的实在本质与生命之流,因此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往往更纯粹、更独特,乃至更具超越性,他们一般都能力出众、富于激情,虽经常遭受命运的耍弄,却又能在绝望中坚持抗争,是现实中很难见到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极富个性化特征。悲剧主人公虽然也有偏执、轻信、嫉妒等性格特征,但是他们纯粹的心灵动机和强大的意志力成功地掩盖了这些缺憾,“整个心灵以其全部充沛的力量深深扎根其间,煽动它们,带动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不断活动”(16)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页。。与喜剧的类型化命名不同,正剧/悲剧的标题多用具体人名等专属名词来证明人物本身的独特和深刻性,如《俄狄浦斯王》《奥赛罗》《哈姆雷特》,等等。柏格森据此判断说,正剧/悲剧是纯粹的艺术,而喜剧则介于生活和艺术之间。
按照常理,喜剧距离生活近,正剧/悲剧超脱于生活,喜剧才应该更易激起人们的共鸣,但柏格森却认为事实上并不如此。作家在创作正剧或悲剧时,总是采用深入内心和自我体验的方式切入人物形象,而喜剧作家对滑稽形象的观察则总是冷静的和旁观的(17)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由于作家对不同类型主人公的创作投入的状态不同,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受并不一样。以对悲剧中人物形象的欣赏为例,现实中的人们虽然受到了理性的压抑,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会因此而磨灭其生命激情,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希望抓住自己身上“最本质的东西”,而观看正剧或悲剧时的“代入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向社会进行报复”的机会(18)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从而揭开了他们自己身上所未曾意识到的那些成分,即人格中的悲剧成分。
观众在悲剧和喜剧中不同的介入态度,也与个体自恋意识不无内在联系。精神分析学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隐秘的英雄主义情结,我们既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万千人中幸运的“那一个”,也经常在历经失望之后觉得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或不公平待遇太多。面对悲剧作品,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内化为悲剧主人公,仿佛自己也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他”,进而在深入感受其生命的激情与痛苦时,产生出同情、怜悯、恐惧等情绪。人们既是为悲剧人物的悲怆命运而哭,也是为自己所遭受的命运磨难而哭。观看喜剧则不同,诚如柏格森所言,“无论喜剧诗人对人性的可笑之处多么感兴趣,我想他是不至于去探索他自己身上的可笑之处的。而且即使他去探索,也是不会发现的,因为只有在我们身上的某一方面逃脱我们的意识的控制的时候,我们才会变得可笑。因此这种观察是以别人为对象的”(19)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喜剧作家尚且如此,作为观众焉能例外。柏格森的这段论述极富深意。它证实了个体之所以拒绝代入喜剧,是因为他对现实有着某种恐惧,即滑稽给个体所带来的恐慌,以及他自身优越感的丧失。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全身心地沉浸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之中,并将自我进行绝对化时,是无法发现并接受“小丑竟是我自己”的结果的。人们虽然有时会故意扮演滑稽角色去逗人开心, 但这与其内心潜藏的优越感并不矛盾,甚或会指向一种自我感动的更高的优越感。
柏格森在论述“笑”的功用时,曾指出“笑”的目的在于使人学会谦逊,并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他认为人类生而自恋,就连反射性的腼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傲,因此,人们要想认识自我就要借助喜剧所引发的笑来省思自己的“虚荣心”,从而学会“真正的谦逊”(20)柏格森:《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在柏格森的视域中,作家/观察者不能过于深入主人公人格,否则就会损害喜剧的可笑之处,这就意味着创作者和观看者必须始终站在作品的外部,凭借知识理性而发出笑声。从这层意义上讲,喜剧用以纠正社会的“笑”其实是带有羞辱性质的,柏格森所理解的个体的“反思”,正是观看者出于一种自己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而沦为他人笑柄的考虑,才不断提醒自我要变得“合乎社会”。
由此看来,柏格森对“笑”的功用的阐释依然回避了个体对“笑”所包裹的内在滑稽性的发现。事实上,我们也要注意柏格森的这一表述:“只有在我们身上的某一方面逃脱我们的意识的控制的时候,我们才会变得可笑。”这句话其实为人何以能发现自身的滑稽性,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自我认知留下了进一步阐释的空间。通常来说,现实功利的考量让人无法在“此在”中分裂自己,因此人不可能实现对当下自我的反观。换言之,当人将自我视为完整的、绝对的主体时,是绝不会发现自身的渺小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即回顾过去的自己时,人才会发现并承认自己的滑稽可笑。这一时刻,人仿佛被分裂为两个毫不相关的存在,当下的“我”观望着过去时空中已无利害关系的另一个“我”,而发出笑声的“我”在现实中仍然是安全的。这就启发我们去思考人是否可以尝试在精神层面上拉开自己,凭借一种相对视角去看待当下的自己,从而发现自己身上的滑稽味?正如威克伦德和杜瓦尔所提倡的那样:“人们有时是把自己当作客体来认识的……采取一种局外人的观点,‘退一步’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这样做了,一般就会变得更能自我意识。”(21)J.L.弗里德曼,等:《社会心理学》,高地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也就是说,人通常沉溺于“自恋”情结之中,以“主观自我”来感受自己,看自己时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但若退一步,尝试一种视角的转换,有意借助“客观自我意识”跳脱出当下并回望自己,在具体语境中不断将自身对象化,从而看“自己”如同看“别人”时,就会确认自己的相对性,发现自己和别人一样可笑。至此,人所发出的“笑”就调转了方向,从指向他人转而指向了自己。在果戈理《钦差大臣》中有这样一处精彩描写——当做着联姻美梦的市长看到赫列斯塔科夫留下的嘲弄书信,感到自己将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时,恼羞成怒地丢下这样一句话:“你们笑什么?你们是在笑自己!”这里的“你们”究竟指的是谁?我们知道这出喜剧在公演后招致上流社会的大肆批判,以至于剧作家不得不侨居国外。那么,这句“你们是在笑自己”指向的难道仅仅是那些恼羞成怒,拒绝将自己代入滑稽形象的彼得堡权贵吗?还是说,这句警告其实也指向了站在全知视角和平民立场,自以为清醒,并在笑声中享受着由对上流社会的精神性侵犯所带来的隐秘快感的广大受众,包括今天正在发笑的我们?毕竟,一旦我们抽离自身,将自己代入对方的逻辑和立场,谁又敢保证自己绝不会是那个正在出丑的滑稽蠢货呢?
至此,“笑”的自我认识功能就在柏格森的“自我谦逊”的层面之外变得更为深刻:人若能发现自己可笑,就会在发笑的同时,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发现自己的渺小,并对自我绝对化倾向心生警惕。
三
人对自身滑稽性和现实滑稽语境的发现,已体现于柏格森之后的现代喜剧研究。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艺术的革新,现代美学家们更为关注人“生而在荒诞之中”的生存状态,而这也就使他们更注意到喜剧所蕴含的悲剧性内核。J.L.斯提安指出在生活的漩涡中,悲喜交加的世界经验导致人性及心绪体验的荒诞与混杂。由于喜剧更涉及人性,因此,新时代的喜剧作家才更需要为读者提供“一种黑色的娱乐,一份混杂着对立的道德成分的冷布丁”(22)诺斯罗普·弗莱等:《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翔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在黑色喜剧中,可笑与可悲之事总会借由一系列的微妙变化相互渗透和转换,整部作品通过决定性的“情调和气氛”(23)诺斯罗普·弗莱等:《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翔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来达成整体上的种种对立因素的相互协调,从而使作品中悲喜兼容的情节和情绪与真正的人生经验相呼应。作家之所以制作这份“冷布丁”,则是寄望于它对肠胃产生的刺激使读者僵化的思想重新活泛起来,能通过戏剧性体验重新感受自身心灵的复杂和裂变。同时,怀利·辛菲尔也站在时代语境变化的维度,提出人们应该尝试从全新的角度去欣赏柏格森的理论。他敏锐地指出,如果说在柏格森的笔下,悲、喜剧之间仍然泾渭分明,那么对于置身于二十世纪的现代人而言,他们在战争中感受的是人生“归根结底的荒谬”,进而发现人生“到处都有喜剧性”,“荒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的生存”(24)诺斯罗普·弗莱等:《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翔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12-14页。。在现实的“尘埃与冲突”中,个体的英雄梦宣告破灭,渺小感与悲怆感的并存导致现实人生的喜剧观与悲剧观交织混融。人们甚至发现,喜剧对人生境遇的荒诞化处理,更适合表现个体感受力不断被剖离的现实境况,这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性。正如卡夫卡小说中,被物化的K以其笨拙的姿态、无望的命运成为社会存在的符号,而卡夫卡站在外围不动声色的描述则更加深了这一滑稽形象的内在悲剧意味。荒诞派代表剧作《等待戈多》中,主角的机械言行和循环往复的行动模式,其实也正是丧失了根本的、不断被现实扭曲的、焦虑无着的现代人生存处境的表达。
那么,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新视角回望之前的戏剧创作,也会发现在塞万提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同样充满了滑稽味和悲剧感的深度融合。滑稽形象的命运和他们的游戏之道本身就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嘲讽,道貌岸然的存在被揭开假面,原本地位悬殊的身份及表达都被倒置。笑声将原本单一的痛苦不断转化为荒谬,并使荒诞的世界被“广场化”。果戈理曾在《新喜剧演出散场》中为“笑”正名,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笑的穿透力,生活的琐屑与空虚就无从让人感到如此震惊”(25)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笑”可以是肤浅和轻松的,但更可以是尖锐和深刻的。它可以打破社会中固有的关系和意义,并将其背后的荒诞与虚无揭露出来。当堂吉诃德、梅思金等人凝视着空想的灿烂星空而跌入现实的陷阱时,这些被现实不断绊倒却始终抬头仰望的理想主义者带着他们特有的纯真和被生活恶意盯视的悲怆凸显了现实的无情。在轻浮的、恶毒的、不断向外扩散的笑声里,狂热的空想家、合理得出奇的疯子们正在以他们富于内在系统性的“心不在焉”成为更具精神深刻性的诗性丑角,进而将世界的荒诞,同时也是每个人自身的荒诞展示给人看。
霍尔茨曾指出,反映定理的价值就在于借助一种表达方式,使得“超经验的现实——恰好作为世界的世界总体——能够被思考”(26)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反映》,刘萌,张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作为现实映射的“笑”也是如此。它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滑稽性,也意识到个体荒诞与世界荒诞的一体同构。那么,在“笑”所揭示的对象关系结构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和调和自身的悲剧体验与喜剧体验,从而重建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不仅关乎人在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也关乎人在主体经验层面上可能采取的行动。
让我们假设一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其实常会面对社会传统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庞然大物,譬如年轻人在行业内部面临的“论资排辈”、女性在求职中遭遇的重重壁垒等。在面对种种约定俗成的压迫时,有人会因为难以承受而放弃抗争,在安于现实命运的同时也走向精神的屈从,从而丧失自我。出于让自己保持他人眼中的尊严的“虚荣心”,他们甚至会转而投向压迫之物的怀抱。毕竟,顺从权威总会让人感到某种“在羽翼之下”的免责与轻松,并且只要在精神上肯定了庞然大物的合理性,似乎就能把自己从滑稽感中摘出来,甚至幻想自己被镀上了权威的光环。就像俗语“媳妇熬成婆”那样,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一些人将自己的所有失败都归因于外在压迫,但转身又用同样的习俗惯例来压迫他人的现象吗?但是,也会有人在发现现实的荒诞之后,意识到庞然大物本身也并非神圣庄严、坚不可摧,它也自有其局限、矫饰、滑稽之处,从而不断激励自己保持真正的自尊,坦然面对且不屈服于现实的困境。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到自身的境遇其实是社会集体共同面对的荒诞处境,这就更有助于个体为自己的抗争赋予意义,并将庞然大物对自身的碾压转化为不同话语斗争的平等对话关系,从而用全新的、自信的眼光认识自己以及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持存一种更加饱满、昂扬、积极的内在生命状态。
前面我们提到,只有跳出现实的功利性,才能实现对当下自我的反观。而悲剧性精神的价值即在于作为一种理想的激情和天然的生命活力,它激励人们为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使人们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当下的生活,而是在泥泞之中仍然存有抬头向上看的勇气。这种意义感来自荒诞派剧作家Havel所说的“责任”,即一种“人类必须看到自身对世界的责任,对自身以外的事物的责任”(27)Vaclav Havel.Disturbing the Peace: A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uizdala,Vintage,1991,p25.。只有在道德和精神层面秉持对某种“至高的存在”或“永恒的地平线”的向往,个体才会真正产生这种责任意识。换言之,这种责任感的内核在于我们并非出于功利的动机,即考虑到一件事情的成功概率才决定“能不能”去做这件事,而是仅仅出于“良心”,觉得自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现代社会的首要特征即在于“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28)张晨耕:《后现代性之于现代性:反叛还是延续?》,《齐鲁学刊》,2021年第6期。。在权力关系中,看似卑微的个体行动对于历史的形成却至关重要。个体对现实的主动介入总是在参与、改变并影响历史。此外,在柏格森动态生命观的视角下,历史并非是静止、僵化的,它由所有人的行动构成,虽然每个人的行动与选择可能是孤立的甚至片面的,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的整体性反观个体的行动,其有限性和片面性就会得到克服和超越。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的是,虽然悲剧性精神有助于个体寻找和树立意义感,但如果这种情绪被持续强化,就极易导致个体不断进行自我放大,从而在不经意间由对抗庞然大物的自信,滑向人性本源中自我神化的另一端,或陷入一种对所谓“神圣意义”的抽空和概念化处理。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同样有必要引入喜剧精神,即发现并反省自我的滑稽性。只有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意识到现实滑稽逻辑的自我内化,才能提醒自己不要过度自我想象,并拒绝陷入自己曾反抗过的机械僵化的概念之中。正如Havel对滑稽性与伟大精神之间的孪生关系的发现:“如果没有那些欢笑我们就不能完成那些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想在对意义的追逐中,“坠入这种严肃而不能自拔并变得无比荒诞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荒诞性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的认识”,“真正的意义只能从荒诞中看到”(29)Vaclav Havel.Disturbing the Peace: A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uizdala,p103.。在这里,Havel确认了“笑”在建构个人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主体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只有扎根于对世界的真切感受与体验,认识到自我的滑稽渺小,才更有助于以一种更为“健康”的心态强化自身的社会情感。Havel本人的经历即证明了这一点,他在面朝“永恒的地平线”时,就从未脱离过他“在下面的”(30)Vaclav Havel.Disturbing the Peace: A Conversation with Karel Huizdala,p101.的基本经验,并始终用这种“在下面的”的眼光来对待现实。所谓“从下面看”,是指一种“具体化的、富有个人经验性和人性的视角,一种拒绝客观化和抽象化的视角”(31)张宁:《“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天涯》,2006年第6期。。正如他最初点燃的社会情感其实源于他的资产阶级身份所带来的充斥着嘲讽和排挤的童年经验那样,他的儿时经历和其后的遭遇让他看到自己被针对的处境并非源于自身的错误,而是社会习俗对人的束缚,他才带着这种荒诞不经的、令人难堪的真实体验和感受投身于理想的“责任”之中。同时,他真切的基本经验和感受也让他能够以一种适当的幽默精神发现并嘲讽自身内在的滑稽性,这就确保了他既不会被僵化空虚的神圣概念框住,也不会使自己的行动成为对以往历史的复制。换言之,人只有从自身的真实体验出发,才能体认自己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从而降低自我放大和自我神化的风险,实现和保证心智的健全和自身的“内在同一性”。也许人的自恋谵妄永难消除,但这种对自我中心的警惕总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真实的感觉,而不是某些幻觉。
总之,不管是在精神层面还是行动层面,“笑”在人的自我认知实现过程中总是至关重要的。它既在破坏,也在创造。它致力于打破人们平静安稳的生活,将整个社会的因果关系、先验的价值立场、约定俗成的社会规约内在的僵化空虚展示给人看,让人在意识到现实荒诞的同时也意识到自身的滑稽渺小。同时,它也鼓励人们在幻想破灭后的废墟之上重建自己的主体认知,探寻自己的真实体验,并以一种敞开自身、主动介入的态度朝向现实,为历史提供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