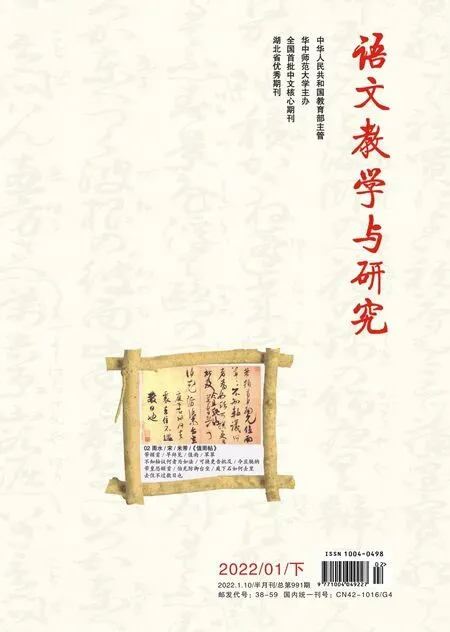从叙事空间角度解读《琵琶行》
◎肖春丽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源自《诗经》,通过千百年来叙事手法不断丰富完善、日益成熟定型,到唐代达到了鼎盛,并对后期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较传统的七律诗而言,叙事诗既要符合一般诗歌对音律和文体方面的规律特点,又要在语言、情节、结构等方面有自身独特的叙事特征。叙事诗的主题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字表层意思,还隐含在深层结构之中。
《琵琶行》作为叙事诗,在实际教学中,不能简单套用传统七言律诗等诗歌的教学方法,而可以结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理论来加以研究,从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交流、叙事空间四个角度对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进行重新解读。
首先,从叙事视角而言,表明上是描写诗人偶遇琵琶女,欣赏琵琶女演奏,倾听琵琶女身世,到与琵琶女惺惺相惜。在实际教学中,为了更好穿透作者复杂的心理变化,必须将时代背景交代清楚。而要深入挖掘作者写作时内心冲动的动因,一定要向学生讲清楚作者的创作总体背景。长诗前的小序介绍了该诗所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琵琶女其人,和作者写作此诗的缘起。但表象的背后是作者对朝廷面对藩镇节度使咄咄逼人的不法行为提出绝不屈服、征讨逆贼的正义主张,最终换来的却是贬为江州司马,从此他早期的意气风发的斗志逐渐销磨,负面消极情绪日渐其多。其次,从叙事节奏来看,此诗结构严谨缜密,错落有致,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全诗将叙事与抒情进行无缝对接,在叙述故事,完整塑造出鲜明人物形象的同时,语言匀称流转、和韵优美,特别是在描绘琵琶女的演奏,比喻精准、化虚为实,将富有特色的音乐形象,通过文字叙述展示在读者面前,奠定了其在叙事诗史上登峰造极的地位。后期清末文学家刘鹗创作的白话小说《老残游记》,就很好继承了该诗的衣钵。再次,我们转换到叙事交流角度,作者叙述作品中琵琶女的高超才艺和她的凄凉身世,通过自身贬官的遭遇和琵琶女漂泊的身世的对照,试图通过这一情境对比,与读者产生情感互动,抒发了个人政治上遭受排挤打击、遭到贬斥的抑郁悲愤之情,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最后,是叙事空间的角度,也是本文探究的重点,从全诗的空间布局来看,从相逢偶遇(共处)、琵琶演奏(共鸣)、聆听遭遇(共情)到感怀身世(共振)。诗人把一个倡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仕途的失意、生活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一、共处——偶遇琵琶女
《琵琶行》全诗共分四段,第一部分从“浔阳江头夜送客”至“犹抱琵琶半遮面”共十四句,写诗人与琵琶女的偶遇。叙写送别宴无音乐的遗憾,于是邀请商人妇弹奏琵琶,详细描绘琵琶的声调和琵琶女的形象。
首句“浔阳江头夜送客”,只七个字,就把时间(夜晚)、地点(浔阳江头)、人物(主与客)等记叙文的诸多要素一一作了概括介绍。随后“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作环境的烘染,这是一个枫叶红、荻花黄、秋风萧瑟的夜晚,离别向来是让人伤感的。而“主人下马客在船”一句,其实际是主人陪着客人一道骑马来至江边,一同下马来到船上。随后送别酒宴开始,由于没有歌女侍应,孤单的酒宴显得格外凄惨,当然就更加让人不快了。“举酒欲饮无管弦”一句中的“无管弦”三字,既与后面的“终岁不闻丝竹声”相呼应,又为随后琵琶女的自然出场和弹奏表演作了铺垫。在“无管弦”的基础上,又递进到“醉不成欢惨将别”,再加上“别时茫茫江浸月”进一步烘染,构成一种强烈的空旷、寂寥、压抑感,使得“忽闻水上琵琶声”具有浓烈的空谷足音之感,为下文的突然出现的情境反转作了准备。
在所有的背景交代结束和环境衬托完成后,作者偶遇琵琶女也就水到渠成了。通过“忽闻”“寻声”“暗问”“移船”等一组词汇,琵琶女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完成偶遇——“邀相见”,这与《红楼梦》中描写黛玉出场如出一辙。从水面上飘来船上悦耳的琵琶声,一下子就吸引了主人和客人,让他们停下各自送别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探寻这美妙的音乐。此时他们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不知道声音来自何处,更不知演奏者的身份。“欲语迟”与后面的“千呼万唤”“半遮面”相一致,这并不是琵琶女在意身份,而是有自己一肚子“天涯沦落之恨”,惭愧自己身世的沉沦,不愿抛头露面,更不愿提起。这段作者偶遇琵琶女,未见其人先闻其琵琶声,未闻其语先已微露其内心之隐痛,为后面故事的发展做好了悬念铺垫。
二、共鸣——聆听琵琶声
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唯见江心秋月白”共二十二句,是这首叙事长诗的第二段,写琵琶女演奏琵琶曲,与诗人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其中“转轴拨弦三两声”,是正式演奏前的调试弦音;而后“弦弦掩抑”,写出了曲调的悲伧,“低眉信手续续弹”,写的是情感舒缓过度。拢、捻、抹、挑,都是弹奏琵琶的技法。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到“四弦一声如裂帛”,描写琵琶乐曲的音乐形象,写它时而急促时而缓慢、时而昂扬时而细弱、时而高调时而无声,与之对应的是情感上的时而悲凄、时而舒缓。这里有落玉盘的大珠小珠,有流转花间的莺莺燕燕,有水流冰下的丝丝细细,更有 “无声胜有声”的宁静安详,诗人在这里用了一系列的生动比喻,使比较抽象的音乐形象一下子变成了视觉形象。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同时展示在读者面前,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接。这里向学生展示的主要是文字的技法,当然这也是叙事诗描述所涵盖的特征之一。
“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里表述了琵琶女的演奏效果。演奏已经结束,而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音乐魅力却正如“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周围鸦雀无声,诗人与客人都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只有一轮明月倒映水中。
三、共情——倾听身家史
从“沉吟放拨插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共二十四句为全诗的第三段,在曲终之后,也开始了关于身世的询问和叙述,而“沉吟”一词,正如“犹抱琵琶半遮面”,反映了她欲说还休的内心挣扎;“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等一系列动作和表情,则表现了她内心斗争后,向诗人吐露衷肠的心理活动。“说尽心中无限事”与之前的琵琶曲互相补充,完成了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琵琶女的形象塑造得异常丰满真实,并具有高度的典型性。通过这个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乐伎们、艺人们的悲惨命运。
正如琵琶声的抑扬顿挫,琵琶女“十三学得琵琶成”后,凭借高超技艺,早年曾成功走穴,盛极一时,她被老辈艺人所赞服,而被同辈艺人所艳羡,被王孙公子迷恋围猎。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时过境迁,人老色衰,琵琶女开始了沦落飘零的另一段人生。“弟走从军阿姨死”,贵族子弟们看不上半老徐娘,都不再登门,原本不多的几个亲属也相继离散而去,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嫁给了一个商人。商人关心的是赚取钱财,在艺术和情感上两人没有共同语言;加上经常外出经商,只留下这个可怜的女子独守空房、独坐孤舟。面对而今的孤独冷落,与昔日的锦绣岁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内心的痛苦只能独自体会,
四、共振——感怀自身苦
叙事长诗第四部分从“我闻琵琶已叹息”到最后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写诗人从琵琶女的琴声和身世,联想到了自身,不觉与琵琶女产生了同病相怜、形影相吊的情感共振。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中的作者,由于要求革除弊政、抑制权贵而受到贬谪的不公正待遇,从京城长安贬到相对偏远的九江,内心非常痛苦。当琵琶女第一次弹出哀怨的琵琶曲曲、诉说衷肠的时候,就已经触动了诗人的心弦,发出了由衷的叹息。当琵琶女诉说身世、泪眼婆娑的时候,就更是激起了诗人在个人感情上的共鸣。
但在情感共鸣之后,诗人不由自主产生了情感共振,他的内心苦闷是由于他政治上受到打击造成的,但是这点诗人也是“半遮面”,不愿更是不想触及这一伤口,因此他采取以彼之详、补此之略的手法,通过寥寥数笔,让读者自然而然联想到此刻他被贬以后的处境和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以后的处境是相同的,心境也是相通的。于是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作者的诉说,反过来又触动了琵琶女的心弦。此刻,她弹奏的琵琶曲与之前的曲调相比,更加凄凉悲惨;而这凄惨的琴声再次让诗人的感情得到升华,以至于老泪纵横,湿透青衫。
随着诗人和琵琶女都进入情感的高潮,在歌女悲惨遭遇明线和诗人官场失意暗线的交织中,全诗戛然而止。《琵琶行》凭借其明暗互衬,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让读者被其曲折的情节所感动,被美而朴实的语言所折服,最终也成就了其成为脍炙人口现实主义杰作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