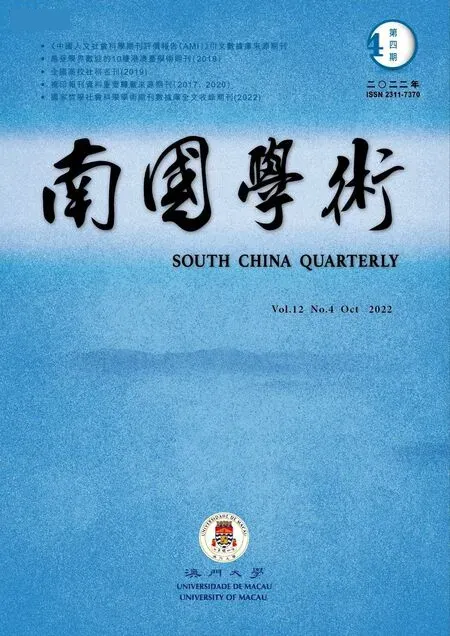從“德”“賽”到“平”“社”
——對“第三種文明”入住中國的考察
張寶明
[關鍵詞]德先生 賽先生 平民主義 社會主義 民氣 第三種文明
1919年,是中國近代歷史加速轉型時段。當五四運動成爲歷史學研究者競相折腰的節點後,很多當時處於邊角料位置的隻言片語在今天看來卻有滄海拾貝之感。以《時事新報》1919年5月12日摘登的一篇“時評”爲例,不能不說是對社會真相的直接感覺:
天地間的東西多得很,究竟要以什麽最利害?唉!那最利害的就是“民氣”!……巴黎人要講“民族自決”,那東亞的強國,還出來破壞他們。難道你們硬不曉得“民氣”的利害嗎?這並不是公理不能戰勝強權……到那公理出來的時候,恐怕強權在地球上沒有地方容了。公理是什麽,就是“民氣”;公理不能沒,就是“民氣”不可侮。……不看那“平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兩位先生,大步大步的在世界上走得非常之快嗎?那兩位先生是誰人?就是“民氣”差來的代表。若是等他們到了,那個利害我也不曉得,恐怕非將世界從根本上翻造一下不爲功啊!①鑒遠:“什麽最利害?”,《時事新報》1919-05-12。
從這個短短的“時評”中,讀者尋繹到了這樣幾個關鍵詞:“民氣”“公理”“平民主義”“社會主義”。而“第三種文明”,則是與其息息相關的邏輯必然。
一 “第三”: 在兩者相對中創造“獨立之境”
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雙子星座,正是陳獨秀、胡適的“姿態迥異,互相補充”,纔有了新文化陣營“互惠互利,相得益彰”的格局。②陳平原:“序三”,張寶明、王中江 主編《回眸〈新青年〉(語言文學卷)》(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第11頁。而兩位能夠引領新文化、塑造新青年的重要思想資源,無非是他們言必稱之的“德”“賽”兩先生。但是,還應看到,具有“桐葉落而天下驚秋”③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言治》3(1918)。那樣敏感嗅覺的李大釗,並沒有受制於“談”與“不談”政治的條條框框,他似乎在默默地獨闢着一條自己熱衷的蹊徑:“第三種文明”④李大釗:“‘第三’”,《晨鐘報》1916-08-17。。
在李大釗筆下,“第三種文明”概念最早是以“守常”爲筆名發表在1916年8月17日《晨鐘報》第三號上的《“第三”》。嚴格地說,李大釗的這一概念還不是完整的“第三種文明”,不過是“‘第三’之文明”。但這裏的意向或說意象已昭然若揭:“第三者,理想之境,復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獨立之境也。”從其文末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據典來看,與其說是一種解惑釋義,毋寧說是一次對未來充滿嚮往、期待、憧憬的呐喊。
這個“獨立之境”的開闢儘管有着同氣相求的基本判斷,但究竟是什麽還是有些抽象甚至混沌的。這個境界可以是“主義”、是“方向”,但卻不是“方法”。換言之,是目前的“烏有鄉”,但在李大釗們看來卻是不日可見的“有托邦”。這一糾結在《新的!舊的!》一文中歷歷可見:“宇宙進化的機軸,全由兩種精神運之以行,正如車有兩輪,鳥有兩翼,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⑤李大釗:“新的!舊的!”,《新青年》5(1918)。方法和原理昭然若揭,進化的道理也明明白白,就是具體落腳點在哪裏卻懵懵懂懂、不得而知。不過,時隔不久發表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再度闡釋這個道理時,則進一步點出了未來可能性之突破點:
東西文明之互爭雄長,歷史上之遺跡,已數見不鮮,將來二種文明,果常在衝突軋轢之中,抑有融會調和之日,或一種文明竟爲其他所征服,此皆未決之問題。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爲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爲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爲功。①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言治》3(1918)。
此文既完整地拋出了“第三新文明”崛起的興奮點,同時爆出了“俄羅斯之文明”的立足點。當然,作爲“方法”的俄羅斯還不甚明瞭,仍處於行船之“方向”一類。②陳獨秀:“主義與努力”,《新青年》4(1920)。
無獨有偶,張東蓀這位不願與政黨爲伍的政論家,對“第三種文明”的解釋既有懵懂的“發凡”,也有傾向的定位:
要而言之,第一種文明是宗教的文明;第二種文明是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文明;第三種文明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現在我請拿這三種文明比較一回。第二種文明是部分自覺的;第三種文明是普通自覺的;第一種文明是不自覺的。第二種文明是偏重個性的;第三種文明是偏重群性的;第一種文明是本性未開發的。所以,這三種文明各各不相同。有人說現在社會主義的新潮流是復古,這便大錯了。③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1(1919)。
這裏,張東蓀與李大釗不僅有幾分相像,還有更多的“同氣”成分。一是對“第三種文明”屬於“群體”“自覺”的認識;二是方向性的高度吻合,諸如對蘇俄革命領導人以及社會主義的讚同與認可,都屬於“第三者”的價值取向。如果說這時的二人有什麽方法論上的不同,那就是,李大釗用的是橫向比較(東西),張東蓀則是以縱向歷史發展爲綫索(古今)。不過,兩者異曲同工,都是對此前以“德先生”“賽先生”爲主體、爲關鍵詞的文化運動的超越。關於“第三種文明”概念,很難說就是李大釗、張東蓀的原創與專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五四”時期倡言最得力者當數兩人。
二 “民氣”: 一種爲“第三種文明”造勢的元素
所謂民氣,古代指的是民心、士氣,近代以來指的是民衆對關係國家、民族安危或走向所表現的意志力。《管子·內業》有言:“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晁錯寫給漢文帝的《言兵事書》說道:“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④〔漢〕晁錯:“言兵事書”,〔清〕姚鼐 編《古文辭類纂(上)》(武漢:崇文書局,2017),第153頁。清包世臣在《藝舟雙楫·再與楊季子書》中描述嘉慶初年的狀況時感言:“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污而民氣鬱,殆將有變。”時至近代,關於“民氣”的使用已司空見慣。尤其是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民族危亡關頭,“民氣”的使用屢見不鮮、直綫上升。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專門撰文論述“民氣”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梁啓超。1906年1月9日,他在《新民叢報》發表《論民氣》一文,從德、智、體三個側面詮釋“民氣”的用與不用。其一,“民氣必與民力相待,無民力之民氣,則必無結果”;其二,“民氣必與民智相待,無民智之民氣,則無價值”;其三,“民氣必與民德相待,無民德之民氣,則不惟無利益而更有禍害”。有鑒於此,民氣“必待民德而後可用,對內有然,對外亦有然”。針對“專以煽動民氣爲事者”,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即是說,有沒有“民氣”固然是衡量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個重要的觀測點,但這衹是必要條件,絕不是充要條件。僅有“民氣”還遠遠不夠,主要看有什麽樣的“民氣”。如果聯想到他此前的一篇發表在《清議報》上的《國民十大元氣論》,人們便不難理解他後文中“必待民德而後可用”那句話的真實意圖了。究其實質,“元氣”張揚的是民族危亡關頭用以救亡的物質與精神力量,帶有與生俱來的原始性、國民性、民族性。而“民氣”則帶有經過啓蒙塑造或說國民性改造後的“新民”或說“新青年”的素質。在這一意義上說,“民氣”和“元氣”不可同日而語。⑤韓釗在《清末時期梁啓超“民氣”論研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一文中說:“20世紀初的論者言‘民氣’者雖衆,然皆不出梁氏所論‘國民元氣’的定義範疇(結合漢語表達習慣,筆者推論近代意義上的‘民氣’很可能是‘國民元氣’的縮略稱謂)。”筆者對此不敢苟同。
在戊戌變法時期,嚴復、梁啓超等人就有過“民德”“民智”“民力”的啓蒙言說,也可以稱之爲“三民”或“德、智、體”①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2(1917)。。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無論是《新青年》知識群體的同仁還是這個陣營之外的代表人物,幾乎都是衆口一詞地將“民氣”視爲衹是代表國民“精氣神”的一種載體。這個載體可以說是“精神”,但就這一“精神”所代表的意義看,並沒有更多的褒揚成分,最多看做是一種蓄勢待發的客觀存在。但在民族危亡、國家式微的緊要關頭,“民氣”則成爲一個時代熱詞,頻頻出現在輿論文章中。單以《申報》爲例,涉及“民氣”一詞的文字從1916年的89條、1917年的44條、1918年的76條激增到1919年的658條。爲了避免老套,這裏衹以張東蓀、李大釗爲主體,分析一下“民氣”是如何在思想家的冷思考中成爲若隱若現的潛臺詞的。
不知是有意迴避還是無意忽略,在作爲多家報刊主筆的張東蓀、李大釗之輿論文字中,很少有像梁啓超那樣對“民氣”一詞的熱衷,更不用說推文專論了。目前衹翻檢到在張東蓀的文字中,有兩篇文章使用了“民氣”:一是發表在1911年《東方雜誌》第三號的《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二是發表在1915年《甲寅》雜誌第七號的《政制論》(上)。前文以“猶太人種”爲例,論述“民氣瓦解,不復成國”的隱憂,後文所用的三次“民氣”則是力陳“民氣消沉”的悲觀,意在“休養民氣”而重振國威。縱觀這裏的“民氣”內蘊,充滿了對國民之萎靡精氣神的提振意識。而就這一概念本身而言,無法與梁啓超“民氣”說相提並論,既沒有層次感,也沒有疑義相析。
1918年12月22日,在陳獨秀、李大釗的主導下,《每週評論》問世。由陳獨秀執筆的《發刊詞》,把陳、李二人的心態表露無遺:“公理戰勝強權。”這個《發刊詞》也代表了屢屢遭受“強權”壓迫之國人的心聲(或說“民氣”):“我們發行這《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畢竟多年遭蛇咬,還是心有餘悸地拋出一個美好的願景:“衹希望以後強權不戰勝公理,便是人類萬歲!”顯而易見,無論是《新青年》群體的內部還是外部,都有同氣相求的共識。以《新青年》爲例,其五卷五號簡直就等於是一個關於歐戰勝利的專號。撇開起頭的“關於歐戰演說三篇”中李大釗、蔡元培、陶履恭的文章不說,接下來加強版的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的“外三篇”更能說問題。②分別爲李大釗的《BOLSHEVISM的勝利》、陳獨秀的《克林德碑》、蔡元培的《歐戰與哲學》。
《庶民的勝利》對“世界潮流”的研判以及對“覺悟”意識的新解流露出強烈的“最利害”心態:“須知這種潮流,是衹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準備怎麽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記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徵幾。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雲發生的先兆……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爲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爲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③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5(1918)。拋開了威爾遜(T.W.Wilson,1856—1924)是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的命題,在顯示出較爲理性的論證邏輯的同時,又自曝出不乏理性但也較爲激情的一面。那就是對未來的預測與嚮往:“好人”並不是“最利害”的,哪怕是“第一個好人”也是靠不住的。衹有由一個人、一件事漸漸擴大、感染的“民氣”纔是“最利害”的。在李大釗筆下,其實不光是李大釗,“新青年派”知識群體似乎有意無意避諱使用“民氣”這個被一代思想先驅梁啓超撰文詮釋過的熱詞。或許是“義和團事件”讓人記憶猶新,或許是“民氣”需要拿捏不能隨便援用,反正在李氏筆下,“潮流”“先兆”“人心”“風雲”組合起來的意象儼然就是那避諱之詞的替身。這樣的勾連和對接乃是文脈或說文氣使然。如果結合“第三種文明”具體承載的涵義,人們會有更多的領略與感悟。
三 “第三種文明”: “平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聯袂
“第三種文明”背後有一個激進的社會進化邏輯,這在張東蓀等人主編的《解放與改造》創刊號上的“發凡”中已明確地指出:“里寧說:‘你們以爲大戰後必定是世界平和,我以爲大戰後必定世界大革命。’……這個結果是個甚麽呢?就是全世界的大改造——依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這裏的“里寧”即列寧(Лeнин,1870—1924)。作者不但提出了作爲原則的“第三種文明”這一概念,而且還有對此後“文化運動”方針的說明:“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協同的性格;要養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①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1(1919)。
如果說張東蓀將這樣的“原則”“方針”看作五四運動之後的運作方向,代表了社會思想界中這一聲音的異軍突起,那麽作爲新文化運動主體的“新青年派”知識群體的“後五四”走向,則可以從李大釗這一典型中得到印證。細說起來,李氏的這一“文明”理路並不顯得突兀,其有着若隱若現、有據可依的“來龍”和“去脈”。
早在《新青年》編輯部同仁主導法蘭西與英美文明的輿論時代,李大釗就對俄羅斯這塊熱土發生了興趣。首先進入他思想世界的是“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他以《甲寅》(日刊)記者的身份,連篇累牘地對俄國大革命揮毫潑墨。對其“遠因”“近因”的分析,對其與中國歷次革命之互動關係的描述,對“官僚政治”“賢人政治”的反思,凡此種種,都流佈在李氏文字中。一言以蔽之,俄國大革命的“醞釀”非一朝一夕,這是“氣運”所致,“唯民主義”之勢不可逆轉。②李大釗:“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甲寅》(日刊)1917-03-29。如果說對李大釗個人而言,這衹是一個思想預熱,還帶有嚮往的意念和成分,那麽隨後的《大戰中之民主主義(Democracy)》以“民主主義”爲杠杆對“俄國民主主義之光芒”的讚賞③李大釗高度讚揚俄國革命和民主主義精神,指出:“俄國民主主義之光芒,既已照耀於世界,影響所及,德國亦呈不穩之象。近日議會中之社會黨人,大聲疾呼,迫其政府改革內政,勵行民主主義。”參見李大釗:“大戰中之民主主義(Democracy)”,《甲寅》(日刊)1917-04-16。,以及《自由與勝利》以“自由”爲支點對“勝利”的解讀④李大釗這樣辨析“自由”與“勝利”的關係:“離於自由之勝利,乃爲牛馬之勝利,奴隸之勝利,其得之也,不惟不足以蒙其福益,且以增長其主上之恣暴,故勝利之結果等於零度。惟俄人知其然也,故於日俄之戰,欲索勝利,先索自由,故於今茲之戰,既獲自由,更望勝利。”參見李大釗:“自由與勝利”,《甲寅》(日刊)1917-05-21。,無不昭示着一種對自由戰勝專制、民主主義戰勝獨裁主義的高度讚美。正是由於這一精神氣質作爲伏筆,在胡適、陳獨秀一唱一和的文學革命中,作爲《新青年》編輯部骨幹的李大釗也不失時機推介《俄羅斯文學與革命》,儘管這篇文章未能及時發表⑤李大釗:“俄羅斯文學與革命”,《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2卷,第258~265頁。,但他還是將《俄國革命與文學家》這些夾槍帶棒的文字投給《言治》以表由衷⑥李大釗:“俄國革命與文學家”,《言治》3(1918)。。
最能體現李氏“自白”與坦誠的,是在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⑦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週評論》(第35號)1919-08-17。的時刻,他儼然以自信甚至有幾分自負的口吻對中國道路或說文化走向作出了何去何從的公然了斷。諸如《Pan……之失敗與Democrary之勝利》《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以“勝利”爲關鍵詞循環往復,將“民氣”這一熱詞掛靠在了世界潮流之“勝利”的戰車上。在李大釗那裏,這是“民主主義”的勝利,也是“勞工階級”的勝利,言下之意乃是“世界的人人”之命運共同體的勝利。“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是“人間普遍心理表現的記錄”。這個“記錄”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民氣”的流佈:“人間的生活,都在這大機軸中息息相關,脈脈相通。一個人的未來,和人間全體的未來相照應。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關聯。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獨是法蘭西人心變動的表徵,實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表徵。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廿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這個字,雖爲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廿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①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5(1918)。
“全世界人類人人”意味的是普天下勞苦大衆的世界。針對弱肉強食的進化理論,思想先驅以人道主義的平等原則爲指標,逐漸由精英(賢人)轉向平民(民粹)。這如同李大釗在《階級競爭與互助》中所理解的那樣:“Ruskin說過:‘競爭的法則,常是死亡的法則。協合的法則,常是生存法則。’William Morris也說:‘有友誼是天堂,沒有友誼是地獄。’這都是互助的理想。……人類應該相愛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進化;不可依戰爭而生存,不能依戰爭而進化。這是我們確信不疑的道理。依人類最高的努力,從物心兩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類,必能創造出來一個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這是必然的事實。”②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每週評論》(第28號)1919-07-06。這與張東蓀所說的“互助”“協同”“合群”如出一轍。③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1(1919)。如果說在這一點上說得還不夠透徹,那麽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李大釗則把支撐“平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盤托出:“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爲正宗。‘馬克思主義’既然隨着這世界的大變動,惹動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誤解。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雖然極其貧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馬克思誕生百年紀念以來,各國學者研究他的興味復活,批評介紹他的狠多。我們把這些零碎的資料,稍加整理,乘本誌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他轉介紹於讀者,使這爲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吾信這也不是絕無裨益的事。”這樣的解讀最終會得出如願以償的結論:“資本主義是這樣發長的,也是這樣滅亡的。他的腳下伏下了狠多的敵兵,有加無已,就是那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本來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到後來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現今各國經濟的形勢,大概都向這一方面走。”④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5-6(1919)。毋庸置疑,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是“科學”的,由此社會主義的實踐也一定是科學實踐。
說到這裏,人們不免產生一個疑問:“五四”之前衆口一詞的屬於西方文明硬核的“德先生”,何以在一夜間就輕輕鬆鬆轉向了屬於“第三種文明”的“德謨克拉西”?在“德先生”與“德謨克拉西”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轉換“機軸”?
四 “兩先生”之間: 語義轉向的潛在機理(上)
如果說造的“勢”即“民氣”是語義轉向的外因,那麽,“理”則是其自我轉換的內在因素。當然,這個“內”不單指當事人個人內在的思想機理,還包括思想界同仁內部的刺激與觸動。
所謂詞語轉義,指固有的意義轉換借代出另外的意義。例如,“社稷”原本指兩神:土神爲“社”,穀神爲“稷”。隨着古代天子、諸侯都要祭祀社稷,後來就以“社稷”一詞指稱國家。聯想到“Democracy”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飛舞與翻轉,當“‘平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兩位先生大步”向我們走來的時候,如果不是逆轉、也不是反轉的話,那麽在這個驟然或說陡然間,多年拱手的“德先生”“賽先生”何以就此別過呢?
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正是有了民主(“德”)、科學(“賽”)兩先生作爲硬核的參與,一切的迎來送往都會顯得從容、自信且有底氣。陳獨秀不就是將兩先生既作爲“矛”又作爲“盾”使用且左右逢源的嗎:“本誌同人本來無罪,衹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纔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①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1(1919)。胡適之所以將“賽先生”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無非看中了它與“德先生”一樣,具有捉妖闢邪的強大功能:“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②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第2頁。
既然新文化同仁對“德”“賽”兩先生有着強烈的認同與“認定”(“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③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1(1919)。),何以這種自信在風吹雨打後會有被“洗禮”的感覺呢?這除卻新文化運動前爲了顛覆、“打倒”、破壞“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以及“舊藝術、舊宗教”,不得不狠下猛藥、一鍋亂煮外,也與運動開始後的輿論對外來思想沒有作系統的揀擇、甄別有關。加之“民主”“科學”本身就是舶來的,在內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混沌性和多歧性,這就爲援引者的各取所需留下可塑性空間。
鑒於問題的複雜性,這裏衹以李大釗爲例加以審視,偶爾也會拉出“南陳”(陳獨秀)作爲必要的陪綁來鋪墊。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乃至之前,“民主”“科學”尤其“科學”是作爲文明之邦的“公理”而大推特推的。所謂文明國家以及對文明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的推崇,無非是說其更公平、更正義。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公理”就是推介西方文明觀的最大理由和依據。這樣一來,也不免能做這樣的換算:前期的“公理”隨時有可能轉換爲“民氣”。因爲,“民氣何自生,生於公理也……民氣足以助公理之伸張,公理亦足以助民氣之發揚也”④默:“民氣”,《申報》1919-05-06。。這從五四運動前後“新青年派”以歐戰結束爲“機軸”來扭轉文化運動的方向,明顯看出是將“公理”與“強權”作爲蹺蹺板的。當人們膜拜的“公理”世界爲“強權”世界的“強盜”邏輯所遮蔽後,“公理”的中軸必將讓位於“民氣”的氣場。
於是,當歐戰的勝利成爲國人歡呼雀躍的興奮劑後,一個新的說法也在刷新着人們對“民主”(包括“科學”)的認知:這是“Democracy之勝利”“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也是“自由與勝利”⑤李大釗:“自由與勝利”,《甲寅》(日刊)1917-05-21。的進一步演繹。一言以蔽之,是“廿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⑥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5(1918)。這裏的“Democracy”,已經是心有所指、心有所向,是“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着Democracy的顏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濟上也有他;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上,凡在人類生活中佔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同時,“戰後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表現。因爲Democracy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應該要求一種Democracy的產業組織,使這些勞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機會,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⑦李大釗:“勞動教育問題”,《晨報》1919-02-14,1919-02-15。。這個“自由”與“Democracy”乃是意向的具體化:“俄國革命”“所創造”的“精神”,說穿了是“民氣”。這裏的“自由”不是胡適、高一涵、陶孟和等英美自由主義派的“自由”,而是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國民(平民)獲得平等、獨立之人道關懷的自由:“此次戰爭告終,官僚政治、專制主義皆將與之俱終,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義必將翻新蛻化,以別開一新面目,別創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紀之新天地。然則吾儕今日,不願爲某一特定之國民希望勝利,而爲世界各國之平民希望勝利;不願爲某一特定之國民祝禱自由,而爲世界各國之平民祝禱自由。”①李大釗:“自由與勝利”,《甲寅》(日刊)1917-05-21。這裏的“Democracy”乃是“小者、屈者、弱者、消者”等“被災殃而逢禍患者”對“大者、張者、強者、長者”等“蒙幸運而樂福利者”的勝利之運勢下的新型民主。②李大釗:“Pan……ism之失敗與Democacry之勝利”,《太平洋》10(1918)。
本來,在中國本土語境中,“民主”就有“民之主”的帝王將相的隱喻。一旦將“Democracy”對應爲“民主”,加之不同思想譜系的五味雜陳,一時間很難有一個明顯清晰的定義。因此,五四運動時期對“Democracy”的理解可謂五花八門,以至於當運動落幕後,當事人爲了避免歧見,再使用該詞時,都有意無意回歸到原汁原味的音譯“德謨克拉西”。③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12(1999)。的確,當歐戰勝利後的巴黎和會不按常理出牌的消息傳入國內後,本來就對西方民主有所猶疑的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原產地也就又多了一層疑慮。“科學”的科學性固然沒有因此拒絕,但這個曾經如日中天的當紅“先生”卻也在悄悄走下了神壇。這時的“科學”作爲觀念已經每況愈下,在“民氣”頤指下,流爲一種徹頭徹尾的工具。按照先前的理解,“科學”是造福於人類的公器:“科學之興,產生二果:其一精力之爲物,大效用於人間之生活;又其一則原料精力變爲有用精力之時,其效率必至增加。……科學智識之增長,人間精力效率之高度,其事至明。人間若不幸無此智識,仍至何時,亦固守愚昧劣等之生活狀態以終。”④陳獨秀:“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續第一號)”,《新青年》3(1916)。但當發現“科學”既能造福也會造孽之際,這個衹剩下工具意義上的中性詞甚至淪爲了主義的副詞與修飾語,“科學社會主義”一詞就是典型。鑒於“科學”與“民氣”的關聯度不是本文論述重點,下面將以“民主”爲支點,審視其如何翻轉爲“平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
就英美“Democracy”的路徑來看,這個“民主(主義)”裏包含着自由、平等、博愛(獨立)三個觀念,如果與法俄“Democracy”的路徑相比,其內涵要素基本相同,但邏輯排序卻是平等、博愛、自由(獨立)。也就是說,儘管觀念相似,但排序先後的不同則決定了英美自由主義與歐陸自由主義的分野。⑤高力克:“《新青年》與兩種自由主義傳統”,《二十一世紀》8(1997)。“五四”前期之所以對“民主”(人權)、“社會主義”等意念模糊,與其認同與理解不一致有關。以《新青年》的“主撰”陳獨秀爲例,他對“Democracy”的理解就有與其他同仁不一致的看法,而且即使對法蘭西人的三大貢獻之一“社會主義”充滿憧憬,也衹能以“理想甚高,學派亦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併未盛行”而暫且擱置。⑥陳獨秀:“通信:答褚葆蘅”,《新青年》5(1917)。不過,儘管有很長一段時間對“社會主義”存在着“渾樸的趨向”的感覺,畢竟還有“卻是唯一的趨向”的堅信。⑦張東蓀:“我們爲甚麽要講社會主義?”,《解放與改造》7(1919)。這裏可從“新青年派”這一知識群體中找到支持。
《新青年》剛創刊時,同仁內部曾有“不談政治”的君子協定⑧張寶明:“‘不談政治’的悖說(1914─1919):對陳獨秀‘五四’政治心態的求解”,《學術界》2(1995)。;後來,就有了思想“武庫”中的雜陳與紛爭。這從魯迅對編輯部會議的回憶中可以窺見一斑⑨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寫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參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6卷,第73~74頁。。在衆聲喧嘩的思想譜系中,又以胡適主導的消極“自由”與陳獨秀主導的“積極”自由分庭抗禮爲主綫⑩張寶明:“胡適‘健全的個人主義”’與‘自由’的分野”,鄭大華、鄒小站 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第403~414頁。。在這樣的思想張力中,儘管陳獨秀是《新青年》的主撰,但胡適(們)卻以“學問家”的內功在陣勢上處於壓倒式地位。因此,人們看到的《新青年》前期思想譜系中最爲突出的還是具有人文主義底蘊的“個人主義”。至於後來“新青年派”與“學衡派”形成了勢不兩立的“人道”與“人文”的對峙,乃是因爲《新青年》後期愈演愈烈的人道主義立場所致。①張寶明:“新青年派與學衡派文白之爭的邏輯構成及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2011)。其實,在“新青年派”群體內部,他們本身就潛存着“人文”與“人道”的緊張。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個人與權利優先的自由,在胡適那裏被表述爲“健全的個人主義”②胡適在《新青年》1918年第6號推出的《易卜生主義》一文中提出:“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衹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麽。……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後來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將其稱爲“最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文選》(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第8頁〕。,在陳獨秀那裏則是“個人本位主義”③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4(1915)。,在魯迅那裏是“個人的自大”④魯迅:“隨感錄·三八”,《新青年》5(1918)。,在周作人那裏則是鮮明的人本主義基調:“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衆’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⑤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6(1918)。後者可以說道出了“民主”意念下的“人”的根本訴求。在胡適的“人”的導向下,李大釗的“人”之“個性的自由與共性的互助”思想不可能佔據上風。⑥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新潮》2(1919)。這也是兩人後來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刺刀見紅的必然原因⑦張寶明:“‘問題’與‘主義’:兩種思想譜系的歷史演繹——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看《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銜接”,《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2004)。。而這一切,都與對“人”的認識有關:“人”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具體到20世紀中國的語境下,又與舶來的“德先生”休戚與共。“平民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先生的到來就是這一思想的延伸和演繹。
如果說“渾樸的趨向”是五四時期“新青年派”以及其他文化群體的共相,那麽在李大釗身上還找到了一種殊相:“唯一的趨向。”在這裏,首先看到的是“雖千萬人,吾往矣”⑧《孟子·公孫丑上》(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第126頁。的思想膽識。作爲新文化陣營中的異數,儘管陳獨秀與李大釗有同氣相求的共識,但在“新青年派”的團體中,前期陳獨秀還是受胡適思想的牽制,後期纔有了李大釗的牽引。陳獨秀固然有“特立獨行”“揮灑自如”的個性,但就其作爲經營一個雜誌和總理一個團隊的“主撰”來說,他不能不作必要的妥協。⑨陳平原:“序三”,張寶明、王中江 主編《回眸〈新青年〉(語言文學卷)》,第11頁。
五 “德謨克拉西”: 語義轉向的潛在機理(下)
早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李大釗就在具有一邊倒的“弱肉強食”、一邊獨大的思想環境中反復述說“協力”“調和”的價值觀:“現代之文明,協力之文明也。貴族與平民協力,資本家與工人協力,地主與佃戶協力,老人與青年亦不可不協力。現代之社會,調和之社會也。貴族與平民調和,資本家與工人調和,地主與佃戶調和,老人與青年亦不可不調和。惟其協力與調和,而後文明之進步,社會之幸福,乃有可圖。”⑩李大釗:“青年與老人”,《新青年》2(1917)。歐戰勝利之際,他獨標異見:“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將“自由”與“人道”相提並論,進而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一條綫索十分分明,與五四運動後力倡的“依互助而生存”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5(1918)。之人道主義思想銜接起來,實現了“從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根萌,都純粹是倫理的。協合與友誼,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法則。”
此後,具有一種民粹傾向的烏托邦式的民主接踵而來,對“Democray”李大釗:“階級競爭與互助”,《每週評論》(第28號)1919-07-06。的翻譯,除去“德謨克拉西”外,最流行的譯法是“平民主義”“唯民主義”“庶民主義”。平民主義的衝擊波滲透到各個領域,“民主”被理解爲一種不需要權威、衝破強權的解放運動。有的甚至喊出“平民直接立法”這樣簡單化的口號①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1(1919)。。陳獨秀也由精英式的“民主主義”者向“唯民主義”過渡:“封建時代,君主專制時代,人民惟統治者之命是從”,而今則應反其道而行之,“是以英法革命以還,惟民主主義,已爲政治之原則”;②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誌》2(1915)。並且指出:“所謂立憲政體,所謂國民政治,果能實現與否,純然以多數國民能否對於政治自覺其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爲唯一根本之條件。……是以立憲政治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③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6(1916)。五四運動發生後,他又進一步提出“平民征服政府”的口號:“用強力發揮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數的政府當局和國會議員都低下頭來聽多數平民的命令。無論內政外交,政府國會都不能違背平民團體的多數意思。”④陳獨秀:“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週評論》(第23號)1919-05-26。1919年,視陳獨秀爲“思想界的明星”⑤毛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湘江評論》(第1號)1919-07-14。的毛澤東從陳那裏借了三百大洋創辦《湘江評論》,在創刊號上,他也如出一轍地宣稱:“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爲‘平民主義’(兌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餘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⑥毛澤東:“創刊宣言”,《湘江評論》(第1號)1919-07-14。這也正是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中指引的方向:“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裏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纔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⑦李大釗:“青年與農村”,《晨報》1919-02-20—23。這即是“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理念下的“勞農共和國”的前奏。⑧李大釗:“赤色的世界”,《每週評論》(第29號)1919-07-06。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自由、平等、獨立、博愛等詞既是那個時代的關鍵詞,也是衆聲喧嘩的熱詞。但翻閱其排列組合之順序,大多沒有具體的章法和規則。衹有將文本細讀之後,纔會發現,原來“自由”優先是“個人主義”時代的基本法則。鑒於這一問題學術界多有論述且業已形成共識,這裏重點關注何時何地變成了“平等”優先。以歐戰勝利後的《每週評論》發刊詞爲例:“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列位要曉得什麽是公理,什麽是強權呢?簡單說起來,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德國倚仗着他的學問好、兵力強,專門侵害各國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敗,稍微懂得點點公理的協約國,居然打勝了。這就叫做‘公理戰勝強權’。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⑨陳獨秀:“發刊詞”,《每週評論》(第1號)1918-12-22。這段話意在表明,“自由”問題已經是“平等自由”的問題了。這裏的“平等自由”不是偏正結構,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不平等的“平等”組合。“公理戰勝強權”一語破的,從此世界是一個人人平等、國國平等的樂園。當然,這個“平等”觀念主導下的社會主義有着本土先天性的土壤和語境,與古代中國“均貧富”“不患寡而患不均”觀念息息相關。①1901年1月28日,留日知識分子所辦《譯書彙編》第2期刊載了日本學者有賀長雄《近世政治史》中的部分內容,其中寫道:“西國學者,憫貧富之不等,而爲傭工者,往往受資本家之壓制,遂有倡均貧富制恆產之說者,謂之社會主義……中國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謂社會主義。”參見吴相湘 主编《中國史學叢書·譯書彙編》(臺北:學生書局,1966),第161頁)。可以說,社會主義傳入東方後,所宣傳的“均貧富”“制恆產”等思想與中國古代的“均平”“大同”等傳統文化思想相契合。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爲社會主義的文化土壤,爲其在中國的傳播做了準備、鋪墊。
當然,“五四”之後強調的“平等”,已經不再是水平意義上、而是帶着垂直傾向的“平等”了。其根本表現是,伴隨着對“精英”的矮化,對“民粹”(底層民衆)日益拔高。其實,新文化運動伊始,“平等”就是那一代思想先驅的根本行動指南。陳獨秀後來曾毫不諱言當年從事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文學的德莫克拉西”,可以用來“反對一切不平等的階級特權”,意在強調下層民衆也享受同樣權利這一定位。②陳獨秀:“我們爲甚麽要做白話文?”,《晨報》1920-02-12。以此類推,1919年後“民主”逐漸爲“民治”尤其是“德謨克拉西”所取代,原因還是由於啓蒙者對經濟上、道德上的多數決定意義上的倚重。這時的平等顯然是有傾向的平等:精英畢竟是少數,“民氣”的形成必然由多數民衆所凝聚。所謂的“民主”“民治”,歸根結底還是多數民衆的“德謨克拉西”。在這個意義上,“德謨克拉西”也就成爲“平民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先生的硬核。
就“民主”在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啓蒙指歸而言,其政治上的意念佔據了核心地位;但就“德先生”“賽先生”張目的過程來看,則是道德理想主義的重現。也就是說,“民主”與“科學”在本土化過程中被新倫理、新道德的要素充塞進了新政治、新社會、新國家的皮囊中。③張寶明:“新文化元典與現代性的偏執:五四啓蒙精神與‘內聖外王’思維的弔詭”,《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004)。但這一潛在的邏輯,因爲新文化人的新名詞、新概念、新說法、新內容而被忽視。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後,這一邏輯其實並沒有因文化的退潮而有所改觀,反而以另一種形式愈演愈烈:那就是在經濟上、文化上(倫理道德)走向了新的終端。這首先表現在“德謨克拉西”和“賽先生”不約而同地成爲道德合理性、倫理正當性的急先鋒,科學社會主義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之平民主義導向十分深入人心。李大釗對這一風靡全球的潮流這樣描述:“現代有一最偉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類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會、產業、教育、文學、美術,乃至風俗、服飾等等,沒有不著他的顏色的,這就是今日風靡全世界的‘平民主義’。‘平民主義’,是一種氣質,是一種精神的風習,是一種生活的大觀;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制度,實在是一個抽象的人生哲學;不僅是一個純粹的理解的產物,實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衝動、欲求的光澤。若把他的光芒萬丈飛翔上騰的羽翮,拘限於狹隘的唯知論者的公式的樊籠中,決不能得到他那真正的概念。那有詩的趣味的平民主義者,直想向着太陽飛,直想與謝勒(SheHey)、惠特曼(Whitmen)輩摶扶搖而上九霄。”④李大釗:“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新青年》6(1922)。這也成爲民心、民氣的內在驅動力。
經濟上的“德謨克拉西”,則是更勝一籌。畢竟,“空洞的自由,須實質的經濟平等來保障,方可算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要求真正的自由,第一就須打破經濟的不平等了”⑤周佛海:“自由和強制——平等和獨裁”,《新青年》6(1922)。。李大釗的《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固然是講求經濟平等的代表作,而陳獨秀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也對經濟平等的意義作了三番五次的論述。陳文深受杜威(J.Dewey,1859—1952)在華講演的影響。1919年5月,杜威來華講學,胡適不斷爲其講演奔走相告。6月,杜威在北京學術演講會的會場做了題爲《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的講演,他認爲,“美國的民治觀念就是自由平等兩個觀念合起來的,要叫個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自由發展他自己的本能”⑥[美]杜威:“美國之民治的發展”,《每週評論》(第26號)1919-06-15,涵廬記錄。。陳文提出了“政治方面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民治主義”兩個概念,前者包含“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以及“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兩種元素;後者也包含兩種因素,即“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類”,強調經濟平等。在陳獨秀看來,“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經濟的民治主義”至關重要:“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原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在這兩種工具當中,又是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我以爲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應當佔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①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1(1919)。而李大釗的一系列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的文章更是將經濟平等提高到了至高的地位——“經濟的決定論”②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新青年》4(1920)。,“宗教、哲學都是隨着物質變動而變動的”,“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義,都在物質上經濟上有他的根原”;③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2(1919)。“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④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2(1920)。,“德謨克拉西,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要尊重人的個性,社會主義的精神,亦是如此。……社會主義與德謨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不過社會主義,目前係注重經濟方面:如男子佔勢力,而以女子爲奴隸;貴族自爲一階級,而以平民爲奴隸;資本家自爲一階級,而以勞動者爲奴隸。凡此社會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現象,都爲德謨克拉西所反對,亦爲社會主義所反對”⑤李大釗:“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國大學的演講”,《晨報副刊》1921-12-16。。陳獨秀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社會主義”即是“經濟的德莫克拉西”,也是用來“反對一切不平等的階級特權”的。⑥陳獨秀:“我們爲甚麽要做白話文?”,《晨報》1920-02-12。
杜威的講演以及胡適的鼓吹,非但沒有造成對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的阻礙,反而成了“兩先生”大步走來的潤滑劑。這從陳獨秀關於“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⑦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1(1919)。的表述以及李大釗等人的引經據典中不難看出其中的印跡。由此也可以說,平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以“倫理”和“經濟”爲切口入住中國的。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此前梁啓超所謂的“民氣”之豐富性在急劇萎縮,路漫漫的啓蒙重任也在減負,彷徨痛苦逐漸被百萬工農踴躍的呼聲所壓倒。猶如熱氣球的升騰速度一般,一夜之間,“德”“賽”兩先生很快被後起之秀“平”“社”兩先生所取代。由此,“第三種文明”的架構基本落定,一個新型的現代國家在20世紀將要屹立於東方。
綜上所述,如果說“文明”是縱向的綫性觀測,“文化”是橫向的比較、帶有固化意念的話,那麽,在五四運動時期最爲叫響的“第三種文明”究竟是文化意義上的還是文明意義上的呢?產生困惑,或許是因爲兩個概念本身的交叉互爲、紛紜膠著造成的,但就學理探究而言,又不能不關注它。也許,新的崇拜或者說新的“文明”是用來“嘗試”的。無論是胡適的“再造”⑧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1(1919)。,還是李大釗的“第三”之“文明”,應該都是這樣一個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