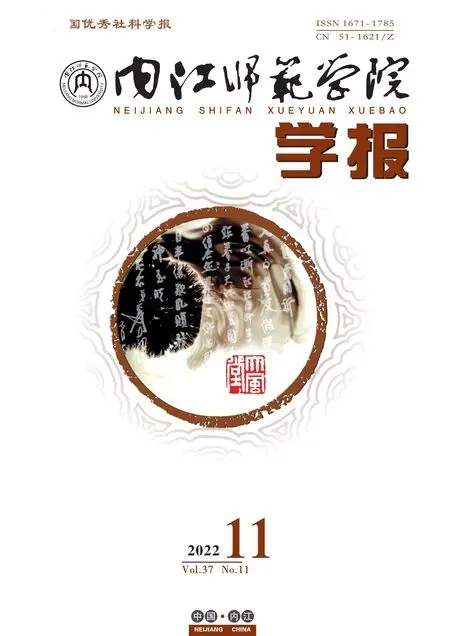论汉代国家正统性之构建历程
邹 国 力
(1.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2.内江师范学院 张大千美术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关于汉代国家正统性的研究成果颇丰,这对本文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梁启超在《论正统》中强调,中国历代史家都以王朝正统性为重要研究对象,可见中国人对于传统正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1]167可见梁启超对于王朝正统性首重血统的观点,所以很多学者基于此观点将研究目标集中到汉代这个由“布衣天子”所建立的王朝上来。梁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汉代帝王受命神话研究》中谈到:“学者们在吸收和引用各家的‘天命观’、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谶纬等观点基础上形成汉代的受命思想,并将其直接服务于汉代的王道政治以证明汉朝建立的合法性,同时也为帝王们带上了神圣的光环。”[2]这为汉代帝王披上了“神圣合法性”的外衣,特别是神化刘邦的出身及外形,从而将其塑造为“刘为尧后”的形象。杨念群在《汉代“正统论”溯源——从“灾异天谴论”到“符命授受说”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谈到:“西汉儒者正式提出‘正统论’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空间(大一统)、时间(五德终始循环论)和‘德性’的养成。”[3]李珊珊、吕晓青在《儒学与专制:汉政权正统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试图以儒学的思想来探讨汉政权正统性构建的历程。全文在探讨汉政权“正统性”之质疑后,从五行学说体系下的汉代正统建构、《春秋》之义下的汉代正统论、从汉政权正统论看儒学和专制这三方面来具体探讨汉代“正统论”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汉代正统性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4]。庞天佑在《秦汉正统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政治与史学的影响》一文中通过对秦汉正统思想的研究来说明“正统思想是中国古代衡量某一政权是否合法的政治思想,又是一种反思政权更替与历史演进的历史哲学思想。秦汉是正统思想形成时期。正统思想与秦汉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汉代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5]汪高鑫在《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一文中以“五德始终说”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说明“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此虽就史学正统方面而言,然而“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盛行于汉代,这对于汉代国家政权正统性的构建同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据。王瑰在《“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一文中,以刘备得到汉献帝“衣带诏”一生执着于兴复汉室为研究对象,说明刘备具“刘皇叔”宗室身份的“刘氏正统”条件,从而可以挑战以曹操为首的“中原正统”,这说明“刘氏正统”与“非刘不王”的正统思想经过两汉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思想根基,这也是刘备在汉代灭亡后得以建立蜀汉的有力思想武器。朱志昊在《“白马之盟”与汉初政制——以政治正当性为线索》一文中说:“各政治势力通过相互承认而达成共识订立了这一具有基础性的开国盟约,其核心在于通过分权共治来换取对汉帝国后世君主继续统治的认同与忠诚。‘白马之盟’展现了汉代早期皇权的正当性,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均势格局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功臣与诸侯王等政治集团的制约。”[7]由此可见,西汉开国者刘邦通过“白马之盟”正式确立了“刘氏正统”的地位。
综上,关于汉代国家正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不乏高质量的文章与专著,从中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汉代国家正统性问题的高度重视。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试图以某一具体方面来概括整个汉代国家正统性的构建,这样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还让研究显得单一与碎片化。因此,本文试图以整个汉代国家正统性的构建史为研究对象,将这些单一的碎片串联起来,试图呈现整个汉代关于国家正统性的构建历程。
一、“周秦之后无正统”——关于汉代国家正统性的质疑
(一)“奉天承运”——汉以前王朝正统性的固有思想
国家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成汤伐桀是膺受天命,文王“受大令”与武王伐商也是“顺天应民”。“天命”至无德者转移至有德者便成为新旧王朝交替的理论依据,这往往也是新王朝正统性确立的理论依据。“奉天承运”自古以来便深入到民众心中。“正统性”源自天命、血统、地理、德行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的汇聚需要艰难而漫长的历史积淀。譬如,秦国自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大一统为止,期间亦历经了600年的积淀。秦以前的各王朝,自虞夏至周秦,无不历长久之积淀,积善累功,德及百姓,方能建国。所以梁启超在论正统时才会说到“自周秦之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所以能得到人民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共同认可,才是国家正统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反观汉代开国者刘邦,一无血统,二无功德,三无积淀,凭一泗水亭长这样的基层小吏纵身成为一代帝王,诚可谓“布衣天子”,这样的“三无之人”也能成为皇帝当然饱受当时人们的质疑,进而其所建立的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性遭受质疑更是无可厚非。
以中原正统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司马迁就曾有感叹:“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8]759其中的“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即与“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8]759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从中可见司马迁也深受此王朝正统思想的影响。
(二)“高帝、吕太后威”——汉王朝国家正统性的质疑声
刘邦在成为天子前“好酒及色”。汉初功勋阶层中的丰沛集团有不少刘邦的酒肉发小。刘邦死后,吕后曾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8]392“北面为臣,此常怏怏”说明当时的勋贵阶层对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并未达到发自内心的认可,这也说明至刘邦逝世时,汉政权的正当性尚未完全确立。直到诸吕覆灭,陈、周二人迎立代王时。代王属下张武亦心怀疑虑:“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8]413这段材料说明,依张武看来汉政权的建立是依靠刘邦与吕后在秦末天下大乱之时的武功而骤然建立起来的。“故高帝时大将”也是因为“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所以张武认为此骤然依靠武功立国的政权在刘邦与吕后二人去世后就不稳固了。换言之,“刘氏正统”直至高帝、吕后去世时仍未完全确立,当时仍有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
从上述分析中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当时对汉代国家正统性的质疑是汉代国家正统性没有彻底深入人心的表现。面对这样的质疑,汉代的统治者不可能置若罔闻,况且就当时国人而言,“天命”“功德”“血统”“正统”“正当”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陈胜这等“瓮牖绳枢之子”造反时鼓舞士气的口号,这是为了打破当时人们心中“王侯有命”的传统思想。即便如此,在陈胜这些“氓隶之人”看来,“王侯有命”已经成为当时广大人民的思想共识,如若不然,又何必玩起“大楚兴,陈胜王”这样的把戏。所以,汉代统治者在面对当时“高帝、吕太后威”这样的质疑声时,不得不将国家正统性的构建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其始终伴随着整个汉代历史,且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二、“岂非天哉”——汉代国家正统性的理论依据
尽管当时人们对汉代的国家正统性存在质疑,但是汉王朝的建立,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匹夫为天子的新型政治共同体中,皇权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天子与其他政治势力之间的交互性承认,功臣、诸侯王承认天子‘功最高’,以换取天子对其军功及其相应的政治利益的认可,天子自身表现出‘德最厚’,以施惠之德换取功臣、诸侯王对其武功的承认。天子与功臣、诸侯王之间借助‘功’与‘德’达成的政治共识是‘匹夫天子’获取政治正当性的基础。”[7]所以,在汉代建国之初,统治者对其国家正统性的构建就显得迫切而必要。司马迁曾感叹“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8]760所以,“受命而帝”是汉代国家正统性最好的诠释。但是,刘邦作为一介布衣成为汉代开国皇帝,称帝之前不过一亭长,甚至“好酒及色”,血统亦无所考,祖上又无恩德于百姓。可以说刘邦不满足“受命而帝”的任何一个条件,所以将刘邦塑造成汉代“受命王”是构建其国家正统性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受命王”刘邦——刘氏正统的塑造
“受命王”是中国古代政权拥有国家正统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刘邦以亭长身份在秦末乱世中起兵,最终以武力立国。他的父亲叫刘公,母亲叫刘媪,都是连一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的普通人,更没有可追溯的功德先祖,可见刘邦没有血统优势。塑造刘邦这个“受命王”形象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汉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说,即所谓的“受命于天”与“王者必受命而后王”。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刘邦“受命王”形象的塑造从西汉初年开始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神化出生
“受命王”是天子,且一般都为开国天子,开国天子的出身自然卓尔不凡。关于刘邦的感生神话的塑造,《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8]341《汉书·高帝纪上》也有相应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9]1这显然是司马迁和班固为了论证刘邦以后成为帝王而塑造的感生神话。通过这两则神话的记载可以看到,刘邦是其母与蛟龙所生,即为“龙子”。“从秦朝开始,龙成为帝王的象征”[10]158这就为日后刘邦成为“受命王”提供了理论依据。班固《汉书》中还记载了“高帝斩白蛇”“东南有天子气”“吕公贵高祖”等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显然为汉代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
2.美化形貌
司马迁有言:“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8]342-343“隆准而龙颜”显然是司马迁将刘邦形貌的美化,因为其先前已经将刘邦塑造成刘媪与蛟龙所生的“龙子”形象,所以“龙子”自然有“龙颜”,只有具备这样的外貌才能异于其他凡夫俗子。所以接下来对其“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的描述也就显得恰如其分了。对刘邦形貌的美化是对其“受命王”形象塑造的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司马迁还为刘邦塑造功德,“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便是例证。
3.溯源血统
西汉末年,刘歆在《三统历谱·世经》构建了一套系统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其中“刘为尧后”便是这一学说宣扬的主旨思想之一。其后,班固在《汉书》中以“宣汉”为目的大力鼓吹“刘为尧后”。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从目的性而论,班固与刘歆的 ‘汉为尧后’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刘歆宣扬 ‘汉为尧后’说,是希望刘汉皇朝能像唐尧禅位于虞舜一样禅位于王莽,因而是服务于刘汉政权和平过渡到新莽政权的一种政治需要;而班固宣扬 ‘汉为尧后’说,则是有鉴于刘邦 ‘无土而王’,致使人们对于刘汉皇朝的建立感到困惑不解,从而需要从神意角度作出历史解说,以为刘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11]有学者认为“刘为尧后”说是为新莽代汉提供理论依据,然“刘为尧后”说也实为宣扬汉代国家正统性提供理论依据,并通过对刘氏血统的溯源或塑造使刘氏的血统具备高贵性与可考性,从而为刘邦“受命王”形象的塑造提供最后一个有利条件。
杨宽在《刘为尧后说探源》一文中明确指出:“新莽以刘氏为尧后,有传国之象,遂自居舜后以图篡窃。刘为尧后之说既为新莽篡窃之典据,而称刘为尧后者,《左传》独有明文,《左传》为刘歆所表章,后人因《左传》刘为尧后之说乃歆辈所伪窜,以媚莽助篡者。骤观之,其说似甚有理,细按之,知实诬枉也!”[12]221依杨氏的观点而言,“刘为尧后”在《左传》中就有迹可循,其认为刘氏来源于晋国士会逃亡秦国时留在秦国的一支(“留”与“刘”同音),而“刘累豢龙”亦有所本于祝融成龙之神话,非刘歆所伪窜,盖断断也![12]226可见“刘为尧后”实有所本,非后世所伪造,但是刘邦之“刘氏”就真是“尧后之刘”吗?若真为“尧后之刘”,以司马迁严谨的史学态度难道不会认真考究开国皇帝刘邦的世系吗?岂会言其父以“刘公”?此中显然可见刘邦世系难考,但凡有蛛丝马迹可寻,司马迁不会就此放过这样的宝贵材料,毕竟血统的高贵是刘邦成为“受命王”最重要的条件。
既然“刘为尧后”有所本,那么刘邦之“刘氏”就可以塑造成“尧后之刘”,甚至必须塑造为“尧后之刘”,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后世以“宣汉”为己任的班固身上。班固在《汉书·高帝纪赞》中考究出了一个明确的“汉绍尧运”的刘氏家族的世系来:“《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9]81-82可见班固将“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说得清楚明了,极力证明士会亡秦之一脉就是“汉帝本系”,所以班固的“刘为尧后”说是其鼓吹刘汉王朝国家正统性的有力理论依据。
至此,“刘为尧后”说自《左传》所本,到班固的成功塑造,再加上之前司马迁的铺垫,刘邦就顺理成章具备了成为“受命王”形象的全部要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刘邦的“受命王”形象终于被确立,而这一形象的塑造与确立是汉代国家正统性构建历程中应攻克的最大难关,可以说也是汉代国家正统性构建的核心,因此刘邦才会“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王充在《论衡》中说:“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于梦矣。”[13]195相比于刘邦这样“三无之人”的“怪奇”,而薄姬梦苍龙生文帝与王夫人梦日生武帝这样的“怪奇”与之相比,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正因为“刘邦”这样“怪奇”的“受命王”形象的成功塑造,其后继之君也理应正统无疑。
(二)“非刘不王”——刘氏正统的确立
刘邦以汉王身份与项羽争天下,从而建立了汉王朝,而建国之初的汉王朝并
不是天下一统的帝国。齐王(后改封楚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后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共八大异姓诸侯王林立。从秦末六国贵族的复国运动与汉初八大异姓诸侯王的分封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传统分封制的认可,而秦帝国在统一天下后骤然实行郡县制也势必会激起不小的社会动荡,这也是加速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刘邦吸取了这一教训,建国之初,为了社会稳定没有骤然实行郡县制。秦王朝由于诸多原因而快速亡国,那么汉王朝接过这个接力棒时势必也要实现“大一统”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要便是铲除这些手握兵权的异姓王。
楚王韩信先是被贬为淮阴侯,接着被吕后设计杀害;韩王信遭到猜忌,投降匈奴,后来被汉将柴武斩杀;彭越、英布、臧荼因谋反被杀掉;赵王张耳早逝,其子张敖承袭赵王爵位后却受牵连入狱,被降为列侯;卢绾叛乱,身死匈奴。可以说八位异姓王中只有长沙王得以幸免,其得以幸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长沙国地处偏远,其实力不足以威胁中央政权。其次是在刘邦剿灭英布的过程中,第二代长沙王吴臣“大义灭亲”坚决拥护朝廷。刘邦之所以要剿灭这些异姓王,一方面是要真正实现“定于一”的大一统,另一方面是要实现他心中“刘氏王天下”的目的,这也可以说是通过武力来构建汉代国家正统性的手段。韩信等七位异姓诸侯王在请汉王刘邦加皇帝号的上疏中提到:“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9]52尽管当时刘邦已经成为天下的共主,各方面势力也在表面上承认刘邦“天下共主”的身份,但是刘邦起于草莽间只用了约八年的时间就成为皇帝的事实,在其内心而言对这样的承认并不放心,今日承认,明日反叛,汉王朝国家正统的身份何在?只有“刘氏王天下”才能让刘邦真正放心,只有“刘氏天下”才能代表正统的汉王朝。
“在平灭英布、卢绾叛乱之后,诸侯王的同姓化改造大体完成,刘邦与功臣、诸侯刑白马盟誓。‘白马之盟’反映了汉初政治势力的博弈,既是对现有政治均势格局的确认,同时也是对未来政治发展的约束与限定,其目的在于通过和保障现有政治集团的利益,来换取功臣、诸侯王等对汉帝统治的支持。”[7]“白马之盟”于史书中虽未明确提及,但从后世频繁的引述中可见确有其事。《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高皇帝刑白马之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8]400《汉书·周亚夫传》中也有记载:“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9]2060-2061可见汉初“白马之盟”的核心内容“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对汉代后期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约束力。换言之,刘邦通过武力对汉初异姓诸侯王的铲除来强迫功臣、诸侯制定了“白马之盟”的祖训。
“白马之盟”就是通过盟誓的手段来换取各方势力对“刘氏天下”正统性的共同认可,如“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这是一条强制措施,因为刘邦以武力立国,他深知武力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即便后来有陆贾为其著《新语》来奠定汉代国家正统性的文治理论依据,以行“仁德”来营造天命依功德转汉的声势,但对汉代后期政治不放心的刘邦也同时需要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措施来巩固他辛苦创建的“刘氏天下”。特别是在吕后死后剪除诸吕的政治斗争中的“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祖训,就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甚至催生出“郦寄卖友”的故事,虽然卖友在当时被大多数人视为见利忘义之举,但是为了“刘氏天下”的正统性的确立,此举在当时看来也是大忠大孝之举,所以班固赞曰:“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9]2089可见“白马之盟”的强大约束力。
“白马之盟”通过强制的约束力迫使各方政治势力对“刘氏正统”的共同认可,“非刘不王,非功不侯”的祖训开始逐渐深入人心。“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9]364这样异姓诸侯王势力消逝殆尽,绝对的“刘氏正统”最终胜出。至此,“家正统”与“国正统”之间画上了完美的等号。
(三)“更始说”与“再受命说”——刘氏正统的挽救
汉代国势初衰于武帝末年,再衰于元帝之后。彼时的汉王朝急需一套继续巩固其国家正统性的理论依据。元帝之时,翼奉甚至上疏迁都于成周:“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已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亶居而改作,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畜。”[9]3176在翼奉看来,汉得天下,非积功德而王,乃是以武功征伐而德化未洽,后世经武帝穷兵黩武,特别是元帝时外戚、儒臣、宦官三大势力角逐,国力内损非常严重,所以必须迁都更始,延长汉祚,所以“更始说”源自翼奉。
继翼奉“更始说”之后,汉成帝时甘忠可则直言“再受命”。有学者认为 “汉德已衰,新受命天子将出”的普遍共识与皇室“汉运虽衰,天命未改”(如翼奉言)的观念而形成。也就是说新天子将出,而此天子依然是汉室。[14]317-318所以,汉成帝改元建始当是受此说影响。哀帝时,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又将“再受命”提上日程:“汉历中衰,更当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9]3192当时,哀帝因宠信男宠董贤而久病成疾,希望甘忠可的“再受命”说真能为其延年益寿,进而延续汉祚,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俱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9]3193但事与愿违,哀帝在“再受命”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后病体未愈,认为此说不合时宜,将夏贺良等入狱,尽除前令。
“更始说”与“再受命说”的目的是为了无限延长国祚。这与“五德始终”说形成了对抗,而此时的刘歆正在为王莽代汉创造理论依据,“更始说”与“再受命说”便与王莽的目的发生冲突,所以刘歆坚决抵制这两种学说。但无论是翼奉的“更始说”还是甘忠可、夏贺良的“再受命说”,对于彼时奄奄一息的汉王朝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此三人为了给衰落的刘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性提供理论依据,亦可谓煞费苦心。刘汉政权既然已经没落,仅从理论依据中去寻找救国的方法显然不可行,这是因为理论依据必须以现实政治为基础。翼奉、甘忠可、夏贺良作为衰落的刘汉王朝国家正统性的忠实捍卫者,可谓尽责,但也始终没能阻挡王莽先封“安汉公”,进而“假皇帝”,最后“真皇帝”的步伐。但这套学说在当时的社会中流行,为日后刘秀完成真正的“再受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莽末年,群雄并立。刘氏宗族后裔刘玄起兵,号更始将军,后被绿林军拥立为帝,建元更始。“更始”二字即为刘氏欲恢复刘汉王朝国家正统性的宣示。另一刘氏宗族后裔刘縯也打出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口号。此时的王莽虽然取得政权,然“刘氏正统”观经历200多年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所以“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口号就是为了遵循“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祖训”,最终致使历时15年的新莽政权昙花一现(新莽政权的灭亡因素之一)。刘縯遭设计杀害后,关中儒生强华向其弟刘秀献《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15]21四七之际是指自高祖至光武初,凡二百八十年,汉为火德。于是刘秀即皇帝位,同时又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刘歆著《世经》前后,汉为火德已是共识,所以刘秀还是以火德受命无疑就是“再受命”,随之而建立东汉政权,这样刘秀就完成了真正的“再受命”,“刘氏政权”又回到了刘氏宗族手中,从而又实现了“刘氏而王”,所以从新莽政权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又继承了西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性。
哀帝何以“再受命”不能成功,而刘秀完成“再受命”就理所当然?《后汉书·光武帝纪》中给出了答案:“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15]86这说明国家正统性的构建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做后盾,只有在此基础上那些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依据才能发挥作用。哀帝之时,外戚把权多年,王莽又以最初恭俭的形象营造日久,西汉末年的刘氏宗族已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为后盾,即便是用心良苦的“更始说”与“再受命说”也无法挽救这个形同枯槁的政权,只有另外的真命天子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破以往的政治形态才能完成真正的“更始再受命”,最终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光武帝刘秀身上。刘秀的“更始再受命”与东汉王朝的建立,可以说是汉代国家政权正统性构建的历史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挽救“刘氏正统”危机的历史转折点。
刘秀在完成真正的“再受命”后,还为东汉王朝国家正统性的构建迈出了更加重要的一步。刘秀在称帝后派遣大将冯异继续对赤眉军进行围剿,于是“丙午,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诏以属城门校尉。”[15]32然后诏曰:“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十余万众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15]33最后“二月己未,祠高庙,受传国玺。”[15]33从上述材料可见,刘秀在“祠高庙,受传国玺”之后才算真正恢复了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性。从上文分析可知,刘邦是汉王朝的开国“受命王”,而“受命王”是受天之命,非人力可为,而一个王朝只能有一个“受命王”,其后继之君直接承继先君,这样自然名正言顺。而刘秀不仅完成了“再受命”,而且还“奉高皇帝玺绶”,并“祠高庙,受传国玺”,这样一来刘秀就既再受天命,又受高帝之命,这无疑是给其所建立的东汉王朝上了一道国家正统性的双保险,并挽救了自元、成、哀三帝以来“刘氏正统”的危机。
三、“蜀汉王巴蜀”——汉代国家正统性的延续
(一)“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
从高帝“白马之盟”到刘秀“再受命”的“光武中兴”,刘汉王朝已将“家
正统”与“国正统”合二为一,“刘氏正统”就是“国家正统”的代名词。新莽末年,无论是绿林军所立的更始帝,还是赤眉军所立的刘盆子,以及刘演、刘秀等都是刘氏宗族后裔,可见“刘氏正统”观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深入人心。随着东汉王朝的建立,这样的正统性得到了延续。但东汉王朝经过“光武中兴”后,在中后期先是外戚干政,继而宦官弄权,最后党锢之祸,又重蹈了西汉王朝末年的覆辙,终于在灵帝时爆发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起义,民众掀起了对刘汉王朝正统性的挑战。
由于东汉末年国力衰退,朝廷无法对黄巾起义实行有力镇压,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不少地方武装势力在对黄巾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愈发壮大,最终形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随着曹操统一北方、位居丞相、受封魏王、迎帝许昌,最终“挟天子而令诸侯”,曹魏代刘汉已经势不可挡。
为了延续汉祚,一位起于民间的“草鞋皇帝”刘备就担起了这项延续汉代国家正统性的重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开篇就记载了刘备的世系:“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16]871可见刘备虽刘氏宗室后裔,但到了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只得“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刘备与高帝刘邦、光武帝刘秀都是起于乱世,凭借功勋而获得帝位。“草鞋皇帝”刘备相比其祖先“布衣天子”刘邦而言,具有血统上的优势。
与此同时,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的理论依据依然是振兴汉室:“绍遂以勃海起兵,将以诛卓。语在武纪。绍自号车骑将军,主盟,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遣使奉章诣虞,虞不敢受。”[16]190可见,在当时汉室衰微的情况下,“刘氏天下”的正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使得当时四世三公的袁绍也不敢公然僭越帝位。相反,“淮南帝称号”的袁术,就被天下割据武装势力群起而攻之,致使快速灭亡。在其欲称帝时,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16]209从中可以看出,阎象认为,首先袁术不及周之德,其次汉室不若纣之暴,隐晦地表达出汉室仍是正统的观念。可见,直至东汉末年汉室衰微之时,各方势力对“刘氏正统”观念依然具有共识。
(二)“刘氏正统”的余晖
刘备凭着血统优势与自身在东汉末年中的功绩创建了巴蜀、汉中的根据地。群臣在拥立刘备为汉中王时表于汉帝曰:“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16]885刘备同时上言汉帝曰:“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成臣忧责碎首之负。”[16]886可见刘备称汉中王是以“复兴汉室”为理论依据,甚至还不忘几百年前其祖先刘邦的“高祖龙兴,尊王子弟”。
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山之南,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16]889刘备以“社稷复存”为称帝理由,并将今日之曹魏比作昔日之新莽,而自己要担起像光武皇帝那样延续汉祚的重任,从而“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王瑰在其《“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魏、蜀、吴三国的国家正统性。魏国的正统来源于“中原正统(或言中国正统)”观的逐渐回归;蜀汉的正统性来源于“刘氏正统”观的继承;东吴的正统性最低,只得依靠武力一统天下后重新建立。由此可以看出,魏、蜀、吴三国的正统性对抗就只剩下了以曹魏为首的“中原正统”和以蜀汉为首的“刘氏正统(或言汉代正统的延续)”。二者都以正统自居,“中原正统”在于地理上的优势,而“刘氏正统”在于血统上的优势,所以它们都具有正统性的理论依据。曹魏在三国中实力最强,而蜀汉以“兴复汉室”为口号在西南立国也具备一定实力。如前文所分析,国家正统性的构建必须以政治实力做后盾,这才是“刘氏正统”与“中原正统”对抗的关键因素。所以在刘备之后诸葛亮才会倾全国之力北伐,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终身目标,就是要向世人宣布汉室犹存,有朝一日,蜀汉定会像光武帝那样挽救刘氏正统的危机,而蜀汉政权就是刘氏正统和汉代国家正统性的延续。但是,事与愿违,由于魏蜀两国国力悬殊,蜀汉最终没有实现“奖帅三军,北定中原”的目标。
蜀汉最终亡于曹魏,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刘氏正统”观也随即退出了历史舞台,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性也不复存在。但“不容忽视的是,蜀汉坚持到亡国前夕的北伐,由于持续时间之长与国力弱小的强烈对比,客观上对三国时代‘刘氏正统’的宣传起到了很大效果,对据中原而正统的流行观念则形成了巨大挑战,令之产生动摇。”[17]从中可见蜀汉政权的建立为汉王朝国家正统性的延续作出了贡献。
四、结论
汉王朝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布衣天子”刘邦所建立,在建国之初其国家正统
性遭到质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正统性为立国之根本,因此汉代国家正统性的构建就显得格外重要。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汉代的国家正统性构建始终伴随着整个汉代历史,建国之初,刘邦剪灭异姓诸侯王后通过“白马之盟”制定了“非刘不王,非功不侯”的祖训,这是一项用武力来胁迫各方势力对“刘氏正统”达成一致共识的政治措施,从而将“家正统”与“国正统”合二为一。与此同时,为了从理论上寻找依据,汉代学者们通过对刘邦“受命王”形象的塑造,从而让刘邦“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并提出“更始说”“再受命说”“三统三正说”“祥瑞灾异说”等一系列理论依据来共同构建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性。在长时间的构建过程中,“刘氏正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被社会所认可。随着东汉的灭亡,偏安西南的蜀汉政权始终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以“刘氏正统”来对抗曹魏的“中原正统”,从而实现了汉代国家正统性的延续。从中可见,关于汉代国家正统性构建历程的艰难,正因为汉代这样一个“匹夫天子”的新兴政权具备一套完备的关于国家正统性构建的理论体系,才为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国家正统性构建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