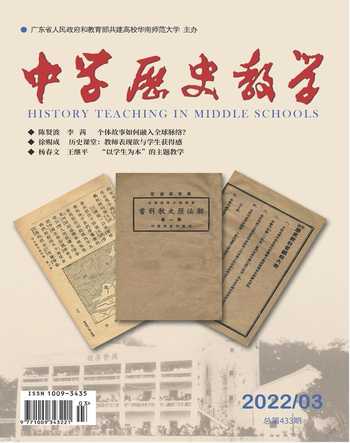个体故事如何融入全球脉络?
陈贤波 李茜
“短促的生活,只是出于偶然才有机会留在书本或文献中”,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年名作《无名者的生活》以此强调,研究者应努力开掘历史记载中的“卑微者”“无名者”以及“那些毫无荣耀可言的人”。[1]这样做,目的是破除精英话语对历史书写的垄断,在主流历史叙述中把淹没的潜流和低音安放进来,呈现更为丰富、鲜活的历史图像。毫无疑问,今天的研究者已经完全意识到,历史行动者既包括精英上层人物,更多的还是不计其数的无名之辈、普罗大众。问题是对于后者的故事,浅谈则易,深究却往往囿于史料而捉襟见肘。笔者近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青年学者韩洁西(Jessica Hanser)新著《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Mr. Smith Goes to China: Three Scots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s Global Empire)[2],以下简称《史密斯先生到中国》,深感其以18世纪中叶三个同名为“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的英国散商(private trader)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广州三地的活动为中心,将零碎的日志、信件、报刊、账簿档案条理成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从而揭示出全球贸易和大英帝国在亚洲扩张的历史细节和动态全景,有助于从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新视角丰富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学,故抛砖引玉,试做评述如下。
一、“毫不起眼的史密斯们”与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
1601年1月,东印度公司獲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特许授权,垄断好望角以东的贸易。3月,东印度公司船队首航东印度,至17世纪早期已经将贸易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获得在广州口岸的通商许可,并以此为中心从事跨国贸易。到了18世纪60年代,得益于对印度的殖民征服,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构建起庞大的亚洲贸易网络,香料、瓷器、茶叶、棉布、鸦片、白银等物品跨越重洋,源源不断地在东西方市场流通起来。[3]各地商人踏上东方之旅,竞逐财富,既有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特许垄断商人,也有蜂拥进入印度和中国经商的自由个体商人。在文献记载中,后者一般被笼称为“散商”(private trader),留下的记载零碎且分散。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下,过去我们对18世纪英国的亚洲殖民扩张和贸易,尤其东印度公司发挥的作用了解较多,问题是活跃在这个商业网络中大量的散商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商人、物品和资金如何缠结在一起,全球性的生意究竟是如何做成的呢?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讲述的三个名为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散商正是在上述剧烈变动的历史背景下从事亚洲贸易的。他们的主要经商地,分别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西海岸的孟买和中国广州,这三处港口城市连结成18世纪英国亚洲商业网络的关键节点。通过作者的钩沉,我们开始知道,以史密斯们为代表的散商和他们的代理人将英国的私人资本(白银)出借给印度的统治者和中国商人,建立起高风险、高息贷款的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由于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行商难以为日益增长的茶叶贸易提供足够资金,散商们筹集私人资本,并以高利率放贷给中国商人采购茶叶和其他商货,填补了这个资金缺口。另一方面,散商利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广州和伦敦的财库(treasury)系统和汇票工具,协助客户将私人财富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他们运输和管理其印度客户所投资或委托给他们的货物,将利润存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并拿到汇票。通常在一年之后其客户可从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财库兑现汇票。这个持续不断的间隔期同样为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巨额流动资金。据统计,仅1769至1792年间,散商向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存入28,817,076西班牙银元,同期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采购的茶叶成本是29,334,051银元。[4]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资金链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由散商的私人资本解决,说“史密斯们”支撑了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也丝毫不为过。
对一般读者而言,如果说“史密斯们”上述亚洲商业活动过于隐秘,那么他们密切联系伦敦政治高层的影响力则无疑更为显眼。作者指出,散商经常性地给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家如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提出政策建议,将他们在远东的商业需求和利益转化为国家的政治议程,其中就包括马德拉斯和广州的两位乔治·史密斯,最终促成了中英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早期交往——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我们已经熟知,英国赴华使团的既定目标是希望通过与清朝谈判,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搜集中国物品、国力的相关情报。不过,通过对当时档案文献的挖掘,《史密斯先生到中国》则揭示出,散商之所以强烈建议向中国派遣一个使团,另有更重要的动机和利益考量,即通过在中国开辟新的市场,“他们都试图抑制东印度公司的航运利益,并逐渐削弱其对亚洲贸易的垄断”[5],相反,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层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派遣官方使团,却千万百计地“使用小伎俩加以掣肘拖延”[6]。有意思的是,最终成行的马戛尔尼使团呈献给乾隆皇帝的赠礼——望远镜、行星仪、地球仪、英式瓷器、绸缎和枪,正是来自其中一位史密斯(马德拉斯)的建言献策。[7]
可以说,在主流历史叙述中“毫不起眼的史密斯们”绝非无足轻重的边缘人,他们是更广泛的历史行动者代表,直接影响着我们熟知的全球化和英国在亚洲扩张的重大历史进程。
二、全球微观史:视角与特色
按照作者韩洁西的说法,《史密斯先生到中国》“对马德拉斯、广州和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以及他们同类人的关注,使人的面貌得以呈现在一些本就复杂抽象的宏观过程之中”。她开篇就强调,本书的微观史方法有助于使“抽象的进程、历史和地理”变得鲜活起来,从“史密斯们”的角度来书写历史,可以讲述一个大英帝国在亚洲扩张的新故事。[8]这种关注个体的故事如何融入全球脉络的研究取向,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全球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新动向,一般称之为“全球微观史”。[9]
最广为人知的全球微观史早期经典,应属当代著名史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名作《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10]该书聚焦来自菲斯(Fez)的北非旅行家、外交官哈桑·瓦桑(al-Hasan al-Wazzan)在不同的地域、政治和文化中的经历遭遇,从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世界揭示出16世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接触、对话和冲突。与《史密斯先生到中国》最直接相关的中国研究,则可追溯至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欧阳泰(Tonio Andrade)的《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范岱克(Paul A. Van Dyke)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以及程美宝的新著《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11]这些精彩的个案研究,无一不关注个体(尤其是小人物)的全球性经历,或者个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调适应变,既细致入微又视野宏阔,极具可读性,显示出这一研究取向的独特魅力。
享誉世界的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这样定义“全球史”,他指出应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具有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广泛影响,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12]概括而言,与通常所见的全球史书写一样,全球微观史一方面重视物品、技术、人员和思想文化的跨界“联系”与“缠结”,重视它们得以流动的网络如何构建和运作起来的机制,另一方面也视“全球化”为“历史过程”,同时把“全球化”作为“研究视角”从而将具体的历史问题和现象置于更为宏阔的脉络之中加以考察。[13]不过,相形之下,全球微观史更关注如何从全球的视角书写个体(甚至某一个物件)的历史,具有如下3个鲜明特色:
第一,全球微观史的研究议题,集中在个体的全球性经历,特别是这些经历所反映的地方情景(地方性)和全球局势(全球性)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研究者青睐的研究对象,虽然往往是那些史书记载中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或者某一个具体物件的交换、流通,但通过他(它)们貌似不起眼的“迁徙”和“旅行”,却能牵扯万千,引导人们去洞察全球化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第二,全球微观史的书写方式,鼓励叙事史和微观深描的结合。由于研究者所开掘的主要史料是日记、信件、回忆录、游记、账簿和其它私人藏品等,相关著述更加强调“嵌入式阅读”,即把每个个案资料都置于其产生的历史情景中,往往于细微处见其深,识其远,更注重研究对象的思想、情感和生活。这种有血有肉的“讲故事”方式,是对历史学作为“人事之学”的原初叙事方式的回归[14],更能吸引普通读者,引发共鸣。
第三,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微观史的精彩个案往往更能展现全球史研究的路径,一种被全球史学者格里高利·库斯曼(Gregory T. Cushman)称为“跟随法”(following)的思维方式。后者的名作《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Guano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acific World:A Global Ecological History)正是“跟随”近代以来秘鲁地区鸟粪开采产业兴衰步伐,分析鸟粪开采与太平洋地区全球化进程,重新书写了近代全球环境史。[15]不难看到,由于研究对象更为聚焦和具象化,研究者关注个体历史的全球脉络,“跟随法”(following)无疑是最常用且恰如其分的研究路径。正因如此,韩洁西将散商史密斯们称为“引路人”,“通过追溯乔治·史密斯们在全球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不列颠商业帝国的运作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开展和加强的”。[16]
三、“史密斯们”启发我们什么?
结合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我們就不难发现,《史密斯先生到中国》讲述的故事,主要散见于《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四单元第14课《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第五单元第16课《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外历史纲要(下)》第六单元第12课《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相关内容是理解清朝中后期统治危机、西方列强对华贸易和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兴起绕不开的关键议题,既是教师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理解的难点。
仅从历史背景发掘和教学资源应用的角度而言,首先,《史密斯先生到中国》讲述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背景、筹备进程及动机和利益考量,有助于深化理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要求扩大对华贸易、开拓中国市场,以及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无法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大历史背景。
其次,以三位史密斯为代表的散商及其代理人利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广州和伦敦的财库系统和汇票工具建立起高风险、高息贷款的金融服务体系,解答了商人、物品和资金如何缠结在一起并最终促成全球性贸易的展开。明乎此,我们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解,就不再仅仅停留在逐利、剥削、血汗等空疏的词汇之上,而是真正开始触及商业经济运作的规律和机制。
最后,与孟买的史密斯直接相关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中所见中英法治程序差异以及英国对在华“治外法权”的持续谋求,又可帮助学生通过这起偶然性历史事件进一步认识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政治文化的鸿沟和冲突,进而对于理解后来西方列强诉诸武力扩张在华势力范围的渊源脉络与近代中国革命先驱对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不懈追求,同样也大有裨益。
进一步放宽视野,我们还认为,从《史密斯先生到中国》所引申出来的全球微观史研究取向出发,“史密斯们”的故事对历史教师时空思维能力的启发或许更值得一提。
诚然,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学科核心素养“时空观念”的表述所言,“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18],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事物”的发生(即历史事件)是一时一地接续发展的。不仅如此,我们往往出于书写叙述的便利,也强调历史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关系,但真实的历史则不尽然。历史事物不仅彼此交错盘结在一起,难以抽离简化,一时一地、一事一物也“全息”地包括一切变化一切事。正因如此,治史者“须能见其‘大,见其‘会通”,否则读史只见眼前事,“历史”徒成识记的条目纲要罢了。由此而论,讲述“史密斯们”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重新认识时间和空间的限度,它表达了全球史研究对历史事物“共时性”(synchronicity)、“关联性”(connectivity)的高度重视,也表达了如何将微观层面的个体故事融入宏观历史进程的全球脉络的洞见。我们相信,对于一线历史教师来说,充分意识到这样做势必将给自身历史思维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正是教学新探索的开始。
最后,作为本文的小结,以下这则小故事或许再合适不过:
1967年,当代著名的全球史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还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前往法国拜访年鉴学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并问道:“历史学者最有价值的特点是什么”,帕克猜想大师可能会说“勤奋”或者“语言”,然而布罗代尔的回答却是简单的一个词:“想象力”。[19]
【注释】
[1]米歇尔·福柯著,李猛译:《无名者的生活》,《社会理论论坛》1999年第6期。该文亦中译为《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收入米歇尔·福柯:《福柯文选Ⅰ·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9—320页。
[2]韩洁西(Jessica Hanser)著,史可鉴译:《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3]有关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和运营,参见羽田正著,毕世鸿、李秋艳译:《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4][5][6][7][8][16]韩洁西:《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第35、152、169、173、11—12、60页。
[9]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08—112页;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89—190页。
[10]娜塔莉·澤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著,周兵译:《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1]参见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陈信宏译:《胡若望的疑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欧阳泰(Tonio Andrade)著,王玫玫译:《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七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4—62页;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江滢河、黄超译:《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郭伟全译:《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程美宝:《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2]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新世界史》,周诚慧译,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13]王晴佳、张旭鹏:《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08—220页。
[14]此处所论“人事之学”,采用的是钱穆先生对历史的定义,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50页。
[15]Gregory T. Cushman, Guano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acific World:A Global Ecologic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页。
[18]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第60页。
[19]该故事参见欧阳泰:《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第62页。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享誉世界的全球史名作《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王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近期亦有中译本引入国内,同样值得品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