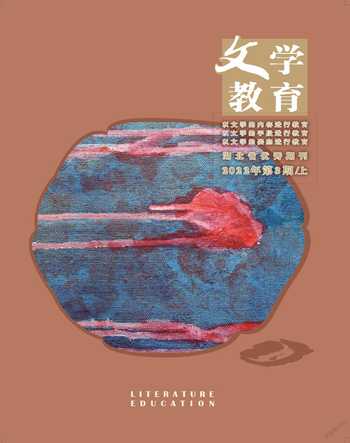村庄的肌理与体温
菡萏的《茵的村庄》是一组从不同角度来呈现当下村庄内在肌理与体温的作品,在“我”的观察中,村庄的自然风貌、家族的历史、个体的命运,共同构成了村庄的精神品格。具体说来,当我们重返乡村的历史,那些在时光深处的票据、账单,拼贴出村庄的经济学图谱,村民的日常生活隐藏在数字化的表述背后,不动声色。数字化是一种路径,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对于茵的父亲而言,会计的职业令他天然地对数字极度敏感,透过一系列的票据和凭证,父亲真实地记录著历史的细枝末节。在这一小节的结尾,作者写道:“曾经数字化的村庄,能否与现今重合?”数字化在村庄的延续与演变,以及其内在的经济学逻辑,无疑是值得读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房屋是村庄的“肉身”,一间间土坯房、长满荒草的小路、陈旧发黑的柜子、露着崭新白茬整齐的柴、面包形的小电视……这些构成了村庄的底色,村庄安静、质朴、天然的本性显露无疑。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村庄里,生活着老伯这样质朴无华的村民,一簸箕橘子传递出其大方热情好客的性格特点。坐在门前,日光下的老人心系儿女,却独自守护着寂静的村子,这是当下农村中较为常见的一幕。村庄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败,那些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纷纷去了城市,村子里变得空落,干瘪,宛如一具具被抽干水分的躯体。
“我是喜欢黑的,像纯粹的语言,忠诚于自己的唇角。”村庄的夜黑得透彻,黑得本分。90岁老伯的泥巴房,深夜里门口扩展出去的那束光,宣告了家和人的存在,有光亮的地方,就有家,就有人间烟火气,这是村庄残存的一丝丝生气和希望。尽管马路对面埋着茵的母亲,“我”和她对于黑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我是厌烦了城市凌乱的灯光污染,急于需求暗夜的补偿;而茵母亲的黑,是终日劳作,不见天日的黑。”“我”是在试图逃离城市的喧嚣,寻求精神上短暂的休憩之地,村庄是作为一种伊甸园式的精神家园的形态存在的。茵的母亲则是为了生存,寄居在村庄,慢慢地消耗与磨损自己,她与命运对抗着,和解着,费尽力气地生活着。对她而言,黑夜意味着一天的结束,同时意味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村庄因人而具有生机活力,母亲永远是村庄最为稳固的存在,在茵的母亲去世后,坟头的菊花勾起了她无尽的回忆,在那些成长的岁月中,母亲与土坯房是融为一体的,关于父辈,关于亲情,关于生死,都引起了茵的无限追忆与思索。“活在死人之上”,既是人类代谢延续之根本,也使得我们在面临亲人离去时多了一分坦然。
在村庄住了两天,离去时,老伯在路旁的一块荒地里种菜,这是颇为让人感伤的一幕,老伯的拐杖横在一遍,他抓黄鳝的镜头定格在“我”的眼前。在老伯看来,“一个人能终老在自己的老屋,是种福分,只要没瘫在床上;不能动时,儿女自当回来照顾,或接走”,老人的内心想法与现实处境让人平添了一丝伤感的意绪,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依恋和膜拜贯穿其一生。
在对村庄的书写中,“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进行的,跟随着茵回到她的村子,“我”看见了茵父亲的账本,也领略了村庄里的自然景观,并深入了解了茵对父母的真挚情感,以及茵的父亲的生存现状,这种观照方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我”是带着逃离都市拥挤的心态而来的,村庄是作为精神休憩地存在的。在作者近乎白描式的叙述中,村庄的自然景观与人文伦理得以呈现,作者的叙述冷静、客观,茵的村庄也在多方位的细节描写中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起来,不可否认,茵的村庄是当下中国乡村的一处缩影。饶有意味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乡村书写不同,作者笔下的村庄祛除了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色彩,而是透露出一种残败、干瘪、空虚的精神气质,这既是村庄面临的现实,也是村庄的宿命。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