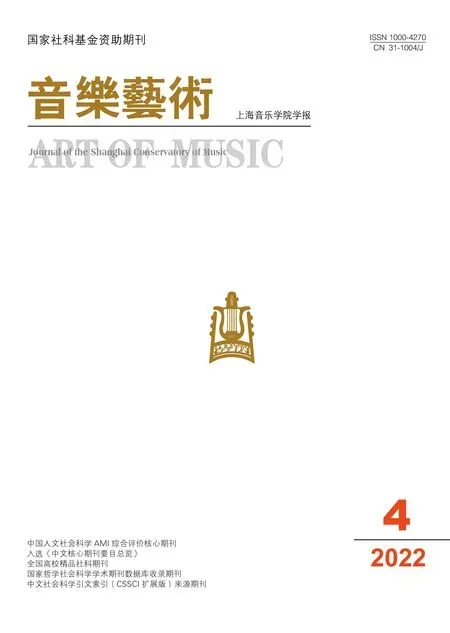生成与建构:中国传统音乐专业化教学思维寻绎
郭树荟
内容提要: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学科“专业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民间音乐专业化教育思想的重要转型。贺绿汀、沈知白等前辈学者所建构的学科体系,深刻体现了不同时期逐渐完善的民歌、器乐、曲艺、戏曲“民族音乐四大件”专业课程设置与理论成果,这不仅是学科高度认知的整体性布局,更有着丰富的学术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研室,于1953年8月以“民族音乐研究室”为名正式成立,由贺绿汀(1903—1999)院长最初提议创立并兼任第一任研究室主任。自此,民族音乐研究室开始逐步对各地民间歌曲、器乐、戏曲、曲艺音乐,进行了连续、集中的大规模实地考察、演出观摩、资料搜集及记谱分析,向民间学习存储民间资料,为编写学院民间音乐教材作储备。短短三年初创期间,为专业化教育奠定了学科最初的基石。1956年5月,民族音乐研究室并入民族音乐系,系主任为沈知白(1904—1968)先生。沈先生以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视野,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布局与人才培养方向。将前期向民间学习、实地考察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步投入教学实践。这期间,在贺绿汀院长、沈知白先生高瞻远瞩地引领下,逐渐完善了民歌、器乐、曲艺、戏曲“民族音乐四大件”的专业课程设置与理论构建,编著了《腔词关系研究》《曲艺音乐概论》《汉族民歌概论》《民族器乐概论》《西皮二黄音乐概论》《弹词音乐初探》等专题论著,以及相关系列教材并陆续出版。
向民间学习、实地考察、记谱整理、收集资料、分析研究、录音录像、书著文论、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创作表演、理论研究等,学科建设全方位铺陈开来。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建设,以及学院专业化教学、理论研究,历经多种探索,复杂的歌种、乐种、曲种、剧种面对当代社会文化的交汇、流变,一系列理论建树与教学研究体系进一步深度发展。回顾历史,贺绿汀、沈知白、黎英海、夏野、高厚永、韩洪夫、陈应时、江明惇、刘国杰、李民雄、连波、赵佳梓、罗传开、刘明澜、林友仁、王品素、胡靖舫、鞠秀芳、黄白、黄允箴、王璨、金建民等诸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先生们,为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全国的教学与研究树立了标杆。
一、贺绿汀创建的民间音乐专业化教育思想
贺绿汀“向民间音乐学习”的提出,是上海音乐学院传统音乐学科生成的重要基石,也是上海音乐学院长期办学方向的重要指南。贺绿汀一生的教育思想,深深打下了民间音乐的烙印,他记谱并保存了大量具有浓郁地域风格的民间音乐,这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深刻地融入他的个人创作。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之后,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意识成为贺绿汀治学、立学的教育理念,成为学院专业化学术创造的精神和方向,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还体现了中国音乐家强烈的中国文化创造的美学品格。巴托克说:“民歌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身为教育家、作曲家的贺老在中西音乐文化的大视野中,以专业研究启蒙了中国音乐创作的一个时代语汇。贺绿汀始终坚守向民间学习的文化信仰,身体力行,对民歌的学习从自己教唱到请民间艺术家进校园、要求师生们记谱学习,民歌课堂内外都成为学院教学的“规定性”课程。“民间性”的内在学术基本骨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表演、创作、理论研究在教学体系建设上的内核力量。历史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整体理论研究,以及创作上的丰硕成果,都与这个时段有着不可分割的学脉关联。
江湾时期的上音校园,贺老带领全院师生大唱民歌的场景,是老一辈上音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贺绿汀院长规定学生每天背唱数首民歌,还在百忙中亲临学生广播站为同学们教唱陕北民歌”①,今天想来,陕北民歌之所以在各地民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和学院教学有一定的关联。②著名歌唱家鞠秀芳③教授说:“1951年至1952年期间,贺院长亲自号召和带领全院师生唱民歌……常常让我到学院广播室去做示范演唱。”④吴国钧⑤教授回忆:“每次贺院长总带着一把板胡走进课堂,用他那带有湖南乡音的语调,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自拉自唱起来……当时他给全院每个系、每个班都上课。”⑥
从成立“民间音乐学习小组”到贺老亲自提议开设“民间音乐课”,其过程是实践与教学的自然衔接,渐进有序。全院各系师生之间互相促进、切磋探讨的集体学习机制与自觉学习意识,因“民歌”而产生的新的学习内容与教学方式,从不会唱到喜欢唱,从课上到课下,从教师到学生,从一把胡琴的伴奏到钢琴、小乐队伴奏。“民间音乐课”的开设,奠定了上海音乐学院民间音乐教学最初的传统。贺院长将自己在延安,以及家乡湖南、苏北、陕西、四川等地收集整理的多种体裁样式的民歌进行记谱并刻印出曲谱,作为教材在课堂上供学生们使用,⑦并指导学生选编了一套民间音乐资料,如《民间音乐研究》《内蒙民歌选》《郿鄠音乐研究》《打击乐》等。⑧贺老除了自己亲授,他还开辟了“第二音乐课堂”,并特别请民间艺术家到学校来上课、表演、传授各地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从北京、陕北等地将民间艺人请来担任学校的民间音乐课教师。这些被贺院长请来的民间艺人没有大套的理论,唯有鲜活的唱、奏。如何把他们随心入腔的即兴表演转换为高校专业教学,除了向他们学习,还要善于去分析、研究、发现民间艺术的规律。弹唱西河大鼓的民间艺人左玉成⑨、京韵大鼓的骆玉笙⑩,单弦牌子艺人王秀卿11、榆林小曲丁喜才12、胡琴艺人孙文明;陕北秦腔、郿鄠艺人黄忠信、任占魁,安徽泗州戏坠胡演奏艺人陈宝洪,河南坠子艺人赵玉凤、韩中东,昆剧名家俞振飞、沈传芷,弹词名家徐丽仙等诸多名家纷纷来校授课、讲座,在上音本科及附中阶段开设民间音乐课,经过记谱整理艺人们的名曲名段,留存至今,这些珍贵的资料还在继续使用。民间艺人的表演实践直观地在西方传统音乐教学体制中出现,作为其特性教学辅助手段与综合性实景课堂,使其成为“建设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最鲜活的、最直接的母语参照,民间音乐课不仅延续了民间音乐艺术在音乐学院中的传承生命力,而且成为音乐学院学生知识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走进校园的民间音乐,专业化的记谱、分析、研究更是重要的课题,既要保护尊重民间音乐自身生命力发展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规律,学院还要以系统化教育中枢的角色,担当专业音乐家的研究、教学和再创造。民间音乐课程纳入设置之后,师生与艺人、艺人与艺人之间相互接纳、接受,平行、并行的中国音乐传统,形成了中国音乐专业教育体系的模型创建和第一代师资骨干孵化的关键枢纽。师资培养是传承的核心,从学唱、记谱、理论研究,从教学课程布局到创作实践整体格局的创造性转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民间音乐整体学、教、研、创的黄金时期。民间艺术离开原有的生长土壤,以兼具表演与传教的新身份开启了另一种“传艺”的方式,这种“转型”浓缩了艺人们自身的经验技巧,以音乐院校的课堂为“开端”,融于具体教学之中,而如何“学”、如何转化民间艺术的资源,如何设置课程、怎样与音乐理论作曲及表演相结合等,这些问题在当年的具体实践中进行了有效的摸索。
“民间音乐课”似纽带链接了民间与学院,并深深注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专业教学体系与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最活跃的血液之中,在创作上,形成了民间与学院的正面交汇。著名作曲家汪立三13曾回忆当时作曲系师生每一、二周固定并持续开展的“新作品试唱(奏)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活跃场景,他创作的钢琴曲《蓝花花》就是其中一例。14饶余燕15老师晚年仍记忆到:“当时老院长贺绿汀一贯主张创作应取材于民间,特别强调以西北民间音乐为素材对学生们进行创作训练,还特别邀请陕西的民间艺人来学院表演,组织学生赴西北采风等,从此结下了‘西北缘’,形成了后来在创作技法上,将多元的复调手法和浓郁的西北民间音乐特色相融合的音乐特性。”上海音乐学院独树一帜的创作及学术氛围不断增长,形成了当时以理论作曲系为核心向全院各系辐射的整体态势。16
许多早期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歌唱家都在贺院长的引领与教导下,实现理论作曲与采风实践的双向结合。采用五线谱编选的《中国民歌选》(1953)到《中国民歌集》选编工作,“一律要用五线谱”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民歌集》在专业标准上的严格要求,即一方面用作理论作曲与分析研究的参本,另一方面通过改编、加工与和声编配使其更加完整,同时还能够通过音乐实践,将其编入教材使其进一步成为教学体系和音乐会中的表演曲目,这无疑对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创作、表演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后1955年出版《民歌独唱曲》17,黎英海先生根据内蒙古、四川、云南、新疆、山西等地及少数民族民歌编配成完整的独唱歌曲,如《槐花几时开》《小河淌水》《阿拉木汗》等,许多歌曲都成为歌唱家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和时代记忆中的音乐经典。随着对民歌的系统收集整理,再到乐曲的编创出版进而构建出中国歌曲的曲目体系,从散落于民间口头的曲调到音乐会舞台上完整呈现的独唱歌曲,实际上浓缩了民间音乐经过艺术化加工,再次以独立、完整的“音乐作品”形式,进行音乐表演舞台实践的转型脉络,并加深了理论研究与创作、表演在音乐作品“中国化”、民间音乐“艺术化”过程中的有机结合。在贺院长的精心筛选与指导下,由音教班班会成员集体组织编订了可供日后工作学习继续研究的六册民间音乐资料,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最早的民间音乐研究资料,成为学院专业化教学中的第一批重要的教学资源。自此,在近八年的时间段里(1949—1956)上海音乐学院民间音乐教学创编实践,初步形成了民族音乐创作、理论的早期格局,作业方式也由原来的集体研究作业逐渐转向个体教学、科研相结合的高校专业化教育模型。
二、沈知白学科建构与大学科布局的重要理念
贺绿汀对人才的选用高瞻远瞩,无论是对上音整体的学科布局,还是对民族音乐学科的未来发展,都运筹帷幄。1956年5月,上音成立民族音乐系,沈知白为系主任18,卫仲乐为系副主任,同时,沈知白先生还负责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室及民间音乐研究室的相关工作。贺院长对沈先生的重用,无论对上音整体学科布局还是对民族音乐学科的未来,都有着重要意义。沈知白先生博古中西、深谙古今,以宏观又精深细致的布局,为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民族音乐专业化教学体系勾勒了学科蓝图。沈知白先生早年学习钢琴、作曲,这是他西方音乐创作技术的实践阶段,也是他建立中西方音乐理论观念的形成时期,更是他全面认知中西音乐文化各自不同特色的重要历史节点。
沈知白先生的中国音乐观念的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已初见端倪,在当时的“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先生小型沙龙中,沈知白与卫仲乐、秦鹏章一起豪情满怀,开办多种以中国音乐为主题的演奏会,学习到许多中国音乐文化的真谛,几人研究古谱、学习昆曲曲牌、为《十面埋伏》演奏谱订谱,“调整过《十面埋伏》某些段落结构,使之精炼、集中,更富有艺术性”19。并成立了“中国音乐学学会”20,就中国音乐理论的探讨与具体的实践,既有传承亦有进步。在当时很多场合及音乐会讲解中,沈先生都谈到了中国乐器的历史,包括古琴、古筝、琵琶、二胡等,这些看似欣赏类的文化沙龙,却显示了沈先生的理论和高远的胸怀,尤其在论及中国古代音乐和典籍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时,沈知白先生从创作到史学研究,从作品具体分析到学科未来理想,他都是一位全能的践行者。当时的民族音乐系教师骨干以原民族音乐研究室为基底,除夏野、高厚永、韩洪夫等成员外,黎英海、胡靖舫分别调入作曲系与声乐系。沈知白先生与卫仲乐先生并肩在师资建设、古乐古谱整理、演奏指法规范、乐器改良等一系列专业领域的艺术活动和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相对稳定的学科发展规划。琵琶、古琴、二胡、笛箫、古筝、唢呐、三弦等乐器的演奏与教学,逐渐在教学中显现中国乐器表演从民间乐班、民间艺术家到学院教学,有了学院专业化转型。并引发了全校各个专业对中国乐器,以及作品的学习热情21,这个学科的初建再一次将沈先生、卫仲乐先生对民族音乐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向历史的高点。
对学习民族乐器的学生们,沈知白先生特别倡导“每个同学都至少要选修一件民族乐器”22。许多当年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都甚为感慨,著名古琴家成公亮回忆:“一般艺术家会三四种甚至更多一点民族乐器很常见,但通常只有一两门艺术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在那一代民乐家里,他的视野很宽,水准很高,艺术上很‘通’。”23对古乐器笙、竽、琴、瑟、笛、筚篥、民间胡琴、唢呐的形制、历史、变革都有大量的文献收集,并涉及古琴和琵琶的吟猱、胡琴和弦子的滑音,以及箫笛的种种花音演奏的音色音响音韵问题,24对经典的器乐曲目如弦索备考《十六板》、琵琶《十面埋伏》《青莲乐府》《飞花点翠》,琴曲《渔樵问答》《梅花三弄》《普庵咒》有音乐和意境的分析与解释。25民族音乐系建立初期的岁月中,民族器乐的专业由一个个独立的乐器,在精神与气质上更具有相合的中国做派,有古代音乐历史的依托,有民间艺术表演的学习体验,有西方音乐技法的新作尝试,更是在民族音乐的课程设置上与教材编写上,形成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综合发展的大格局,并相遇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的繁荣时代,成为20世纪民族化道路上的一条独特风景线。
沈知白先生的中国音乐观念和理论的思考,从民族音乐创作实践到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全盘布局,勾连了他将自己一生的学术主题放置在与中国音乐研究相关的多视角多学科的比较、求证、交叉的全方位视野中。他“最早提出‘民族音乐理论’这一术语,并把它用作一个独立学科专业名称。沈先生认为:‘民族音乐’的概念比‘民间音乐’要宽,还可以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士大夫音乐’‘文人音乐’等等,‘研究’只能指称一种行为,不适合作为一个专业或学术领域的名称,一个专业一个学术领域,不仅是指‘研究’这件事,它还包括一系列研究出来的成果,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体系,从而表达了最终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的意向。”26对大学科的横向交叉,沈知白先生有从文学诗词角度切入的古代音乐形态,从古典戏剧解析其中曲牌诗句韵律,以及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的音韵比较。“沈先生提出,民理专业要有文学基础和好的文笔,要补古典文学,看懂古典音乐文献,补充古典诗词素养。沈先生提名从文史馆调来龙榆生先生,开设古典文学课,讲《词曲概论》等专题。”27民族器乐理论的建设上,他指导高厚永撰写《民族器乐概论》、胡登跳撰写《民族管弦乐法》、陈应时撰写《琴律学》。20世纪40年代沈先生就有关于中国戏曲唱腔、伴奏、曲牌和板腔的研究,沈先生在文章中所涉及的曲种就有河南坠子、弹词开篇、北方大鼓、单弦牌子曲、宣卷、莲花落等。多重知识储备和音乐学术观念的形成,使他在东西方创作理念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上,有着清晰的认知,这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始终将理论放置在以创作、表演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之中的学科渊源。
江明惇先生回忆:“(沈先生)去‘瓦格纳音乐节’听瓦格纳歌剧,每次去听一部之前,他们把总谱进行非常详细的分析。”28 从音乐分析到关注作曲家自身特点,从钢琴音乐到歌剧音乐,技术性的学术含量是进入音乐理论研究的入口,更是西方音乐如何“中国化”转换的双重实践。沈先生还认为:“德彪西的一大贡献是面向东方。…… 一直到德彪西发现了东方以后,才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其实,德彪西所发现的东方是有限的。我们中国人才能真正理解、掌握中国的音乐、东方的音乐。发展中国音乐无疑将是对世界音乐的一个巨大的贡献。”29桑桐院长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沈知白时写道:“我在40年代中曾以南唐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一词写了一首独唱曲,其钢琴部分的和声即深受德彪西的影响。请沈知白先生阅后,他很赞成这种尝试,给了很多鼓励,并详细介绍德彪西的音乐与我国诗词、绘画、音乐等在某些意境、气质上的相似之处,使我得益匪浅。”30沈知白先生非常敏锐地提出中国音乐观念与世界对话、本土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的资源、西方和中国相遇的技术与文化层面的问题等,反观中国音乐的历史与情境,沈先生是冷静和坚守的。著名作曲家罗忠镕31先生回忆道:“沈先生的课大大地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陷,尤其是我们民族音乐方面的知识,可说那完全是沈先生灌输给我的。而且直到现在,我头脑中所保持的民族音乐发展的脉络和线索,还是那时从沈先生的课堂上得来的。……记得沈先生在课堂上就曾说过,研究中国音乐应尽量探求活的音乐,不应只停留一些史料的搜集和编排上,只满足于一些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的和数字的计算。”32由此可知,沈知白先生对史学的认知所建立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他对中国音乐的历史和现状的教学理念,影响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诸多作曲家们,他与贺绿汀、丁善德有共同的教育理念,培养年轻学子建构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理念,在今天看来,意义是重大的。著名复调教育家陈铭志先生在纪念文集中写道:“他指出,整理研究民族民间音乐,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改编、创作,赋予其新意,是作曲家们重要的任务。沈老常常谈到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说他由于亲自深入民间记录民歌,然后予以再创造,故而他的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个人的独创性。”33沈先生对民族音乐教育的理想,在当时作曲系师生举行的多种创作演奏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民族化创作最初的理论热潮从20世纪50年代的高峰时期延续至今,可以窥视到这种思想内在发展的轨迹,沈先生的教学与学术影响力沉淀着上音几代学者的传承,它不是一天两天生成的,是可以寻觅到的、代代相传的学术踪迹。
三、表演、理论、创作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
表演、创作为专业教育注入鲜活的养分,上音的“三足鼎立”模式将理论、创作、表演推进兴盛时期,显示了成熟的学科高度。高厚永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值得记住的历史瞬间,1956年底,上海市中等教育局号召所有中学音乐教师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于是邀请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老师为他们开设了五场讲座,其内容分别为中国音乐史、戏曲音乐、说唱音乐、中国民歌、民族乐器和乐队。34自此,民族音乐理论“四大件”体裁研究的模式成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史论结合的中国音乐研究大学科共同体。与此同时,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建设与“学科布局”出现新起点,在民歌教学与研究的同时,展开对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民族音乐理论“四大件”的稳定格局,并随着夏野、高厚永、胡靖舫、韩洪夫等人的采风记谱、资料整理、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作为主要教学师资与教学资料,在上音附中和大学部正式投入教学。这一时期投入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有:《中国民歌选》《单弦牌子曲》《山东大鼓(犁铧大鼓·胶东大鼓)》《山东琴书音乐》《戏曲音乐研究》《山东五音戏唱腔集》《山东吕剧唱腔集》等。同时,中国文艺理论、西方音乐理论、声乐演唱技术、民族器乐表演等,在尝试中逐渐被列入学习的课程。唱、奏、分析、创作、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渗透,民间音乐课、民间音乐小组、民间音乐研究室、民族音乐研究室的创立,在短短的几年中,使得民族音乐从感性到理性,从民间到学院,从创作到表演,从实地考察、汇演整理到理论研究,贺院长倡导的中国民间音乐思想逐渐形成了更具有体系化、专业化、学科分明的理想雏形。
民族音乐系各专业的教材从无到有,由贺院长、沈先生领衔,民族音乐理论教材有高厚永编写的《民间歌曲教学研究大纲》、夏野编写的《戏曲音乐研究教学大纲》,还有《说唱音乐研究教材大纲》。民族器乐专业由卫仲乐先生和陆修棠先生主持,每种乐器都以从浅到深的乐曲编排成册。1958年教研室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了师生很大关注,影响极大。江明惇先生说:“民歌研究中,老师教得很细致,那时候我提出的山歌音乐性表达的陈述关系时,分成唱词陈述的曲调成分和音乐抒咏的曲调成分,这些研究先生们很认可的,记得当时进一步补充了‘字密腔长’,这是十分重要的山歌音乐形态,与即兴性、直敞的表现这样一种音乐性格都是有紧密关联的。”35当时的戏曲培训班,是学校与院团紧密联系,选拔研究人才的平台,弹词越剧由连波先生挑起重任。除了教学,教研室老师分别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椐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了专业化的思考。如何将百年来的传统戏、地方戏融入现代戏唱腔中,如何将曲艺中旋律性音调与地方方言的音高特色进行改编创新,如何将具有程式性的板式变化与当代角色情感表达自如转换,这些既具有理论意义上的思考,又需要创作上技术语汇的实践操作,是传统戏曲向当代戏曲改良的重要转型。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强调保护、整理、研究、创作为一体,建立中国化的音乐教育高地,寻找其整体性、规律性特色,凸显中国旋律在声腔类研究中的“综合研究”理念,传统艺术的音乐形态技术化分析与创新,是当时民族化的热潮,也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工作,民间音乐的化合作用发生极大的效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催生,“其中既有低层次、类别性的民歌、曲艺、戏曲、民族器乐的各门‘中心教材’,又有高层次的专题性的‘综合研究’,由此有机联系形成一个整体。”36《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教材的出现,使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化研究形成新的高度、深度,既可以聚焦个案专题深入研究,又可以进行全面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使这一学术工程真正地建构了与西方不同的专业化“四大件”。教研室聚焦大综合、小综合研究与沈知白先生提出的两个“四大件”理念一致,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上又有着纵深的拓展。“民歌音乐研究”“民族器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曲艺音乐研究”形成了中国民族音乐在高校系统教学与学科研究的结构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上音成立民族音乐系,到在全院开设中国音乐史、民间音乐、东方音乐、西方音乐史等课程,以及成立了高等音乐院校最早的音乐编译室,贺绿汀院长、沈知白先生高瞻远瞩的学术布局,成就了中国音乐实践与理论的高度融合,出现了一批在民间与学院、理论与创作、教学与教材建设方面富有特色的系列成果,形成了现代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建设的成果,这是留给后辈丰厚的文化典范,更是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重要的历史贡献。向民间学习是学院教学、创作、表演的重心,表演与教学方面汇聚了卫仲乐、陆修棠、孙裕德、王巽之、王乙、金祖礼等著名的演奏家、教育家,同时也有叶栋、胡登跳、陈应时、江明惇、何占豪、夏飞云、李民雄、阎惠昌等民乐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
1979年,贺绿汀院长再次倡建并亲自指导“民间音乐抢救小组”的工作,委派江明惇先生担任组长,与黄白、陈应时、黄允箴、王璨、金建民等前辈学者,积极参与湖南民歌、云南民歌、杠棒号子、黄海渔号、莲花山花儿会、二人台弹唱、陕北说书、苏州弹词、苏南十番等民间音乐的抢救工作。1989年,多卷本《中国民族音乐大系》系列丛书《民族器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古代音乐》《歌舞音乐》的相继出版,续接与深化了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研究的学术传统。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建设,以及学院专业化教学、理论研究,历经多种探索,在复杂的歌种、乐种、曲种、剧种的交汇、流变中,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建树、研究体系、教材专著,为学界所瞩目。传承初创时期的教研理念,仍然以实地考察、记谱整理、收集资料、分析研究、录音录像、书著文论、教材编写为主,面对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中以院校学生传承的特点,进行学科整体布局与整合,面对不同时期的民间艺术的变异,民间艺术与民间艺术家进学院之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展示,而是经过学院再造的民间艺术获得了新的且可传承的生命力,这是专业化教育的根本,文化自身发展的艺术主体,不再是蜻蜓点水般走过场,而是把音乐作品、实地调研的资料转换成研究对象,转型为艺术化创作主体与民间艺术被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
20世纪下半叶,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在体裁、教材、教学上相对走向独立,即使民族作曲、民族器乐表演、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几经分合,当年留下的深深痕迹,民族器乐表演、理论、作曲、指挥、教学等多元一体的格局与思路,终在这所音乐学府的中国音乐血脉之中延续与流淌。先生们倡议的“两个四大件”提出,西方音乐四大件:和声、复调、配器、曲式与中国音乐四大件:民歌、民器、戏曲、曲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音乐研究的必修课程。这或许是音乐研究中核心技术的力量所在。1986年,上音将民族作曲合并到作曲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合并到音乐学系,黄允箴、王璨、郭树荟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力量随着本科教学传承及硕士、博士青年学者的相继加入,不断得到深入、充实。教研室老师们秉承几代大师的学脉与学术传统,使教学与研究展开了新的局面。随着《中国传统音乐摹唱与实践》《中国音乐美学》《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分析》《民歌与传播》《中国传统音乐与当代社会》《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宗教音乐与民俗》《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等课程的新设,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与当代社会》在2001年开设,距今已20余年,在学科意识上依然继承前辈的思想衣钵,聚焦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性及其变迁,观照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与民俗文化等特征,面对当代音乐创作中大量的传统音乐基因、元素的运用、借鉴,也更直面当下。当教学新生态、民间新生态已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早期个人研究、个案研究、少量学生学习,逐渐到课堂教学、体系化的建立,直至如今高校年轻学生成为学习传承传统音乐的重要群体。随着全院共同课、音乐学专业基础课、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增长,原有的少数、精英式的培养不能满足当下的教学生态,因此新课程、新编教材、研究视角逐步进入教学体系。《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中国传统音乐导学》《中国民歌与风土》《中国传统音乐》(上下)等出版37,学科建设与教研室在新时段发展中,以传承前辈学者奠定的中国音乐形态分析为基础,强化图文并茂的中国传统音乐再次启蒙教育的思想,实现2011年由教研室发起的首届九大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会议”分层推进高校各专业教学的愿景,成为推动学科相互交流的教学工作之一。
结语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学脉传承构建的传统音乐文化结构思维,不仅是专业化教育理论的中国化的最初模式,而且当时已经进行了跨学科学术范畴的深入实践。一代代学人教学思维、研究思维、创作思维伴随着历史的更迭,却终有不变的初心和守护。古往今来,从先秦时期的“采诗官”考察民风,采集于民间的诗和歌谣之时,到杨荫浏、曹安和记谱录音阿炳的《二泉映月》,几乎每个历史时段,都有着相似的学术情境。事实上,民俗、文化、语言与民间音乐的关系亲密,在学院传承的专业化研究教学体系中从未分离。20世纪匈牙利艺术家柯达伊访问上音,向师生们建议,每一首民歌的记录除了谱面还要细致记下演唱的相关情景、歌手身份、时间地点等,这些历史遗产的记录随着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的进入,日趋丰富、日渐成熟。从民间艺术的即兴表演现象而言,音乐形态研究依然是传统音乐专业化理论的技术核心之一,却从来都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摆在学科面前的传承链条在跨学科及多种学科进入和交叉时,时常出现学术次序的混杂,甚至萎缩,主体性研究被稀释,这个过程显现学科自身主体核心不够强大和稳固。在分离与融合的过程中,从历史的常识中认知传统音乐的学科特色,冷静选择和借鉴多学科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洛秦教授说:“我一直强调,音乐人类学根本不是学科,它的作用是开启人们进行不同视角,特别是对于音乐形态与现象原因的解释,一旦大家对此达成共识,音乐人类学就寿终正寝了,所以最实在的学问还是在于音乐史学与乐种形态的解释。”38由此想到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曾说:“鸟类专家只能从鸟的声音来辨别不同的鸟类,而音乐家是可以将鸟的声音记录下来变成音乐,这是鸟类专家做不到的。”39
前辈奠定的学科传统,在今天看来,应该是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所树立的现代中国音乐理论研究范式,构成了学院教学、学术对象、研究方法的学科重要标志。在上海音乐学院理论研究的核心力量上,创作、理论、表演的表层关系始终在中西方音乐相互融合中。民间艺术的滋养、西方技术的手段,生发出具有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两重交织的图景,只懂西方不懂中国和只懂中国不懂西方,那就很难出现像贺绿汀、沈知白这样的学者及一大批具有上音学统的教授先贤。向民间学习、模唱民歌及名曲名段、演奏、教学演示及创新作品等,成为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最为生动的传承途径。上音的民族化学术现象是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理论教学与研究更是架构了民族音乐的“中国化”教育体系,《牧童短笛》《梁祝》《民族管弦乐法》《汉族民歌概论》的乐音、文论历久弥新,不断回响,这种意味深长的传承和隐形作用是绵长、不息的。
注释:
①朱予:《贺院长尊师重教》,载王梅初主编:《音乐大师贺绿汀》,岳麓书社,1998,第171页。
② “当时老院长贺绿汀一贯主张创作应取材于民间,特别强调以西北民间音乐为素材对学生们进行创作训练,还特别邀请陕西的民间艺人来学院表演,组织学生赴西北采风等,从此结下了‘西北缘’,形成了后来在创作技法上,将多元的复调手法和浓郁的西北民间音乐特色相融合的音乐特性”,详见:饶红妹:《“未完成”的心愿(代序)》,载《饶余燕钢琴作品选》,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13。
③鞠秀芳(1934— ),1950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中国专业教学体系下培养的第一位民族声乐演唱家。专攻江南及各地民歌演唱,代表性演唱曲目:《五哥放羊》《挂红灯》《姑苏风光》《一根丝线牵过河》《杨柳青》等。
④ 鞠秀芳:《探索求新—我是怎样学习、整理、演唱民歌的》,载《音乐艺术》,1982年第4期,第22 — 28页。
⑤ 吴国钧(1927—2021),1950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1955年受贺院长之托,组织创办上海音乐学院附属音乐小学,先后担任附小副校长、校长之职长达37年。
⑥ 转引自上音附小校长吴国钧回忆“贺院长教我们学民歌”,踏迹寻音微信公众号,2022 — 01 — 11。
⑦ “贺院长特别重视民族音乐,而且重视的方法也很特别:他组织人力将各地的民歌、戏曲选编后油印成册,发给大家,不管你是哪个系的,不管你是什么专业,不管高班低班,不管教师学生,人人都必须熟背。”详见:苏澜深:《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汪立三先生访谈录》,载《钢琴艺术》,1998年第1期,第4 — 9页。
⑧ “他衣着朴素,神态亲切,夹着一把二胡,拿着一摞准备发给我们的油印歌篇走上讲台……后来贺院长因为工作繁重不能坚持来上课,音教班班会在贺院长的关心和指导下,选编了六本民间音乐,用油印办法分发,人手一份,包括《民间音乐研究》《内蒙民歌选》《郿鄠音乐研究》《打击乐》等等。”详见:俞玉姿:《在“纪念贺绿汀百年诞辰缅怀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载《上音校友通讯增刊》(一),2003年4月10日。
⑨ 董洪德:《我所接触的贺绿汀院长》,载王梅初主编:《音乐大师贺绿汀》,岳麓书社,1998,第168页。
⑩ “1949年11月30日,特邀著名京韵大鼓小彩舞来院演唱”,详见:常受宗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人民出版社,1997,第99页。
11 王秀卿(1909—1978),民间艺人,擅长多种北方鼓书艺术。1951年,贺绿汀院长在老舍先生的引荐下,将王秀卿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民间音乐教师,此后长期担任学院单弦牌子教唱、正音课及三弦等教学工作十数年。
12 丁喜才(1920—1994),民间艺人,擅长榆林小曲自弹自唱。1953年9月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后,被贺绿汀院长聘请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将榆林小曲作为全院各专业、年级必修的民间音乐课程,在校任教长达30余年。
13 汪立三(1933—2013),1956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代表作品《蓝花花》《东山魁夷画意》组曲、《他山集》等。
14 “贺老鼓励全院所有系科,不管是作曲系,所有师生要自创新作品,形式不拘。写出来后就要在新作品音乐会上演出,让大家自由讨论,相互交流”;“《蓝花花》这首曲子是以上学术环境的产物。因为我当时是一年级,刚学和声,还没有上作曲主课,是自己瞎写的。如果当时不提倡学民歌,不鼓励自由创作,这首曲子也就出不来了。”详见:苏澜深:《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汪立三先生访谈录》,载《钢琴艺术》,1998年第1期,第6页。
15 饶余燕(1933—2010),195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56—1958年抽调担任苏联作曲家阿尔扎马诺夫复调音乐班业务秘书,整理记录了《复调音乐讲座》讲稿。代表作品:民族管弦乐《音诗—骊山吟》、钢琴组曲《延安生活素描》等。
16 1951年6月“本院学生会主办民歌演唱会。作曲、声乐两系合编《联合系刊》,发表师生学习、研究、改编、创作、演唱民歌等方面的体会。全院形成学习民间音乐热潮。”详见:常受宗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人民出版社,1997,第108页。
17 黎英海(1927—2007),1952—1964年,黎英海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曾任院民族音乐研究室副主任、作曲系副主任。在院长贺绿汀的领导下,深入民间采集第一手资料,《民歌独唱曲》(新知识出版社,1955)是较早出版的学院民歌教材。他的代表书著《汉族调式及和声》是探索中国民族化和声发展极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18 沈知白(1904—1968),音乐理论家、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翻译家和作曲家。1946年起被受聘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在1950年国内最早的音乐学术研究机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研究室”“民族音乐研究室”中主持工作,建立民歌、器乐、曲艺、戏曲四种体裁的研究模式,为20世纪中叶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传承与理论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并入正式建立的民族音乐系,沈知白先生出任系主任。沈先生以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视野,奠定了中国音乐学科布局与人才培养方向。
19 江明惇:《辛勤的播种者》,载姜椿芳、赵佳梓主编:《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第407页。
20 赵佳梓:《沈知白先生传略》,载《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第324页。
21 “贺院长大力提倡西洋专业民族化,并规定教授西洋乐器的老师,每人必须学一件民族乐器,而选民族乐器者以二胡居多,所以陆修棠等二胡教师分外忙碌,这一来,二胡就再也不像狗叫,而学琵琶的难度以及琵琶乐曲的丰富表现力也使人赞叹。”参见:高厚永:《鉴往而知来—为民族音乐系成立五十周年而作》,载王建民主编:《乐苑凝香—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五十周年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2007,第41页。
22 俞抒(1957届作曲系),《坦荡率真的贺院长》,载贺元元、贺逸秋编选:《永远的怀念—人民音乐家贺绿汀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23 成公亮口述、严晓星执笔:《秋赖居琴话》,中华书局,2015,第187页。
24 沈知白:《和声在中国已往不能发展的原因》,载 《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
25 沈知白:《中国音乐、诗歌与和声》《怎样改革旧戏的音乐》,载 《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
26 沈洽:《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评介(1950—2000)》,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1期,第1—14页。
27 2018年笔者专访江明惇先生,上海音乐学院南楼219室。
28 同27。
29 同19,第414页。
30 桑桐:《借鉴与创新—记沈知白先生关于民族风格问题的一些看法》,载《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第371页。
31 罗忠镕(1924—2021),1944年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9年,师从丁善德教授学习对位法。代表作品:《第一交响曲“浣溪沙”》、交响合唱《沙家浜》、歌曲《涉江采芙蓉》、民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改编)等。
32 罗忠镕:《沈先生对我在作曲方面的指导》,载《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第373页。
33 陈铭志(1925—2009),1951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在复调音乐创作与教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曾协助沈知白先生整理古谱。1959年,在沈先生的启发下,陈铭志发表了《对我国民间音乐中复调因素的初步探讨》一文,沈先生看后给予很多鼓励,并提出了以上建议。详见:陈铭志:《沈先生是如何指导我学习中外音乐的》,载《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第380页。
34 高厚永:《鉴往而知来—为民族音乐系成立五十周年而作》,载王建民主编:《乐苑凝香—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五十周年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2007,第41页。
35 同27。
36 戴嘉枋:《走向毁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第106 — 120页。
37 该教材为《中国传统音乐》(上下),郭树荟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出版,2021年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首届精品教材奖。
38 2022年6月与洛秦先生的微信对话。
39 摘自纪录片《作曲家梅西安的音乐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