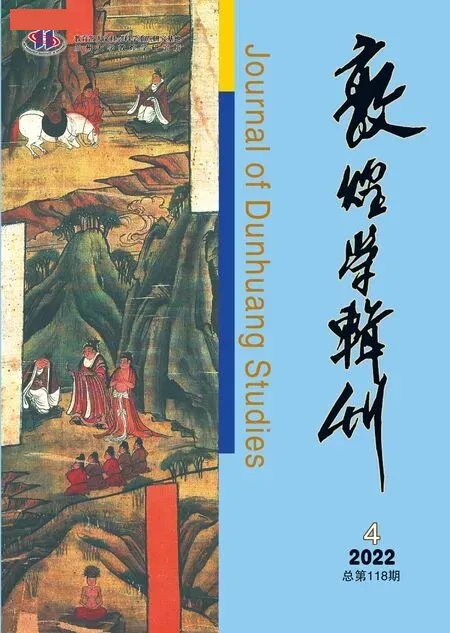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组像考释
许 栋 刘继玲
(1.太原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1;2.太原师范学院 艺术理论研究中心,山西 晋中 030619)
长治观音堂位于长治市西郊梁家庄村东,该观音堂虽然规模不大,但因其正殿内悬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日前,笔者一行在对该殿进行考察时,发现殿内十八罗汉组像中,一大肚罗汉像的造型及组合形式皆较为罕见,而其题材却一直为学者们所“误读”,故本文中我们拟对该组造像的内容、题材等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 造像概况
长治观音堂正殿坐东朝西,面阔三间,殿内正壁(东壁)前的佛坛上塑三大士像,主尊观音菩萨右腿曲倚、左腿下垂,游戏坐于犼背上的莲座之上,左侧文殊菩萨右腿盘屈、左腿下垂,游戏坐于狮背上的莲座上,右侧普贤菩萨左腿盘屈、右腿下垂,游戏坐于莲座上,坐骑白象卧于座前,三大士身后的墙壁上满塑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南、北两壁亦皆布满彩塑,这些彩塑大致可分四层,第一层塑十八罗汉像,第二层塑二十四诸天像,第三层塑十二圆觉菩萨像,“第四层北壁塑孔子七十二贤人,南壁塑玉皇大帝、西王母、八仙庆寿等”(1)魏小杰《长治观音堂明代彩塑相关问题的研究》,《荣宝斋》2012年第12期,第46页。。虽然两壁塑像数量较多,但这些塑像,布局合理、主次分明,排列有序,与正壁彩塑一起营造了一种佛教、道教、儒家三教合一的宗教信仰空间。

图1 长治观音堂南壁罗汉像

图2 大肚罗汉组像(采自长治博物馆编《长治观音堂明代彩塑》,第22页)
本文中所讨论的大肚罗汉组像位于观音殿内南壁第一层所塑九尊罗汉(图1)中由东向西数的第二尊(图2),右侧为睡罗汉,左侧为讲经罗汉。其中,主尊大肚罗汉,光头,面相丰圆,满脸堆笑,双耳垂肩,身着大衣,右侧衣襟经腹部下方后向上搭于左肩上,袒胸露腹,右臂搭于右侧胁侍肩上,左臂隐于门内;左侧胁侍面向大肚罗汉以七分侧面的姿势立于罗汉身侧,头梳双髻,为童子状,面相与主尊相似,戴耳珰,身着红色交领右衽绸袍,左臂垂于身侧,右手握长柄月牙铲,铲头内凹呈弯月形,铲尾为其他彩塑所遮挡,形制不清。右侧胁侍搀扶大肚罗汉,头梳双髻,亦为童子状,面容亦与主尊相似,戴耳珰,左臂隐于大肚罗汉背后,右手搭在大肚罗汉手臂之上,身着交领右衽绸袍,与大肚罗汉一起做进门状。这组造像置于一个半开状街门的背景之中,人物皆满面堆笑,而且位置安排一致,整个画面表现出一种对称性与均衡感。
二 、大肚罗汉为“弥勒罗汉”或“看门罗汉”像献疑
长治观音堂中的大肚罗汉因为造型与大肚弥勒相似,所以现有研究成果中一般称其为“弥勒罗汉”,又因其“刚从一门中走出,童子为他扛着禅杖”,故也被称为“看门罗汉。”(2)长治博物馆编《长治观音堂明代彩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3页。而这两种称谓是否与此造像的题材相吻合?这是本节中我们探讨的重点。
(一)大肚罗汉与弥勒罗汉的关系
笔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弥勒罗汉”一词似乎仅见于涉及到长治观音堂的相关论著中,在繁峙公主寺、阳高云林寺、平遥双林寺现存罗汉组像中,此类大腹便便、笑容可掬的造像一般被称为“布袋罗汉”。虽然有学者称布袋罗汉就是唐玄奘所译的《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及北宋天竺沙门阇那多迦所译的《十六大阿罗汉因果识见颂》中的“因揭陀尊者”,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布袋罗汉的形象与唐玄奘及阇那多迦译经中关于“因揭陀尊者”的记载无关,而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中所描述的布袋和尚契此密切相关。据《宋高僧传·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中记载:“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鄽肆……号为长汀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于大桥上立,或问‘和尚在此何为?’曰:‘我在此觅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则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以天复中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3)[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1《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3页。而《景德传灯录》《鸡肋编》中提及契此和尚时,所述内容均与上述引文相似。虽然此后契此和尚经历过一次由“形裁腲脮,蹙頞皤腹”向“大腹便便”“笑口常开”形象的转变,但其随身携带的“布袋”或“布囊”,一直是辨识该和尚身份的重要标识。而长治观音堂中被认为是“弥勒罗汉”的大肚罗汉造像虽然与常见的布袋和尚契此的形象十分相似,但是其手中布袋或布囊的缺失,以及二世俗形象胁侍的出现,都使我们对该造像为“弥勒罗汉”的身份存疑。
(二)大肚罗汉与看门罗汉的关系
看门罗汉又称注荼半讬迦尊者,可能是因为在玄奘所译的《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中有关于该罗汉与“自眷属千六百罗汉,多分住在持轴山中”的记载,所以我国民间根据“持轴”一词演化出了该罗汉去化缘时,曾因敲门击垮他人房屋、被佛祖赐予锡杖的故事,而“锡杖”也就成为识别看门罗汉的重要标识。从现存的阳高云林寺、长清灵岩寺、杭州孔庙碑林中的十六罗汉碑刻等彩塑、石窟、壁画、纸本绘画中的相关图像来看,除手持锡杖外,看门罗汉多为老者形象、且多以坐姿示人。而长治观音堂中的大肚罗汉像虽然被塑造成一种“刚从一门中走出,童子为他扛着禅杖”的形象,但是对照现存于其它地方的“看门罗汉”图像来看,二者形象及背景图像之间差异很大,所以仅凭一处大门或一根“禅杖”就将长治观音堂中大肚罗汉的题材判定为“看门罗汉”的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造像题材的释读存在着较多的误区,亟待重新剖析与修正。
三、大肚罗汉组像身份的重新认识
上述两种对大肚罗汉造像题材的判断之所以会出现失误,很大程度上与学者们在研究中,仅凭该造像中的某一特征对该造像进行题材判定有着密切关系。笔者以为,对佛教造像题材进行辨识时,应尽量对造像的整体进行把握,力图准确判断造像的身份。就长治观音堂中的大肚罗汉而言,我们在判定其身份时,不仅要考虑到其主尊为大腹便便僧人形象的特点,而且还要将其置于两胁侍中间进行讨论。因为目前学界对这铺造像主尊的特点已有较多的关注,故此处我们拟将主尊身份的问题暂时搁置,首先讨论二胁侍的身份,并以此为突破点,从而对整铺造像的题材进行探讨。
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造像中的二胁侍,虽然头束双髻、面带微笑做童子状,但是其面容却与常见的、面带稚气童子图像不同,而是表现出一种成人的样貌,梳理目前已刊布的古代佛教人物图像时,我们发现此种情形常见于寒山、拾得的图像中,如明代刘俊、张宏所绘的《寒山拾得》图中的寒山、拾得,清代黄山寿、丁元公所绘的《和合二仙》图中由寒山、拾得演化而成的和合二仙的形象皆与其类似。寒山、拾得与布袋和尚契此一样,均是中国佛教神异僧中的典型代表。关于二者较为详细的生平事迹,最早见于题为闾丘胤所作的《寒山子诗集序》,《序》中称:“详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疯狂之士。隐居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每于兹地时还国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寻常收贮余残菜滓于竹筒内。寒山若来,即负而去。或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时僧遂捉骂打趁,乃驻立抚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4)项楚《寒山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页。据崔小敬、罗时进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知,寒山、拾得的形象经过佛教徒一系列“改头换面孔”的操作,逐渐被禅宗接受,成为禅宗谱系中的一对应化圣贤。寒山、拾得图像中所表现出的禅意也越来越浓厚了,“笑”逐渐成为二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特征。所以如果我们将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组像中的二胁侍图像,置于上述图像及文字资料所设置语境中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这铺造像组合中二胁侍的身份,可能与寒山与拾得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其形象也可能是受到了元、明时期流行的寒山、拾得图像样式的影响。
为了能够进一步确定这铺造像的题材,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线索进行探讨。在梳理涉及寒山、拾得记载或内容的《寒山子诗序》《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及《四睡图》《寒山拾得丰干图》等文献、图像资料时,笔者发现这些资料中除了关于寒山、拾得的记载及图像之外,丰干也是这些文字或图像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如闾丘胤的《寒山子诗集序》中,虽然以记述寒山的事迹为主,兼及拾得的事迹,但是整个故事却是以丰干遇闾丘胤为契机而展开的。而在《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料的相关记载中,丰干的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他不仅被赋予了拾得的“养父”的身份,而且还曾与寒山、拾得展开过一些充满禅机的问答,三者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此外,由于他们皆与天台山国清寺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所以佛教史料中又将三者合称“天台三圣”或“国清三隐”。虽然现存的寒山、拾得图像中较为常见的是只表现寒山、拾得组合的图像,但是在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诸如《四睡图》《寒山拾得封干图》的“三圣”或“三隐”图像系统,在这类图像中丰干的图像不仅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元素,还经常被置于图像中心的位置,是整幅图像构图的关键。而且丰干的形象与寒山、拾得一样,也曾经历过一个“改头换面孔”的演变过程,图像的样式由枯瘦老僧转变为鼓腹大笑的大肚僧人形象(5)孟丽《明代伴虎大肚神僧组像考释——兼论佛教信仰实践中的形象转用与母体演化》,《文艺研究》2020年第2期,第141页。,如从南宋法常所绘的《寒山拾得丰干图》到默庵灵渊所绘的《四睡图》中丰干形象的变化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表现,长治观音堂中的大肚罗汉像也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综合上述的图像及文字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出长治观音堂中大肚罗汉像的身份应该就是丰干。行文至此,我们再将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与二胁侍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对该组造像的身份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这组造像属于“天台三圣”或“国清三隐”图像系统,中间的大肚罗汉为丰干造像,左右两侧的胁侍分别为寒山、拾得造像。

图3 禅宗三奇僧(采自孟丽《明代伴虎大肚神异僧组像考释》,第145页)
这组造像的组合形式与常见的三尊像有着较大的差异,而似乎与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图书馆的、绘制于15世纪的《团形三诗僧图》(图3)中所展示的团形构图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关系。虽然长治观音堂中的“国清三隐”造像组合并没有像《团形三诗僧图》一样形成一种完整的“团形”,但是二者之间在构图形式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仔细比较长治观音堂中的“国清三隐”造像组合与《团形三诗僧》图像,我们会发现二者的内容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两组造像中丰干与寒山、拾得面部的关系都较为特殊,如果我们将两组造像中寒山、拾得的侧脸拼接在一起,正好就可以组成各自图像中丰干的正脸,可以达到一种合三人以为一的效果,此种情形也与明宪宗朱见深所绘的《一团和气图》中的人物面部的构成方式极其相似。由此可见,长治观音堂中的“国清三隐”、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图书馆的《团形三诗僧图》,以及明宪宗朱见深的《一团和气图》三幅图像的构图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大致来说皆属于团形构图的范畴。
四、造像组合的内涵及功能
虽然现存的“国清三隐”造像组合主要集中于纸本绘画中,但是同时代的彩塑或金铜造像中也有部分此类造像留存,如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上寺弥陀殿中扇面墙背后所塑的丰干、寒山、拾得三尊像,以及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怀柔县博物馆中所保存的金铜佛像皆是类似题材的造像(6)孟丽《明代伴虎大肚神僧组像考释——兼论佛教信仰实践中的形象转用与母体演化》,第138页。,由此可见“国清三隐”图像涉及到多种造像材质,是一种自成系统的佛教造像体系。我们知道每一种佛教造像题材的形成、发展皆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及演变过程,就上述图像体系而言,虽然该图像体系的形成没有佛教经典的依据,但是闾丘胤的《寒山子诗序》《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文献资料中的关于寒山、拾得、丰干的相关记载是此类图像形成、演变的基础。在闾丘胤的《寒山子诗序》中称,丰干禅师对闾丘胤说:“寒山文殊,遁迹国清;拾得普贤,状如贫子,又似疯狂,或去或来,在国清寺库院走使,厨中著火……二人连声呵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唤,乃云:‘丰干饶舌,饶舌弥陀,不识礼我何为?’”(7)项楚《寒山诗注》,第2页。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天台三圣”或“国清三隐”造像其实质就是阿弥陀佛、文殊、普贤三尊像。现存的关于这三尊像神格的说明,最早见于日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该书卷一提及国清寺“三贤院”时称:“三贤者,丰干禅师、拾得菩萨、寒山菩萨,弥陀、普贤、文殊化现。禅师傍有虎,二大士是俗形也。”(8)白化文、李鼎霞校点《参天台五台山记》,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5页。书中明确指出了丰干、寒山、拾得三者的身份是“弥陀、普贤、文殊”在人间的化现。
三尊像是佛教造像中常见的一种造像组合,从其题材来看一般有“释迦三尊”“华严三圣”“西方三圣”“药师三尊”“弥勒三尊”“三大士”等等。但是阿弥陀佛的胁侍一般来说是观音、大势至二菩萨,而文殊、普贤则经常作为卢舍那佛的胁侍出现,所以阿弥陀佛、文殊、普贤组合是一种综合了“西方三圣”与“华严三圣”中的内容而形成的一种“结合型三圣”(9)释见脉(黄淑君)《佛教三圣信仰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8页。。这种组合形式的主尊是西方三圣中的阿弥陀佛,二胁侍分别为华严三圣中的文殊、普贤二菩萨。其出现的背景则既与相关的佛教义理有关,也与晚唐五代时期阿弥陀信仰、文殊、普贤信仰的流行,及其宋代出现的净土宗、华严宗二宗合流的趋势有关。如果我们将闾丘胤的《寒山子诗序》置于阿弥陀佛信仰与文殊、普贤信仰在天台山传播、发展的相关背景中,再去梳理该《诗序》中所叙述的丰干、寒山、拾得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天台三圣”或“国清三隐”造像形成,可能与阿弥陀佛信仰及文殊、普贤信仰在天台山中流行的先后次序有关,阿弥陀佛信仰在我国流传的时间较早,而且天台宗人接受阿弥陀佛的时间较早,所以相关叙事中阿弥陀佛的化身丰干出现于天台山国清寺的时间,要早于文殊、普贤菩萨的化身——寒山、拾得,并在故事中一直承担着一种向他人宣扬文殊、普贤化现于天台山的作用;与阿弥陀佛信仰相比,文殊、普贤信仰不仅在我国形成的时间较晚,而且传入天台山的时间也远远晚于阿弥陀佛信仰,所以被附会为文殊、普贤化身的寒山、拾得,在相关故事中是由丰干介绍给闾丘胤的。正是由于这几种佛教的佛、菩萨信仰在天台山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再加上三者中阿弥陀佛在中国佛教界中的最为崇高地位,所以故事中丰干不仅被塑造成拾得的养父,而且也被赋予了寒山、拾得的师长的地位。由此可知,“国清三隐”或“天台三圣”故事的形成,不仅与丰干、寒山、拾得的神异事迹相关,更是阿弥陀佛、文殊、普贤信仰中国化、民间化的一种反映,其中不仅强调了文殊智、普贤行在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更是突出了简单、易行的阿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国佛教中的作用,而且三者以神异僧的形象出现也较原有的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在民众中更有亲和力,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亲近及接受,也与我国佛教逐渐世俗化的趋势相符合。所以在元、明、清时期的寺院中,既可以见到“国清三隐”或“天台三圣”以常见的三尊像的形式排列于山西洪洞广胜寺上寺弥陀殿中扇面墙背后的情形,也出现了像长治观音堂这样、以团形构图的方式被置于十八罗汉中的情形。
罗汉又名阿罗汉,在我国一般意指佛教中声闻乘修行最高境界的“阿罗汉果位”,是声闻四果中的极果(10)陈清香《罗汉图像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第3页。,故其多以比丘的形象出现了中国佛教绘画中。虽然罗汉在我国早期佛教中只是一种出家人修证的果位,但是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期已演变成承佛法敕,常住世间,显扬佛法,化度众生的圣僧,被赋予与大乘菩萨相似的性格。而且罗汉的数量也经历了一个由四大罗汉到十六罗汉,再到十八罗汉乃至五百罗汉的发展过程。其中四大罗汉及十六罗汉皆有诸如《法住记》之类的佛教经典的依据,但是其后出现的十八罗汉及五百罗汉,不论名称及来源,皆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本身没有经典文本支持,加之唐宋变革以来知识下移难以在非官方注目的信仰层面获得权威认证”(11)王鹤琴、方圆《中国罗汉信仰的域外起源及本土再造——以十六、十八罗汉的生成路径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48页。。故而罗汉的名单一直不能固定下来,即使有经典依据的十六罗汉,在我国民间也出现了多种传说故事、汉化的名称及形象,这些名称及形象虽然不一定为佛教界所接纳,但是在民间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相对于佛教中的其它信仰体系而言,“汉地的罗汉则在名号与形象之间缺少对应关系,创作者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或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灵感来源。”(12)王鹤琴、方圆《中国罗汉信仰的域外起源及本土再造——以十六、十八罗汉的生成路径为中心》,第48页。而且,明清之际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这种情形变的更加普遍。所以虽然我们目前已难以确知长治观音堂被置于的十八罗汉组像中的“国清三隐”造像,取代布袋和尚或注荼半讬迦尊者(看门罗汉)成为十八罗汉造像组合中的新的一员的具体过程。但是此种变化应该与当时长治地区的社会及信仰背景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从长治观音堂现存的《创建观音堂宝殿记》等明代碑刻中的记载可知,该观音堂建造于明万历十年(1582)。据明、清时期长治地区的地方文献记载,当时的该地区有着浓厚的商业活动氛围,地方史料中关于当地人以商业致富的记载数不胜数,明代沈思孝在其《晋录》中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13)[明]沈思孝《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而且当地土脊民贫、物产不丰,“非肩挑负贩,不足佐其耕获”(14)[清]《同治阳城县志》卷5,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即使是小村落的居民也“强半携中人产,走数千里外,求子钱供朝夕”(15)[明]张慎言《洎水斋文抄》,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11页。。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大量潞府民众游走逐利于全国各地,依靠商业、贩运为生,以致于“久客不归”,家中多由妻儿勉力维持。顺治年间刊刻的《潞安府志》中就有大量此类事迹,如该书中记载周景妻王氏,“潞州人,翁志、夫景俱客死郸县。王年才二十四,闻讣几痛绝,觅人归二丧。长子伦方数岁,次子备遗腹生。二子稍长,括遗赀使治商贾,家遂裕”(16)[清]杨晙修纂《潞安府志》卷13,顺治十六年(1659)刊印,第30页。等等。可见此种情形,在当时的长治地区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对远足亲人平安归来的祈盼、对亲人团圆的渴望,是当时潞府民众的一种普遍心愿,而且较之其他地区,此类观念在民众心理中可能有着特殊的地位。
笔者以为,“国清三隐”造像作为十八罗汉之一出现于长治观音堂中,与当时当地民众中的上述心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深入探究二者联系,则有必要对“国清三隐”中寒山、拾得身份及其被赋予功能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据相关学者考证,元、明之际,“国清三隐”中的寒山、拾得在延续唐以来流行于文人雅士中的禅门逸士的形象的同时,又逐渐被市井间的民众赋予了一种“和合二仙”的身份。虽然现在一般认为由寒山、拾得演化而成的和合二仙的主要功能为:由男女和合而演化出的主管婚姻的功能,以及由“和合利市”而演化出的财神的功能两种。但是如果追溯和合二仙信仰的原始功能,我们发现该信仰出现之初与唐宋时期万回信仰有着相似的功能。据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卷1“万回哥哥”条中称:“临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岁腊月二十四日各家临期书写祖先及亡者名号,作羹饭供养,罢即以名号就楮钱焚化,至来年此日复然。惟万回哥哥者,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每一饭必祭……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名万回。”(17)[元]刘一清《钱塘遗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33页。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宋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今其祀绝矣。”(18)[明]田汝成辑撰,刘雄、尹晓宁点校《西湖游览志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由此可知,宋代万回信仰实质是民众对亲人团聚的一种期盼,该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亲人只有回来,才能和合,所以万回亦是民众心中的“和合”之神。从《钱塘遗事》《西湖游览志余》中的相关记载可知,万回作为和合之神的地位主要流行于宋代,至明代“其祀绝矣”。但是与亲人团聚是人类心中的一种永恒的祈盼,所以《西湖游览志余》中所谓的“今其祀绝矣”并不是民众对“和合神”的信仰绝迹了,而只是万回作为和合神的时代结束了,其地位逐渐被由寒山、拾得所演化出的、新的和合神所取代。所以,由寒山、拾得所演化出的和合二仙最初被赋予的神格中就包涵了保佑远行之人能够平安归来、与亲人团聚的功能。这种神格也正好适应了明代长治地区商业文化盛行的社会风气中,潞府民众对亲人团圆的渴望。正所谓“人心所望,神即因之,不必实有其人也”, 长治观音堂中打破惯例,将“国清三隐”像置于十八罗汉中,可能就是为了满足当时民众精神上的需求。而“国清三隐”组像中被置于一半开的街门中,三者皆满面堆笑,亲人团聚时的喜悦之情跃然而出。上文中提到,长治观音堂正殿虽以佛教信仰为主,但是其中塑像的内容融合儒家与道教信仰,营造了一种内容较为庞杂的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信仰空间,观音与十八罗汉造像同时出现,也是明清之际观音堂造像中一种较为常见的配置,所以在长治观音堂中,“国清三隐”造像取代十八罗汉中布袋和尚或注荼半讬迦尊者(看门罗汉)成为十八罗汉造像组合中的新的一员,不仅不会与该信仰空间产生抵触,而且还在一定程度扩展了该信仰空间的功能。
以往单纯从造像形式出发将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组像的主尊身份判定为弥勒罗汉或看门罗汉的观点值得商榷。通过梳理现存图像实例,结合历史与地域情境进行释读,笔者认为长治观音堂大肚罗汉组像的形象源自丰干、寒山、拾得的“天台三圣”或“国清三隐”,目前虽难以确定其出现于十八罗汉中的具体过程,但是其出现的背景应与由寒山、拾得演化出的和合二仙所具有的满足民众对团圆的祈盼密切相关,与明代潞府民众普遍所具有的、祈盼远行经商的亲人能够平安归来的社会心理相适应,是明代佛教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