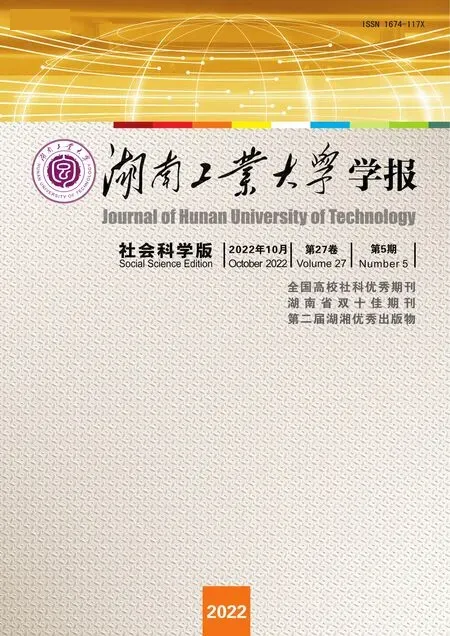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范文杰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在于谁才是希腊人的教师,掌握教育民众的权力。在古代希腊世界,民众教育问题说到底是城邦政治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统治者的德性才能,影响着邦民的风俗教化。长期以来,古代希腊人以荷马等诗人为师,“诗教”长期掌握教育民众的大权。随着历史和政治的发展,民主制、僭主制交替更迭且战乱频仍,“诗教”逐渐难以解决希腊人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公元前5世纪,希腊掀起了哲学启蒙浪潮,哲学教育随之占据上风。《理想国》以此为背景开启了思想史上著名的诗哲之争,研究者多从哲学角度审视该论题且多为哲学背书。但笔者认为,《理想国》中的诗哲之争并非以哲学的胜利告终,它揭示了诗歌教育与哲学教育的共同危机,指出哲学教育以诗歌教育为基础和起点,并以新的冥府神话示范了诗与哲学在民众教育事业上可能的融合路径。
从冥府主题切入《理想国》诗哲之争问题的探讨原因有二。第一,冥府意象几乎以均衡的结构比重贯通了全文:卷一苏格拉底“下行”佩雷欧斯象征着下降至危机中心的思维景象[1]104,在“下行”处观看的本荻斯女神的庆祝活动以下抵冥界又返回人间为仪式主题[2]47;卷七苏格拉底借用冥府的幽暗无光将雅典人比作手脚被铁链束缚、在火光中面壁观影、并将幻影当作真实的洞穴人;卷十的结尾处,苏格拉底创造了厄尔游历冥府的新神话。第二,贯通全篇的冥府主题实则隐喻着雅典的诗歌教育与哲学教育均面临严重危机,苏格拉底在夜谈中下行雅典,试图拯救深陷危机的雅典民众。
一、佩雷欧斯的诗教状况:阿德曼托斯之惑与理想城邦的起因
《理想国》在十卷的篇幅里讨论了诸多问题,有两个问题宏观地盘踞于整篇对话之上:第一,对正义本质的讨论如何引出对正义城邦的讨论?第二,在进入正义城邦的讨论之前,苏格拉底为什么对阿德曼托斯关于正义本质的困惑保持沉默,而在整个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做出回答?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阿德曼托斯的困惑。继色拉叙马霍斯和格劳孔之后,阿德曼托斯重申并抛出了众人的诘问:“别只依靠论据向我们展示正义强于非正义,而是展示两者各自根据自己的本性对拥有它的人产生什么影响,各自能否躲过天神和人们的眼目,使得一方好,另一方坏。”[3]367e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发展了色拉叙马霍斯的僭主式正义,他们向苏格拉底发问,当最大的不义伪装成最大的正义,而最大的正义忍受着一个最大的不义的名声,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理解正义。阿德曼托斯的有力论据是荷马史诗,他指出了色拉叙马霍斯和格劳孔虽未提及但都受其塑造的“荷马史诗式的世界观”。在阿德曼托斯看来,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诘问,正是来自诗人的那套说辞。荷马教育了整个希腊,参与了希腊社会习俗的构建,但荷马描述的神却“可被凡人引诱利用”[3]364d,“分配给许多好人糟糕的命运和痛苦的人生,而给富有的坏人相反的命运”[3]364b。阿德曼托斯十分大胆地指责了诗人所言的神非但不保证赏善罚恶,甚至是破坏正义秩序的元凶。苏格拉底坦言,有关神的相关说法是诗人编造的虚假谎言,但神以及敬神对城邦政治的重大意义不容反驳。苏格拉底的意思是,神本身是没有错的,如果诗人描述的神让人们迷惑,其原因在于诗人不负责任地编织了虚假的谎言,他们描述的并不是神本身。如果诗人描述的并非神本身,那么诗呈现的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塑造了希腊人的性格,希腊人的性格与习俗反过来又塑造和巩固了诗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诗本身就是希腊社会的一个缩影,“荷马事实上创作了一部文化百科全书”[4]66。苏格拉底指控诗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但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即便是再拙劣的模仿,诗人凭缪斯赐予的灵感和迷狂也需要一个类似于诗之“理念”的范本。诗人缺乏哲学家以理性主导的甄别能力,他的模仿对象是希腊人以及远古希腊人生活的自然状态。因此,诗本身并不全然是为了教育希腊人,也是对人类状况的呈现与表达。其次,人们的确从诗中汲取伟大人物的传说当作楷模,但是说荷马是整个希腊的老师,这样的断言并非从荷马史诗本身的意义出发,而是从目的出发,选择了一种理解荷马史诗的方式。阿德曼托斯援引荷马史诗控诉神的不义时,并未检审自己对正义概念的理解,也并未考虑正义在史诗中的特殊时代语境。哈夫洛克从语文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考察荷马史诗的正义问题时指出,在荷马史诗中,并不是正义的普遍规则统一管理着所有人类关系,荷马忠诚于社会的得体性意识,史诗中的正义象征了在特定情况中特定的人物有权期许着什么,以及期待什么才是正义的[4]222。另外,人们对神的看法,多半决定于人们对崇奉这些神的人的看法[5]36。在厄尔的神话中,苏格拉底反向重提了神的正义问题:神不作选择,人间的悲喜得失与神无关。苏格拉底对神不参与人间事物的设定恰恰回答了阿德曼托斯对神的指控——史诗呈现的含混性,是对“人的灵魂或者日常生活行为”[6]16的模仿。由于诗呈现与模仿的世界具有变动性,这就造成人们对诗的诠释和理解会追随这种变动而改变。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苏格拉底在清理奢华城邦时提到的腓尼基人传说:好的统治者要恰如其分地安置和守护一土所生、互为弟兄,但灵魂深处混合着不同金属品质的人们[3]415a。仔细体会这个传说就会发现,它分明低语着诗人赫西俄德在《神谱》中讲述的英雄与人类起源的古老教诲。苏格拉底改编的腓尼基人传说,本来就描述了一个人类世界流变的历史图景。在赫西俄德那里,从黄金到黑铁,金属的价值渐次衰落,人类的生存状况也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7]114-115。那随风逝去的英雄时代不知不觉滑落成为往昔,变成一种记忆,而一旦如此,希腊人在古风和黄金古典时期所展现出来的特殊天才,也会变成一种回忆[8]305。在诗人赫西俄德构筑的变化图景中,生逢黑铁时代的人们淹没于无尽的战争、动荡的政体以及衰败的世风中,自然无法想象也不会认同已逝年代的正义与神意,他们的欲望和需求有着黑铁时代独有的特征。苏格拉底显然熟稔赫西俄德的诗歌教诲,尽管有所犹豫,但他试图改编这一神话给人们以希望,使宝贵的金属品格与衰朽的黑铁品格共存。格劳孔在听完这个传说之后理解了苏格拉底的欲言又止,也服膺苏格拉底的判断:没有任何妙计能使他们本人相信(这个故事)[3]415d,因为我们即是黑铁的种族[9]116。
对人类世界充满无常变化的体验被纳斯鲍姆称之为“善的脆弱性”。纳斯鲍姆认为,如果柏拉图对他为什么选择哲学家的生活确实有所论证,他很可能是想要告诉人们,一种好的生活为什么应该尽量排除或者减小我们最为脆弱和最不稳定的个人牵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总是为欲望牵制,就会像布满漏洞的容器,永无满足之日[10]136。阿德曼托斯之惑的根源在于其所接受的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也恰恰证明了膨胀的欲望如何影响人对正义和神的认识。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认知方式,着重于模仿和记录人类世界的诗必然会跟随时间的消逝呈现出变动不拘的形态。黄金时代、英雄时代的秩序已逝,如果人们不能从流动变化的世界图景中甄别出永恒不变的存在,阿德曼托斯之惑就永远没有妥帖的答案。荷马时代的古老诗歌像一块未经打磨的自然原石,包含诸多神秘的知识,只有全面地掌握这些知识,才能整全地认识这块原石的自然,才能构成对诗的真正理解。苏格拉底毫不掩饰诗人对他的滋养,与众人不同的是,他具备认识诗之自然的能力。
为了让有天分的青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苏格拉底将荷马史诗中呈现的、黑铁时代已经不再认同的世界秩序解释为诗人编造的谎言,并暂时悬置了阿德曼托斯之惑,将众人引入城邦政治问题的讨论。从全书来看,寻找正义之路是艰难的,苏格拉底面对的众人被强大的习俗和时流意见所裹挟,他需要先促使众人深陷危机中的灵魂发生朝向真理本质的扭转,之后才能给出关于正义本质的回答。也只有在灵魂发生扭转的时刻,认识到光之所以为光、黑暗之所以为黑暗的本质,这一回答才是有意义的,才有可能被理解。因此,苏格拉底引导众人目睹一座健康朴素的城邦从繁盛走向衰败的全过程,用城邦隐喻了雅典人的灵魂危机。
采用城邦隐喻的原因其一出于男性公民的政治热望;其二则由于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天然的人类状况,是与每一个人切身相关的社会、战争、生存等问题的根源,是古老史诗呈现的世界,也是讨论正义问题最根本的场域;城邦隐喻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在于直接启蒙的危险性。苏格拉底在第七卷把深陷教育危机的人比作生活在洞穴中的人:“这些人从小就在这里,腿上和脖子上都绑着锁链,他们始终待在一个地方,受锁链的束缚无法掉过头来。他们身后的上方燃烧着一团火光,这团火和这些被绑着的人之间有一条通往上方的道路。”[3]514a5-514b5一部分人由于古老的习惯和灵魂的差别安于生活在幽冥般的洞穴里,洞穴外的光芒一旦下行进入幽冥之地将会因打破其长久的积习而遭受指责甚至围攻。所以,通往洞外的光明之路是一条需要灵魂自己产生向上欲望的上升之路。如何消弭天资优秀的青年人对强大积习的依赖,如何从古老的习俗和时流意见中拯救对城邦政治葆有鲜活爱欲的青年,这些问题的严峻性更加巨大,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是诗与哲学纷争的重大意义所在。佩雷欧斯之夜,在场的所有人都跟随苏格拉底经历了一番构建理想城邦从而寻找正义的旅途,苏格拉底引导能够发生转向的灵魂自己掌握看的能力,超越绝大多数人向下涌和返回中间路段的欲望本能,指引他们抬头走向真正的高地,去获得本质的充实,品尝既可靠又纯洁的快乐[3]586a。
佩雷欧斯的诗教状况十分复杂,苏格拉底由此展开的谈话对众人乃至整个雅典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玻勒马霍斯来说,苏格拉底可能帮助他剥离其父克法洛斯所代表的强大习俗的藩篱;对色拉叙马霍斯来说,苏格拉底可能纠正其灵魂,让他看到真正的哲学家与智术师在灵魂上的差别;对于格劳孔这个有着强烈政治爱欲且品质优秀的年轻人,苏格拉底以理想城邦的建构给予他所热望的政治启蒙;阿德曼托斯是相对复杂的灵魂,因为我们无法看清阿德曼托斯所爱欲之事,他对政治和城邦习俗有着冷静的认识,他的诸多问题代表着一股反诘苏格拉底哲学的根本性力量,是洞穴中人拒绝被真理之光照亮的本能抗拒。阿德曼托斯也因此最具有哲人的气质,他是一个熟谙雅典习俗之强大且认识自身所处洞穴的可教者。让我们再次返回这场谈话的开头,苏格拉底被迫下行佩雷欧斯港,“在留住他的那个深处,他开始了探究;他在友人身上施加劝导性的力量,不让他自由地回到雅典,而是让他们跟随他来到理念的城邦。路始自比雷埃夫斯的那个深处,不是回到马拉松的雅典,而是向前、向上走到由苏格拉底及其朋友们在他们灵魂中建立的城邦”[1]104。
二、佩雷欧斯的哲学状况:从消逝之诗攀登哲学的线段阶梯
佩雷欧斯的诗教状况让苏格拉底决心将诗人和诗暂时逐出理想城邦,苏格拉底为理想城邦设计的统治者是天生记忆力强、擅长学习、思路开阔、气质和蔼、喜欢并亲近真理、拥有正义感、充满勇气、具有节制精神的哲学家[3]487a。但阿德曼托斯随即指出,苏格拉底描述的那种哲学家绝大部分将其一生都投入了哲学研究当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批对城邦根本无用的人。苏格拉底并没有否定阿德曼托斯的看法,实际上,他十分认同阿德曼托斯的说法。由此,构建理想城邦的假设语境在这里已经被替换为现实语境,所谓将诗逐出城邦的结论在这里成为一种吊诡的反讽——现实中,被逐出城邦的并不是诗以及诗人,而是哲学与哲学家。一方面,阿德曼托斯的质疑指出了时下雅典社会相当流行的关于哲学与哲学家的看法;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辩护也面临着十分艰巨的挑战。佩雷欧斯的哲学状况与诗教状况的博弈就此展开,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逐渐移步至谈话的核心部位。笔者认为,苏格拉底分别讲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雅典社会哲学教育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另外,通过著名的“线段喻”和“洞穴喻”,苏格拉底实际上论述了诗以及诗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其实是攀登哲学高峰的起点。
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教育了希腊人的不是诗人和诗,而是智术师派[3]493a-493d。人们大多从贩卖知识的智术师那里获取知识,诗在智术师这里成为教学的材料,智术师掌握了诗的解释权。雅典城邦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缴纳学费学习知识,换言之,众人皆可读诗,诗既可以成为描述世界的工具,又可以被智术师任意解释。智术师对诗的解释依赖诗所呈现的世界和社会现状,取决于人们的爱憎追逐和流行风尚,因此流逝性和变化性就必然环环相扣于诗和人们对诗的理解之间。与此相对,哲学涉及事物的本质,诗缺乏的稳固且具有绝对真理的本质恰恰是哲学最基本的特点。苏格拉底认为那种本质才是真正的真实。并且,哲学对人的天资与灵魂有着特别的要求,只有一少部分人适合学习哲学,而这一少部分适合学习哲学的人需要通过长久的培育和艰辛跋涉,才能靠近哲学,成为真正的哲学家。诗之所以会被逐出理想城邦,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象征着流变不拘的爱欲。但在斯坦利·罗森看来,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也承认哲学的本质就是爱欲[6]12。爱欲从未消失过,只不过苏格拉底试图使诗中毫无节制且损害理性的爱欲转变成对哲学的适度的爱欲。斯坦利·罗森试图从这个角度论证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不成立,但却未能对爱欲目标的差别作出区分。苏格拉底的确论述了爱哲学本身也是爱欲,但哲学欲求的不是欲望本身,如果爱哲学是一种爱欲的转移,这种爱欲的目标指向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借用苏格拉底的比喻,如果将民众繁杂的爱欲比作河流分开的旁支,那么对哲学的爱欲将是一条没有旁支的奔腾的河流,而这样的河流少之又少,因为曾经讨论过的一切所具有的暂时性都会腐蚀灵魂,他们的目标都并非事物的本质。
经过一系列推论,苏格拉底认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应该是真正的哲学家,理想城邦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城邦民众在工作与灵魂方面都能各司其职,这是一种未曾遭受任何败坏的理想社会状态。但是,当经验世界的状况摄入理论建构的城邦,哲学以及优秀哲学家的品质又面临着无法避免的被腐蚀与被破坏的局面。本质上,这又是哲学代表的绝对理念世界与诗力图展示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当众人跟随苏格拉底把目光移至哲学,他们惊奇地发现哲学教育面临的危机状况并不比诗好多少。苏格拉底虽然承认哲人统治城邦的不可能,但却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他详细分析了哲学以及哲学家所面临的危害,并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哲学家难以生存。首先,雅典社会不具备培养哲学家的合适土壤。前面已经论及,当时社会中最活跃的教育者是智术师,但他们败坏了教育并侵占了诗教的权力。其次,具有哲学家潜质的人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顺利地走向哲学,他会在各种牵制力量中被扭曲变形,离哲学越来越远。孤独的哲学这个时候沦落为被人利用的空名,这就是哲学以及哲学家的现状。与哲学现状相对应,《理想国》中出现了三种哲学家,分别是:理想城邦中作为城邦护卫者的哲学家;现实城邦中与智术师无异的伪哲学家;“洞穴喻”中那些凭借自己对真理的渴求向上走进光明中的真理,又迫于使命被迫返回洞穴履行统治义务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隐微地用“洞穴喻”完成了由言辞中的理想城邦到现实城邦处境的转换,洞穴里由火光照亮的虚假白天和洞穴外如阳光般耀眼的真理之间,究竟哪一种哲学家才被苏格拉底认可?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所言的真正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哲学?
由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洞穴喻”之前的“线段喻”。“线段喻”首先将世界一分为二,这两部分分别是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接着这两部分又分别被再次分割:可感世界被分成影像和实物;可知世界被分成数学和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理性领域。苏格拉底的理想设计中真正重要的是可知世界,在可知世界的线段部分,苏格拉底希望灵魂认识到,“理性并非把那些假设当作原型,而是本质上就把它们当作假设,如同动身和出发的起点,以至于理性走到没有假设的领域,走向每一事物的原型,当理性依附上原型后,它就开始返回,带着一切跟随对方而来的东西,如此从高处走下,来到终点,不利用任何可感的东西,而只利用这些理念本身,从理念到理念,最终又到达理念。”[3]511b5-511c“线段喻”在《理想国》的诸多比喻中最为抽象枯燥,可其中却暗藏玄机。“线段喻”是苏格拉底纯粹的理性设计,是他为灵魂设计的能够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但是,它就像理想城邦中的护卫者哲学家,是理想当中的完美设计,却并非现实之中的可取之路。将第六卷的“线段喻”与第七卷的“洞穴喻”相结合我们将会发现,苏格拉底频繁地提及要将洞穴中的人们“从枷锁和无知中释放出来”[3]515c,“把灵魂从生成变幻的世界拉向本质的世界”[3]521d,“让他们从生成的世界走上来掌握本质的世界”[3]525b……也就是说,可感世界,人们生存并感知和体验的世界,诗所呈现的那个具有消逝性的世界才是通往本质世界的起点。如果我们把“线段喻”看作是整个世界的分割线,那么“线段喻”本身其实是一座通往哲学高峰的阶梯,攀登的过程必定不能脱离阶梯的任何一层。苏格拉底提到的走出洞穴由黑暗适应阳光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剥离可感世界的过程。如果没有诗或者影像展示的可感世界,这种剥离就没有起点;而缺乏可感世界的对照,可知世界似乎也无从界定。所以,苏格拉底哲学的完整过程其实包含着对洞穴生活的体验,包含着对诗所呈现的可感世界的体验。没有诗,通向哲学的线段阶梯将没有起点。苏格拉底就像一个历经艰辛的攀登者,他转过身,伸出手,不厌其烦地向听众描述着这条阶梯可能的长度和阶梯之上的朗朗世界。消逝之诗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但阿德曼托斯之惑的答案不在阶梯的第一层,也不在第二层,它包孕在这个完整的攀登过程之中,拒绝攀登的人,势必永远得不到答案。
真正的哲学“是把灵魂从某种黑夜般的白天扭转过来,面向真正的白天,这是一条向上、通向本质的道路”[3]521b。苏格拉底所言的黑夜般的白天是洞穴中被火光照亮的虚假的白天,是诗呈现的充满变化的人类世界的秩序幻影。从理想城邦被构建的起初,苏格拉底就在不停地引导谈话者向上看,被向下涌动的欲望拖拽着的听众只有逼迫自己的灵魂向上看,对把握真理和本质的能力充满渴求,才有可能抵制灵魂的败坏,才有可能在流俗的意见中拥有分辨的能力,才有讨论正义本质的基础和理解正义本质的前提。阿兰·布鲁姆在《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中提到:
《理想国》的对话有一种上升的特点,从洞穴攀升到理式的领域,在攀援之顶,苏格拉底揭示出自己是个幸福快乐的人。苏格拉底没有强求格劳孔不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只是让他意识到还存在着专制独夫无法获得的益处,以及摆脱政治欲望的别种追求。因此,做一个像暴君那样的非正义的人才是不正义的[11]95。
格劳孔认识到,苏格拉底创建的理想城邦并不属于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苏格拉底从一开始就坦言,这的确只是言辞中的城邦。这一虚构城邦的存在意义是试图通过一个完整的想象过程,使人们意识到当下众人所深陷的灵魂危机以及真理世界所能提供的帮助。苏格拉底回答,“太空中也许屹立着一个典范,它为某个想看到它、看到它后又想让自己定居于此的人而存在,这一个城邦是否眼下或者将来存在于某个地方,这没有任何区别。”[3]592c虽然理想城邦是言辞的虚构,但只要它能够存在于对政治葆有健康爱欲且认同这座理想城邦的爱智者的灵魂之中,它就是存在着的。
苏格拉底对诗人和诗的严苛态度有其特殊的现实语境,但他并未否认荷马的重要和深奥。在一场奥德修斯式的冒险夜航中,苏格拉底也像奥德修斯一样,不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告诉同行的同伴,因为他无法识别这些同伴的接受能力以及各自的灵魂品质。在这场下行救护众人的旅程中,苏格拉底也不可能在天亮之前将所有重要的问题予以清晰的教诲,他只能告诉众人,哲学最高的那个目标在哪里,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诗对民众教育乃至城邦政治的影响。而更加复杂的知识,苏格拉底将会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他的谈话。
三、诗与哲学的交融:奥德修斯的第二次选择与诗之重返城邦
在论毕佩雷欧斯的诗教状况与哲学状况之后,我们已经清晰地感受到,诗与哲学的关系并非“纷争”一词可以尽数概括。《理想国》对诗哲问题有着多维度的认识和考量,对诗哲关系的呈现具有丰沛的层次感。城邦的理想设计与城邦的现实状况在苏格拉底与众人的夜谈中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交锋状态,并在终章由苏格拉底创造的冥府神话中达到高潮。
苏格拉底对诗有一个著名的看法,认为诗人的创作是对真理模仿的再模仿。对那个创造了理念的神,苏格拉底谈到,他也创造了大地、天空、众神以及那些属于哈德斯之处的东西[3]596c5。由此可见,诗人口中的众神与冥府其实被苏格拉底所描述的神涵括了,苏格拉底的神涵盖了宇宙万物,也涵盖了荷马史诗中的众神。荷马史诗中的神虽然比人强大,但也自然地承受着命运流变的无常。逻辑上讲,理念之神的无所不包赋予了苏格拉底创造新神话的基础与合法性。在创造新神话之前,苏格拉底解释了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
这一斗争意义重大,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成为一个好人或坏人,而是为了做这么一个人,他不会在名誉、金钱、某种权力甚至诗歌的诱惑下认为自己值得放弃正义和其余的美德[3]608b。
苏格拉底曾经提到过,真正的哲学以及哲学家的使命在于“生活在一个合适的体制中,在不断的成熟中拯救人们的共同事业以及他们的个人事业”[3]497a。如果说从冥府返回人间的神话主题象征着人对穿越死亡之域、重获生命的渴望,哲学以及哲学家的拯救使命恰恰在苏格拉底的冥府神话中对此作出了回应。由此,我们可以将诗人的冥府神话与苏格拉底的冥府神话做一番对比,以便从《理想国》最后一个比喻中洞悉苏格拉底关于诗与哲学关系的教诲。
在《奥德赛》著名的冥府片段中,奥德修斯并不是以已死之人的身份进入冥府的,而是为了从先知特瑞西阿斯处获得归返伊塔卡的方式和其命运的预言,以活人的身份进入冥府。奥德修斯在冥府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意外死去的同伴,随后见到的主要是历史上高贵的女眷和曾经一起参加战斗的英雄。也就是说,他在冥府见到的是现实中人未竟的心事与状态。人类死后的世界在诗人那里,被固定为现世命运最鲜明的高光时刻,人的形象在冥府中是被保存下来的。奥德修斯不关心这些灵魂的终极命运以及死亡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因为他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仍要返回人间世界。奥德修斯穿梭于生死世界之间,获得的最大的知识却并不是如何化解神谕施加于他的诅咒。基尔克的安排的深意在于,她帮助奥德修斯确定的唯一整全的知识是关于人生的有限性,无论生死,这都是世俗人类不能摆脱的命运。奥德修斯认识到,即使是在一个充满诸神和魔力的世界当中,诸神与魔力也充满了局限。奥德修斯从埃尔佩诺尔那里知道了自己作为国王对这个无名小辈所负有的神圣责任[12]140;从特瑞西阿斯那里,他知道了自己注定漂泊的命运;从母亲那里,奥德修斯知道了生命的脆弱与情感的珍贵;在阿伽门农的故事后,不相信任何事也不相信任何人似乎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幽冥世界里,奥德修斯知道了有必要埋葬死者,学会了做奥林波斯诸神的信使[12]142。在诗人的冥府中,奥德修斯学到的知识几乎都能够用“命运”一词概括,即使诸神也难逃命运。时间在诗人的冥府以及全部的历险当中并没有对奥德修斯产生任何影响,严格来说,时间只能给诗人的主人公留下纯外表的印记[13]21。奥德修斯始终是一个机警精明、充满战斗力、矢志不移夺回王权的勇士,所有的行动和思考“始终处在地点和时间的现时性中”[13]6。在荷马这里,奥德修斯窥见了生命的规律,他知晓了命运以及有关生死的知识,这一经历是生命的例外状态。只有在有限的生命由于意外进入冥府,探知生死交界处的状况而后重返人间,才能讨论特瑞西阿斯对奥德修斯命运的预言应验后,面对生命的自然终结,也即奥德修斯去到冥府的第二次选择时——究竟是进入诗人的冥府还是哲学的冥府。苏格拉底在这方面效法了荷马,他采用了诗人的思维模式,在厄尔关于宇宙结构的描述中建构了对“线段喻”的又一次喻中喻——苏格拉底以冥府神话的方式描述了人们无法想象也未曾到达的线段阶梯的高处景象。
在苏格拉底的冥府神话中,厄尔作为一个死去战士的亡魂进入冥府,他在这里洞见到的不仅仅是对人生有限性的认识,还包括整个宇宙的运行与人生命运的分配和选择。人生的未知性在苏格拉底的冥府中是不存在的,厄尔的神话代表了哲学家对整个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冥府的教育是关于确定性知识的教育,是对人生有死性和人生机运的确定性体验。因为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人类死后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依旧有着密切的关联——过去的生时世界决定了现在的死后世界,死后灵魂的选择决定了将来下一个一千年后生的世界。在苏格拉底的冥府神话中,时间之神对人的命运有着绝对的影响。宇宙在克洛佗、拉克西丝、阿特罗珀斯三位时间女神的守护下运动着,三位女神分别代表着时间的“现在”“过去”与“将来”,“现在”与“将来”分别站在“过去”的两边,经由“过去”连接在一起[3]617c-617d。由此可见,哲人冥府的时间概念与现实的时间不完全相同,在苏格拉底的神话里,他将时间的过去性置于现在和未来之间,现在和未来分别位于过去的左右两边,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是现在以及未来的基础,过去决定着现在以及未来。所以,哲人冥府的亡魂在进行来世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需要依靠的仍然是自己在过去习得的所有知识和理性。也就是说,一切祸患的根源并不在于命运以及各种神灵,而在于每一个亡魂自己造成的过去;灵魂的正义在此时不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自律[8]19。
当苏格拉底在神话的最后回到《奥德赛》,哲人设定的冥府语境赋予奥德修斯与众不同的选择就显得十分恰当。奥德修斯是最后一个上前作出选择的人,他选择了一种几乎被所有人拒绝的普通平民的生活。这既像是苏格拉底对《奥德赛》的续写,又像是他为众人作出的一种示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诗以及诗人。如果说诗人的冥府教给奥德修斯最重要的知识是认识有死人类面对命运时的有限性,那么哲学冥府的知识恰恰是对命运的不顺从,因为在哲学的冥府中,过去的一切才是命运的成因,过去掌握在每一个生命的不同选择之中。由此,从哲学的冥府出发观察奥德修斯的选择,我们可以肯定,他依据的就是诗人荷马在《奥德赛》中为他书写的一生。关于厄尔神话描述的奥德修斯最后的选择,西格尔认为,“唯有奥德修斯久久思考,也唯有他选择了人形和自己原有的性别,未被外在事物所蒙骗。这里我们可以认出荷马的奥德修斯,他在同伴中独自抵抗着基尔克的野兽变形……这个段落用神话的语言总括了贯穿于〈王制>中的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斗争。”[14]245布鲁姆则认为,“奥德修斯——智者的原型——医好了对荣誉和野心的热爱,并且看到人类生活的所有可能性,最后选择了作为个体的私密生活……”[11]95与洞穴中的哲学家的本意十分相似,奥德修斯走出了有限人生的洞穴没有再选择回来;或许也并非如此,他只是用过去所有的知识选择了一种居中、适度的生活。苏格拉底对奥德修斯最终选择的隐喻是基于诗人荷马对奥德修斯的塑造,这再次证明了诗在攀登哲学高峰过程中的重要性。苏格拉底用一个新的冥府神话替换了荷马的冥府神话,他希望有能力走出洞穴的灵魂“不仅在这里,而且在那历时为一千年的路途中,都会过得很顺利”[3]621d。关于诗人冥府中的奥德修斯,伯纳德特认为,奥德修斯似乎把曾经到过哈得斯当成一种特权,就好像他以后不会再到哈得斯一样[12]148。如果伯纳德特的断言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至少奥德修斯不会再回到荷马的冥府,直到他“找到这样的部族,那里的人们未见过大海,不知道食用掺盐的食物,也从未见过涂抹了枣红颜色的船只……那时你要把合用的船桨插进地里,向大神波塞冬敬献各种美好的祭品……”[15]198-199这之后,死亡将会给予奥德修斯第二次选择的机会。苏格拉底抓住了诗人荷马给出的留白,诗人的冥府和哲学的冥府得以通过这一留白被关联起来——进入哲人的冥府是经过哲学沉思之后的奥德修斯的第二次选择。
行将结束的《理想国》戏剧最后印证了这一猜想:苏格拉底再次提起了诗的问题,这是苏格拉底唯一一次主动开启的关于诗的话题,他用一个全新的冥府神话替换了诗人荷马的冥府神话,但此时创作的诗显然并非是他唯一认可的颂神诗。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苏格拉底诗性外衣之下的哲学教诲,但这层诗性外衣并非索然无味的装饰,更像是一种回归诗人荷马的示范。在这个神话中,苏格拉底没有再遮蔽史诗中于民众灵魂无益的内容,而是为听众的自主理性留出了充足的空间,使他们自由聆听冥府中所有生命的选择,使他们能够利用佩雷欧斯之夜的哲学教诲严肃认真地观察并审视现实世界。在厄尔的冥府之旅后,荣耀本荻斯女神的净化仪式似乎也在净化着现实城邦的教育。净化过的城邦将会重新引入起讫于古风时代的诗教传统,让诗性教诲与哲学的理性判断相互交融于雅典民众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