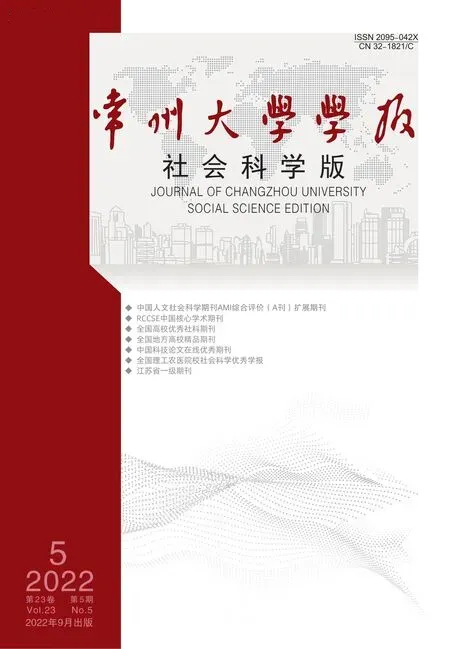以“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方式来“淬励人心”
——《中央日报》上的三篇吴祖光集外佚文释读
高强
吴祖光除了是著名的戏剧家,创作有《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捉鬼传》等知名剧作外,在戏剧评论和影视导演领域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吴祖光的研究依然呈现出戏剧创作解析“一家独大”的情形,全面立体、丰富复杂的吴祖光形象尚需努力识别。要充分研究吴祖光,首先必须充分获取并占有吴祖光的各类作品资料。迄今为止,收罗吴祖光创作最全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六卷本《吴祖光选集》。号称收录“吴祖光四十年里写下的与戏剧有关的文章七十余篇”的《吴祖光论剧》一书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吴祖光研究专集》,则是最重要的两本吴祖光资料集子。吴祖光的作品资料貌似多样,但这些著作或多或少都存在失收、漏收的情况,显得极不完整。因此,对吴祖光的集外佚作进行收集整理,就显得十分迫切。近日,笔者在重庆版《中央日报》上就发现了三篇吴祖光的集外佚文,兹略作钩沉。
一
1938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第4版的《戏剧周刊》第15期刊有《抗战历史剧》一文,署名“吴祖光”,照录如下:
经过了三十余年演变的话剧,到今日才发挥了它最大的功能。大时代的推动,使它从大都市深入到民间;从贵族的娱乐品变成了抗战的利器。这种惊人的进展,不是我们在战前的几秒钟之前所能预料得到的,那末在抗战结束最后胜利实现之后,我们话剧更将得到多么美好的收获,更不是现在能够想像的了。
几年来,话剧运动在万般艰苦的状态之下奋勇迈进,一切的困难似乎都还不难度过;进展虽然慢,然而总是在进步着的。可是有一个恐慌一直无法解决,那就是“剧本荒”的问题,到如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好像我们不应该再谈到这个问题了。以抗战剧来说吧,在抗战的十几个月里,剧本的出产量的确可观之至。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抗战剧渐渐公式化,看来看去情节往往相差无几。写剧本的人常觉得他想说的话被前头的人说完了;很不容易翻出一个新花样。看戏的听完了第一句话也就猜出了第二句话;看完了第一幕,也就想出了第二幕是怎么回事。所以剧本产量尽管增加,内容往往大同小异;两两相抵,“剧本荒”依然如故。
这就是因为现实的生活是在抗战之中,大家的感觉常常是一样的。抗战中所发生的故事虽多,但总不外乎是烈士成仁,汉奸卖国,敌人凶暴等等题材。这有限不同的方式,总有被人写穷了的时候;更何况现在的剧作大半是应时急用性质,尤不免陷于粗制滥造,这就是无怪乎要发生上述的情形了。
于此我们似乎不得不另打出路,而向历史上去找材料,过去话剧用历史材料的实在太少了,自然编历史剧会遭逢到许多困难,不过假如我们不能克服这困难的话,我们就是坐失了一条发展话剧的路。只以有关抗战的史料来说吧,中国立国数千年,其间数遭灭亡之惨,但都能恢复规模;在如今这种情形之下,还是屹然不为所动。这就是民族的力量有以致之;这力量不是偶然的,是几千年来我们无数的先圣先贤遗留下来的精诚所制。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会骗人的。我们无数先烈以大勇大智血肉写成的故事,永远是我们的模范;他们成仁取义的精神所影响于天下后世,因果分明。他们的故事尤极慷慨激昂,可歌可泣之至,足以成为我们最精彩动人的戏剧题材。
戏剧不但是抗战的利器,而且也是淬励人心的社会教育工具,这两种功用在今日是不可分的。中国在近百年来国势日削每况愈下;实在是因为自己不知振作,习于晏安,习于无耻,外侮迁凌正是自己造成的结果。挽回沦亡的道德实在是救国图存的当前急务,戏剧在这里不能漠视它的使命。应该把我们忠勇的先烈的精忠史绩搬上舞台,使民众得到警惕发奋图强,辅助抗战,促成最后胜利的早日实现。
翻一翻历史,我们会觉得好戏太多了。演出上的困难其实是不成其为困难的。这种浩然正气的表现自会使顽夫廉,懦夫立,重振起我们光荣的国魂。
《中央日报》的《戏剧周刊》附属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由国立戏剧学校主编。该刊于1936年1月创刊,1938年9月《中央日报》迁往重庆,《戏剧周刊》也随之迁渝。抗日战争爆发后,“发动抗战的意志,整齐抗战的步骤,激起抗战的情绪”[1]被视作文艺的首要任务。于是,具有强烈情绪感染作用、深受观众喜爱的戏剧便一跃成为最受文化界青睐和重视的抗战动员形式。在南京出版期间,《中央日报·戏剧周刊》的探索呈现出浓郁的学院化色彩;到了战时重庆,《中央日报·戏剧周刊》则响应抗战的询唤,主张“戏剧入伍”[2],此后,力推和探讨“街头剧”的写作与演出,译介外国戏剧作品和戏剧理论逐渐成为《中央日报·戏剧周刊》的一大特色。抗战,使得《中央日报·戏剧周刊》面貌一新,对于整个戏剧艺术门类来说,同样如此。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创痛,但却使戏剧艺术地位猛升、风头强劲,吴祖光口中所谓的“惊人的进展”、所谓的“从大都市深入到民间,从贵族的娱乐品变成了抗战的利器”正是对这一情形的最佳注解。
受战争激发,戏剧作品的产量突飞猛进。可是,喷涌而出的抗战戏剧却“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3],性急的鼓动、直观的高呼俯拾皆是,于是便产生了“抗战剧渐渐公式化,看来看去情节往往相差无几”的现象,这不能不让戏剧里手吴祖光心怀忧虑。为了解决抗战戏剧面目单一的公式化弊病,吴祖光提出了“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戏剧创作路径。将历史上先圣先贤激烈悲壮、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重新编演成剧,以之感召民众、振发民心。此类题材虽不直接取材于抗战本身,但其背后蕴含和传达出来的却是坚实有力的精神思想;而且,因为相关故事在民众中长久流传,早已“渗入”寻常百姓的心灵深处,所以当借之表现抗战时代的新命题时,与观众之间的差距和隔膜自然会降低不少,这种“迂回作战”的戏剧创演策略,比起正面强攻,似乎更易取得事半功倍的良效。事实上,“向历史上去找材料”,借古人古事来启迪今人、服务今事的历史戏剧创作和演出模式,是抗战时期蔚为大观的文艺风貌。以往,我们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常常只是以“古为今用”云云来简单概括,吴祖光此文则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戏剧热潮的产生和时人对抗战戏剧公式化弊病的纠治之间存在着某种因缘联系。
另外,《抗战历史剧》一文所主张的“向历史上去找材料”,还蕴含着戏剧家吴祖光在抗战这一特殊语境下极具远见的戏剧编演策略。如上所言,当吴祖光提出“向历史上去找材料”时,乃是为了纠治抗战戏剧公式化的病症,是确保戏剧不会因遵循抗战询唤而丧失“艺术”本体性价值。但是,宣扬“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吴祖光,又绝非鼓吹戏剧艺术逃避现实、远离现实。他明确表示,“戏剧不但是抗战的利器,而且也是淬励人心的社会教育工具,这两种功用在今日是不可分的”。换言之,呼吁戏剧界“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吴祖光,其实既在着力凸显戏剧的抗战功能,又在通过“回溯历史材料”的方式来谋求创立中国戏剧艺术的独特的“民族形式”。如此一来,吴祖光便得以悄无声息地在艺术与政治、一时之功与长久之计之间开展某种平衡协调工作,以使得戏剧艺术既可因一时之抗战而繁荣,又不因抗战终止而衰退;既可因抗战而成“利器”,又不因抗战而丧其“艺术”。这一“通达权变”的策略,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来说,是极富理论见识和实践价值的。
二
1941年10月24日第4版的《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刊有评论文章《读〈北京人〉——我们是第二代的“北京人”》,署名“吴祖光”,照录如下:
我时常想到在无数千万年以前,那时候天地初分,乾坤始奠;天上出现了日月星辰,地上也出现了山川河流;风云雨雪开始在空气里循环,山谷间流出了清冽的泉水,平地涌成了无涯的海洋,花树从地层中抽出了它们最早的新苗,在四时的佳气里欣欣滋长。
这世界是美丽的,但亦是寂寞的,荒凉的,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因为还没有人类,它缺少的是“人类的爱”。
又过了无数年的长的时间,当第一个“北京人”——我们就姑且认他是人类的祖先——从这荒漠的大地上出现时。
当第一个北京人从这一片荒漠中出现时,他是多么吃惊啊!他看见上面的天,脚下的地,四周的山川草莽时,他又该怎样地想啊?从这一个时候起,世界在变了,因为人类开始为地球带来了爱,带来了生命,宇宙万物都发出了声音,唱出它们对人类的祝颂:泉水在泠泠地响,大海中滚起了汹涌的波涛,日月增光,星辰含笑,地上的锦绣丛中透出了花香同草香。远远地,从白云堆里飞过来,停在北京人肩上的,是那代表光明,象征和平与奋斗的鸽子。
北京人便是这宇宙万物的主有者,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北京人的,这些无偿的朋友随时在给他欢笑,给他同情,给他无限的温暖。
然而北京人的命运却是艰苦的:严寒苦恼着他,他没有衣服;风雨攻击着他,他没有房屋;豺狼虎豹随时会杀害他,他无法抵御;雷霆电闪给他惊奇;洪水波涛使他恐怖;正像是大洋中的一叶孤舟,无时无刻不在雨风冒险,任何时候都会倾覆,死灭,前路茫茫,毫无把握。
但是北京人不怕这些个。为了御寒,他造起了衣服宫室;为了应付野兽的威胁,他发明了弓箭戈矛;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仗着他一付聪明的脑筋,一双有力的手,我们光荣的祖先含辛茹苦,开创了人类的万世不拔的基业。
北京人为什么能生活?就为了他爱生活,他就有力量生活。
现在我们真应该大声疾呼啊!世界在蒙尘了,人类正在遭劫,腐化的势力正在人世间暗暗飞也似地滋长,世界需要第二次的重新开辟,我们将是第二代的北京人!
这就是我读了曹禺的《北京人》后所感觉到的。这天才的作家,这杰出的作品,是历尽了多少世纪的酸辛,是体味了多少人生的艰苦,又是多么尖锐地指出了我们的病根,更是多么圣明地告诉了我们那新生的路向。
世界还有救,人类的爱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已被摧毁的废墟上正建立起光明的堡垒,长眠了的“北京人”的精神,正在争自由争幸福的人的心里复醒起来。
我们要踏着第一代的北京人的往迹再前进,重新奋斗,群策群力,自强不息。培养新的生命,决不顾惜旧的残余,任凭旧的堕落,腐朽,死亡。
曹禺先生的《北京人》的演出,将是人类胜利的前奏,也是我们剧坛的光荣。
让我来喊:唾弃那黑暗!歌颂那光明!重开辟新生的世界!我爱《北京人》!
1941年10月24日,曹禺的《北京人》由中央青年剧社首演于重庆抗建堂,导演张骏祥。而吴祖光的这篇评说《北京人》的文章,刚好于同一天发表,显得十分应景。该文也是除各种演出广告之外,笔者目前所见的第一篇关于《北京人》的评说文章。吴祖光的这篇《北京人》剧评文章,不仅问世迅疾,而且面貌独特。与常见的剧评文章不同,吴祖光此文并非规矩理性的文艺评论,而更像是一篇情感充沛的诗意散文。经由吴祖光浓墨重彩的渲染和发挥,“远古北京人(中国猿人)”历经艰辛、开辟世界的征程,不仅构成了曹禺剧作《北京人》中最亮眼、最关键的存在,而且跃升为战时中国人民这群第二代“北京人”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把“猿人”视为《北京人》一剧的中心,大力彰显“猿人”不畏艰险、勇毅奋斗的精神价值,这一点显然不合于当下通行的认识。比如,颇具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北京人》是探索生活孤独处境的“生命的诗”,是在历史的参照与对比中,对曾文清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沉滞性与荒谬性的审视[4];田本相则更是将《北京人》归为“一出‘与抗战无关’的戏”[5]293;而曹禺本人则说“愫方”才是他“用了全副的力量”塑造的“主要人物”[5]299。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对旧作进行修改后出版了《曹禺选集》。在此过程中,他曾坦诚地表示:“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6]换言之,不但当今的研究者与吴祖光对《北京人》的认识存在分歧,就连曹禺自己也表示创作《北京人》时并没有为了强调剧作的革命性而刻意将“猿人”拔高成全剧的中心。然而,与吴祖光相仿的评说角度,在《北京人》上演之际并非特例。柳亚子就在《新华日报》发文礼赞道:“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7]邵荃麟则批评《北京人》“还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要从这家庭的悲剧去看社会的悲剧命运,却是不够明确和具体”[8]。柳亚子的歌赞与吴祖光的评说如出一辙,邵荃麟的批评与吴祖光的言说彼此对立,实际上都是从抗战对文艺提出的战斗鼓舞性诉求出发做出的判断。邵荃麟认为《北京人》主要反映了一个家庭悲剧,视野偏狭,社会层面的悲剧性不足,因而缺失了对抗战时期民众精神的感召动员效力。吴祖光则认为,得益于“猿人”这一角色的存在,《北京人》便具备了激励人心、引人向上的现实功用。有鉴于此,吴祖光便尽情抒发了对“猿人(北京人)”的感佩和崇仰,而不及其余。归根结底,吴祖光之所以将“远古北京人(中国猿人)”这一形象拔高、强化为话剧《北京人》中无可取代的光芒万丈的主角,实际上还是基于让戏剧艺术“淬励人心”进而提振全民族抗战精神的考量。《北京人》中的“猿人”,无疑是中国人历史血脉的源头,就此来看,吴祖光大力推崇的“北京人”形象,恰恰高度契合着“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主张,“北京人”就是抗战戏剧家“向历史上”寻绎、提炼出来的能够担当“抗战利器”的“材料”。
(2)了解渗透到有机化学中的一些无机物体现的性质和用途,以及化学反应。Cl2、Br2、Na、NaOH、Na2CO3、CO2、HNO3、H2SO4、H2S、CuSO4、NH3·H2O、AgNO3、KMnO4等无机物都在有机化学中有相关的应用,这其中当属 Br2、NaOH、H2SO4和KMnO4应用最为广泛。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已经涉及这些方面,要引起关注。
三
1942年2月1日第4版的《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刊有评论文章《我发见了舞台上的孩子——看了〈表〉的演出之后》,署名“吴祖光”,摘录如下:
致力于儿童剧,无论在编剧,导演,表演,装置等等方面,我以为首先有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要认清儿童与成人不同的特点;假如儿童而说大人话,作大人事,则又何异于大人?其实这正是最简单的基本要求;一句话就是舞台上的孩子要像孩子。做不到这点,就谈不到儿童剧。
固然现在的确有许多孩子颇有大人气,然而这就牵涉到这种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种教育是有病的教育,所以这种孩子变成了有病的孩子,不足为训。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我以前所看到的几个儿童剧的演出,都犯了这种毛病的缘故。但是如今我却意外地得到一种满足,终于在舞台上发现了我“熟识”的孩子,像是他们引我回到记忆的宫殿,他们不再使我感到生疏,那是在我看到了本月份在抗建堂的《表》的演出之后。
《表》的演出,为儿童剧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是一件成功了的工作。
纵使撇开“儿童剧”的立场不谈,《表》亦是一个完整的演出。导演的安排,演员的表演,布景的装置,都得到一致的协调。
导演的手法值得夸赞,从开始到结尾都保持简捷而明快的调子,没有牵强,没有生硬。导演儿童剧想来该是一件极艰难的事,这导演不但必须具有对儿童心理及生活的深刻认识,而且更要有惊人的忍耐;征于这次演出上的面面顾到,找不出破绽之处,导演的确尽了他的任务,而得可宝贵的收获。
演员都是育才学校的小朋友。育才学校有“天才学校”的美称,就是它的教学方法没有死板的范围,而是就学生天性所近因材施教的,这当然是进步的方法。这次《表》的演出不啻是它的成绩展览,使社会上对这个新兴事业团体一向毁誉参半,莫名究竟的模糊心理,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以前我所担心的,是怕这群小朋友有可能为他平素所学的理论功课磨成了“望之不似”的小大人。然而在看了这次演出之后,我是释然于胸了。最宝贵的,不同于常见的所演过的许多儿童剧的,就是他们都保有儿童应有的天真,而且在舞台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次演出之所以成功,这一点实在是一个决定的力量。从小扒手裴七一直到他的许多小朋友,都在舞台上表现得栩栩如生,自然生动而可爱。在台辞的诵读方面丝毫没有像以往儿童剧常犯的像“读书”的毛病。所有情节的发展与转折都交代得明白清楚,决不含糊;教人看得出来优秀的导演需要优秀的演员才能配合,才能相得益彰。我认为这也是育才的天才教育的成功。
…………
…………
为了使剧本更完整,我有两点意见:第一是民族化问题。自然《表》的原本是外国的,然而我们既然把它改成中国戏,就该尽可能地弄得它像中国事情;这些孩子们或多或少地都带点非中国的神气,最轻而易举可以改好的:我们为何不把小扒手偷了一块蛋糕改为偷了一个馒头,更使中国人看了觉得亲切呢。还有那个警察谭开球,也不像是中国警察。我们所看见的中国警察对待穷孩子的方法大概不是这样的;虽说警察也是人,各有不同的个性,然而我们不该写出一个一般中国警察的典型吗?
第二是儿童剧的口语问题,这是儿童剧的根本问题,在《表》的剧本里也不能免掉这方面的毛病,就是:不免仍旧有许多不是小孩子说的话由小孩子说出来。也许有许多意思非儿童的日常口语所能表现,然而儿童不是仍有他们的生活吗?仍旧有时生活得相当复杂吗?所以剧作者非得去跟儿童学习说话不可,他们一定有他们最活泼的能代表各种意见的语言的;这点困难如果不克服,儿童剧就仍旧不成其为儿童剧。说到这里,举一个例罢,譬如“儿童剧”这三个字就不是孩子的话,假如改成孩子口语的话,我们应该改成“孩子戏”或“小孩儿戏”才更适当。
除去这一点小毛病,《表》真是成功的演出,其实说来平常,就是各方面都像孩子,没有大人气。这有什么不能办到呢?致力于儿童剧的朋友要认识这起码的一点。
如果说《读〈北京人〉——我们是第二代的“北京人”》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的话,那么《我发见了舞台上的孩子——看了〈表〉的演出之后》则是一篇较为标准的剧评文章。吴祖光此文评论的是著名儿童戏剧家董林肯的代表作《表》。在正式介绍吴祖光的评论意见及《表》的价值意义之前,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现代儿童戏剧的发展脉络。
现在普遍认为,1919年11月14日郭沫若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独幕剧《黎明》是中国儿童戏剧的开山之作。《黎明》描写了一对从海蚌中跳出来的光洁的小兄妹,他们载歌载舞,努力唤醒更多的兄弟姐妹,一起去迎接新生。尔后,被称作“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的黎锦晖开始把音乐、舞蹈、诗歌等元素融入儿童戏剧,创造出了更加契合儿童欣赏习惯的“儿童歌舞剧”这一崭新的艺术样式。初创期的儿童戏剧,以神话剧、童话剧为主,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在艺术风格上,儿童戏剧多带有强烈的浪漫抒情色彩,富含象征意味,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旨在“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达到“人的根本改造”[9]。抗日战争爆发后,儿童戏剧创作和其他各种类型的艺术门类一样,开始汇入“民族救亡”“抗战建国”的时代潮流中,涌现出了如于伶《蹄下》、陈白尘《两个孩子》、许幸之《古庙钟声》等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与初创期相比,抗战时期的儿童剧创作多以“小战士”“小英雄”“流浪儿”为主角,写实倾向日渐突出,早期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戏剧风格被浓郁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色彩取代,“中国儿童戏剧初创期的‘儿童本位’创作理念被搁置起来,儿童戏剧的政治性、宣传性、教育性得到空前加强”[10],结果,儿童戏剧最重要的主体和本质——“儿童”,就遭到了严重忽略,儿童戏剧与成人戏剧之间的界线越发模糊。
董林肯(1918—1982),江苏昆山人,中国儿童戏剧运动的创始人、领导者。董林肯的戏剧活动始于学生时代,1938年在昆明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剧团——昆明儿童剧团,创作并导演了街头剧《难童》、三幕抗战儿童剧《小间谍》《小主人》等,轰动一时。戏剧《表》的原作者是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后由鲁迅译成中文,1941年董林肯将之改编成戏剧。该剧主要情节是:流浪儿裴七在拘留所里偷了醉鬼顾大爷的金表。之后,他被送进保育院。后来顾大爷来向裴七讨还金表,大家为裴七叫冤,使裴七良心受到谴责。同时,案犯“独眼龙”从狱中逃出躲进保育院,正当“独眼龙”要抢走金表时,大家将他捉住。接着,警察送来了一个小女孩,其母因无钱治病死了,其父就是顾大爷,这使裴七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终于把金表还给顾大爷的女儿。最后,裴七当选为模范儿童。
董林肯改编的《表》以儿童为表现主体,在实际演出时,也时刻考虑、注意并遵循儿童在语词、表情、体态等方面的特征,避免使儿童戏剧与成人戏剧相混淆。而如前所述,抗战时期的儿童戏剧竭力配合抗战时期民族国家的宣传教育任务,儿童戏剧的独特性丧失殆尽。因此,吴祖光在看到了董林肯改编的《表》后,欣喜地表示终于在抗战儿童戏剧的演出舞台上“发见了孩子”。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重庆后,于1941年上演了《乐团进行曲》《秃秃大王》《猴儿大王》等多部直接表现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戏剧,轰动山城,广获赞誉。但新安旅行团总结演出经验时,曾自我反省:“成人化”与“差不多都是汉奸,聪明的小孩,和最后的胜利”[11]的公式化现象,是当时儿童剧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剧普遍存在的“成人化”倾向相比,《表》最大的成功便在于维护了儿童戏剧之儿童本体性,而导演手法、演员表演以及舞台装置布景,在吴祖光看来,则是《表》取得成功的三个关键因素。虽然在文章末尾,吴祖光提出了《表》还应该在“民族化”和“口语日常化”方面有所加强,但总体来说,置身于抗战时期儿童戏剧被各种“大观念”“大形象”统摄的背景下,董林肯改编的《表》毫无疑问显示出全新的风貌,“为儿童剧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如果说,曹禺《北京人》中的“猿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系所在,那么《表》中成功规避“成人化”的儿童群像,则可视作每个中华儿女个体的起源。“猿人”是戏剧家向民族历史上寻找到的“材料”,儿童则是戏剧家向个体历史上寻找到的“材料”——归根结底,吴祖光在此盛赞的还是一种“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戏剧创演路径。并且,“猿人”聚集着整个民族的昂扬向上热气,儿童则保留了民众个体的纯真乐观心态。就像激赏“猿人”形象,便意味着向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众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能量一样,吴祖光之所以欣喜地为“发见了舞台上的孩子”而欢呼,也是为了将纯真乐观的儿童心态接续到抗战时期的时代氛围中,以之来提振感召民众。
四
抗日战争,既是现代中国的一段极为痛楚且关键的历史阶段,也全面重塑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演变格局,特别是戏剧这一独特的文艺门类,更是被赋予了千钧重任和无上荣光,由此造成了抗战戏剧的繁盛局面。抗战戏剧,不仅数量巨大、势头强盛,更与复杂的抗战历史文化紧密绾合在一起,结果抗战戏剧在繁盛之外又增添了繁杂的面影。要洞悉和理解抗战戏剧的繁复面影,可借助“文学生活研究”这一视野方法。所谓“文学生活研究”,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充分关注和考察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12],而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占有使用则是这一关键环节的基础。本文披露的吴祖光发表于《中央日报》上的三篇戏剧评说类集外佚文,正是抗战戏剧当事人在历史现场中的发言表态,是切近抗战戏剧历史现场、深入认识抗战戏剧繁复面影的重要史料。
抗日战争期间,民众动员成为文化工作者肩负的主要任务,为了有力且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人们多方位出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传统元素的利用改造便是其中广受青睐的途径。譬如,江苏文人创作的抗战民歌,便将抗战的政治符号嵌入传统民歌,进而重构民众的政治文化,增强民众的革命认同感[13]。同理,抗战时期众多历史戏剧的涌现也是重构传统的家族成员。《抗战历史剧》《读〈北京人〉——我们是第二代的“北京人”》《我发见了舞台上的孩子——看了〈表〉的演出之后》,这三篇吴祖光发表于重庆版《中央日报》上的集外佚文,均显露出在抗战的彼时彼地回望、言说传统的策略,此即所谓“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戏剧编演路径。《抗战历史剧》类似于“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戏剧编演路径的总纲;《读〈北京人〉——我们是第二代的“北京人”》《我发见了舞台上的孩子——看了〈表〉的演出之后》则是“向历史上去找材料”的戏剧编演路径的具体指向,前者是从民族的历史脉络线上去“找材料”,后者是从个体的历史起源上去“找材料”。不论去哪个“历史”上“找材料”,最终目的都是用这些历史上的“材料”来辅助现实中的“抗战”,是以“历史材料”编就的戏剧故事来“淬励”抗战烽火中苦行且勇毅的中华儿女的人心精魂。
按理来说,本文收集的这三篇文章所谈论的问题和所涉作家作品,都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内容,不是冷门话题,吴祖光更未使用什么冷僻的笔名,此类文章不应该被吴祖光各类作品资料集的编选者无视。本来是谈论热点话题的文章却沦为了集外佚文,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吴祖光这三篇文章都发表于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副刊上,编选者或许顾虑《中央日报》这一背景,便先行判定吴祖光这三篇文章内容“不当”,因而有意漏收之。事实上,虽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日报》所刊发的文章都是“反动”“落后”的,具体到重庆版《中央日报》,更可以在其上发现大量提倡抗战、激励民众的进步文章。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普遍加入民族国家反抗的大合唱中,重庆版《中央日报》恰恰在这一大合唱中迸发出了十分嘹亮的高音。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从“卢沟桥主题艺术运动”的策划到联合作家们团结起来成立“文协”等全国性组织,都可发现重庆版《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台前幕后主导的身影[14]。吴祖光这三篇“淬励人心”的集外佚文首发于重庆版《中央日报》,无疑是《中央日报》及其副刊有力参与抗战文艺生成、壮大过程的明证。对于研究者来说,如若从后设的单一政治立场出发来看待过去,极有可能一笔抹杀《中央日报》的历史价值,将吴祖光这三篇重要的集外佚文“打入冷宫”。此类片面的思维方式,显然只会严重损伤繁复多姿的历史景致,理应对之严加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