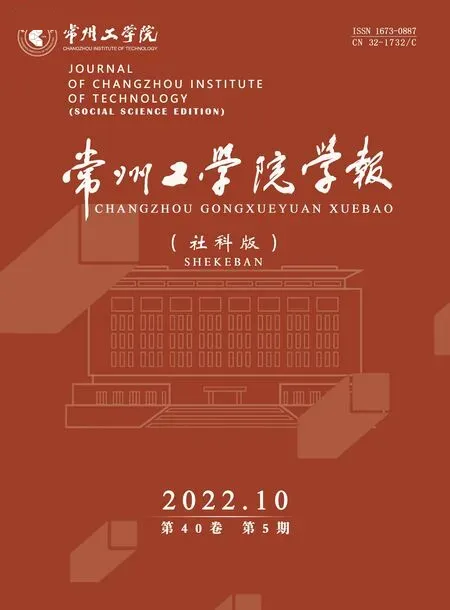萧纲诗歌中的影意象研究
李艺蕴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诗歌中的影意象,经历了由实体物象到虚化符号的嬗变。其间,有关影意象自然属性的描写逐渐淡化,它在不断传写中被赋予了多层人文内涵。本文试图探究萧纲诗歌中影意象的类型、形成缘由,并发掘其价值所在。
一、萧纲诗歌中影意象的类型分析
萧纲喜爱写影,也擅长写影,他笔下的影种类繁多,共计20种,包括花影、珠影、旗影、日影、舆影、树影、人影、山影、弩影、帘影、叶影、月影、烟影、栏影、电影、鸟影、藤影、灯影、楼影、镜影。下文对其诗中出现次数较多,成就较大的天文类影、植物类影、状物类影和人物类影进行详细解读。
(一)天文类影
萧纲诗歌中共有10处涉及天文类影。按照其写作目的可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用影直抒胸臆,歌颂日月等,主题十分明确。如《咏朝目》中的“光随浪高下,影逐树轻浓”[1]1971,写阳光投向水面,日影随着波浪的起伏而忽高忽低地晃动,随着树木的疏密而或浓或淡地变幻。作者以日影逐树表现阳光随物而移、变幻不定的特点,笔法灵活跳跃。再如《望月诗》中的“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1]1972,连用比喻,语意通俗,对仗工整。“九秋霜”将缥缈的影子化虚为实,利用通感极力凸显月影的皎洁清冷。第二类是用影营造诗境。有的以影为环,推进诗歌中的时间进程,如《晚日后堂诗》:“幔阴通碧砌,日影度城隅。岸柳垂长叶,窗桃落细跗。花留蛱蝶粉,竹翳蜻蜓珠。赏心无与共,染翰独踟蹰。”[1]1955诗歌由远及近一步步展开画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逐渐聚焦,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远方的城隅日影,近处的岸边柳树、窗边桃花,最终定格在抒情主人公身上。整个视野转移的过程环环相扣,其中,“日影度城隅”展现了时光流逝的缓慢过程,暗示抒情主人公已踟蹰良久,无以慰藉。全诗时空转换十分自然,所选日影意象明显经过作者缜密构思。后世诗评家已注意到了萧纲此类诗歌,并对其写影隽句多予品扬,如明人陈祚明在其《采菽堂古诗选》中曾评价“丝条转暮光,影落暮阴长”(《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句“写日影笼葱,大佳”[2]716,“镜澈倒遥墟”(《玩汉水》)句“丽语兼以生致”[2]711。
(二)植物类影
萧纲诗歌中共有12处涉及植物类影。古往今来,花草树木作为审美客体受到无数文人墨客的青睐,其中花影意象作为花意象的派生,既有花意象优美动人的特点,又有影意象含蓄委婉的意味。这在萧纲的《苦热行》中就有很好的体现,如“云斜花影没,日落荷心香”[1]1908描写了盛暑苦热之状:浮云斜挂,短暂地遮住了骄阳,花朵下的阴影消失殆尽,夕阳西落,荷花散发出缕缕清香。全句并无“热”字,却通过“花影没”等进行侧面烘托,形象地展现了夏日之酷热。作为较早运用花影意象的文人之一,萧纲并未仅关注花影清丽婉约的表面,他运用拟人手法,通过花影赋予花灵动的活力。花若有心,影当含情,这就比同时代大多数单纯咏物诗歌略胜一筹。如《纳凉诗》“落花还就影,惊蝉乍失林”[1]1946中的“就影”一词,有意赋予落花感触,好像它也因天气炎热想要像人一样避暑,所以依偎花影而栖,塑造了落花自惜、惹人怜爱的娇憨之状,既紧扣纳凉主题又使得诗境瞬间鲜活起来,将形与影之间的亲密关系呈现得生动而逼真。除花影外,萧纲还有写树影、叶影、藤影的诗句,都能较好地与诗歌整体氛围融为一体,如《仰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诗》“水观凌却敌,槐影带重楼”[1]1966句虽为作者巡城时信手拈来之作,却用影巧妙,暗藏玄机:槐影像衣带一样环住万千高楼,既照应了前诗帝京暮秋的肃杀之气,又象征着士兵昂扬的精神风貌,达到了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的创作目的。
(三)状物类影
萧纲诗歌中共有12处涉及状物类影。这些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萧纲真实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如他有3处写到旗影:“羽旗承去影,铙吹杂还风”[1]1936(《旦出兴业寺讲》),“风旗争曳影,亭皋共生阴”[1]1930(《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诗》),“苍龙引玉轪,交旗影曲旃”[1]1943(《和藉田诗》)。3句均以纪实手法再现了帝王之家出席活动或举办宴饮时的盛大场面。然而萧纲并未完全沉迷于物质享受,他通过诗歌中部分状物类影流露出了生命忧患意识。如《咏笼灯绝句诗》:“动焰翠帷里,散影罗帐前。花心生复落,明销君讵怜。”[1]1974诗人由眼前灯影联想到了灯笼彻夜燃烧,天亮后却无人问津的凄凉,表达了哀怨苦楚的情感。萧纲虽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帝王,但他生逢更替迭代、动荡不宁的乱世,由灯笼无人在乎,被利用后就随时可能被抛弃引发了无限感慨。萧纲《卧疾诗》首句“沈痾类弩影,积弊似河鱼”[1]1945以影入典,也是在暗示自己现实生存状况的艰难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深切担忧。“弩影”出自汉应劭的《风俗通·怪神·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晋书·乐广传》也有类似记载。文中杜宣看到杯中弩影似蛇感到害怕,却因地位卑微,屈服于应郴的权势而被迫饮下杯中之酒。同样,萧纲表面上地位至高无上,实际大权旁落,受人摆布。杜宣这种身不由己、看人脸色行事的社交场面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亦会出现。萧纲引此典故足见他当时身心受到折磨。“弩影”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诗词中胸腹顽疾的代称。
(四)人物类影
萧纲诗歌中共有6处涉及人物类影。他笔下的人物类影往往婀娜多姿,带有很强的女性化特征。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3]113一方面,他作诗并不是为了传播大道,而是主张娱心,要大胆地追求美的享受。所以他常以娱乐的态度物化美人,并细致描摹其方方面面,包括与美人随行的影。《咏舞诗二首·其一》中有“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1]1942句,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赏心悦目的瞬间画面,围绕舞女表演时扇开影乱的动态美进行描写,以达到放松心情和愉悦情感的效果。再如“拂镜弄影情未极,回簪转笑思自亲”[1]1980(《歌》)句描写歌伎拂镜弄影、回眸一笑的娇媚姿态,也是从女性最吸引人的特征入手描写。影随形,写影的最终目的在于写形,作者简化细节,以影之美来衬托形之美。另一方面,“文章放荡”又要求诗歌放浪豁达,抒发真情。如《同庾肩吾四咏诗二首·其二·照流看落钗》中的“流摇妆影坏,钗落鬓花空。佳期在何许,徒伤心不同”[1]1964句描写女子临水照影、步摇掉落、倒影破碎的场景,由此产生的情思,视角独特,富有故事性,其中的“影坏”“花空”既是写景,又暗喻佳期无果。诗人将自己化为怀春佳人,设身处地地摹写女性大胆渴望爱情的心理。此间影意象已融入作者的情感体验,具有悲剧意蕴,诗人不再仅把女性的影当作美的物体来简单摹写,因此诗作看似格调不高,读来却情意绵绵。萧纲以艺术的手法描绘影,融情于影,在中国古典诗歌写影史上留下了值得称道的一笔。其诗中的影意象反映了文人对女性世界独特视角的观照。袁行霈先生曾言:“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 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4]萧纲诗歌中集中出现的人物类影意象正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
二、萧纲诗歌中影意象的形成缘由
(一)对先秦散文中影意象的继承
影意象最早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老子》河上公注:“心善渊,水深空虚,渊深清明。与善仁,万物得水以生,与虚不与盈也。言善信,水内影照形不失其情也。”[5]河上公赞美水影诚实可信,将事物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这里的影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简单观照。《管子》中的“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6],《列子》中的“关尹谓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7],亦是借用自然现象来说明社会现象,其中的影是一种因光而生的虚像,没有象征意义和过多的情感寄托。这类影在萧纲的部分诗作中存有,如《水中楼影诗》:“水底罘罳出,萍间反宇浮。风生色不坏,浪去影恒留。”[1]19764句全是对所见之象的客观描绘,艺术成就不高,但作者独具慧眼,选取影作为独立诗材,尤其是“风生色不坏,浪去影恒留”句,表面上是写风吹波动,水流浪溅,楼影摇曳水中,流水不能将其冲去的自然景象,实际上却与先秦散文一样富有理趣。色、影是佛家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色是不实的,影也是虚幻的,但“风生”“浪去”而“色不坏”“影恒留”,这不正是佛家所追求自性清净吗?在佛家看来,物我是非,都不过是心的产物,只要明心见性,梵我合一,那么色坏与不坏,影留与不留,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瞬息的亦可永恒,虚幻的亦显真实。
(二)写影风气的影响
南朝已进入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佳句云集,众多诗人开始关注影意象,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诗作中就出现过月影、鸟影、石影、云影等。同为齐梁咏物诗创作的中坚人物,萧纲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沈约的影响。诗作内容上,有描写月影的诗句,如“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1]1972,有描写鸟影的诗句,如“孤飞本欲去,得影更淹留”[1]1973等。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两人也颇有相似之处。如沈约《豫章行》中的“双剑爱匣同,孤鸾悲影异”[1]1615与萧纲《金闺思二首·其一》中的“日移孤影动,羞睹燕双飞”[1]1969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诗都运用了反衬的表现手法,以双衬单,更显孤影之悲怆。除沈约外,与萧纲交往甚密的文人在诗歌创作中也大量选取自然景物的影像进行描绘。他们还经常以影为主题进行诗歌唱和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写影兴趣。如萧纲《山池》中有“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1]1933句,写诗人赏玩傍晚山池景色。王台卿、庾肩吾、鲍至、庾信皆写影与萧纲相和,如王台卿《山池应令》中的“长桥时跨水, 曲阁乍临波”[1]2089,庾肩吾《山池应令》中的“水逐云峰暗, 寒随殿影生”[1]1986,鲍至《山池应令》中的“树交楼影没, 岸暗水光来”[1]2024,庾信《奉和山池》中的“荷风惊浴鸟, 桥影聚行鱼”[1]2354。再如,萧纲《咏舞二首·其一》中有“扇开衫影乱”[1]1942句,刘遵、徐陵各有“影逐相思弦”[1]1810(《应令咏舞》)、“烛送空回影”[1]2529(《奉和咏舞》)句与萧纲桴鼓相应。萧纲《汉高庙赛神》中有“日正山无影,城斜汉屡迴”[1]1943句,刘遵、王台卿均有《和简文帝汉高祖庙》诗,分别以“霓裳影翠微”[1]1809和“树出垂岩影”[1]2088呼应萧诗。总之,萧纲笔下众多的写影句反映了当时写影蔚然成风。他在《倡楼怨节》中的“片光片影皆丽”[1]1941句,可形容该时期诗歌写影的盛况[8]。
(三)佛学思想的渗透
萧纲之父萧衍曾多次遁入空门,其母丁令光也常年食素,精通佛理。萧纲成长过程中,佛学氛围浓厚,因此他与不少僧侣禅师交往密切,他本人也经常出席宗教活动。萧纲诗歌中直接阐释佛教教义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萧纲本人对佛理有一定见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大为兴盛。影除了作为自然现象(阴影)和视觉形象(倒影),在佛经里更象征着佛陀的法身。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记载了佛影修行的具体方法:“佛灭度后,佛诸弟子,若欲知佛行者,如向所说;若欲知佛坐者,当观佛影。观佛影者,先观佛像,作丈六想,结加趺坐,敷草为座,请像令坐。见坐了了,复当作想,作一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清白石想……”[9]由此可见,影成为修佛者修身冥想的对象。除上文提到的《水中楼影诗》外,萧纲《十空诗六首》中的“息形影方止,逐物虑恒侵。若悟假名浅,方知实相深”[1]1938借现实中形与影的关系对佛教的核心问题——色与空进行了探讨:追逐物欲就会有不尽忧虑,这种忧虑像影随形般相伴而生,至死方休。“假名”和“实相”是佛教用语,前者指虚妄的概念、语言,后者指宇宙事物的真相或本然状态。这一真一假、一实一虚,也如形影关系耐人寻味。再如萧纲的《咏烟诗》:“浮空覆杂影,含露密花藤。乍如洛霞发,颇似巫云登。映光飞百仞,从风散九层。欲持翡翠色,时吐鲸鱼灯。”[1]1956此诗虽不是专一写影,但影意象却颇有深意。首句“浮空覆杂影”写烟漂浮空中遮蔽了杂乱的影子,后又用“乍如”“颇似”“欲持”“时吐”等词,及“从风散九层”,强调烟变化无端。整首诗描绘了一个千变万化最后归于虚空的景象。烟飞灭之后杂影仍在,相较之下,它的存在状态还不如本就极虚的影,这种转瞬成空的极度无力感似乎让命运同样变化无端的萧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0]。以“影”入诗不仅是萧纲在诗歌运用新鲜意象上所做的积极开拓,契合了他好为新变的文学主张,更反映了他善于从宗教角度思考世界和人生的态度。
三、萧纲诗歌中影意象的贡献
(一)有意为影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萧纲作品近300首,其中包含影意象的诗作有52首,超过总数的1/6。在萧纲之前,描写影意象的诗人及其诗作数量分别为:阮籍4首,傅玄12首,张翼3首,陆机8首,曹植3首。同时代的情况为:萧泽28首,庾信20首,庾肩吾11首,刘孝威6首。除上述举例外,其他诗人的写影句在数量上远不及萧纲。萧纲在诗歌中对影的大量描写并非无意为之,他有意营造一个庞大斑斓的影世界,以影作为自己诗中的独特意象。他的写影宗旨可概括为格局远大,落于细微。他曾说自己为文时“近则潘陆颜谢”[3]115,但他并未照搬前人移步换景、力求场景宏大的固有模式,而是有全新的审美追求。如《晚秋诗》“乱霞圆绿水,红叶影飞缸”[1]1957句,作者把关注点放在细微事物上,将取景框对准水中霞光,以缸中叶影见微知著,反映晚秋这一宏大主题。全句从距离、速度、重量多重维度构筑晚秋氛围,功力极深。
(二)寓目写心
萧纲为创作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时常被人诟病为词藻靡丽、感情苍白。由于佛思的融入,萧纲笔下的部分影意象已开始脱离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创造了别样的情感内蕴。他仿佛局外人一般,置身事外专心描摹,总能发现特定环境下影的细微差异。如“促阴横隐壁”[1]1947(《秋晚》),“疏槐未合影”[1]1933(《饯庐陵内史王修应令》),“细树含残影”[1]1952(《晚景出行》),这3处分别表现了影短、分、疏的不同特点。对这些影,他不像以往的诗人那样作共情式的“赏”,而是作静心体察式的“观”,因此他的刻画才格外精细。这些影没有任何附加意义,只是作为景物的一部分被记录下来。因此《秋夜诗》中的“乱霞圆绿水,红叶影飞缸”[1]1957并未表达悲秋情怀,他笔下的秋令人舒心闲适,诗中的影与其他景物一起,客观再现作者一直追求的不为外物所动的平和的心灵状态。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指出创作要“寓目写心”[3]114,说明诗人不重可见之物,注重透过表象来明心见性。这样就无需借影抒情,因为无论眼前是否有影或者究竟为何影,他真实的情感都是平淡内敛的。后世王维诗歌中的影意象与萧纲笔下的影意象有一脉相承之处。
(三)影响深远
北宋的张先因写影出色而有“张三影”的美称,其不少诗词作品都有萧纲写影的痕迹,如其《天仙子》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11]23与萧纲《苦热行》中的“云斜花影没”[1]1908无论在意象组合还是诗境构造上都有相近之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评论说:“‘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12]44民国诗人沈祖棻也曾道:“其好处在于‘破’‘弄’二字,下得极其生动细致。”[13]由此我们得见张先修词炼字的造诣。其实在诗词中使用“弄影”一词并非张先首创,萧纲在《歌》中已用此词形容舞女身姿曼妙,只不过张先使用拟人手法做了更深层次的开拓。再如,萧纲《晚景纳凉诗》中的“珠帘影空卷”[1]1946与张先《归朝欢》中的“帘押残花影”[11]99,两位作者都以帘为媒介陪衬影意象,影在帘上,所以有了柔软朦胧的特点。此外,萧纲《汉高庙赛神诗》中的“日正山无影”[1]1943与张先《木兰花·其六·乙卯吴兴寒食》中的“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11]58,都塑造了无影之影。
影作为一个特殊物象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会受到光的影响。导致无影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光线过强,二是光线不足。从“日正”和“月色正清明”可看出,这两首诗词中的无影都属于第一种情况。萧纲诗中的山无影是为了凸显日光的灿烂,张先词中的花无影是为了凸显月色的澄澈。两人都是明写影暗写光,光影和谐,相得益彰。山无影暗示山高大巍峨,花无影暗示杨花轻盈通透。经过萧纲的创新性引领,影才得以成为张先等众多诗人争相雕镌的诗眼,影意象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宋词影响深远。
——《花影》(水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