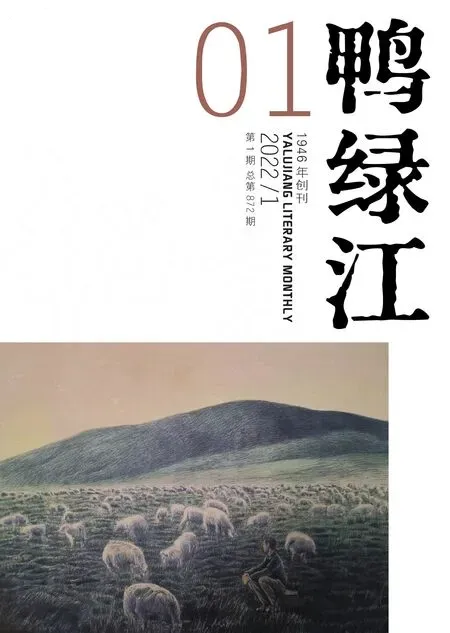消失的年糕和豆腐
出生与成长在辽西努鲁儿虎山深处的我经常吃两样东西:年糕和豆腐。以1984年我离开我的小山村郝家沟走进城市为分界,我吃年糕、吃豆腐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这两种食物的制作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品质判截然不同,内涵更是大相径庭,吃起来感觉当然就完全不一样。前一个阶段是品味,是享受,甚至是仪式,再进一层,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性的、灵性的满足;后一个阶段就单纯是填饱肚子了。人类开发出的食物五花八门,可是我们经常吃的也就区区几种,豆腐便是最大众化、最普遍的食物之一。
事实上,进城后仍然经常吃年糕和豆腐。每当把豆腐或年糕吃到口中,我都会隐隐约约地产生一种遥远的怀念,有时甚至会有一种神圣感。同时我还会回想起两样现在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生存工具:碾子和磨。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体或者说精神家园多如星辰,如孔子的杏林、周敦颐的濂溪、王阳明的龙场,如甲骨、青铜、青花瓷,而在我心底,碾子和磨也是其中之一。
1
我离开家乡进城时,郝家沟只有20多户人家、90多口人,碾道和磨道位于村子中央。碾道与磨道,就是碾子房和磨房。为什么叫“道”,直到现在我也没搞出确切答案。是来源于老子和孔子的道吗?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点点意味吧。
碾子和磨,是蒸年糕与做豆腐最重要的工具。蒸年糕与做豆腐是春节最重要的两项内容,可以与杀年猪相提并论。年糕的原料是大黄米和芸豆。黍子是中华民族种植了好几千年的古老农作物,大黄米就是它的果实。蒸年糕的主力军是母亲,我和妹妹是小跟班儿。母亲在供奉天地的天地牌前点上香,拜三拜,然后淘米。接下来是一幅至今在我眼前仍然栩栩如生的画面——母亲、我、妹妹一起向碾道进发。我牵着小毛驴,驴驮米袋子,母亲和妹妹拿了好几样东西,包括大簸箕、箩、笤帚、铲子。脚下是覆盖着白雪的村路,咯吱咯吱地响着。不远处有房舍,有农田。稍远一些,有苍苍莽莽的远山。村里有狗吠鸡鸣,有小孩子高喊低叫。村外有不知名的鸟的呢喃,甚或有不知哪种小兽的呼喊。
进碾道,套上驴,轧面工作开始。把大黄米铺在碾盘上,由驴拉着碾轱辘不停地转。驴走的是一条很短却又没有尽头的路,需要用捂眼儿把它的眼捂起来,让它看不出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大黄米本来是金黄色,轧破后变成了白中带黄。大黄米本来就有一种香味儿,这时香味儿会更浓。轧到一定程度,母亲开始箩面。把轧过的大黄米铲入箩中,往大簸箕里箩。箩一阵后细面没有了,剩下的揚到碾盘上继续碾轧。这样不断地箩,大簸箕里面越来越多,两个多小时后,一袋子大黄米都变成面粉了。我帮母亲把面粉装入口袋,让驴驮着回家。
离郝家沟两公里的大队部有碾面机房,由电动机带动碾面机,几分钟就能把上百斤大黄米碾成面粉,特别方便。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不用碾面机碾,而是用碾子轧。母亲说用碾面机碾赶不上用碾子轧好吃。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不知道。之后不久,我就弄明白了,碾面机里有一个转盘,转盘上有密密麻麻的铁棒,在电动机的带动下高速旋转,铁棒把大黄米活生生打碎,同时转盘转动产生气流,把大黄米面吹向出口。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刚出碾面机的大黄米面会热得烫手。热来自大黄米跟铁棒之间的撞击,产生热了,意味着大黄米的分子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
到家后立刻开蒸。蒸年糕有很多讲究,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人蒸的年糕一个味道。蒸年糕分凉锅蒸和热锅蒸。先说凉锅蒸:在锅里添上水,放上蒸帘,在蒸奁上铺一层煮到八分熟的芸豆,把大黄米面淋上水,搅拌均匀撒在芸豆上,然后把锅盖得严严实实,开始烧火。大约一个多小时,年糕便蒸成了。再说热锅蒸:在往蒸帘上铺芸豆时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在水蒸气向上呼呼冒的同时把大黄米面往芸豆上撒。面很快会改变颜色,由雪白变成金黄。面粉撒得要均匀,达到一定厚度时能清楚地看出哪里薄哪里厚,因为薄的地方蒸气冒出得较多。这时就要往薄的地方撒面,以使蒸气不至于从那里跑掉,使整锅年糕均匀受热。待面的厚度达到五厘米左右时把锅盖上,再烧一段时间火便大功告成。
年糕出锅后,我立刻切下一块吃,大多数时候会蘸上红糖水。一定是蘸红糖而不是白糖。年糕是热性极高的食物,红糖为阴性,对年糕的热性具有中和作用。红糖甜味是含蓄的,不像白糖那样浓烈,不会把年糕的香味遮盖掉。
这就是我最最钟爱的年糕。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没有哪种主食比这样的年糕更有味道。年糕是金黄色的,芸豆是红色的,首先色彩就特别诱人。入口糯糯的又很筋道,既清香又浓醇。进城后,我吃过很多五花八门的年糕,却觉得没有一种能跟郝家沟的大黄米年糕相提并论。有时我甚至认为那些年糕根本不配叫年糕,管那样的东西叫年糕是对“年糕”这个词的一种轻蔑。
2
那时我家有一样活计一定是由父亲承担——做豆腐。父亲几乎从来不做饭,做豆腐却一定亲自动手。母亲也会做,但父亲认为母亲做的不好吃。这天父亲起得很早,在天地牌前礼拜,然后去碾道,把几十斤黄豆碾轧一番,回到家后把黄豆放在簸箕里,端着用力晃,脱落的豆皮会浮到最上层,父亲把它们弄到一边,剩下的就是没有皮的豆瓣儿。把豆瓣儿装进水桶泡上,然后去磨道。父亲挑着沉重的豆瓣儿担子,我拎着一个空水桶,妹妹牵着驴,拿着一把勺子。
套上驴,给驴戴上捂眼儿,让它拉着磨转圈儿,磨豆浆的工作正式开始。我知道大队部有打浆机,很多人做豆腐都是用打浆机把黄豆打成豆浆,方便快捷得很。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用打浆机,父亲说用打浆机做出的豆腐没有豆腐味儿。
大约两个小时后,豆浆磨成,回到家立刻进行下一道工序。在锅台上架起豆腐架子,铺好豆腐包,豆浆进一步稀释后舀到豆腐包上过滤。父亲告诉我,磨豆浆用的水和此时稀释豆浆的水必须来自同一口井,用两口井的水豆腐就做不成。最终留在豆腐包上的豆腐渣有好几斤,白白的,像雪面子一般。
接下来母亲生起火,开始熬豆浆。父亲把卤水放在锅台上,认真盯着锅里的动静。豆浆一烧开,立刻会向上沸涌,必须适时停火。温度降到一定程度,父亲用勺子舀起卤水,小心翼翼地往豆浆里点。这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卤水点豆腐。父亲认为母亲做的豆腐不好吃,主要指她在这个环节掌握不好。这个环节包括豆浆的温度、点得快慢、多少,等等。没有诀窍,只能靠感觉。很多诀窍性的东西都是这样,用语言没办法描述。很快,絮状的豆腐脑出现,越来越多,浆水则越来越清。点到什么程度必须把握好,点老了豆腐会发苦,点轻了豆腐会太嫩,豆腐味不浓,口感太淡薄。一段时间后,父亲把勺子放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再看锅里,絮状物和浆水泾渭分明。
最后一道工序是把豆腐架子重新支起,把豆腐脑连同浆水舀到上面再次过滤。浆水渗出,豆腐脑则会留在豆腐包中。最后把豆腐包移到一块木板上,整理得方方正正,上面放上木板,用稍重一些的东西压上,以便多余的浆水继续渗出。压得不能过紧也不能过轻,过轻豆腐不实,过紧豆腐会过硬,不实或过硬都会影响豆腐的品质。
从早晨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豆腐终于做完。这天晚饭自然就有豆腐吃了。母亲做的是猪肉白菜炖豆腐。豆腐是一片一片的,形状完整,没有任何破损,用筷子夹起来会微微颤动,光洁而晶莹,放在口中咀嚼,又软又稍有弹性,味道美得无法形容。豆腐到底啥味儿?估计没有一个语言大师能清清楚楚地描绘。父亲烫一壶酒,提议我陪他喝两口。我说:“我可以喝酒了?”父亲说:“你已经是大小伙子,过年了,可以喝点儿。”我说:“好吧,喝点儿。”父亲拿来一个小酒盅,亲自给我倒上。我小心翼翼地抿一小口,又苦又辣,勉强咽下去,觉得肚子里像着了火。我咧了嘴,表情痛苦。我说:“这也太难喝了。”父亲说:“你觉得只有甜的香的好,说明你还没真正长大。真正长大了,你会喜欢苦味儿、辣味儿,甚至臭味儿,会知道甜和香是最简单的味儿,同时也是最经不起咂摸的味儿。”
3
进城后,我由地道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小市民。时光飞逝,眨眼间,十几二十几年就成了梦幻泡影。这期间,国家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变化不仅体现在城市,同时也体现在小山村郝家沟。
我进城后没几年,碾道和磨道就被拆掉了。碾子塌了,碾盘歪在基座一侧,碾轱辘滚到了十几米外。两片磨盘不再珠联璧合,而是相隔数米,无声相望。没有任何人管它们,冬天会被积雪覆盖,夏天会被野草掩映。也许只有我还惦记着它们,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在城市里吃什么都不可口,吃什么都没有感觉,总是回想用它们做出来的年糕和豆腐的味道。有时回到村中,我会到碾轱辘上或磨盘上坐一会儿,静静地回想那种质朴、浑厚和清纯,回味那种与当下截然不同的生活。
某年初秋的一天,因二叔家的堂弟结婚,我从省城赶回郝家沟。以前人们管大米白面叫细粮,把玉米、小米、高粱米叫粗粮。在细粮极少的年代,人们办喜事摆宴席主食往往是年糕,副食极为单调,豆腐自然而然地成了席桌上的主角。此时主食是大米饭,十多个菜中也有豆腐,是十多里外一户专门做豆腐的人用三轮车送来的。郝家沟所有人都是同宗本家,跟我坐一个桌吃饭的相互之间或为兄弟,或为叔侄,或为爷孙。大家一边吃一边说话,一项重要内容是评论哪个菜好吃哪个菜不好吃。关于豆腐,年纪稍大一些的都会说现在的不如以前的好吃了。
我突发奇想,有些突兀地提出一个建议:把碾子和磨重新支起来,用碾子轧大黄米面,用磨磨豆浆,蒸一锅年糕,做几屉豆腐。谁都能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一时间都不说话。我却觉得我的建议非常伟大,甚至为自己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激动得热血沸腾。我不想让这个建议成为泡影,开始跟他们做思想工作。我说:“你们都说这豆腐不好吃、没豆腐味儿,为什么不弄一些真正好吃的豆腐好好吃一回呢?过年我回来时你们说年糕不如以前的好吃了,为什么不蒸一回真正好吃的年糕呢?反正现在地里没啥活儿,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几个年轻的在外地工作,跟我一樣是特意赶回来的,说必须得尽快赶回去。我说:“大伙儿齐心协力,最晚到明天晚上就能把年糕蒸出来,把豆腐做出来,你们不是省长不是市长,晚一两天回去能有啥了不得的?”我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说谁不赞成我的建议,以后去省城我就不接待谁。最终,老少爷们儿同意了我的建议。
酒足饭饱后,工程正式开始。在离碾道和磨道不远的地方,选一块空地,平整好,以便把底座垒起来。不论是碾子还是磨都极为沉重,底座必须牢固。套上驴车,从大河套里运来石头,然后开垒。石头中间的缝隙必须用泥灌满,于是在几个人垒石头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弄土挑水和泥。一个远房哥哥是木匠,见不论是碾子还是磨上的木制构件都已老朽,于是量了尺寸,寻到木料后开始加工。
干到天黑时分,两个底座垒成了。晚上,老少爷们儿饭后聚到底座旁边,很随意地在石头上坐了,天南海北地闲聊。他们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吃喝不愁了,很多事情都比之前方便了。比如交通,公路已经修到村边,有班车直通县城;比如通信,村里已经有了手机信号。农活儿不像以前那样累了。以前夏天除草是重活儿,持续时间也较长,现在改成洒除草剂了。以前收割后要把庄稼的根刨出来,并把泥土砸掉,现在用上了灭茬机,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还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存款了。大伙儿也说到了生活中的不如意,比如大多数年轻人去城里了,不年不节时村里只剩下不到20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街上不再有小孩子跑来跑去,如此一来就少了生机、少了活力,甚至少了希望,因为照这样下去,等这一批老人没了,这个曾经近百人的村子势必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少爷们儿还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比起来,有点没意思了。比如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不论多好的东西,吃到嘴里都觉得没什么味道。不仅年糕和豆腐没有以前的滋味了,连大米饭、大馒头也吃不出以前的香甜了。以前吃一口肉能香得全身舒泰,现在呢?似乎没有任何感觉了。还有,生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方便,同时,也越来越觉得空落落的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十多个人就又聚到一起,用绳子把碾盘牢牢拢住,绳子上插五六根杠子,十多个人上阵,抬起来,慢慢地走向建好的底座。为了统一步伐,一个50多岁的叔叔还喊起了号子。众人踏着号子,走得平平稳稳。碾盘放上去后还要找平,木匠哥哥竟然用上了一个很古老的水平尺。接着,把碾轱辘抬到碾盘上,位置调整好,把木轴和木框装上,碾子的安装便大功告成了。磨比碾子轻一些,也很快安装完毕。接下来要把碾子和磨清洗干净,好多年不用了,上面积了厚厚的土。要让它们转起来,一边转一边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往上泼,同时还要用笤帚扫,最终还要轧一些玉米,磨一些玉米浆,冲洗不掉的土会被玉米面和玉米浆带走。
男人们安装碾子和磨时,几个女人已经把大黄米淘好,把黄豆备好,然后开轧开磨。这时碾子和磨周围已经聚了很多人,不但村里人全来了,连邻村都有人来看热闹。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本来想走,这时也留了下来。小毛驴拉着碾子磨走得四平八稳,几十人在旁边议论纷纷。一些人跟我聚到一处,说我的决定无比英明伟大,从昨天下午到现在虽然累了个够呛,但同时觉得特别轻松,此时此刻则有了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这天晚上又摆了宴席,主食是大黄米年糕,副食主要是豆腐,有炖豆腐和拌豆腐。炖豆腐分两种,一种里面加了肉,一种里面加了粉条。拌豆腐只加盐和葱花。吃第一口时我心中有一些忐忑,很怕吃不出那种深藏于内心深处的味道。可是当把豆腐放入口中稍加咀嚼后,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没错,这正是我好多年来特别想念的味道!也可以说,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的味道,也是那种已经消失的生活的味道,还可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味道。我拿一块年糕,轻轻咬下一小口,让它在嘴里慢慢滚动,感觉到的,同样是能渗透到骨髓深处的香醇。
这天晚上宴席一直摆到深夜,最终是把村里各家各户所存的酒喝光,一大锅年糕和近百块豆腐也所剩无几。大多数人喝醉了,有的随便找个地方睡觉,有的三五个聚在一起闲聊,有的坐在一边一声不响,有的跑到某个角落吐得一塌糊涂。但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好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宴席了。我也喝多了,但头脑还算清楚。我在村街上转了一圈,最终在碾盘上一直坐到东方发白。
4
某一年秋天,我去一个叫观星山庄的度假村参加会议,看到整个山庄的地面都是用碾盘和磨盘铺成,向工作人员打听,得知那些东西是老板从各处搜罗来的。我心中特别不安,觉得那属于我的碾子和磨也有可能被运到这里,成了垫脚石。在我心中它们是无比高贵的,当成垫脚石是对它们的亵渎。会议结束后不久,我驱车回郝家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的碾子和磨是否还在。
那年把它们重新支起来,蒸了年糕做了豆腐大吃一通后不久,年迈的父母被我接到省城,到现在十多年了,我再没有回郝家沟。起初一段时间,每每跟二叔通电话,我都会问起碾子和磨,二叔都说它们安然无恙,但从来没有人再用过。最近几年一直没问,它们的境况也就不得而知。就算没有人再用,就算郝家沟消失,它们也必须留在那片属于我的土地上,而不是被搬到像观星山庄那样的地方。
驶进村中,我把车停在当年重新支起碾子和磨的地方,下车,看到它们还在。两个底座都塌了,碾盘和下片磨歪得不成样子,碾轱辘和上片磨又滚到了一边。我長长地出一口气,悬到嗓子眼儿的心,在肚子里落了个踏踏实实。
父母进城后,老宅不再有人住,不过我还是去看了一下。不但院子里长满了草,连房顶的瓦缝间都有草长得茂盛茁壮,草间开着颜色多样的花。打开房门进屋,立刻闻到一股腐败的味道,同时又感觉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清新。我很贪婪地做了两个深呼吸,在炕沿上坐下,看到很多年前曾经用过的一些家具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比如饭桌、柜子、凳子……坐了一会儿来到外屋,看到锅灶仍然完好,锅台旁边放着几把农具,包括锄头、镐头、铁锹、镰刀,北墙上挂着一个豆腐架子。
我小心翼翼地取下豆腐架子,端到眼前打量。它是用榆木做成的,黑褐色,压手。吹去浮尘,依稀可见沧桑的包浆,像是一件珍藏的瑰宝,散发出一股遥远的宁静质朴的美好气息。
我回来的消息很快在村中传开,一些人聚到了二叔家。这些人——也不过十来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有跟我同辈的,有辈分比我高的。二叔告诉我,现在村里只剩下这些人了。我问:“就这些人?”二叔说:“全来了,就这些人。”一个远房哥哥说:“你还想把碾子和磨支起来吗?”我说:“想是想,可是靠咱们这些人,肯定是支不起来的。”哥哥说:“是,支不起来了。”二叔说:“你实在想支起来,我从别的村找人帮忙。”
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有那样的想法了。
事实上我是有那样的想法的,只是觉得实在太麻烦了。郝家沟现有的几个人都已老态龙钟,想来邻村情况也差不多,那么巨大的工程靠这些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确实想再吃一次地道的年糕和豆腐,愿望却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那样的味道,那样的感觉,已经埋在我内心深处,就算永世再也吃不到,也已不会消失。
【责任编辑】铁菁妤
作者简介:
郝万民,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经济类报纸做过记者、编辑,1997年进入辽宁作家协会,曾任《文学少年》《鸭绿江》编辑部主任。2011年调至辽宁文学院从事数年教务工作,现任辽宁文学馆副馆长。在《湖南文学》《文学界》《天津文学》《鸭绿江》《海燕》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十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