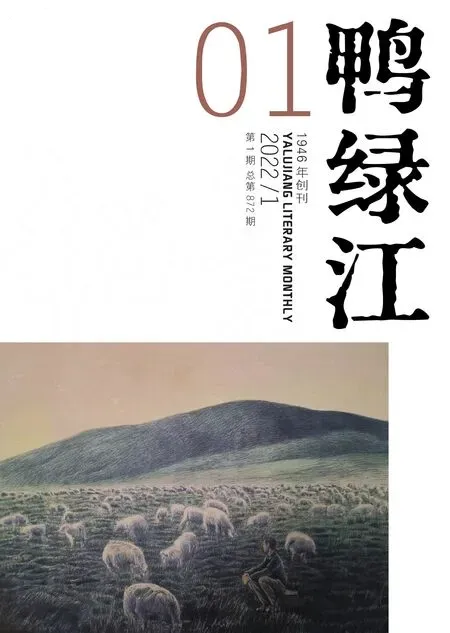脚手架
穿行于高楼林立的都市,到处可见耸入云端的脚手架,我偶尔会想起我的父亲。可他不在脚手架上,他已汇入脚手架上空的一朵朵白云,在俯瞰这个世界,也看着行走的我。
60多年前,在国庆十周年前夕,辽宁工业展览馆即将举行竣工庆典,我的父亲却已经躺在床上。他在拆卸脚手架时被一块跳板砸伤了,他的血染红了刚刚搭起的剪彩台。
当父亲咬牙从床上坐起,奶奶和母亲给他伤口换药时,我幼小的心灵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后腰下有一张嘴似的伤口在往外吐血水。父亲从家里被拉往医院的时候,有邻居讲:“张大个子这一走就再不能回工人村了。”谁知半年后,父亲给医院留下一根肋骨,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怀里抱着我,像从前线凯旋的英雄那样回来了。
刚出院的父亲需要在家休养一段日子,这下成全了我。我总是坐在父亲的身边,听他讲故事。他一边和我摆着积木,一边讲他和工友们用汗水盖的辽宁大厦和中国医科大学。仅上过两年夜校扫盲班的他,给我买了两盒看图识字卡片,毎盒一百张,两盒有三四百字,没用多长时间我就记得滚瓜烂熟。每逢家里来人,父亲总是让来人考我,受到表扬的我也总是给家人长脸。我不但认识卡片上的字,就连家中墙上奖状里的字我都能倒背如流,比如“解放思想,处处争先,巩固成绩,继续前进!奖给张凤祥同志。一九五九年”。
我出生之前,父亲已是厂、公司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了。
厂里为父亲重新安排了工作,让他当安全员,本来是管安全,他却差点弄丢了自己的命。
一天傍晩,到了吃晩饭的时候,父亲仍没有回来,却来了父亲的一个工友。他紧绷着脸,同母亲嘀嘀咕咕一阵子之后,母亲便和他慌慌张张地走了。原来,父亲他们施工的吊车在经过摩电车道时,吊臂刮在了摩电车的电线上了。当时正是下班通行的高峰,身为安全员的父亲看到正在驶近的摩电车,一着急用手去支那电线,强大的电流将父亲从五六米高的吊车上击到地上,当场人事不省。经过医院抢救,命保住了,但一只眼睛瞎了。
父亲又得在家养病了。不能上班,50多块钱的工资只能拿到一半,五个儿女还有奶奶一共八口人,僅靠父亲和母亲那点工资显然是捉襟见肘。那时,家里很少来客人,但有一个收房费的张叔每月都赴约似的来一次。他一来,父亲和母亲又是点烟、又是倒水,为的是将一块多钱的房租从这个月挨到下月。当新学年到来,哥哥姐姐拿着从父亲厂里开的困难证明,三块五的学杂费就可以免交了。
学费是免了,可免不了穿衣服。于是老大衣服穿小了,就传给老二、老三,再由老四传给老五。缝缝补补中,父亲学会了翻制衣服,一件破旧的衣服经过他比量来比量去,用那台总掉皮带轮的老缝纫机一缝,基本和新的一样。
那时,全国建设最早、最大的工人居住区已经建成好几年了。这片有一百多栋苏式红砖楼的住宅群,不仅享有“全国第一村”的盛名,当时在国际社会也有影响,一些国家领导人慕名而来,工人村成了展示中国工业进步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一张名片。
我家就是外国来宾接待户,全楼只有四家能有这种让邻居羡慕的荣耀,因为我家是劳模之家。这也要归功于我奶奶。奶奶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别看她脚小,干起活儿来干净利落,街道人员到我家查卫生时,无论哪个角落,戴着白手套去摸,都是一尘不染。为此,我家被评为沈阳市卫生之家。自从我家搬到工人村,奶奶逢人便说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当外宾来时,就能看到围观的人群,他们像是在说:“瞧,他家就是接待外宾的。”还有人擅自走进我家,看看我家究竟有多好。
到过我家的人就会知道我家很一般,屋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搬进时配套发下来的。如果说外宾来时有些变化,那就是奶奶将父亲工厂奖给劳模的大床单铺在床上,这种漂亮的花床单是许多人家没有的。等外宾一走,奶奶连忙把床单叠好收起来。
一次接待日本的教师访问团,当把他们送到大客车上后,我回到家里,一看床上有一台照相机。这显然是日本来宾遗落下的。我马上拿着相机追了出去,可是大客车已经没影了。我把相机交给了街道办事处,几天后传来消息,这件事得到了市外事办的表扬。一个月后,一封来自日本札幌的信寄到我家,找到懂日语的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叫秋叶榆夫子的年轻女教师寄来的。她信中说,在1946年以前,她父亲是一家日资企业年轻的技术员,在铁西广场附近待过两年,只不过那时铁西广场的西南方还是一块荒地,还没有工人村。她在信中向我们家表示真诚的感谢,也表示歉意。原来她是那个照相机的主人,照相机是她们离开我家时故意落下的。她想用这样的方式考验一下我家人的素质。让她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她们访问团晚上回到辽宁宾馆时,那台相机已经等着她了。这让她觉得很是羞愧。
父亲大病痊愈,每天带着饭盒早早地走出家门,晩上很晩回来,脸上是满足的神情。家里有个老挂钟,父亲经常把它拆个七零八落,用大小齿轮上下比量,然后再安装上。后来,当父亲从厂子拿回“技术革新能手”奖状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拆装挂钟是在琢磨改进设备,经过他的改造,他们设备的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三倍。
上小学了,我常和同学们比谁的爸爸厉害。有同学问我:“我爸爸是党员,你爸爸是吗?”我想,我爸爸这么能耐,他一定是。
我看过我爸在工地上干活儿。他一手拿着一个长杆子,另一只手攀扶着脚手架,双腿紧盘着脚手架,往上一蹿一蹿,不一会儿就到了有三四层楼高的顶端。他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像走钢丝绳的空中王子,有时还两腿挂在横杆上、头朝下往上传钢管,就像是以蓝天白云做背景的杂技演员,既惊险又威武,老厉害了。
这么厉害的爸爸,这么能不是党员呢?
一个星期天,爸爸又在家拆老挂钟,我忽然想起同学问我的话,便问:“爸爸,你是党员吧?”
冷不丁听我这么一问,爸爸一下愣住了,转过脸瞅了瞅我,“你问这个干啥?”我盯着爸爸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党员?你一定是吧!”
爸爸放下手里的螺丝刀,从桌前站了起来,转过身背对着我甩出一句“小孩不要什么都打听”。我连忙说:“一楼门的山子、五楼门的二伟,他俩的爸爸都是党员,我告诉他们,我爸也是党员。”
我爸马上冷冰冰地回应了一句:“你别出去乱说,我不是党员。”我一听,以为爸爸是在骗我,便嚷道:“你唬我,你一定是党员,你得了这么多奖状,怎么能不是党员呢?”
爸爸不耐烦了,“上外面玩去吧,别在这儿捣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和小伙伴比过爸爸。长大后,我知道了父亲没能入党的原因。就在他经常得奖的最初几年,厂领导总找他谈话,说:“鉴于你工作表现这么好,组织上要发展你入党,但你还没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主动提出申请,组织上才能发展你入党。”
他说:“我还不够格,再努力努力吧。”
后来,他又在公司大会上受到了表彰,公司一位领导问厂领导:“老张是怎么回事?听说他还不是党员?赶快发展他入党。”
厂领导说:“我们同他谈了几次了,让他写入党申请书,他总是说自己做得还不够,再努力努力。”公司领导说:“赶快让他写申请,这样的人不发展入党,还发展什么样人?”厂领导又找到父亲,让他写入党申请书。他说:“我不会写。”于是,厂领导便安排人帮父亲写了入党申请书。
很快,厂领导就把入党政审表交给了父亲,让他尽快填写。
后来父亲对我讲,在对他政审的那些日子里,他整天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的。
一天,厂领导找到他,“老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厂领导拿出了父亲的入党政审表,沉着脸问:“老张,你说,你有几个舅舅?”
父亲一听这话,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这下坏了,到底查出来了,便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我有四个舅舅。”那位领导脸一下板了起来,吼道:“那么为什么你在政审表上只填了三个舅舅,那个舅舅哪儿去了?他是怎么回事?你为啥不写他?你这不是隐瞒欺骗组织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对党的不忠诚,你要如实向组织交代。”
父亲如实地向这位领导坦白了所隐瞒的实情。
父亲说:“正是我有这么一个亲戚,我知道不符合入党的要求,我才不敢写申请书。我真想入党,党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要好好工作,报答党的培养,可是我又怕说了入不了党,才没在政审表填上我那舅舅。我对党组织隐瞒了家里的问题,属于对党不忠诚,请党组织再给我一次机会!”
父亲的那个舅舅,因为解放前在老家镇公所当过差,解放后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总是默默地抽闷烟。
有一天,父亲下班时闷着头回家了。原来他搞技术改造出了问题,负责生产的厂长严厉地训斥了他,说他是名利思想在作怪,破坏了生产,让他写一份检讨,深刻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问题。那阵子,本来内向的他,嘴巴闭得更严了,一天到晚很难听到他说几句话。至今,当我回想起父亲那时的神色时,我觉得父亲是怀有一种负罪感的。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工厂给的荣誉,而在崇拜他的儿女们面前,他觉得自己无颜以对。
一天夜里,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是父亲肚子疼,豆大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母亲说上医院吧,父亲说:“大半夜的折腾啥,别惊动孩子,天亮再说吧。”就这样一直挨到天亮。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对母亲埋怨道:“你们可真够呛,这人胃穿孔都这样了,胃里的东西都流到腹腔里了,这个人也真能挺,再晩一会儿要死人的。”
原来,头一天晚饭,父亲吃的是家里放了好几天的煎饼,由于长期没有营养,胃黏膜溃疡已经变薄了,被煎饼穿了个有五分钱硬币大的孔。
为了使父亲的胃不再穿孔,家里每人每月仅有的二斤细粮,尽量可着父亲吃。父亲吃饭时,我总是看父亲碗里的大米饭。一碗饭,父亲只吃到一半便推给我,说:“我吃饱了,你吃吧。”长大了,我才知道,哪个父亲能受得了饥饿的儿子那贪婪的目光呢?
三年后,父亲的胃穿孔又犯了,胃需切掉四分之三。手术后,厂里考虑到父亲干不了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儿,便安排他到工厂铁路专用线工作。每天他来往于货车、货场、仓库之间,当看到散落在地上的脚手架扣件、连接头时,他总是马上捡起来,送到库房货架上。他说,别小看这一个个小小的扣件和连接头,缺了它们脚手架就立不起来。
上山下乡的哥哥姐姐从农村回到城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女儿出嫁还容易答对,做两床被褥就算完事了,可儿子娶媳妇怎么也得有个住处。
从不给厂里添麻烦的父亲,在母亲的数落下开始向厂里提出要房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仅有16平方米的屋子里,进屋全是床。可房子哪是轻易要的。于是,父亲求厂领导特批买回来一些残损预制板,在奶奶不大的院子里挖地基,大兴土木,硬是给二哥盖了一个算是四面有墙的栖身之处。
至今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父亲肩顶着撬杠,抬那几百斤重的预制板的情景,瘦弱的肩膀扛着山一样的岁月。
房子有了,屋里也不能啥也没有。父亲又在厂里求爷爷告奶奶弄了几张劈柴票,买回来一些边角余料木材,开始同二哥打起了大立柜、小圆桌、木箱子。家的窗外成了家具作坊,又是拉锯,又是刨板,又是凿铆,当一个个油光锃亮的家具立起来的时候,邻居们羡慕地说:“这张大个子是真能耐,没有他不能做的!”
谁又能想到,这是一个少了一根肋骨、胃切除四分之三、仅有一只眼睛的人做到的呢。况且这个人要连续上一天一夜的班,回家后非但不休息,还要从事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父亲有一个工友,我叫他杨大爷,他和父亲交替上班。杨大爷热心肠,当厂里发工资而又赶上父亲不当班的时候,杨大爷总是在他当班的下午将父亲的工资送到家里,比马跑得还快,好像这工资今天不送来,明早父亲到班时就会变成纸。父亲见杨大爷来,总是热情招待,买酒买肉,平时不大喝酒的他也陪杨大爷喝上几口,谈天说地,恰似酒逢知己。杨大爷做好事来得快,喝起酒比牛吃草还慢。一次老哥儿俩正喝在兴头上,母亲下班回来了,脸上露出了难色。杨大爷感到有点尴尬,给自己个台阶下就走了。事后,杨大爷总拿这件事揶揄父亲,说父亲是“妻管严”,弄得父亲像欠了杨大爷天大的人情似的。其实,杨大爷心如明镜,他每做一次好事,父親少说拿出四五块钱来招待他,够咱一家老小用好几天的。
1986年,父亲和母亲离开工人村,搬到了郊区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
一天夜里,母亲慌慌张张地跑到我这边来,大半夜的,公交车已经回库,母亲是怎么从那么远的路过来的?原来父亲得了心梗,正在医院抢救,工厂都下班了,那时没有电话,母亲在工厂满院子找,才求到一个拉货的翻斗车把父亲送到医院,在医院安置妥当,才跑到我这边来报信。经过抢救,父亲大难不死又躲过一劫。
20世纪80年代末,辛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退休了,虽然刚过60岁,但积劳成疾让他多病缠身。为让父亲能有个清静一点儿的环境养病,母亲与在外地的叔叔商量,将奶奶送到他那里暂住一阵子。不料,第二年正月十五,一份报丧的电报送到我手上,奶奶仓促地走了。
我揣着电报来到父亲面前,不知怎么开口。父亲患了心梗,就怕刺激。我让母亲给父亲吃了一片镇静的药,才告诉了他,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随后,我同两位兄长和父母连夜乘火车赶赴叔叔家,料理奶奶的后事。
在为奶奶送葬时,父亲对我说:“你代表我向到场的人讲几句感谢的话吧。”父亲说这话时,目光是黯淡的,身子佝偻着,我猛然发现,我的父亲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站在脚手架上的那个人了,他那布满岁月沧桑的脸告诉我,他老了!
我入党那年春节前,父亲买回一个大猪头,精心处理干净,放入大料、花椒、料酒等调味品,慢火烀至烂熟,用纱布包好,在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放入小下屋冷冻。全家吃年夜饭时,父亲将猪头肉切成片,装入盘中上桌。看着我们蘸着蒜酱有滋有味地吃着,他端起酒杯对我们哥儿仨说:“你们都入党了,让我这脸上也有了光,在外面我也能抬起头走路了,我打心眼儿里高兴。来,我这当老子的和你们干一杯。”我们哥儿仨马上端起了杯,二哥说:“爸,我们能有今天,能入党,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谁知好景不长,父亲又得病了,吃不下饭。跑了几家医院检查,诊断是胆结石,住进一家大医院。动手术那天,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在手术室外,当主刀医生将从父亲胆内取出的碎石拿给我们看时,我们看到了希望。然而三天后,父亲全身泛黄。医生也蒙圈了,提出再开一次刀才能确诊。父亲躺在担架车上哀叹一声,他再也没有能力像三天前做手术时那样,自己走进手术室了。
诊断结果出来了,医生背着父亲对我们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是晩期胰头癌,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已没有治疗的必要了。”
出院那天,父亲走出病房,看到对面建筑工地上高耸的脚手架,他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他那僵硬的表情流露出一种无奈。
回家后,父亲躺在床上就没再起来。看着整日躺在床上的父亲,看着他那瘦弱单薄的躯体,像是晩上停电时点的蜡烛,一支连眼泪都燃烧的蜡烛,向我述说着并非传奇但属于光的往事。
父亲弥留之际,我们五个儿女轮流守护他。也许是父亲太宠爱我了,他将走的日子冥冥中选择了我在他身边的时候。
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喂他药时,他的嘴紧闭着,拒绝吃人世间的任何东西,父亲要走了。在母亲的呼喊声中,我镇静地给他最后一次穿上衣服和鞋,然后抬着他上救护车到医院。既然父亲走的时辰已到,那就让他走吧,在这个世上他受的苦太多,就让他的苦难到此为止吧。当我用一张洁白的布覆盖他的身体时,觉得是在为父亲蒙上一张白纸,只不过这张纸没有写下任何文字,只有我的泪像感叹号一样滴落在上面。
恩重如山的父亲享年64岁。
送父亲走的那天,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天地间白茫茫的,举目一片肃穆。天很冷,心更冷,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我没有再流泪,忍辱负重的父亲是看不得他儿子眼泪的。在灵车启动的那一天,我心里暗暗地说:“爸,到了天堂你可别回来啦,来世也别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灵车经过工人村我家老楼前时,一些老邻居得知是为张大个子送行,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站在大雪纷飞的马路边上。我坐在父亲的灵车里,向外撒着纸钱,望着马路边一张张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我心潮起伏。我对躺在灵车里的父亲说:“爸,咱们回工人村了,你看啊,工人村的老邻居们来送你了。”
这时,马路边一阵骚动,我在车里扭头一看,是杨大爷跪在路边的雪地上。我忙下车走了过去,杨大爷老泪横流地说:“老张呀,你这工人村的酒我可是没少喝呀,你这一走,工人村的酒我也就喝到头儿了。来吧老张,咱老哥俩儿再喝最后一次酒吧!”杨大爷打开了手中的两瓶老龙口,一扬脖猛喝了一大口,把两瓶酒一碰,浇在了雪地上。
父亲只是工人村千万工人中的一个普通工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得到了如此高的礼遇,这是工人村的人们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第一代工人村人致敬。
【责任编辑】铁菁妤
作者简介:
张瑞,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沈阳市沈河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981年起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毕业于辽宁文学院。有詩集《真诚的回眸》、散文集《圣地工人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