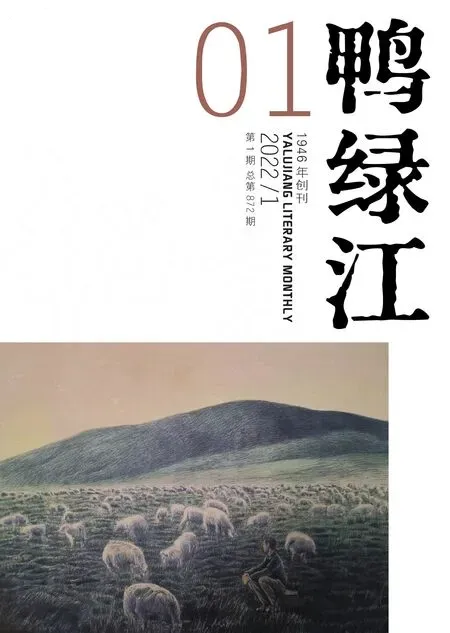如此甚好(组诗)
周末我想写首诗
大多数人试着放松,让生活
从严肃变成不严肃
周末,我只想写一首诗,找来纸笔
我想等窗外那些扛着命运奔走的行人
变成一个消逝的点之后就开始写诗
我告诉我自己当州城的高大建筑
矮下身子与地平线齐平
一块石头蹲在大地上
像一个长者就开始写诗
我告诉我相较于消逝的点
少年是后来人,让他抬头看天
混进大雁队伍在天空试飞一会儿
尽管闪电有时会撕扯天空的幕布
室内有桌椅和书籍、茶杯,角落里
有脱落的毛发和积尘,它们
从不相互摈斥
却也不愿从回忆中找到值得信任
存在的事实,尽管我有些焦虑
一些陈词滥调
已不能制成火把照亮一些消沉的
片段。我铺开的白纸
就像铺开一场大雪
文字是或深或浅的脚印,但是我
还不能理解雪,我还未腾空思想
不能理解某种单纯的激昂的白
是否会对语言形成掣肘,上午
我到过市府路,在打字复印店
打一份发言稿
有着白净面孔的店主不可能知道
刹那,我从心窝子里掏出一只灰雀
而他惊诧的眼神将形成
鸟笼子的竖条。所幸
一首诗大概就是一个出口
我们在答案揭晓前,习惯
保持过期的一致和深刻
如此甚好
天空开启剧场,透出光,忽明忽暗
群山从古老中醒来,走向另一种古老
语言或词语,其实也很古老
它们为无数验明正身的众生
开设过忍耐的祭坛
往往都是这样,在你转身的一瞬
河流的骨头已被寂静取走,只剩下
软绵绵的流水,从赋形的思想中
向着更低处夺路而逃,尽管它
曾淹死过一匹野马……如此甚好
如此,在城乡接合部,遇见一个
熟悉的醉酒男人,让他爬上巨人的肩膀
从高处向下俯视
啊!日常的建筑、车辆、行人,
渐渐收缩,物事变小
正被肉眼无法观察到的某种永恒的法则
捆绑,教育。如此甚好,让他
必然忘记危险的
追赶和趋同,忘记金灿灿的粮食
和白花花的盐,忘记寡妇邻居
试图用一团火焰交换少年的积雪
告诉我
告诉我,你等待的邮差是否会迷路
假如遇到极端天气,请暂且献出
你的温暖居所,让他躲避风暴、雷雨
告诉我,沙漠里的一滴水,如何
救活一条鱼。我每天上班都路过
嘈杂的菜市场,知道世界并非咸鱼
它有时是坚硬的,有时也是柔软的
县城十八屯石坎早已被无数来往的
脚步磨平。拾荒的老人,黄昏
像一池深深湖水曾淹没他的头顶
想起我母亲一辈子迷信,她说
夜晚的猫头鹰是在呼喊某人的名字
告诉我,移步的忧伤模仿后台演员
仅换一副脸孔和腔调出场
多年来,我仿佛丢失过一块生铁
现在我急于找到它
用火淬炼,把它打造成一颗
亮铮铮的钉子把白昼和黑夜挂起来
把大海和内陆挂起来
把语言和沉默挂起来
把一个人思想的
版图挂起来——那有限的悲喜
啊,却也抵不过火焰
及灰烬的洗礼。告诉我,光线簇拥的
少女是否带来一粒种子,又或割腕的
刀片。她听过风吹城市高低建筑的
口琴吗?她看见风转入山野为一只虫子
拨动草木之弦吗?等待得太久了,少女
穿墙而入,为妥协而贫穷的野心
饱满起伏的胸部。县城十八屯石坎
早已被无数来往的脚步磨平
告诉我那倒着走路的人是谁?告诉我
人们习惯沿着物事
去披荆斩棘。沿着心的召唤的人
一次次被俗世击倒
盐
县城银行大楼的玻璃幕墙上,人影
交错拉长。卖菜的老人,发丝上
有经年的盐霜。她怎样才能传递出
找零硬币的温度?她手指微曲
悄悄告诉我这个季节不易破产
而一个下午就像一个鼓满风的
食品袋。古老的盐,原谅我还未
修行出草木般的淡然态度,原谅我的
思想不够古老。历史的官道上
盐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盐的尊严
就是人的尊严。在血管中奔跑的盐
翻译冰与火,光明和黑夜
唯有死者辜负、背叛过盐
在另一个世界,有人省略掉
羞愧和舌頭。此时,我看见大地上的
匍匐者,在研细的反光晶体审判下
振作起来,仿佛被一个
恒久的符号扶起意志
建在山顶的房子
黔之西南腹地,有人将房子建在山顶
建在语言稀疏之处,鹰要俯冲
神要站在高处,也得跟随想象爬升
事实上,山顶风大,事物省略交谈
各自谦逊地活着,但是否也省略了
生活奖励的蜜和咒语?
草木邻居,可以将房子主人引向深入
可以用孤寂扶稳孤寂,丢掉
那些从记忆中打捞出的脸,在落雪的
故乡,形同为幽僻的词语,摆下宴席
可以打开天窗,牧养一颗星子
邀一片云朵,装饰屋顶。语言复苏
让拖出尾焰的喷气式飞机,从房顶
轰隆隆飞过,患抑郁症的旅客,试图
飞向另一座城市,治疗将要发生的事情
建在山顶的房子必然领受过一张
图纸的专制,像这个雨夜
我路过咖啡馆的橱窗,那些交错的
身影或思想,仿佛正在签约一份新合同
而我知道,饥饿是下山唯一的路
也知道另一个维度里,时间
也是一所危险的房子
雨季漫长
一片残叶的小船,搁浅在流水尽头
一只蚂蚁,拖走一只苍蝇的肉身
雨季漫长,仿佛连死亡都是
湿漉漉的。雨水击打在草木叶面上
如击打在
盛放光线和语言的古老器皿
雨水是否抵达了天空口授的预言
在苍茫大地上,如一个趔趄的人
倏然抵达未曾为自己辩解的命运
如一颗子弹,抵达未知的目标
一种真理唤醒另一种真理,雨季
漫长,我们隐藏发芽的虚空,假装
与固执的居所,签订一份合同
我们将成吨的谎言填充在
稠密的空气中,然后
若有所悟,雨声打湿世界,打开
窗户的作者,搬运来一个新故事
——当我在林畔发现一只逃跑的
松鼠,这并非沮丧,而像雨季
消失的思想留下证据
山中即景
连日雨水,终于浇灭七月盛夏
这一次,我们要上山去
走访一户人家。每个人的胸腔里
都需要安装一架顿悟,或调节
冷暖的壁炉。沿途鸟语,可以
修复一池山塘,蚂蚁的律度
是在匆忙的人类面前,放弃经验
草木兽虫陡增遗世之美
——一种思想曾在夜晚死去
想起古董般的月亮,挂在
浩瀚天幕,如一件破损的响器
被风触动,再往山上爬升,我们
似乎距它又接近一些,想起
这些年来,坚硬的事物埋下暗疾
寂野,能否开出一具治愈的处方
在山垭口一弯草地,一匹灰马
在草坪上啃食草芽,在它抖动
脖颈鬃毛,打出响鼻前,我确信
世界已趋于静止,但是为何
我们的身体里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
它们仿佛被一条浅睡眠的河流
运送而来。抵达某个时间的地址
我们在山上走访了一户人家
这一次,我们会将命运的缰绳
轻轻地拴在一棵小树,也许是一块石头
我们深知并非从某种完整的
缺憾中脱逃
荒城
驱赶走身体里的兽虫、鸟类
或许是一片幻形的云
这一天来,它们被太多疲乏
和徒劳代替,它们有着不为人知的
羞怯。久居黔地,群山之中
在困厄中练习戒备,博爱,松弛
七月,飞龙雨水伸出舌头,舔过
远山和村镇,舔过毛玻璃
的屈服,通过它,我看见街面上
小贩暂时浇灭喧哗的烈焰,汽车
急促的喇叭似已發现伟大真理
提裙碎步的少女,还未长出
一副沉甸甸的乳房
啊,多么诚实的路径。此时
我已忘记杯中茶水的味道,我将在
失去仪式的废墟中返回
如这一天中,我曾关掉手机
登山及顶。俯视久居的小县城
啊,那些发生在城中的悲喜
仿佛被陡然交换的身份,开凿出
一道庸碌的光辉,我知道每一种
语言最终都将走向沉默,如同
知道内心供养着一座生长的荒城
林区行车记
汽车在一大片林区疾驶。车灯
打在抽象的树干和蹲着的矮灌丛
像光的荒诞投射在虚无之物身上
令人对它们的真实性
产生怀疑。夜晚蓬勃,风
原始的草寇在车窗外潜伏
汽车马达声试图摆脱某种
凶险的纠缠。转过弯来,一只
野生动物忽然横穿公路
司机在惊诧中踩了一脚刹车
我的身体前倾。瞬息之间
却在回头的兽虫眼眶里
窥见,嵌入黑暗凝聚的绿宝石
——仿佛被什么击中,唯有黑暗
不接受黑夜的绑架和剥削
再多一点耐心,我们将
驶出这片林区
黑夜的负担
那个摁下开关,在深夜枯坐的人
那个被俗套的子弹击中思想
用一把戒尺测量
子弹飞行轨迹的人
那个在黑暗中掘土
在身体里安装飞机跑道的人
停下来。试着呷饮一杯,黑色的
宗教。总得有什么减轻黑夜的负担
夜的摊铺:有荣光、羞耻
有密谋者的档案,无边的欲望
迷途的酒鬼,一枚发光的词语
能否成为夜的别针?晚年的博尔赫斯
并不需要用肉眼去观察
这个世界,或许他只是
上帝安插在人们身边的盯梢
但我们不相信上帝
就像我们从不相信死亡的蜜
会涂在余生者的乳房
事实上我们只相信时间
让昼与夜,相互接受教育
要相信时间会安顿好一切
尽管时间也制造灰烬
宛如最后的纵火犯
【本栏责任编辑】林雪
作者简介:
吴春山,男,贵州晴隆人。诗歌作品刊于《中国作家》《诗刊》《星星》《诗选刊》《绿风》《草堂》《山花》《飞天》《山东文学》《四川文学》《延河》《扬子江》《百花洲》《中国诗歌》《诗歌月刊》《诗潮》《新华文摘》等报刊,有部分作品入选年度选本。现供职于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