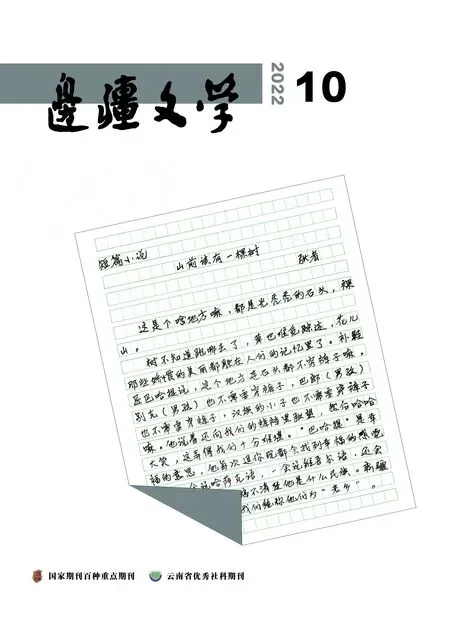悬棺猜想 组诗
谢健健
悬棺猜想——兼赠苏仁聪
离开云南,带着许多未竟之事
车外群山蒙着雨幕,构成候鸟
危险的一次迁徙。山涧孤绝,
听同伴说起过其中的悬立棺木:
原住民,会在长久的死亡中站立
像是抽掉孩子的积木,每一具悬棺
都蜷缩在祖先的山洞之下
也许每一代都曾接受过峰顶的庇护
这多像我们的客车,超载但
仍盘旋在曲折的公路。高原之上
大雾,风雪,带着重力的雨,
每一样都使引擎难以喘息——
友人,我们是否还有下次相逢
再一起去看岩壁,和它之上的悬棺
从而听见棺椁有节奏地撞击
那来自我们微弱的语调,为世界
沉沦,而发出的一点儿低语
草海站
列车晚点以后,举牌的二道车贩
蹲在铁皮外和时钟对视
蒸汽的笛鸣像还没开始的故事
我知道友人正想象抽烟
烟雾中会映现他本质的颌骨
揽客声中隐藏着上世纪的中国
流向不同的边境和年龄不同的床
人群开始涌动了出来,握着
瓜子壳,或是一卷过时的报纸
伴随旅店打开所有窗户的黄昏
朋友们来了,满是疲倦,
从上一座车站赶往这座车站
他们要从海水中打捞起我
捕获一次潮汐过后
湿漉语言已浸透的海洋之心
车站保留了相见的庄重,人们
握手,人们致意然后拥抱、
谈论得以缓解远行的悲哀
我们共同信赖,古老的等候——
它是双向的风将要扑个满怀
省耕湖,秋色
走完整条临湖的水街,入秋的叶
闪耀在留影者的身后加深光线
雪山前,有人通过远眺
握住云雾偶尔散去的寒冷部分
当落叶不安地纷飞,在湖心街道
省耕湖,到处长满了金黄的银杏
这古老的风景适合站在中轴线
有人低头仰拍,快门将帷幕掀起
有人捡起一枚书签,水面破碎
的暮色,谁封存这一页时间之书
这是秋天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将桂花佩戴在发间,对抗消逝
的甜。会有未结绳的野鸭
从入水的涟漪里浮游而出
为我们晃动水汽朦胧的疲倦
洒渔镇——兼赠芒原大哥儿女
苹果树下,孩子在吹她的蒲公英
冷水河湍急,垂柳正作别岸上的来客
她羡慕哥哥可以大口吃苹果
年龄是一小圈谜语,困住她的好奇
她不明白叔叔们为什么摘食玉米秆
连那河边几只小羊都发出了抗议
如此古老的小镇,真正意义上的乡下
她不知道自己怀有怎样高贵的生活
就像被我们扔出的鹅卵石,水漂般激荡
原始的生活纹路一圈圈,回旋在我眼前
河流的交汇处
竞速区像是一个隐秘的比喻
总有汇入同一赛道的时刻
远山被冲淡了,只剩下杂音
使你置身假日的观众席位
一瞬,一架滑翔的雎鸠飞过河面
为你重新分割V 字衣领的河洲
解剖或再现古老的诗意源头
我们注视河流的交媾,深陷其中
采诗官曾经深入这百濮之国
用他四字的短句为我们标记前路
但那足够了吗?当河流彼此交汇
交换各自体内的欢乐和忧愁——
或许我不是守旧的牧羊人
爱着两条河流冲刷岸边的响动
但我信赖那路过逆流航行的机船
它倒置的影子搅碎古典传统
使人确信改道不是南曲里的游园惊梦
旅行史
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
他会定义故土的全新阐释
两排树林里的新鲜脚印
用深浅不一的泥印替他发声
这儿昨天下过一场雨,雨中的人
会消失于灌木丛中的阴影
那条令我们着迷的小路出现
指引我们不断地开始旅行
我的母亲,梵高笔下的农妇
送给过我一双结实的鞋子
她说开始走吧,从这儿到那儿
去那些你父亲没去过的土地
于是我出发,伴随体内不安的血液
那来自读书时,吉普赛人无形的馈赠
母亲,我挣脱了那张浮力的网
你看那只灰鲟,正在退化有力的鱼鳍
古老的生活——致瓮安县城
车过桥*了。地平线下的后浪,
难以逾越这垂直数百米的高差。
滚动的车载音乐,给乘客催眠,
但司机健谈的引擎永不熄火:
桥对岸是四线以后的城市,
略带方言的叙述缓缓从他舌尖展开。
清明雨水落在临近放学的校园,
被一种躁动弹起,迅速蒸发。
人们用形色不一的老油伞
认领红领巾后面容相似的孩子,
同时认领一段稍长的假期,
获得长足的休憩,还有对来路的回忆。
卖弄炸食的街贩为生活撑起遮蔽
风雪的帐篷,试图隔绝一种注视,
那窥视旧钱盒,不确定的训诫书。
油花飞溅,但难以透过坚韧的茧,
手掌有灵活的特质,握手或恳求,
他们总是秉持略显软弱的交往之道。
揽客声中隐藏着上世纪的中国,
最后三天清仓的甩卖,从一座城市
到下一座,无处退守时就在这常住。
过时的老气音乐,曲调里混杂着
青春、爱与被爱,那些早不新鲜,
但在这仍然是刚刚萌芽的小城故事。
非常奇异,就像又经历了一次
童年:你从雨水中的学校里走出,
这么多年流浪异乡,旅行使人
克制,常常远离故土。但在小县城,
你却因熟悉的场景流下九零年代的眼泪——
这古老的图卷,你最早经历的生活。
*:清水河大桥,位于贵州瓮安,世界第二高桥。
高原上的灯塔
山顶信号塔的闪烁像是一种喘息,
使我想起登山者疲倦的面容。
据说他们生长在平原和海边,
对高处充满基因里的渴望。
我的水手父亲曾穿越过巨浪,
海水在他眼前凝聚成山峰,
攀登过去,就是归港的灯塔。
晚年他在陆地的工厂上班,
噤言那些在海上登山的往事,
但常提起灯塔,说那种明亮,
“是黑夜里潜行的一束光。”
云层之上我注视高原的灯塔,
在另一片海里回忆溺水的经历:
那样冰冷没有尽头的黑暗,已淹没
在和人闲聊的话题之中,淹没
对海的渴望,淹没于无数次登山。
对峰顶的执着让我常年流浪异乡,
在一次次的旅行中试图放逐自我,
褪去潮水与海风浓烈腥咸的气息,
但一切都是那样巧合,令人无言——
父亲在海上登山,我在高原上见海,
我所叛离的,南辕北辙回到我身边。
我静默于生活,这偶尔明亮的色彩。
在石鼓镇观长江第一湾
汛期的石滩隐藏于东流的金沙江水,
只探出头,给人错过江心洲的遗憾。
神迹般的拐弯使人侧耳,倾听导游
那缥缈的回音:就是在这,金沙女神
突破了玉龙和哈巴两位兄长的阻拦,
不顾向南流亡境外的两个姐姐。离别,
至今仍在延续,只凭一颗孤勇的心。
石鼓,适宜在高处远观,那黑瓦环绕
的纳西古镇,保留了八百年来的方言:
赶集声或许回荡过念青唐古拉山,唯有
穿越过茶马古道的家族才被允许叫卖,
鬓白盛装的妇人,以贫穷为别样的勋章。
你注视一切随着江水向东无休止地流逝,
唯见青山不改,亘古与小镇流水人家作伴。
拉市海
颠簸过泥塘才能走进茶马古道。
初次来到另一个以海为名的湖泊,
你,伴随着几阵夏日午后的骤雨,
那样温热,融入水中全都不见。
一滴气泡破裂在被时间忘却的海,
你得以探出头,从被星群擦拭过
如今远胜西洋镜的湛蓝湖面之中,
拥抱湖水像拥抱亲密的爱人。
褶皱的纹理,刚刚游荡过野鸭,
搅碎你头顶的白云。岸边的垂柳,
倏忽蹿下筑巢的松鼠,迅速的消失,
它的尾巴耸动间是一圈棕色的谜。
浸泡在湖水中你感受到浮力的轻盈,
陆上生活,你厌倦它难以启齿的沉重。
像是忽然被放逐到了贝加尔湖畔,
你接替苏武牧羊,但渴盼它无后而终——
一切的复刻都忠实浮现于拉市海,
经冬复历春,记录忧愁也记录欢喜;
群山的阴影被湖水推动着上岸,为你
带来峰顶的荫凉,和候鸟北来的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