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仲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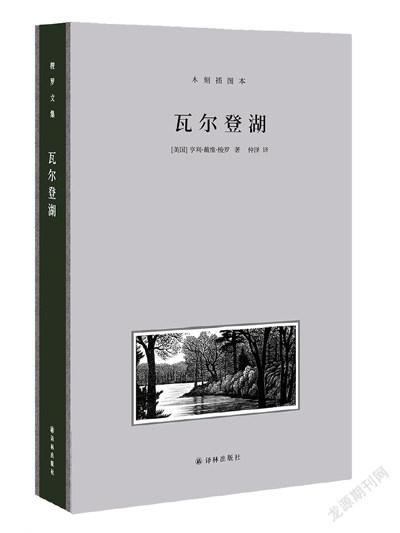



本书用澄澈的思想和文字告诉读者“物质极简、灵魂丰盈”的生活真谛。作者远离喧嚣,在瓦尔登诗意秀美的四季景色中过着极简生活,不断地思考如何生活才能离自己的心灵更近。他用文字竖立了一根真实世界的标尺,让后世知道,假相和幻景屡屡泛起的洪流到底有多深。
医生会明智地建议病人更换空气和环境。感谢老天,瓦尔登湖并非整个世界,七叶树不会在新英格兰存活,这里也绝少听到嘲鸟的鸣叫。野雁比我们更像世界公民,它会在加拿大进早餐,在俄亥俄州用午餐,夜间则会在南方的池沼梳理羽毛。即便是野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紧跟季节:先在科罗拉多州收割牧草,然后应召前往黄石公园那边葱绿更甚、肥嫩有加的草场。但我们却在考虑,若将农田周围的篱笆拆去而垒成高高的石墙,我们的领地便会就此圈定,我们的归宿也就有了着落。如果你成了镇上的文员,今年夏天非但不能去趟火地岛,反倒可能会去火地狱。宇宙比我们眼中寥廓浩渺。
如若有所发现,纵然像探知的海岸那样标为黑色亦属枉然。难道我们该探索尼罗河、尼日尔河、密西西比河的源头,而或环绕美洲大陆的西北航道?难道这就是人类最该关注的问题?难道唯有弗兰克林一人失踪,致使妻子牵肠挂肚,急于寻找?难道格林奈尔先生会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還是做你自己溪涧和海洋的蒙哥·帕克、路易斯、克拉克和弗洛毕舍吧,在你自己高纬度的地方探险——若有必要,满载罐头肉食作为给养,然后将空罐子摞得天高当作信号。难道发明罐头就是为了储存肉食?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内心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为思想,而非贸易,去开辟新的航道。每个人都主宰着自身这方领地,与之相比,身外世界纵如沙皇的俗世帝国也只是一方弹丸之地,只是冰雪遗漏的一处山丘。然而,有人就会无视自我而成为一个爱国者,去做一些因小失大的牺牲。他们挚爱将成为自己坟墓的土地,却漠视依然在为肉身赋予生机的精神,爱国情绪成了盘踞在他们脑子里的一条蛆。南海探险若非间接地认可这一事实:在精神世界里存在着大陆和海域,人人都是其地峡和入口,只是自己尚未探究;若非借以说明:与孤身探究那片隐秘的海域,与探究自身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相比,由政府出资提供航船,五百男子和孩童给予辅助,历经寒冷、风暴和食人族的考验,长达数千英里的探险倒显得轻而易举——若非如此,则这次仪式炫惑、耗资甚巨的探险又有什么意义?
环球航行去桑给巴尔岛清点那里的野猫有何必要?但是,你若无力做得更好,不妨先这么做,或许,你会发现某些“西姆斯洞”,最终还能钻进地球。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还有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等等,无不朝向这方隐秘的海域,但他们没有派出哪怕一艘三桅船向茫无陆地的方向开进,尽管那个方位毫无疑问就是印度。即使你会讲所有民族的语言,又能奉行他们的习俗,即使你的航程之远同辈难及,又能适应所有的天气,还能让斯芬克斯将头撞向巨石,你还得遵循古代哲人的规箴,去探索你自己。这种探索需要识断和胆气。
据称米拉波曾对拦路行劫很是上心,“以确定人得有多大的决心,才能将自己置于跟神圣无比的社会秩序根本敌对的位置”。他声称,“士兵作战所需的勇气也不及拦路劫匪的一半”,“荣誉和宗教也不抵周密而坚定的决心”。正如世人所见,行劫自有一股豪气,可是,若非铤而涉险,则属放浪之举。心智成熟的人会发现,因为他遵从更为神圣的律令,所以时时觉得自己跟那些被认定为“神圣无比的社会秩序”“处在根本敌对的位置上”,因此,无须刻意为之,他的意志与决心就获得了验证。人无须用这种态度对待社会,但他必须坚持自我,坚持自己因恪守生活之道而形就的任何态度,如果他有幸遇上正义的政府,这种态度绝不会与之相悖。
我离开丛林的原因一如进入其中那样合理,或许,我应该还有多种生活可以选择,不必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过本书描述的这种生活。让人吃惊的是,人们会在不经意间轻易地习惯于某种特有的路径,并最终成为自己的程式。我移居湖畔不到一个星期,就从门口到湖边踩出了一条小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六年,却依旧清晰可辨。我担心有人会执着于这条小路而让它始终存在。人的双脚易于在松软的大地表面留下脚印,思想之旅亦复如此。世间的大路定然踩得坑坑洼洼,布满浮尘,而习俗和成规的辙迹又是何其深刻!我不愿在船舱里航行,而宁愿置身于世界之甲板,在桅杆之前行进,因为在这里才能清楚地欣赏映于群山的月色。现在,我不想走下甲板。
通过试验,我至少明白:如果有人能够满怀自信地在梦想之路上前行,努力践履构想的生活,他就会收获一种通过寻常方式难以预期的成功。他会将某些东西置诸身后,会跨过那道无形的界限;那新颖、普泛,也更加自由的法则会在他身边形成,在他内心生根;或者,陈规旧习会得到拓展,在更加自由的意义上,获得于他有利的内涵,因此让他活得自如、卓越而超拔。他的生活越是简约,宇宙的法则便会显得越发单纯,而孤独不再是孤独,贫穷不再是贫穷,软弱也不再成其为软弱。你若将城堡建于空中,你的努力便不会白费,这其实也是它的理想所在。那么,现在就开始打地基吧。
这种要求似乎很重要,好像离了他们,你的话就无从理解;好像上天只允许一种理解方式,好像它会供养走兽而弃绝飞禽,选择爬虫而拒斥鸟类;好像只有“哈嘘”和“呼儿”,这种布莱特能懂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英语;好像唯有变得愚蠢才够保险。相反,我最担心的倒是自己的措辞还不够极端,唯恐受限于个人狭隘的日常生活,若是如此,便无法透彻地表达我所确信的真理。极端地表达?那取决于你的环境。逐水草南北而迁的水牛就不会像授乳的家牛,在挤奶时踢翻奶桶,跃过栅栏,跟着幼崽逐跑那般极端。我渴望在没有限制的地方说话,言者清醒,听者清醒,因为我坚信,要想为真切的言说提供基础,怎样夸张都不算过分。难道听过音乐就会心存顾忌,唯恐往后出语极端而言辞发露?着眼于未来和可能,我们该从容无拘地生活,让前景丰富多变,让我们未来的身影像罩着雾气那样隐约不明,一如我们在太阳下的身影,因难以察觉的汗气而显得模糊朦胧。我们言语之中的真理一旦逸出,剩下的只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言辞外形,真理随时会转化为其他形态,留下的只是一块语言的碑石。表达虔诚信仰的话语形式多变,难以确定,但是对卓越的心灵,它却意味深远,馨若乳香。
我们何以始终让智识沦为陈腐无比的观念,并且誉为常识?俗见是睡眠的官能,是伴以鼾声的呓语。我们有时会将超凡的智者与十足的蠢人相提并论,那是因为只能领略智者三分之一的才智。在我们的世界里,只要某人的作品容有多种诠释,就会给责难留下口实。我并不觉得自己的表述晦涩含混,就我的文字而论,如果其中的致命缺陷不比瓦尔登湖冰的缺陷为多,那我会引以为荣。南方的消费者拒绝瓦尔登湖冰的蓝色,似乎视为晦暗混浊,而那恰好是它纯净的表征,他们喜欢剑桥的冰块,这些冰块固然呈现白色,却混有杂草气息。人们钟情的纯洁如笼罩大地的雾气,而非高迥蔚蓝的太空。
活狗总比死狮强。难道一个人就因为自己是俾格米人而去上吊,为什么不尽其所能地去做个俾格米人中的巨人?请所有人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勉力而为,成就本然的自己。
我们为何要不顾一切地匆忙于成功,不顾一切地沉溺于所谓进取?如果有人无法跟自己的同行人并驾齐驱,可能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种鼓声。还是由他随着自己听到的鼓点前进,不管什么节奏,也不管多么遥远。他能否如橡树和苹果树那样成熟并不重要,难道要他把自己的春天变为夏天不成?如若成就我们的条件尚未成熟,我们罔顾眼前的现实又复何益?我们没有必要在幻境之中翻船。若在头顶上建起一方蓝色玻璃的天空,纵使完工,我们肯定还会凝视它上方那个更加高远的真实苍穹,好像前者没有似的——谁愿费尽心思自讨苦吃?
科鲁城有位艺匠,此人执着于完美的追求。一天,他突發奇想,要做一柄手杖。在他看来,未臻圆满的作品属于时间,而已臻圆满的作品则归于永恒,于是,他暗自思忖,这柄手杖无论在任何方面都该尽善尽美,尽管自己一生可能因此而无暇其他。他立即进入森林,决定选取最佳用材。他在林中选了又丢,丢了又选,反反复复,极意寻觅,其间朋友相继离去,且因忙碌而衰老逝去,而他却一无老态。他因坚定执着虔诚如一而青春永在,自己却对此浑然不知。他没有向时间低头,时间便为他让道,由于战败,唯有在一旁徒自叹息。待他终于觅得尽善尽美、如意称心的材料,科鲁城早已满目灰白,沦为废墟,他便坐在土堆上给那根原材剥皮。他的作品尚未成型,坎达哈王朝便覆灭不再,他于是操起手杖,用尖端在沙上写下了城中最后一个人的名字,然后继续忙碌。就在他打磨修饰手杖的当儿,尘劫也不再有天际北斗那样的意义,他尚未给杖头装上宝石,梵天也几度梦醒又复入眠。我为何要特意讲述这些?就在这位艺匠完成最后一笔之际,他突然惊恐万状,呆呆地目睹那柄手杖获得升华,而成为梵天诸作中臻于极致的作品。他做成了一柄手杖,而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秩序,一个和谐均衡、完美无二的世界,尽管城市和王朝在这里已然灰飞烟灭,但是瑰美有加、辉煌无比的城市和王国却代之而起。现在,身旁那堆削除的废料在脚下依旧光鲜如初,他由此领悟到,对于他和自己的创作,先前逝去的时光恍若幻景,不啻梵天脑际闪出的一粒火花,落在凡人心头而腾起光焰的一个瞬间。用材至纯至洁,作品尽善尽美,除却神奇精妙,尚复何种结果?
我们在乎万物的表象,最终都不及关注真理让我们受益,只有真理经得起考验和磨砺。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处身其中的地方迷失了自己,而居于一个错误的位置。因为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构拟了一种情形而将自己置于其中,因此同时囿于两个场景,所以也因双重阻遏难以脱身。在心智正常的瞬间,我们只会认定实情,即那个真实场景。还是言说必须言说的一切,而非应该言说的内容,实情总比假象要好。白铁匠汤姆·海德站在绞架旁,当问及是否有什么遗言时,他说:“告诉裁缝,缝第一针的时候,记得在线头打结。”这番告诫垂于世间,随员的祈祷却被人置诸脑后。
不管生活有多鄙陋,直面而生,切勿逃避,不必名之艰辛,它还不至糟到你之为人的那种地步。人在豪富之日便是赤贫之时,挑剔的人身在天堂也会吹毛求疵。纵然生活窘迫,应该满怀热情,即使处身寒舍,或许也能享受欢乐、兴奋和荣耀。济贫院窗口折射的落日余晖跟富人轩窗的夕照反光明亮无异,门口的积雪同样也会在春天应时消融。我深信,若非心灵宁静,没人能在济贫院怏然自足,满怀欢欣,如同置身宫殿之中。在我眼中,镇上的穷人常常过着无所依傍的生活,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数量甚众而不觉得受之有愧。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屑于镇上的接济,其实好多时候,他们恰恰不免采用下作手段借以支撑,这是更为可耻的行径。以圣人为范,像打理园中的花草那样对待贫困。不要因为喜新厌旧而劳心费神,不管是衣物还是朋友,翻出旧的重加利用。一切都不会变化,变的是我们自己。卖去衣物,留下思想。上帝会保你没有社交也无所妨碍。如果我像蜘蛛被成日关在阁楼的一角,只要思想不失,天地照样开阔。有位哲人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要为寻求发达而满心焦虑,也不要委身于诸种影响而身遭戏弄。谦卑像暗夜,会展现出天国的光辉。贫穷和卑琐的影子在我们身边晃荡,“瞧,收益增长,近在眼前!”我们当时时警醒,设若被赋以克罗伊斯那般的巨额财富,我们也必须坚守初衷,矢志不渝,连手段和方式也不能有根本改变。此外,如若困于贫穷而无力挣拔,比如,难以购书,无法买报,其实你仅仅受限于卓尔不凡、干系莫大的体验之中,不得不面对那些糖分最多、淀粉最富的养料,贴近骨头生活才最有滋味。这样,你将会免于蝇营狗苟。只要气度恢宏,处身微贱也能守住自己。过量的财富只能购买过量的物品,要满足灵魂的需求,金钱没有用武之地。
我住在铅墙的一隅,其中混入了稍许钟铜。在我午间休息时,屋外常常传来聒噪耳鼓的叮叮当当,那是同乡的扰攘。邻人告诉我,他们在攀附达人,争逐名媛,那是他们在餐桌上邂逅的显贵和名流。可我对这等事情毫无兴趣,默然冷淡毫不亚于阅读《每日时报》。他们都是些转瞬即逝的过眼云烟,弄得我最后耐不住性子。我乐于回归自己的方式,不愿在盛典宏仪中列队行进,不愿在显赫醒目的地方现身,如果可能,我倒愿意跟宇宙的匠师同行。我也不愿生活在这琐碎扰攘、紧张喧嚣的十九世纪,而愿置身局外,伫立凝神,端坐沉思。他们都庆祝些什么?他们都是主管统筹和谋划的委员,时时刻刻都在恭候某人训话。上帝只是当日的主宰,韦伯斯特则为他发言。我乐于估量、确定,并趋向对我吸引最甚并合情合理的那些东西——不会挂于秤杆,意欲称得少点——不会拟想一种场景,而是认定当下的一切,走在我唯一可行、任何力量也休想阻拦的道上。如果尚未获得牢靠的基础,我就不会放心地着手撑起拱门。不必玩那种踩着薄冰的小儿科游戏,哪里都有坚实的基础。我们曾读过,面对眼前的沼泽,旅人问男孩底部是否硬实,男孩给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旅人的马匹很快便陷入其中没及腹部,他便对男孩如此比画:“我以为你是说那沼泽下面是硬的。”“是啊,”男孩回答,“那是因为你还没走完一半。”社交圈里的沼泽和流沙亦复如此,但只有老男孩才会清楚。只有所想、所说和所做这三者罕见地保持一致才算可取。有人愚蠢地硬是在既已上灰的木板上钉钉子,我不会与此辈为伍,如此行事让我在夜间无法安眠。给我一把锤子,然后让我摸索着钉上板条,不要指望油灰吧。将钉子敲得到位,钉得结实,你会在半夜醒来满意地回味欣赏,不会羞于请缪斯嘉许认可。上帝会因此为你助力,也只有如此他才肯帮忙。每一枚钉好的钉子都应跟宇宙这部机器的其他铆钉相似,如此,你继续了造化的事功。
我不要眷顾,不要金钱,也不要声誉,给我真理。我坐在桌旁,上面摆满了佳肴和美酒,旁边是曲意逢迎的侍陪,但缺乏诚意和真情,我饥肠辘辘,离开冷漠的桌板而去。这份盛情寒冷似冰,我想,再无须拿冰块给它降温了。他们告知我那酒的年份,还有用以酿制的葡萄名头,但我想要一种更古老、更新颖、更纯净的酒,它由更光彩、更尊贵的葡萄酿成,这种酒他们没有,也无从购买。在我眼里,那派头、屋舍、场所和“款待”,都一文不值。我曾拜访一位帝王,但他让我在大厅等候,行止举动好像不谙待客之道。我身边有人住着树洞,却有地道的帝王仪范,如果前往拜谒,感觉想必更好。
我们坐在门廊里奉行无聊陈腐的美德还要多久?做任何事都不会比它粗鄙荒陋。恰似有人在饱受折磨中开始一天,却要雇人薅锄土豆,而到了下午,又揣着策划已久的良愿履行基督徒的恭顺和慈爱。我们是何等年轻的哲人和实验师!我的读者中尚未有人体验过完整的人生,那可能只是人类生命中的一段春光而已。纵然我们经历了七年之痒,也尚未经见康科德的十七年之蝉。我们对生活的地球仅仅了解一层薄膜,多数人连地下六英尺都不曾钻研,也没有向上跃至同等高度。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且终生有一半时间沉于酣睡,然而,我们却自命智慧,在地上制定了规矩。我们真是沉潜至深的思想家,我们的确是抱负非凡的精灵!当我在林地上俯视松针丛中蠕动的虫子时,它便费尽气力地藏匿自己,我深自纳闷:它何以会执着于卑微如许的念头,自许自珍,而对我藏头缩尾?或许我还能为它施惠,将喜讯带给它的同类。我由此想到那伟大的智者和恩主,他不正在俯视我这条爬虫?
新颖事物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世界,我们却对难以置信的陈腐物什安之若素。只需提及,即便在极其开化的国度,人们依然在聆听何种训导。那里不无欢欣的诉说,忧郁的陈述,然而,那只是用鼻音哼唱的圣歌叠句,心里依然放不下庸常和鄙俗。我们认为自己能换的只是衣服。据说大英帝国无比强大,荣耀加身,美利坚也荣列强国之林。我们却不相信,人的身后都有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潮,只要这股潮流涌入他的心灵,就会使不列颠帝国像草芥那样逐流浮沉。有谁知道,从地下涌出的下一拨十七年之蝉又会是什么品类?在我生活的那个世界,其政府建构不像英国那样,只需宴后侑酒而谈便告完成。
我们的内在生命好似河水,可能会在今年泛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焦枯的高地浸入汪洋,乃至今年可能就是多事之秋,将会淹毙所有麝鼠。我们所居之处并非从来就是干地,我在遥远的内陆就见过古代河流冲刷的堤岸,彼时尚无科学记录。有个传遍新英格兰的故事人尽皆知,据说有条硕大漂亮的爬虫从一张果木餐桌的干透桌面钻了出来,果树活着时,那虫卵就寄居其中,这张餐桌摆在农家厨房,当初是在康涅狄格,后来到了马萨诸塞,根据上面的年轮可知,已有六十年之久。当时,人们听到桌子中的咬噬声响达数周之久,可能是就近盆罐的热量孵化了它。听了这个故事,有谁不会对复活和不朽信心大增?又有谁知道,在干枯腐朽的社会里,存有何其美丽、身带羽翼的生命,其虫卵长年处在层层围裹的木头之中,起初,它居于绿意葱茏的边材里面,而这棵树木逐渐老去,最终显出了于它非常相宜的墓冢特征——那咬噬之声已有多年,就在家人欢度节庆,围坐桌旁的时候,偶有一两声传了出来,令人惊愕——可能,不期而然,这条生命会从烦琐无比的社交行头和庆贺陈设中脱身飞出,最终享受它臻于圆熟的生命光辉!
我并不是说约翰跟乔纳森会明白这些,这是明天的特征,但仅凭时间流逝却无法迎来它的黎明。让人目盲的光线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片黑暗,只有苏醒才有黎明,然后,黎明会接踵而至。太阳,无非是一颗在早晨升起的星星。
[美] 亨利·戴維·梭罗
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哲学家。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1841年后转为写作。曾协助爱默生编辑评论季刊《日晷》,一生支持废奴运动。主要作品包括《瓦尔登湖》《非暴力抵制》《河上一周》等。
仲泽
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从事语言教学研究及翻译。译有梭罗作品《瓦尔登湖》《四季之歌》《夜色和月光》等。
《梭罗文集·瓦尔登湖(木刻插图本)》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仲泽 译
译林出版社/2020.10/8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