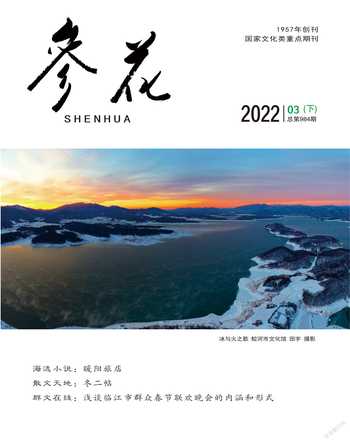冬二帖
我写的是两个节气。是冬天里的大雪和小寒。
大雪小寒,像一对姐妹,乡下的丫头,一冬农闲爱绣花。她们在白冬的底色上绣生活呢!绣黑瓦檐下粗大的冰凌,绣灰烟囱里瘦薄的炊烟,绣旧牛棚内嶙峋的老牛……瘦骨凛凛的冰雪寒气里,小日子清汤寡水,像老僧,吃斋念佛一样的寡淡。却踏踏实实,把每一寸光阴都过成自己的良辰,满足着呢。用尽力气,热爱。
朔风知我意,吹我回少年。
所以,我也是在写昔年的冬二帖里,那些虽面黄肌瘦,筚路蓝缕,却精神温暖又明亮的故人。大雪,小寒,有阔朗的老戏隐隐而来,廓然,清冽,被老光阴里草木灰气息的风裹挟着。泡一壶老白茶,心事從容,看锣鼓声起,旧事重提……
大雪
大雪。二十四节气中,最像小妇人。
白雪横窗带仙气,有诗意,雅得过分,十指不沾阳春水。色温生动烟火气,热腾,又质朴,最民间。
枯黄的草叶拴住一羽、两羽……白的雪铺就白的衾,怎么会衾寒枕冷呢?鹅毛般的雪花瓣正燃烧着爱情呀,仙女集体思了凡,爱上了北方苍郁的汉子们。织女恋上牛郎的草窝,一冬无粮也不嫌弃。
天庭无情味,人间好生动。端正好光阴,安分守己呢,生儿育女吧。
旧光阴里的大雪节气,重情重义,刻骨也铭心。少年透过贴着窗花的木窗棂,看大朵大朵的雪花渐渐堆满对面的黑瓦檐。娘在灶间里咳嗽,湿柴生闷烟,定是呛得她满脸的泪涕。红薯粥单薄的香味在茫茫雪气里打旋儿,少年抽了抽冻得红红的鼻头,饥肠寡淡,却神思正茂密,想起《红楼梦》里,大雪那一天她们的奢华。
彼时,少年像被摄了魂魄似的,痴想着哪怕若能做个暖香坞里,那个被嫂嫂称为“心冷口冷心狠意狠”贾家四小姐惜春的三等小丫鬟,也心甘,也情愿:捧个漱口的盂,净手的盆,也好啊!尚能落得了一身脂粉香气和玲珑笑语,也能穿香而过,像兰汤里沐了浴呢。那颗泊在贫寒里的心,也能往妩媚里靠一靠,不至于太悲情呢!
大雪里少年的痴心妄想卑微到了雪泥里,冬眠的种子,来春也苏醒不了,长不出羞惭几株。鸿爪雪泥,多年后,我对遥远光阴里有那种念头的少年的我,嗤之以鼻。
大雪里,湘云和宝玉架火烤鹿肉呢。火红的炭,洁白的雪,喷香的鹿肉,锦袍裘氅的少年,富贵闲适的人生。
雪花探着身子想飞进来,旧木窗前有点妖气,戏弄十三四岁的少年,猝不及防脸蛋上就被亲了一口,冰冰凉凉,柔滑的香。少年时的雪花是有香气的,分明是小女子手帕子冲着情郎颌下一甩,含羞带媚,一股子幽香。雪花有体香。
彼时,窗外大雪窗内冰。捧读书页泛黄的《红楼梦》,我十指冻僵,根根像娘挑出来扔给小白兔的红萝卜,又细又硬,窝里胖兔子的三瓣嘴拱一拱,一兔脸的嫌弃。
书里的他们锦衣玉食,百般的金尊玉贵。可我,连一瓶城里堂姐姐那样的雪花膏都没有。她只赏了我用剩下的旧瓶子,旋开盖子,指尖探一探,少半个指甲盖就能触到底。终究是平日里舍不得用,宝贝似的压在粗布褥子下。
过年穿新布衫罩旧袄,才配得上雪花膏。娘细心地给我编一条四股的麻花辫,油黑发亮,搽了一点她极珍贵的桂花头油,梢头扎一朵红绒花。对着小镜子细细地涂薄薄一层雪花膏。齐齐的刘海,红脸蛋,咋看着就像旧社会的童养媳呢?一副小娘子的味道。
把大观园里的小丫头子们对照了个遍,都带几分书香和灵气呢,唯独我没有。居然不如她们的丫头们!我不委屈,不怨艾,也不自卑,突然觉得自己是《红灯记》里的铁梅,提篮小卖,根正苗红好家风:奶奶,你听我说……
豪气万丈一低头,绿漆斑驳的小木桌上,一碗寡淡的红薯粥。再低眉看看下地窖掏红薯时弄得一身掸不净的湿泥,倏忽间,自卑就邪恶地狞笑着迎面走来了,我缩了缩瘦小的肩头,像躲在梅花后的小乞丐,衣衫褴褛,还能挣扎着直起灵魂清贵的小腰身吗?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望梅止渴吧。想一想《红楼梦》里,大雪天里有鹿肉也就罢了,居然连“诗情画意”这雅玩意,也给大观园的一团贵气里,锦上添花!看呀,白雪天她们从栊翠庵落得一枝枝梅花插瓶。贾老太太也跟着凑热闹,雍容富贵牡丹之姿,又诗情饱满,白雪世界里颇有老梅花之意。好一个仙境般的大观园,雪花如小仙,不羡瑶池羡人间,不顾羞涩,铺天盖地,投怀送抱。
看看身上娘给做的青布对襟袄,黑布软棉裤,突然就想起那十来位千娇百贵的女孩,她们一色的大红猩猩毡的斗篷,都是羽缎羽纱的,映着琉璃白雪,好不旖旎啊,羡煞!特别是黛玉: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
那么孤清纤弱的女孩,裹在一团避雪华裳里,几多娇嫩嫩的美,团宠的怯态。好不让人生怜。
白雪为媒吧。十来位女孩儿都冰清玉洁,无一人妖气离离。我就让宝玉的眼睛一直放在林颦儿的一举一动上。隔着白雪翻飞的羽翅,趁着曹翁打盹儿的当,我愣生生地给纸上加了一笔,给宝玉一个爱意直白的特写。我愣头愣脑,莽撞又自信。粗通文墨又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妄想,更是因为偏爱林妹妹,什么宝钗、宝琴都走开。我在旧柴门里隔空抛一根红线,牢牢拴住一对玉儿的手腕,度红尘中有缘人。莫笑少年狂!营养苍白,精神明亮,大眼睛少年哟!
我彼时,洋洋得意。忘了娘小灶屋里一声声带着愠色的呼唤。起床了,喝汤,热气蒸腾的红薯汤……那年那月,大雪,带着一股红薯味儿。贴心又贴胃。
漫天大雪载着我的痴想,孟浪,漫无边际,载歌载舞。饥肠辘辘的少年和村庄,丰衣足食的却是少年茁壮的理想。那理想热气腾腾,日月璀璨呢。
倔强啊少年,勤奋啊少年。对所爱捧出倾城的喜欢,像雪花,明明艳艳扑向我的村庄,抱着饥渴板结的土地,滋润啊滋润,土膏像木讷的汉子渐渐有了回应,一点点舒展,松软开来。雪花和土地千万颗爱情的种子啊,貌似冬眠着,却在热烈地孕育。只待春风一起,便掀掉白被子,抱出一地铺的绿娃娃,农夫像公爹,又羞又喜,宠溺万千呢。
我在自己逼仄的一亩三分地的王国里,自立为“女王”,摇曳着满头的珠翠,下旨:造良辰美景,姹紫嫣红开遍。造一座你侬我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新红楼。林妹妹和薛姐姐各得好姻缘。从此后林妹妹面如桃花,不再珠泪儿暗洒闲抛,实实在在,一把摸得着的“木石前盟”,新鲜鲜的一枚小妇人,小富贵添丁进口,儿女绕膝呢;薛姐姐也不再芳心暗渡,无须借薛姨妈之口、赖头和尚之嘴,说什么“金玉良缘”了,终于觅得了如意佳婿,举案齐眉去了,扮公宠婆爱的贤妻良母去了,各得其所。
她们的好日子。白雪从大街小巷倾巢而出,红红的软轿子,汩汩滔滔的唢呐,热烈的红鞭炮谄媚,讨喜,白雪上艳艳绽落千朵红玫瑰。
夜半,一朵雪,兩朵雪,雌雄情话。我在大雪里忙里忙外。我不是送旧帕子的晴雯,也不是操碎心的袭人,不是痴忠的紫鹃,不是口嫩语拙的雪雁,我就是庄公梦蝶。我是少年的曹翁小书童,替曹翁着了急,自作主张,在《石头记》上涂鸦,信手,孩子气,初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确实符合中国人观剧的心:福禄寿喜,花好月圆,皆大欢喜吧。
大雪似乎要掩了柴门,柴门还未醒来。吱扭一声,是爹娘披着棉袄轻轻咳着在扫雪。我的梦戛然而止。热乎乎一碗红薯粥。
小篱笆院是大雪襁褓中的婴儿。黎明即啼。新鲜鲜的好听。
大公鸡,小黄狗,鸡飞狗跳,热气腾腾的人间,万般美好!我繁华的梦,随着我故作文人书生的风雅状掩卷,而止,虽藕断丝连,但肉体还了魂,从曹翁的宽袍大袖里偷偷看尘世。
大雪里,摇摇晃晃的灶屋,纤纤细细的炊烟,爹爹佝偻着高高瘦瘦的身躯,娘亲一张不施粉黛不失清丽的脸。柔软的小白兔顿时从心里跳了出来,带着我千般万般温软的爱恋。我不眼煞遍身罗绮的大观园。我深爱我的爹娘,我贫瘠的篱笆院,我生锈的大铁锅,我深深的红薯窖,我屋檐下吊着的冰凌和红辣椒,我冻得缩肩缩背的大白菜……
我大雪的少年,阔绰得情味横流,烟火浩荡啊!
彼时,少年的心里一团火啊!我深爱的娘,大雪染不白的青丝,夜夜好繁忙,女红上了灯花。我深爱的爹,大雪染不白的黄牙齿,一管旱烟袋,指点家事,如指点他的一檐江山。
大雪,小烟火炮制节气之气,生活之气。爹娘不知道红楼,只知道红薯。大雪之下的一窖红薯,是我和哥哥们六个孩子的好口粮。
“碌碡顶了门,光喝红黏粥。”白雪满天飞,天冷不串门,只在家喝暖乎乎的红薯粥度日啊!红薯粥,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细粮少,红薯凑。娘在黄昏里,指挥我和哥哥们下地窖掏红薯,我是金贵的女孩呢,胆子小,怕蛇,怕黑呢,只在窖门口和娘一起提溜绳子拴住的红薯篮子,扯着哥哥们又黑又脏的袖管往上拽。
压水井里的水,大雪天里冒着热气。把沾了泥的红皮红薯洗净了,放进大铁锅里烀。各家各户吃红薯的方式和时间都相同,开村民大会似的,老槐树上的大铁钟无须撞,也早就不撞钟了,那已是久远年代的旧事了。可黄昏时烀红薯的香气,听到拉钟似的云集而来。顿时,淹没在大雪色的小村子,被红薯的香味儿攻城略地般的占领了。
猴孩子们扯着一角棉衣襟,包住刚出锅烫手的红薯,高高地站在村头土坟包、石磙上摇旗呐喊,扮小鬼,扮张飞,扮山妖,少不了偷出来爷爷的瓜皮帽,娘的绿头巾,姐姐的红肚兜……如鬼怪出洞,四方震动,鸡犬不宁,喝了烈酒似的欲上房揭瓦去,把五脏六腑里十五六年长出来的壮气,都撕破了口子倾泻出去。
雪旷村子瘦,任由青春撒了野,撒了欢,一场大雪全了少年的心。惊得雪后觅食的鸟雀“轰地”一下四处里散,不甘心呢,时不时扑下来,眨着小黑豆鬼机灵的小眼睛,飞快地抢食少年们洒下的红薯皮。
大雪里一群光脚穿棉鞋的少年。袜子太奢侈,那是城里人的物件,矫情。天黑回了家,少不得挨一顿骂,娘扯了干柴给烘烤湿透了的新鞋和棉裤脚。
娘除了烀红薯,还精心地熬制红薯白米粥。我们兄妹六个端着大瓷碗满村里串,直到各自收集够了满碗眼馋的目光和哈喇子,方才自在回家转。我有一个做裁缝的姥爷,每年大雪的馋冬,会给我娘一小袋极珍贵的白米。村里的小妇人们各种理由来讨要,娘大大方方地赠予,一脸白雪公主般的纯净圣洁,更像赠人甘露的观音娘子。
哪个少年敢说没吃过我家的白米?多年后回家乡,偶遇胡子拉碴的汉子们,当年儿时的小伙伴,还亲昵昵地喊我白米公主。我霎时就挺了挺依旧婀娜的小腰身,一副被故乡娇宠的公主霸气范儿。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大雪节气的风俗之一就是腌肉。“未曾过年,先肥屋檐”,说的是到了大雪节气期间,腌腊肉,灌香肠。
极淡极远的年代,食能果腹,粗茶淡饭也是一户好繁华。腌腊肉,灌香肠,村子里百家能有几家?寥落如晨星。即使有节余,也不做吧,孩子们的食欲禁不起挑逗,与红薯,与粗粮,那是糟糠之妻长厮守,就像凤姐说的,她和平儿是“一对烧煳了的卷子”,不能见美人,黄脸老妻见惯了的,等一日遇了腌肉腊肠这肉香香的美人,偶尔亲近了那么一两回,还不得是贾瑞遇见了凤姐一般难以把持吗?即使凤丫头不毒设相思局,瑞公子也会得下相思病。抓耳挠腮地想,坐卧不安,魂不守舍呢。
彼时的穷孩子和贫村庄,安贫乐道,肠胃清寒,而大脑清晰呢!他们是雪被下的种子,暂且冬眠呢!等春风。
少年的大雪前,村人们已忍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饥荒,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呢!三五个月的光阴不见油星子,攒着一点丰腴过了大雪过大年呢!七大姑八大姨呢,人穷礼节不能穷,瘦骨也凛凛呢!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馋呀!馋得吃饭直咬腮帮子。我家那几个牛犊子似的哥哥,日日清汤寡水,食肠反而更宽大,个个饭碗换成了盆。一簸箩锅饼一顿净,粗粮、红薯都告罄。娘又怜又爱又无奈,直呼他们是直肠子的小驴,没嗉子的呆头鹅。愁得爹一袋接一袋,旱烟抽得一间屋子烟熏火燎,呛得花脸猫跳到窗台上,冲他愤愤不平地叫。爹黑着脸,一鞋底子砸过去,它怪叫一声,破窗而逃……
终究是娘出了面,去镇子上老爷的裁缝铺子帮了几天工。熬红了眼睛,带回了一袋玉米面,一布兜鸡蛋,一块猪肉。家里过年似的欢腾开了。娘是千金小姐,是织女,是阳春白雪,嫁给了爹,像嫁给了牛郎,从金窝窝住进了牛棚呢!
娘是爹的白雪公主。住在简陋的屋子里,住在爹的心尖上。一直是。
哥哥在柴门内覆着厚厚白雪的一角落,扒拉好半天,露出墨绿老迈的菠菜,挂着碎硬的冰碴子。送菠菜去呀,再抱上檐下失了水灵的白菜。避开爹严厉的目光,溜着墙角跑出去。大雪呀,大雪……大雪站在不远处等着他。
村野出俊鸟,小家子气的女孩,青布小袄黑棉裤,黑溜溜的发,白生生的脸。清秀不水灵,像大雪里的一朵瘦梅,寒气里蜷缩枝头未舒展,等阳光呢。大雪的眼睛冬天也荡着春水的涟漪,我见过,楚楚动人,勾魂摄魄。哥哥的魂儿被勾了去。村里论辈分,他喊她“雪姑姑”。
他涨红着脸喊得生涩又费劲。
我突然觉得哥哥像金庸笔下的杨过,大雪是小龙女吗?
大雪没有小龙女轻纱一样的白衣,也不是冷若冰雪,小门小户的女孩,也清丽也碧玉呢。哥哥正是情窦盛开时,对雪姑姑动了真情,堤防溃决,情意如潮呢。爹古板,守旧礼。同村同姓怎能婚配,且不说还乱了辈分,老脸往哪搁?大雪也染不白一世的好清名。
可雪姑姑雪地里一身青布棉衣,分明是玲玲珑珑一朵梅。
她唤着哥哥的乳名,软语又低声:牛儿,你喜不喜欢我?最深的妩媚和楚楚。
刹那间,村规的陈腐律令交了械,像白胡子的族长颓废地仰天一声叹,威仪被侵略,一地碎片。
柔软的往往是世间最锐利的武器,无坚不摧,战无不胜。
雪姑姑泠泠玉语,耳边似乎只听小龙女柔声对杨过道:“过儿,你过来。”
杨过依言走到床边,小龙女握住他的手,轻轻在自己脸上抚摸,低声道:“过儿,你喜不喜欢我?”
爱情,一旦冰清玉潔,前世今生,便美得不像话。
那个青布斜襟袄的大雪,冰清玉洁的女儿态,却又风情万种。
她绣的鸳鸯戏水鞋垫儿,缝做的天青色小背心,桃花灼灼的手帕子,都妖娆,都风情。声音也婀娜,会撒娇。哥哥顶风冒雪地给她寡母买草药,送白菜,甚至偷了娘做的腊肉。
我趴在木窗上看白雪飘飘,看发了情的哥哥春心荡漾,似乎一副天荒地老、白首不分离的架势。
终究雪葬了那一段缘。关于哥哥和雪姑姑的,多年后,爹绝口不提他心中的那一段“孽缘”。至于棒打鸳鸯的“罪魁”,生生拆散牛郎织女的“王母娘娘”,爹一直坦荡着呢,无愧无惧。他这副模样,哥能忍吗?雪也能忍吗?
前世姻缘天注定吗?谁说的呢?老掉牙的黑白电影《小二黑结婚》里三仙姑说的?读书、看电影有点杂,小脑袋里枝角横生,张冠李戴,也是有的。我才不信呢。到底是激情如春潮,退潮了,沙滩上水中月雾中花,明明白白露了原色。就明明朗朗,大浪淘沙摆在那了,你看吧,自己看吧!要还是不要?
月老自有好安排。哥哥娶了大雪外可人心意的女子,雪姑姑嫁了比哥哥还威武的军人。都是良缘,幸福着呢。多年后,两家的儿女联了姻。
可惜,爹已不在人世多年,要不然呢?
旧年的大雪节气,有村意,回味动人。当初,少年大雪里深埋下理想的绿种子,不屈亦不惧!如今呢?长成了织锦的日子,一直在华美,在盛放。
小寒
节气有古意。小寒,像二十四节气的第二十三个女儿,尤其在诗里,不仅有古意,还清孤。在人间,也小民,接地气呢!
小寒惟有梅花饺,未见梢头春一枝。
吴藕汀在他的《小寒》里,捧来了梅花。给那日的小寒殷殷送去呀!小寒是诗词里的小寒,像披着白锦袍的女子,只喜欢在青花瓷的瓶中插几枝绿梅,闺房里雪洞一般,姑娘只在鬓边簪一朵颤颤的白玉珠,梅花状的。无关人间烟火事啊!
白居易也在小寒前后那几日,酿好了淡绿的米酒,烧旺了小小的火炉。天色将晚雪意渐浓,能否一顾寒舍共饮一杯暖酒?浪漫,闲适。透着富贵。白居易喝的是唐朝的酒,话的是唐朝的事。风花雪月,也没有柴米油盐。
诗人喝酒作诗过小寒。小寒风雅像女子,是深宅大院里的闺秀。贵气滋养着她的骄矜。清贵,书香,又透着隐隐的寒气,冰清玉洁,只读书,只喜欢墨色的白色的裙,不施粉黛,对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冷冷的孤傲,看也不看一眼,拖着曳地长裙兀自走过。像《红楼梦》里的妙玉,像《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寒。在唐诗里,在曹翁笔下,在古侠剑气里。它真真像极了金庸笔下的李莫愁等人,性情清冷,却美若琼宇梨花。动不动就蛾眉倒竖,长剑呼啸。
小寒在民间呢?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呢?是不是像国破被掳的亡国公主,是不是像家道沦落的闺秀,是不是像《红楼梦》里千般娇贵的巧姐,流落到刘姥姥的粗茶淡饭里,成了板儿的媳妇呢?居家过日子,一粥一蔬地算计着过?
民间的小寒,清苦是清苦的,却透着柴米油盐的香,像扒开土膏埋下红薯,野地里吃得满嘴黑,又心满意足的香甜。我少年时的小寒,满溢着穷孩子野地里烤红薯的味道。那味道和香气犹如小鬼狐附体,缠绵在我的少年。
记忆中的小寒,虽然,它像衣衫单薄的少年,面黄肌瘦,哆哆嗦嗦,冰霜里的寒号鸟一样,但是,接地气,像红薯面窝头,筋道,有嚼头。筋骨凛凛,支撑着乡下穷孩子伶仃的理想,倔强,不屈,向着不远处的春天,争奔。偶尔,中年回头,那个昔年小寒中的乡村,潦草,却铮铮。虽贫犹荣。
彼时少年。每到小寒,天气就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似的,所有的怨艾都一股脑地发泄出来,蹂躏缺衣少食的乡下穷孩子。冷若冰霜,雪上加霜。我最不喜欢的节气,就是小寒。干冷干冷的,冷的寒鸦都哑了嗓。天空灰扑扑的,一副欲雪不雪,老态龙钟的样子。
小谚说:“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
不喜小寒,尤其讨厌娘给做的棉衣。笨手笨脚的娘,也是被姥爷娇宠坏了的,不会做饭,不会做鞋,更不会做棉衣。每年的棉衣,新做的,翻新的,都做成了一个模样:像又肥又笨的邻家傻媳妇,皱皱巴巴苦着一张脸,怎么抻巴,也平整不了。那时我常常盼着二姨来,二姨做的棉衣,和她人一样,又美又苗条。绵柔,合身。碎碎的小花布棉衣,还给我带来一双绣花小棉鞋。穿着它们去上学,心花开成了一朵梅。
有一年,二姨一个冬天都没来。我偷偷把娘做的丑婆娘一样的棉衣,扯了线,掏了絮,一条腿薄,一条腿厚,穿着去上学。被同学讥笑是小事,还冻得寒号鸟一样哆嗦,娘一摸额头,人成了烫手的火炭。至今,还怀念二姨。美人似的农家妇人,美人似的农家小棉衣。把彼年的小寒,点缀得新嫁小娘子一样俊,土是土了点,却像年画一样古朴又喜庆。
小寒,在古书和古词里,风雅,孤高。披着黑锦袍白锦袍呢,冷冷的,不理人。可在我的少年时,小寒却像乡野丫头,贫瘠是贫瘠,却像村里宣传队的女孩演《红灯记》的脸蛋,沾了白扑扑的粉,俗气又喜庆,民间着呢。
“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记忆中,小寒到来时,在镇上姥爷的杂货铺帮工的娘,会带回来一只羊腿。那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呀!粗粗的麻线绳捆粽子似的,缠结实,高高吊在屋梁下。细细地吃,一直吃到年三十。爹会做饭呀,是四邻八村红白事的大厨。我和哥哥们,每天晚上都挤到又黑又窄的小灶屋,像一群冻得敛翅的鸡子,挤挤挨挨地争着往灶前那点子暖火凑。爹砍下极小极小的一片羊肉,切一棵大白菜,撒一把干椒碎,煮起一大鍋的羊汤,香气在瘦瘠静寂的小村里飘散,能砸死一头牛。
饿,这个字,是带了兵的主帅,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夜晚半梦半醒之间杀将过来,只需片刻,就杀得少年们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肚子里此起彼伏地咕咕乱叫,如一炕青蛙。
村里几个半大小子实在馋不住,从被窝里爬起来,穿着四处开花的撅腚破棉袄,讪讪地踅摸来,倚门边,蹲门槛,吸溜着清水鼻涕,眼巴巴盯着我们手里的碗。娘从我们六个人的粗瓷碗里各匀出一小勺,冒着热气递到少年凉凉的手里:尝尝,都尝尝!祛祛寒!
漂着白白菜帮子,红红干辣椒,那些年小寒前后的羊汤,几乎不见肉的羊汤,暖了多少少年漫长无趣的冬夜。记忆里的佳肴美味,许多年,那么香,是羊汤的传奇哦!
爹一口也不喝,他抿着那些红白事的主家送的小酒,很惬意,很享受。笑着说我们:一群小馋狼!会有那一天,让你们敞开肚皮吃个够……一灯如豆,爹的眼里有晶晶亮的东西在滚动。多愁善感的少年,当时也被热气哈了眼。
这些年,小寒,每到小寒,除了爱臭美的棉衣,滚烫的羊汤,还会有一个清瘦的身影被往事带出来。
一看到“小寒”两个字,就想起那个名字叫小寒的女子。彼时,她十八九岁,一副梨花带雨的娇怯模样,她嫁给了我的堂兄。因为她的名字冬天里叫着就冷,那谦卑的女子好像欠了村里人一笔债似的,轻轻笑着:小寒那天出生的,娘给取的名儿。一副忍气吞声的温顺模样。堂兄脾气暴躁,还酗酒,时常动手打小寒。黄昏放学时,经常看见小寒在牛屋旁的老槐树下嘤嘤啼哭。寒冬里,她背影单薄得像一张挂在老槐树上的画。长长的黑发遮盖了肩头,远远望过去,美的又像蒲松龄笔下的女狐。这个无父无母的外乡女子,流落到村子里,像她名字一样的孤寒。
少年记忆里,天寒野旷。小寒是苦,但苦里总有一股力量,是冬眠的僵芽,雨水只要一敲锣,顷刻间就会排兵布阵,好戏要在春天演。
近来读书,忽然发现,小寒是最有情有义的节气。探梅,冰戏,腊祭,吃腊八粥,画图数九……民俗灼灼,都像是阅尽人世沧桑后的或浓烈或禅净。
小寒不苦。故乡里那个叫小寒的女子也不苦,她早就重遇了一场两情相悦的盛大爱情,潺潺水气,皑皑白月,地久天长,柴米油盐过细碎的生活,精神明亮又温暖。新爱情的结晶一个叫小安,一个叫小暖。小寒的人生,安暖,妥帖。哪里还有苦寒?早就温润成苏堤的雨,白堤的月了呢!百般的美与好。
我眷念小寒之下的旧事故人,烟火,动容,天长地久;也喜欢小寒之下的诗人雅趣,也丰盈,也孤清。
作者简介:朱盈旭,笔名梅妆。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学习强国平台”、《大河报》《散文选刊》《参花》《散文选刊·海外文摘》《东方文学》《黄河报》等,著有散文集《杏花微雨》等。现供职于商丘市文联。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