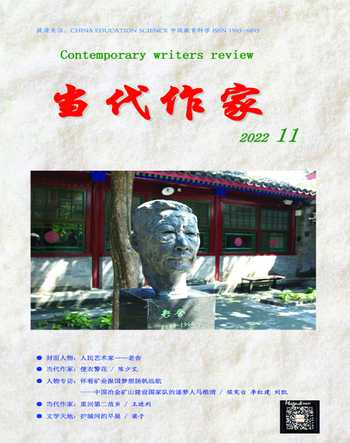顺小王的父老乡亲
孙朝剑
我们家不是本地的,但只要有人问及我“哪的人”时,我回答都是“顺小王人”,而且从五十年前,上初中填第一张入学登记表开始,在“原籍”栏目内都公正规范地写上“静海县蔡公庄公社顺小王村”,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社”改成了“乡”,再后来改成了“镇”,但“顺小王村”这几个字从未改写过。一直到退休前的两年,组织部逐项核对履历表中的内容,并多了个“出生地”栏目,还在填表说明中做了“出生地就是原籍”的规定,我才按要求把原籍改写成“河间市米各庄镇后榆杭村”。但是,在组织部的“填表”之外,涉及“哪的人”时,我一如既往地回答“顺小王人”。因为,在我们艰难落魄的时候,顺小王村给了我们雪中送炭的帮助,真诚热情的关照,让我一生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六次安家
1967年春节刚过,静海县蔡公庄公社召开了公社、村、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午休时间,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赵铁夫,把王虎庄村革命委员会主任桑仲青,土河村革命委员会主任毛之江和我父亲喊到他的宿舍正商量把我们全家迁到哪个村的时候,顺小王村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凤岐推门而入,见此场景便说 “你们在研究事啊?背我吗?背我,我一会儿再找赵(铁夫)主任……”
“不背,不背!” 赵(铁夫)主任一边回答着一边用手指了下我父亲, “这不,占学因为他父亲的地下党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政策,也成了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还在太平村劳动改造呢,他老家那个村红卫兵小将们不懂历史,
还旗帜鲜明,天天揪这个,斗那个,娘儿几个没法过日子,咱不能看着不管啊!我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也算是根叶红躯干硬,我了解战争的经历,主要是咱不能总看着好人受委屈啊!我想把他们迁到咱这来,正研究去哪个村落户呢……”
“去顺小王吧,俺们村就是穷,只要不嫌穷,我们热烈欢迎!”杨凤岐非常响快的说。
“你们村……” 赵(铁夫)主任皱皱眉,正要说别的。我父亲立刻站了起来,冲着杨凤岐拱拱手 “那就多谢了,就去顺小王,我们不怕穷!”
在场的桑仲青和毛之江两位主任几乎异口同声,“顺小王一个工值才一角三分钱,孙校长,你可要想好啊!
父亲笑了笑 “我想好了,就去顺小王!” 也许正是 这个“穷”字刺碰了我父亲脑海里那根警觉的政治神经,才毫不犹豫地下定了决心。
说迁就迁,不到一周时间,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母亲和部分物品;我(十三岁)卸掉了舅舅 给的大铁驴自行车的车坐子,骑大樑带着八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妹妹;当家子的福宠爷和学敏叔(奶奶的娘家侄儿)用淮海战役支前的那种小推车,推着我们家的全部家产,在一个清冷的,天蒙蒙亮的早晨,毅然决然离开了那个祖祖辈辈居住却带给我们伤痛的村庄。
我望着微微泛红的天光,背井离乡的茫然,对新生活的期盼,随着天色越来越亮,在心头堆积、沉淀、又逐渐模糊……
我们骑自行车比推小推车快很多,太阳快落山的时侯就到了顺小王。我们直奔大队部(现在的村委会),那时大队部在村中心高台上李如海家的西偏房内,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凤歧正坐在办公桌旁,见我们全家人到了跟前儿,“哟!还真上俺们村来啊!”惊讶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对我们的到来,显然是没有准备的,或者说,压根儿就不认为我们真的会到顺小王落户。
那个年代通讯非常不方便,如果把我们起身赴顺小王落户的相关事宜告诉杨凤岐大伯,得骑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五十里之外的河间县邮政局打长途电话,再加上县、地、省,省、地、县邮政局之间反反复复地转接,就得三四个小时,如果打电话的人多,或某县某公社开电话会或广播大会占用线路,就得等一整天,因为许多情况下,战备线不能用,地、县之间仅有的两棵民用电话线还经常用来开广播大会和传送县社村之间的各类通知和民用电报等等……
总之,突然到来的我们一家五口人,确让杨凤歧大伯有点措手不及,……
“先住下,先住下,……住哪呢……?”杨大伯正左思右想并吟吟出声的时候,张宝新大伯进了屋,“孙校长来了,这么晚了来顺小王,有事啊!”
当知道了原尾后便说:“住我们家,”张大伯毫不犹豫,非常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了他们家,让两个成年的女儿和儿子都和他们挤到了一个屋,给我们腾出一间住下,并说“以后有合适的就搬,没有合适的就住我们家”。那种真诚和热情,一下让我们离开故土的不安踏实了下来……
晚上,张大娘蒸的虾酱招待我们,虽然是不值钱物,但吃起来,感觉比现在的炖鱼熬肉还香。晚饭后,大队革委会主任王砚恒和杨凤歧大伯一起去看望了我们,王砚恒主任告诉我们 “顺小王就是穷点儿,但是,有贫下中农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并告诉已经把我们安排到全村工值最高的第六生产队。
第二天晌午刚过,福宠爷和学敏叔用淮海战役支前的那种小推车把我们的全部家产推到了顺小王。当天晚上,我们就搬进了“新居”。
新居是民兵连长杨凤东家,杨凤东让自己的成年妹妹和父母搬到一个屋,自己住到了民兵连的枪械库里。
我们在杨凤东家住了半年多。虽然我们生活得很惬意,但是我们心里明白,我们住的这间屋是凤东伯伯唯一的新婚用房,却让给了我们。
为此,当我们找大队革委会求助的时候,王少洲爷爷找到我父亲,“他孙伯伯,我那三间房已经上盖儿了,就是泥垛的,潮点儿,如若不嫌弃,搬我那去吧……”王爷爷的雪中送碳让我们感动不已,因为季节已是晚秋,杨凤东及他的父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们搬走,一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才搬到王少洲爷爷家居住。后来我们才知道,已是大龄的杨凤东伯伯,为了不让我们住潮湿的屋子而推迟了婚期。
在王少洲爷爷家住了一年多,这期间,王爷爷家除了二儿子当兵不在家之外,一家五口人,为了我们全家挤在了一间屋内生活。
一年之后,王爷爷的二儿子要回家结婚,王爷爷背着我们让其旅行结婚去了部队,可半年之后,大儿子与天津知青成婚,没有房哪行啊!我父亲把情况向王砚恒和杨凤歧两位主任做了匯报,第三天两位主任就亲自动手,帮我们搬进了两间房子的住处。居所比原来宽敞了一倍,很是高兴,可喜悦的激情还未散尽的时候,知道了这家的主人叫刘炳珍,天津知识青年,二十岁,是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为了给我们腾房搬到了家族的一个叔叔家去住了……
尽管刘炳珍姐姐多次表示“我一个人,怎么都方便,况且我是在自己的叔叔家住,他们对我照顾不是更方便吗!”;尽管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们都多次叮嘱我们 “安心地住着。” “不要多想” 但我们全家心里总是觉得一个姑娘家,离开了大城市,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够不容易了,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居住,还得去寻宿度日,太难为她了,我们于心不忍啊……
在我父亲多次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说服下,两位主任也意识到了“让一个远离父母的女孩子寻宿生活 ”确有些欠妥”,于是当场决定,“一周之内,让闺女搬回自己家住”
只过了三天,我们就搬家了,……然而,我们搬进的是大队的磨房。原来,大队把四间磨房重新调整了磨粉机的位置,为我们家腾出了两间居住,我们一家子好感动,安顿好屋子的那一刻,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全家人的感受 “顺小王人真好啊!”,……于是,没过三天,我们就把与叔叔一家五口在一个屋里挤了好几年的奶奶从天津市和平区接到了顺小王。
转眼间,我们在磨房又住了一年多,虽然大队砍了两棵树当檩条,在磨房的东边用泥垛了个小棚子,存放磨完的面粉和未磨的粮食,但毕竟面积太小,给全村的社员带来了许多存放的不便,我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时候……“913事件” 发生了,中苏(前苏联)关系更加紧张,国家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措施,大城市一批又一批的人员向农村和山区“转移” 和“输散”,我的婶母和两个妹妹需要从天津市区迁到顺小王落户。大队革命委员会、毫不犹豫的签字接收了,但是来了以后住哪呢? 于是,无意中我母亲向张宝珊大娘(原民政局局长张家声的母亲)吐露了内心的不安和愁怵。张大娘一边听着一边紧皱眉头,并很快与张宝珊大伯叙说了我们家几次搬家的事实经纬和婶母一家也来顺小王落户的消息,张宝珊(时任府君庙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大伯主动找到我家和我父亲说: “我离家太远,想把你嫂子接到离我近点儿的地方,对我也是个照顾,你们搬我那住吧,一块给我看着家……”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张大娘一家搬到了府君庙公社的北五里村。
一处有偏房,有院墙,有大门的三间正房的独门独院便成了我们家。在当时,几乎全村的房子都没有院子,没有大门,我们三世同堂的十口之家,算是住进了别墅,幸福的喜悦溢满了全家人的眉宇和脸庞。
为了感谢张大伯一家的赐房之恩,春节时,父亲派我和二弟去给大伯大娘拜年,骑车六十多里路,到了静海城北的北五里村才发现张大伯一家四口,像之前我们家在顺小王一样,也是与村上的社员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处土房中,……我恍然大悟,张宝珊大伯哪里是为了让大娘对他有个照顾,分明就是为了让我们和婶母一家子十口人,有个落脚的处所,不再为住房愁得忐忑不安,也别再让全村的社员因为我们家的存在,磨面时都感觉着不方便而做出的倾诚付出……
盖房善举
“既然在顺小王落户了,就必须得盖房,别再给全村的父老添麻烦了”,我们全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向大队革命委员会提出了盖房的请求。主持日常工作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凤岐大伯给选了一块既在村内,又很宽阔的宅地,东西长二十米,南北宽十八米多,在没有土地红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全村也是曲指可数的一块好宅地了。
那时候盖房很简单,只要有了房檩和门窗,基本上就可以动工了,不用做碱(防碱质侵蚀的砖或石头砌垒的房基),用带埝草(各种杂草)的泥直接垛起,有劳力的户家,一般不耽误生产队干活,起早挂晚儿有一个多月功夫,不用求人帮忙,自己就大功告成了;有条件的,即有足够的麦滑秸(用碌碡轧过的麦杆)的,找几个人帮忙脱坯,干打垒(不坐泥直接垒墙),有十天左右,房就起来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埝草是个大问题,生产队分的和自己菜畦收的麦滑秸都加在一起,一年也不足百斤,得积存多少年才够盖房的啊!
全家都为此上愁的时候喜从天降,在顺小王参加劳动锻炼的新生农场(团泊洼劳改农场)四分场场长林庆和(渡江干部)林大伯听说这个情况后坐在了我们家的炕头上,告诉我父亲 “咱俩都是老团泊洼了,回来我安排一下,你们有个准备,麦收前让弟妹和侄子去农场打几天麦黄草,盖房做埝草应该没问题。”
1974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母亲带着林大伯的亲笔信,通过警卫部队的检查后进入场区,在场部职工宿舍住下,一个干部模样的军人把我们领到一望无际的条田边,用手指示着告诉我们,哪个沟里草多,哪个沟里草好,……说心里话,平生真没见过那么高,那么厚密的稗子草,我们就像在菜畦里割韭菜一样,割了三天,估计差不多够用了,回村和队长李庆如大伯要了辆马车把晾晒到半干的草拉回了村。正要卸车继续晾晒的时候,李庆如大伯走来,大声地召唤: “别卸了,把它拉到队房去。” 我有点诧异和发愣时,他接着说 “这么好的麦黄草当埝草,太可惜啦,再说,托坯也不好用,给生产队喂牲口,你家盖房时,生产队的麦滑秸你们随便用” “对!对!,脱坯还是麦滑秸好。”我和母亲都愉快的回答。
埝草解决了,大项投资就是檩条和门窗的过木了,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静海域内集市上卖檩条的一是太少,二是太短,三是太贵;于是我父亲就求领导,领导又求领导的领导,费了好大的劲,只搞到了一分木料(一根半檩条)的供应指标,全家紧锁眉头时,干了一辈子建筑的叔父告诉用八个圆的盘条,自己打水泥檩,比传统木檩的耐压强度要高几倍,使用寿命比木檩更长。但是,计划经济的年代,钢铁也需要指标。哪里去搞指标呢?副主任杨凤岐把我们家的情况在大队(村)革委会会议上做了汇报,革委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决议,让大队弹簧厂的业务人员向天津市弹簧厂求助,帮助解决钢材问题,并让技术员张道亮向我父亲寻问了所需型号等。外行的父亲担心八个圆的盘条承受不住压力,把叔父說的直经八个圆说成了十个圆,对建筑都外行的大队革委会领导们担心十个圆达不到耐压强度,又给增到了十二个圆,最后在天津市弹簧厂的支持和张道亮技术员的负责下,四间正房,东西三间偏房的檩条和门窗及门楼的过木所需钢筋、套子和绑丝全部得到了解决。 只收了516元的平价钢材费。
顺小王村北约500米处是机场的弹药库,村东约600米处是机场的油料库,村南约一公里处,是津浦铁路伸向机场的军用专线,在这“军三角”中心的顺小王民兵连担负着保卫空军机场的战备使命,是天津警备区的重点民兵连。冲锋枪、全自动步枪、高射机枪近百支,特殊的战略位置,特殊的武器装备,特殊的战略关系与机场驻军形成了特殊的军民鱼水情缘,机场的许多清擦油罐、基建养护等杂活或小工程都让顺小王人干。当听到我们们家要到县物资局去买石头子儿和砂子做水泥檩条的时候,在机场干活的社员们纷纷告诉我父亲,机场的一项工程剩下了许多石头子儿和砂子,他们还都分别给问过油料股的叶赤股长,都说“叶股长说了,没用了,让大队领导出下头即可。”于是,革委会主任王砚恒专程和叶股长一起去团部说明了情况,经团首长同意,砂石料全部得到了解决,给我们家不但省了料钱也没花运输费用。
1975年,五一刚过,队长李庆如大伯就给安排了二十多人,六 架坯模子,还有四个大婶给做饭,几乎半个生产队的壮劳力都投入到了我家脱坯的这项活计中。整整干了两天,村子南头的道边、坑边、井边、河沟边和六队的整个打麦场上,全部都是给我们家脱的坯。
脱完坯以后,李庆如大伯告诉我和父亲 “爷儿俩儿该干嘛干嘛去吧,坯的事就甭管了,晒两天把它立起来,干透了以后把它码起来,这些都甭管了,选个好日子做碱,麦收前不忙的时候把房盖起来。”于是,刚刚落实政策的父亲去大邱庄学校(中小学在一起)主持工作,我返回了热火朝天的大港水库施工工地的县团质控站。
我和父亲约好,五天以后是星期六,我们爷儿俩儿晚上都赶回家,并提前告诉市里的叔父求人搞点肉票,买几斤猪肉和韭菜送来,第二天(星期日)请五六个壮小伙子把晒干的坯码成垛苫好土准备盖房用。
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周五上午十点多钟,西北方向,乌云密布,天越来越黑,渐渐的有了凉风,队长李庆如感觉天不大对劲儿,有下雨的可能,于是 “ 别锄了!” 叫停了正在村西边锄着地的三十多人,“这天不对劲儿,咱得赶紧把孙占学家的坯垛起来去,否则,一下雨,这坯我们就白脱了!”说时迟,那时快,三十多个社员停止了锄地,跟着李队长疾步赶到脱坯的现场紧张地把一个一个哂干的大坯码成坯垛并迅速在上面苫上了厚厚的一层土。
可是,恶劣的天气也快速袭来,
风协着凉气,夹杂着尘土扑面而来,远处也轰隆隆响起了雷声,然而,四间正房,三间偏房,门楼子,墙头子的全部用坯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三十多人累得满头大汗,但码成垛的坯也就有三分之一,大部分晒干的坯都直直地竖着、呆呆地立着,惊恐地面对被大雨冲瘫的灾难。李队长见势不妙 “大家伙抓紧点,我再召唤点儿人去!”一边大声召呼着,一边奔大队广播室跑去。
大队会计王广远(原县工业局局长王兆仁的父亲),给开开广播,李队长气喘吁吁地拿起话筒“六队的全体社员注意啦,无论在哪干活的,都放下干着的活计,赶紧到村南边把我们给孙占学家脱的坯拾起来,否则,一淋雨我们就白脱了!”李队长用急促的声音广播了好几遍,最后喊了句“都动作快着点儿!”之后,也小跑般地向坯场赶去。
李队长离开广播室后,大队会计王广远大伯见天越来越黑,云越来越低,雷声越来越响,也拿起了话筒 :“全体社员注意啦,孙占学家在村子南边脱的盖房的坯都立起来晒干了,天要下雨,雨一淋这坯就全瘫了,离得近的社员们赶紧帮帮忙,给他家码起来!”王大伯反复广播了多遍。在村东南、正南和西南边干活的四队和五队的社员们听到广播都不约而同的瞬间一愣,脱口而出:“不立起来没事儿,立起来了就怕下雨”大家异口同声的议论着……
四队队长李振端,五队队长杨凤文像我们队长李庆如一样,听到广播,立刻“命令“ “走!赶快给孙占学家把坯拾起来去”!于是,一路召呼了好几处干活的,其中还有不属于他们管辖的第三生产队的孟凡杰等十多个社员,都疾步赶到村南边的路边、坑边、井边、沟边,投入了把干坯垛起来的“抢险战役”。一百多父老乡亲,在雷声和闪电中,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坯全部码成垛并苫盖好了土。雨水、汗水浇透了大家的身体,尘土、泥土弄脏了人们的衣裳,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怨言……三位队长都大声召唤着“大伙赶紧走吧,别都淋湿了!”人们很快离开了现场,但李庆如、杨凤文、李振瑞三个队长,和我们队的政治队长杨凤士、副队长李贵珠、民兵排长程书田怕人们在紧张的忙碌中土苫的不够厚或漏苫,又冒着雨逐垛检查并将芷得不够厚的重新芷盖了一遍。我家的坯像人穿上了雨衣,安然无恙了,他们却让雨淋得像水捞的一样……
多么好的乡亲啊,他们的淳朴、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令我终身难忘……
第二天傍晚时分,父亲、叔父和我分别从大邱庄、天津市区、北大港水库工地如期而至。听奶奶和母亲说完了上述这些情况后,都惊讶了,“没下雨啊!”我们爷儿三个彼此问寻着,都说“这一道没看到哪下雨啊!” 但顺小王发生的这一切,确是真真切切。惊讶之中,感动之下,我们爷儿三个顾不上长途跋涉的劳累,水没喝、饭没吃,赶紧分别到附近的街坊邻居家道声“谢谢!” 特别是在大雨中淋着雨给我家苫盖坯垛的四、五、六三个队的队长、副队长和民兵排长,我们爷儿三个一起逐一上门进行了望看,当我们问及“没让雨击着吗?” “没感冒吗?” 深表谢意的时候,他们几乎说的是同一句话,“谁知道了這事儿都会去帮忙,否则,那么多坯,不就白脱了吗!”,政治队长杨凤士还风趣地说“大伙给你们家做好事,老天爷给大伙做好事,周边村的暴土都没有压住,咱们村下透了!庄稼一宿长了一大块,以后天旱了,你们家就托坯,我们还去做好事儿!”逗得我们彼此都笑出了声……
一晚上,全家人回想着来顺小王这些年的朝朝暮暮,久久不能入睡……从进村那天张宝新大伯“有合适的就搬,没合适的就住我们家”那句暖心且真诚的话语,到杨凤东自己去民兵连的枪械库长期值班,把屋子腾出来让我们住;从王少洲爷爷盖了新房,自己没有享受宽敞,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屋生活,腾出一间给我们,到刘炳珍姐姐的两间房让给我们全家,自己在叔叔家寻宿;从大队改造磨房,让全村父老为我们家的居住承担不便,到张宝珊大伯全家迁到北五里村,把一处尚好的独门独院儿让给我们十口人三世同堂;从一车麦黄草给生产队喂牲口到生产队的麦滑秸随便用;从给最好的宅基地到向天津市弹簧厂求助钢筋;从向机场驻军求助砂石料,到安排二十多壮劳力用两天时间给我们家无偿脱坯、起坯、晒坯,再到四个生产队,一百几十号人主动地在雷电和风雨中把四间正房,三间偏房,门楼,茅房和二十米院墙的干坯堆码成垛并苫盖好,……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在顺小王全村人的关照中,善举中,温暖中……让人倍加感动的是,不是几个人,几家人这样,而是全村人都这样对待我们。奶奶激动地说: “我活了快七十岁了,从没听说过这么好的村,更没有见过全村人都这么好!”
轶事难忘
那时候砖和瓦都很便宜,砖一分钱一块,县砖瓦厂的瓦不到四分钱,运输费用可以不计,只要生产队的大车可以调配开,都是无偿提供拉运。我父亲在当地是高工资,比刚参加工作的干部或职工的工资多一倍,虽然家庭人口多些,但生活条件在全村尚属偏好。于是,两年后,房子墙用砖包了皮,顶苫了瓦,院子用砖漫了甬路,十四米宽的大院子,有偏房,有柴草屋,有厕所,居住得很是惬意。
1983年,爷爷的地下党问题落实以后,父亲也重新落实了政策,工资连调三级,全家农转非,妹妹入伍当了兵,尽管他的年龄和学历已不符合当时的提拔条件,但教育局党委根据这些年被“搁置”的实际情况,破格提升他为国办蔡公庄中学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被压抑了多年的工作热情一下子全部焕发了出来,为了让母亲照顾好他的生活,以便全身心投入工作,1985年,父亲把房子卖给了西邻杨凤东叔叔,全家都搬到了中学的家属宿舍。后来,当我知道了这若大一处房产仅卖了三千元,而且是多怎有了钱多怎再付款时,不谨有些不解,有些埋怨的说 “1985年,这不也是白菜价吗?” 父亲很平和的回答: “这宅基地,这处房的坯草埝料,砖瓦砂石,所有的用工,都是顺小王乡亲们无偿给的,咱都不应该要钱啊!……”
听了父亲的一番话语,我接连点头 “是!是!是!……”从1967年到1985年,在顺小王村住了整整十八年,十八个春夏秋冬,我们全家在顺小王得到了接纳、关心、照顾、体贴和保护,这些善良的义举是无价的,是金钱永远都无法衡量的。
记得在全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汇报总结大会上,各大队都汇报开了多少场批判大会,批斗了多少阶级敌人,唯独顺小王大队革委副主任杨凤岐汇报“我们村没有阶级敌人”惹得主持会议的公社领导大怒 “全国到处都是阶级敌人,难到你顺小王是片净土?没有地富反坏右?”
“没有就是没有吗!” 杨凤岐斩钉截铁地回答: “原来有家地主,解放前就搬到天津(市里)去了,现在顺小王除了贫农就是下中农,难到没有阶级敌人,还非得找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批斗吗?”,大庭广众之下,公社领导有点下不来台,把桌子一拍 “孙占学家是被杀户,难到不是阶级敌人吗!”
“孙占学的父亲是地下党,到底是共产党处决还是遭敌人暗杀,政府没有定论,始终是个悬案!况且,战争年代咱八路军不也经常装扮成鬼子杀鬼子,装扮成伪军杀伪军吗!”众目睽睽之下,杨凤岐大伯的反驳让会场气氛紧张的有些窒息……
会后,公社革命委员会派专案组进驻顺小王检查和暗访,全村无论大队革委会成员还是生产队长,还是全村的社员们,无一不力挺我们,说我们这一家人这好那好,旗帜鲜明地对我家予以了保护。
父母离开顺小王以后,每到蔡公庄的集市日,都有顺小王的父老乡亲到中学去望看奶奶和父母,秋天的季节还常有人带点自家种的茄子、辣椒 、西红柿、山芋、胡萝卜等给我们尝尝鲜儿,一家人一如既往地享受着顺小王父老们的关心和惦念。后来,父亲退休住进了县城,虽然远离了顺小王村,但每到中秋和春节都有街坊邻居到县城看望奶奶和父母。
1996年,我的女儿考入静海一中,为了照顾女儿的学习和生活,老伴向教育局提出了进城的申请,然而,只有一个进城指标,想进城的人员需在全镇教师代表大会上公开申明理由后,由全镇教师代表现场投票决定。老伴在申诉理由时,除了说明女儿需要照顾之外,还说了句“公爹脑出血后行动有些不便,也需要我们做儿媳的临近身边,慰享晚年。” 当场得到了全镇教师代表们 “一边倒” 的高票通过,但不知哪位教师代表无意中将消息传到了顺小王村上,第二天开始,先后有十多个顺小王的叔叔、伯伯和兄嫂去县城看望父亲,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肢体残疾,走路都很困难的杨加余开着三轮车,跋涉六十多里地,还买着营养品专程去望看我父亲……让我父母和奶奶都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2003年3月8日,九十六岁的祖母寿满天年,当时正值“非典”,各村街屯和小区都采取了严格的封控措施,顺小王村两委班子给予了确保安全下的极大方便,部分父老乡亲们按要求闻讯而至和返回,为了不影响城区的防控,村主任李贵珠带着自己的儿子等四人在二街的公墓给祖母挖了墓坑,并与顺小王的红白理事会成员一起,无偿为祖母送行,让祖母的葬礼在亲戚朋友,特别是在祖母娘家众多的后代们面前显的简约且隆重。
2013年3月14日,父亲逝世,顺小王的几任书记、主任、部分老村委会的后勤成员,红白理事会成员,多年的街坊邻居、叔叔、婶婶、伯父、伯母,以及兄、嫂、弟、妹们都跋涉六十多里地前来悼念和操办葬礼,……
那天去殡仪馆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为父亲送行的车辆排成了长长的车队,足足有四五十辆,我的心突然一愣,“我除了按规定向单位要了一辆二十多坐位的大轿子车之外,没有向朋友要车啊!” 我不禁暗想“这不成了‘讲排场 了吗?这是群众对公务人员最反感和忌惮的,也是上级纪检机关要“约谈”“告诫”或问责的啊!”……从墓地回来以后,听操办葬礼的几位前任书记、主任说,除了我们河间老家的亲戚、弟弟妹妹朋友的车之外,近一半都是顺小王的父老乡亲们闻讯专程来送行的……此时此刻,我好感动,好多好多的话撞击着激动的舌头,好多好多感恩的情愫伴和着热血一道奔流……激情下,感动中,我当着老书记,老主任们的面,朝著顺小王的方向,深深地躹了一躬 “谢谢!谢谢!谢谢顺小王的父老乡亲们!”
光阴似箭,从1967年至今,五十五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孩童变成了古稀闲叟,但仍然享受着顺小王父老乡亲们的关心、惦念和情感慰藉,麦收季节能吃到顺小王的新蒜、瓠子、土豆,秋天能吃到顺小王的大葱、山芋和新玉米面,虽然,这些超市里都能买到,但内涵不一样,吃到嘴里的味道和内心的感受截然不同;因为,乡亲们都是让后生们专程送来或托人捎来的,里面浸透了顺小王父老乡亲的真诚和善良。
对一个非亲非故的外来户,外地人,顺小王的父老乡亲们先是接纳,之后是全村人不约而同的关心、照顾、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全村都视我们全家如亲人。这样的民风和村风,这样的善意和善举,无论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还是在当今改革和复兴的征程中,全村的人都与人为善,都帮人于难,都厚德施爱,而且磨砺了五十多个岁月的沧桑,那种质朴、质真、质纯的初心依旧,良俗依旧,实属罕见和难能可贵。
我们家与顺小王,就像天上飘下来的雪花,落到地上,结成了冰,化成了水,就再也分不开了……
顺小王,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深情厚谊,这里的每一位乡亲都是我今生不能忘怀的至亲。
感恩顺小王,感恩顺小王的父老乡亲……
( 注:《天津日报》2022年9月14日,10月11日,10月25日分上、中、下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