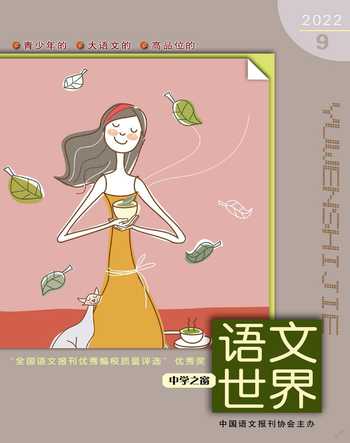茉莉花开 光影流年
王跃波
七月,校园里的草茉莉开了。紫的黄的白的、半黄半紫双色的,抑或层层晕染有如洒金织锦的,各色花朵在柔嫩的绿叶间摇曳生姿,天真纯然。纤细的花蕊微微颤动,引得蝴蝶逗留。微风里送来淡淡的香气,和着蝉鸣,总有一种岁月安然的美好。
乡下,这种草茉莉极常见,房前屋后,撒下一把种子,不去侍弄,靠天将养,时节到了,自有一片葱茏繁盛。然而每每见到,总觉心弦拨动,那些沉淀于心底的记忆一触即发,远去的学生时代在恬淡花香中渐次显影,铺陈开来。
一
初见草茉莉是在村里小学的院子里。小小的花坛,各色的茉莉花热热闹闹地开着。傍晚放学时,似乎香气更浓。上了一天课,最后一节课总是自由活动。我们三五个小女孩就去采花,挑那些大的美的,扎在辫子上,别在耳朵后,插在衣襟扣眼里,或者用狗尾草穿成手串、项链戴在身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叽叽喳喳说着,笑着。(大女孩们在旁边跳皮筋或者抓子儿,并不参与这种幼稚的游戏。)老师从来不说我们,只是看着我们笑,满是宽容与慈爱。我们也是有分寸的,只是偶尔摘来玩,并不故意糟蹋,那花啊开得太好了,看不够呢!
我们这个小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全村三十多个孩子,从育红班到三年级,小到五六岁,大到十三四岁(那时候可以留级,家长要是觉得孩子念得不好,就让孩子留级,留个两三年也是常事),都在这里念书。老师姓刘,嫁在邻村,不过二三里路,天天骑自行车来回,从不迟到早退,也从未请过假。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起来殊为惊异,我也是做了二十多年的老师,不知当时瘦瘦弱弱的刘老师是如何做到风雨无阻从不缺课的。
一个人就是一所学校,是真的啊。
既然只有一个人,那所有的课也就只有刘老师一个人教。好在只有两门:语文和算术。四个不同年级的孩子在同一个教室上课。老师自有她的调度,给育红班的孩子讲故事,就叫另三个年级的孩子写作业,如此循环。那时候作业很少,基本就在学校写完了。学的知识也简单,我作业写得快,老师给高年级孩子讲课时,我也常常支棱着耳朵听,等轮到给我们讲时,好多知识已经学会了。从那时起,我的成绩就名列前茅。不过实在不值得骄傲,因为我这个年级一共就四个人呀!我、我的双胞胎妹妹,另外两个是一对堂兄弟。
最高兴的莫过于过“六一”。临到“六一”,各村小要准备节目,到中心校去演。每到这时,刘老师就担起音乐老师的职责。教室里有一架脚踏钢琴,刘老师一边弹琴,一边教我们唱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八月桂花遍地开》《让我们荡起双桨》……刘老师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學。一板一眼的琴声,荒腔走板的歌声,某个孩子的轻笑声,老师“再来一遍”的指令声,充满了整个教室。明明只是学一支歌曲,可是从老师到学生都是如此认真庄重,仿佛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当所有人都能跟上老师的琴声,整齐的歌声缓缓流出的时候,大家是多么高兴啊,单纯地发自内心的快乐!当然,去中心校肯定不是表演大合唱,可就是借着“六一”这个时机,我们学会了很多歌,获得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刘老师是代课老师,一直在我们村小教书,教了很多年,后来赶上政策,转正了,算起来应是早已退休了。工作后,我常常想,如果给我这样一群孩子,给我这样一个教室,我能担起这份重任吗?那样的年代,那样的老师太多太多了,作为乡村教育的中坚力量、基础教育的神经末梢,他们付出了整个青春,默默无闻,但功德无量。
二
四年级起,我和妹妹就去外村读书了。三年后,我如愿考上重点初中,妹妹则因几分之差落榜,执意去复读。自此,上学路上便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
进入初中,我开始住校。宿舍是一间大房子,两条大通铺,没糊顶棚,抬头就能看见檩柁。每个人只有一个枕头宽的地方,枕头碰枕头,褥子是对折铺的,不然铺不下,一张通铺挤十几个人,根本翻不了身。没有电扇,没有暖气,夏天闷热,冬天寒冷。整个女生宿舍区,只有一个旱厕,连灯都没有。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家长挤破脑袋也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因为这是一所老牌重点中学,师资好,管理严,升学有保障。
每天雷打不动,学生五点半起床,六点进教室,一天的课满满当当,第八节课照例是体育活动,要么操场训练,要么越野跑,训练度满格,直到晚上九点下自习,一天结束。一年四季,天天如是。那时,一周上六天课,周六下午放假,周日下午返校,不能耽误上晚自习。到了初三,一个月便只休一天。我家离学校二十多里路,一般下午四点钟就要骑自行车从家出发,冬天则要更早,不然天就黑了。回学校要收拾东西,交作业,换饭票,稍一磨蹭就赶不上趟儿。
赵天增老师是我初二时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数学老师。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只是天生头发少,头顶锃亮,仅其余三面有些头发,拱卫中央,保持着最后的倔强,属实是“聪明绝顶”。他个子很高,瘦,长脸,小眼睛,眉毛很淡。不笑时,一脸严肃,让人摸不着头脑;笑起来和蔼可亲,嘴角上扬,眼睛里都蓄满笑意。
他“御下”极严,做事极有条理,也颇有分寸。总之,我们大家都挺喜欢他,背地里叫他“赵老头”,虽然他并不老。他大概也知道,但不以为忤,他看我们真像看自己孩子一样。他数学讲得极好,总是三言两语点出要害,又常常语出幽默,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数轴,他说:“数轴就是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想要有多长就有多长,可以向两端无限延伸,需要时能一下子捅到天宫,不需要时变成一根火柴棍藏到耳朵眼儿里。它还是它。”比如合并同类项,他问我们:“仨猫加俩狗等于多少啊?”我们笑着说:“老师,这没法加啊,不是一个东西。”他说:“对——喽,猫加狗不能加,x加y也不能加,加到这就到头了。”“哦——”我们中有人恍然大悟。至于徒手画圆,秒算得数更是不在话下。我至今仍记得他背着一只手,面朝我们反手画圆的神气,一个,又一个,都是标准圆。看着我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不可置信的神情,他笑得很洒脱,说着:“这有什么啊,瞧——”反手又是一个圆。服了!
在他的影响下,我第一次对数学如此着迷,第一次觉得数学是那么神奇那么美。更重要的是,他让我知道,女生也可以学好数学,不逊于男生。因为他从来不会说“到了初高中,女生学数学就后劲不足”那样叫人泄气的话,他说只要好好学,每个人都能掌握数学学习的密码。一个班60多人,期末考试数学平均分108,是不是无敌了?这就是无敌啊!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会常常想起他。想起他明明相貌平平,一站到讲台上就神采奕奕,整个人仿佛会发光的样子;想起他把我们这支“队伍”拉到操场上,舞动着双手做指挥,指导我们分双声部唱《打靶归来》的样子;想起他拿着小木棍,迎着北风,带着我们一丝不苟踢正步、练队列的样子;想起他在拔河比赛上,站在我们身边,用力挥动双臂大声呼喊给我们加油助威的样子……他把整颗心都给了我们啊。有他在,我们是那么踏实,那么有依靠。
三
1997年初中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师——廊坊师范学校(即现在的廊坊师范学院),一扇崭新的大门朝我慢慢打开。我第一次从家乡三河的一个小镇走进一个繁华的城市,也第一次面对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
说来惭愧,我真正读书其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家里世代务农,一个读书人也没有,小学阶段我几乎没读过课外书。中学几乎是全封闭学习,假期倒是有时间,可是依然没书读。买,当时没那个意识,也没那个条件。借,无从可借。中师的学习没那么紧张,课余时间很多。干什么,读书吧。学校宽阔明亮的图书馆,于我而言,就是一座宝库,我第一次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
我跟着基督山伯爵层层布局快意恩仇,酣畅淋漓;我目睹茶花女沦落风尘命运多舛,黯然落泪;我看到历经磨难的冉·阿让依然仁慈善良,照护他人,生出对抗苦难的勇气 ;我感叹出身贫苦的简·爱敢于蔑视权贵,自尊自强,悟到精神强大的可贵。
我读到余光中,“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立觉余音袅袅,绕梁三日;我读到席慕蓉,“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瞬间沦陷于那佛前女子的深情,千回百转,柔肠百结;我读到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顿悟这样坚强柔韧的女子,才是吾辈典范。
就这样一路读下去,读林语堂,读余秋雨,读汪曾祺,读史铁生……囫囵吞枣,生吞活剥。那时,我常常在图书馆二楼临窗而坐,初夏温柔的阳光照进来,高大的法桐枝叶茂盛,清风吹过,窸窣作响。
毛笔字也是从那时练起。这得益于学校开的书法课。书法老师叫李健,四十来岁,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浓眉大眼,眼角略下垂,有一股慈眉善目的味道,说话不疾不徐,四平八稳,常常一副老干部打扮。上课时,他总是拿一个暖壶盖,里面装半下清水,一支大毛笔,一布袋子书。
李老师教的柳体。柳体瘦硬,结体严紧。我常常想,若论“字如其人”,他教颜体定然也是极好的。最喜欢看他写字。他拿毛笔蘸了水,从横竖撇捺、钩折挑点开始,在黑板上给大家一一示范。他一面运笔,一面讲解:“看,长横,逆锋向左,轻起笔,起;折笔向下轻顿,顿;折向右中锋行笔,行,手要稳住;到末端微向上提笔,提;折向右下顿笔,顿;回锋收笔,收。好,我们再来一遍……”一节课下来,我们就在他的“起顿行提顿收”的延长音中度过。
临完点画,临部首,再临字,循序渐进。我虽学得认真,但初入门不免把字写得东倒西歪,向老师求教,老师说:“嗯,这个字写得不错,练多了就好了。你练得多?你这才练几天?人家写一辈子了。不能心急。”老师说话一贯是慢悠悠的,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串起来才是一篇话。我暗想,不愧是学书法的,养气的功夫的确一流。
学了大半年,早也写,晚也写,到考试那天更是连午休都弃了,一心一意临帖,写到手酸。考试当场写,当场出成绩。老师站在讲台上,被我們团团围住。拿回我的字,挤出人群,看着老师在宣纸上用朱笔画的红圈,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同学们也是,大家纷纷数自己得了几个红圈,红圈倒比分数更让人在意。那是真的好,才给画圈的。自然,如果是方框,那就要注意了,说明这个字笔法或者结构肯定有问题。
记得一次课上,我正在写字,老师踱到我这里,指着那个“慕”字,徐徐地说:“这个字写得真好,比我写得都好,你看这一捺,笔意到了。”我都傻了,真的那么好吗,盯着那个“慕”字,看了又看。老师一脸真诚,不似作伪。说完,转身又去指点别人了。无论如何,这句“比我都好”着实鼓舞了我,每每想要偷懒之时,记起这句话,便又提起劲头再写下去。二十多年过去,那温和醇厚的声音似乎犹在耳畔。
茉莉花开,光影流年。那些遥远的青春岁月去而不返,那些上过的课,经过的事,看过的书,写过的字却都一点一滴融入骨血,长成性情,铸就品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就让我和我的老师们一样,好好教书,默默耕耘吧。总有一天,我的花儿也会开满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