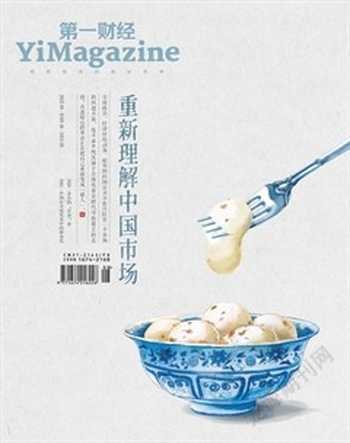什么是自由?
王俊煜
今天不想谈工作了,想谈谈自己。
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那时候我们的家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小山坡上,生活区的门口是一条又长又直的斜坡,一直通往山下。意外发生在一天清早,妈妈骑着车去上班,然后被发现倒在了斜坡脚下的路边。
那是1985年前后,我只有几个月大。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住到了1997年。等到我四五年级的时候,每天清早我也会骑着车去上学,冬天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就会出门,沿着广深公路骑四五公里到怡园小学。理论上这和妈妈当年去上班的路线是一样的,区政府搬走之前,就在怡园小学旁边。我也喜欢骑着车在斜坡上冲下去,有时会撒开双手,想看看单车完全依靠地心引力,能自己滑多远。
我搬走以后就没有回去过。写到这里的时候打开地图看了一下街景,发现那个斜坡没有我记忆中那么长。
我很少和别人谈起妈妈,并不是因为我对此感到痛苦。恰恰相反,我看起来从来没有为此难过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意外发生时我太小了,对妈妈毫无记忆。照片当然有,妈妈在照片上永远是一个八十年代清澈干净的年轻人模样;除此之外,我对妈妈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其他人为数不多的转述,例如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常常会在我去买六毛钱一只的菠萝包的时候夸赞我妈妈有多漂亮,顺便夸我长得像妈 妈。
妈妈的墓就在韩江边上,我去看她的次数也非常有限。有一次我和妈妈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一起去看她。我听着小姨哭着喊姐姐,扶着她勉强站立,想象着,妈妈一定是个很善良的人吧。好像在那一刻,我才第一次感受到,她原来曾经真切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愿意谈及此事,既是因为没有必要,也是因为担心社交上的窘迫:朋友们听到这个故事,应该如何回应才显得得体?那太难了。假装一切正常并不困难,即使去同学家里玩的时候正好在看《鲁冰花》,又或者学校可能会教《世上只有妈妈好》,我都可以看成一件恰好与我无关的事情。这几年我自己有了小孩,我的妻子变成了妈妈,我看到她如何爱我们的孩子,才模模糊糊地知道,噢,妈妈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才明白,噢,原来自己其实是少了点什么的。
最近想起这些,甚至愿意写出来,是因为在想,什么是自由。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很自由—那些我引以为傲的、忍不住想要去到处炫耀的自由。比如,按照我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我可以说自己是财务自由的,这意味着我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必担心自己或家人生活无着落。比如,当我在2010年想创业的时候,我就辞职了,我想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回Google去工作,反正我一定是能回去的。比如,毕业的时候我其实可以要北京户口,但我都懒得去办,把户口扔回了广州。比如,我考试的时候从来都可以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考到第一名,直到上了高中才见识了真正的“对手”—但我最后还是考了第一名,不是么?这也给我挑选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专业的自由,虽然我最后还是读了一开始选定的物理。比如,我还有不用考试的自由,高考前我就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考前我也已经拿到了华南师大附中的录取通知书。等等。
应该列举得足够多了,你可以看出我是多么骄傲了。我觉得自由很重要,我也拥有它。我给小孩子取名字的时候,这是他名字的唯一含义。我那时候认为,自由的唯一障碍就是自己,只要你敢去选择,自由就属于你。
但我最近意识到,我所骄傲的这些自由事实上非常脆弱,我并不真正拥有自由。我原来觉得自由的前提是强大,但自由不应该是强大带来的,那不是自由,是特权,我只是倚仗着那些我身上最骄傲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作威作福。享受这些特权,并不需要我去面对什么真正的恐惧,放弃什么我真正在意的东西。其实我未曾真正面对过自己的恐惧。
当然,如果没有得到过一个东西,也就不会恐惧它的失去。
妈妈去世后我和奶奶一起生活了几年。1989年,我回到了爸爸身边。
有恐惧的人,才是活着的人,他们带着恐惧勇敢地走向未知,那一定是通往自由的路。
和爸爸两个人一起生活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周末会去北京路的儿童书店,然后去西湖路或是教育路吃云吞面。我们在火车上练习速算和24点,以及他并不成功的围棋教学。我想起和他一起相处的画面,最深刻的還是坐在他单车的后座,同样是在夜晚的广深公路上,要在雷暴雨降临之前赶路回家。货柜车在身边呼啸而过,天空布满蜘蛛网一般的闪电,我抬着头,惊叹自然的神奇。应该是有雷声的才对,但这幅画面在我的脑子里面安静得可怕。
后来我有了新的妈妈。事实上妈妈对我很好,她很了不起,但她也似乎始终无法和我建立某种连接。1991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同一时刻,我也有了两个弟弟。那之后,爸爸妈妈更忙了,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书。应该说,我只能看书。那几年家里没有电视,爸爸有很多书,放满了两个大书架,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翻来看。时至今日,我买本类似于《论自由》这样的书,爸爸还会说,买这个干什么?家里明明有,当年五毛钱一本买的。
我只能自己看书。有一天晚上弟弟生病了,爸爸妈妈在医院。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等到很晚,绝望之中把所有的书都扔到了地上。在那之后,我应该就没有再为此生过气了。
生气也没有用,不是吗?要做个懂事的乖孩子。我也的确是个乖孩子。高中我考上了华南师大附中,外婆和小姨说,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就曾许过心愿,将来要是肚子里的这个小孩能考上华南师大附中该有多好。她应该会很欢喜。
那还是看书吧。我后来迷上了看报纸,广州的3个报业集团加起来每天会出版6份日报和晚报,我零花钱充裕的时候会买其中的三四份,在自己的房间里看。除此之外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很感谢它们,它们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结。那可能是那时候的我和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
所以,我一直觉得阅读就是我最热爱的事情。为什么孜孜不倦想做相关的工作?大概也是我常常想起那时候的自己,想象今天的某个角落可能也有那么一位类似的少年,如果做的事情能帮到他们一点点,我会感到快乐,“让认真阅读的人在互联网上有栖身之地”。
直到最近,我想,我可能错了。阅读只是我逃避恐惧的方式。
我记得书房那扇窗户。窗户外面是一片树林,晚上什么也看不到,鄰居的哥哥说会有鬼火,所以我不太敢看。远处能看到黄埔港的灯光映红了半边天,也可以听到广深公路上货柜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星星,但是也没有望远镜。
我的恐惧是什么?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面对它,也不能或不敢在这里描述。只是慢慢地能看到它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无所畏惧。
但我能看到一些片段。2008年前后,我发现自己有一个身体指标非常高,高出正常值两个数量级。那是一个肿瘤标志物指标,花了几个月时间,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但我开始想象自己随时会得癌症,然后死去。我又想,如果不知道能活多久的话,那不如抓紧时间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后来创业,并将工作和生活画上完全的等号,跟这个想法有很大的关系。
十多年过去,那个指标还是非常高。我已经放弃去寻根究底了,反正不想看到的东西还是没有出现。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恐惧死亡,正如我以前觉得我并不恐惧失去一样,可能我并没有真正见过它的模样。我没有如常理一样好好爱惜我的健康,但我确定我恐惧时间的流逝,所以我的应对方式是花很多时间工作,熬很多夜,并把我的恐惧传递给其他人。
我从前也没有觉得我的工作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那是我想做的事情。2013年左右第一次有人报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想收购豌豆荚,我好像想都没有想就回绝了,甚至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当然,技术上是必须讨论的,我才意识到,原来身边的人和我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我在未名湖边哭了很久。2014年崔瑾想离开团队,我意识到她和我在一起工作也并不快乐。这些都是恐惧,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我提到过我某次路过四海镇时的想法,那也是我的恐惧。我们那时候说两三个月没有钱是可以接受的,现在阅览室已经做了6个月了。我有时候觉得,做和阅读相关的工作可能只是我的梦想,但代价却不全部由我承担。我害怕别人为我的梦想而付出,这也是恐惧。
我也知道我面对恐惧往往会选择封闭,就像从前躲进自己的房间阅读一样。其实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个茧房,我身边有许多真正自由的人,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恐惧,面对自己的脆弱和不勇敢。一位朋友告诉我,自由首先需要完全接纳自己,完全接纳自己的恐惧,接纳自己的求而不得,接纳自己的有限,接纳自己的一切;不再执念于得到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也不再害怕失去已经完全属于你的。
对我来说,我今天只是开始意识到恐惧的存在,理解恐惧的来源和它如何支配自己的行为。我也许会试图去战胜它,但我想,承认恐惧的不可战胜,并且和它共存,可能才是真正的自由。恐惧会阻碍我们通向自由,但也是通向自由的唯一障碍。
所以我觉得,能面对自己的恐惧的人特别了不起,那是真正的自由。有恐惧的人,才是活着的人,他们带着恐惧勇敢地走向未知,那一定是通往自由的路。
好了,作为放在财经杂志上的专栏,有些不合时宜了。下期我们还是谈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