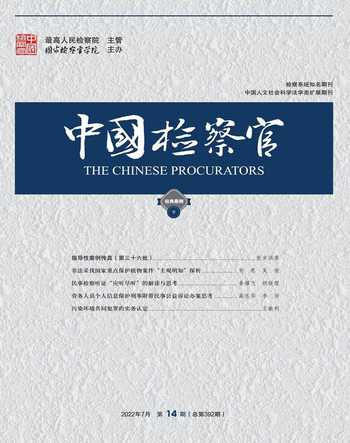复数行为犯中主行为的认定
摘 要:对于复数行为犯的定性,应以复数行为中的主行为性质来认定案件性质。而准确认定复数行为中的主行为,关键是从复数行为间的关系入手,分析哪一个行为是主导行为或者支配行为,即哪一个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诱发或促使行为人产生犯意的行为一般是主行为,将犯意付诸实施的后续行为一般是从行为;在犯罪进程中最难完成的核心行为一般是主行为,较容易完成的辅助行为一般是从行为;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一般是主行为,明显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一般是从行为。
关键词:复数行为 主行为 从行为 罪刑相适应
一、复数行为犯的提出及定性
[案例一]鲍某有一天加班到很晚,临走时发现隔壁办公室没有关门,办公室内的灯和电风扇也没有关,鲍某便走进去关电风扇,其在俯身关电风扇时看到办公桌底下有一张存折,鲍某捡起来一看是同事王某的活期存折,鲍某心想肯定是王某遗失在这里的,他便把存折放进口袋,关上门后离开了。次日鲍某来到银行,根据他所知道的王某手机尾号和帮王某买机票时掌握的王某身份证号,猜配出存折密码,取出现金15000元,存入自己名下。(以下简称“活期存折案”)
[案例二]闫某伙同杨某,利用某商厦开展民惠龙卡(具有打折、积分功能)积分返券活动的机会,闫某在商厦用本人及他人身份证申请办理了近10张民惠龙卡,杨某利用曾经在商厦电脑部工作过并掌握密码的便利,私自进入商厦的计算机系统,向卡内虚加积分80余万分(积分应由实际消费所得,一定的积分可以兑换一定的礼金券,在商厦可等同于人民币进行消费),再由闫某持积分卡到前台找熟人穆某兑换礼金券(兑换的时候应核实身份,核对积分记录及购物小票)。其间闫某和杨某共兑换礼金券共计人民币5万余元并进行消费,后穆某感觉有问题便停止兑换,直至案发。(以下简称“积分卡加分案”)
[案例三]李某在网上看到有人出售电脑,便与王某策划商量了一个方案将这台电脑搞到手。第二天,李某與出售电脑的张某约好在市物资大楼交易,张某带着电脑如约来到物资大楼,李某提出要看一下电脑,张某便把电脑交给李某。李某打开电脑包看了一下外形后,提出他一个朋友就在旁边开了家电脑公司,他要拿给他朋友去看一下质量有没有问题,张某表示同意,李某便拿着电脑走在前面,张某紧跟在后面。走了几分钟后,王某按计划开着摩托车突然停在李某面前,李某立即跳上车,王某即加大油门,疾驰而去,等张某反应过来,李某、王某早已没有了踪影。(以下简称“骗夺电脑案”)
刑法分则中,某个条文对某一犯罪客观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实行行为不是单一行为而是两个以上的行为,刑法上称为复行为犯[1],如高利转贷罪包括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高利转贷他人两个实行行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包括编造和传播两个实行行为;丢失枪支不报罪包括丢失枪支和不报告或瞒报两个实行行为等等。复行为犯的罪名刑法已作明确规定,一般不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类案件系行为人在一个整体的犯罪故意支配下,先后实施了两种以上不同性质但紧密关联的实行行为,应整体评价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如上述三个案例。对于这类犯罪,为了与复行为犯相区别,笔者称之为复数行为犯。对于复数行为犯的定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首先要准确认定复数行为犯中的主行为,再以主行为性质确定案件性质。这种案件定性分析方法,可称为关键行为定位法。[2]
二、复数行为犯中复数行为的特征
对于复数行为犯的定性,首先要准确把握和认定复数行为犯中的复数行为。复数行为犯中的“复数行为”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复数行为犯在整体上只具备一个犯罪构成。复数行为犯是基于一个犯罪故意支配下,实施了相互关联的两个以上实行行为,整体上只具备一个犯罪构成。复数行为犯是实质上的一罪,而不是实质上的数罪、处断上的一罪,因而不同于牵连犯、吸收犯等罪数形态。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复数行为是两个以上的实行行为,不包括教唆、帮助、预备行为;二是这两个以上行为都是基于一个犯罪故意;三是这两个以上行为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常见的关联如手段与目的、目的与结果等。比如积分卡加分案,就是出于一个犯罪故意(非法占有商场财产的故意),只侵害一个客体(商场财产所有权),但客观方面实施了私自给商场积分卡加分、使用积分卡兑换购物券、持购物券进行消费等多个实行行为,这些实行行为彼此之间紧密关联,一环扣一环,环环递进。这些实行行为结合在一起,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具备一个犯罪构成要件。
第二,复数行为只是观念上的不法行为,并非刑法上评价为犯罪的行为。现实生活中,有些犯罪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系列的手段才完成犯罪,这个过程中可能有骗、窃、夺、诈等多种成分的行为,这些行为混杂在一起,共同实现一个犯罪故意,即复数行为犯。复数行为犯中的骗、窃、夺、诈等多种成分的行为,只是人们观念上的骗、窃、夺、诈等不法行为,而不是刑法上被评价为犯罪的诈骗、盗窃、抢夺、敲诈勒索行为。如在骗夺电脑案中,李某、王某实施了系列骗的行为(骗张某来到物资大楼、骗张某将电脑交给自己、骗张某走出大楼)、夺的行为(李某持电脑跳上摩托车,王某疾驶而去),但这个骗、夺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观念上的“骗”和“夺”,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诈骗”和“抢夺”。具体来说,“骗”的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诈骗”,因为刑法上的“诈骗”不仅要求行为人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还要求被害人对财产有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即基于陷入错误认识的认识瑕疵而自愿处分财产。而在本案中,张某只是临时将电脑交到李某手里,而非对电脑的所有权作出处分,张某并不存在自愿交付财产,因而本案的欺骗行为只是我们生活中“欺骗”的概念,不是刑法上的“诈骗”行为。“夺”的行为也并非刑法意义上的“抢夺”,因为刑法上的抢夺是指通过作用于物的暴力,公然夺取他人财物,行为人之前是不占有、控制财物的,通俗地说,刑法上的抢夺是从他人手上夺走财物。而本案中李某跳上摩托车时,已经持有电脑,即已经将电脑“骗”到手,而不是从张某手上暴力夺取过来的。因而这种“夺”的行为也并非刑法上的“抢夺”。本案中“骗”“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才是刑法意义上的一个犯罪行为。
第三,复数行为中的主行为也并不是单独成立犯罪的实行行为。如前所述,复数行为中的任何一个实行行为都不能单独成立犯罪,而是两个以上实行行为在整体上具备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确立复数行为中何者为主行为,是为了根据这个主行为的性质特征,确定复数行为犯在整体上应认定何罪。如在活期存折案中,有日常生活观念上“捡”(将王某遗忘物捡走)的行为、“盗”(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猜配出王某存折密码进而将存折内钱取走占为己有)的行为、“骗”(冒充王某或王某委托的取款人,使银行误以为鲍某就是王某或王某委托的取款人)的行为。而确定何者为主行为,并不意味着单独这个行为就构成犯罪,并按照这个行为性质定罪,如认定活期存折案中“捡”的行为是主行为,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为就是盗窃犯罪行为(因该遗忘物在王某控制范围内,鲍某“捡”走属于盗窃),从而认定全案构成盗窃罪。因为鲍某盗走的只是一张存折,属于财物记载凭证,如果鲍某不知道密码或者不去猜配密码,或者即使猜对了密码但不去银行取款,存折对他来说也就只是一张废纸,那么其“捡”的行为不能单独认定为盗窃他人财物,不属于刑法上的“盗窃”犯罪行为。
三、如何区分复数行为犯中的主行为和从行为
对于复数犯罪行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前面的行为就是主行为,后面的行为就是从行为。[3]主行为的认定标准应该是看哪一种行为对实现行为人的犯罪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起了关键、决定性或主要的作用,[4]也即哪一种行为在整个犯罪行为中是关键行为、主导行为或支配行为。具体而言,体现和表明犯意的行为是主行为,将犯意付诸实施的后续行为是从行为;在犯罪过程中最难完成的核心行为是主行为,较容易完成的行为是从行为;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是主行为,明显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是从行为。
(一)体现和表明犯意的行为是主行为,将犯意付诸实施的后续行为是从行为
具体而言,就是看哪一个行为是体现和表明犯意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主行为,其他将犯意付诸实施的行为或者说实现犯意的行为是主行为的自然延伸,是从行为。
比如活期存折案,有论者认为鮑某行为构成三角诈骗型诈骗罪,因为如果只是盗窃存折而不取款,被害人不会遭受损失,也即造成损失的行为不是盗窃、侵占存折行为,而是取款行为,因此,应根据取款行为的性质定性,而不能根据取得存折的行为定性。[5]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行为构成普通型诈骗罪,因为猜配他人取款密码可视为是一种无形偷盗行为,但猜中密码并不意味着取得了他人存款,行为人支取他人存款,是凭借银行的信任通过银行的交付得以实现的,由于银行的信任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是行为人隐瞒真相冒用他人名义致银行误以为其具有取款合法资格的结果,是典型的冒用诈骗行为,故应认定诈骗罪。[6]笔者认为,在此复数行为犯罪中,“骗”的行为并非主行为,“捡”的行为才是主行为,应根据“捡”的行为即取得存折行为的性质来确定案件的性质。主要理由是:第一,“捡走”活期存折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行为中起了主导作用。在“捡走”活期存折、猜配密码、取款这三个行为中,“捡走”活期存折的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损失的关键所在,若行为人没有“捡走”活期存折,后面的系列行为均无从发生。同时,鲍某明知存折就在王某办公桌底下,王某很容易就能够发现,却故意“捡走”,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故意,“捡走”行为直接体现了其犯意,在这种犯意支配下,进而实施后面的猜密码和取款行为。可以说,行为人“捡走”活期存折对于其实施侵财犯罪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整个犯罪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第二,行为人“捡走”存折等于实现了对存折记载财产的控制占有。本案中,虽然行为人“捡走”的只是记载财产的支付凭证而不是财产本身,但这个可以即时兑现的活期存折如同一个存有财产的“百宝箱”,存折密码就如同打开这个“百宝箱”的钥匙。行为人“捡走”这个活期存折,就等于拥有了对存折记载财产的控制和支配权,只要猜中密码,就可以打开这个“百宝箱”,进而将他人财产占为己有。因此,行为人最终能够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捡走”存折的行为至关重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三,取款行为只是实现侵财犯意的自然延伸行为。鲍某故意“捡走”存折,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接下来的取款行为就是实现这种犯意的必然行为。因此,取款行为是“捡走”存折这一关键行为的自然延伸,是行为人实现占有存折记载财产的从行为或者说辅助行为。
确定了本案主行为是“捡”存折行为,本案即应认定为盗窃罪。主要理由是:第一,“捡”的行为在刑法上实质上是“盗窃”行为。前文已述,复数行为犯中的实行行为都是观念上的不法行为,而非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本案中行为人鲍某从隔壁办公室同事王某办公桌底下“捡走”活期存折,实际上是刑法上的盗窃行为。因为王某的存折就掉落在自己办公桌底下,没有脱离王某控制,王某很轻易就能发现,存折并不是王某的“遗忘物”,更非遗失物。鲍某明知存折并未脱离王某控制,仍然在王某控制之下将存折“捡走”,实际上是秘密窃取行为。鲍某窃取王某存折后,通过猜中密码的方式将存折中财产取出,并占为己有,这是一种将盗窃所得支付凭证兑现的行为,虽然是一种观念上“欺骗”银行的不法行为,但实际上是盗窃的事后行为,并不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因此,根据本案主行为的法律性质,本案应认定为盗窃罪。第二,取款行为也不是刑法上的“诈骗”行为。本案中的取款行为不仅不是复数行为犯中的主行为,而且也不是刑法上的诈骗行为。因为持活期存折取款5万元以下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也即银行并不需要验明取款人真实身份,没有义务核实取款人是否系存折户主。即使其他人来取款,银行也不存在陷入错误认识的问题,取款人“诈骗”银行也就无从谈起。第三,本案也不成立所谓的“三角诈骗”。笔者认为“三角诈骗”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传统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这种改造并无必要。“三角诈骗”强调的是被诈骗人并非财产所有权人,其构造是“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对象陷入错误认识——基于有瑕疵的认识处分了他人的财产——第三人财产权受到损害”。[7]但按照传统的诈骗罪构造“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完全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诈骗罪的传统构造中“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认识处分财产”并没有限定是处分被害人自己所有的财产,当然也包括处分被害人管理、持有、控制下的他人所有的财产。至于最终遭受财产损失的是被害人还是第三人,那是被害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刑法上可以在所不问。因此,所谓的“三角诈骗”构成要件与传统诈骗罪构成要件其实并无二致,客观方面都要求实施了诈骗行为。而如前所述,本案中的取款行为并非刑法上的“诈骗”行为,自然也就不成立所谓的“三角诈骗”。
再如积分卡加分案,行为人在商场积分卡上私自加分,这就表明行为人具有侵犯商场财产所有权的故意,后面持积分卡换购物券的行为是实现犯意的自然延伸行为、后续行为,持购物券消费更是不具有刑法评价意义的支付凭证兑现行为,因而私自给积分卡加分的行为就是主行为。因此,全案应根据私自给积分卡加分的行为性质定罪(这种私自、秘密加分的行为实质上等同于窃取商场财物,具有盗窃性质),应认定本案成立盗窃罪。
(二)在犯罪进程中最难完成的核心行为是主行为,较容易完成的辅助行为是从行为
具体而言,就是看复数行为中哪一个行为在促使行为人犯罪得逞中的分量最重,或者说看哪一个行为是整个犯罪行为中最难完成的行为,这个最难的行为往往就是最核心的行为,因而应当认定为主行为,其他的辅助行为则应认定为从行为。
如骗夺电脑案,行为人以交易为名,将他人电脑“骗”到自己手上,这个环节的行为是相对容易完成的,而被害人一直跟在行为人身后,电脑并未完全脱离被害人控制范围,行为人最终能否实现非法占有,关键在于跳上摩托车,疾驶而去的行为。因而,行为人最后“夺”的行为是主行为,前面“骗”的行为是准备行为、辅助行为,是从行为。因此,应根据“夺”的行为来定罪,认定全案成立抢夺罪。如果反过来,行为人能够通过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完全将电脑交给行为人,行为人独自离开,在已经完全脱离被害人视线或者控制范围后,为了避免被害人醒悟后追上来,跳上摩托车,疾驶而去,那么,前面“骗”的行为就是主行为,后面跳上摩托车逃离的行为就是后续行为、保障行为,是从行为。
(三)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是主行为,明显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是从行为
定罪量刑的一般思路是先定罪后量刑,但在疑案分析中,量刑反制定罪理论也是有实践价值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定罪分析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存在争议的各种定罪可能产生的量刑结果来检验定罪是否科学、合理。[8]复数行为犯中主行为的认定不同,必然导致案件定性不一,而案件定性不一,量刑也就可能产生较大差异。对此,司法人员可以从不同主行为相对应的案件定性产生的量刑来考察,看是否与行为人的罪行轻重程度及主观恶性深浅程度相称,也即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这一定性相对应的主行为的判断就是合理、准确的。罪刑相适应的判断,除了司法人员以司法的专业眼光,从犯罪原因、犯罪情节、犯罪后果、社会危害及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犯罪前一贯表现、犯罪后表现等主客观方面作综合评判外,还应从常识主义刑法观角度,考虑刑罚不能违背常识、常情、常理。
如活期存折案,运用量刑反制定罪理论来检验案件定性,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和量刑数额标准均明显高于盗窃罪,如果认为“骗”的行为是主行为从而认定本案成立诈骗罪,则量刑明显偏轻,因为行为人明知存折尚在所有权人控制范围内,并非他人遗忘物更非遗失物,这种情况下仍然“捡”走存折据为己有,在违法性认识上,行为人应当认识到这是在窃取他人财物,其主观恶性等同于盗窃,故而评价为盗窃罪更能体现罪刑相一致,量刑结果更显公正,由此也就可以反推而得出结论,应認为“捡”的行为才是主行为从而认定本案成立盗窃罪。
以上复数行为犯中主行为的认定思路仅是笔者的管窥之见。笔者建议“两高”就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发布指导性或典型案例,指导司法人员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准确定性,促进司法公正。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三级高级检察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330038]
[1] 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页。
[2] 参见熊红文:《公诉实战技巧(修订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页。
[3] 参见张明楷:《单一行为与复数行为的区分》,《人民检察》2011年第1期。
[4] 参见刘仁文、狄世深、吴孟栓:《私自给商场积分卡加分兑换购物券进行消费应如何处理》,《人民检察》2006年第20期。
[5] 同前注[3]。
[6] 参见刘一守:《程剑诈骗案——猜配捡拾存折密码非法提取他人存款行为的定性》,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3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7]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3页。
[8] 参见梁根林:《量刑反制定罪与刑法基本原则》,《中国检察官》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