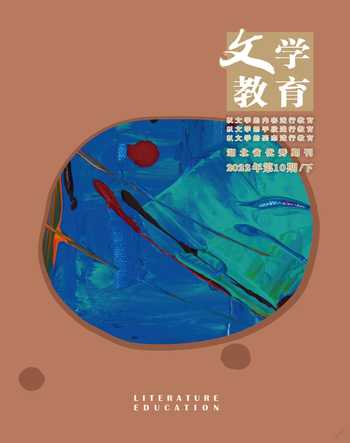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的中心地位
吴月
内容摘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作为论述中心,凸显了悲剧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从《诗学》一书出发,并结合亚氏其他著作,把握悲剧作为全书核心和“诗”的典范形式的原因:悲剧的形式更完整;所用语言和技艺都更加成熟;所摹仿的对象更高尚,达到的效果更好。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诗学》 悲剧 中心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涉及悲剧的定义、本质、创作要求等方面,千百年来散发着理性的光芒。在众多研究中,悲剧在全书中的中心地位和对于其他文体的示范作用常被忽略,相关论述不多。通过对《诗学》一书的归纳可发现,“悲剧”作为独立名词出现94次,“喜剧”出现30次,“史诗”出现20次。悲剧的中心地位不言自明。那么悲剧为何能越过喜剧和史诗成为全书论述的中心?这一点在《诗学》一书自身的论述中就可找到答案。从全书论述的内在逻辑而不仅仅从概念的拆解或悲剧理论的现实运用出发去探讨悲剧理论,能够进一步的把握悲剧这一体裁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其他文体的示范意义,更能通过分析这一关键词梳理全书逻辑,重新把握悲剧这一形式的审美内涵。
一.从悲剧理论基础看“悲剧”的中心地位
悲剧是《诗学》中论及文学艺术时出现次数最多的文体。悲剧何以成为《诗学》论述的中心?就悲剧自身发展来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悲剧和喜剧都源于临时口占这一表演艺术,前者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后者是从下等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在酒神祭祀仪式上,人们会扮演酒神的伴侣围绕神坛载歌载舞并演唱酒神颂,其内容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人间遭遇种种苦难,最后战胜苦难取胜的故事。由此可知,悲剧的产生具有仪式性,体现着人对神的尊敬和膜拜;喜剧源于当时的滑稽表演,是城市中流行的表演形式之一,但属于下等表演的一种。因此从两者起源出发,悲剧的社会价值要高于喜剧。
就悲剧的认识价值来看,由于人类社会在当时物质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古希腊先民对许多自然现象感到困惑。当种种自然现象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他们的内心就会产生恐惧和困惑的情感。这种自然界对古希腊先民的生存压迫,使他们意识到了生存的危机,进而导致了他们悲剧意识的产生,并将对自身命运的发现和思考表现在悲剧之中。因此悲剧自产生以来就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思考,与命运的抗争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与渴望,具有深刻的内涵。
就悲剧的创作状况和受重视的程度来看,首先悲劇的发展过程一直以来都有较为明确的记录,受到重视,而喜剧诗人见于记载时,喜剧的形式已经相对稳定。其次,到了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悲剧在这一时期创作颇丰,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名家辈出,如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因而悲剧在当时已然是日臻成熟、成果卓显的文学和表演样式。由此,亚里士多德将悲剧这一体裁放在论述的中心位置不无道理。
此外,亚里士多德对于摹仿的看法与老师柏拉图相反。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与理式隔了三层,因而是不真实的。且诗人在摹仿时往往迎和人性中低劣的、非理性的部分,会养成观众的哀怜癖,这对于民众的生活和理性发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应该把诗逐出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否定艺术真实性、否定悲剧价值的看法,建立起逻辑严密的诗学系统。他肯定摹仿的价值,认为摹仿是人的天性,人们从摹仿中可以获得知识,进而肯定艺术的价值。就悲剧而言,他认为悲剧的内容不是远离真实,而是通过展现可能或应该发生的事情去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去表现人生普遍的情绪与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悲剧比历史更加真实,更接近哲学。
因此,从悲剧的发展状况和亚氏的艺术观点出发,可以看出悲剧作为《诗学》论述中心不无道理。
二.从《诗学》内部看悲剧的中心地位
(一)悲剧的形式更加完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悲剧形式的论述集中出现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二十六章。
从悲剧的构成来看,亚氏在第五章最后一段论及“至于成分,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因此能辨别悲剧好坏的人也能辨别史诗的好坏,因为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不是在史诗里都能找到的”。显而易见,悲剧与史诗相较,构成更加复杂。形象和歌曲是悲剧独有的成分,虽然不是悲剧构成的核心,但其作用不可小觑。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诗学》中很少论及其重要作用,但在《政治学》中对这一点予以了说明。亚氏在《政治学》第八卷论及青少年是否应该学习音乐时提到:“音乐应以教育和净化情感为目的,第三个方面是为了消遣,为了松弛和紧张的消逝”。他认识到了音乐的重大感染力,论述了音乐的多种用途,体现了音乐具有的正面作用。因此歌曲在悲剧这样反应严肃主题的演出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应该是积极的,有益于净化情感,教育观众。
关于形象的论述在《诗学》中有两处,分别出现在第六章和第十四章。他肯定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认为形象不应该成为诗人关注的重点。亚氏在第六章中论及形象时指出形象固然能吸引人,但“跟诗的艺术关系最浅”。在第十四章指出“诗人若是借形象来产生这种效果,就显出他比较缺乏艺术手腕”。亚氏在《诗学》中对艺术形象的轻视主要是由于它与作诗的技艺相关性较低,并不是由于这一成分会破坏悲剧的艺术性,降低悲剧的格调。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高明的诗人应多着眼于情节的安排而不是一味靠形象来引起效果。实际上亚氏对于形象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诗学》最后一章中提出“悲剧具备史诗的所有的各种成分(甚至能采用史诗的格律)。此外,它还具备一个不平凡的成分,即音乐(和形象)”。体现出他意识到音乐和形象这两个成分对于悲剧而言的价值,只不过提醒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要把握重点,避免本末倒置。
就悲剧的形式而言,亚氏在《诗学》中论及悲剧在表演形式上采用画景,场数有所增加,演出过程中有三个演员,合唱队在表演中的参与成分减少,对话成为悲剧的主要部分;并且运用到了面具、服装等用作装饰的其他道具。在创作方面,悲剧在加入对话后取长短格,具有一定长度,情节不再简单,言语相对庄重,不再有滑稽的词句,并且抛弃了以往的活泼而获得了庄严的风格。由此看来,悲剧的形式在当时业已定型,相当完善。
因此,悲剧综合六种成分,形式完善,风格合宜。就其构成的复杂和形式的完整而言,悲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要优于史诗。以悲剧为主对作诗的技艺进行分析说明,内容更加全面,更能体现诗的特殊审美价值,亚里士多德将其作为全书论述的中心也是理所应当的。
(二)悲剧运用的技巧更加成熟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在情节的建构和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优于史诗,在创作过程中这两方面所运用的技巧更加成熟。相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二十三章。
亚里士多德呼吁史诗诗人们在建构情节方面学习悲剧创作的技巧和手法。史诗虽然有篇幅较长的优势,但常常因为规模宏大而忽略了情节的整一性。他指出当时的史诗诗人在创作时都变成了历史家,史诗内容总是写一个时期内涉及的所有事件或是围绕一个人物写关于这个人物的所有事件。这样的情节建构是有所偏颇的。因此他在书中第二十三章中提出“史诗的情节也应该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在史诗诗人中,亚氏最推崇荷马。荷马不仅是《诗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诗人,并且每次都以被肯定的姿态出现。亚氏将荷马对于作诗技巧的运用作为诗的创作技艺的典范,部分原因也在于荷马的史诗作品中重视情节整一性的安排,建构十常精妙。亚氏优秀的史诗作品应该学习悲剧,注重情节的整一性,而不是单纯的以时间为线索或以人物为中心去进行材料的堆积,而是有选择性的去建构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十分注重视听对悲剧表演的影响。他认为“视听必然属于诗的艺术。”要求诗人在这方面保持审慎的态度。关于“视”方面的重视主要在于形象,上文已述。在“听”方面,除了歌曲以外,主要指的是悲剧的格律和用语。《诗学》第四章的结尾处论及悲剧所运用的格律主要是短长格,这是因为“短长格是最合乎谈话的腔调,证据是我们互相谈话时多半用短长格的调子,我们很少用六音步格,除非抛弃了说话的腔调。”肯定了悲剧的格律。第十七章在论述情节安排时要求要求悲剧诗人应该竭力使用各种语言方式传达情节,不仅要表达清楚,还要充分体现人物情感,并符合人物的情感倾向。由此可见,在加入对话后,悲剧不仅采用了合乎谈话的腔调,还充分运用言语上的种种技巧,要求悲剧的语言不仅要符合对话用语,符合格律,也要符合人物情感。因而悲剧的用语要求更高,更富于技巧。
亚氏在《修辞学》的第三卷中也论及了悲剧的用语。他肯定了悲剧用语的合理并且认为悲剧的语言相较史诗更加恰当。他指出悲劇作者们不再沿用以前的写作方式,并且抛弃了日常谈话中不用的词汇,但以六音步格写作的诗人至今仍在使用这些词汇。“所以去摹仿那些连发明者自己都不再采用了的写作方式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这里提到的六音步格也就是史诗格。由此可见,悲剧在用语上要优于史诗,其语言更符合当下生活,比史诗用语更加灵活贴切。
综上,悲剧在情节建构和用语技巧上都为史诗做了示范,体现出了悲剧对于史诗的典范意义。悲剧由于长度受限,情节波折,因此在创作过程中要求的技巧性更强,以悲剧为中心去论述作诗的技艺也就更为充分和合理。
(三)悲剧摹仿的人物和对象更加高尚
前文主要论述了《诗学》中悲剧相较于史诗而言地位更高,形式更完善,技巧性更强。在书中对于悲剧和喜剧的区别也有所涉及,主要集中在第二章、第四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第二十六章。
亚里士多德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论述到悲喜剧的所摹仿的人物。悲剧总是摹仿品性更高尚的人,这一点有别于喜剧(喜剧总是摹仿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但是与史诗相似。在这里似乎可以确定悲剧的摹仿对象要优于喜剧。但第十三章在论述情节的内容中又提出,悲剧中所写的人物应该是介于两种人之间的人,不是绝对的善良或公正。这种人声名显赫,家庭幸福,但却因为过失受到惩罚。那么悲剧摹仿的对象究竟如何要高于其他人却又介于两种人之间?这种人究竟是否要优于喜剧所摹仿的对象?
这一观点在《诗学》中没有详细说明,但在亚氏的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首先品性更高尚的,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怎样的呢?就道德层面而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三卷中指出在一个城邦中,公民的德性不会只有一种。所有的公民都应当是善良的公民但不必然都是如此,因而也更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人:“一个善良之人就在于有一种德性——完满的德性。显然,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该有的德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公民”。这里似乎从道德层面将公民分为三层,道德最高尚的是善良的人,接下来是良好公民,最后是其余公民。因而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应该指的是良好公民或善良之人。就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来看,亚氏认为在城邦中,往往德性越完满的人,政治权利越大,地位也就越高。这种观点与中国“德以配位”的观念相类似。同时他还指出“教育和高贵的出身更经常伴随着那些更加富有的人,富人们差不多拥有了诱使人们为之犯罪的事物,由此获得了高尚、善良和通情达理的美誉”。综上我们可以推出,悲剧所摹仿的比我们“好”的人应该是指德性良好,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都相对较高的人,这也解释了悲剧的选材为何常常着眼于大家族的成员或统治者。那么从外在条件和内在德性来看,悲剧就摹仿的人物而言要优于喜剧。
其次,为何这种德性良好甚至是完满,拥有权利和地位的人又必须是介于两种人之间的人?这主要是由于亚氏对中庸的推崇。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伦理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在这里就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过度和不及会产生失误,中间就会获得并受到称赞。他是推崇中间性的。亚氏所追求的中间性不是苟且的折中,而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谐”一切可称赞的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中间性。青年人如初生牛犊,血气方刚,偏向冲动和粗暴;老年人历经沧桑,又偏向怯懦。只有中年时期的人才人格分明,充满力量。在悲剧中,描写具有过于善良或过于邪恶的人都是不合适的。只有着眼于这些处于生命丰满时期,历经过生活的种种考验,又能够安然应对眼前重大人生时刻的人物,才能在自身和谐的形式中反映出来的刚健而富有生命力的美。因此悲剧所模仿的对象是有良好德性的,有较高的地位、良好的教养和相当数量的财富,但又不那么完满,常因为无知或本性如此造成过失,进而受到惩罚的人。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深刻的认知价值,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从各方面而言要优于喜剧所摹仿的比较坏的人。
就悲剧的摹仿对象而言,亚氏在第六章对悲剧下定义时明确悲剧是对一个“严肃”活动的摹仿。怎样的活动是严肃的活动?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一个人越高尚,他的活动就越是严肃。所以一个高尚的人的活动,其本身就是优越的,从而是幸福的”。同时“幸福在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因而有理由说它是“是合乎最高善的”,因此悲剧所摹仿的活动是高尚的人的活动,是优越的和合乎德性的。那么喜剧所摹仿的活动是怎样的呢?在现在流传的《诗学》版本中,亚里士多德并未展开对此问题的论述。但他提到“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动”,对这种行动的摹仿最初是讽刺诗的内容,后来变为喜剧。“喜剧是对比较坏的人的摹仿”。在这里,“坏”与特定的恶相关,但并不带来痛苦,也不属于毁灭性的东西,滑稽算其中之一。那么这些滑稽的人所做的活动势必要劣于合乎最高善的活动。因此就两者所摹仿的对象进行比较,悲剧所摹仿的严肃的活动是高尚的人所做的幸福的、合乎德性的活动。是一种较喜剧所摹仿的活动而言更为优越的活动。
不论从摹仿的人物还是从摹仿的对象来看,悲剧所摹仿的人物和活动本身就要优于喜剧。因而从内容来看悲剧往往在人物形象和活动中寄寓思想,试图去表达对于人生的认识甚至是普遍性的哲理,有传达思想的价值,教育意义更强,更有助于引导观众做出正确的选择。
(四)悲剧引起的效果更好
就悲喜剧的所引起的效果而言,论述集中在第六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要能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诗学》第十三章中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 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亚氏在《修辞学》中进一步对这两种情感进行分析:怜悯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看到毁灭性或痛苦的灾祸发生在不应该遭受这种痛苦的人身上引起的痛苦情绪,而恐惧是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的或引起痛苦的灾祸即将发生引起的痛苦情绪。同时,从《诗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情感都受到理性支配,理性使得观众对怜悯和痛苦的对象做出选择。《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提出情感都是受理性支配的这一点。由此可见,怜悯和恐惧是受理性指导的快感和痛苦的情绪。这种情绪如何使观众受到陶冶呢?学术界对于悲剧的功用仍未达成共识,往往各执一端。但不论是认为其功用是“宣泄”、“陶冶”还是“净化”,都是通过悲剧调节矛盾,让观众重新体会人生深刻的意义,进而使其情感在理性原则指导下达到适度,并从中获得教益。由此悲剧所引起的情感使得人们的心胸从感情的压迫与挣扎中超脱出来,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看待社会和人生。
喜剧引起的效果在《诗学》中没有提到。但在《修辞学》中,亚氏提出滑稽会引起快乐。《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快乐的性质作了论述:“每一种活动都有自己所固有的快乐。属于善良活动的快乐是高尚的,属于邪恶活动的快乐是鄙下的”。喜剧是对特定的恶的活动的摹仿,恶的活动引起的快乐也不会是高尚的快乐,对人而言也不一定有所教益。因此从教化作用出发可知喜剧引起的效果不如悲剧。总之,悲剧产生的效果更符合德性,更能体现文艺的社会功用和对观众的教化作用,因此将悲剧放在全书的中心地位,突出其在“作诗的技艺”方面也更具有典范意义。
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涉及悲剧理论的内容进行梳理,就会发现悲剧的中心地位和典范意义在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呈现:悲剧形式更加完善,技巧更加成熟,表现形式更完整,能够达到更好的表演效果;情节更加集中,能够让观众在情节的整一性中感受其中的深刻意蕴;摹仿对象更优越,能够通过对高尚的人的严肃活动的摹仿,塑造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審美价值。通过归纳梳理书中作为论述焦点的悲剧,可以让我们在理解其构成的同时更意识到这一体裁的深刻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
[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
[5]陈明珠,《诗学译笺与通绎》,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
[6]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发展概述[J].戏剧艺术,1995(03):34-44
[7]李昊,李卿,刁海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创作论[J].作家,2008(16):185
[8]张婷.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及现实主义精神探析[D].安徽大学,2020.DOI:10.26917/d.cnki.ganhu.2020.000082
[9]徐兴根.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结局观看古希腊人的悲剧审美人格[J].求是学刊,1991(04):74-77
[10]徐蕾.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2):42-46
[11]弓艳.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论述的认识[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1):21-22.DOI:10.16227/j.cnki.tycs.2008.01.006
[12]纪园缘.从《诗学》中探究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悲剧理论[J].网络财富,2009(23):87+89
[13]龙志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J].赤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版),2011,3(09):124-126
[14]卢晓燕.从《诗学》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3(09):65-68
[15]秦明利,罗贤娴.近10年国内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综述[J].外语教育研究,2014,2(03):61-66.DOI:10.16739/j.cnki.cn2
1-9203/g4.2014.03.003
[16]刘龙.论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的论述及其他[J].祖国,2017(12):76-77
[17]李剑楠.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J].艺术家,2020(05):188-189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