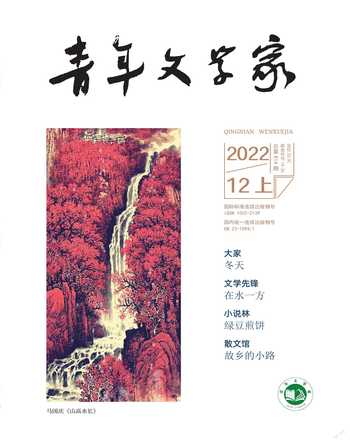“举重若轻”的时间与空间
张更祯

余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余华的思想比一般的作家更加独特,更加新颖,他的作品视角颠覆了以往的传统观念。在余华先生的诸多作品中,《活着》最突出的文学特色,是其具有典型的双重叙述结构和鲜明的文艺美学特色,这种结构贯穿于小说的每一段故事,既体现了“活着”的真实生活哲学,又极大地衬托了它特有的美学效果。其双重叙事空间中的巨大张力、不同频率、不同时差所产生的韵律,赋予了其叙事的特殊时空美。另外,在小说的艺术形式背后,还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审美意蕴,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审美力量。在富有美感的叙述结构和艺术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举重若轻”的美学意蕴,这就是人们在面对变幻的命运时所表现出的顽强、伟大、原始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至高的审美力量。
一、“举重若轻”的空间美感
(一)第一人称叙述层
在第一人称叙述层面,“我”并不负责讲故事,“我”的真正任务是引导故事,在故事的连贯性上表现出特定的观点,偶尔还会对故事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恰当的评估,或者在与故事情节类似的地方,以串联的形式将下一段故事的情节串联起来。《活着》中,“我”成功地将福贵老人引入了剧情,而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他真的成了一个听众。这样“解构”式的叙述,让“我”在福贵老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听话、懂事、通情达理的倾听者,而福贵老人对“我”的忍耐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但是,这里的“我”是以串场的形式出现的,“我”经常会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出现,而这个时候,就会使故事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降低了小说的速度,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活着》里的“我”,主要是通过耐心地聆听福贵老人的独白而得到认同,而“我”则是其中的“采风人”,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将民间的事情记录下来。“我”的重新出现,其实就是为了表现福贵老人的强大心态,增加了读者的同情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是真正的故事作者,“我”的存在是为了凸显福贵老人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样的烘托方式,让读者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也让读者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福贵老人的内心,让他的故事变得更加悲壮。同时,要注意的是,“我”在达到巅峰的时候,会悄然现身,制造短暂的停顿,营造一种祥和的气氛,让读者能深刻体会福贵老人内心的痛苦,并尝试着让读者“在风中寻找答案”。
(二)以福贵为主的叙述层
本文的第二个叙事层面上的福贵,是整个故事的真实叙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体。福贵老人将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父亲被自己气死,母亲病逝,儿子有庆因献血过多而死,女儿难产而亡,妻子、孙子相继死去,最亲近的人都离开了他,最后只剩下勤勤恳恳的老牛陪伴着福贵老人。他说起自己的家人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更多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掩饰不住心中的悲伤。就《活着》的叙事结构而言,“我”和福贵老人这两个叙述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平行的结构,“我”的叙述层主要是起到了导向的作用,福贵的故事层主要是揭示事情的本质。从福贵老人的讲述中,可以知道,福贵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在受苦受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那种无助的感觉,让福贵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悲伤,但这并不能磨灭福贵一家人对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坚定信仰。而家人的离开,却让现在的人更加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决心,在这份真实的痛苦中,福贵老人超乎常人的承受能力和心理素质,令人不禁称赞他的乐观。福贵老人从不长吁短叹,埋怨苦楚所造成的悲惨命运,也从不埋怨世间的不公平,即使到了最后,身边只有一头老牛相伴。余华也说得很清楚,《活着》里的福贵,除了苦难就是苦难,但是仍要乐观面对,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说,福贵的人生阅历让他的心灵越来越坚强,也让他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形成了一颗坚强的心。无论国家、民族、社会如何变迁,福贵都能忍受、平静地接受,用自己的劳动去忍受乡村变革的苦难,而福贵这个角色的形象和他的不幸经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数十年来的艰苦历程。
二、“举重若轻”的时间美感
(一)节奏美感
在叙事学中,频率是叙述时间的一部分。通常,“按照故事中的事件与叙述之间的重复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类:一次发生一次的事件,描述多次发生的事情,多次讲述一次的事情,叙述一次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活着》一书中的重复,是一种“描述了多次发生过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是对“同一性质”和“同一主题”的多次描述。
首先,我们从“重复”的去世开始分析。自从1992年《活着》问世以来,最让人难忘的是,主角福贵的家人们以各种方式死去,无论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该作品大致分成两个叙述层次,福贵老人作为叙述者的第二叙述层次是故事的主體。其中,“我”的四次插足导致了故事的中断,将整个故事分为五段,讲述了福贵七个亲人的“死亡”:第一段,福贵是有名的富二代,他成天吃喝玩乐,把家里的财产都输得一干二净,他的父亲当场昏倒,从粪坑里掉了下去;第二段,福贵洗心革面,老婆家珍也把儿子接回家,可是好景不长,福贵为重病的妈妈抓药,半路被当兵的军官强行带走,两年后回家妈妈就去世了;第三段,福贵与妻子儿女平安度日,一家人其乐融融,谁知有庆给县长妻子捐血,却因为医生抽血过多而不幸身亡;第四段,福贵家中喜气洋洋,妻子身患重病,但奇迹般地痊愈,女儿凤霞与二喜结婚后不久便怀孕,但不幸的是,她因难产大出血而去世,没过多久,家珍也去世了;第五段,二喜在工作中被两排水泥压死,而福贵仅剩的一位亲人苦根,但他七岁时也因为吃太多的豆子而死。通过上述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福贵的生命中,美好和快乐的人生往往是如此的短暂,当家庭和睦、喜事来临之时,总有一些亲人离世。更可悲的是,福贵的七个亲人,一个也没能逃过一劫,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只有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因为疾病过世,其他五个都是因为意外而死。所以,作者把福贵的一生谱写成了一首哀乐,他的每一位亲人的逝去,都会成为一道沉重的音符,敲打着读者悲伤的心;而那些痛苦的故事,就像是一首主题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让“死亡”的沉重和压抑变得更加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活着》中的重复性叙述,除了七个亲人的相继过世,还经常出现“太阳下的福贵”这个情节,作者用一种平和的语气,用清新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宁静的田园景象:福贵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坐在一棵茂盛的大树下,眺望着远处的田野。偶尔有一阵清风吹起他那一头稀疏的白色头发,旁边还有一头正在啃食青草的黄牛。村子里一片寂静,老人看起来是那样的平静。如果说福贵的七个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死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一幅幅恬静温馨的农庄画面,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活着”这个词。小说的文本实质上是“生”和“死”的交错,确切地说,是生胜于死,是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而福贵却还在,在为生存而活。由此可以看出,《活着》并非单纯的“死亡”歌曲,而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打断节拍、转换情感,减轻了痛苦所带来的沉重。换句话说,“生”和“死”这两种旋律交织在一起,既展现了音乐的韵律美,又创造了一曲普通而又宏大的人生之歌。
(二)速度美感
一篇小说要表现出一种跌宕起伏、张弛有度的时间美,就必须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改变时距来控制叙述的速度。具体而言,若缺乏文字的加速,则情节的发展将会停滞,因而变得枯燥乏味;反之,若缺乏慢节奏的文字,则会使故事的内容失去真实感,令人生厌。就《活着》来说,作家巧妙地把握了叙述的变化,让时间赋予了“故事与神奇”。
首先,小说中有很多“加速”的动作来描述“死亡”的情景。福贵的七个亲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人世,占据了更多的篇幅。然而,读者们却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死亡”的整个故事情节上,而忽视了作家在这一刹那的表现。回顾余华“先锋”时代的作品,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死亡场面,作者常常会放慢叙述的节奏,以“慢镜头”的方式,细致地描绘着角色的死亡,让作品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而在《活着》中,作者用简短精练的文字,省略了本来可以“大显身手”的一幕。在“有庆死亡”的故事中,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描述有庆为什么要捐血,也没有说有庆是怎么死的,只写了寥寥数语,福贵赶到医院的时候,有庆已经在一间小屋中躺着,福贵带着有庆回家,葬在了“我爹”和“我娘”的墓上。福贵安葬有庆之后,在村口看着通向镇上的道路,一共十一页,而有庆的去世,只有两段很短的片段,极大地降低了读者对死亡的消极情感,减轻了读者内心的压抑和沉重。
其次,在对温馨画面的描绘上,存在着许多“减速”的现象。《活着》通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福贵的人生所遭受的磨难。实际上,我们若仔细阅读,会发现其中蕴藏着许多温暖的日常场景,用“慢镜头”来减缓叙述的节奏,创造出一种温暖、祥和的气氛。比如说,在故事的后半段,家珍和有庆一起从娘家回来,这对本来就家道中落、妻离子散的福贵而言,当然是一桩大喜事。正文在“有庆半岁归来”这一段话后,又详细描述了“家珍身穿一件大红旗袍,手里拿着一只蓝底白花的包袱”,接下来是对周围环境的描述,“道路两边的油菜花都是金色的,还有蜜蜂在嗡嗡地飞”。“水红”和“金黄”显然是一种温暖的色彩,它能营造出一种温馨、愉悦的气氛,而“漂漂亮亮”“飞来飞去”等词语,则以活泼的声调。作者在这幅温暖的画面中,采取了“减速”的手法。可以看出,《活着》中的“加速”活动,可以有效地缓解“死亡”所带来的沉重,而温柔的“减速”,则为读者营造了一种温馨与安宁的气氛。余华善于运用时间的变换,使得作品具有张弛的美感,而且一再强调“活着”这个主题。
三、“举重若轻”的美学意味
俞敏华指出,对小说的艺术形态的探讨,并非把它们视為机械化、抽象化的象征,而是要以文本为核心,通过叙事学、语言学等理论对文本进行细致地解读与剖析,从而使之成为文学作品所构建的文学世界。而在审美上,则要以审美的直觉和敏锐的洞察力来全面地评判作品,探索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蕴。所以既要从《活着》的时空美入手,又要对其背后的深刻审美内涵进行剖析。或者说,通过形式分析,深入到更深层次的含义。
时空的空间化、双重叙事空间的并列、叙事时间的弹性变化、两种旋律的交错“重复”,实际上都在形式上实现了“沉重”的死亡与“苦难”的消解与超脱,使读者与作品之间的美学距离得以拉开,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张力,使小说的叙事方式呈现出“举重若轻”“化重为轻”的美学效果。其实,《活着》更多的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形象化的人生寓言,而“举重若轻”这一艺术形态,最终所指向的却是人生的真实力量与审美内涵。具体来说,福贵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年代,却失去了自己的家人,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然而,福贵以一种平和、轻松、乐观、积极的态度,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不仅体现了“举重若轻”的表达手法,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情趣。换句话说,作者运用这种艺术形式,就是要表现一种“举重若轻”的生命力:人在生存的荒谬和命运的无常面前,并不是软弱的,而是在与现实的痛苦斗争中,迸发出强烈的生命活力,从而实现“人”的自我身份,以及对“活着”的真正含义的肯定。所以,余华最后要表现的是“举重若轻”的美学意蕴,那就是人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时所表现出的顽强和伟大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崇高的审美力量。而从这本书中,读者们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一种在苦难面前,依然充满着温暖和希望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最终反思,一种对生命崇高力量的肯定。
总体而言,余华在《活着》的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上做了一种特别的艺术处理,他想要表达的并非“死亡”的沉重和荒诞,而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种与命运抗争中所产生的崇高美。也就是说,福贵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但他却还活着,这是一种超越了死亡和痛苦的精神境界,用“活着”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表达生命的本质,就像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后,依然“举重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