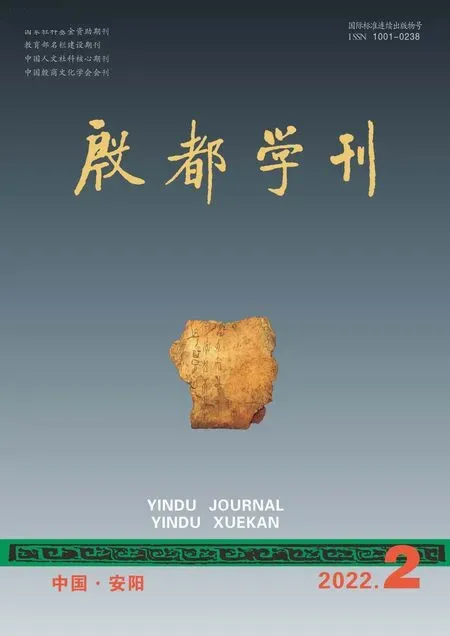豫北内黄(梁庄)方言的呼语变韵
李学军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2)
一、引言
梁庄镇位于内黄县最南部,东依中召乡,北靠后河镇,西与浚县接壤,南与滑县毗邻。梁庄话属于内黄方言(中原官话郑开片)的南片。
本文所说的“呼语变韵”主要是指人名和部分亲属称谓词作呼语成分(呼唤语和称呼语(1)李宗江:《呼语的形式和话语功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七)》,商务印书馆,2014年。时其末尾音节所产生的韵母变化现象。该现象是2017年5月我们在梁庄镇南部调查方言时偶然发现的,当时仅初步记录了南里庄村的情况。2019年4月和5月我们又进行了两次实地复核,并补充调查了周边10多个村庄。
从音变性质以及表达功能两个方面来看,人名变韵遵守D变韵规则,其作用在于增加响度(开口度增大)借以提高听话人的注意力。亲属称谓词变韵主要遵守另一套规则(下文姑且称之为C变韵),个别韵母为u的亲属称谓词则遵守D变韵规则,其作用在于增添感情色彩义借以进一步拉近和听话人的关系。从通行范围以及生存状态两个方面来看,人名、亲属称谓词D变韵仅通行于临近滑县地界的南李庄、阿虎寨、小后河、曹李庄等极个别村落,且限于50岁以上的个别人口语中,已明显处于接近消失的濒危状态。而亲属称谓词C变韵则通行于梁庄全镇以及中召乡、六村乡、后河镇的部分村落,适用的年龄层次也更为广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不论老少,可以变韵的亲属称谓词面称时一律使用变韵形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梁庄镇处于三县交界处,历史上曾划归滑州(今滑县),其方言内部的匀质性不如其他乡镇,且与典型的内黄方言(以城关镇为代表的中北片)在舌尖声母的分组、部分古知组、章组合口三等字的读音、“得/子”尾词的构成、D变韵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2)李学军:《河南内黄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下文对呼语变韵现象所用例词的标音一律按梁庄话的实际为准。
二、人名变韵
人名变韵主要用于长辈对晚辈或平辈之间年龄大的对年龄小的面对面称呼或远距离呼喊之时(晚辈对长辈、平辈之间年龄小的对年龄大的一般不能直呼其名),且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熟悉,系亲属关系或邻里关系。该类变韵与内黄方言中的谓词、小地名变韵等使用同一规则,所以也可以称为“人名D变韵”。
双音节人名是发生这种变韵的主体,其变韵规则如表1。

表1 内黄方言人名D变韵规则
这里说明几点:第一,D变韵母与基本韵母的关系我们在讨论谓词变韵、小地名变韵时曾讨论过,这里不避重复。第二,表中所列人名变韵的零形式,其作用没有谓词变韵零形式的作用那么显豁。第三,表中的双音节人名是我们实地调查得到的,其变韵的情况多属于发音合作人的转述。第四,表中的数字符号①、②表示人名空缺,即在当地未发现末尾音节含有该韵母的双音节人名,即使含有该韵母的单音节人名也未发现。第五,每个韵母都能实现变韵,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音节都能实现变韵。如:“彬、斌、宾pin24”一般不能变作piɛ24(避讳豫北方言中詈词性极强的“鳖”的读音)。第六,因版面所限,对表中的人名变韵实例仅在右上角标写变韵符号,不再加注国际音标。
交际中,双音节名字作为呼语直接喊即可,一般不带姓氏,且末尾音节变韵。如表1中所示。而单音节名字有所不同,须带上姓氏(没有发现复姓的情况)方可用作呼语。
单名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解放而逐步多起来的(因重名问题严重,加上公安局的建议,目前新添人口的名字启用一般只能使用双音节),其变韵形式为“姓+名D”。如:马凯Dk‘ɛ55、苏奇Dt‘iɛ42、张涛Dt‘o24、刘静Dtio312等。
乳名(内黄方言里一般称作“小名儿”)能否变韵则需要区别对待。部分已经固化的双音节名字,可以作呼语,且能实现变韵。如:二妮Dniɛ24(男子名字)(3)长辈或同辈年长者按排行面称女子时一般使用“排行+妮儿[nir24]”的形式:“大妮儿、三妮儿、五妮儿”等。、二孬Dno24、孬蛋Dtɛ312。而新兴的双音节叠音型乳名和正式名字(内黄方言里一般称作“大名儿”)通用,可以作呼语但一般不能变韵。如“媛媛、宽宽、豆豆、兰兰”等。
昵称与乳名的情况类同。由排行加上双音节名字中一个音节构成的昵称,做呼语时可以实现变韵。如:二庚Dko24(本名“贵庚”,排行老二)、三海Dxɛ55(本名“俊海”,排行老三)、二民Dmiɛ42(本名“院民”,排行老二)。由双音节名字中的一个音节(一般是后一音节)加上“子”缀或“-儿”缀构成的昵称,可以作呼语但不再变韵。如“海军”可以构成昵称:军儿、军子。主要用于家庭内部大人对小孩儿称呼的人名代称形式“老+排行”格式在视线之内一般可以作呼语,如“老二”“老三”等,但一般也不能发生变韵。

这里强调指出,含姓氏或人名的社会称谓语可以用作呼语但不能变韵。主要包括以下四类情况:①老+姓氏单。如“老王、老张”等。该格式用来分别称呼比较熟悉的某姓成年男子,这种用法应是受普通话影响后起的。因为在内黄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县城、乡镇机关外,这种称谓并不流行。②姓氏单+职位/职业。如“李乡长、郑老师”等。③男名+家。这是内黄方言典型的称谓语,用来指代该男子的妻子。如“贵家、学庭家”等。因为前两类形式都不能发生变韵,所以我们这里不把这一格式视作变韵的零形式(“家”的韵母ia在D系统中属于不变韵母)。与之相对的“女名+家”指代该女子的丈夫或未婚夫,仅能用作娘家人对女婿的背称。④“人名+他(她)+亲属称谓词(通用)。如“凤英她奶”“贵臣他爹”等。
人名D变韵主要用于两种场合:一是看到某人而称呼或呼喊对方,二是视线之外寻找某人。前者一般作独立成分,意在提醒对方;后者主要构成呼语句,期待对方的应答。如:
(1)思勇Dyo55,恁爹往地嘞走了冇?(独立成分)
(2)山民Dmiɛ42!山民D!山民D!(呼语句)
三、亲属称谓词变韵
亲属称谓词变韵主要用于晚辈对长辈以及平辈之间年龄小的对年龄大的打招呼或呼喊之时,交际的双方一般是亲属关系或街坊邻里关系等。变韵形式已发展成为面称,并与本韵形式表示的背称构成对立(4)这里所说面称与背称的对立主要针对亲属称谓词的概念义而言,不包括面称时以近内亲称呼外亲、远亲甚至是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的情况等。。
与人名变韵完全遵守D变韵规则不同,亲属称谓词变韵虽然涉及的原韵母音节只有11个,但却使用两套规则:原韵母为u的3个音节“姑、叔、夫”使用D变韵规则;原韵母为a、、ɛ、i、iɛ、ia的8个音节(不计声调)“哥、奶、弟、爹、姐、爷、妈/娘”则使用另一套规则,我们称之为“C变韵”。为便于比较,记写使用D变韵、Z变韵的类同方式,在称谓词后上标“C”,并加注国际音标(变韵实例中,声、韵、调完全相同的音节只标注第一个),归纳如表2。

表2 内黄方言亲属称谓词变韵规则
与人名大都可以实现变韵有所不同,亲属称谓词只能有选择地部分实现,如表2所示。可以作呼语成分是其变韵的必要条件。仅有背称的亲属称谓词,不管辈分高低、年龄大小,也不管是血亲还是姻亲,不能作呼语也就谈不上变韵。如“公公、婆婆、丈人、丈母娘”等等。可见,梁庄话亲属称谓词的变韵面称形式应该是从原通用的亲属称谓词中进一步分化而来的。
从社会关系上看,能够实现变韵的亲属称谓词绝大部分属于具有血缘关系的近内亲,且一般限于长辈以及平辈中的年长者。具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外亲“姨、舅、姥爷、姥娘、妗/妗子”,具有姻亲关系的内亲“嫂/嫂子、婶/婶子、大娘”等,其面称只能使用与背称一样的本韵形式。这种“内外有别”“取大舍小”的选择(5)郭继懋:《常用面称及其特点》,《中国语文》1995年第2期;卫志强:《称呼的类型及其语用特点》,《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说明该类变韵要比谓词变韵、人名变韵受到更多的文化因素制约。
表2中可以变韵的亲属称谓词,除了“爹、娘/妈”之外,其余一般都有排行的问题。如“哥”的面称有“大哥C、二哥C、三哥C”等,其余类推。需要指出的是,“兄弟C”这一面称的排行则是“二弟C、三弟C、四弟C”等,没有“大弟C”的说法,只有“大兄弟C”这一面称形式。当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心,亲属称谓词面称的排行问题越来越淡化。
能够实现变韵的亲属称谓词虽然不多,但其变韵形式作为面称的覆盖面极广。这一点内黄方言与其他方言以及普通话亲属称谓词面称的使用特点基本一致。因为人们在交际中为协调人际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规约:借用亲属称谓词面称形式来称呼许多只有背称(个别只有他称)的外亲、远亲,甚至是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等。这种泛化使用见表3。

表3 内黄方言(梁庄镇)C变韵的泛化使用
②除表中所列直接借用形式外,还有两小类间接借用形式:a排行+变韵面称(爹C、娘C除外)。该类形式与直接借用基本相同(“排行+爷C/奶C”不能称呼亲爷爷、亲奶奶)。陌生人为了拉近与年龄相仿的对方的关系之时泛用“大哥C”或“大兄弟C”来称呼。b人名+变韵面称。该类形式倾向于称呼远亲或街坊邻居。如:“桂芬姐C、玉臣弟C等。
亲属称谓词变韵的使用场合与人名D变韵稍有不同。视线范围之外寻找辈分高的或同辈分的年长者,亲属称谓词一般不能构成呼语句(即使是称谓词前可以带上人名也是如此)。因为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视线之外的亲属称谓词呼语即使能够听到一般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3)书芬姐Ctiai55,恁家嘞车得在家嘞冇?
(4)三姑Dkuo55,俺姑夫叫你麻利回家嘞。
值得注意的是,变韵的亲属称谓词在特定条件下(作为亲属,设定跟死者说话)可以用作“呼告式”呼语。
(5)爹Ctiai24,路上拿你嘞银钱吧。(开吊的当晚,亲属在佛爷庙上送死者上西天之路时的嘱咐之语)
(6)哥Ckai55,家嘞事儿都安排好了,甭再搁记了。(亲属在死者相片或坟头前进行祭奠时说的话)
四、来源问题
就豫北方言而言,讨论人名变韵的报告仅见李进立(2010)(7)李进立:《汝阳方言的人名变韵》,《新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王自万(2011)(8)王自万:《开封方言变韵的几个问题》,《汉语学报》2011年第2期。王文仅列举了“小三sɛ、铁蛋tɛ、小孬n、小九ti、大喜iu”五个乳名的D变韵。不过,从他的分析看,前两个似乎更符合韵尾为n韵母的Z变韵规则,最后一个显然属于韵母i的Z变韵,中间两个似是Z变韵和D变韵在开封方言中产生了混同。。不过,王文所提及的开封方言中的小名(乳名)D变韵似乎更符合静态性的Z变韵规则,即不论面称与背称都可以使用变韵形式。李文所讨论的汝阳方言中的人名变韵具有呼语性质,但文中并未指明这一点。从结果上看,汝阳方言中的人名变韵很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来源。按李文的分析,韵基为的来源于人名末尾音节和小称后缀“娃儿”拼合,而韵基为ɛi的则来源不明。
内黄梁庄话的两类呼语变韵也肯定有不同的来源,因为两者使用的语音规则差异很大。与汝阳方言人名变韵部分存有明显的合音痕迹不同,梁庄话人名D变韵则属于凝固化程度很高的融合性音变,其演变轨迹早已模糊不清(即使是广泛报道的谓词D变韵,目前也只能根据功能将其来源的主要特点笼统地概括为“异源同形”(9)陈保亚:《〈官话方言变韵研究〉序》,载张慧丽:《官话方言变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合音的演化链尚不能完全接得上(10)王洪君: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里主要来讨论带有拼合痕迹的亲属称谓词C变韵的来源问题。
从内黄及周边方言呼语的使用情况和历史文献来看,亲属称谓词变韵应主要是源于其末尾音节和语气词“唻·lai”的合音。依据有三:
第一,以城关镇为代表的内黄方言普遍存在一个韵基为ai的语气词。该语气词的用法与梁庄话称谓词变韵的用法完全一致,仅能附于名词性呼语成分之后或呼语句(感叹句)末尾表示提醒或感叹(11)梁庄话等也存在这一语气成分,只是一般仅用于非变韵称谓词或普通名词之后。。
受呼语尾音节韵母的影响,该语气词存在以下几种弱读形式:①在a、o、、、ai、ei、i、ia、i、ua、u、uo、y、y、yo等韵母之后读作·iai/·ai;②在之后读作zai/ai;③在前鼻韵母之后读作nai;④在后鼻韵母之后弱读作·ŋai;⑤在u、au、ou、iou、iau韵母之后读作·uai。⑥儿化韵音节后面一律读作·lai。这里仅举称亲属谓词作呼语成分或构成呼语句的例子:
(7)爹□·iai,恁也得听听俺姊妹几个是咋说嘞呀。/叔□·uai,再喝点儿吧。(呼语成分之后)
(8)我嘞那大娘□·ŋai!/二哥□·iai/·ai!(呼语句句尾)
(9)小儿□·lai,你听说吧。/孩儿□·lai,怎得儿弄不中。(呼语成分之后)
(10)我嘞娘儿□·lai!/妮儿□·lai呀!(呼语句句尾)
第二,内黄周边方言亲属称谓词的变韵不仅与梁庄话大致相同,且变韵形式大多存在“亲属称谓词+□·ai”这一等价形式。
西南部相邻的浚县、滑县以及长垣等方言的亲属称谓词的面称、背称较为发达。这里主要以滑县方言为例来说明。主要涉及9个音节,如表4所示。

表4 滑县方言亲属称谓词的背称与面称
需要说明的是,①“兄弟”一词的使用同梁庄话一样,仅在泛化用法中才有背称、面称之别。②“爹”的面称与背称只存在于老年人当中,年轻人一般只使用“爸”的面称与背称。③“叔、娘”也有面称形式,但似乎还是两个音节,分别读作u55·ai,niaŋ42ai,只是“娘”这一称谓词仅保留在老年人口语中。
与梁庄话不同的是,滑县话在使用“姐、哥、爷”等亲属称谓词作呼语时(语度较慢),还可以分别读作tiɛ55·ai 、k55·ai、iɛ42·ai 等。后一个弱化音节十分含混,可视作合音前的“一个半音节”的阶段(王洪君,1999)。合音(取前一个音节的声母、介音、声调,取后一个弱化音节的韵母)与弱读形式并存在豫北方言中十分常见。
第三,从文献资料上看,附于名词性呼语成分之后表呼唤语气的虚词只有“唻”。
近代汉语中,元杂剧开始出现该用法。以下例句来自明代臧懋循的《元曲选》:
哎,婆婆唻,我便是得生他天界。(张国宾《汗衫记》四折)
柳翠唻,谁着你那两叶儿眉黛愁。(无名氏《度柳翠》二折)
宋江唻,这是甚所为,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康进之《李逵负荆》二折)
当然,元杂剧中还有一个与“唻”同功能的“俫”字。例如:
刘家女俫,你与我讨一把火来。(无名氏《鱼樵记》二折)
《汉语大词典》(1993)(12)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010)(13)《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分别采用词条和字条分立的方式注音释义,并未深入讨论“唻”和“俫”作为语气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且多有龃龉之处。钟兆华(2015)按照“词形、音读有差异的同义词分立”原则,将二者分立为同表呼唤语气义的两个词条。前者标为去声lài,后者标为阳平 lái(14)钟兆华:《近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李崇兴等(1998)将二者视作同一个语气词,且只收“俫”条(15)李崇兴、黄树先、邵则遂:《元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任晓彤(2012)则基于三个理由(二者同出现在呼语之后、语法功能完全相同;臧懋循的音释都注为“离靴切”;在元杂剧不同选本中存在换用现象)认定“唻”和“俫”属于同一语气词的不同记音字(16)任晓彤:《元杂剧语气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我们基本认同李崇兴、任晓彤两位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将“唻”视作语气词的本字。理由是:①与“俫”相比,“唻”字在元杂剧中作为呼语后语气词的使用频率高。初步查检《元曲选》的结果显示,两字的这一用法共计20例,其中15例使用“唻”。②从字源和字义演变上看,“俫”作为“来”的繁文,起源更早(最早见于战国陶汇文字),从人,来声。字义的发展主要是围绕动词“来”扩展。至宋代增加了“见”(辽《龙龛手鉴》,997)“玄孙之子为俫孙”(《类篇》,1066)义等,元代又产生“元杂剧中扮演儿童、小厮的角色”等名词义。而“唻”作为后起字虽不见于古文字材料,但收入字书比“俫”还早。南朝《玉篇》(534)训释为“歌声也”。字义的演变一直围绕“声音”义进行。至宋代产生“呼犬声”义(《龙龛手鉴》),后扩大为“声也”和“呼声”(《集韵》)等。虽说表呼唤义语气词的语法化过程尚待进一步探讨,但“凡口类皆从口”的“唻”字显然更有资格充当这一角色。③从字音演变上看,中古“来”“俫”“唻”三字同韵(《广韵》《集韵》),到近代“俫”与“唻”依然同韵(《元曲选》(17)(明)臧懋循:《元曲选》(重排),中华书局,1989年。),但与“来”的韵母分化(《中原音韵》:“俫”属于车遮部,“来”则属于皆来部。杨耐思(1981)分别拟为iɛ、ai韵(18)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发展到现代三字又合并为ai韵。将参与合音的本字分析为“唻”至少不会与“俫”字产生语音上的不协调。
最后顺便提一下韵母为u的“姑、叔、夫”三个音节所产生的D变韵问题。我们认为,这三个音节之所以不能变作uai韵,可能跟这三个词与“唻”合成的kuai55(拐)、uai55(□)、fuai三个音节不理想有关。前两个容易联想负面义词,后一个则念起来非常拗口。但为什么最终选择uo韵,我们推测可能跟“夫”音节的弱读形式(·fuo)密切相关。“夫”的读音偶然与D变韵规则契合,并借助D变韵的强势,将“姑”“叔”两个音节覆盖。
四、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从共时角度描写了内黄梁庄方言人名、亲属称谓词充当呼语时所产生的变韵现象,包括变韵规则、变韵功能、变韵的名词语类别、适用的场合、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等,并结合内黄及周边方言对亲属称谓词C变韵的可能来源做了简要分析。
目前关于呼语变韵的报道还不多见,里面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梳理。如:处于变韵过渡区的梁庄话,其D变韵范围为什么比典型的内黄方言还要宽泛?呼语变韵为什么使用两套变韵规则,这两种规则处于怎样的历史层次?人名变韵的来源及其与谓词变韵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
尽管语法音变现象早已成为北方官话方言(包括晋方言)研究的一个热点,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这方面的描写工作还算不上细致、全面、深入。在城乡高速一体化、方言面临生存危机的今天(19)邢福义:《汉语事实在论证中的有效描述》,《语文研究》2014年第1期。,如何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抢救性记录、及时整理各类富有价值的方言濒危现象,已成为我们每一个方言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附记】写作过程中,作者曾就“唻、俫”两字之间的源流关系等问题先后请教于汪维辉、张生汉、李宗江等先生,获益良多。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十届年会(2019.10,临汾)上宣读时,又蒙麦耘、汪化云等先生提出批评与建议,这里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