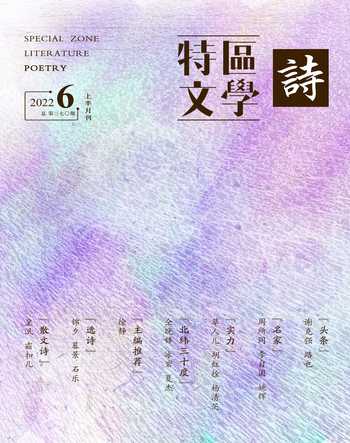《荒废帖》
嫩草长成劲草,以蓑草终
如野心与雄心并驾,却被灰心刺死
当年月消逝,每年枯萎的大梦
零落成泥
足下经年骨血,无人识,无人听,无人问
如游魂腐败的肉身,无人收拾
每当我看到湖畔成片的芦苇在寒风中低下头去,又
抬起头来
我就又有了活下去的力气
那远离人群的一株是孤单的鹤
或一只承露迎风,舒展翎羽的野鸡
那些苍白花穗,独自跳舞
碧波中的照影并无丝毫
自怜、自弃与羞愧
也并不嘲笑被繁华抛弃至此
无人过问的逐水流花
谁又不曾被弃或自毁?谁又没有
哀愁与怨怼。一场冷雨后
重新收拾的残骸
都是今天一身生机勃勃的血肉,活在人间
编者注:蓑草,似应为衰草
诗人简介:
沈鱼,男,本名沈俊美。1976年生于福建省诏安县。毕业于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作家。著有诗集《借命》、《花香镇》等。曾获《诗刊》年度青年诗歌奖、《诗探索》中国诗歌发现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诗歌奖等,《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成员。
世 宾:周而复始的生命
诗人沈鱼的《荒废帖》所展现的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它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的“离离原上草”。诗人用了“草”“骨肉”“芦苇”“孤单的鹤”“野鸡”“逐水流花”“重新收拾的残骸”这几个意象,从生命枯荣的自然规律、自然界的孤寂和静默,到人性的柔弱和悲剧性命运“被弃和自毁”“哀愁与怨怼”几个方面,抒写了生命无论顺其自然,还是“独自跳舞”,都有相同的结局,都置身于无法逃避的生灭命运。诗人在这首诗中,使用了他惯用的笔调,阴郁、哀愁,仿佛蘸满了四月的雨水抒写了他目睹的生命,没有喜悦,明亮和蔚蓝都被抽离了,只有那灰暗的基调深深地浸透在生命的底色里。在一些人眼里,这可能是一种悲哀,但在诗人眼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必然,一种生命的基调,诗人并不因此而颓废,他只是默认生命或命运的灰暗的必然。在诗歌中,在灰暗的笔调底下,一直贯穿着诗人不屈的生命观,灭了又生,低下头又会抬起头;该灭时就灭,该生时就生,该凋零时凋零,该繁茂时繁茂。诗歌的最后一行,就像在给这首诗定调,用简洁的四个字“活在人间”,铿锵有力地展现出无论经受多少遭遇,生命唯有像“今天”这个生机勃勃的样子,才是不变的样子,其它只是过程。《荒废帖》不荒废,沈鱼的阴郁笔调底下,总有燃烧的不屈的火焰。
吴投文:并非只有荒废
很喜欢沈鱼的这首《荒废帖》,但又说不出喜欢的原因。这是读诗时经常遇到的情况。读一首诗,来自直觉的判断很重要,就像读此诗,有一种被即刻裹进去的感觉,这就是一首好诗。诗中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荒废的气味,但在荒废中也有倔强的挺拔,并非只有颓废,像“重新收拾的残骸/都是今天一身生机勃勃的血肉,活在人间”这样的诗句,在前面铺垫的基础上,显得精练自然而富有意味。这可能是我喜欢此诗的一个原因。
此诗名为“荒废帖”,全诗围绕荒废而展开,诗中的情境和意象都符合荒废的图景,如一片断墙残垣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却又透露出“活下去的力气”,在荒凉中显示出亮色。我想,这都是从诗人的生命中流露出来的,来源于他对环境的敏感,来源于他对人生的真切感受。所以,此诗是有其复杂性的。在诗人复杂的意绪中,包含着不可抑制的坚定,他并非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执着于心灵的完整。对人生的不妥协,实质上就是心灵的完整。诗中的意象都是灰暗的,却不见得就是悲哀,而是在意象之间的联结中透出不屈、不认命的坚定。诗的语言也不是那种完全忧郁的调子,而是在悲伤中暗暗生长着一种力量。所以,此诗表现出来的荒废固然是生命的一种图景,其中还是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辩证理解。他的心中有一种力量,隐约克制着荒废對人生诗意光彩的侵蚀。
此诗有前后两节,在结构上带有比兴的意味,“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也”。前一节以草木兽物比喻人生,有一种荒寒的气息;后一节大概才是诗的主体部分,才是诗人心里真正要说出的话。但仔细推敲一下,似乎去掉前一节,后一节亦可独立成为一首诗。当然,我这样说,未必确切。前一节所引起的氛围,对于带出后一节还是有意义的,前后两节的关联固在,却也并不意味着一首诗恰如其分的完整。
向卫国:“活”在“荒废”中
《荒废帖》的主题当然是“荒废”。“草”会荒废,“心”会荒废,“梦”会荒废,“芦苇”会荒废,“鹤”“野鸡”无不荒废。
荒废的过程:“嫩草”—“劲草”—“衰草”,或者“野心”—“雄心”—“灰心”。
荒废的原因:“被弃或自毁”。
荒废的心情:“自怜、自弃与羞愧”,或者“哀愁与怨怼”。
因为世间万物都会荒废,所以时间即荒废。这就是真相。
但是,万物的生机也在于此:“一场冷雨后/重新收拾的残骸/都是今天一身生机勃勃的血肉,活在人间。”诗歌的主题,就此由“荒废”180°转向“生机勃勃”地“活在人间”。
问题在于,这一转身会不会过于突兀?我们回头再看,原来诗歌其实已多次暗示了“荒废”的过程,也是生命力自身的展示:“芦苇在寒风中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我就又有了活下去的力气”;“一只承露迎风,舒展翎羽的野鸡”;“那些苍白花穗,独自跳舞/碧波中的照影并无丝毫/自怜、自弃与羞愧”等等。
总之,这一“帖”之诗,并不只是“荒废帖”,同时也是“生机帖”或者生命赖以循环相依的“生肌帖”。没有荒废便没有万物的重生,一切“活”在“荒废”中。
最后想说一说诗歌题目中的“帖”字。帖,原本指书写用的布帛等材料,引申为样本等意思,比如学书法用的字帖。将此字用于诗歌的标题,大约是近十多年来(没有具体考证过)的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其中大约也暗含着某种诗歌的抱负,因为“样本”也可以说是“样板”。此诗列举了多种“荒废”的事物,以之为样本,但最终想要突出的显然是作为人类样本的“我”。
周瑟瑟:诗歌的人文立场
自古以来,诗歌是有人文立场的。但在当下,我们看多了没有人文立场的诗人,诗歌没有骨气精血,一滩死水,一堆烂泥。有的人写作就是谋求好处,谋求活得体面高贵,但越是把文学当作谋求好处的工具,文学越没有尊严,所谋求到的“体面高贵”已经是奴颜媚骨、斯文扫地。这是我读沈鱼《荒废帖》想到的。
在疫情居家隔离的最后一天,细读沈鱼的《荒废帖》,让我想谈谈诗歌的人文立场。习惯了封闭与解封的日常生活,《荒废帖》所写的“嫩草长成劲草,以蓑草终/如野心与雄心并驾,却被灰心刺死”,如此景象,正应验了此时的心境。
诗歌的人文立场是什么?是掩面而泣,是大悲无泪,大悟无言。“足下经年骨血,无人识,无人听,无人问/如游魂腐败的肉身,无人收拾”。如此悲声,客观呈现,干脆清净如水中石,如屈原怀里的石头,尖硬冰冷。
诗歌的人文立场是什么?是热血沸腾,是“活下去的力气”。“每当我看到湖畔成片的芦苇在寒风中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我就又有了活下去的力气”。
我们每个人的写作构成了诗歌自身的人文环境。放眼看四周,掩面而泣的有几人?热血沸腾的在哪里?我们中间谁是当代杜甫?首先要做“远离人群的”“孤单的鹤”,然后要放弃文学的好处。
我曾提出中国诗歌现代性启蒙,但四周一片沉寂,他们在忙于谋求文学的好处,并不需要启蒙之声。他们都是极其聪明滑头的诗人,他们明白丧失诗歌人文立场的写作,没有骨气精血的写作才能谋到文学的好处。
“重新收拾的残骸/都是今天一身生机勃勃的血肉,活在人间”。《荒废帖》大悲无泪,重拾残骸,给了一幅“今天一身生机勃勃的血肉,活在人间”的诗歌人文图景。
宫白云:重获生命的终极质感
徐敬亚老师把沈鱼的这首我当年推荐的诗《荒废帖》提了出来,重读后依然是诸多感觉向我涌来……好诗就是这样如嚼橄榄,常嚼常新,经得起岁月的淘洗与沉淀。
重读后,沈鱼的这首《荒废帖》最直接打动我的还是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那种微妙的认同感和感性的觉知,它依然痒痒地刺激着我的神经,与诗人一起历经诗歌中的所有起起落落。这或许就是通常所说的具有诗歌之魂的诗吧。沈鱼很高明,似乎一伸手就能将人生的境遇一网打尽,而且视角的切入十分的巧妙,以“嫩草”“劲草”“衰草”对应后面的“野心”“雄心”“灰心”,从而让一种“枯萎”的心境自然地到来,而这些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事物,却充满着内在的合理性,特别是以一种荒凉的语调说出,更加具有萧疏况远的味道。而连续四个“无”的排列,丝丝入扣,让浸淫到骨子里的况味以无羁的方式涌向四方。最妙的是三个意象“芦苇”“鹤”“野鸡”饱含大自然的灵气,显现意在言外的多姿。字里行间虽然散发着无奈、困惑但并不灰暗、颓废,反而给人一种奋争与雀跃。特别最后两行应是诗核所在,有镜头定格的意味,它让一切的个人得失从“荒废”中弹跳出来,“劫后重生”地获得生命终极质感。
另外这首诗的“內部”语感也特别值得称道,用徐敬亚老师的话说:“似乎像一首放大了、变化了的‘宋词’。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诗中一个典型的节奏案例。”评价之高足以说明它的非同一般。可以说正是这首诗古典式的韵律,张弛有度的节奏,配合着诗境,一步步把此诗带到最后的关口,形成一种音乐般的回环往复……好的诗人,就是要这样尽其力还给“诗”以“歌”的肌理。
赵目珍:写出了人在精神上的一种反转
这首《荒废帖》,从整体上,以赋的笔法写出了人在精神上的一种反转。由此,“荒废帖”遂也祛除了字面和名义上的“荒废”义,一变而成了“励志帖”。虽然在诗中诗人并未明确表态要“洗心革面”,但是意志上的那种坚强已经暴露无疑。
在结构上,诗歌共分两节,节奏分明。
第一节铺陈“荒废”的情态,内嵌比兴的手法。从意思上看,颇疑首句中“蓑草”为“衰草”之讹。因“蓑草”为草之一种,是特指。而“嫩”“劲”皆指草的生长状态,故“蓑草”当以“衰草”为是。唐代诗人李贺诗中有“衰兰送客咸阳道”之句,“衰兰”即指秋天已衰老的兰花。此诗中,“衰草”与此意同。当然,不得不说,诗人以“衰草”写“枯萎的大梦”有着非比寻常的震撼力。尤其是连用四个“无人……”句式渲染出的欲寻“枯萎”而不得的这样一种孤窘与无力,将人之“荒废”的情态,写到了登峰造极。这体现出诗人对语言的高超驾驭能力。不过,这一节的铺陈,显然是为下一节的反转埋伏笔的。
第二节也仍然可以说,内嵌了比兴的手法,如以“芦苇的低头抬头”来写“人有了活下去的力气”。接着,仍然用比的手法,假“鹤”“野鸡”“芦花”三种事物来一层层铺写,以物喻人;并通过外物的启示,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反省,从而加剧个人内心的觉醒。也因此,这首诗到最后不得不出现一种“上升”的气象。其实可以看得到,诗人正是以宏大的“壮语”来收束全诗的。这也是诗在起承转合之后,要达成的最终目的。
高亚斌:写草就是写人
沈鱼的《荒废帖》,用了象征的手法,先是写草,写草由“嫩草”“劲草”再到“衰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蓑草”当为“衰草”之误。)的一生。如同一个人从少不更事的蓬勃少年,到长大后的经受烈日风雨,然后,开始步入枯槁的暮年,草虽有着强烈旺盛的生命力,但它受制于气候或某种强大的外力,而身不由己地陷入荣枯的轮回。
草是有着自己的“野心与雄心”的,但草毕竟是草,它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也不能成就经天纬地的鸿业,于是,它所有的“野心”“雄心”,最终难免归于“灰心”。鲁迅在《野草》中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荒废帖》所要表达的,也是这种生命的荒废和虚度之痛。
诗人写寒风中的草,是一个人面临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苦难时的困境象征;而它虽备受苦难,却依然“生机勃勃”地“活在人间”,以“低下头去”和“抬起头来”的姿态迎风舞蹈,这无疑是对生命的礼赞,对生命卑微的认同和生命价值的肯定。写草就是写人,草的脆弱就是人的脆弱,同样地,草的坚强就是人的坚强,其人格化的特征非常明显。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个体的脆弱与坚韧、易朽和不屈、死亡和新生,读来令人极为叹惋。
不过,就诗歌的整体而言,这首诗的语言不够洗练,结构也显得松散。而且,在构思命意上,全诗也并没有超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表达的野草生生不息的主题窠臼,未能开拓出更加深远的诗境。
徐敬亚:现代诗意大概分两种,此诗可为标本
如果极度归类,现代诗中的诗意方式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金句型:①情感线索清晰,诗意转换迅速;②将帅分明,不流连铺张细节;③追求诗意深度,痛点凸凹。金句,作为一首诗的最深划痕,如匕首锋刃上放血的沟槽。我心目中金句诗的标准:一是生命意识要重,二是感觉层面要轻,三是语言修辞要透明。
我着重说另一种,丝绸型:①这类诗的整体平滑,诗意起伏微小,情绪一体化。这时诗发出的是一种微光,并非聚光灯只激射某几行。它的光不刺眼,却是一种通篇发光的亮体。②语感纯净,节奏纯然一色,这使它往往成为感觉性的、旁若无人的自述。③视角个人化,常常出现独立于世的唯己、唯一的情感。每一句都温吞似水,但细品有罗宋汤的浓度。我认为,这与其说是诗的分类不如说是人的分类。后一类诗更难写也更难被人理解。它需要诗人自燃炉火,通体透亮,甚至暗中藏有个人化的的哲学与美学。金句型诗人追求闪光的亮度,后一类则是低调的高僧。依我的阅读经验,后一类诗人基本是悲悯的、忧伤的,走在月球的背面。因此可以称此类诗是忧伤的丝绸。
这正是我最初读《荒废帖》的感觉。《荒废帖》是一首可以让人沉醉的诗,如果你深谙它的节奏,可以产生一种催眠的效果。
9年前作为主持人,在读《特区文学》2013年第2期稿件时,我最先看到了宫白云对此诗的评荐。我忍不住破了一次例,在宫的评荐后面缀了【徐敬亚加评】:请读者注意本诗另一特点,内部“语感”。细细读,似乎像一首放大了、变化了的“宋词”。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诗中一个典型的节奏案例。朗诵效果可能不错。其中,连续四个“无”之间,加入了8字的比喻。之后用了全诗最长句(22字),最后又是一个“又”字,把节奏忽然放缓……
开头几行的尾音,基本保持了一平一仄。3个无(无人识,无人听,无人问)之后又狠狠地加了第4个“无人收拾”。音韵是落下去的。第二节开头一个在最长句之后的那个“又”,非常有力!有谁能注意到这首诗的节奏,说明他心中存有古典韵律,而如能在语感中滑行,他心中便有现代诗意。
本期这两首选诗,可以用作考驗批评家阅读能力的样本,尤其是这一首。《关系》基本属于第一类,但兼有第二类的小特点。最后我想说,《荒废帖》是一首有骨头的丝绸诗—诗意在一片衰败中徐徐展开,却行行暗藏反转,处处显露出生命力的强劲与不甘!不能不令人想到陆游的“零落作尘碾作泥”。作为现代诗人,沈鱼说出了本诗最漂亮的一句话:“每当我看到湖畔成片的芦苇在寒风中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我就又有了活下去的力气。”
韩庆成:“荒废”的气势
《荒废帖》曾被《诗歌周刊》2012年第38期“本期头条”推荐。当时推荐的沈鱼四首诗,《荒废帖》放在第一首,因此印象很深。我特地找到那一期我写的主编荐语,看到一段题外话,像是一个预言,不妨转到这里:“《特区文学》‘十面埋伏’栏目最终决定第四次改版,把《诗歌周刊》‘中国网络诗歌抽样读本’的理念移植到‘十面埋伏’栏目,从2013年第2期起付诸实施。今后,《诗歌周刊》发表的诗歌作品,将有机会在这个已有八年历史的中国诗坛品牌栏目接受检阅。”这是《荒废帖》被《特区文学》第二次检阅了。时间过去十年,再读这首诗,依然被它特有的气势所打动。
诗的题目叫荒废,按说行文基调应是颓丧、低沉的,但沈鱼笔下的荒废,不“自怜”,不“自弃”,不“羞愧”,诗的语言勃勃,节奏铿锵,硬是让荒废的主题别有了一种昂扬的气势。当然,诗人绝不是要把“丧事”写成“喜事”,而是要表达“承露迎风”的“雄心”与“大梦”,因“被弃或自毁”而壮志难酬时的不甘和不屈,因而才有了“一场冷雨”后的“重新收拾”,才有了“活在人间”的“一身生机”。
霍俊明:一首诗“说”得太多了
沈鱼的《荒废帖》让我在“帖”这一字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对于当下诗人而言借用“帖”来说话并不罕见。那么传统化和文人化的“帖”与当代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写作来说如何才能处理得更为有效?雷平阳和陈先发以及其他的模仿者都在借用“帖”这一看似传统化的形式说着各自的心事,除了雷平阳和陈先发之外却很少有惊动我们内心的文本出现。显然,“荒废”就是诗人所要反复揭示的命题。第一节,草的成长和衰变过程与时间以及人的心境形成了同构。第二节开端出现的“芦苇”与诗人的“思考”之间形成了写作和思维的惯性运动,而写作者只有避开这一“惯见”才有可能具备更多的生成性的精神空间。诗人试图在第二节中反复强化精神状态,尤其是荒废之感,但是从整体性来看这一部分却显得拖沓、烦冗。质言之,第二节诗人“说”得太多了,“表达”得太多了,而诗的质感和空间就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