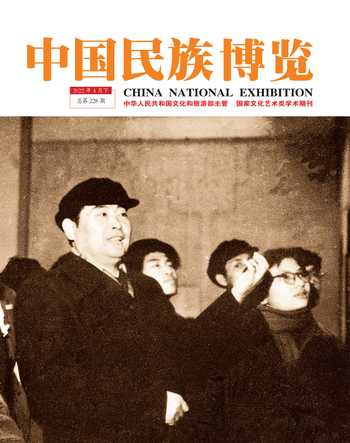“感物移情”与“及物移情”
李妍妍 武丽娜
【摘要】中西方文学理论在探讨美感的生成时都曾以“情”为立足点,注重物我关系的统一,突出审美中的移情作用。但是中国文论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更强调物对情的感召,而西方文论则在主客二分前提下强调情对物的推及。立足于比较视角,将中西方不同的“感物移情”与“及物移情”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二者的异同之处及其形成背后不同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 物感说;移情说;感物移情;及物移情
【中图分类号】J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8-176-04
【本文著录格式】李妍妍,武丽娜.“感物移情”与“及物移情”——中西方美感生成论之比较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2,04(08):176-178,192.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传统儒家文化智慧与当代乡村治理创新研究”(18CZWJ07)的阶段性成果
审美移情作为文学创作中的普遍心理现象,受到了中西方理论家的关注。虽然中西方在论到移情现象时都在讲心物关系,但是又有明显不同,正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西方“移情说”主张主体在观照客观外物时主动将自身的情感外射到客体当中,仿佛它也有一定的感觉、思想与情感,主体从而再对其进行审美欣赏,产生美感作用。在这里,主体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客体被视为无生命意识的欣赏对象,本质上是强调主动将主体的精神、情感给予客观对象,即“由我及物”,或者我們可以说其移情的过程是按照一种“及物移情”的方式进行的。而中国古代的移情理论则同时看到了“由物及我”的过程,侧重先由人受感于物引发情感,后由人的情感来感染物的双向交流,通过“心”与“物”之间的双向互动形成一种相互交融的和谐状态。在这里,“移情”的过程也就是“心”与“物”双向交感的过程,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移情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感物移情”的逻辑。
一、“物感说”中的“感物移情”
中国古代文论很早就从“心”与“物”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文学创作活动,认为创作活动始于“物”对“心”的感召,继而主体接受感召,“心”与“物”相互感应,于是形成了美感经验,后世将这一理论称之为“物感说”。因为其中包含移情于物的内容,讲究物我同一的审美感受,所以经常被拿来与西方的“移情说”进行比较研究。
《礼记·乐记》最早从“心”“物”关系入手来探讨艺术创造的审美问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认为,艺术作品从根本上来说,产生于“心”与“物”的感应。首先是物使心动,接连人心受感于物后产生不同的情感变化,不同的情感状态与外物发生感应后,就会产生格律各异的艺术作品。不难看出,《乐记》已经开始注意到,在艺术创造的审美感应过程中,“心”与“物”的运动关系是双向的,包含着“物使心动”与“心感于物”两方面。由此可见,这时的审美活动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感物移情”的重要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陆机进一步继承了“物感说”,提出了先由外物引发人的某种情感继而由其影响到主体心理创作的观点。“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作者先由四季及外物的景象变化而产生一系列情感反应,继而在文学创作中达到文思鲜明、物象清晰的特点。这就说明文学创作始于“物”对“心”的感召,继而主体形成特定情感后将其应用于创作过程,体现了“心”“物”双向感应的互动过程,实现了“感物移情”的重要过程。
刘勰继而在《文心雕龙》这部“体大精深”的理论巨著中提出了“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的独到观点,他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首先受到外物自然形貌的影响产生一定情感,继而在受感于物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特定情感移至外物当中,并最终通过刹那间的心神领会达到物我统一的境界。在心物交感中,刘勰也充分认识到了其包含的“物使心动”以及“心感于物”的顺次过程。《文心雕龙·神思》中进一步论述到,在创作过程中这种主客观的交互感应具体表现为“神与物游”,达到“心”与“物”的统一,最终产生“意象”。也就是说,意象的产生便是“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所表现出来的心物交感的“移情”结果。
清代的王国维进一步提出“意境论”,并将“意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有我之境”即“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种艺术境界充满着强烈的主体情感色彩,正如五代南唐冯延巳《鹊踏枝》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诗人将自己感怀伤春的感情代入其中,这里所描绘的客观事物为了服从于主体传情达意的需要因而染上了较强的主体情感色彩。“无我之境”即“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种境界虽曰“无我”,但并非真正无“我”。只是在这种境界中,主体顺从客体,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占据着主导地位,主体的感情溶解于被描绘的客观意象当中,超然无欲,物我无间,以物之自身观物。这种观照方式并非否定主体的存在,更非要排除主体的一切情感,而是要排除主体的“情感之欲”,达到一种与世无争的闲情逸致。这样,在“移情”的过程中,“我”向客体靠拢而不执意移情于“物”,主体以“物”之自身观“物”,使“我”融于“物”,故而构成“无我之境”,这都是“感物移情”的重要体现。
二、“移情说”中的“及物移情”
“移情说”作为西方近代美学中较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发源于19世纪的德国心理美学,后来遍及欧洲并对世界美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与浪漫主义运动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浪漫运动追求自我的个性解放,力图冲破封建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范畴,把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想象与情感提到首位,从而力图冲破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移情说”的基本主张便是主体在关照客观外物时主动将自身的情感外射到客体当中,彷佛它也有一定的感觉、思想与情感,从而主体再对其进行审美欣赏,产生美感作用。这就说明西方“移情说”的出发点便是“凸显自我”,即作为主体性的人在与物的对立中自我意识与情感的不断伸张。
西方“移情说”的先驱者是德国美学家费肖尔父子。弗里德利希·费肖尔注意到心理美学中的移情现象,提出了“审美的象征作用”,即“在审美观照中,形象与它所象征的观念融成一体,我们‘半由意志半不由意志地,半有意识半无意识地,灌注生命于无生命的东西’,形象与观念的关系也是若隐若现。”他的儿子罗伯特·费肖尔后又将其所提出的“审美象征作用”改称为“移情作用”,他将审美欣赏与人体的视知觉联系起来,认为审美欣赏在经过了知觉、感觉等特定环节后才会产生审美的移情作用,认为移情作用是直接随着知觉来的物我同一。费肖尔父子基本奠定了“移情说”的基础,充分肯定了人的思想情感在引起美感因素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人在“移情作用”中的主体性地位。
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进一步发展了“移情说”,侧重从主体的心理层面揭示美感经验。他通过援引道芮式石柱的例子来说明移情作用发生的重要方面——“人格化的解释”,也就是把物看成人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总是按照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的类比,即按照我们切身经验的类比,去看待在我们身外发生的事件。”实际上这种“人格化的解释”并不涉及意识活动,这种“以己度物”方式之所以产生也是为了“使事物更接近我们,更亲切,因而显得更易理解”,因此,在他看来,客体自始至终是为了适应主体而存在的。立普斯的“移情说”更侧重于由我及物的过程,移情作用也就是审美主体向审美对象的一种情感外射,并不存在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心灵交窃。因此,他的“移情说”虽然内容上涉及客体对于主体有所反映的方面,但究其本质还是主体间的自我审美转换与自我价值的肯定,映射到审美活动中便常常出现死物的生命化等结果。
关于审美活动理论,德国美学家谷鲁斯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展。谷鲁斯认为凡是知觉都以模仿为基础,审美的模仿不同于一般知觉的摹仿,审美的模仿大多内在而不外现,只是一种“内模仿”。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以模仿审美对象的运动和情感特征为观照,在心中自发地产生一种想要模仿的冲动,从而获得一定美感。这一过程也仅仅是涉及主体的生理冲动,而不涉及意识活动。谷鲁斯认为“内模仿”是美感经验的精髓,朱光潜认为这其实就是“移情作用”。与立普斯的“移情说”所不同的是,谷鲁斯的“内模仿说”更侧重于由物及我的方面,认为其是一种审美对象引导审美主体的情感内注活动。可以说,移情作用和内模仿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同一审美活动阶段中的两个不同的心理环节。
西方的“移情说”被作为美学理论引入我国,其中朱光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朱光潜的移情理论并不是对西方“移情说”的简单介绍与继承,而是来自中西方美学理论的多元整合。朱光潜认为移情作用的重要表现是“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在这里,他批判地继承了立普斯与谷鲁斯的学说,认为移情作用既是将我的情趣投向事物,又是将物的姿态吸收于我,形成物我双向互动交流的过程,这就同时涉及到由我及物和由物及我的两方面过程,说明其移情理论的实质是主体意识和客观实在的统一。朱光潜还提出了“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还震荡,全赖移情作用。”这一看法,他认为人与物都是富有真实生命体验的客观存在,移情作用便不单是主体向客体之间进行简单的情感外射,而是包含着内在生命之间的往复沟通。不难看出,朱光潜的移情理论同时涉及心物之间的相通相感,这和中国传统美学中心物浑融交感的审美活动如出一辙。但是朱光潜又大多是站在西方有关理论、概念的框架上对移情理论进行阐释,在阐述过程中就很难不带有西方“主客两分”的认识论模式。他从“物我同一”的角度论说美感,认为“物我同一”就是主体意识与客观实在在审美活动中达到的统一,而也正是这主客统一的要求暗含了主客互相分离的前提条件。同样作为我国美学大师的宗白华也对审美的移情作用做出了阐释,他认为美必须经过主体心灵意識的改造才能得以显现,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美产生的条件——“移我情”与“移世界”。在他看来,物我本来就是一体,自然与人有着相同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指引下,宗白华发展出了他的“同情论”。他更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和谐交融的体验,其前提是物我原本为一,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三、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的差异
总的说来,中国的“感物移情”与西方的“及物移情”虽因文化背景等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形态与模式,但是二者始终都寓于一种“物我同一”的融合性状态之中,追求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教相融的一致性,强调了主客体之间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物感说”中的“心”与“物”具有双重互动关系,首先由外物激发人的情感,继而人对物进行源于内心深处的审美感受与体验,两者在彼此融汇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物我同一”的关系。西方的“移情说”则注重主体将自身的情感等外射到客体中,通过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立的消失来达到“物我同一”,其前提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占有,从而实现客体的退出。但是两者在“物我同一”的前提下主客体之间的地位却大有不同,“物感说”中“情”所产生的过程侧重于由客体引发主体的情感,同时又由主体情感感染客体的双向互动交流。物感人的同时人同样感物,物感人使人“情”动,人感物则将“情”移入“物”中。心物感应往往是主客体之间刹那间的心神交会,二者无主次之分,在这里,物我的地位是平等的,两者同样具有生命体验,形成一种相互交融的和谐状态。西方的“移情说”则认为,审美欣赏的实质是主体将自我“映射”到审美对象里去,其主要过程是主体情感对客体的移入或外射、内模仿等,客体只能被动地等待着主体对它的认知,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因此,“移情说”的重心更多转移到主观体验上,突出主体的地位,认为客体的形式只有通过主体的心理内容才能成为审美对象,否认客体具有独立的审美地位。
中西方的移情作用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方式,究其深层原因是双方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哲学层面上的基础性差异,中国传统哲学自诞生起就算作一种内省的哲学,其一贯致力于探究贯彻于天地万物的统一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统一。早在儒家文化就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的相似结构,将自然视为人的道德精神的某种象征,进而形成“比德说”。自然万物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是作为独具审美意义的整体而存在,人们认为自然始终与人相生共存,并将自然看成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到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与自我是一个无法截然分开的整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中国古代的“感物移情”论提供了哲学基础,赋予了其独特而深厚的审美旨趣。西方文化思想自诞生之起就被赋予了主客两分的理性概念,较为彻底地扫除了原始诗性思维,走向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主客地位不平等这一痕迹明显的“移情说”便是西方社会主客二分哲学基础上的生动产物,在这里,物我关系完全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自然与自我处于互分你我、难以调和的关系之中,因而相较于中国古代哲学中讲求和谐相融的物我关系来说,多了几分突兀。
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古代的“感物移情”根植于“天人合一”观念强烈的中国传统社会,体现的是自然本位论的思想模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强调将人在与物的和谐交融中体悟客体的存在,主要运用直观、感性、象征等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更趋向于包含更深层次的直觉和顿悟,这种领悟只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之中,是处于不可名状、虚空飘渺的境界之中,追求的并不是对事物的一种明确的认识,而是包含认识在内的、对于事物发展规律和总体样貌的一种深刻把握和领悟,这就容易给主体留下极大的阐释空间。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周易》到老庄哲学都在强调一种体悟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都以“道”为根本指向。正如“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混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道”本身在形式上就是混沌难分的,因而无法从外在的直观形式對其进行界定,这就说明了古人正是因为具备了由体悟而衍生出来的抽象思维能力,才从意识中提炼出了“道”本身的模糊性与抽象性。所以,中国古代呈现出来的“感物移情”自思维方式的不同就决定了它的气质,从而导致“感物移情”的根本方式就是体悟式的“感应”。这种主观式的体悟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的,它更重视人的情感寄寓,重视人与物之间的对话交流,认为万物同人一样具备生命与情感,追求真正“物我合一”的境界,更加强调抒发自然的本我之情。而西方的“移情说”则立足于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重视理性和逻辑分析。西方的思维模式主要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认识客观事物,力图达到精确又极致的水平,力求排除阐释对象的任意性。从唯理主义到经验主义无一不在强调逻辑的重要性,正如笛卡尔“把数学看作是哲学方法的典范,他指出,要研究逻辑,靠研究数学来运用逻辑规律。”因此,西方的“移情说”很难不带有主客分离的现象,他们不相信个体的感官经验,更多依靠的是主体的反思与批判。自然景物触发的情感不能直接成为艺术创作的来源,而需要经过主体的客观分析和判断,因此产生物我两分的现象。
中国的“感物移情”与西方的“及物移情”都注意到了审美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西方的“移情说”更加侧重于从移情作用中的主体接受角度出发探究美感的生成,其本质上还是一种“物的人化”。而中国的“感物移情”则侧重在审美活动中使“心”与“物”相融相生,突出美感生成过程中人与物之间双向交流的平等关系。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方的移情方式在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面对当今世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资源,比较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之异同,将有助于为我们在今后的中西美学交流中提供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2]礼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
[3][晋]陆机.陆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晋]陆机.陆机集[M].中华书局,1982:1.
[5][梁]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
[6][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译注.[M].施议对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7][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译注.施议对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6.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七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七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272.
[1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七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1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37.
[13][战国]庄周.庄子[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
[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5][美]梯利.西方哲学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作者简介:李妍妍(1980-),女,山东菏泽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要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武丽娜(1997-),女,山东潍坊人,研究生,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