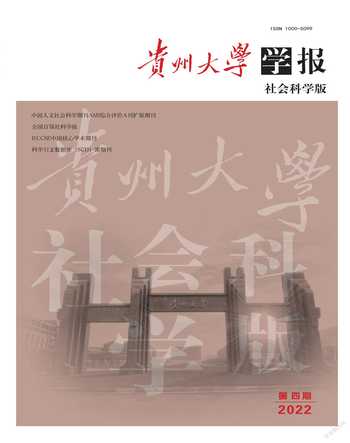20世纪中国思想中的酒
摘要:20世纪以来,科学传入中国成为人们理解、对付酒的新方法。饮酒伤身耗财被视作进德之障碍,不饮酒之风遂起。在唯科学主义者眼中,饮酒使人昏乱、妨碍理智、影响卫生,理当被禁绝。尽管不少思想家自己饮酒,但却一直将饮酒与萎靡困顿、意志消沉、懦弱、麻木不仁、自轻自贱、自我陶醉等相关联,对酒充满敌意。科学垄断了对酒的说明与解释,酒成为一种没有文化、没有精神的液体。然而,革命者自发利用饮酒来振发精神,寻求自由、突破、超越。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压倒了科学对酒的贬抑,饮酒成为人之常情与日用之需,但对酒精神的反思一直阙如。
关键词:酒;不饮酒;中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4-0026-08
当饮酒在明清时期成为日常之事,无论它出现在祭天祀祖、婚丧礼俗之中,还是沉入日常交往合欢之时,酒总是浸透在深厚的精神传统中,黏附着丰富的精神属性。进入20世纪,因被欧美战败,传统思想、传统生活被断定为落后、腐朽,祭天祀祖和婚丧礼俗,乃至相应的精神想象都被裹挟其中,一并被抛弃。从科学世界观出发,传统思想与生活方式都被祛魅。反傳统思潮也斩断了依附于传统思想与传统生活的酒的各种精神属性,酒遂成为一种没有文化、没有精神的液体。在科学理性的审视下,酒往往以反面形象出现在思想史中,成为思想攻击与禁绝的对象。
一、饮酒有悖进德
酿酒耗费粮食,饮酒让人麻醉、昏乱、消沉,酒桌上建立的人际关系脆弱腐化。简单地说,饮酒既危害生命,也损耗财富,这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饮酒风俗,有识之士或主张革命,或主张改良。比如在1912年2月23日,蔡元培起草的《社会改良会宣言》所附的《社会改良会章程》第二十九条有:“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及各种烟酒等)。”酒被归于鸦片、吗啡、烟等有害之物,甚至被当作毒品禁戒,这比《酒诰》以来对酒危害性的揭示更进一层。
民国元年,蔡元培、吴稚辉、李石曾、汪精卫、张静江、张继等人在上海发起进德会。会员分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饮酒”被视为恶习之一,“不饮酒”则是远离恶习、洁身自好之品行。进德会欲以此德行与旧式贪官污吏划清界限,让他们自惭形秽,以达到救治社会的目的。
在1912年5月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蔡元培提到了饮酒的具体危害,那就是对修身之不利:“酒与烟,皆害多而利少。饮酒渐醉,则精神为之惑乱,而不能自节。能慎之于始而不饮,则无虑矣。”酒醉,失去理性,精神昏乱,身亦不能修。要修身,“不饮”是前提。
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但基于师法废顿,他对修身进德一直也没有偏废。他认为,人事当以道德为本,尤其在大学中,学者之德与才应当相配。蔡元培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研究“学问”乃第一要务,但“学问”的增进离不开“做学问的人”。“兴趣”“人格”可以推动学问的进展,可以视为研究学问的前提。因此,“兴趣”需要认真培养,“人格”需要不懈完善。“人格”涉及人的内在涵养,特别包括情感、意志的修为,也包含在社会中与人交接的自由、平等、友爱等素养。为了促进学者们人格德性之涵养,同年6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并成立了“进德会”。按照“进德会”的章程规定,入会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三戒之上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丙种会员更在五戒之上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据载,当时入会的甲种会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许德珩、沈尹默、章士钊、马寅初、罗家伦、胡适、王宠惠、张国焘、辜鸿铭等;乙种会员有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等;丙种会员则有梁漱溟、李石曾、张崧年(张申府)、傅汝霖等。一呼百应,这表明修身进德乃当时大多数学问家之共识。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中陈述了“进德会”之旨趣。他首先区分了公德与私德,并指出,在社会中,个人私德会影响全体。他举了仪狄进大禹旨酒的例子说:“昔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司马迁曰:‘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子反湎于酒,而楚军以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诸如此类,不可胜数。”饮酒属于私德,但其祸往往超出个人而及于社会。尤其是掌权者,其骄奢淫逸会导致祸变纷乘、浸至亡国。因此,需要防微杜渐、修德自救。同时,饮酒也会影响自身健康、败坏口味,影响“味道之乐”。
对科学的信奉是20世纪国人的基本思想状况,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开始拿科学来为饮酒定性,同时主张以科学助力戒酒。他说:“不饮酒、不吸烟二项,亦非得科学之助力不易使人服行。盖烟酒之嗜好,本由人无正当之娱乐,不得已用之以为消遣之具,积久遂成痼疾。至今日科学发达,娱乐之具日多,自不事此无益之消遣。如科学之问题,往往使人兴味加增,故不感疲劳而烟酒自无用矣。”科学不仅告知饮酒有害健康,还可以为人提供健康的、可以替代饮酒抽烟的娱乐。这种说法,非深醉于科学者不能言。
作为民国以来首屈一指的学界领袖,蔡元培对饮酒的态度很快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一股不饮酒的风气。不过,吊诡的是,蔡元培本人始终嗜好饮酒,每餐都要有他家乡的黄酒,他的酒量还不小,尽管他从没有因饮酒误过事。
二、饮酒不科学
世纪之初,以近代科学技术支撑的欧美工业化已经渐入佳境,中国民族工业蹒跚起步,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仍以传统工艺为基础。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组织参会的展品多以茶叶、丝绸等传统产品为主,其中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酒类。陈琪的《中国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纪实》记录了中国在博览会上的所有获奖明细,其中酒类获奖的有直隶省官厅的高粱酒、河南省官厅的高粱酒、山西省官厅的高粱汾酒、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酒、山东兰陵公司之兰陵美酒等数个省40余单位的各种酒。依靠传统工艺酿造的酒代表着中国工艺发展的水平,也表现出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酒缠结在一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落后的社会状况与饮酒有何关联?日用而不知的民众对此惘然,但以苍生为念的知识分子则不能不思。
世纪初期的中国屡战屡败,民族心理阴郁,对自身的认知也多持否定。脱离黑暗,开启民智,以智修德,成为一代知识分子之共识。饮酒致人昏乱,于智于德有害无益,故时人常拒斥之。现代精神以科学为根底,以理论理性为手段,以效率为表现形式。饮酒会影响科学活动,会拖延、干扰理性、降低效率。在此意义上,现代精神与酒似乎不能两立。由此,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家们大都将酒视作敌手,态度最激烈的要数激进的科学主义者,如丁文江、陈独秀悖论的是:飲酒庆祝本是传统观念,本不饮酒的陈独秀在庆祝时也沿袭着传统观念。据载,“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吴稚晖、张申府等。
作为“科玄论战”之科学派主将,丁文江从不掩饰其对科学的热爱与信仰。“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 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将科学视为修养最好的工具,遇事皆能自觉以理性去分析、判断、决定,以科学指导生活。他们眼中,酒有诸多危害,比如:酒对身体有害(有害健康),酒摧毁理智。简言之,饮酒不是科学的人生。丁文江留学海外,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讲究科学人生。据说,他工作再忙,每天都要保证8小时睡眠。他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外出用餐,必用开水烫洗器皿。在酒席上他从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
丁文江自己不饮酒,他也一直劝常饮酒的挚友胡适不饮酒胡适说丁文江:“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1930年11月,丁文江就连续两次致信胡适,劝他不要拼命喝酒,认为“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他的第二封信则抄录一首戒酒诗:“‘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每饮辄呕泄,安得六府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有讥诃。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对朋友,丁文江是真诚的。自己认为饮酒有害健康,便也热忱劝诫朋友止饮。其对酒之敌意不可谓不深。
国民党元老中张静江、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1912年便参加了“进德会”,一直不饮酒。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张申府等人也不饮酒。这些人一方面主张启蒙,反对醉生与梦死,另一方面又坚定地以理想改造现实社会,甚至于将旧社会连根拔起。因此,在对未来社会图景的设计中,他们力主摧毁众神,以可信的科学理性为根基建构新道德、新精神。酒让人昏乱,是理智的敌人,被人厌恶、被人嫌弃,自然在新世界新精神中被剔除。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以建体立极为任。酒迷乱心神,同样被疏离。当然,梁、熊二人深研佛学,不饮酒也可能受佛学影响。
这些以救世救心为己任的思想者,提出或接受一种主义往往也都努力去践行,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都能自觉检讨。对饮酒的过激反应表明,他们已经触及了酒的精神。尽管他们对酒还没有形成主题化思考。
三、对酒的敌意
自由派思想家饮酒,代表人物是鲁迅、胡适、蔡元培、金岳霖等。但他们对酒并不友善。
1912年,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据他日记中记载,他时常“饮于广田居”,间或“颇醉”“甚醉”。这年8月饮酒10次,并且,在8月17日池田医院就诊,医生“戒勿饮酒”后,仍然“大饮”几次,9月又饮酒8次。常饮酒,偶尔过量而“醉”可能是年轻人失去了节制,也可能是不服酒、豪兴起而与酒斗败。对于志在四方的年轻人,更可能是在理想遭遇挫折之后的不满与发泄“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又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这些缘由对于官场中的鲁迅而言,可能都曾遇到。他自述:“他(范爱农)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范爱农是鲁迅的老朋友,在生活无着,前途无望中不停地喝酒,最后也因酒醉溺水身亡。“醉”是自我暂时之迷失,能够放心一起醉的朋友也是能够愿意彼此包容、相互交融的朋友。但是,一直醉则意味着一直放弃自我,可以说是“沉沦”了他说:“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有时也还喝……但是和青年说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可喝酒。”。鲁迅作《哭范爱农》曰:“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他们在一起,即使小醉,说些疯话,亦能“把酒论天下”,酒意激发起豪情,关心天下兴亡而非沉沦于酒。更多的天下人酩酊大醉却依然行尸走肉般活着,那才是真正的沉沦!范爱农生活无着落,偶尔小醉却身亡,岂不痛哉!
鲁迅曾因为常饮酒而遭到攻击。1928年1月15日,冯乃超在创造社刊物《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把鲁迅比成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老生”。1928年5月,叶灵凤在《戈壁》第1卷第2期发表漫画,将鲁迅描绘成酒坛后很小的“阴阳脸老人”。为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作为反击。当然,按照鲁迅的逻辑,喝酒不喝酒由自己的意志决定,他人无权干涉。基于此,鲁迅一再为自己饮酒辩护:“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我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将饮酒视为个人私事,视为可以自主决定的权利,这正是鲁迅一贯的自觉。
对于来自他人的批评,鲁迅会带着情绪反驳。但信奉科学的鲁迅自己对酒殊无好感。他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饮酒出于无奈,这颇类似魏晋人。事实上,正因为鲁迅有此无奈,他才会深刻地理解阮籍的无奈。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了竹林名士饮酒的缘由,特别是阮籍。他指出:“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没有说话的自由环境,不得不饮酒。现实残酷,无力改变,寄情于酒方可得些安慰。在此意义上,被迫饮酒悲壮而可叹。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鲁迅本人同阮籍一样不得不醉。所谓“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且持卮酒食河豚”;“深霄沉醉起,无处觅菰蒲”[10]470。道出的都是对世道的深深无奈。然而,不得不醉又非“装醉”。“装醉”是基于某些不良的动机而饮酒,比如赢取名士之名利。不得不醉更不是借酒发疯。对于借酒发疯,清醒的鲁迅一语道破:“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依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不得不醉为悲剧,“装醉”是不负责任的人的行径,则是闹剧。
国贫民弱,思想家们竭力寻求贫弱的原因,与贫弱黏附一起的酒似乎逃脱不了干系。酒总是和欲望、享受、昏乱、蒙昧联系在一起,饮酒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不思进取、贪图享受,是蒙昧堕落;不饮酒则表示理性、自制、清醒、振作。没有神圣,不用祭祀,酒也沦落凡俗。在追求光明的眼睛里,饮酒的生活愈发黑暗。鲁迅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孔乙己、阿Q等人皆嗜酒。如我们所知,周公在《酒诰》中规定了“饮唯祀”(包括祭祀时饮酒、孝养父母时饮酒、祭祀之后宴饮),汉代将酒作为圣人颐养天下之物,但汉代确立酒傕制度,酒价非下层民众所能承受得起。宋代经济繁荣,为增收酒傕,政府鼓励、诱惑饮酒。在观念上,宋人将饮酒视为“人之常情”,明清则有饮酒为“日用之需”说可参见贡华南的《北宋生活世界与饮酒精神的多重变奏》和《良知与品味二重奏下的大明酒精神》。饮者由祭司(“尸”),到皇亲贵族,到“士”,最终到平民,所有阶层都与酒纠缠不清。我们不难理解,孔乙己、阿Q等社会最底层的人也都嗜酒。
鲁迅对咸亨酒店中人物的刻画非常简约深刻。他聚焦饮酒,由此显露众人的身份地位,也曲折地透露出饮酒对于江南民众的精神价值。“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短衣帮”是做工的穷人,散了工每每会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酒不仅可以解身体之乏,还能够暖和灵魂,为卑微的生活提供精神支撑。
对于主人公,鲁迅一句话就鲜明地展示出他的底细:“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通常都是“短衣帮”,而孔乙己偏偏“穿长衫”,生存处境与身份认同在打架。尽管生存窘迫,但孔乙己还会“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窘迫的处境需要酒来调理,尽管在酒店中总会随时增添烦恼。当别人说他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他“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但当他喝过半碗酒,则“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在孔乙己被人打折了腿后,他用手撑到咸亨酒店,还要“温一碗酒”,并很有尊严地说:“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最后一碗酒同样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喝掉,然后从众人的视域中消失。那碗酒比旁人的说笑更重要,或许可以说,他的命随那碗酒而去。
阿Q属于鲁迅所说的“短衣帮”,无家无产,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他的精神同样离不开酒。鲁迅安排阿Q以喝酒方式出场:“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說……”他的故事随之展开,首先便是他“那里配姓赵”。在他被打败,通过精神胜利法心满意足之后,阿Q“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一切都像未曾发生。酒麻醉阿Q,使他遗忘,使他在重重挫折之后精神复原。在调戏吴妈而被赵大爷打骂,赔钱认罪之后,还剩下几文,他不赎毡帽,而“统统喝了酒”。在他从城里发财回来,便“走进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在不准革命之后,他感到无聊,欲报仇而不能,于是,“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酒对于阿Q,可以忘掉委屈,恢复丢失的脸面,可以使被惊吓的精神还魂再生。约言之,酒是“精神胜利法”的载体与具体表现。魏晋以来,大多以酒解忧的人与阿Q并无本质的差异,无怪乎鲁迅会将“精神胜利法”上升到“国民性”高度。
鲁迅笔下还有不少经典人物也以不同方式饮酒,比如《在酒楼上》中苦闷无出路的知识分子(“我”与“吕纬甫”)借酒浇愁比如,《在酒楼上》写道:“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他们萎靡困顿、意志消沉。《孤独者》中魏连殳一意喝烧酒对抗孤独。孔乙己是懦弱、迂腐、麻木不仁的下层落魄知识分子。愚昧、自嘲、自解、自轻自贱、自我陶醉的最底层民众(阿Q)时不时饮酒以度日。饮者都是沉沦不醒者,基于此,不难理解饮酒的鲁迅何以对饮酒又不以为然。
四、徘徊在饮与不饮之间
命运与酒相互纠缠的思想家不在少数。
明清以来,饮酒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胡适都熟悉且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胡适一直在中西古今之间游移,对酒亦是如此。对酒的态度,胡适一生经历有变化,大体可分为三阶段。
胡适年轻时,在上海过了一段自感荒唐的日子。与朋友一起喝酒、赌博、看戏、逛青楼,不仅因喝酒喝醉打了警察被关进监狱,而且还有过喝酒喝得差点醉死的纪录。他自述:“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地打牌;有时候,连日大醉。”年少轻狂,饮酒作乐,醉而乱为,这形象与文质彬彬的胡适似乎有点距离。但这正是胡适的真实生命,经过酒洗礼的文质彬彬才真实。
1925年,胡适与太太江冬秀为了他与曹诚英的恋情而关系紧张。在这段时间里,胡适不仅独喝闷酒,而且还与江冬秀赌气互相牛饮,有时醉得一塌糊涂。陆小曼曾专门致信胡适,劝他不再喝酒。在胡适40寿时,江冬秀送与丈夫“止酒”戒指。挚友丁文江则一再写信劝他戒酒,似乎胡适在酒中沉沦了。
待胡适自节自持,饮酒渐渐收敛,命运却又将他与酒捆绑在一起——因为白兰地救命而后半生一直随身携带酒壶。胡适心脏病首次发作是在1938年12月4日,他应邀到纽约演讲《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后,在友人家里吃夜宵时,忽感胸口疼痛、冷汗直冒。情急之下,友人递了杯白兰地,他当场一饮而尽,疼痛随即稍微缓解,由友人陪同回到饭店休息。隔天他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心血管阻塞,马上住院接受治疗,连医师都说,或许是那杯白兰地救了他一命,自此,装着白兰地的酒壶再没离开身。或许白兰地对他的体质是有些帮助。但胡适随身携带白兰地酒壶,还是难抵心脏病突袭,在1962年2月24日,他在新科院士的欢迎酒会上,再度病发骤然辞世。酒救过胡适的命,但这次却没能再现神奇。
因为饮酒而险些丧命的还有金岳霖。金岳霖对酒醉的体验丰富。他曾谈及:“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喝黄酒的机会多,醉也大都是黄酒的醉。黄酒的醉有恰到好处的程度,也有超过好处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学艺术的创作,超过程度就只有坏处。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维了。就醉说,最坏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转,走不能,睡不是,吐也吐不了。”能明辨不同酒的醉,此非亲醉者所不能言。尽管金岳霖也承认醉酒有其益处,但金岳霖醉过一次后就不再大喝。后来,每天睡前喝一两。他对理性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一个醉鬼不知道酒精对他有害,当他死于酗酒时,他只是值得同情,而他本人不一定不幸福;但是,如果他知道酒精对他有害却依然贪杯,当他死于酒精中毒时,他就制造了一个悲剧。知识本身是否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值得怀疑的。”强大的理性抑制了他对酒的欲望。但是,面对人情,金岳霖却不知道如何拒绝。他自述:“应酬场合上喝酒经常过多,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曾多次承认过‘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说的主要是喝酒。”金岳霖具有强大的理性,然而,生活在人群中的个人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理性所主导的方式生活。理性在人情面前退缩,酒便乘虚而入。庆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情世故发生变化,金岳霖也很少饮酒了。
冯友兰先生强调理性反思,他对饮酒也这样。他曾以喝酒为例谈“中庸”问题:“对于有些人,喝酒是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在普通的情形中,一个人喝酒,若至一种程度,以致其身体的健康,大受妨碍,则其喝酒即为太过。若其喝酒,有一定的限度,并不妨碍其身体的健康,而却因别的关系(例如美国政府行禁酒律之类),而不喝酒,则其喝酒的要求,即受到不必要的压抑。如此则其喝酒的要求的满足,即是不及。此所谓不必要,是对于此人的本身说;此所谓不及,亦是对于此人的本身说。喝酒的过或不及,本都是因人而异的。若一个人喝酒,只喝到恰好的程度,既不妨碍他的身体的健康,亦不使其喝酒的要求,受到不必要的压抑,则其满足即是得中,即是中节。”冯友兰信奉孔子思想,他对饮酒的态度也大体接受孔子“无量,不及乱”之说。他不反对饮酒,甚至还能理解、同情饮者。在他看来,每个人的酒量有差异,健康状况有差异,只要能喝得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否则便陷于过与不及之两端。
当然,个人的酒量、健康状况都需要每个人用理性去估量,饮酒中庸只能在理性指导下实现。冯友兰一再强调说:“一个人要喝酒,到哪里去喝酒,用什么方法去买酒,这都是要靠理性的指导。喝多少不至于妨害身体、妨害事业,这亦要靠理性的節制。如果一个人喝十杯酒,可以得到快乐,而不至于妨害身体,妨害事业,理性对于这种满足,只有赞助,决不禁止。所以孔夫子亦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冯友兰对酒的态度不像道德洁癖者、极端科学主义者那样唯恐避之不及,表现出对酒的极大宽容。同时,他也对自己的理性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尽管他本人不饮酒,这种态度不仅难得,也更接地气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几位重要的哲学家大体都能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思想饮酒。比如牟宗三很喜欢喝酒,尽管他酒量不好。冯契晚年主要喝黄酒。李泽厚喜欢喝酒,他曾自述:“朱先生(朱光潜)还告诉我,他每天必喝白酒一小盅,多年如此。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朱先生便用酒招待我,我们边喝边聊。有一两次我带了点好酒到朱先生那里去聊天,我告诉他,以后当妻子再干涉我喝酒时,我将以高龄的他作为挡箭牌,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
五、酒运转机与酒思的缺席
如我们所知,酒不仅能让人醉,让人沉沦,還能提神,让人振奋,走向反叛与升腾。革命者与酒精神一拍即合,酒便具有了革命精神。章太炎因《訄书》受迫害而避难日本,与孙中山相会定交于横滨中和堂。其时“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据说,章太炎共饮70余杯而不觉其醉。兴中会革命者相聚,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国家而会饮。当然,纵酒痛骂袁世凯更为人熟知。饮酒既为激发革命之斗志,也为超越现实之理想。20世纪不少思想家也都注意到酒的这一面向。比如陈天华:“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功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虽然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了。”(陈天华《警世钟》)黑暗日久,网罗积重,非大力不能冲决。激发深掩的人性,振奋人心,又需要借助酒之豪情。饮酒具有振奋精神,凝聚人心作用。李大钊也注意到这一点:“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罫,全其优美高尚之天。……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参见李大钊的《青春》,载于《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饮酒而振奋,寻求自由、突破、超越,这与追求数学化、程式化、清晰化的科学精神不同,但无疑亦为时代所需。当然,通过饮酒而振发精神,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更像是“起兴”,并且是自发地“起兴”。对于“酒”精神,他们既没有主题化思考,也没有深入思考之时机。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建设新社会、发展生产力以改善民生成为时代主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被当作“硬道理”,消费则被当作生产的必要环节而得到鼓励。欲望被激发起来,欲望逻辑随之而起。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被正常化的欲望混杂在一起,并裹挟着科学、资本,不断推动生产的发展,包括酒的生产。“科学”被“发展”谋划,主导着对酒生产的说明与规范。比如,从化学、生物学角度说明其原料(高粱、小麦、大麦、玉米等)、储存条件(避光、恒温等)等,同时也有“过量饮酒,有害健康”等善意的提醒。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引诱饮酒成为常态为了引诱饮酒,走向市场的酒业都会大量投资广告宣传。如“力波啤酒,喜欢上海的理由”等。这些广告对酒的品质、历史的宣传,以及将饮酒与地位、身份、健康、品味或隐或显地关联起来。这尽管与宋代朝廷出面引诱民众饮酒形式上有差异,政府支持、企业出资做广告在实质上还是引诱民众饮酒。在对美好生活的筹划中,饮酒成为人之常情与日用之需,并逐渐在精神生活展开中产生影响。在此形势下,人们不再着意酒的伦理定性,对酒的敌意也大大缓解。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中国思想家拒斥饮酒多以理性、道德、文明、科学为据,有其高度的理论自觉性。而饮酒的思想家对其饮大多基于根深蒂固的习俗、生活习惯,对酒都缺乏反思,可谓饮而不知。随着酒不断深入到民众生活,对此生活基本物的理论反思已经无法回避,也日渐迫切。饮酒何以在历史上屡禁而不止?酒对生命、生活何以必要?被科学祛魅的酒如何返魅?回答或肯定或否定,或深刻或浅薄,但是,“思的缺席”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陈琪.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M].北京: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1917:169-181.
[4]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145-146.
[5]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53-54.
[6]胡适.胡适文集:第7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39.
[7]丁文江.丁文江文集:第七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8]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4.
[9]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3.
[13]贡华南.北宋生活世界与饮酒精神的多重变奏[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32.
[14]贡华南.良知与品味二重奏下的大明酒精神[J].美食研究,2021(1):1.
[1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胡适.胡适文集: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7-88.
[17]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1.
[18]金岳霖.金岳霖全集:第四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9]金岳霖.金岳霖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8.
[20]冯友兰.贞元六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1]李泽厚.悼朱光潜先生[J].语文教学與研究,2017(3):20.
[22]徐寿裳.章太炎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 娅、杨 波)
Wine in Chinese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GONG Huan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62)
Abstract: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has become a new way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wine. Drinking, harming health and wasting money, then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obstacle to cultivating virtue, the non-drinking custom thus develops. In the eyes of scientism followers, drinking makes people dizzy, obstructs reason, affects hygiene,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banned. Although many thinkers drink alcohol, they have always associated drinking with malaise, depression, cowardice, insensitivity, self-contempt, self-indulgence, etc., showing their full hostility to wine. Science has monopolized the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wine, and wine has become a liquid without culture and spirit. However, the revolutionaries spontaneously used drinking to boost their spirits and seek freedom, breakthrough,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ti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has gradually overwhelmed the scientific deprecation of wine. Drinking has become a human routine and a daily need, though the reflection on wine theory has been missing.
Key words:wine; non-drinking; Chinese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