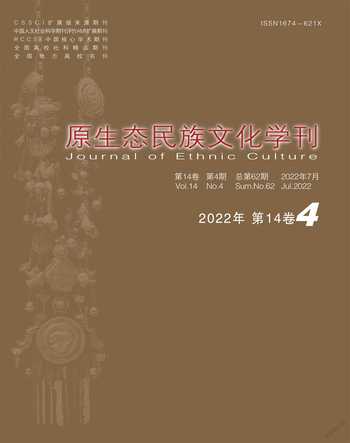民俗医疗与本土医药传承研究
聂选华
摘 要:民俗医疗作为傈僳族聚居地区历久弥新的一种疾病认知方式和治疗实践模式,涵盖了中医医学特有的病因观和诊疗方法,并体现出傈僳族疾病认知的复杂性和治疗实践的特殊性。通过对傈僳族疾病认知观念、本土医药传承和疾病治疗实践的实证分析发现,傈僳族民间形成的具有民俗性质的诊疗方法,对傈僳族的求医行为方式产生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影响,并在不断的调适过程中建构起具有实用性质的地方性医药知识、疾病诊治技艺等医疗体系。从实践层面来看,傈僳族民俗医疗与本土医药传承在宗教信仰、民俗习惯和治疗实践之间描绘出一幅相互交错的文化图景。深入探究傈僳族的疾病认知观念、治疗实践模式及其社会文化意蕴,厘清傈僳族医药文化从形成发展到继承创新的脉络,有助于为研究傈僳族疾病、医药、治疗与文化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并对传承和弘扬傈僳族本土医药文化和疾病治疗方式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关键词:傈僳族;疾病认知;治疗实践;本土医药;民俗医疗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4 - 0140 - 13
发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在继承中创新,是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使命及任务之一。民俗医疗及其文化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原始性和传统性,多存在于少数民族及乡村地区[1],其文化差异导致各民族对各类疾病的病因形成不尽相同的解释路径。随着医疗体系的当代转型,传统医疗1(亦称“民俗医疗”)逐渐受到学界的推重,诸如民族地区民俗医疗的诊疗方法[2]、医疗民俗与疼痛叙事[1]、民间信仰与疾病治疗[3]、疾病的文化隐喻[4]等相关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傈僳族的传统医药文化和疾病治疗方式丰富多样,独具民族特色的民俗治疗方法即“神药(医)并行”的模式长期在民间流传,并成为民俗医疗的瑰宝之一。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傈僳族特色医药诊疗方法[5 - 8]、宗教信仰对传统医药的影响[9]、祭祀和“叫魂”仪式祛除疾病的内涵和社会功能[10],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构建了傈僳族民俗医疗历史和经验的多重面相,为探究傈僳族民俗医疗与本土医药传承提供了理论视窗和方法借鉴。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傈僳族对疾病的认知观念、医药文化传承和疾病治疗实践的深层次内涵,借此诠释傈僳族多元民俗医疗体系在疾病治疗实践中的社会功用,以期裨益于当下少数民族医药及疾病治疗实践经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民俗医疗视域中的傈僳族疾病认知观念
民俗医疗及其成就是各民族长期与自然环境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遗产,民俗医疗中的传统智慧及经验总结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民俗医疗在民族医疗尤其是各民族疾病心理疗愈及疾痛诊治成效方面发挥着一定程度的效用,其作用力和时效对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医疗体系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一)傈僳族的病因观
傈僳族是云南境内的世居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余部分散居在昆明市、丽江市、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11],另外,四川省德昌县亦有傈僳族散居分布。“从傈僳族的源流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时期贯穿着‘同源—异流—同流’和‘同源—异流—异流’的分化发展规律,并成为彝语支各民族源流发展的重要特点”[12]。傈僳族与自身所处的生态和社会环境相互依存,并在本民族特有的宇宙观和生命观的影响下,形成对疾病认知观念、治疗方法和医疗实践的差异化阐释。自古至今,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及鬼神崇拜是傈僳族民间宗教膜拜形式的统一体[13],并在傈僳族的疾病认知和治疗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
任何医疗体系都拥有自身文化特质和内涵的用以解释病因、症状发作或复发、医疗方式的一套理论网络,并且具有生理性和心理性疗效的双重功用[14]。在傈僳族的疾病认知观念中,“尼”被视为所有自然现象的精灵,疾病和灾害与“尼”息息相关。傈僳族认为生产和生活活动都能得到“尼”的庇佑,“尼”如影隨形、力量无穷,唯有杀牲祭祀方能使民众消灾解难[15]15。疾病的发生不仅受限于社会生产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实施办法以及资源分配模式的差异化,而且受到以上因素所造成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态的制约[16]。调查发现,在傈僳族的认知世界中,疾病的产生和生离死别由鬼神作怪造成,傈僳族治愈个体的疾病需要巫师根据病情研判来祭祀各路鬼神。傈僳族民间治疗疾病的巫师有“尼扒”和“尼古扒”,他们是人与各路鬼神的沟通者。“尼扒”在傈僳族村寨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部分本村寨头人即是“尼扒”,其职责是在村寨中开展驱鬼、占卦和诵经等活动;相较“尼扒”而言,“尼古扒”的社会地位偏低,仅在民间替人卜卦或杀牲驱鬼辟邪[9]45。傈僳族相信人和宇宙自然万物一样,任何个体自身都拥有灵魂,主宰自然现象的精灵是“尼”(有“恒刮尼”(家鬼)、“白加尼”(天鬼)、“结林鬼”(路鬼)以及“山鬼”等多种),无论是山川、日月和星辰,还是江湖、河流和树木,皆是傈僳族崇拜的对象[15]15。傈僳族在开垦荒地、起房盖屋以及狩猎之前,都会请村寨巫师占卜,通过卦象预测吉凶,亦通过举行各种祭祀神灵的宗教仪活动,祈祷免灾祛祸和逃避疾病侵袭。傈僳族将疾病与生活禁忌相互关联,1他们认为任何不遵守规范或触犯鬼神的人,都将招致各种病痛。
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巫和医难以明确区隔,尤其是在部落社会中,疾病被视为是魔鬼和妖婆之属的反社会因素,它从社会外部渗透到社会个体的肌体和灵魂深处并造成混乱。因此,部落社会通常采用跳大神的方式来疗愈疾病,敲锣打鼓围绕病人狂呼和起舞是治疗病痛的主要方式。在治病期间,整个村寨的人都和患者相聚,希冀从病人身心中消除致病因素。任何历史阶段的生老与病死都是人生礼仪的重要构成,亘古通今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与社会文明过程中的道德秩序重塑有重要联系。傈僳族认为,鬼魂与神灵影响着个体生命的健康,疾病的暴发流行因人们惹怒和得罪神灵所致,杀牲祭祀方能与神灵重修旧好。傈僳族是“以植物、动物作为姓氏的民族”,受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傈僳族将长期形成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作为重要精神寄托[17],祭祀鬼神的仪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村寨民众对生老病死的心理恐惧,杀牲祭鬼和祷告神灵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原始宗教是一种较早存在于傈僳族社会中的传统宗教,它对“尼”充满敬畏,在社会秩序即将被打乱或终究被扰乱时,“尼扒”就会被请来开展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寻求社会的井然有序。在傈僳族驱除鬼神和疾病的法事或祭祀仪式中,“尼扒”通常施以“搭桥”、咒语、占卜和“通神”等阈限活动[18]。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白岩村傈僳族的宗教信仰体系为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和灵魂观念是村民信仰的主要内容,当遭遇灾害和疾病时,主要采用宰杀牲畜加以祭祀[19]。傈僳族认为,各种各样的鬼神和灵魂主宰着世间万事万物,同时也降临祸福于人间,但他们信仰的鬼神都是描述性的,没有抽象性的鬼神。每逢人生病没有医药,则认为是鬼神缠住了人的灵魂,需要宰杀牲畜祭祀鬼神。傈僳族民间的求医行为方式和疾病治疗方法的沿袭和流传,其文化内涵在傈僳族传统文化认同理论的解释框架下得到系统阐释。
(二)傈僳族的疾病消解
傈僳族医药没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在19世纪末期,伴随中西医的流传,傈僳族民间医药得到较大发展。20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云南怒江大峡谷地区,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地位受到挑战,基督教通过与傈僳族传统文化进行互动整合,形成独特的傈僳族基督教信仰,宰杀牲畜祭鬼和卜卦求医的行为方式,被服药和祷告的“神药两解”治病方法所取代[20],故而传教士治病救人的方式方法在傈僳族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尤其是在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传教士在怒江傈僳族聚居地区掀起教改运动,旨在革除傈僳族民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生活陋习和部分风俗习惯。乌撒(基督教称上帝)是傈僳族原始宗教中的创造灵感,而在傈僳族民众加入当地基督教教会后,他们可以在祭祀鬼神和信奉上帝之间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8]71。在祛除疾痛的仪式和过程中,傈僳族以贡献祭祀物品的方式获得“尼”、鬼、神、精灵的宽宥和惠赐,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惠利与共关系主要基于交换的公平原则得以实现。受原始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影响,傈僳族民间形成巫医合一、神药并用的医药认知体系,并具有以“万物有灵、爱与救赎”为核心的双重价值特征,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傈僳族医药文化中得到突显。傈僳族医药历史极其悠久,人们在与各类疾病作斗争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医药知识,使独具本土化和民族特色的疾病用药方法与经验得到民众的推崇。
在信奉基督教的傈僳族教徒身患疾病时,请教会组织教民为每一位患者进行祷告,主要方式为大家共同唱赞美诗、患者叙述病情以及执事带来教民为其祈祷[21]。巫师采用巫术与民间医药的配合方式对患者进行诊治,而教会则采取祷告与西药配合方式进行治病。无论是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巫术,还是基督教的祷告,皆以宗教信仰或神灵信奉为依托,其目的是凭借心理安抚及示意,为患者找寻精神上的慰藉和依赖,旨在减少或消除疾病患者的肌体疾痛,甚至是对生离死别的顾忌。就鬼神致使的疾病而言,傈僳族采用“尼扒”“尼古扒”等巫师举行驱鬼、迎神等仪式进行治疗。对于流行性传染疾病,傈僳族采用开具民间土方和服用中草药汤等传统治疗方式治病,若感冒则服用“大锅药”,跌打损伤就使用当地野生草药附片包扎。在应对严重流行性感冒时,傈僳族选择赴西医医院进行救治。傈僳族的疾病观、万物有灵观与民间信仰始终伴随他们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历程,并对傈僳族的疾病认知观念和求医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地方性医疗知识:傈僳族疾病治疗过程中的本土医药传承
傈僳族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卫生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优势,承载着新时代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价值及思维方式。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傈僳族医药存活于民间乡土社会之中,并在傈僳族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得到传扬,为促进傈僳族本土医药的利用和保护提供了路径依赖。
(一)傈僳族本土医药的应用及传承
傈僳族治病救人所用的医药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述,有关诊治病人用药的经验事实和记载只能凭借言传身教的方式得到保护和传承,其方式主要有祖传、师传、自学和民间流传四种方式[6]64。傈僳族“草根治病”“树叶止血”的传说最早见于唐朝,迄至明朝后期,傈僳族民间出现药材经济交易的活动。伴随社会的发展,傈僳族认识到植物和矿物对身体的重要作用,促使傈僳族的用药实践经验得到积累,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的长期存在,使傈僳族医药传承呈现出巫医合一、药神并用的特色。在傈僳族祭天活动中所唱述的《祭天古歌》祭词里,有训导人们使用药材疗愈疾病的“乃词托俄”(即《药书》)[22]。傈僳族治病救人所用药料通常源于就地取材,其药方以单方为主,配方则较少,内服和外用是两种用药方式[6]40 - 58。胃病是丽江傈僳族聚居地区较常见的地方慢性疾病,傈僳族草医治疗胃病的草药有“洗胃药”和“养胃药”两类,洗胃药旨在让患者将体内的有毒物质和细菌排出,养胃药则重在使患者的胃部黏膜组织得到修復和再生,以使疾患得以根治。
傈僳族本土医药的应用主要基于民间患者的疾病治疗和草医医生诊治疾痛的创造性建构,为民族文化传播和公众身体健康提供了丰富的传统医药知识。云南境内的傈僳族多居住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谷、山区和半山区地带,他们长期步行于峭壁沟壑,由外伤引起的骨折疾病在傈僳族村寨最为多见,因此傈僳族草医擅长治疗骨折疾患,但是不同地域的傈僳族草医对骨折的治疗方法略有不同,用药方式亦存在差异。傈僳族草医采取手法复位和夹板外固定,以及中药材外敷、熬煮中药和酒泡中药内服等内外兼治的方法治疗骨折损伤,怒江峡谷的山歌草(又名接骨草)亦可治疗跌打损伤和舒筋接骨。傈僳族草医的行医技能通过家族祖传和接受短期中草药知识培训获得,并在走村串寨治疗实践中积蓄了丰富的骨折医治技艺和疗理用药经验[23]。骨折诊疗技术是傈僳族在长期的治疗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优秀医疗文化,是傈僳族宝贵的医疗卫生资源,尽管受现代医疗技艺和医护药品的冲击,但由于傈僳族民间骨折治疗成本较低,诊治技术简单易行,草医就地取材治病的方式为公众普遍接受,从而为傈僳族民间的骨折诊疗技术传承提供了条件。
据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记载,贝壳可治疗眼疾,蜂蜡能治愈上肢疼痛,酥油治理下肢疾痛,石藤可治头痛,草根可疗治腰疼,野果治疗心脏病[24]。在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境内,傈僳族草医用药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则,并根据不同病人的病情配制药方,1通常以多味和单味制成内服药,抑或配制成方剂煎汤服用,再或将药材研磨为粉,并用温白开水或白酒送服。傈僳族草医使用外用药较为讲究,用药方法为用开水煎熬中药,针对不同的疾患可用中药汤清洗或浸泡,亦可采用中药熏蒸疗治或药包热敷[25]。此外,傈僳族草医治疗疾病通常用白酒泡制各种中药材,并在藥酒医治各种病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例如,白酒浸泡虫草口服能实现化痰止血、保肺益肾的功效;口服蛇酒有助于疗治惊风癫痫、肢体麻木、气虚血亏、风湿关节炎等病症;白酒泡制草乌擦拭肌体外表,可以治愈疼痛。怒江州的傈僳族草医常用中草药、土方治病,并以口头流传的方式保存了常用的药方。1
傈僳族保存下来的传统医药主要是能够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以及五官科等相关疾病。傈僳族草医通常采用视、触、叩、嗅、听等方式,对患者进行疾病诊断,并根据不同的病情,就地取材,采用煎服中草药、用中草药汤洗涤,以及箭穿、旋转、刮痧、口吸、割治、火灸、拔火罐、放血和药浴等方法根治疾病或减缓患者病痛[8]72。傈僳族医药的主要特征是以新鲜药物为主,单方多于配方。傈僳族聚居地区丰富的药用资源影响着民间医药的发展进程,采集中药草作为傈僳族的主要副业之一,为民间草医积累丰富的药用知识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和传承予以关注,怒江州对民族传统医药药方进行发掘、收集和整理,政府通过开展讲座和集中培训的方式,对傈僳族中草药人员和草医医生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组织医药技术人员对草药、中药、验方和民间单方进行整理和开发[8]71。
(二)傈僳族本土医药的发展空间
傈僳族本土医药知识体系与民间乡土医生用药经验积累和疾病治疗实践相关联,其作为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傈僳族民间医药传承和治病救人的良方,极具保护和开发价值。傈僳族本土医药文化的世代流传和草医医生的用药实践,促进了傈僳族民间医疗从业者和疾病患者之间角色的互动,傈僳族以“把脉”“开药方”为象征符号的民俗医疗得以仪式化传播,丰富了傈僳族疾病治疗实践的内涵。此外,傈僳族本土医药的传承为疾病治疗提供了宝贵药方,并在傈僳族医疗文化的传承中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征,其传统性、民间性、地域性、活态性和生活性根植于傈僳族对疾病防治的实际需要和治疗实践经验的概括。“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的本体论视角,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聚集物与实践、富含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生成性过程”[26],傈僳族本土医药文化的创造源生于民众、发展在民间,疾病治疗用药的“可获取性”和“可承受性”体现着它的生命力。
本土医药是傈僳族民族民间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傈僳族民间医生长期的医疗实践和用药传承是具有独特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是傈僳族本土医药的原始性、神秘性和实用性的表达。作为具有民族特色医药理论、诊疗技术和养生保健积累总和的本土医药[27],傈僳族医药在预防和治疗常见地方性疾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傈僳族民间本土医药知识和用药经验通常以民俗形式流传并得以保存,其内涵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主要蕴藏在傈僳族的民俗事务之中。伴随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具有深厚民间基础与传统文化积淀的傈僳族本土医药面临着现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由于傈僳族本土医药经验和知识缺乏文字记载,传承方式以口承传授为主[28],因而未能建立起科学化的学科体系,在现代建构过程中被置于制度化的边缘,目前仍处于非正式制度1的行列。
当前,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医疗资源和医改政策的惠益逐步削弱了傈僳族本土医药的“廉价”优势,尤其是现代化性质的县、乡、村三级疾病治疗和卫生防疫保健模式的建立,限制了傈僳族草医医生选择集市摆药摊和行医治病的传统疾病治疗方式的再度延续。民族民间医药是一门新兴学科,合理地应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创造和发展成果是其得以创新发展的动力。傈僳族本土医药的现代化发展,需要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并综合利用植物化学、植物学、药理学、生药学、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充分发掘其传统知识和用药实践的丰富内涵,以进一步指导医药的保护传承与现代应用。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疾病谱的改变,傈僳族本土医药传承路径的创新以及研究成果的突破,因地制宜加强对相关医药文献的整理,由专业技术人员建成合作研究团队,协同创新、集中攻关,有助于推进傈僳族本土医药的系统研究和创新发展。
三、“神药并用”与傈僳族疾病治疗实践的路径阐释
傈僳族本土医药知识纵向传承和疾病治疗实践横向借鉴的基本模式和内在机制,揭示了傈僳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认知,而傈僳族民间的疾病治疗实践,则推动着本土医药的传承创新和科学发展。推动傈僳族本土医药和疾病治疗方式的传承,是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发展好、传承好少数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傈僳族传统疾病疗法
民俗医疗是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民族应对各类常见疾病的本土知识和传统方法,是民族民间公众所使用的自然与超然、经验认知与不成文的、本土地理环境孕育和滋长出来的疾病医疗观念与辨症施治行为[29]。具体而言,民俗医疗是本乡本土的产物,是本地人知悉和惯于运用的疾病诊治知识及技艺,“是当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习而不察地融合在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的,是每个人基本的一套医疗知识,是一有疾病便首先采用的反应”[30]。傈僳族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氐羌民族中,属于传统宗教观念保留比较完整的族群[31],因而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对民间医药发展及疾病治疗实践产生着重要影响。傈僳族聚居地区以走村串寨形式存在的、具有专业技术水准的行医者出现长期断层,民间懂得诊治疾病方法的医生属于“神药两用”的兼职务农人员[8]71,一般情况下,傈僳族聚居的每个村寨有1 - 2名或3 - 4名不等的掌握民族医药知识的民间医生,他们有丰富的疾病治疗经验,但由于文化知识水平有限,部分医生甚至不懂汉语,行医都不做病例诊断和用药记录,因此疾病治疗方法传承仅以言传口授方式[32]。疾病的诊断方式和疗治行为模式具有较强社会属性,疾病治疗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病患个体客观存在的既定困局最先在情感方面变得能够被想象和建构,“使肉体难以忍受的痛苦变得可以被思想所接受”[33]。傈僳族民间医生的行医技能一般通过2种途径获得,一种是家族式传承,即不断总结先人的经验,行医治病,草药多为自采自用;一种是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民间医生进行系统的中医药理论培训和学习,在疾病治疗和用药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医技和治疗方法[34]。
傈僳族认为春天沐浴能够增强免疫力并消除肌体病痛,食用漆树油脂能够获得疏通血脉和驱寒祛湿的效用。居住在怒江大峡谷地带的傈僳族长期以来都保持有“春浴”的风俗习惯,凡是怒江流域有温泉流淌之处,皆是傈僳族的齐聚沐浴之地。在“春浴”期间,傈僳族都会携带行李和年食,并选择距离温泉较近的地方搭建竹棚,抑或寻找岩洞以供停驻和歇息。通常而言,傈僳族会在温泉周边歇宿3 - 5天,每天洗浴多达5 - 6次,他们认为反复的洗澡可驱除各种疾病和增强肌体的免疫能力,开展新年的生产劳动才会有旺盛的精力[35]。傈僳族将病患归结为是超自然和非人類的干预活动而致的医疗观念,是民族医学体系中拟人论的医学观。这种拟人论的医学观与现代生物医学观有着根本不同,虽然其为治疗举行的仪式,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安慰,但在治疗时间方面仍然逊于生物医学[36]。
民俗医疗并非是民间医药和医疗的单向互动,其作为社会文化各要素交互关系的组成部分,与地方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任何人在遭遇身体肌理或心理障碍问题时,都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文化对疾病或疼痛进行不同的解释,并试图采用各种较为理想的治疗方法加以防范和应对,这种有关医疗的文化逻辑在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因为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某种单纯的治疗方式,“大多数社会都具有医疗多样性或者多种治疗方案的选择”[37]。就疾病治疗而言,治疗者所施用的诊疗方式方法是基于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族群和不同社会文化在处理健康与疾病、生老与死离等关系的文化表达[38]。疾病的产生与生命体在特定条件下同自身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因而傈僳族的疾病史料不仅是一种文化形式和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生理过程和社会文化过程[39],但傈僳族的疾病医疗并非是纯粹的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因为傈僳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不同的疾病认识观念,人们对病因理论和治疗行为的认知亦有较大差异。
(二)傈僳族疾病治疗的实践
傈僳族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形成独具特质的鬼神观和治病救人的传统医治文化。傈僳族将常见的地方病归结于“尼”系统,疾病治疗方式需通过仪式专家唱诵经文和举行献祭仪式驱赶病魔。在怒江州兰坪县傈僳族聚居地区,傈僳族相信人有灵魂,人的灵魂一旦跑掉,人就会生病,通常采取“叫魂”的方式进行治病。如果患者久病不愈,傈僳族认为是魂魄在野外游荡所致,需要请“尼扒”举行招魂仪式,目的是祈求家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及生产顺利。傈僳族的叫魂仪式具有疾病认知差异和治疗实践的文化内涵,并贯穿于本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群体的生活中,且因仪轨形式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10]58。个体的病痛作为一种文化建构,体现的是一种心理感应,即社会经验事实,这种建构本身涵盖了复杂多向的社会和心理过程,这一过程又对疾病的发生及其治疗产生影响。傈僳族的叫魂仪式作为一种仪式治疗的手段和民族文化建构,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傈僳族在宗教信仰体系和乡土语境中有关卫生健康、疾病和治疗的认知和行为选择。
傈僳族的医疗实践活动主要内化于本土的社会关系之中,依靠本民族的祖传医师来治愈疾病是疗治者与疾病患者共同形成的文化解释模式,因为民俗医疗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搭建了相对较为融洽的医患关系,治疗者的病因解释也能够被患者所接受。傈僳族居住的每个村寨都有祖传医师,尤其是在以前交通闭塞和医疗条件状况落后的情况下,傈僳族祖传医师会配制中草药药方,能够根据患者的病症情况予以诊治。例如,针对打摆子、发寒症和感冒等常见疾病,傈僳族祖传医师都有土方可治。傈僳族俗语“猴子不用碗,傈僳族人不建庙”,表明的是傈僳族历来没有建庙的习惯,但是碰上家里人生病而长期无法痊愈,傈僳族还是会进庙祈福。关于疾病与鬼的关系,傈僳族根据病情确定患病的时间与鬼相关,如果治疗两周后还未痊愈,则认为祭山神、信鬼信神、驱鬼方能治愈疾病。尼扒是傈僳族自古就有的从事祭祀活动的执行者,而找尼扒的情况只有一种,即家里的人四处求医而不得治时才寻求他做法事,其余情况都是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
医学本身是社会个体肌理病变和疾病缠绕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社会群体,抑或是政府部门,都难以回避与个体健康相关的社会问题。梁其姿认为:“在最高的层次,社群与政府处理疾病的策略与方式,均能反映社会或国家治理的主流理念。在中间的层次,专业医生、艰涩的医典其实并没有垄断对身体、疫疾的想象与解释。处在医疗关系最底层的病人、或其家属其实都各有一套身体观、疾病观、疗疾习惯、死亡观等;宗教人员也可能另有一套。”[40]傈僳族的疾病认知和求医行为模式,主要基于地方性疾病知识经验、疾病观和身体观的差异化和整体化得到系统表达和建构,傈僳族的疾病认知和疾病医疗实践,系统地阐释了傈僳族疾病观、宗教信仰与疾病治疗的交互关系及其社会影响。“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阈里,对不同社会文化里的传统医学的关注既延续了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取向,也为传统医学在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发展挖掘了更多的可能性”[41],因而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傈僳族医疗文化与疾病治疗、患者疾病认知观念和行为选择模式的深层次内涵,有助于揭示傈僳族聚居地区医疗模式的多元性。
(三)傈僳族疾病治疗的现代转向
傈僳族的疾病治疗与其民俗活动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傈僳族民族医药、疾病治疗和民间习俗相互重叠、相互交错,进而使诸多民间的医药经验和知识通过民俗的方式得以保存和传承。灾害文化作为少数民族与自然灾害相伴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提升优化转型的困境[42]。傈僳族的疾病治疗方式具有传统性、地域性和口承性,傈僳族民俗医疗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与傈僳族聚居地方的文化传统、自然环境、饮食习惯以及医疗系统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傈僳族将疾病发生与治疗修复的各个环节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与傈僳族信奉原始自然宗教和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念密切相关。
毋庸置疑,傈僳族疾病治疗方式的现代化转向,是民俗医疗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外在于自身的危机和挑战做出的自然选择与调适。傈僳族疾病治疗的现代转向在于现代化对地方性的医疗实践路径和思维方式的质疑,而现代化对傈僳族疾病治疗的影响,则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化对社区格局和家庭结构的重塑和再次建构。从现实层面来看,生物医学的诊疗方式使傈僳族的求医路径、就医行为和治疗体验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因为现代化的医疗实践模式不仅降低了傈僳族对本土医药的接触概率,同时也使人们加深了对生物医学1的了解,傈僳族传统的疾病认知观念无疑受到来自“病原菌”“致病菌”等学说的冲击。“医学绝不只是一门单纯的在病房和实验室谈论的学问,而更基本的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大众民俗生活中实现人的第一需要(健康生存)的生存技术”[43]。伴随中国医疗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卫生健康服务能力的显著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医疗传承面临极大的挑战,傈僳族的疾病认知与治疗实践应当得到改变,并在现代化转向中适应现代医学研究范式、医学教育体制以及标准化的医学实践和管理方式革新的需要。
当前,傈僳族民间的疾病治疗方式呈现传统医疗(傈僳族民间草医和中医)、民间医疗(即独具傈僳族文化特色的大众医疗知识、地方性的疾病治疗仪式)和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疗并存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尽管三者存在一定的互补共存关系,但现代性的疾病治疗方式仍然具有独占鳌头的态势。尤其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部分傈僳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他们的求医、就医行为逐渐发生异化,傈僳族民间先前寻医问药于乡野的极具民族文化气息的治疗体验,往往被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西医医院及西医医生所取代,因为“城市化给少数民族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同时,也改变着少数民族的就医行为;由于接触民族医药的机会大幅减少,民族医药的受益群体也就大量流失” [44]。不可否认的是,面对现代医学的挑战和融合,傈僳族聚居地区的传统医疗和民间医疗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诸如村卫生室在傈僳族村寨的建立,以及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机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和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医疗与现代医疗的结合。
健康是社会公众最具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需要,而疾病医疗则是民生突出的后顾之忧。“大健康”具有全局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健康问题并非是单一的疾病治疗和公共卫生问题,已经上升为影响国家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全局性问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的战略任务,从疾病治疗到促进健康,充分體现了现代化性质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与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强傈僳族医药健康文化宣传,推广普及傈僳族养生保健知识、技术和方法,大力培育从事傈僳族医药研究和疾病治疗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民族医药学科带头人,提升傈僳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水平,有助于发挥傈僳族本土医药在傈僳族民间卫生健康服务中的功用。
四、结语
疾病犹如生命本身一样古老,而生命有机体从健康转向疾病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傈僳族疾病认识观念的形成和现代化转变,不仅与傈僳族朴素的病因观、多元医疗模式和求医行为价值观相联系,还与傈僳族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致病因素、疫疾认知、宗教信仰、疾病治疗方式等密切相关。傈僳族聚居地区流行的疾病主要有鬼神致使的特殊疾病以及现代医学意义上的流行性传染疾病两类,面对不同的疾病及其致病因子,傈僳族民间有着不同的针对病症的应对方式和行为选择。与此同时,傈僳族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与各类疾病相抗争,并在生产实践和生活体验中积累了丰富的病痛对症治疗经验,进而塑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俗医疗文化。然而,科学研究证明,灵魂世界和鬼神世界并非是真实存在,傈僳族关于疾病的认知观念以及疾病治疗过程中笃信鬼神、凡事占卜的行为方式是违背科学的,因此在传承和弘扬傈僳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当秉承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彻底摒弃傈僳族民俗医疗中的鬼神因素,辨证、批判地继承傈僳族民俗医疗和本土医药中的合理成分,使其与建设“健康中国”实现双向调适。
傈僳族民俗医疗与本土医药的传承弘扬,需要从社会发展需要的事实出发,制定科学的传承规划和创新发展思路,使民俗医疗和本土医药在傈僳族所处的生态环境、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到合理的位置。与此同时,傈僳族民俗医疗和本土医药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传承需遵循创新和发展规律,使之与现代化相结合。在“健康中国”战略的驱动下,傈僳族的疾病治疗实践和本土医药传承将伴随社会空间结构的异化、生计方式的改变、宗教信仰的变化、民族多向交流以及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而实现改变。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傈僳族疾病治疗面临现代化的转向,但传统医疗、民间医疗和现代医疗三者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包容的关系,因而需要从医学人类学的文化“主位”“客位”来认识和理解傈僳族医疗模式多元共存的合理性。
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医疗健康”布局的加速调整,云医疗、云健康、云保险和云医药的医疗卫生创新服务网络平台逐渐形成,逐渐淡化了傈僳族传统医疗方式和疾病治疗模式固有的魅力,有效提高傈僳族本土医药防病治地方性疾病的能力,有助于推进傈僳族本土医药的传承及其产业的创新性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傈僳族本土医药的精髓,推进傈僳族本土医药的信息化建设,健全傈僳族医药健康服务网络,完善傈僳族医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傈僳族本土医药用药标准化体系建设,促进傈僳族本土医药与国际医药知识体系相结合,提高傈僳族医药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服务能力,是推进傈僳族本土医药实现科学化发展、传统民俗医疗方式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戴望云.民俗医疗、医疗民俗与疾痛叙事研究述评——兼论建构医疗民俗学理论范式的可能性[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27 - 133.
[2] 冯智明.身体认知与疾病:红瑶民俗医疗观念及其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14(6):94 - 99.
[3] 龙开义.壮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医疗[J].青海民族研究,2007(2):110 - 114.
[4] 高登荣,黄昕莹.芒市傣族的疾痛认知、传统疗法与文化隐喻[J].广西民族研究,2020(3):71 - 78.
[5] 周元川,郑进.怒江流域民族医药[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0.
[6] 杨玉琪,贺铮铮.傈僳族医药简介[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
[7] 朱儒林.丽江傈僳族民间草医草药[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7.
[8] 杨麒,周月倾,王洪云.滇西傈僳族医药文化内涵研究[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9,25(9):70 - 72.
[9] 左媛媛,陈普,郑进.云南怒江傈僳族宗教信仰对其传统医药的影响[J].医学与哲学,2013(1).
[10]朱凌飞,和芳.治疗仪式与文化表演——对白岩傈僳族“叫魂”的人类学阐释[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2):58 - 64.
[11]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傈僳族文化大观[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1.
[12]段丽波.多元视角下的傈僳族源流考释[J].思想战线,2020(6):120.
[13]余德芬.傈僳族传统信仰与禁忌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9.
[14]汪丹.分担与参与:白马藏族民俗医疗实践的文化逻辑[J].民族研究,2013(6):70.
[15]沈坚.基督教与云南怒江傈僳族社会[J].历史教学问题,2006(1).
[16]莫瑞·辛格,林敏霞.批判医学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框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8.
[17]徐黎珺.傈僳族本土化的防灾减灾:民间传统知识的运用——以福贡县架科村的泥石流灾害为例[J].文化学刊,2015(5):52.
[18]张晗.社会共生视阈下的多元文化空间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68.
[19]张晗.抉择与共生:云南边民基督教信仰的“地方性”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2.
[20]陈艳萍.彼岸玄思 天堂地狱——傈僳族宗教信仰中的死亡观[J].思想战线,2009(6):128.
[21]程寒,黄先菊.云南怒江地区傈僳族民族医药特色与现状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3(10):2512.
[22]欧光明.中国傈僳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213.
[23]杨玉琪,瞿广城,贺铮铮,方路,金锦,马克坚.浅谈傈僳族民间骨折诊疗技术的传承与保护[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3(5):70.
[24]蔡武成.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41.
[25]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撰委员会.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785 - 786.
[26]赖立里.成为少数民族医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视角[J].思想战线,2020(2):9.
[27]俞永琼,倪凯,梁志庆,金锦,郭世民,和丽生.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的相互影响[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20(10):66.
[28]曾玉麟.滇人天衍:云南民族医药[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8.
[29]曹宜.略论民俗研究对民族医药发展的影响[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7):2.
[30]张珣.疾病与文化[M].台北:台湾稻乡出版社,1989:86 - 87.
[31]张泽洪.中国西南的傈僳族及其宗教信仰[J].宗教学研究,2006(3):118 - 125.
[32]马克坚,杨玉琪,杨剑,戴水平,张静.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调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6.
[3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34]金锦,郭世民. 云南省5个特有民族医药的保护和调查研究初探[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6(12):100.
[35]《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25.
[36]卢成仁,徐慧娟.文化背景与医疗行为: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1):52.
[37]范长风.安多藏区曼巴扎仓的医学民族志[J].民俗研究,2019(1):141.
[38]张振伟.身体与信仰:西双版纳傣族仪式治疗中的二元宗教互动[J].思想战线,2013(2):57.
[39]罗伯特·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M].禾木,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342.
[40]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
[41]李婉妍.醫学人类学视阈下国内民族医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4):63.
[42]周琼.换个角度看文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刍论[J].云南社会科学,2021(1):118.
[43]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44]景军.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34.
[责任编辑:吴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