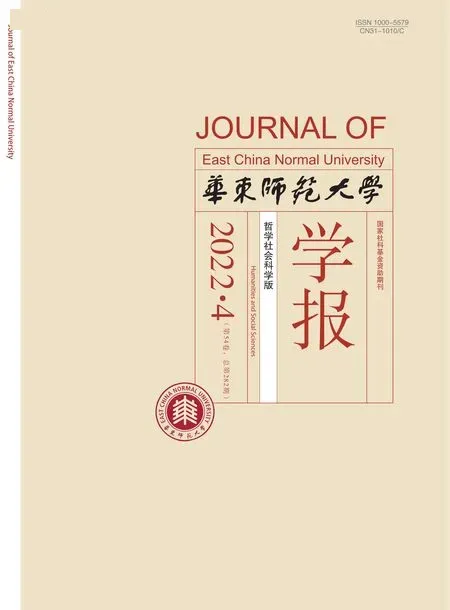城市社区高龄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及分类保障研究
王建云 钟仁耀
一 问 题 的 提 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到2020年11月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6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8.7%。①资料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第五号)》,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1日。《“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曾预计,到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②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7年3月6日。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 估计,我国仅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41.90%,仅老年人独自居住的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约10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独居。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老年人的独居比例更高,更值得关注。有研究发现,在城市社区,独居老年人比例约为50%,大城市中处于空巢或独居状态的老年人达70%以上,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37%(Wong & Leung,2012)。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迁,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破损家庭或不完整家庭(丧偶、未婚、离婚等)增多,独居老年人群体不断扩大。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流动的分居,以及老年人与多个子女契约的轮养在可预见的将来加大了独居老年人群体的规模和复杂化。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老年人价值观转变,为追求自由和独立而选择独居安排,进一步增加了独居老年群体的复杂化。根据以往学者的界定,独居老年人是指没有居住在同一住所的共同生活者的老年人,判定标准是1套房子内晚上睡觉者仅1位老人(桂世勋,2019;戴建兵等,2017)。目前,独居老年人既包括无子女无配偶(未婚、丧偶、离婚)老年人、无子女有配偶(失独、未育)老年人,也包括有子女无配偶(丧偶、离婚)老年人和有子女有配偶(分居)老年人。在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子女和配偶是老年人主要照料资源、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的供给者(王磊,2019),甚至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不同家庭类型代表不同的照料资源、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及社会关系网络,对独居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生命健康质量涉及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状况等,既包括主观感受,也包括客观评价(桂世勋,2001;邬沧萍,2002)。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独居老年人是弱势群体,面临生活无人照顾、经济困难、无法就医和住房条件差等困境,生存质量不高。一是独居老年人属于躯体健康高风险群体,躯体健康较差。与非独居老年人相比,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更差,更有可能报告健康状况不佳、视力低下、日常生活活动困难(Kharicha,et al., 2007;秦俭,2013;杨海晖,2017),有较多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生活照料需求和专业护理机构的护理和服务需求(张震,2004;王磊,2019;Osamu,et al.,2018;Lage,et al.,2018)。而且,独居老年人医疗可获得性更差,由于没有子女的监督和提醒,缺乏健康管理,易漏服、错服药,不能定期复诊,治疗依从性较差。此外,独居老年人遇到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常常因无人求助而延误就医,更易引起并发症,甚至出现生命危险(Bilotta,et al., 2010)。二是独居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处于断裂或半断裂状态,精神更加脆弱(Harada,et al.,2018;周建芳,2015;李月英,2017)。三是独居老年人受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等健康因素以及一些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影响较少参加社会交往,社会适应差(钟仁耀,2004;张文娟、王东京,2018)。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独居老年人不是弱势群体,其生命健康质量与非独居老年人无差异。一是独居是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或居住安排,独居并不意味着身体健康质量差。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表明无配偶无子女的女性独居老年人与其他家庭类型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Cwikel,et al., 2006)。二是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孤立以及精神质量差。有研究发现无配偶无子女的独居老年人的孤独感最低,反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非独居老年人因各种矛盾表现为精神健康质量最差(Umberson, et al.,2010)。三是独居并不意味着社会参与减少。发达国家的老年人为享受自由主动选择独居,他们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和积极的社会参与,定期开展健康检查,享受休闲娱乐等,而且女性独居老年人有较好的社会参与并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Wenger,et al.,2007)。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独居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状况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已有文献多是在研究居住安排时,与非独居老年人对比分析整个独居老年人群体的生命健康质量,忽视了独居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本文认为,独居老年人内部存在复杂性和异质性,不同家庭类型的独居老年人的照料资源、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及社会关系网络存在差异,相应地,其生命健康质量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从家庭类型的角度细分独居老年人群体,探讨其生命健康质量的异质性,以期提高政府对独居老年人的精准关爱和分类保障,为后续不同家庭类型老年人养老保障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二 研究假设与因子分析
(一)研究假设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3年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费孝通,2001),认为我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关系为主轴的“水波纹”状社会关系网络,并由此反映社会关系的亲疏。此后,一些学者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血亲价值论和家庭系统理论,即家庭中子代与父代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家庭有抚育子代的功能,子代有照料和支持父代的责任(姚远,2001;王莉莉,2012)。在我国“少年夫妻老来伴”和“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影响下,子女和配偶是老年人的主要社会支持和重要养老资源的来源,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分家改变了老年人居住方式,家庭支持减少导致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下降,死亡风险提高(王磊,2019)。已有研究表明,独居老年人的家庭支持资源越少,其生命健康质量越差,幸福感和满意度越低。有子女照顾的非独居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生命健康质量高于无子女的独居老年人(王武林,2009;王磊,2019);有配偶的高龄老年人身体更好,死亡风险更低(顾大男,2003)。可见,子女和配偶对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至关重要,尤其对家庭类型复杂的独居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家庭类型不同,独居老年人的照料资源、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及社会关系网络存在差异,其生命健康质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根据以上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可知,家庭成员完整并且拥有更多家庭养老资源的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更好。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有配偶有子女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好,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差。
H2:有配偶有子女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好,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差。
H3:有配偶有子女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最好,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最差。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的调研数据。该课题组于2013—2015年采用四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成都市、呼和浩特市、大连市、广州市和上海市等5个城市展开“中国大城市城区 70 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其调查对象为:(1)70岁及以上中高龄独居老年人(下文简称“独居老年人”);(2)6个月以上独居生活的老年人(夜间仅1人居住);(3)可以正常理解和回答问卷有关问题。本次调研从5个城市的20个行政区(每市随机抽取4个)中抽取了36个街道(每区抽2个,上海抽1个)、72个社区(每街道抽2个),在每个社区根据门牌号从前到后抽取 50 名(上海为100名)、共3 363名符合条件者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问卷包括“短表”和“长表”,对于经由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SPMSQ量表)测量后认知能力得分6分及以上(总分是10分)的老年人,请他们回答“长表”。本文使用 “长表”数据,样本量2 801个,其中成都429个、呼和浩特587个、大连593个、广州472个和上海720个。剔除主要缺失变量后得到有效样本数据2 752个(见表1),其中: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75人,约占2.8%;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2 273人,约占81.4%;无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7人,约占0.14%;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397人,约占15.6%。本次调查使用四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独居老年人群体展开调研,样本中不同家庭类型独居老年人的占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某一地区独居老年人家庭类型占比的真实情况。由于无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无生育、失独)数量较少(仅7人,约占0.14%),难以单独作为一类分析,因此,将此类数据删除,最终使用样本2 745个。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值为0.702>0.7,内部一致性较高。对主要题目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774>0.7,显著水平为0.000,问卷的效度较好。

表1 独居老年人分类矩阵(n=2 752)
(三)变量选择
1.躯体健康质量的测量。参照胡静(2015)的研究,从躯体完好、功能正常两方面选取健康自评、患疾病及慢性病种数、自理能力衡量独居老人躯体健康质量。其中,自评健康用“您觉得目前健康状况如何”衡量,采用李克特量表打分,5=“很好”,3=“一般”,1=“不好”。患病情况用“你有哪些确诊的疾病及慢性病”衡量,答案有11类,据此重新分为5=“未患病”,4=“1种疾病”,3=“2种疾病”,2=“3种疾病”,1=“3种以上疾病”。自理能力用“您目前自理能力如何”衡量,5=“能自理”,3=“部分自理”,1=“完全不能自理”。
2.精神健康质量的测量。本文用“是否担心未达到子女的期望(抑郁感)”、“是否经常感到孤独(孤独感)”和“是否时常感到忧虑(忧虑感)”等评估精神健康质量,由独居老人根据自身情况打分,5=“从未感到”,3=“有时感到”,1=“经常感到”。
3.社会适应质量的测量。社会适应质量从兴趣爱好、参加活动频率、社会联系及社会支持等方面评估(钟森等,2016)。本文选择生活满意度、社区邻里关系和社会活动参与率作为社会适应质量指标,前两者分别由“您对目前生活状况是否满意”、“你觉得与邻里关系好吗”测量,5=“很好”,3=“一般”,1=“不好”;后者由“近三个月是否参加过社区居民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或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各类老年学校和户外或室内健身点”的项目数衡量,5=“参加过5项”,3=“参加过3项”,1=“参加过0项或1项”。
4.家庭类型的测量。问卷中对配偶和子女情况分别设计题目,其中:对于配偶,1=有配偶,0=无配偶(丧偶/未婚/离婚);对于子女,其数量为连续变量,取值范围0—9。本文根据配偶和子女情况划分家庭类型,1=无子女无配偶,2=有子女无配偶,3=有子女有配偶。
5.控制变量的选择。控制变量由基本人口学特征变量和相关社会保障变量组成,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连续变量)、性别(1=男,0=女)、受教育程度①1982年我国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下降到22.81%,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和义务教育(资料来源:《教育公平之路》,《南方周末》 2019年9月26日)。因此,本文选用义务教育的结点“高中”作为学历分界点。(1=高中及以上,0=初中及以下)、收入②本文采用对应城市最低工资作为参照系,区分独居老年人的经济收入高低。2015年,上海市最低工资2 300元,广州市最低工资1 895元,成都市最低工资1 500元,大连市最低工资1 530元,呼和浩特市最低工资1 640元。(1=高于当地最低工资,0=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变量包括医疗保险(1=有医疗保险,0=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1=有养老保险,0=无养老保险)。
(四)生命健康质量的因子分析
生命健康质量的测量指标较多,为防止共线性,更深入地分析不同家庭类型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需要用因子分析法对生命健康质量测量指标降维。此外,因子分析方法不受量纲的影响,因子旋转后,可得到新的因子载荷矩阵,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一维度指标的信息,有利于对公因子进行合理解释。检验本文样本数据各题项的偏度、峰度及带正态分布概率密度曲线的直方图,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KMO值为0.774>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为1 080.117,P值为0.000;本文样本量(2 745人)是变量的10倍以上。以上表明,本文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因此,笔者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用少数公因子代替原始变量衡量独居老人生命健康质量。
假设有i个样本,j个指标,X=(X1,X2,X3,…Xi)T为随机向量,寻找公因子F=(F1,F2,F3,…Fj)T,则模型:

矩阵A=(aij)为因子矩阵,aij为因子载荷,表示第i个变量在第j个因子上的载荷,也就是第i个变量在第j个公因子Fj的重要性;ε为特殊因子,指公因子以外的影响因素。
在因子载荷矩阵A中,各列元素aij的平方和记为,有:

当某一题在相应共同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或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共同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时,该测量指标应该被删除(吴明隆,2010:492)。据此,本文删除了PSMS值、IADL值、迷茫感和活动后心情等指标。对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生命健康质量因子可以提取躯体健康质量、精神健康质量和社会适应质量3个潜变量因子。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5次后收敛,生命健康质量可以按照特征值大于1提取3个因子,3个因子的解释力度分别为20.052%、18.371%和15.211%。
如表2所示,第一公因子F1载荷因子与孤独感(0.716)、抑郁感(0.747)和忧虑感(0.526)等3项度量指标相关,将F1命名为精神健康质量因子,解释力度约为20.05%。第二公因子F2载荷因子与自理能力(0.533)、健康自评(0.755)和疾病种数(0.842)等3项度量指标相关,将F2命名为躯体健康质量因子,解释力度约为18.37%。第三公因子F3载荷因子与社区邻里关系(0.751)、生活满意度(0.598)和社会活动参与(0.626)等3项指标相关,将F3命名为社会适应质量因子,解释力度约为15.21%。

表2 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的因子载荷
三 实 证 分 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不同类型独居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如表3所示,总样本中男性独居老年人占32%,女性独居老年人占68%,男性与女性之比约为1∶2;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中男性占51%,远远高于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占28%)和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占24%)。独居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8.47岁,其中年龄最小为70岁,最大为107岁;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6.23岁,低于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78.84岁)和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78.38岁)。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独居老年人占25%;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占42%)高于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占17%)和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占22%)。独居老年人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比例较小,仅为40%,其中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这一比例(占44%)高于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占32%)和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占39%)。八成以上独居老年人拥有医疗保险和有养老保险,且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占89%)、医疗保险(占92%)等社会保险的比例高于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人(分别占88%、90%)和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分别占89%、87%)。有配偶的独居老年人占16%,无配偶的独居老年人占84%;无子女无配偶老年人中未婚的约占6.7%、离婚的约占6.7%、丧偶的约占86.6%;有子女无配偶老年人中未婚的约占3.9%、离婚的约占5.2%、丧偶的约占90.9%。

表3 描述性统计
2.不同类型独居老年人独居原因分析。如表4所示,对有子女老年人独居原因分析后发现,仅有15.6%的独居老年人为追求自由而选择独居生活;约47.9%的独居老年人能自理,因其子女年纪大、身体不好、经济状况不佳等原因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而选择独居;17.8%的独居老年人因子女家住房条件有限(面积小、上下楼不方便)而独居;9.9%的独居老年人因与子女关系不好而选择独居;4.8%的独居老年人因子女在外地工作而独居。其中,有子女无配偶老年人独居原因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能自理、不想影响子女(占48.2%)、子女家住房条件有限(占18.2%)和喜欢单独居住(占17.2%);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独居原因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能自理、不想影响子女(占43.6%)、与子女关系不好(占26.9%)和子女家住房条件有限(占15.7%)。值得注意的是,约占四分之一的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人因与子女的关系不好而选择独居。

表4 有子女独居老年人独居原因分析
(二)不同类型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比较分析
如表5所示,三类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从躯体健康质量来看,三类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具有显著差异(F=2.560,P<0.05),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好(M=0.124),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差(M=-0.169)。从精神健康质量来看,三类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具有显著差异(F=1.675,P<0.05),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好(M=0.158),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差(M=-0.102)。从社会适应质量来看,三类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具有显著差异(F=5.014,P<0.01),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最差(M=-0.603),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最好(M=0.041)。

表5 三类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方差分析
(三)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别以精神健康质量因子、躯体健康质量因子和社会适应质量因子为因变量,探寻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的影响因素(详见表6)。研究发现,子女数量与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呈负相关,子女数量越多,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越差,这可能与多子女父母操劳程度较高导致身体健康质量下降有关。医疗保险与躯体健康质量呈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可能的解释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自愿参保,易产生道德风险,躯体健康质量好的独居老年人参保意愿低,而躯体健康质量差的独居老年人参保积极性较高,从而呈现有医疗保险的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更低的现象。男性独居老年人的躯体健康质量高于女性。年龄与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呈负相关,年龄越大的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越差。受教育程度与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呈负相关,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独居老年人的躯体健康质量较差,这可能与其多参加脑力劳动而忽视身体锻炼有关。收入水平与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呈正相关,收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的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较好。此外,对精神健康质量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男性和收入水平与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与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呈显著负相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低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独居老人,这可能与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独居老年人对精神文化需求更高有关。对社会适应质量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和收入水平与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呈显著正相关;男性与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与女性独居老年人相比,城市中男性独居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表6 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四 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对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研究发现:一是独居老年人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根据家庭类型的子女和配偶两个维度可将独居老年人划分为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无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和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这种分类比较科学合理,由此提出未来的政策将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操作性。二是不同家庭类型的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精神健康质量和社会适应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好,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差,假设H1不成立;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好,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差,假设H2不成立;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最差,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最好,假设H3不成立。三是子女数量、医疗保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对独居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子女数量、医疗保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影响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子女数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影响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子女数量、性别和收入影响独居老年人社会适应质量。
本文根据差序格局理论提出的三个假设,在实证中均未得到证实,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1.对躯体健康质量假设即H1不成立的原因分析。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最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市社区中无子女无配偶老年人属于孤寡老年人,往往被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对象及社区重点关注人群,老年人经济困难或者躯体健康质量变差(患病较严重或不能自理)时,可享受社会救助而入住养老机构,其医疗卫生资源、社区服务资源以及养老院、护理院等养老资源的可及性较高;另一方面,本文回归分析发现,子女数量越多,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越差,因此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身体健康质量较好也可能是由于其没有抚养子女的操劳、经济状况更好、更注重个人身体保养等等。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质量之所以最差,可能是因为他们中男性占比较大(占51%),独居前由配偶洗衣、做饭、做家务、照顾饮食起居,独居后倾向于“凑合”过日子,饮食不规律、营养跟不上、吸烟酗酒等导致患慢性病比例增多,躯体健康质量下降。
2.对精神健康质量假设即H2不成立的原因分析。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精神健康质量最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老年人既享受子女和配偶的精神慰藉、感情交流,又享受舒适的私人空间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本文回归分析发现,男性的精神健康质量更好,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中男性占比较大(占51%),他们很少紧张、敏感,往往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其孤独感、抑郁感和忧虑感较低,故精神健康质量较好。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质量最差,一方面是由于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中女性占比较大(占72%),而女性独居老年人心理脆弱,更易感到孤独、产生情绪问题;另一方面,调研对象中有子女无配偶的独居老年人以丧偶老年人为主(约占90.9%),丧偶带来孤独感、抑郁感、忧虑感等,进而导致他们精神健康质量最差。
3.对社会适应质量假设即H3不成立的原因分析。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质量最好,一方面是由于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因丧偶或离异等生活面临困难,子女会有意识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鼓励独居老年人融入社区生活,并把老年人托给社区邻里帮忙照顾,无形地增加了独居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另一方面,本文回归分析发现,女性独居老年人相对于男性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质量,而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中女性占比较大(约占72%),她们有较强的交流愿望并希望融入社区和邻里,对生活满意度较高。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因缺少子女和配偶照顾,其非正式养老支持系统就处于断裂状态,社会关系网络较简单、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较少;其社会参与意识较低,不愿走出家门,不愿参加社区活动或服务,故其社会适应质量最差。
根据上述分析,由于独居老年人群体的异质性,不同家庭类型独居老年人生命健康质量存在差异。因此,有关部门应探索构建独居老年人精准关爱和分类保障的社会支持体系,通过精准识别独居老年人的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生命健康质量以及养老服务需求,提供更加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以提升独居老年人的生命健康质量。
第一,建立社区独居老年人信息库,分类提供社区精准关爱服务。社区应对独居老年人的家庭类型及独居原因摸底排查,建立完备的独居老年人信息库,以便分门别类地为本社区独居老年人提供精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例如,根据独居老年人的家庭完整程度和家庭资源的多少,将独居老年人分为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无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和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对不同家庭类型的独居老年人分类提供精神慰藉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社会适应及互助养老服务。
第二,关注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躯体健康。首先,应出台家庭养老支持政策,调解子女与独居老年人的家庭矛盾,帮助独居老年人的子女承担养老责任。例如,实行多代同住购房优惠政策,如果子女购买住房接回原独居父母同住,在购房税费上给予一定的扣除。此外,增加有独居父母的异地工作子女的带薪休假时间,保障子女带薪探亲假的落实和监督,对不执行的单位实行严格的问责或处罚,对将探亲假挪作他用的子女给予一定的教育或处罚,从而保证子女真正尽到赡养独居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其次,邻居经常敲门探望躯体健康质量较低的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预防和减少他们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和突发身体疾病。最后,鼓励子女借助科技力量掌握独居老年人的生活及躯体健康质量,以防止突发疾病和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减少“孤独死”事件。例如,社区牵头为有子女有配偶独居老年人安装紧急呼叫设备、红外线探测仪、身体各项指标检测仪等,方便子女随时跟踪独居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第三,关注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首先,为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丧偶、离异等对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是沉重的精神打击,致使他们情感支撑缺失,情绪会长期陷入低落,从而产生孤独感、抑郁感和忧虑感。因此,应该为丧偶、离异的独居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精神慰藉服务。其次,倡导社区邻里与有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结对子”,帮助和鼓励他们走出丧偶或离异之痛。最后,社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要定期组织对他们开展社区心理辅导,如心理预防、心理慰藉等,帮助和引导这类独居老年人走出精神困境,鼓励其参与文体娱乐活动,积极融入社区生活,进而保障其精神健康质量。
第四,关注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社会适应。目前,社区和社会已广泛关注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和社会保障,但相对缺少对他们的社会适应及社会融入的研究和帮助。很多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因长期无人沟通和交流而性格孤僻,不知道如何与他人沟通和相处,社会适应能力差,进而影响其生命健康质量。为解决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社会适应问题,首先,要引导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处理好邻里关系。可通过“老伙伴计划”等互助小组引导无子女无配偶老年人与邻里沟通交流和相互帮助,增进他们与邻里的融洽关系,完善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要鼓励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积极提升社会参与。应鼓励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最后,要通过各种方式,做好帮扶服务,满足无子女无配偶独居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启蒙终结”的观念*
- 高度关注低龄老人适度“参与”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
- 养老服务补贴制度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