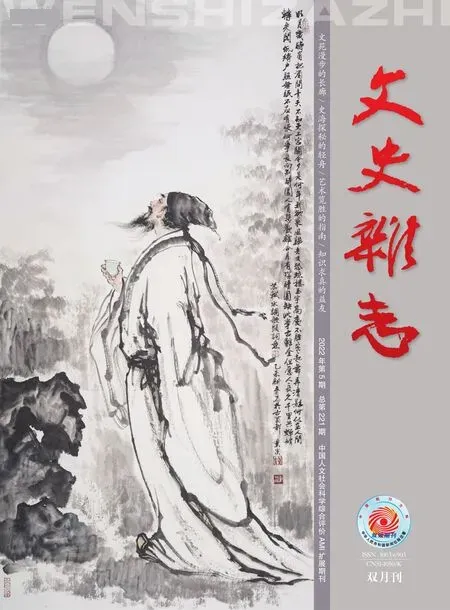论著传世,风范长存
——王文才先生书集绪(上)
李天道
2022年6月22日是王文才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四川文艺出版社拟将文才先生生前精心撰写的五本著作结集出版。年初,王珏师兄将文才先生的这几部著述的书稿交给我,嘱我写“绪”。余欣然应允,并谨以此“绪”表达对文才先生的深切怀念。
研究生学习期间,文才先生为我们开设古代文学史。其风范儒雅,一口崇州话娓娓道来,让我难以忘怀。聆听先生教诲之后,既收获知识,又感动心灵。毫不夸张地说,听文才先生讲课,是一种极高的精神享受,也是我求学生涯中最宝贵的记忆之一。而这几部著述中就有文才先生当年讲课的讲义,从中不难看出先生当年授课的音容笑貌,是胸有锦绣,笔生美文。先生讲授作家作品,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生动逼真。其学术成就、学术思想以及治学方法,均极有见地。饮水思源,师恩难忘。如今细读其遗著,感到尽皆考核精详,论述深湛,自成一家,是内涵丰富的学术遗产。
摆在面前的这几本遗著近两百万字,出版社按其体例,分为两部,第一部收入《先秦文学讲义》《汉魏六朝文学讲义》(简称《讲义》)与《近代诗史》三书,集中呈现了文才先生在古诗文研究、校辑、考订方面的成果;第二部为《〈西使记〉笺》《〈益州记〉笺》(简称《〈记〉笺》),是文才先生为《西使记》与《益州记》作的笺,即对两《记》的注释与对古人注笺中不好理解地方的解释。它们在笺注文本,注疏诗文,疏通文意,阐明经典方面,亦显出文才先生的功底。其文献资料征引翔实,且往往以今古文的融合来进行描述,辨析诗文的确切含义;又以此为基础,窥探中国古代文学变迁的真实轨迹。
一、文本笺注,经典阐释
这里评述的两本《讲义》与一部《近代诗史》,凝聚着文才先生的半世心血。作为川内著名学者,文才先生在中国古代诗文史研究、杨升庵研究、巴蜀文化研究和成都地域文化考证等方面均名扬四海,留下了大量极富价值的学术著述,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文才先生的五书结集里,浸润着他严谨的学术风范和治学精神,其在治学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也有许多经验值得后来学者汲取。这部五书结集中有关先秦、汉魏六朝、近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品文献中有关的语词,在古代很多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往往需要作为现当代学者的文才先生根据语境来判断其所指。文才先生以深厚的学识与确切的感悟,加以诠释与笺注,析解精审,见解独到。即以《讲义》为例,说是“讲义”,实际上已是学术专著。因为所谓“讲义”,在中国古代乃是指讲解经义之书。如《南史·梁纪中·武帝下》云:“初,帝创同泰寺,至是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这里的“讲义”,即阐释讲析书籍义理,又指事先撰写好的讲解书籍义理的书籍。现今,一般将书斋中的研究与课堂上的讲析之著述称之为“讲义”。然而刘师培所撰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名义上虽乃课堂讲析的教案,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学术著作。现代大部分学者多在大学或科研院所工作,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在某种意义上经过课堂的宣讲、演练和修改,委实闪耀着课堂上即兴发挥的思考的光辉。王文才先生的《讲义》,就是这种著述。它们实质上乃课堂讲述与学术研究合二为一之独特的学术著作。
这里的两本《讲义》与一部《诗史》,应该是文才先生对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史的主要问题所进行的宏观的审视与微观的解析,其特色是纵横开合,深而入微,容量巨大,视野宽阔,见解精深。从宏观而言,文才先生从总体上深度概述了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歌的艺术风格、构成特点以及其研究的难点和意义。这既是文才先生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甘苦之见,也是其学识和学养的精彩再现。从微观而言,文才先生以《诗经》《楚辞》、汉乐府歌、汉魏诗赋散文,以及近代诗人与诗作,先秦汉魏六朝作者如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曹操、曹植、陶渊明、嵇康、阮籍,近代诗人如黄宗羲、蒲松龄等为研究个体为例,展开微观详尽的研究。这种具体精深研究的个案演示,既印证了文才先生的思路和观点,也展示了文才先生突出的操作能力。

1945年成都正声诗词社同仁合影
就《先秦文学讲义》看,共分“诗经”“楚辞”“古代神话和周秦散文”三讲,点面结合,实质上是断代史。内容安排上与通行的文学史不同。通行本大都分为五部分,即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文才先生的《讲义》则分三部分。同时,应该说,相对于秦汉以后的文学史,先秦文学历史发展进程的展现不够清晰,缺乏具体的、不同时段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叙述。基于此,文才先生这本《讲义》,在整体的基本架构中,以中国传统的体例,即神话歌谣散文、《诗经》《楚辞》为主要形式,编排、讲析了先秦文学的著作篇目、写作背景及艺术风格等等,建构了以《诗经》《楚辞》“古代神话和周秦散文”为主体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先秦文学体系,对先秦文学包括佚诗和散文进行了深入讲析,并例举汉代以来的有关研究加以剖析、探究、评讲,研讨先秦文学作品的时代、艺术特点等问题,使读者对先秦时期的文学有了一个清楚的线索与体认,为先秦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供给了相对全面和立体的认识,有助于读者从时间的“纵轴”与空间的“横轴”上了解、把握先秦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及整体风貌。《讲义》对先秦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均有独到讲述。作为中国文学的起始,先秦文学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胚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发展进程。在创作方式上,《诗经》和《楚辞》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史传和诸子则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同时,先秦文学创造了多种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词汇丰富,表达方式灵活,给后世的文学以借鉴和启迪,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先秦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不是那么清晰,相对而言,具体的、不同时段文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记载比较缺乏。而文才先生则鉴古以知今,通过重点讲述,以使其《讲义》既能够使读者明白先秦文学的“然”,更能够懂得其“所以然”。文才先生的《讲义》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学与文化训练。先生通过系统讲解、精选篇目,不但阐释先秦诗文之诗性内容,还从人文的高度,深入剖析、解读先秦文学之名家名篇,解读其中的艺术特色、文化内涵、历史和社会背景,使读者对于以屈原为代表的先秦作家作品,通过今古辨析,更能明达,对先秦文学以及其生成的社会人生、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因此,应该说,文才先生的《讲义》,是在充分了解先秦文学与其所出文化土壤的基础上,精研细析而成的。先生通过《讲义》来提升读者对先秦文学的认知能力,使之能从更高的文化与艺术视域去看待先秦文学。可以说,文才先生的《讲义》,汇聚了一种人文情怀。如对《诗经》的讲析,文才先生就指出,“所谓‘变雅’,往往是对昏庸贪婪的统治阶级的诅咒。这种诅咒,大概是站在‘国人’——市民阶级的立场说话”。这样彰显“市民”,即一般民众志向的内容,是真诚坦率的,充盈着一种人文思想,别具一格。《讲义》中,从《诗经》《楚辞》到“古代神话和周秦散文”,不同文体、不同观点俱有,在鼓励批判性思维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个人身份和人格形成的严肃选择。重个性,轻地位与利禄,且能潇洒自如,这就是文才先生选文析诗的要旨所在。
文才先生一生勤勉不懈,努力耕耘,将很大一部分心血用于古诗文的研究、笺注、讲析方面。他的《先秦文学讲义》,由于所研讨对象年代久远,文献大多散佚,只能依靠辑存来获取必要的资料。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文才先生采摭编纂,考订谬误,对文学文献资料作了进一步辑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解读。而这本《讲义》则记录了文才先生在校辑整理与研究解读历程中辛勤跋涉的足迹。
二、讲析精细,解读入微
文才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讲义》也分三讲,即汉魏六朝乐府歌辞、汉魏六朝的文人诗歌、汉魏六朝的辞赋散文和文论,重点对其时诗文发展进行研究讲析;还对五言、七言诗的产生年代,做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探究。
应该说,《汉魏六朝文学讲义》乃文才先生用心对其时文学所做的评析。尽管文才先生《讲义》的内容,仅能体现其研究的一部分,但他的研究功绩是显而易见的。《讲义》收入了先生对乐府歌辞,对两汉乐府章法、乐谱所进行探究的精到论述,对其时文人作品和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的诠释、评论,展现了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形成的观点;对一些问题,如“陶渊明的开始农耕和接近农民”“仕于桓玄、刘裕”“归隐与躬耕自资”等问题均进行了详尽论述,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到现在,虽然时隔多年,但读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对读者很有启示。
文才先生在探究和讲评作家作品等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讲义》对《乐府》有精细的探究。如在讲授“汉魏六朝的文论”一节强调指出,“《史记》为屈原、司马相如作专传”,表明对文学作家的重视。“刘向校书,也把‘诗赋’独立为一类,但专业文人,却从东汉才逐渐加多,《文苑传》是从《后汉书》才开始有的”。他又指出,“建安时期,曹氏父子重视文学,因此,对于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也以极严肃的态度从事研讨”。就此,文才先生提到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到“文气”说,以及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及其诗学理论等,并且都有精到的阐述,如指出陆机的《文赋》“深入讨论修辞技巧方面的问题”,“钟嵘的《诗品》,采取品第的态度,对汉魏以来五言诗,作了较正确的批评”。他还对刘勰的文学观、“风骨”论和《文心雕龙》以及“作家的品第、作品的得失、文章的体裁”诸方面,予以系统研究,进行了全面地讲述,且有独到的体会。由此可看出先生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之深。
关于“汉乐府诗”这一当时新的诗歌体裁,文才先生在《讲义》中指出,这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汉代乐府诗,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乐府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才先生指出,其时,“乐府”这一官府机构的设立,对“内地歌谣起了交流作用”,而“外族乐歌的输入,更增加了新的形式,所以民间的音乐和诗歌很快地有了新的发展”;强调汉代的“乐府诗”乃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出的一种诗歌新形式。应该说,文才先生对汉乐府的研究,其深刻精微的分析,以及所时时展现出的对“乐府诗”眷恋至深的拳拳赤子之心,尤具魅力。至今,读到其《讲义》,文才先生的风度境界、音容形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心底,其对汉魏六朝文学的解读揭示所蕴含的曲折深意也会生动展现、敞亮出来;而先生倾注其间的情感力量,也会在这种解读中透溢出来。文才先生对陶渊明《归田园居》的分析,即是这种解读的一个典型例子。先生从这首诗的用韵和景物描写入手,指出曹丕是用慢慢感染的方式,先烘托出一种感受的气氛,由平淡而入深沉,将读者的情感引入所抒写的怀想之中。其中对陶渊明“厌恶官府虚伪、热爱农村淳朴的心情”,特别举出鲁迅的评价。尽管陶渊明在政治上有些失意,但他的文学成绩是别人所不能否认的。他的田园诗和咏怀诗都对后世影响巨大,尤以田园诗为甚。他平淡自然的语言包含着不露斧凿之痕的艺术韵味,以白描和写意的手法描写了恬静优美的乡村风光,表现了淳朴的农村生活情趣。这种描写乡居生活,讴歌劳动和躬耕自给的诗在盛行玄言诗的两晋时期开辟出一块新天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思想内容空虚狭隘、肤浅乏味的局面。至于他的咏怀诗和叙写时事的诗,则与田园诗截然不同,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为金刚怒目,反映了陶渊明飘逸悠然,自然冲淡的风格以外的慷慨豪放。这也表明他在享受恬静田园生活的同时也难以释怀对庙堂之事的关心。如此等等解说,尤其是对陶诗中从自然景物到离别哀伤的往复过渡,由个体之悲到茫茫天地之悲的逐渐扩展,“无理之词”与“至情之笔”的相互映衬,先生体察得极为深婉细腻。其真挚动人的情感体验,在先生的妙解之下,也如深渊之鱼衔钩而出。
文才先生论汉魏六朝文学,有许多真知灼见,对人启发至深。比如,关于建安时期文学发展的评价问题,先生独具慧眼,指出建安时期诗歌发展与“曹操、曹丕、曹植都竭力提倡文学”,加上“许多文人也集中到曹氏那里,随声附和,彼此投赠”,这才成为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先生特别提到建安文学的“梗概多气”“忧生之叹”,认为曹植“写得更为沉痛”。在当时诗文创作上的超众之处,曹丕之诗不同于曹植纯任深情的写情一路,其作品是以感取胜。是论深有见地。先生指出,曹丕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认为这才是认识曹丕诗作的关键所在。建安曹氏兄弟在诗歌创作方面,恰见《庄》《骚》之别,其优劣至少应是难分轩轾。曹丕自幼“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后人谓曹丕之诗反映了传统诗歌创作从“汉音”到“魏响”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也说明曹丕之诗更能体现时代的新潮流。文才先生以学者与诗人的敏锐目光,不同众见,其识见与其背后的学术功力实在是不同凡响。又如在讲评散文时,先生特别指出,其时“纵横游说之士,贾谊、晁错诸人文章,都能够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反映出当时广大农民的苦痛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后来的董仲舒、刘向、匡衡等,都用他们的‘奏议’批评当时政治,作风和贾、晁相似”。
《史记》既是史学名著,也是文学经典。它的文学经典化过程从汉魏六朝时期起步,以后逐渐发展。文才先生指出,《史记》“注重描述历史上各个角落、各个层面的社会情况和人物动态”,既是历史纪实,同时“又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杰出作品”。他从《史记》诞生说起,结合其时政治文化背景,对《史记》的散文艺术特色进行了考察,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分析了其散文特点,认为“司马迁以高度的历史和文学修养,抉择了典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叙写,用了通俗活泼而又肆意的语言,把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这些人物的言行和性格,生动地再现出来,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形象性,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学理论,先生分析了《史记》的叙事文学特性,说明《史记》在文学领域已被认可接受,强调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认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文才先生指出,司马迁的不朽之作《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史记》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的确立起步于汉魏六朝时期。可以说,汉魏六朝时期关于《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认可和评价,对以后史传文学经典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其思想独特,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极高。汉魏六朝时期,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都对《史记》进行了评论,肯定其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就文学方面而言,刘勰《文心雕龙》在《史传》篇中就把《史记》列入文学范围进行评述。虽然刘勰的认识还不到位,但能将其纳入文学理论的范畴进行评论,却有其重要意义。先生高度肯定了司马迁的散文叙事才能,尤其是肯定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讲明《史记》的散文叙事成就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认为《史记》散文写人,充满“奇”的色彩;大量的奇人奇事,使《史记》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先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对《史记》文学的内涵、价值、魅力、情感等都有挖掘和阐释,指出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在文学理论方面具有新的发展和提升。司马迁《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之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实质上揭示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真正从理论上继承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志思蓄愤”说与钟嵘《诗品》提出的“怨愤说”。
在这本《讲义》中,文才先生通过对这一时期代表人物陶潜等人著作的解读,说明他们的文学思想,进一步解释其中所蕴含的文艺观念、作品所反映的创作思想,系统论述了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其特征,开拓出研究的新领域。该著虽以文学为论述对象,但涉及面较广,有助于人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深入了解。在论述乐府诗词时,先生既凸显其特点和代表作,也揭示了它们在不同时期的演变;纵横交错,点面结合,清晰地描述出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进行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需把握文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这不仅是文学研究,更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代,文学史的研究,除了阐明其审美价值外,其文化价值也值得重视。

陈沫吾书司马迁《报任安书》(节录)
文才先生的两本《讲义》对先秦、汉魏六朝文学深入解读,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力图呈现文学历史文本的要妙。可以说,《讲义》给人一场不同凡响、极为难得的审美体验,让人读来既获得知识又感到有趣而有价值。先生对古诗文的讲析,考镜源流,讲析详审,既含英咀华,融会贯通,准确精当,又深思明辨,生动传神,珠玉纷呈,将诗文讲析阐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现代诗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种由讲释入手进行研究的良好学风,对读者启发颇大。
三、超汉越宋,别树一宗
就《近代诗史》看,在系统梳理近代诗人别集和总集的基础上,文才先生立足于文本分析,从特色和成因探赜,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清诗总叙、道咸新声、咸同诗风、同光体诗、唐诗遗风五部分,从诗体、诗风入手,对龚自珍、魏源等四十三位诗人进行讲析探究,针对近代诗独特的诗体风范和艺术特色,做出分析。下编则分江湖诗人、湘湖诗人、蜀中诗人、岭南诗人、南社诗人五部分,以地域特色为主,对秋瑾、黄遵宪等三十九位诗人进行剖析和讲述。段落划分与文本选取,极有特色,人物选取颇具个性化特色。在先生看来,清代学术,超汉越宋,文、学并重。所谓“文、学并重”,即表明清诗的特色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统一,近代诗也是“文”与“学”的统一。这种特色,宣统元年编撰《国朝文汇》的黄人(摩西)曾概括为:“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道、咸之文激昂峭厉、纵横排奡,同、光之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道、咸之交,权舆于龚魏而扬厉于汤冯,其气跌宕,其辞嵚崎。延及同、光,或神圣方姚,或参谭羽嵚。近代诗,有周、秦之神智而不诡僻,有东西京之博雅而不穿凿,有魏晋六朝之新隽而不纤薄,有唐之闳肆而不繁缛,有两宋之纯正而不尘腐。文化积淀深厚,学术化倾向明显;风格多样,流派单一,且雅俗兼行;既有迂阔之论,也有对新事物、新观念的反映;注重经世致用,轻视审美情趣,因而显得理性有余,灵性不足。清自道、咸后,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欧风东渐,不断输入了比封建社会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自成体系的哲理、政教,尤其是新的美学方法论,这些必然深刻影响到文人的创作。文才先生从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对近代诗作一番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认为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超汉越宋”“别树一宗”的时代特色。先生指出,从形式看,近代诗的雅与俗非常明显,但基本上是由古雅而逐渐通俗化的。汪琬、龚自珍的诗,可算是“尽雅”了。而傅山、汪缙、郑燮、谭嗣同、梁启超,可谓“尽俗”了。但是,古奥高雅对大众没有实用价值。“文、学并重”只是近代诗的整体特色,如以风格论,则理学家、朴学家之诗偏于“学”,诗风质朴;文人之诗偏于“文”,其诗富于文采。把顾炎武、戴震和袁枚、郑燮的诗一对比,这种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从内容看,更能体现出近代诗的特色,从形似而神似,错综变化,风格独特,诗风雅洁。“雅”是正,包含内容与形式,庄重、严肃、大方、高尚。赵庚夫《题茶山集》云:“‘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二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三家句律相似,至放翁则加豪矣。”文才先生说,据魏氏所言,又知子苍诗法,流衍于江西,而剑南以久寓蜀中,又将江西曾氏之学,间接以授于蜀人,展转流布,灼然可寻。他如荆公山谷二家,并以赣人为诗坛盟主,篇章流布,遐迩承风。其为遗集作郑笺者,一为丹棱李壁,一为新津任渊。李任并皆蜀人,他省人之景仰江西者,无此勤劬也。流风未远,轨辙犹袢。今蜀中诗人之卓然自立者,并能本山川之灵秀,发秩世之清辞,所谓峻刻苍秀之境,正与文与可、韩子苍、唐子西诸人之所为者,手载后遥遥默契也。
文才先生认为蜀中近代诗家,刘光第、杨锐、宋育仁、顾印愚、李鸿裔、赵熙、王明征、林思进等,此派诗家,体在唐宋之间,格有绵远之韵,清而能腴,质而近缡。蜀中诗派,自有其渊派可寻,广雅、湘绮虽启迪之,蜀人未能尽弃其所学而学之也。近代诗派与地域文化相关。胸次高简,状蜀中山水,其所为诗载蜀山蜀江之青碧而出。诗人每与地域山水相发,甚肖蜀中山水者,苍秀密栗,清奇神异,淡不可收;神奇之极归于平淡,平淡之至转见神奇。雄穆浑厚,淡静温雅,清丽奇古,清风卓尔,华实敷腴,沉挚凄凉,秀逸朴厚,别具风格。闲消世虑,洞抉玄微,韵味旁流,惟深自秘惜,不轻示人,故流布不广。然语蜀中诗人,逼肖蜀山蜀水之青碧者,香宋而外,当推病山。晚岁侨寓申江,鬻医自隐,易名王潜,又自号潜道人云。此四家者,惟裴村比部稍能奇丽,余皆清苍幽峭,字不避习见,语必求惊人,临川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者,此类诗是也。综览蜀中近代诗人,咸多此体,语其著者,尚有华阳王雪岑。雪岑精目录校勘之学,收藏甚富,偶事吟咏,自然澹雅。绵竹杨叔峤《说经堂诗》,拟古为多,自写性情之作,正复清远。富顺宋芸子,识时之彦,明于中西治术,忧国之言,朝野传诵。其诗多感时抚事之作,蕴藉绵远,不失雅音。江安傅沅叔,精金石流略之学,兼好收藏,宋椠明钞,插架万卷,装池题记,罔不精绝;今之陈仲鱼、吴兔床也。校理之余,间事吟咏,综贯故实,尤多逸闻。学有余于诗,故典雅深醇,渊乎味永。若枵然无具徒为寻章摘句者读之,鲜不爽然自失矣。成都邓守瑕,久官都下,亲见危亡,草生凝碧,借泣香红,梦故国之觚棱,摩千年之铜狄,有凄婉之音,极回荡之致。盖其诗植体玉溪,而得力韩渥者也。富顺胡铁华,为香宋弟子,韵昧气格,绝类其师。华阳林山腴,与尧生倡和,清新俊逸,兼而有之;早年与尧生、漱唐、畏庐、石遗,同居宣南,诗酒之会,罔不参预,联吟接席,闻见遂多;返蜀以后徜徉园林,而诗曰益工。

王文才部分著作

王文才整理彭芸荪《望江楼志》
以纵向而言,文才先生按照时间线索分期分阶段清晰准确地梳理了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再现了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史的诗文审美风貌的发展历程。以横向而言,先生从多个方面深度考察了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文与政治、经济及思想的关系,借以厘清其文化背景。在这样大幅度地纵横开阖宏微交汇中,巨大的信息量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有机地融汇其中。比如,对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文三个构成特点的归纳,就是在与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近代文学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归纳出来的各种文体并存、作家人数众多、作品数量大,完全契合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文的实际。
这两本《讲义》与一部《诗史》,是文才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史与诗学风貌,对先秦、汉魏六朝、近代诗文研究所做出的切实精深的描述,又是对地域文化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具有开拓性价值,能够由此而辐射到整体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研究。从所论述的内容,可以全面深刻地了解文才先生为人、治学和著述成就,其意义极为深远。
文才先生在古诗文研究方面,每多真知灼见。其古代诗文之研究,所作阐释,皆精到深入。其近代诗之研究,先以传记尽其生平梗概,又从各方面探其诗艺,识见湛深,以诗史互证为主;于近代诸家诗之笺释,如龚自珍、王闿运、张之洞,皆元元本本;对这些诗家及其诗作之评点,又多抉阐文心,考察其艺术特色。可以发现,由于蜀学的影响,文才先生对古代文学与近代诗之研究既有朴学烙印,又涂满历史文化色彩;从文学到诗歌艺术的视域出发,使其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融通的气象。同时,其教授身份又对其研究具有独特作用,往往能洞见精髓。先生的体验式与感悟式研究,更能够贴近诗文原本真相,故而所取得的成就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