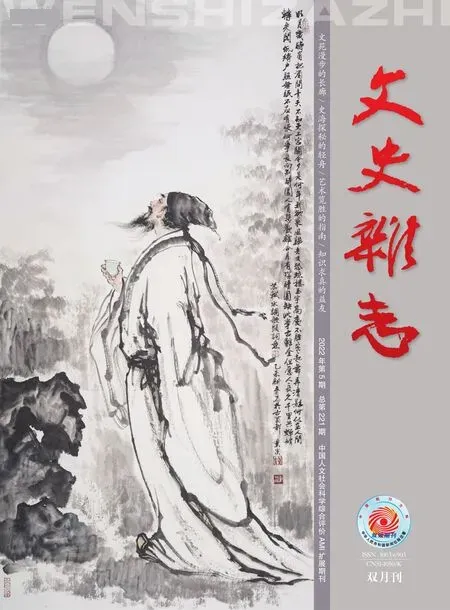古蜀神话的概念与范畴
周 明
近年来,随着川西茂县营盘山、成都金沙、广汉三星堆等考古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社会各界对古蜀文化予以了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古蜀神话的高度关注。那么,“什么是古蜀神话”就成为认识和研究古蜀神话的首要问题。

卫聚贤:《巴蜀文化》(选自《说文月刋》1941年第3卷第4期)书影
一、古蜀神话的概念
“古蜀神话”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特指在古蜀地域产生和流传的各类神话故事。它与“巴蜀神话”及“巴蜀文化”的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内涵和外延上,“古蜀神话”小于“巴蜀神话”,是“巴蜀神话”的一部分。同时,“古蜀神话”又和“巴蜀神话”一起,从属于“巴蜀文化”,是“巴蜀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941年,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上以《巴蜀文化》为题撰文,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文中,卫聚贤先生说道:
四川在秦以前有两个大国——巴、蜀。巴国的都城曾在重庆,蜀国的都城则在成都。巴国的古史则有《山海经》《华阳国志》的《巴志》所载,惟其国靠近楚秦,故《左传》上尚有段片的记载。蜀国的古史,则有《尚书》《蜀王本纪》(扬雄作,已亡,他书有引)、《本蜀论》(来敏作,《水经注》引),及《华阳国志》的《蜀志》。不过这些古史既不详细且多神话,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
很明显,卫聚贤先生在文中着重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古代文献《山海经》《尚书》《左传》《蜀王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中记载有相当数量的巴蜀神话,且构成巴蜀古史的基本轮廓。然而他接着说到的“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却让人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觉得卫聚贤先生的论述有些自相抵牾——似乎是说古代的巴蜀神话不属于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卫聚贤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巴蜀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而是特指“巴蜀考古文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卫聚贤先生通过对汶川石纽、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广汉太平场、成都忠烈祠街古董商店、成都白马寺等地的出土文物及文化遗址等地的考察后发出“故知其蜀人文化之古,而不知其蜀人文化之异”的慨叹。这种慨叹背后,就隐约包含了“古蜀文化”或“古蜀神话”的概念。
卫聚贤先生之后,“巴蜀文化”成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其他文化学界广泛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运用,其范围大大超出了考古学本身。
特别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巴蜀文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概念被应用到巴蜀考古与巴蜀古代史的研究当中,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年)、商承祚《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辨》(1942年)、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1942年)及《古巴国辨》(1943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1946年)等等。正如台湾学者许秀美在《巴蜀神话研究》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些探讨中,提出了‘巴蜀独立发展说’与‘巴蜀文化’一词之诠释”,并重点探讨了“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巴蜀古史的可靠性、巴蜀遗物的辨认与断代”等四个问题。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大量运用卫聚贤先生提到的“不详细且多神话”的古史文献如《山海经》《尚书》《左传》《蜀王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水经注》等等,将巴蜀神话纳入巴蜀文化的范畴加以考察和论说,只不过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巴蜀神话”的概念。

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特别是四川本土学者沿袭了“巴蜀文化”的概念,通过众多神话色彩浓郁的巴蜀文献资料来研究巴蜀出土文物和巴蜀古代史,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其代表者有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1955年)、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和《巴蜀文化续论》(1960年)及《论巴蜀文化》(1981年)、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1959年)和《略伦〈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1962年)及《巴蜀古史论述》(1981年)、冯汉骥《关于楚公蒙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1961年)、童恩正《古代的巴蜀》(1979年)、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1981年)、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1983年)、董其祥《巴史新探》(1983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984年)、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1986年)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87年)、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1989年)等。这些研究,将巴蜀神话融入巴蜀文化之中,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挖掘其文化价值,提高了其文化内涵。但是,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中并没有将“巴蜀神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加以明确。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国内神话研究的大热,“巴蜀神话”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研究概念被提出,一批研究成果也先后出现。
1993年,巴蜀书社组织相关作者准备编辑出版一套《巴蜀文化系列丛书》,深耕中国神话多年的袁珂先生申报了一部20万字左右的专著,书名就叫《巴蜀神话》。这本著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出版,但是袁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前言以《简论巴蜀神话》为题发表在《中华文华论坛》1996年第3期(文章署名为袁珂、岳珍)上。差不多同时,贾雯鹤在《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巴蜀神话始源初探》一文,李诚也于该年在电子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巴蜀神话传说刍论》一书。“巴蜀神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正式登场。
那么,什么是“巴蜀神话”呢?
对此,袁珂先生在《简论巴蜀神话》一文中有这样的解释,他说:
巴蜀神话范围的界定,以历史地理的划分和广义神话的含义为前提。……中国幅员广阔,神话丰富,各个地域都产生有自己的神话。除了中原神话和巴蜀神话外,应该还有荆楚神话、吴越神话、闽粤神话、东北神话、西北神话等等。在神话的研究中,地域神话的研究显得特别薄弱。这是一个有待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领域。巴蜀神话起源早,内容丰富,在所有的地域神话中,巴蜀神话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也是唯一可以和中原神话比肩并论的地域神话。巴蜀神话有自己独立的神话母题,充分显示出巴蜀的地方特色,值得进行专门的探讨研究。
也就是说,所谓“巴蜀神话”,袁先生认为其实就是巴蜀地域神话。它以地域区划为特征,与中原神话、荆楚神话、吴越神话、闽粤神话、东北神话、西北神话等相并列。从内涵上讲,巴蜀神话就是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独立的神话母题,充分显示出巴蜀的地方特色”。
同理,“古蜀神话”同样也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从属于“巴蜀神话”,是“巴蜀神话”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特指古蜀地域的神话。从文化概念上讲,“古蜀神话”也是“古蜀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古蜀文化”。
从目前的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第一次从神话研究的角度系统整理古蜀神话,并将相关文献归入“古蜀神话”类的是袁珂先生。他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中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叫“古蜀编”,搜集编排了从上古蚕丛、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到秦代李冰、二郎等一批神性人物的神话资料,使古蜀神话文献相对集中地展现出来,成为一个系统。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古蜀神话”这个概念,但将相关神话资料归入“古蜀编”本身,就是对“古蜀神话”概念的肯定和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古蜀神话”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不断出现在相关研究论著中,并逐渐成为与“古蜀文化”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之一。
二、古蜀神话的地理范畴
前面我们提到,巴蜀神话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从内容上讲,包含了“巴神话”和“蜀神话”两大块,也就是指在“巴”和“蜀”两大地域上产生和流传的全部神话。关于巴蜀神话的地理范畴,袁珂先生在前述《简论巴蜀神话》一文里有一个简短的论述,他说: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禹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古代巴蜀的地域为九州中的梁州。《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位于现在陕西华阴县南。华阳即华山的南边。黑水是传说中西方的一条河流,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金沙江。不过关于古黑水的说法很多,至今尚无定论。从《禹贡》的记载看起来,古代的巴蜀地区东起华山之南,西至黑水流域,大概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的南部和湖北的部分地区。晋代常璩作《华阳国志》,即以此为古代巴蜀的疆界,这也就是巴蜀神话所依据的地理范围。

《华阳国志·蜀志》疆域示意图(选自刘琳《华阳国志校注》)
但是,关于古代巴蜀的地理范畴,历史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疆域和范围,正如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所说:
巴蜀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它不同的范围:有先秦巴国、蜀国的区域,有秦灭巴蜀后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初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武帝以后巴郡、蜀郡的区域,这些都显然各不相同。更应注意的是与巴蜀同俗的区域,那就更为广阔。
也就是说,依附于巴蜀地域的“巴蜀神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理范畴也是有所不同的。《尚书·禹贡》所说的“梁”是先秦时期一个比较大的地理概念,巴、蜀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巴、蜀的具体疆域和分界究竟在什么地方,由于史料的缺乏或语焉不详,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只有一个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巴”“蜀”的概念,不过其大体位置还是能够明确的,那就是在今天的西南地区。
至战国时,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后,分建了巴郡和蜀郡,其疆域和治地才大致明确下来。
据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巴志》和《蜀志》的记载,巴的疆域是:“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蜀的疆域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这个区域,按蒙文通先生的说法,基本上是秦灭巴蜀时的疆域。它大致应该和先秦时期的巴蜀疆域差不了太多。
由于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古蜀神话问题,故关于巴的地理范围和神话暂且不论,只重点探讨一下蜀的地理范围问题。
按照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的说法,蜀的疆域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具体来说,当时蜀的疆域东边与巴接壤,位置大致在今四川射洪、遂宁至重庆合川一带;南边与越接壤,位置大致在今云南、贵州部分及越南北部一带;北边与秦分界,位置大致在今陕西南部汉中一带;西边覆盖了峨、嶓(秦时的武都郡和汶山郡),位置大致在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和陕西西部部分地区。显然,这是秦灭蜀时的地理范畴,并不是古蜀王时代的蜀地范畴。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书影
对古蜀王时期的地理范畴,《华阳国志·蜀志》还有一种说法,其云:
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这里所说的古蜀王杜宇时期的地理范畴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心区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边至四川理县玉垒山,南边至峨眉山城郭;二是外围区域,北边以秦岭山脉的褒斜山谷为前门,南边以青神熊耳山、芦山灵关山为后户,西北方以岷江上游的汶山地区为牧场,西南方以越巂、牂柯(今四川西南部的凉山、雅安等区域和云南、贵州北部)等地为狩猎区域,再加上岷江、嘉陵江、绵远河、雒水流域的大片区域,就构成古蜀王杜宇治下的地理范畴。童恩正先生说:“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虽是夸大之辞,但仍可以看出古蜀国的大致疆界。按褒斜在今陕西汉中,熊耳山在今青神县,这也可能就是当时蜀国直接统治区域的南北界。在西南,可能到达了今芦山、天全一带;在东面,则大致以涪江作为与巴的分界线。至于其间接统治或影响所及的地区,很可能包括了今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全部,以及云南北部。杜宇移治的郫邑,即今郫县,故瞿上城则在双流县南十八里。”
很明显,这一区域要比战国司马错灭蜀时的蜀地区域要小一些,应该就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地理范畴,主要就是现在所说的川西地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古蜀神话,也就应该在这个地理范畴之内。这个地理范畴相对狭小的古蜀神话,我们姑且称之为狭义的古蜀神话。

司马错败蜀王入关(剑门关关楼浮雕)
那么,广义的古蜀神话的地理边界又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广义的古蜀神话的地理边界是与历史上蜀地地理边界的确立相适应的。
司马错伐蜀以后,分建巴郡、蜀郡,蜀的地理范畴如上所述,应该是比较清晰的。汉初,这一地域略有调整,汉高祖分巴、蜀之地另置广汉郡、犍为郡。至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个刺史部,置益州部,内含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巂郡、牂柯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益州郡等郡,下辖146县,其地理范围包括今四川、重庆全境及贵州、云南部分以及陕西汉中盆地。这时,“益州”成为“蜀”的代名词,“巴”亦被涵盖其中。
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最后魏、蜀、吴三分天下,蜀汉占有整个西南地区。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文化的影响力非常深远的一个时期。随着魏、蜀、吴的分立,进一步强化了“蜀”在地域文化上的地位,而“巴”的文化地位进一步弱化,并逐渐融入到“蜀”的文化概念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废除了秦汉以降的州、郡制,将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益州(大致为今天的成都平原)改为剑南道,而将原来的梁州(大致为今天陕西的汉中盆地)改为山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剑南道又分为剑南西川节度和剑南东川节度,“川”字开始在四川地区区划名称中出现。
宋时,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开始对州县大加减并,宋军灭掉后蜀政权后设置西川路,原属巴蜀的地域开始大幅缩减。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分设峡西路;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为川峡路;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又将川峡路拆分为四路,即益州路(后改成都府路,治地成都)、梓州路(治地三台)、利州路(治地广元)、夔州路(治地奉节),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四川”之名开始出现。
到了元代,元世祖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将川峡四路合并成四川行中书省,四川省名得以确立,并沿袭到现在,简称为“蜀”,其中就包含了先秦“巴”的相当部分地域。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出秦汉以后巴蜀地域范围的变迁情况,其目的是想说明广义的“古蜀神话”的地理范畴不仅包括古蜀王杜宇时期古蜀国的地理范畴,还包括秦汉以后的益州、梁州、剑南道、川峡四路、四川行中书省的地理范畴。这一范畴,大于现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地理范围,还包括了今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的部分地域,是广义的“蜀”的地理范畴。
另一方面,从字面上理解,“古蜀神话”亦可解释为“古代蜀地的神话”。按这种理解,凡是清代以前在蜀地产生流传的神话,都可称其为“古蜀神话”。这无疑就属于广义神话的范畴了。
三、古蜀神话的民族范畴
明确了古蜀神话的地理范畴,再来谈谈产生和传承古蜀神话的人的问题。
先秦时期,在古蜀地域上生活的大小民族众多,其名称和族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此,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从历史文献上看,正如徐中舒先生指出的那样,由于“战国以前,除《尚书·牧誓》外,就没有有关蜀的记载”,因此,要探讨古蜀地区的民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不过仅就《尚书·牧誓》而言,从武王伐纣的八个氏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来看,历代注家多认为它们位于西南,如汉孔安国传就说:“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唐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云‘羌在西蜀叟’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传据蜀而说。西晋左思《蜀都赋》云:‘三蜀之豪,时来时往。’是蜀都分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别名,故《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东偏,汉之巴郡所治江州县也。”可见,从武王伐纣的西南八个氏族中,蜀、羌、髳、微都是生活在先秦巴蜀地理范围之内的氏族部落。
除此之外,先秦巴蜀境内还有若干土著小氏族与巴人、蜀人共同存在,其主要者,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也就是“滇、獠、賨、僰、僮仆”等,计有“六百之富”。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这四五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小诸侯,就是所谓“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巴蜀的疆域也只能说是所联盟的疆域,主要的还是要从和巴蜀同俗的文化区来看。蜀自然是个文化的中心,所以蜀就显得更为重要。
很明显,“这四五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小诸侯”,就包括古代巴蜀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首领。
至于蜀人,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来源与周秦人同宗,是古氐羌人沿岷江河谷南下的一支,与周秦人乃至中原人(即华夏人)有着较为紧密的血缘联系。
历史文献中关于蜀地、蜀人的记载有很多,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照从前人的见解,巴蜀和中原的不可分割性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如此的,直到秦灭巴蜀时止,其关系不曾间断过。”由此,顾颉刚先生系统地梳理了有关人皇、钜灵氏、蜀山氏、伏羲和女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禹,乃至商周、春秋人物和史实的一些文献记载,并概括道:
综合上面的记载,可知古代的巴蜀和中原的王朝其关系何等密切。人皇、钜灵和黄帝都曾统治过这一州。伏羲、女娲和神农都生在那边,他们的子孙也建国在那边。青阳和昌意都长期住在四川,昌意的妻还是从蜀山氏娶的。少昊和帝喾早年都住在荣县。颛顼是蜀山氏之女生在雅砻江上的。禹是生在汶川的石纽,娶于重庆的涂山,而又平治了梁州的全部。黄帝、颛顼、帝喾和周武王也都曾把他们的子孙或族人封到巴蜀。夏桀、殷武丁、周武王以及吴王阖庐又都曾出兵征伐过巴蜀。武王还用了梁州九国的军队打下了商王的天下。春秋时楚国主盟的一个最大的盟会是在蜀地举行。游宦者有老彭、苌弘,游学者有商瞿,都是一代的名流。
尽管从整体上讲,顾颉刚先生并不认同这些文献记载,认为“古代巴蜀史实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川西地区大量的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包括营盘山、宝墩遗址以及三星堆、金沙等地的发掘成果,已充分证明了古蜀王国的存在和繁荣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某些实质性的联系。
现代巴蜀史的研究提出将古蜀人的族属和来源进行分层,即分为底层和移民层。底层是土著古蜀人,移民层是中上古时期(包括开明王朝以前及秦汉时期)移民至蜀地的新蜀人,如汪启明、于潇怡在《中上古蜀人的来源、结构与层次》中所说:
中上古时期的蜀人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多元混生系统。这个系统从地理分布上看,在某些时段,其核心地域应该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周边少数民族为辅,大杂居,小聚居。从结构和层次上看,蜀地原生民是古蜀人的底层和核心,秦汉时期的外来迁民是中上古蜀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来自于关中、荆楚两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和民族融合是中上古蜀人的上层。
实际上,古蜀地区除了蜀人和前面提到的“滇、獠、賨、僰、僮、仆”等主要氏族部落外,还有邛、笮、冉、駹等氏族部落的存在。对此情况,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曾有一段较为中肯的论述,他说:
蜀境民族实不止此。如《华阳国志·蜀志》又言:(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棘”。按青衣为一支羌人的名称,分布在今雅安地区青衣江的上游,故至今这条江又称羌江。直至秦汉,在青衣羌地设置郡县,这支羌人遂逐渐与汉族相融合。根据秦汉时川西民族分布的情况上溯,先秦蜀国境内还应包括邛、笮、冉、駹这些民族在内。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邛属濮越系民族,而笮、冉、駹均属氐羌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实为精辟的概述。所谓夷指的是氐羌系民族,而越则指濮越系民族。其实,何止南中,整个巴、蜀,乃至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构成基本超不过这两大支系。时至今日,除苗瑶语系外,中国南方仍以壮侗语系及藏缅语系的民族为主。
李绍明先生这里重点说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构成的两大支系,也包括了西南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演变。
以上我们简单地回顾了一下历史学和民族学界关于蜀人族属和来源的一些主要观点,其目的是想说明,无论是狭义的古蜀神话还是广义的古蜀神话,其民族范畴都应该包括两大块:一是以土著古蜀人加上历代移民形成的新蜀人为核心的汉民族(华夏人)的神话;二是以庸、羌、髳、微、卢、彭、濮、滇、獠、賨、僰、僮、仆、邛、笮、冉、駹等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少数民族神话。尽管这些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有相当部分被汉民族(华夏人)同化而不复存在,但一些现存的经过演变的少数民族仍然长期生活在巴蜀大地上,如“藏羌彝走廊”上生活的藏族、羌族、彝族,以及一些人数相对较少民族如苗族、纳西族、傈僳族、土家族等等。他们当中流传的神话,也属于古蜀神话和古蜀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中也应该受到与汉族神话同等的重视。

藏羌彝走廊范围图(选自“新型城镇研究”公众号)
[1][2]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
[3]参见许秀美:《巴蜀神话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4]参见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5][8][15]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第6—10页,第32—33页。
[6][7][9][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第113页,第118页,第113页。
[10]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1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2](汉)孔安国传,(唐)陆德明音义:《尚书》卷六,四部丛刊本。
[1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十一,续四部丛刊本。
[16][17][18]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载《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第42页,第91页。
[19]汪启明、于潇怡:《中上古蜀人的来源、结构与层次》,《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0]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和族属问题》,载《巴蜀民族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